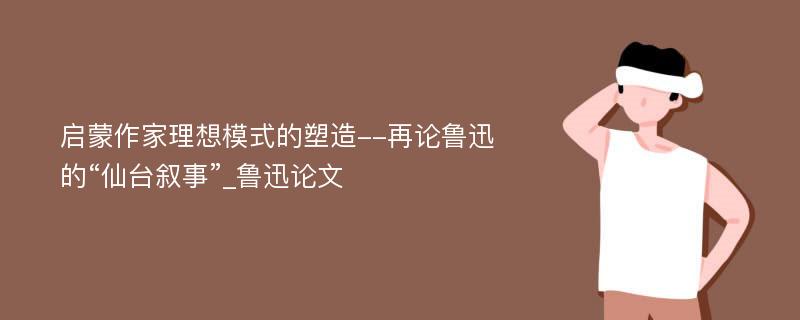
塑造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鲁迅“仙台叙述”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仙台论文,鲁迅论文,典型论文,理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1-0058-10
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自叙传略》、《鲁迅自传》①等文字中,曾多次叙及他在仙台留学的诸多体验及对其后来文学道路的影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也把鲁迅这段形成“独立觉醒的意识”的时期,称为鲁迅的第一次“文学自觉”,即“启蒙文学”或“预言文学”的开始②。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有关仙台生活的文字,已经成为某种足以概括鲁迅留日期间情感、思想和心态的“仙台叙述”,并在不同时期得到了研究者持续深入的探讨。然而,在后人对鲁迅仙台生活的调查和研究中,鲁迅仙台叙述的某些细节也屡屡遭到质疑,而论者也往往据此否定鲁迅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要想厘定鲁迅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他在仙台的实际经历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恐怕在于考察仙台叙述所呈现的留学体验,对于鲁迅第一次“文学自觉”具有怎样的意义;由仙台叙述所建构的鲁迅形象与五四前后作为启蒙文学者的鲁迅,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而作为与作家记忆相关的书写方式,仙台叙述又具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询,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无论是作者本人的叙述,还是研究者的描述,对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仙台学医时所发生的“幻灯事件”和关于考试“漏题”的“找茬事件”③,本文的探讨也从这两个事件开始。
1923年,鲁迅在其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回忆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经历,对于其中为人所熟知的“幻灯事件”,鲁迅写道: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④
这里的“画片”即是幻灯片,是当时日本方面关于日俄战争的宣传品。在已经调查整理的鲁迅在仙台的资料中,找到了十五张当时上课所用的幻灯片,但并没有发现鲁迅所描述的关于“示众”场面的那张⑤。因而,目前学界关于“幻灯事件”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鲁迅的确看了幻灯片,而那张幻灯片没有找到;二是鲁迅对事实进行了艺术加工,将从报纸或者杂志上看到的图片说成是教室里看的幻灯片⑥;三是那张幻灯片根本不存在,所谓“幻灯事件”也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类似于佛陀“顿悟”的神话或传说⑦。
分开来看,最后一种结论整体上否定了鲁迅所叙事件的真实性,其偏执是明显的;而前两种结论在对留学生周树人当时接触的人物及其生活环境做了大量的采访调查之后,从还原历史事实的一面,也对鲁迅的叙述提出了质疑。事实上,这三种结论,无论是从文学虚构的角度否认事实的存在,或是从历史传记的角度质疑鲁迅的叙述,它们终究无法取代鲁迅自身对以往生活经验的表述。换言之,对于文学者鲁迅而言,即使他的叙述中有与当年经历不一致的地方,但至少“诱发”其思想转变的类似事件也存在过。由此,笔者认为,对于鲁迅的仙台叙述,值得我们探讨的恐怕不仅仅是对其进行“纪实”或者“虚构”的定性,而是进一步探讨历史事实与文学叙述之间的缝隙及其产生的缘由,以及鲁迅在此一叙述过程中存在的动机与心态。
于此,有必要一并考察鲁迅仙台叙述中经常提到的“找茬事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提到,作为留学生的周树人,受到解剖学老师藤野先生修改课堂笔记的照顾。但当他在这门要求严格的课程得了一个中等的成绩后,却有同班的日本学生怀疑是授课教师有意漏题,因而他们给周树人写了一封责令其忏悔的长信。就此,鲁迅写道: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⑧
正如“幻灯事件”一样,鲁迅对于“找茬事件”的叙述也遭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质疑。他们根据对当年鲁迅的几位日本同学的采访,对于鲁迅所叙述的细节提出了一些修正性的疑问⑨。然而,细节上的些许差异,并不能改变鲁迅有可能在“找茬事件”中形成的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以及多年后在写作中对于这种屈辱感的回忆,并且伴随着以此昭示当下读者的目的。进一步考察鲁迅对于这种屈辱感的表述方式,将有助于理解此类事件对于鲁迅的深刻影响。
在上述《藤野先生》的引文中,鲁迅在讲完“找茬事件”后,并没有另起一段,而是紧接着马上讲述他在《〈呐喊〉自序》中叙述过的“幻灯事件”。可以看出,从“找茬事件”转入“幻灯事件”,鲁迅的行文是颇为急迫的。这种急迫性,似乎显示了二者之间颇为紧密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种可能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藤野先生》比《〈呐喊〉自序》晚了三年多发表,在这并不算短的时间里,鲁迅写过的文章何止百计,但当他写到仙台经历时,何以在“找茬事件”之后重复一次三年多前所讲过的“幻灯事件”?而且两件事的前后相接显得如此紧密?而在这种前后相连的事件的叙述后面,鲁迅带有总结性的话语是:“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这很难不让人认为,其弃医从文的转变因素,并不仅仅是他三年多前在《〈呐喊〉自序》中所叙述的“幻灯事件”的刺激,而是有着新的刺激因素。这种新的刺激因素,或许正是“找茬事件”所显示的。鲁迅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表明,他透过“找茬事件”找出的关于中国学生在异国求学却遭人怀疑的原因,正在于“中国是弱国”。如果说,在“幻灯事件”的叙述中,鲁迅所展示的是他对于精神与肉体何者更为重要的一次顿悟,那么,三年多后所追加的“找茬事件”,则呈现了鲁迅对于弃医从文之动力的另一种解释。而二者作为刺激的共同之处,则是鲁迅在遭人“质疑”与观看同胞被杀戮的画面而不得不“随喜”之时,所透露出来的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及民族危机感。
那么,这种屈辱感或者民族危机感,如何成为鲁迅后来仙台叙述中的核心要素?其依据何在?在关于作家经验与艺术创作的问题上,杜威指出:“使一个经验变得完满和整一的审美性质是情感性的,正是情感在事件朝向一个所想要的,或不喜欢的问题的运动中将经验的多种多样的部分统一为整体,在此过程中,情感赋予自我一种肯定性。”⑩由此,或许可以认为,鲁迅在仙台经历的事件,并不一定如他所叙述的那么切实,但他确实由类似于“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的日常经历中,体会到一种弱国子民的屈辱感,最终整合成一种关于肉体发达而国力羸弱的具有强烈对比意义的民族危机感。也就是主要由于这种情感,让鲁迅得以在回忆中将仙台的诸多经历最终转换成一种带有审美性质的“仙台经验”,成为他后来用以解释弃医从文等人生选择的心理依据。
鲁迅在仙台留学期间,不少医学老师对其功课有过帮助,其中有与藤野先生共同上过“解剖学”的敷波重次郎教授,他担任的课比藤野的多,而且笔记上也有不少他修改的痕迹(11)。然而最终是藤野先生而不是敷波教授成为鲁迅多年后追忆的对象,其中的原因,自是与藤野先生当年对留学生周树人“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有关,也与后来鲁迅回忆以往生活时的思想情感及其叙述动机有关。
在《藤野先生》一文的末尾,鲁迅写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12)
鲁迅在这里说,由藤野先生删改过的解剖学笔记丢失了。可是后来人们还是在绍兴发现的鲁迅家藏的三箱书中找到了这些笔记,其复印件现在就陈列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基于对鲁迅解剖学笔记的考察,研究者认为鲁迅所叙删改笔记的环节,确实有艺术加工的成分(13)。自然,这种写作中的艺术加工,并不能妨碍留学生周树人对于藤野先生的感激成为其日后所叙的内心真实,乃至成为文学者鲁迅与“正人君子”斗争的思想动力,这也是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然而,研究者们很少考虑的一点是,在什么样的思想立场上,或是在怎样的情感逻辑中,身在异域的藤野先生会成为归国后的鲁迅与社会抗争的动力?按照《藤野先生》一文所述,藤野先生给予鲁迅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严谨的科学精神及其慈祥谦虚、循循善诱的态度,二是其对于留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关爱。然而,对于第一点,后人在研究鲁迅的解剖学笔记时发现,藤野先生在上面做了许多看来确属过分的批改;与此同时,藤野先生的热心反而致使留学生周树人被怀疑为靠了漏题而考得好成绩,使他实际上感到一种负担。这些方面使得研究者们认为,藤野先生当时给予周树人的回忆并非十分愉快,只是经过近二十年后,饱经风霜的鲁迅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并不愉快的场景转化为甜蜜的回忆浮现在眼前,以至于总把恩师的照片放在身边(14)。
那么,最有可能感动鲁迅并一直让他长久不能忘怀的,恐怕是第二点。然而,尚有必要追问的是,藤野先生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关爱,如何与后来鲁迅对于“正人君子”的斗争达成“影响”方面的逻辑一致性?对于这一点,《藤野先生》一文并没有提供足以解释这种一致性的叙述。退一步说,单就情感而论,藤野先生对于鲁迅的激励行为,也并不一定需要达成关于“影响”方面的逻辑一致性,因为情感的东西往往很难用清晰的逻辑来阐明。但如果真是这样,与“幻灯事件”对于弃医从文的觉悟相比,鲁迅如此描述的作为其后来斗争之激励要素的藤野先生的精神面貌,仍然不具备足够的明晰性与直接的说服力。这就可能触及写作时的鲁迅基于“励志”的需要,在处理以往的实际经历与后来的自我体验之间的叙述策略。换言之,《藤野先生》中对后来的鲁迅构成“影响”的精神面貌的模糊性或者逻辑上勉强的一面,恰恰可以说明写作《藤野先生》之时的鲁迅在重构自身经验之时的心态:或许对于他而言,叙述之中所必需的精密的逻辑关系,乃至藤野先生当年的过于热心所导致令当年的自己不愉快的一面(15),与他此时对于以往经验所附加的情感及其为赋予激励机制合法性的迫切之情相比,显得是次要的乃至微不足道的要素。而这,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鲁迅在写作中重构经验时的复杂心态。
因而,对于1920年代的文学者鲁迅而言,“幻灯事件”与“找茬事件”的真切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信自己的人生选择就在仙台的那段时期内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这转变的原因正是他在那里所感受到的屈辱感和民族危机感,并且成为他日后回溯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所愿意承认的一种无需证明的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研究者而言,“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提到的金心异(钱玄同)劝其写作的事件一样,都作为鲁迅道路的转折点,其实不一定要把它们看作传记中的真事,而应该从文学创作或者作者思想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件。当然,鲁迅仙台叙述的文学事实与留学生周树人当年的生活真实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仍然是重要的,经由其中或隐或显的差异,我们可以试图探寻鲁迅在写作中追忆过去经验时的独特感受及其叙述动机。
在此,有必要再来考察鲁迅的仙台叙述中另一个为研究者所质疑的细节。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而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又写道:“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这两处行文,鲁迅都意在表明,在其叙述的仙台生活中,除了幻灯片中看到的以外,就只有他自己这个中国人。然而,鲁迅关于仙台“没有中国的学生”的叙述,在后人的调查考证中却表明与事实不合。至少,与鲁迅当年差不多同时到达仙台的,就有另一位从东京转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施霖(16),他到此学习的是工兵火药专业。1904年9月13日仙台《东北新闻》第7版一则《清国学生》的消息,报导了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与施霖来仙台的情况,并说他们暂住在片平丁五十四番地的田中宅旅店(17)。此外,周树人与施霖还极有可能一同在官川信哉先生经营的公寓中住宿过一段时间;两人于1905年9月合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的每个人后来都被手工画上胡子,称为“胡须照片”(18)。如此看来,周树人与施霖之间恐怕不止于点头之交而已。因而,如果从纪实的角度讲,鲁迅在近二十年后所写的回忆文字中,至少有必要将他与施霖的交往补记上一笔的,但他实际上于此丝毫没有涉及。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事隔多年,鲁迅已然忘记了当年所接触的人与事了?这自然是有可能的。然而,与其多年后的叙述中十分确信当时在仙台只有自己这个中国留学生,以及对“幻灯事件”、“找茬事件”诸多细节的深刻记忆对比,至少让人感到鲁迅的文字中,对于以往生活经历的交代,具有选择性叙述的倾向。
时隔多年后,鲁迅在文学中重构他的仙台经验时,其对于“幻灯事件”、“找茬事件”以及藤野先生的详细记述,自是与其遭受的情感体验有关。那么,当他无论出于有意或是无意地忽略与施霖交往的这部分记忆时,其可能的情感体验或者心理动因为何?根据后人调查的材料,中国留学生施霖在仙台除了体操课满分外,其他科目都不及格。据此,有研究者指出,在仙台医专校园里那些对中国人怀有偏见的日本学生的眼中,施霖事实上成了心智愚弱但体格健全的“示众的材料”,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施霖成了鲁迅不愉快的记忆,所以鲁迅要努力地将他遗忘(19)。然而,值得推敲的是,如果真如研究者所说,施霖作为留学生周树人的“创伤性体验”是多年后鲁迅“营造‘仙台神话’”所要避开的记忆,那么,为何他在极力忘记施霖的同时却选择了幻灯片中围观砍头盛事的“庸众”?换言之,鲁迅在回忆其“创伤性体验”时对于“示众材料”的选择,其舍弃个体符号(施霖)而选择集体符号(围观砍头盛事的“庸众”)的心理动因或者情感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在1904年10月8日一封写给同乡蒋抑卮的信中,周树人汇报了到仙台后的相关情景:
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已东渡,此外浙人颇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20)
由这段书简来看,周树人在仙台时的主要心境和思想状态可以概括如下:其一,周树人当时已经在考虑国民素质的优劣、国民地位与国家强弱的问题,而这些思考无疑部分来自于阅读《黑奴吁天录》所得到的启示。其二,周树人选择去仙台,确如后来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东京与仙台》、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等文章所言,有远离“清国留学生”的心理动因(21);但他到了仙台后,还是不时会接触到关于留学生或中国人的信息;近乎矛盾的是,他甚至感慨不能与友人及同乡聚会;而到仙台后的实际心情也是“形不吊影,弥觉无聊”,其心理状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
施霖虽然没有正面出现在周树人写给蒋抑卮的信中,但完全有可能成为周树人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信息的一个方面。然而此时的周树人在书简中仍然将他们可能的交往视为不存在,很可能是他与施霖之间客观上的不熟悉,或者是他与施霖在志业上的不同取向。而客观上的不熟悉与志业上的不同取向也不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书简接下来的内容中,周树人谈及了自己到仙台后的食宿及搬家情况,也谈到了日常所修功课的情况: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以接。组织、解剖二科,名次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
看得出,周树人对于所修课程与自己的作息时间不谐调以及“奔逸至迅,莫暇以接”的状况颇为不满。在书简的接下来部分,对于所学内容,周树人甚至抱怨:“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此种抱怨,透露出其无法安顿的心态显然与所修专业的特点有关,甚至还与他原先感兴趣的学问有关。在这封信的附言部分,周树人除了告诉蒋抑卮新的通信地址外,尤其感慨如下:
前曾译《物理新诠》,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22)
由上面的抱怨连同附言部分的感慨可以看出,此时的周树人对于医学专业中那些“只求记忆,不须思索”的“死学问”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还担心自己长此下去,有“恐如木偶人”的危险。与此同时,他再三引为“恨事”的是未能继续之前已经翻译了四分之一的《物理新诠》这样“皆理论,颇新颖可听”的著作。
这样的对比,其实颇富意味。《藤野先生》中所记周树人在画解剖图时出于美观而将血管移位的细节,部分佐证了周树人当时对于医学这种专门技术科学的选择,并非是他原先志业的主要部分,看起来倒像是违背自己学术兴趣的一时选择。这显然与多年后的鲁迅在《〈呐喊〉自序》等文字中对“弃医从文”的叙述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在文学者鲁迅后来的叙述中,并不显得十分突兀。因为从实际来看,仙台时期的周树人对于“只求记忆,不须思索”的“死学问”的憎恶,对于“进化论”的痴迷和向往,以及对自己可能变成不会思考的“木偶人”的担心,种种念头都表明,与他多年后对仙台的回忆叙述,其中隐含的价值立场不仅显得大同小异,而且堪称一脉相承,这就是关于身体与灵魂、体格与精神的选择。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刚到日本时,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就经常与许寿裳一起探讨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23)在将近二十年后的《〈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4)
在鲁迅后来关于留学经历的诸多文字中,清国留学生给他最深刻的印象,除了《藤野先生》所提到的头发梳得油光可鉴、堆得像富士山,“咚咚学跳舞”之外,还有“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25)等;即使是当时以排满革命闻名的吴稚晖,其演讲的场面也给鲁迅留下了“留学生好象也不外乎嬉皮笑脸”、“无聊的打诨”(26)等印象。所有这些关于清国留学生形象的元素,在鲁迅的主观意识中,其呈现的一方面是打扮、精力、食欲、言谈等身体或与身体相关的穷奢极欲,另一面则是思想的匮乏和精神的无聊。这就是彼时留学日本的鲁迅所要逃避的那些“中国主人翁”。
与周树人同期到达仙台留学的施霖,虽然也是浙江同乡,但其所学的兵工火药专业与当时鲁迅的志业无干,交往可能就不太密切;此外,如以往研究者所言,施霖的体操课满分而其他功课都不及格的状况,也很可能在周树人的意识里留下肉体发达与精神匮乏的印象。因而,文学者鲁迅多年后在突出自己最终选择“改变精神”的自我建构中,于有意无意中,将其归入那些体格健壮而精神匮乏的“愚弱的国民”之中并予以忘却,也不无可能。但此中更为关键者乃是,无论留学当年对于清国留学生群体的有意回避,抑或多年后的回忆文字中对于清国留学生之个体(施霖)的有意(无意)忽略,都显现出鲁迅对于“清国留学生”这一身份的淡漠,及其身份认同上的心理危机。换言之,从这些“逃避”与“忘却”的面向,不难看出鲁迅自留学日本起直到晚年,在将自我排除在他所描述的“清国留学生”群体方面,其情感立场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个人对于群体的有意逃避,往往伴随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在容易获得独立于“庸众”的自我优越感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个人心理上的孤独或者对于孤独的心理需求。然而,根据上面所引写给同乡蒋抑卮的信来看,周树人到达仙台后,思想上要逃避清国留学生们,心理上却无法承受孤独。这种近乎悖论的心境,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东京弘文学院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在《黑奴吁天录》中看到的被压迫民族的命运,以及在仙台遭遇的屈辱感和民族危机感,使得留学生周树人看到,仅仅依靠医学或现代西方科技,并不足以改变弱国子民的命运,相反,只有利用文艺对国民精神进行整体的改造,才可能挽救这个衰颓的民族。而这种改造方案的实施,已经不是埋头于苦学某种现代科学技术所能解决的了,而是必须密切关注现实人生,了解时人舆论和心态,获取足够的信息源,并将之传达给民众,使之发挥相应的刺激效用,由此达到变革民心和改良社会的效果。由此,在后来的文学者鲁迅看来,曾经作为逋逃薮的仙台及其医学课程,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这一思想要求了,离开仙台而回到政治文化的中心东京,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从东京到仙台再到东京,体现的不止是周树人生活空间的转换,更是其思想变化的轨迹——他最终放弃了为逃避创伤性体验而寻求的孤独感,回归自己曾经厌恶并且逃避的清国留学生群体。与此同时,当他以启蒙的理性引导自己并战胜自身情感的时候(27),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已经诞生了。从此,他不再逃避现实世界,而是重新投入他所批判的那些国民之中,通过写作以及相关的文化活动实现对于各方面的接触。此一过程,就如卡尔·雅斯贝斯指出的,是由“疏远世界而进入孤独”到“对于群众和当下的历史性沉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与世界疏离造成一种精神的个性,而沉入则在个体自我中唤醒一切属人的东西。前者要求的是自我修炼,后者是爱。”(28)换言之,此一由“疾世”到“入世”的过程,体现的不仅是鲁迅在理性方面的自我定位,更是其情感上对于“群众”的包容与接纳。
从整体上看,鲁迅的仙台叙述正面凸显了对精神、国民性的思考,书写了对屈辱、感激之情的深切体验,而对于体格、肉身乃至麻木、轻浮的个体和形象,则多所忽略或者抱持批判的态度。此一文学叙述与实际经历之间的差异,在彰显鲁迅的启蒙观念的同时,也蕴含着文学创作中“纪实”与“虚构”的基本命题。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在那些自叙性作品中,作家的自我叙述与其实际经历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棘手的问题。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卢梭为例,关于《忏悔录》中的卢梭与真实的卢梭之差异,几百年来一直争议不断。在这些争论中,德里达的看法最为激进。他以解构主义最为典型的思路,直接质疑通常假定存在于自传文本和作者的真实生活之间的鸿沟,宣称“文本以外别无他物”(29)。然而,他的观点并非否定真实的卢梭及《忏悔录》等的存在,而是隐含着如下意思:诉诸所谓卢梭的真实生活,只不过是在诉诸某个表达的过程,某种语言构成的描写或叙述,而不是诉诸某种可以被准确无误地称为让-雅克的东西。德里达对卢梭《忏悔录》的论述,尽管无法对解读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但他毕竟提醒我们,即便是出自最为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或实际调查,研究者们都不能把根据这些传记资料而产生的描述或者叙述,等同于传主本身或者他的实际生活。
按照卢梭在《孤独漫步者遐思录》第4卷中对道德效用与事实真实以及哲学真实的论述,有学者提出,卢梭其实给出两种解读《忏悔录》的线索:按照一种方式解读,《忏悔录》主要关心的是实践目的和道德目的,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卢梭可能愿意为了作品的效用性(effectiveness)而损害其特殊真实性(particular truthfulness);但用另外一种方式阅读,《忏悔录》则是以某种不同寻常的形式表现一般真实(general truth)。换言之,自传同时与效用和一般真理有关。因而,当卢梭虚构故事时,他并不是在说谎,而是试图像卢梭自己所表述的:“至少用道德真实代替事实真实。换言之,就是(试图)准确表现人类心灵的自然爱好,并且从中取得教益,也就是说把这些虚构视为道德寓言或比喻。”(30)把虚构当作道德寓言来阅读,表明卢梭废除了用事实真实的标准评判作品的需要,从而将一般真实即情感真实摆在了第一位。
无独有偶,对卢梭《忏悔录》称许有加的鲁迅也认为,文学创作中有意的虚构,相比号称真实的日记、书简中的撒谎,往往更让人可信。1927年5月,郁达夫发表了《日记文学》一文,认为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带点自叙传的色彩,若要让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不感到幻灭,则用第一人称写作要比用第三人称写作更有效,“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31)。对此,鲁迅并不赞同。他指出,写作的关键并不在于体裁,无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写作,“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32)。此一论述表明,与卢梭一样,鲁迅也将情感真实(文学真实)放在了评判作品标准的第一位。同时,对于事实真实在进入作品中的局限性,鲁迅深切明了切身情感体验的获得,并非就是说凡作品所写之事都要自己亲历:“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33)换言之,写实作品中描写对象的真实性,不是源于简单的照搬现实,而是作者依据作品表达情感的需要,把各种分散的不相关的众多社会生活现象,通过抽取、缀合,然后写出,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这也就肯定了文学中必不可少的虚构成分。因而,鲁迅说自己的创作“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34)简言之,鲁迅认为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写作需要去“选择”事实,甚至对事实真实加以生发和改造。
虽然鲁迅也曾坚称《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等10篇文字“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35),但与他那篇反省自我人格并且被归为小说的《一件小事》相比,《藤野先生》、《〈呐喊〉自序》、《自叙传略》等文字中描述自我觉醒的文字,至少从细节上来说,也都颇具小说创作的笔法。就实际而言,鲁迅的仙台叙述在整体上描绘了自我经“顿悟”而成为启蒙文学者的理想画面。这些画面不仅本身颇具戏剧色彩,而且充满道德教诲的倾向。对于读者而言,鲁迅这些描述自我思想历程的文字,无论归诸何种文体,都像是一种充满启蒙色彩的道德寓言,它们在呈现启蒙文学者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历程的同时,也蕴含着某种既是劝诱读者也是暗示作者自我的双重道德效用。
鲁迅在诸多文字中所描述的仙台经验,正是他对于当年留学生活的选择性叙述。从文学创造过程来看,“选择”正是“虚构”的一种形式。按照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说法,文学文本是作者以文学形式介入现实世界所采用的一种姿态,但这种介入不是通过对现实世界存在结构的平庸模仿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来实现的;这种改造的手段即是虚构,即对于原始素材进行有选择的加工。“而选择,作为一种虚构化行为,它赋予了文本意向性……它勾勒出了参照系统(即原始素材——引者)的基本轮廓,‘解构’这一系统将其转化为自我呈现的材料。”(36)依此看来,鲁迅仙台叙述中的留学体验与其实际经历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选择”乃至“虚构”叙述的必然结果。当然,在选择的同时,由于自我情感的统一功能,鲁迅也许在不自觉中将一些不同场合出现的原始素材,聚集并融合到所谓的“幻灯事件”、“找茬事件”等等的叙述中,由此建构起一种关于启蒙者觉醒的理想的“仙台经验”,并将其塑造成一生从事文学启蒙运动的动力和支点。
经由“幻灯事件”、“找茬事件”等所组成的仙台叙述,其真实成分到底有多少,对于鲁迅自身而言,恐怕不是最重要的。鲁迅对这些事件的追述,更接近于一种文学性的重构,它将现实中那些也许原本无意识的、无价值的生活片段,凝结、转变为有意义的文学素材。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提到令其思想观念转变的原因在于:“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在这段于仙台经历近二十年之后写下的文字中,鲁迅回溯自己弃医从文的理由,其中也带有追忆迄今为止的生活轨迹和思想变化的意味。但此一状况也表明,鲁迅对于以往生活的说明和评价,自是与他对今后趋向的选择和认同有关。诚如研究者指出的,对于轻肉体重灵魂的极端性和偏激性的表白,实际上隐含着鲁迅的一种强烈探寻自己的思想轨迹并对之进行深刻反省的动机:在对弃医从文过程的回顾中,鲁迅同时又在力图克服自己思想中的踌躇和犹豫(37)。如此,在鲁迅的仙台叙述中,由“幻灯事件”、“找茬事件”等回忆所组成的留学经历对于鲁迅自身的意义,也正如本雅明在论及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时指出的:“一件经历是有限的,无论怎样,它都局限在某个经验的领域;然而回忆中的事件是无限的,因为它不过是开启发生于此前此后的一切的一把钥匙。”(38)
文学表现的对象并非原始的生活事件,而是那些作为作者的回忆、生活经验与思想内涵而呈现的东西。如此,“当回忆、生活经验及其思想内涵把生活、价值和意义的这种关联提高为典型性,当事件由此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载体和象征……在这种文学作品的普遍性的内涵中以生活的意义被表达出来的,不是对现实的一种认识,而是对我们的生存覆盖层的关联的最生动的经验。”(39)鲁迅在仙台叙述中不断地重构乃至虚构他的留学体验,其关键正在于以一种建立在自我回忆、生活经验和思想内涵之上的方式描述自己;重要的是这种描述的方式,而不是所描述对象的真实性。本雅明有言:“对于回忆着的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所经历过的事情,而是如何把回忆编织起来。”(40)鲁迅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也说道:“要照自己心中想说的说,说出的东西才是不死的。”(41)此一论说,让人不得不认为,鲁迅想必深切明了“照自己心中想说的说”的必要性,也同时在其写作中实践着这一理念。而就实际而言,启蒙者鲁迅也切实在诸多“我曾经如此”的仙台叙述中,展现了一个别人未曾与闻的“往昔的自我”,也由此塑造了一个关于启蒙文学者觉醒经验的“理想典型”(42)。
由此,鲁迅仙台叙述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回忆与事实之间的差距,而在于鲁迅以重构的方式阐释“仙台经验”对其成为启蒙文学者的决定性意义——其中的“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与其实际经历在细节上自是有别,这些事件对当时的留学生周树人也不一定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但在多年后鲁迅的回忆文字中,却扮演了决定性的因素。进一步而言,鲁迅文学叙述中的仙台经验,其真正的意义恐怕并非在于说明“往昔”如何,而是在于强调“当下”何以然,这是真正与启蒙文学者鲁迅此时的事业息息相关的所在(43)。当他在经历了东京时期文学运动的挫折,乃至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以抄写、拓印古碑自我麻醉之后,在友人的劝说下再次出来从事文学运动,其精神动力大半正是多年前的那场带有决定意义的转变,而新青年同人的解体和五四的退潮,又使他处于彷徨的境地。就客观而言,此时的鲁迅回顾自己成为启蒙文学者的思想历程,不仅对总结及确认自我身份,起到自我暗示的意义,对于当时的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也以昭示“顿悟”的方式提供了某种“榜样”的作用。
鲁迅的仙台叙述以其对于记忆的独特选择与驾驭,建构了一个连接着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理想自我之诞生的丰碑,也由此塑造了一个启蒙文学者的“理想典型”。一座丰碑可以激发仿效的热情,在文学史上树立一个启蒙者的“理想典型”,无疑具有相似的效果。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读者或者启蒙对象而言,鲁迅通过仙台叙述所描写的情感真实,自然比叙述单纯的事实真实,可以传达更丰富的信息,获得更理想的效果;但对于鲁迅而言,此种建基于个人情感体验的仙台叙述,毋宁说呈现了其所愿意承认的仙台记忆对于自我与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连接关系。反过来说,这种连接关系也正体现了仙台记忆对于清国留学生周树人蜕变为启蒙文学者鲁迅的实质意义——诚如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言:“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来说,只有当记忆凝聚了过去的印痕和未来的计划,只有当记忆允许人们做事时不忘记他们想做什么,允许人们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而又不停止他们所是的,允许人们是他们所是的而又不停止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记忆才真正重要。”(44)
注释:
①《自叙传略》原题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载1925年6月15日《语丝》第31期;后来,作者于1930年5月在《自叙传略》的基础上增补修订为《鲁迅自传》,生前未发表。
②参见[日]伊藤虎丸著,孙猛等译:《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119页。
③这些提法最早见于竹内好1944年出版的《鲁迅》,但竹内好认为鲁迅的第一次“文学自觉”是在北京抄碑帖的时期。参见[日]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7页。
④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8页。以下标明《鲁迅全集》者皆同此版本。
⑤参见江流编译:《鲁迅在仙台》,《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33-469页。
⑥参见[日]吉田富夫著,李冬木译:《周树人的选择——“幻灯事件”前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⑦参见张闳:《走不近的鲁迅》,《橄榄树》2000年第2期。另一位研究者则将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叙述的弃医从文及其与藤野先生交往所体现的日中友好为主体的故事称为“仙台神话”。参见董炳月:《“仙台神话”的背面》,《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
⑧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17页。
⑨比如,关于事件的处理,根据当时班级总代表铃木逸太1974年的回忆,是铃木很快就把漏题的“谣传”告诉了藤野先生,并“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是铃木和同学结束的这件事。在另一场合,铃木也说,因为当时谣传得“很厉害”,所以“什么都没对周君说”,只是去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而这与鲁迅写的“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一同去诘责“干事”不同,因为并没有存在“干事”,而类似于干事的只有作为总代表的铃木而已。参见[日]吉田富夫:《周树人的选择——“幻灯事件”前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⑩参见[美]约翰·杜威著,高建平译:《艺术即经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4-45页。
(11)[日]松田章一著,刘红译:《教过鲁迅的“敷波先生”——散文〈藤野先生〉中未被描写的金泽的医学者》,《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
(12)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18-319页。
(13)[日]竹内实著,程麻译:《中国现代文学评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
(14)如百百幸雄《〈解剖学笔记〉读后感》、岛途健一《鲁迅与仙台——相遇之契机和结局》都持此看法。参见[日]大村泉编著,解泽春译:《鲁迅与仙台:东北大学留学百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53-156页。
(15)有研究者指出,根据对藤野批改鲁迅解剖学笔记的研究,藤野先生对于鲁迅的“过于热心”和过多批评里,未尝没有“大日本主义的心态”。参见[新加坡]王润华:《回到仙台医专,重新解剖一个中国医生的死亡——周树人变成鲁迅,弃医从文的新见解》,《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
(16)施霖,字雨若,浙江仁和人。1902年官费留日,先入弘文学院学习,1903年进入正则学校学习,1904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二年级学习,研学工兵火药。他是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参见《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17)参见《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134页。
(18)参见江流编译:《鲁迅在仙台》,《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460-464页。
(19)以上参见董炳月:《“仙台神话”的背面》,《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
(20)(21)《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9,330页。
(22)参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1-612页;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日本》,聊城: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8年,第31页。
(2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文集》上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2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439页。
(25)鲁迅:《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鲁迅全集》第3卷,第199页。
(26)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78页。
(27)参见[德]伊曼纽尔·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28)[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69、176页。
(29)Derrida,Jacques,Of Grammat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158.
(30)[美]凯利著,黄群等译:《卢梭的榜样人生——作为政治哲学的〈忏悔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6、20页。
(31)郁达夫:《日记文学》,《洪水》第2卷第32期,1927年5月。
(32)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23页。
(33)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27页。
(3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7页。
(35)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36)以上参见[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著,陈定家、汪正龙等译:《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20页。
(37)[日]阿部兼也:《鲁迅仙台时代思想的探索——关于“退化”意识的问题》,吴俊编译:《东洋文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38)[德]本雅明著,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98页。
(39)[德]威廉·狄尔泰著,胡其鼎译:《体验与诗》,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47-148页。
(40)[德]本雅明著,张旭东、王斑译:《启迪:本雅明文选》,第216页。
(41)鲁迅:《关于革命文学》,1927年11月2日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参见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3页。
(42)“理想典型(ideal type)”原为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本文借其字面意义来指称个体经由文字表述等方式所建构的关于价值、观念、身份等等的理想“自我”。
(43)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也曾指出:鲁迅《〈呐喊〉自序》的写作是在仙台时代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十七年之后,所谓幻灯事件是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在鲁迅心中形成的“故事”;应当认为,那与其说是叙述回忆中的那时候(1905年)的自己,不如说是叙述正在回忆的时候(1922年末)的自己。参见[日]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6期。
(44)[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