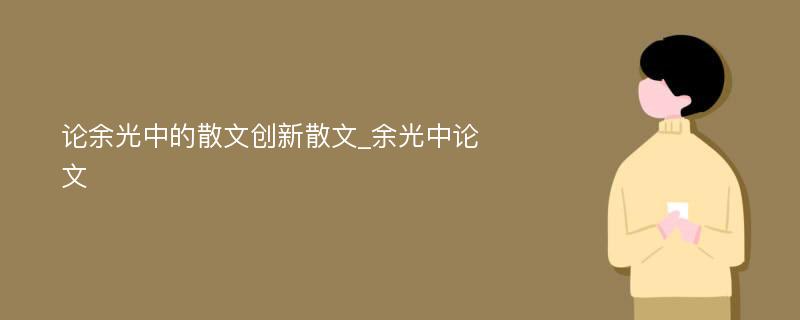
论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余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6271 (2000)1—0079—06
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台湾著名文化人,余光中有三重身份:诗人、散文家、教授。但以大陆的一般情形而言,除极少数专门家即研究工作者之外,许多人心目中的余光中,主要是一位诗人。
但实际上,据我看,余氏的散文创作,无论从风度到气质,从格局到技巧,都不在其诗歌的成就之下。这当然是就其各自在本门类创作大形势之下的实际地位与贡献而言,并非将二者之间作简单的、实际上无可比性的比较而言。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即其诗歌与散文,其实思想情感主旨或曰母题完全一致,那就是人所共知的“故国之思”与“文化乡愁”,并且其实在对这一思想情感主旨或曰母题的表达——演绎和阐释上,也许其散文相对于诗歌,反倒做得更好,但它们所引发的阅读—接受效应,却恰恰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以今日之文化情势与文学现状而论,不是散文相对于诗歌,更广泛、更深入地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吗?
我以为根由之一,就在于他的散文,是更现代、更新派、更先锋的。这在台湾已不足奇,而在大陆,虽然并非这里较为落后,却不能不说毕竟还相当少见——我们诚然也有不少自己的“新潮”散文,却与余氏散文并不完全相同。这一则是因为,文化与文学现象,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实际上是社会与经济生活的“衍生物”,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状况不一样,其所“决定”的文化与文学形态,自然也就会有明显差异;二则是因为,以文化与文学本身的传统而论,台湾与大陆,虽然在总根子上,是孕育和成形于同一土壤,却毕竟又是在不同的两块地方自生自长起来的,其间的各种分别,自也顺理成章。例如“五四”的散文传统,在大陆的影响堪称牢固而深远,但在台湾就不然。而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及其革新,又恰恰是得益于这样两个文化基础,即:(一)台湾的“孤岛”状态及其工业化的现代生存环境;(二)对“五四”以来中国大陆散文传统的隔膜与反叛。而余光中的诗歌就不然:前一个文化基础是与其散文创作无异的,后一个文化基础就不同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余光中的诗歌主张与创作,有一个从现代回归传统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实若仅就“现代性”而论,大陆诗歌已经走得够远,故余氏本就无所谓隔膜与反叛可言。这样,余氏作为散文革新家的形象,就格外地突出而鲜明了。
1
余光中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反叛是相当积极而自觉的,在这方面,其姿态丝毫也不逊色于当初他身为台湾现代诗歌阵营中的“猛将”时的勇毅。而这当然首先是缘于他对上述传统及其所造成的散文创作现状的强烈的不满情绪,此亦即我所说的隔膜。这种隔膜的造成,总的说来,是因为他作为“少小离家”的台湾现代文化人,深感按照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传统路子,根本无法表达一个远离故园并且总在不断漂泊与流浪之中的华夏游子,身处与故国、家园隔离、疏远极剧的现代社会——“异地”中时,自己发自灵魂深处的全部复杂而微妙的思想、情感与精神现实。这些东西,也许在余光中看来,不是身临其境、深受其扰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揣测、猜度与言说的。并且,绝非每一个海外华人及其子弟,都能像他本人那样,感受、体验得极其细腻、深剧和强烈——自然,在他与他们之间,也无疑有诸多的甚至在其根本点上的共同性与一致性,但作为集诗人与学者于一身的余光中,其所“独”具的特殊器质,却应当说,该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否则,何以在台湾人才济济的文坛上,人们都写“乡愁”,并且因此而使所谓“乡愁散文”,几十年来竟成为该地长盛不衰的散文潮,而独独余光中的“乡愁”散文,极其显明地而且是遥遥领先地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文化”味呢?何以他的这些执意并尽情抒写甚至刻写“文化乡愁”的作品中,总是无一遗漏地烙有鲜明的“故国之思”而不是单纯的“家园之忆”的印证乃至于刻痕呢?
余光中作为具有高度“情性——理性——智性”的文化人,我以为,其“文化乡愁”与“故园之思”中所包容的内涵,是博大的、精深的、高远的、广阔的,确非一般人所可比拟。不仅如此,或许是因为深受现代生活之严峻性的刺激,或许是因为在漫长的思念与眷恋中其心灵已饱受煎熬,或许是因为在这样的一颗心灵中还有旁人尚未能萌生和企及的更为雄大的理想,或许也还因为在余氏本人的性格中原本就有极为坚毅、顽强、执着的因子因而其人性、人格质地从来就有些特异之处,其“文化乡愁”与“故国之思”的情感特质,同时还是特别刚性的。坦率地说,我从余光中抒情散文的阅读中,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这些东西。现在我在这里谈论这些东西——余光中抒情散文的首要的文本特质时,它们已然是一种“果实”,但它们作为余光中散文创作积极而自觉追求的成绩,却是从“种子”而经浇灌和培育才得来的。于是回过头去看其当初的散文创作宣言时,就会深深地感觉到并且确信这一切的确并非偶然和绝非无理。余光中对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由隔膜而到反叛,初看似乎不尽合理因而难于接受,但事实上,若在对当代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细加体察、剖析的同时,投以历史的、艺术发展的眼光,则他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其“偏激”之论,是有着鲜明的现代文化立场,并事实上起到了推动中国散文创作进一步走向现代化以适应现代生活与人们精神文化之新的需求的有益作用的。而其成功的抒情散文创作本身,则是这种推动的有效性的明证。
余光中的现代散文创作宣言,是从对“目前中国的散文”的俯视与声讨,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传统的清算与批判开始的。
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他说:“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而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散文,可以分为下列的四型”,即:(一)学者的散文:这一型的散文限于较少的作者,像钱钟书、梁实秋、李敖的散文,均属之。其特点是“融合情感、智慧和学问”,能够“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但“这种散文,功力深厚,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无法作伪”,绝非一般的作者同时也“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达到这样美好的境界”。于是在“学得不到家,往往沦幽默为滑稽,讽刺为骂街,博学为炫耀”的同时,多有“不幸的一类”分别异化为“洋学者的散文和国学者的散文”,均乏味之极,面目可憎;(二)花花公子的散文:这一型的散文“到处都是。翻开任何刊物,我们立刻可以拾到这种华而不实的纸花。这类作者,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学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它们“已经泛滥了整个文坛。除了成为‘抒情散文’的主流之外,它更装饰了许多不很高明的小说和诗”。它们“像一袋包装俗艳的廉价的糖果,一味的死甜”,而“伤感,加上说教,是这些花花公子的致命伤”;(三)浣衣妇的散文:这一型的散文,与“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恰成鲜明对照,其“毛病却在太淡、太素”,“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其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又“都是散文世界的‘清教徒’。她们都是‘白话文学’的善男信女,她们的朴素是教会聚会所式的朴素,喝白话文的白开水,她们都会十分沉醉”,其所奉行的主义,只是“老处女主义”或“赤贫主义”;(四)现代散文:这一型的散文,是尤为“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而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质料,“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底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在这“四型”散文中,对于“学者的散文”,余光中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但无论从其现状还是前途,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因为太难实现;而“现代散文”,余氏明确说是“一种新散文”,因为目下能为之的和尚已出现的并不多,他是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型态来寄予厚望的;余光中此文——这是其进行散文革新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而且是侧重在“扫荡旧习”这一面——的重要深意之所在,是对“目前中国”所触目可见的“二三流”、“四五流”、“七八流”散文进行猛烈的轰击,试图通过对“花花公子的散文”和“浣衣妇的散文”加以清算和批判,并正面提出自己全新的散文主张,来呼吁重造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散文的世界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稍稍梳理一下,可知余光中对于“二三流”、“四五流”、“七八流”散文所进行的轰击,大抵是从两个相对而又相背的方面加以突进的,那就是所谓“太硬”和“太软”。前者包括上文所说的“洋学者的散文和国学者的散文”以及“浣衣妇的散文”,后者则专指他所痛加嘲笑的“花花公子的散文”。它们或则将“含糊等于神秘,噜苏等于强调,枯燥等于严肃”,除了“半生不熟”的“翻译”,便是“不文不白,不痛不痒,同样的夹缠难读”的“鼓吹”,“令人读了,恍若置身白鹿洞中,听朱老夫子训话,产生一种时间的幻觉”;或则“千篇一律”,纷纷“攀在泰戈尔的白髯上,荡秋千、唱童歌、说梦话”,不但“热心劝善,结果挺身出来说教”,而且“用起形容词来,简直挥金如土。事实上,他们的全都是赝品,其值如土”。而其总根子则是完全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进程脱节或剥离,“现代诗,现代音乐,甚至现代小说,大多数的文艺形式和精神都在接受现代化洗礼,作脱胎换骨的蜕变之际”,唯独散文仍不肯改掉它的陋习。
2
由此余光中说:“散文,创造的散文(俗称‘抒情的散文’)似乎仍是相当保守的一个小妹妹,迄今还不肯剪掉她的那根小辫子”。而作为散文革新家,他所赋予自己的文化使命,就是站出来,勇敢地、果断地“剪掉散文的辫子”。然而剪子何在?他高举起“现代散文”的旗帜,打算赋予其什么样的“现代”品格”?
据我的观察,余光中所赖以建构“创造的散文(俗称‘抒情的散文’)”的“现代”品格的手段,大抵主要是三样东西,即:诗性、知性、文化性。有了这三样东西,现代性才水到渠成。
还是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余光中劈头就说:“对于一位大诗人而言,要写散文,仅用左手就够了。许多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写出来的更漂亮。一位诗人对于文字的敏感,当然远胜于散文家。”他把工诗,比喻为“会飞”,而工散文,则不过是“善于走路”而已,显见是认为诗和诗人,是理所当然甚至天经地义地是要高出于、高明于散文和散文家的。于是他甚至还坦白地说:“在实践上,我总有一个偏见,认为写不好(更不论写不通)散文的诗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我总觉得,舞蹈家的步行应该特别悦目,而声乐家的说话应该特别悦耳。”类似的说法和同样的见解,余光中在他的不同文章中,曾反复表述过;他还详举众所公认的实例,来证明“好诗人必定兼工散文,而好作家却往往不能工诗”。这当然不是意在褒诗而贬文,而是企图阐发一个规律,申说一种见解:缺乏诗性,散文是写不好的。
但余光中所说的散文应当包含诗性,我们却并不可以大而化之地作简单的理解。至少有两点,我们在一开始接触这一命题时,就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其一是,他所说的诗性,是侧重于指现代诗歌的某些艺术特性,除他自己所曾反复强调过的“音容并茂”即“文字流畅、音调圆融、比喻生动”,以及在“弹性”、“密度”要求下的“质料”好等因素外,实际上还主要指的是像意象、隐喻、象征这一类现代诗歌创作中的常用技巧,可以说恰恰是与比如说大陆散文家杨朔所谓的“把散文当作诗来写”相去甚远的,如果不说它们截然相悖的话;其二是,他之所以格外强调这种诗性,恰恰又是与他反叛“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抒情形态这一革新的大目标相一致的,例如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指责上述传统及其继承中的“滥情”、“伤情”流弊,包括“伤感,加上说教”和“太浓、太花”、“一味的死甜”等“致命伤”,为此甚至还明确地否定像朱自清这样的散文大师的既有文风,而诸如“若是一味纯情,只求唯美,其结果只怕会美到‘媚而无骨’,终非散文之大道”,若“把散文等同于诗,而且是非常狭窄的一种抒情诗,恐怕也非散文之福”之类的断语,在其文中更是几乎比比皆是。可见余光中的主张散文中应具有诗性,一方面是希望其充满现代感,另一方面则是在要求散文“有骨”的前提下,具备一种刚性,而这与他的既反对“太硬”——所谓“急于载道说教,或是矜博炫学,读来便索然无趣”,又反对“太软”——所谓“一味抒情”和“只解滥感,也令人厌烦”,并不矛盾。因为这种刚性,非生脆冷硬之刚,乃坚韧沉实之刚,所以很现代。
在申说上述意见的同时,作为其散文革新之另一份纲领性文件的《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则更加充分地阐述了关于“现代散文”应当具备“软硬兼施”、“情理兼修”、“文质彬彬”品质的理论主张。此中的“硬”、“理”、“质”,虽其原有的语义内涵并不相同,但在余氏的理论阐说中,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样东西,即他所特别津津乐道的“知性”。在余氏看来,写作现代散文而无知性,那是名不副实并且难以想象的。那么,什么是知性?知性与感性是何关系?
关于知性和感性,余光中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这两个概念的既定内涵,其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关于知性,他说:“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但又说:“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前说近乎“知识性”和“思想性”,后说则与“智性”较为相通。关于感性,他说:“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性经验”,又说:“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广义的感性甚至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声调、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前说大抵是指触及人们生理、心理层面的东西,后说则似乎又侧重在散文对于写景、叙事、状物乃至抒情方面以及与之相关的某些技术处理问题了。故他又说:“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效”,“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所以看上去又像是指抒情的技巧。
但不管余光中关于知性与感性的解说,在逻辑上有多少不严密、在界定上有多少不清晰之处,他的本意,总归是在强调现代散文写作,应当努力做到知性与感性的统一,并且当然,这种统一既应做到圆转、和谐、浑然、自如,又必须以二者不可或缺为前提。为此,他可以说已经在理论上,作了多方面的,最大的努力。
比如在《余光中散文·自序》一文中,他曾把散文的“功能”,分列为六项,即:(一)抒情;(二)说理;(三)表意;(四)叙事;(五)写景;(六)状物。一方面,他说:“实际上,一篇散文往往兼有好几种功能,只是有所偏重而已”;另一方面,他又说:“情、理、意、事、景、物六项之中,前三项抽象而带主观,后三项具体而带客观。如果一位散文家长于处理前三项而拙于后三项,他未免欠缺感性,显得空泛。如果他老在后三项里打转,则他似乎欠缺知性,过分落实。”显见此中所透露出来的对于知性与感性的理解,与前述之见解并不完全同一,而似乎又“知性在我,感性在物”,接近于“悟性”的意思了。
但我以为,余光中虽然同时是一位学者即教授,然而这些见解,我们不妨视之为一位诗人兼散文家的“感性”经验之谈。那么,余光中所谓现代散文尤应给予重视和接纳的“知性”,至少是包含了下述几件东西的,即:(一)知识与见解,亦即学识;(二)智慧与思想,或曰智性与“理性”,但后者是浅层次的(相对于作为哲学概念的那种内涵界定而言),亦即经验式的;(三)心念与感悟,前者即所谓“意”,后者是对生活进行感受、体验并经咀嚼、回味和积累、沉淀,再经提炼、结晶之后的心灵之所得,其中有时也不排斥一定的抽象与升华的过程。故余光中又常常还有一些这样的说法,如:“一位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兼有心肠与头脑,笔下才能兼融感性与知性,才能‘软硬兼施’”;“文章的风格既如人格,则亦当如完整的人格,不以理绝情,亦不以情蔽理,而能维持情理之间的某种平衡,也就是感性与知性的相济”;“许多出色的散文,常见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两者之合,而非两者之分”,等等。他认为纯感性的散文是不可取的。
3
说余光中认为纯感性的散文不可取,并非他觉得纯知性的散文就可取。总的来说,他的基本意见,是认为好散文应当做到知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为此他在以散文的六项功能为据,将散文的文体作出大略区分,亦即抒情文(或小品文,此乃“散文的大宗”)、议论文(或说理文)、表意文(即“表意的散文”,旨在“捕捉情理之间的那份情趣、理趣、意趣,而出现在笔下的,不是鞭辟入里的人情世故,便是匪夷所思的巧念妙想”,所“展示的正是敏锐的观察力和活泼的想象力,也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灵发乎自然的好奇心”),叙事文(即记叙文,其中又有“描写文”)、写景文、状物文(即“状物的文章”)六类,或概而言之、统而言之、大而言之地区分为知性散文(以“学者的散文”为主体)和感性散文(亦即“美文”或“纯感性的散文”)两类时,均特别强调了无论是上述小类和大类中的哪一种散文,在知性和感性的体现上,都不可偏废,即使其在内容、表达、文体上确实“有所偏重”。但作为散文革新家,亦即广义“现代散文”的大力提倡者,他在指斥“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抒情形态的弊病时,的确明显是把重心放在对其感性的泛滥和知性的缺乏的批评上。像这样的表述,在他的理论探讨文章中,是屡见不鲜甚至有点喋喋不休的,如其《缪斯的左右手》一文指出:“好散文往往有一种综合美,不必全是美在抒情,所以抒情、叙事、写景、议论云云,往往是抽刀断水的武断区分”,“许多拼命学诗的抒情散文,一往情深,通篇感性,背后缺乏思想的支持,乃沦为滥情滥感,只成了空洞的伪诗”;其《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指出:“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即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为美文”,“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为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写景、叙事、抒情的散文,也可以得之于议论的字里行间”,“何以知性的议论也会产生美感呢?那是因为条理分明加上节奏流畅,乃能一气呵成,略无滞碍。理智的满足配合生理的快感,乃生协调和谐之美”;其《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对“花花公子的散文”的抨击,更是集中而强烈地体现出了他对于“软性散文”的极度反感:“这类散文,是纸业公会最大的恩人。它帮助消耗纸张的速度是惊人的。千篇一律,它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论作者年纪多大,他会常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小,他会说出有白胡子的格言来。这类散文像一袋包装俗艳的廉价的糖果,一味的死甜。有时袋里也会摸到一粒维他命丸,那总不外是‘记得有一位老哲人说过,人生……’等等的金玉良言。”他还明确地以徐志摩、何其芳、陆蠡等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因有独特而丰沛的诗人气质而“感性散文”写得极好乃至于“最出神最出色”的“散文家中的纯艺术家”为例,指出正因为其文“缺乏知性来提纲挈领”,“每逢说理,便显得不够透彻练达”,或“全然投入一个单纯的情境,务求经营出饱满的美感”,而留下了“缺憾”,其结论是:“仅凭如此的美文,却不能充分满足我们对散文情理兼修,亦即文质彬彬的要求。于是我们便乞援于‘学者的散文’”。相应地,他甚至对“所谓散文诗”这一文类都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而理由呢,只有一条,即它“一味抒情而到滥情的程度”,说它是“最可厌”的文体,“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一个阴阳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两者的美德,但兼具两者的弱点。往往,它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这当然是偏激的,但内在的意图很明显。
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张,意在(一)欲使散文革除传统抒情散文的软性弊病,(二)欲使散文以鲜明的现代品质雄立于当今。这就使得它本身就具备了文化活动的性质。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张中,明确打出“文化性”旗号的言词几乎没有,但统观其相关的理论文字,这一意向却是极为明显的。其具体表现是,第一,在意图救正“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抒情形态及其巨大影响的弊病时,他有一个相当广阔的文化视野。第二,内中还包藏有一个作为上述观念之坚硬内核的文化情结,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却之不能、挥之不去、时时萦念并且执着坚守的酷爱,而其中对于“母语”即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和精粹性这类文化价值的理解与珍视之情,更是显得至为感人,为此他一方面在散文革新主张中和现代散文建构中尤为重视语言文字——文体层面,另一方面还选择另外的角度,写了不少诸如《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作者·学者·译者》之类论文来进行学理的探讨,从而使之成为其散文革新理论主张中的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余光中同时所进行的现代散文创作实践,更是成功地以出色的实绩,支撑、增援了他的散文革新主张,并成为其正确性的有力的佐证,而其中的美质,除现代诗性、知性之外,作为其个性化特征并具有极大启示意义的文本素质,就是文化性——比如同样是写“乡愁”,余光中抒情散文之区别于并高出于在台湾为时既久并业已形成大势的“乡愁散文”潮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所抒写的,是一种“文化乡愁”,即一个文化人的以其强烈的文化情结为底蕴、为灵魂、为经纬的“故国之思”,而非简单的仅以物质和自然时空为基础,仅仅停留在生活现象浅表层次的“家园之忆”,内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精神文化价值,乃至作品从形式——艺术表现层面的全新运作中所透现出来的与前者相一致的“意味”,及其所能够和业已给予现代读者的阅读感受与接受效应,的确均非那些因袭传统抒情方式的“乡愁散文”所可以比拟(对此,笔者将另作专文加以讨论)的。这当然也有力地反映出了余光中重视现代散文写作的“文化性”的意向。
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张,不是一个密针合缝、自成宏大系统的理论实体,但它的内涵是博大的、精深的、高远的、广阔的。这得益于他是一个兼具高度感性与知性的现代文化人,得益于他从自己的现代生活感受与体验出发,立足散文创作的发展本身,但又取了宏阔的、深邃的文化视野,以诗人的热忱和学者的敏锐所进行的思考。他希望现代散文具有一种刚性的质地的想法与实践,我以为是非常睿智的。
[收稿日期]1999—09—27
标签:余光中论文; 散文论文; 乡愁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文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读书论文; 诗歌论文; 抒情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