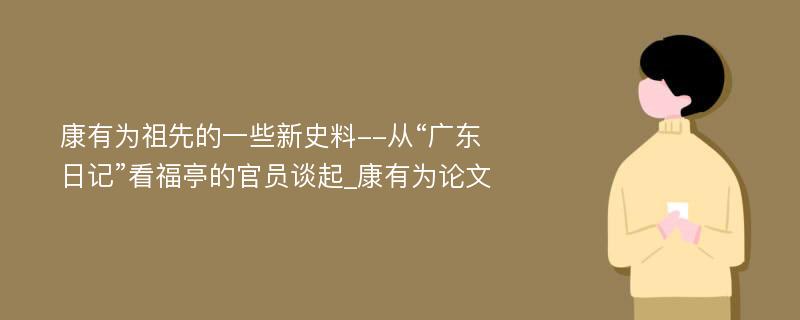
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祖辈论文,史料论文,所见论文,康有为论文,日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2-0092-07
广东人民出版社在2007年影印出版了《清代稿钞本》,其中第10-19册收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日记作者杜凤治(1814-1882或稍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举人出身,同治五年(1866)到光绪六年(1880)历任广东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罗定州知州。他的日记现存40本(缺第2本),收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已故的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周连宽曾撰文介绍①,近几年也有人利用这部日记做了一些研究②。这部几百万字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极有价值的史料。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必须同本县绅耆打交道,所以,日记中多次提到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和从叔祖康国器。这些记载对了解康有为的祖辈以及家族情况有一定帮助。
一、日记关于康赞修的记载
除康有为自己的各种记述外,笔者只在宣统《南海县志》看到过一篇539字的康赞修传记。如果康赞修不是康有为的祖父,相信今天不会有学者关注他。康有为父亲早逝,从10岁起即依祖父康赞修生活,祖父“是对少年康有为影响最大的人物”③。在康有为的著作中,所有写到“连州公”(康赞修殉难于连州训导任上)之处都反映出他对祖父的怀念与崇敬。
杜凤治在任南海知县之前已在日记提到康赞修。同治九年(1870)十月他再任广宁县知县,向典史张某询问县内当押店有多少,张回答:“城内两处,乡间石狗一、江谷一,城中向送到任及节寿礼,乡押减半,如今并且不送,索亦无有,有石狗押,康姓所开,恃粤西方伯康国器大人是伊伯叔,江谷押系本地绅士曾姓有分开设,亦恃族大不顺。”杜说:“何不往索?虽有限,亦系照例之事。伊藐视长官,此其一端,不可长也。康姓石狗初开时,予尚未卸事,康赞修连州学官,为康方伯之兄,丙午举人,与韩老师同年,初开时有五十金官礼亦未送,虽伊有恃不恐。亦韩老师之鬼也。”④ 押店开设时由康赞修出面,康国器其时正在广西布政使任上,加上县学教谕韩廷杰是康赞修同年,韩从旁帮忙,杜凤治对其不“照例”送“官礼”虽不满亦无可奈何。康家的押店既然连知县的“官礼”都敢于不送,对更小的芝麻官典史就更不理会了。
这则资料可帮助我们了解康家的经济状况。康赞修任训导(县学的副职),廉俸收入极为微薄,而当押店是“高利润”行业,但需一定势力才能顺利开设,显然,当押店的收入是康赞修维持一个大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开设当押店时康赞修曾亲自到广宁,平日则由康赞修的一个儿子经营。其时康有为父康达初已病故(此前几年也在家养病),二叔康达迁在外当官,三叔康达守有通判职衔,“不仕而营实业”⑤,在广宁当押店的应该是康达守。
康赞修曾出任羊城书院监院,康有为自编年谱把此事系于同治十二年(1873)⑥,但杜凤治日记反映事在同治十一年(1872)。是年八月十七日,原监院许仲言突然病故,尚欠生童膏火银300两,有人愿意代还一半接任此职。次日,广州知府冯端本告诉杜凤治,他曾与布政使邓廷楠讨论继任人选,“康佑之藩台之兄康述之名赞修,丙午举人、连州训导,现在戴、林营中随同办乡,伊欲得此,藩宪似已允之矣”。当日,康赞修便求见杜凤治,两人谈了一阵关于清乡办匪的事之后,杜对康说:“闻羊城书院许仲言已作(古),藩台言及君,君愿之乎?”康回答:“甚愿!尚求栽培。”三天后,布政使对杜说“已下札委康矣”。⑦
书院监院是山长的副手,掌管书院膏火银发放等事务,是一个既体面又有一定收入的差事,所以愿意担任者不少。许仲言一病故,当天就有人表示愿意接任并代为填补部分亏空。康赞修也立即多方活动,最终如愿接任。同治五年(1866)康国器升任福建按察使,其时邓任福建布政使,两人曾有同僚之谊。从邓的话,可知广东大吏委任康赞修也有看康国器面子的因素。
康赞修作为地方绅士,对清剿盗匪非常积极。康有为自编年谱同治九年(1870)记:“……广东布政使王公凯泰闻先祖行望,檄调还广州办积匪。”⑧ 康有为写的康赞修行状则将此事系于同治十年⑨。行状所记时间肯定有误,因为王凯泰同治九年七月即由粤藩调任闽抚,到光绪元年(1875)死于闽抚任上,不可能在同治十年仍过问广东的事务。同治九年之说也有些不合情理之处:办匪并非重大军事行动,也非布政使的专责,康赞修是学官,当日又不是非常时期,为何要“檄调”他回省城?从杜凤治的日记看,康赞修是以地方绅士的身份自告奋勇参与清乡的。
同治十一年(1872)初,两广总督瑞麟命副将戴朝佐会同委员林直(子隅、子御)、吴廷杰(荆南)等办理南海清乡,康赞修也同去,戴朝佐说:“(清乡)不可无本地绅士,以其深悉其人,熟识各乡绅士也。”几天后,杜凤治在谒见瑞麟时“又将康述之同往一层禀之”,瑞麟对此大加赞扬,称康赞修“其人正直无私,为绅士中不可多得之人”⑩。从杜凤治描写的对话情景,康赞修似非总督或其他省级高官所委派。康赞修临行时杜凤治与其约定“有事彼此亲笔通信”,康在参与清乡时便与杜凤治有函件往还(11),但日记没有抄录函件内容。
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知府冯端本告诉杜凤治:“康述之赞修来言,戴(朝佐)前次在沙头、大桐一带与绅士意见不同,此次到彼恐亦难得手。”杜即到羊城书院拜访康赞修,康告诉杜刚从连州回来,因为他是实缺连州训导,前两个月在连州有考试事务。杜凤治记录与康赞修的对话:“予劝述之定要回家,何不到营帮同办事,康唯唯。予又言即或一时不能去,有所见务速作信告之,康谓然。康又问方亚芬如何,予言自足下言后不三月伊认供,去冬即办讫矣。述之笑言此真好事也,即廖亚根亦杀有余辜者也。”(12)
在清朝,学官不同于其他地方官,不必随时在官署坐班,只须在有考试事务时到场即可。杜凤治的同年开建县训导吴乃煌,出任佛山团防局局绅,系“禀明带印留局办事”(13)。康赞修羊城书院的监院职务以及参与清乡事务,也是“禀明”上司后继续保留连州训导职务的兼差。
在晚清的广东,督抚授权清乡官员抓获疑犯后可以“讯明即就地正法”,对未能取得确供者则押回省城继续审讯。疑犯是否定为盗匪,主要根据士绅的“攻”(指证其为盗匪)、“保”(担保其为良民)来确定。官员往往视清乡为例行公事,虽然也草菅人命,但有时因为证据不足,出于因果报应的考虑,也不愿意过于轻率地处决疑犯。但乡居士绅是盗匪的直接“受害者”,所以通常更主张严办,康赞修便是绅士这种意见的代表者。杜凤治的日记反映出,康赞修对戴朝佐等人办匪“宽大”不满,甚至表示不再参与清乡,杜凤治则极力劝他继续留营协助戴朝佐等人。上面提到的方亚芬、廖亚根都是清乡时拘捕的疑犯,官绅对他们是否确为“积匪”有争议,故未“就地正法”,但因为康赞修坚持“指攻”,他们终被处决。
研究者都知道,康赞修最后是在连州训导任上遇难的。关于康赞修遇难的情形,各种资料的记载有出入。
方志记康赞修遇难经过为:“光绪三年回连州送考,猝遭大水,城不没者三板,雇舟避之,水退后泊河干,舟为坏墙所压,奔避不及,溺于水。其子达迁因水退,先回学署扫除,闻耗奔救起,气已绝矣。时年七十有一……督抚两院宪入奏请恤,加教谕衔,荫一子入监读书。”(14)
朝廷的谕旨也提到康赞修遇难的事:“辛卯,谕内阁:御史邓华熙奏:广东省北被水大概情形,请旨饬查妥筹赈抚各折片。据称广东北江,长堤绵亘,为清远等县屏障。闻本年四五月间,雨水过多,江河泛滥,石角围堤决口百数十丈,此外河堤复溃塌十余处。又闻连州于五月间山水陡发,居民淹毙万余人,训导康赞修漂流不知下落,四野田庐均被淹没等语……”(15)
康有为自己的记述是:“光绪四年五月朔日,连州水骤溺,平地水涌,公官训导,扶老病,亲巡视官廧。风水怒号,浪涌涛奔,樯倾舟覆,公殉然。救起,面如生……”(16)
杜凤治在光绪三年五月初六(1877年6月16日)的日记提到,县署幕客余滋泉呈送其父连州知州余镜波(杜凤治的同年)的信,希望杜在连州的通禀送到省城之前先向督、抚、藩、臬口头报告连州水灾的惨况。该信提到四月二十六日(6月7日)到二十八日(6月9日)连州水灾、大量房屋以及大段城墙坍塌;接着写道:“学院正在按临,老生甫考毕,童生正场尚未开考,目下断不能考,老生、童尚未闻有被水淹者。”杜凤治在抄引余镜波来信后在日记中写道:“伊信未言及康述之广文名赞修,即康佑之方伯之堂兄,丙午举人、学宫绅董、羊城书院监院,年七十余矣。伊本系连州训导,在省当差,因学院按临,到彼办考云。大水后其人不见,群谓康公骑鲸去矣。虽无实据,而不见其人,事实可疑也。”(17) 五月二十八日(7月8日)又记,康赞修“在羊城书院开丧”,杜凤治去吊唁,行礼时见到康国器(18)。六月二十二日(8月1日)的日记转抄了邓华熙关于连州水灾奏折中的话:“连州大水,人死万余,训导康赞修漂流不知去向。”(19)
综合上面记载,康有为对祖父的一些记述令人生疑:康赞修的“诰封奉直大夫”封典(从五品)与其子孙的品级并不对应,或许是后人加捐的;“教授”(府学主官,正七品)官衔的来历,行状的说法是康赞修钦州学正任满后,“同治三年,以烟瘴满擢知县,公老矣,不欲为外吏,改教授”(20),自编年谱所记相同,但为何写于1909年的《〈连州遗集〉叙》没有提康赞修有此官衔(21)?杜凤治日记、朝廷谕旨、方志传记,都只说康赞修终于训导(县学副职,从八品)任上,身后的恤典才加教谕衔(县学主官,正八品),“教授”的官衔也完全没有提及,从清朝的制度看,康赞修的“教授”官衔有些费解。此外,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光绪二年(1876)记“是年应乡试不售”,此前有同治十年(1871)、十一年(1872)两次应童子试不成功的记录,接着却没有入学的记载(22);康有为说过自己是荫监生(23),这只能是因祖父殉难而得(24),康赞修遇难于光绪三年,康有为在光绪二年究竟以什么资格应乡试的呢?
二、日记关于康国器的记载
康国器曾任福建、广西布政使,又护理过广西巡抚,康有为也为这位从叔祖“中丞公”写过事状,并在著作中多次提到。康国器因为当过大官,有关史料自然比康赞修多得多,正史、方志都有较详细的传记,在咸丰、同治年间的朝廷上谕和大臣奏折中也常提到他。然而,康国器回籍后的事迹,目前能见到的极少,因此,杜凤治日记留下的一些零散史料便具有参考价值。
同治十年(1871)四月,杜凤治署理南海知县后不久,就碰上一宗康国器族人被劫的案件。总督瑞麟接见杜凤治时说起南海金利司康晋(后又写作“康进”)家被30余人抢劫衣饰一案,杜凤治一时回答不出,总督乃责备了他几句,并责成要迅速破案,杜当即想到:“康晋者,大约即康国器一家,方伯乃兄连州教官,时见中堂,必有言也。”十几天后,杜凤治向总督报告已经拿获两名疑犯,不久,又向总督报告已抓获4名犯人,并到花县抓获“米饭主”(窝家、主谋)(25)。其时,康国器正以广西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瑞麟本与康国器有旧,自然会更加重视,杜凤治不敢怠慢,一个月内就报称案件破获。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广西知州孙某托人恳求杜凤治帮忙,此人看来是个贪官(日记称其与康国器有过节),署容县知县卸事后被受害百姓抢劫报复,康国器护理广西巡抚时曾将其“列入大计”(列入拟参劾人员名单),新巡抚刘长佑到任后将其名除去,但康仍不肯放过他。康国器是在任布政使,如果坚持,刘长佑不易包庇。孙乃求杜请瑞麟向康国器为其说情。杜认为这样做不妥,乃建议孙某请其座师董恂(户部尚书)致函刘长佑,而杜则找与康国器有交情的许其光(高第街许姓人士,康赞修的同年)向康关说(26)。日记对此事再没有下文。康国器的传记说他在护理巡抚期间“整饬纪纲,兴利除弊……以秉直奉公,谣诼交集,遽解组归”(27),看来不假。
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杜凤治主持县考,头场康国器“侄孙康伯英”榜上有名,但此后府试头场出案以及府试后所发六大县长案所录南海县童生名单中,此人再没有出现(28)。当年南海县应试的童生有3000多人,而同为首县的番禺只有2200多人,香山则是1700余人(29),要中式入学确实不易。相对科举考试其他环节而言,县考容易说情和照顾关系,杜凤治日记中时有官绅关说的记录,但都没有提过康赞修和康国器直接间接过问县考。
康国器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出过死力,但他的“圣眷”并非甚隆,朝中也无有力援奥。同治元年(1861),康国器率军在闽浙同太平军苦战,发布的上谕竟无故提了一句“康国器亦非超群出众之才”(30)。同治十年(1871),广西巡抚出缺,康国器作为布政使只是短期“护理”,而不是一般惯例的“署理”(“署理”规格高于“护理”,往往有机会接任)。同年十一月的上谕称,各省藩臬两司中有“阘茸不职”、“尸位旷官”、贻误公务者,特谕刘长佑“确切查明”广西布政使康国器、按察使佛尔国春能否胜任,“据实具奏”(31)。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康国器奉旨入京,没有得到新的任命,不久即告病回籍。当年十一月,杜凤治记下了首次拜会康国器的情形:“禀见不肯请,必换名片方请。见须发浩(皓)然,貌甚魁梧清奇,唯跛一足,行走甚不雅观。启口即父台公祖,说了许多恭维语。”(32) 康国器官比杜凤治大得多,他在会面时的谦恭态度是超出正常官场礼节的。
康国器回籍后,受到广东地方官的礼遇。同治四五年(1865-1866)间,康国器奉左宗棠命由闽入粤清剿太平天国余部,其时瑞麟以广州将军兼署粤督,康国器也要接受瑞麟调度,从当日的上谕、奏折看,两人关系良好,至少是正常的。同治十二年(1873),瑞麟为65岁大寿宴请官绅,日记所记康国器的席位排在西二席第一位,在所有赴宴绅士中,席次仅排在四大山长之后,宴后,瑞麟又留康国器等三位地位较高的在籍官员坐谈刻许方散(33)。
回籍不久,康国器就为其亲戚的一宗钱债案请托杜凤治。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的日记记下:“孙石泉来,为邱某少爷控告邓权惠欠项,邱父曾任新会、香山,邓父由守备仕至参将,曾拜邱官门下。据孙说,欠项实有,票亦非假。且邱子为陈纳人之婿,请追本银一千,利银一千,余愿充公。而邓姓一边,先由吴荆南来言,云康佑之方伯托之,云与邓有戚谊,欠固渺茫,票亦捏造。方伯不便亲身面谈,先浼荆南介绍,继由安良局陈古樵作函关说。予均复以候亲讯一堂再说。”几日后,杜凤治在臬署碰到吴廷杰(荆南),吴再提康国器所托事,杜“告以陈孙二先生缘故,左右皆难,容亲讯一堂再说”(34)。
因为原告邱少辂的岳父陈光照(纳人)是督署幕客,杜除了要根据案情处理以外,还要在卸任广西布政使和现任总督师爷之间平衡。杜凤治按照当日处置钱债官司的惯例,先把被控告欠债的一方收押。康国器继续通过杜凤治的亲家吴廷杰请求作出有利于邓权惠的处置。杜接着记:“吴荆南早来,为邓权惠欠邱令之子千金一事,愿偿,唯身押捕厅,恳邀诚实可靠铺家保出在外,自向邱宅面议讫项(其票作两单,一六百两,一四百两,其利按月二分,已二十余年,如按年按月计算,利将不赀,为此须出去浼人说合也)。予谓此亦未尝不可,但恐一去无音,必须保家可靠肯肩承,限以十日或半月,说定。伊固不肯按年利计利,然亦断无按年月计利之事。远年债务,一本一利,不能少矣。荆南言邓某意在归本而已,利不计也。予谓如此恐难。”杜凤治同意邓权惠取保释放出来与邱氏洽谈债务的本利问题,因有借票,“有在场目击者,无可饰卸”,这项欠债很难否认,但杜对邱20年后才提起债务诉讼感到很奇怪(35)。
稍后,康国器再托杜的同年许其光向杜凤治谈邱、邓钱债事,“邓之堂兄,康之婿也”,康要许转达:“如要罚邓权惠捐书院膏火经费一千二百两均可,若还邱姓,一文无有。”杜凤治称罚款“无名”,既然邓权惠愿意把银缴官,那就缴银一千两来,马上就可以放人。许其光满口答应。杜凤治打算收到这笔银子就转交给邱少辂,这样两方面都可以交代得过去(36)。
此后日记再没有提起这宗钱债案,大概也就此了结。康国器虽为自己亲戚关说,但始终没有通过杜的上司干预,所请托的几个人均为杜的亲友、同乡。
日记透露康国器在广州城内开设了当铺。同治十二年五月,候补知府衔广粮同知方功惠拜客,其在街上等候的轿夫、执事人与祥升当铺争闹互殴。杜凤治命差人查拿当铺中人及帮闹之街邻,但值日头役执行不力。杜凤治得知祥升当铺系康国器少爷所开,事发时少爷在当铺内,“其下人敢得罪地方官广粮厅者,有所恃而不恐也”。方功惠是总督的红人,又是杜凤治的密友,杜表示要查封当铺,但方功惠来信要求只把肇事者枷号以全自己脸面,切言不可封禁,以免不好收场(37)。康国器子康熊飞早已亡故,在当铺的当系其继子(也可能是杜凤治误记)。日记并没有康国器过问此事的记载。
杜凤治的日记两次记载准备下乡拜访康国器,但都没有见面。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南海县金利属岗头乡、九江属沙涌乡发生劫案,杜凤治下乡督促缉捕,原先准备“到官山与康佑之方伯及诸绅耆商量弭盗之法”(38)。杜到了岗头乡,传见该乡耆老,谕以“地方官责任固重,然安能各村各家而亲来保卫之,是必各村自为防备,立定章程”,同仇敌忾对付盗匪。接着到了九江乡,到沙头公局传见局绅。南海绅士中著名人物、九江局绅明之纲(进士)冒雨赶来,参与讨论防御、缉捕盗匪之事。因为康国器地位高,杜凤治自不可以“传见”,但杜也没有去拜见,“以相距二十余里,雨后难行,不能前往”为理由,派人持手本至康国器家作礼节性的问候,放弃了原先准备同康国器“商量弭盗之法”的计划(39)。
同年十一月,杜凤治下乡催征,到官山公局,士绅陈伯翔来见,告之“康藩台(国器号佑之)即居伏龙堡”。杜带差勇亲往催征,打算顺道拜会康国器。日记记:“门口言近日病足,卧病在床(本跛一足),寸步不能行,拜伊少爷。方伯有子早卒,亦无孙承继,一侄未在家中。”杜凤治没有下轿进入康宅。日记描写了康氏宗祠:“在银河桥见康方伯所居对河新盖两祠堂,一为康氏大宗祠,一为诰赠资政大夫康○圃公祠,盖方伯之父也。石工甚巨,一式新凿,门前两支将台旗杆,台基在河中。两石狮虽小而新,雕镂工巧,此盖去年新造者也。”接着杜凤治在日记中对广东造祠堂、拜祖讲究排场、慕繁华、爱体面的风气发了一通议论(40)。
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康国器为南海乡间“赌风太盛”、“赌匪充斥”到省城见总督、巡抚,并将写给督抚的信稿给杜凤治看,杜表示“无他办法,唯有责成各村绅耆具结禁绝交匪而已”(41)。
各种传记均称康国器告病回乡后相当低调,康有为称康国器“寡叶单枝,无所缘附,不居城市,不谒当道,罢官十余年,无一书至京师”(42),杜凤治日记的记载可以作为佐证。
三、从日记看康氏家族在广东绅界中的地位
在康有为的著述中,康氏是历代簪缨的世家大族。因为康国器当过大官,康氏子弟跟随康国器镇压太平天国得官者甚众,我们也很容易认为,康氏家族在南海和广东有很大势力,但从杜凤治的日记和其他资料看,情况不尽如此。
本来,康国器任过实缺布政使、护理过巡抚,回籍后无疑是省内名列前茅的大绅,但据杜凤治的日记,看不出康国器对地方有很大影响,前面提到的邱、邓钱债案以及康国器的当铺被处罚的事,反映出他在地方上的权势,与他的官衔不是很相称。在杜凤治日记有不少大绅士讨论、参与广东地方重要事务的记载,例如省城文澜书院大绅梁纶枢(盐运使衔、二品衔)、伍崇晖(道衔、三品衔)、马仪清(翰林、在籍道台),以及西关的大绅士梁佐中(江苏道台、曾署苏藩)、梁肇煌(在籍顺天府尹)、李文田(探花、在籍翰林院侍读学士)、苏廷魁(前河道总督)等人,他们都是官衔与康国器相近或低一些的在籍官员,但康国器似乎完全置身事外,他在省城甚至没有住宅(住在亲戚家)。康有为著作中多称康国器为“中丞公”(巡抚的别称),但杜凤治日记所有提到康国器的地方都称之为“方伯”(布政使的别称),这个细节,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康国器在广东官绅眼中的分量并没有康有为描述的那么重。
康国器的官阶和影响没有使康氏成为豪绅望族,可能与他个人保持低调、身体伤病有关,但也是广东情势使然。与湖南、安徽等省不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官绅在广东并没有成为一股势力,而通过平定红兵起事,广东也出现了大批通过保举之类产生的异途士绅,他们并不被官府和正途士绅看重。对这些“异途”绅士,杜凤治在日记中轻蔑地记下:“咸丰三四年起捐项通融以来,乡曲无赖、僻壤陋夫,无不监生职员矣。”(43) “十余金即捐一监生,故不成器人皆充绅士,况红匪闹后六七品功牌亦多,亦自以为绅士。”(44) 在广东绅界,科举正途出身者仍然完全主导。康国器原来是小吏出身,他的官是“打”出来的,没有科举同年人际网络,在广东大绅家族中也缺乏世交、婚姻等联系,在广东绅界显得有些另类和孤立。跟随康国器从军的康氏子弟,除康国器子康熊飞外,“余无至知县都司者”(45)。康氏多数人的官衔,很可能是从捐纳得来。康氏虽然号称十三世为士人,但从康有为的曾祖以下四代,多数人的官职官衔并非来自科举,在康有为中进士之前,四代人中只出了康赞修一个举人,另外还有几个生员(46)。较之一般庶民,康氏家族当然算有威势,但在士绅如林的南(海)、番(禺)、顺(德),这样的家族远不能与南海潘氏、番禺何氏(沙湾)、省城梁氏(西关)与许氏(高第街)、顺德罗氏与龙氏等望族相比。
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记录了光绪十九年(1893)乡试中式后回乡争夺西樵公局同人局务、进行乡政改革受挫的事:因局绅张嵩芬(在籍知府)庇盗,康有为乃号召西樵“三十二乡之绅、合三十余人攻张,令其将局戳交出”,张嵩芬的族人企图以武力劫持康有为夺回局戳,而康的乡人也携军械来营救。此后,康有为在同人局中兴办教育,传授中西学问,清匪禁赌,后来被张嵩芬、潘衍桐(在籍翰林)运动官场罢免,追回局戳。他甚至把此事与戊戌维新的失败相比较(47)。读了康有为绘声绘色的描写,我们会觉得因为其祖辈及本人的声望,他在西樵绅界、乡人中很有号召力。黄世仲的纪实小说《大马扁》第8回“谈圣道即景触风情,为金钱荣贵争局董”、第9回“据局戳计打康举人,谋官阶巧骗翁师傅”也写了这件事,不过,故事与康有为的说法大相径庭,黄世仲以极为刻薄的笔调指名道姓地把康有为丑化了一通(48)。小说自然不能视为信史,康有为自己的说法也未必真实,但事情最终的结果是清楚的:康有为被排除出公局。
晚清广东的公局是士绅掌控的基层权力机构,局绅通常通过绅耆“投筒”等程序产生,再由州县官下谕单委任。出任局绅者多为举人、贡生、生员,进士极少,局绅的地位一方面由本人功名职衔决定,另一方面与宗族势力有关,局绅多数也是某族的族绅(49)。西樵的公局名同人局,康有为说是其从伯祖康国熹创办的,“中国地方自治,实自公始起,至今粤各乡局,皆其遗风也”(50)。但县志康国熹传只是说创办团练“国熹之力为多”(51),没说是他创办。杜凤治日记有大量同公局局绅打交道的记载,包括西樵一带的局绅,但从未提到过康氏族人。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杜凤治曾与安良局局绅陈古樵(西樵人)说打算拜会康国器商议发动西樵绅耆设局治理盗匪。陈古樵认为:“亦无益,设局先要措赀,伊乡前曾办过,因是不成,今更难。且康系小姓,族微人少,乡人恐不为用也。”(52) 陈古樵是康氏同乡,与康国器关系良好(康国器曾托陈为邱、邓钱债事致函杜凤治),他的话应可信。康国器健在时,康氏家族在西樵尚且无足够的号召力,康国器死后9年,康有为想要重整和掌控家乡的公局,就更难成事了。
认识康氏家族在绅界中的地位,对了解康有为青少年时代成长的背景有一定帮助,他日后的政治活动在广东遇到很大阻力,与此多少也有一些关系。
收稿日期:2008-08-17
注释:
① 宽予:《望凫行馆手稿跋》,收入《艺林丛录》,香港: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② 笔者也利用该日记写了两篇文章:《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③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④ 《清代稿钞本》第12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6-567页。“石狗”、“江谷”均广宁县之圩镇。
⑤ 《康氏家庙碑》,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各集版本同,不另注),第440页。
⑥⑧ 《我史》,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60页。
⑦(11) 《清代稿钞本》第14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下各册版本同,不另注),第248-249、255,19页。
⑨ 《诰封奉直大夫敕授文林郎升用教授赠教谕衔连州训导康公行状》,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69页。
⑩ 《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579、586页。
(12) 《清代稿钞本》第15册,第89-90页。
(13) 《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280页。
(14) 宣统《南海县志》卷15“列传”。
(15)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光绪三年六月辛卯。
(16) 《诰封奉直大夫敕授文林郎升用教授赠教谕衔连州训导康公行状》,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69页。行状把康赞修殉难的年份搞错,估计是笔误,因为早年写的自编年谱不误。
(17)(18) 《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299,328页。
(19) 《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379页。从杜凤治所引余镜波的信看,连州水灾致令大量房舍倒塌是在6月7日到9日期间,康赞修遇难也应该在这几天。余镜波的信没有提到康赞修遇难,可能因为尚未找到遗体,不能以传闻向上司禀报。杜6月16目的日记称康赞修在水灾中失踪,发布上谕的辛卯日即阳历7月17目,如果康赞修遇难后当时就找到遗体,杜凤治为何到8月1日抄录邓华熙奏折时仍照抄“漂流不知去向”的说法?
(20)(23) 《诰封奉直大夫敕授文林郎升用教授赠教谕衔连州训导康公行状》,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69,70页。
(21) 《〈连州遗集〉叙》,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99页。
(22) 《我史》,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60页。
(24) 康赞修遇难后,朝廷的恤典是“加教谕衔,荫一子入监读书”,康赞修长子即康有为父康达初先卒,另外两个儿子达迁、达守已有候选知县、候选通判等官衔,康有为应该是作为长孙得荫而成监生的。此外,康赞修的“诰封奉直大夫”(从五品封典)与康有为的官职并不对应,很可能是加捐而来。康有为关于康赞修“升用教授”的官衔的来历的说法也很费解,姑存疑。
(25) 《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200、202、226、248页。
(26) 《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11页。
(27) 宣统《南海县志》卷16“列传”。
(28) 《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91、120-121、160-161页。
(29)(32)(33)(34)(35)(36) 《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32、118,377,524-526,502-503,507,526页。
(30)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38,同治元年八月戊寅。
(31) 《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324,同治十年十一月己酉。
(37)(38)(39) 《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577-578、579、533、545页。
(40) 《清代稿钞本》第15册,第232-233、233-235页。
(41) 《杜凤治日记》第36本《重莅首邑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初六、初七日。18册,第345-346、348页。
(42) 《诰封荣禄大夫广西布政司护理巡抚康公事状》,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2页。
(43)(44) 《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332,446页。
(45) 《诰封荣禄大夫广西布政司护理巡抚康公事状》,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2页。
(46) 《康氏家庙碑》,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438-440页。
(47) 《我史》,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83页。
(48)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0-264页。
(49) 关于公局可参看拙文《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
(50) 《伯祖种芝公〈六太居士遗稿〉叙》,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86页。
(51) 同治《南海县志》卷17“列传·节义”。康有为称康国熹“布衣”,方志称康国熹“国学生”,他充其量只是例监生,西樵士绅众多,按一般情况他不会成为公局的主持者。
(52) 《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5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