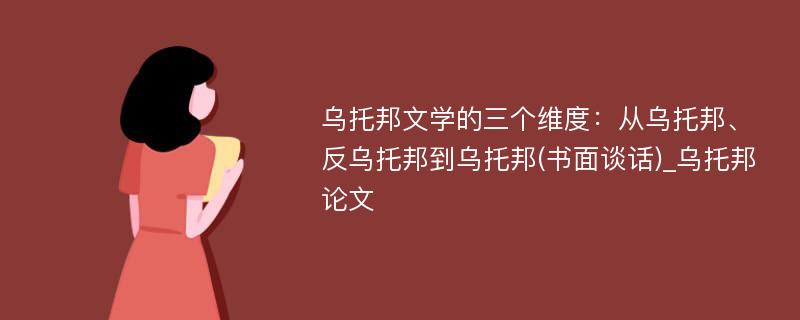
乌托邦文学的三个维度:从乌托邦、恶托邦到伊托邦(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笔谈论文,维度论文,文学论文,恶托邦到伊托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5)03-0040-07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传统及其变异
麦永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野中皆属后者,因此与人的社会存在及其现实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按照理查德·基尔尼《现代性诗学》的看法,它们是社会想象的两个重要维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两大基石。
意识形态是思想史、政治、哲学和文艺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在20世纪,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问题正式进入哲学和美学领域,是以德国卡尔·曼海姆教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1936)和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讲演录》(Paul Ricoeur,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1986)为标志的。就文学而言,乌托邦传统源远流长,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大变异:一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恶托邦”的出现——其标志是以乔治·奥维尔《1984年》为中心的“恶托邦”(反乌托邦)文学和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中关于“恶托邦”的论述。二是“伊托邦”概念的提出——其标志是美国学者威廉·J·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的面世。[1] [2] 由此,在意识形态理论观照下,乌托邦(Utopia)、恶托邦(Dystopia)和伊托邦(Etopia)三个维度成为了重新审视乌托邦文学传统的一个新视野。
众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皆视意识形态为虚假的意识,并认为要在理论上对意识形态异化人类意识的方式加以解魅或解神秘化。利科认为,意识形态想象有三个主要功能:统一(integration)、掩饰(dissmulation)和统制(domination)。正如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所言,社会体制倾向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将它们合法化,以确保统治者获取的权力。而乌托邦想象则是我们社会想象的未来维度。基尔尼指出,当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些术语相对应使用时,可以做如下表述:当意识形态将一个既定实体的观念统一和合法化时,乌托邦常常是去颠覆它。[3] 从曼海姆和利科关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理论视野来审视反乌托邦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在性质上,反乌托邦不仅是乌托邦的一个分支,而且更重要的是,反乌托邦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社会想象。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超越现实的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与某个阶层对现实的掌控相联系,后者与历史意识及全人类理想相联系;在利科看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都是社会想象,前者是统治者和主流社会体制用于制造合法化统一观念的政治工具,后者则具有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对现存社会体制的蓄意肯定,乌托邦是对现存社会体制的想象性或理想性否定,恶托邦则是对乌托邦的理想性的反讽和否定。恶托邦的特殊功能是无法取代的:它从否定辩证法和否定美学的角度提示人们对社会政治现实和人类未来前景进行反思的必要性。
恶托邦亦称“反(面)乌托邦”(anti-utopia),欧美文学史上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代表,即20世纪上半叶三部具有共同思想倾向和艺术表现特征的小说:苏联作家叶·扎米亚京的《我们》(We,1924)、英国作家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乔治·奥维尔的《1984年》(Nineteen Eighty-Four,1948)。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曾经对这类小说做了一个简明的界说:“当一部作品对未来世界的可怕幻想替代了美好理想时,这部作品就成了‘反面乌托邦’或‘伪乌托邦’讽刺作品。”[4] (p327)反乌托邦的预言家对邪恶事物的即将到来加以预警,希冀他们的预言不要变成现实,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对自己所预告的可怕前景的来临感到厌惧。在思想渊源上,反乌托邦小说与柏拉图《理想国》、康帕内拉《太阳城》、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脉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作品有思想关联,是对浪漫的乌托邦思想加以反拨。在文学渊源上,它又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出现的科幻小说密不可分。反乌托邦小说虽然也具有明显的科技和幻想的因素,但似乎更侧重社会批判、政治讽刺和对人类未来阴郁恐怖前景的描绘,将对历史与现实的凝重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忧患意识融合在一起。
在时间维度上,“恶托邦”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这并非偶然的现象。从全球性视域来审视20世纪,可以看出反乌托邦与异化都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关键词Humanism(注: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上,Humanism一词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可以根据语境译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在现代主义崛起之前,它与三个历史环节密切相关:(1)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思想——突出地体现在希腊神话的“神人同形同性”的基本特征中和在三大悲剧家的命运悲剧中。(2)文艺复兴时代的核心精神人文主义。(3)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突出地表现在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和俄罗斯文学“小人物”系列中。无论是乌托邦、恶托邦还是伊托邦,其实质上所关注的共同焦点皆是人的存在与人性问题。)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20世纪既是一个人类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时代,又是一个人被全面异化的时代,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空前残酷的时代,更是一个科学技术与信息交流空前发达的时代。与人类存在危机意识密切相关的异化问题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马克思和卢卡奇那里得到了较集中的反映或分析。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中叶极权主义的出现,使得奥斯维辛之后的人与历史问题成为阿多诺、本杰明等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理论家对人的异化进行总体批判和布洛赫“希望美学”的基础。而对极权主义——无论是法西斯式的还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或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极权主义——的警惕和批判,则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特征。极权主义用政治强权和现代大众传媒对人性加以异化的现象,在以乔治·奥维尔《1984年》为代表的20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中得到了充分而深刻的反映。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嬗变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历史进程:进化与异化如影随形,交织互动。人们在现实中感到不满时往往会陡然引发浪漫之思,通过怀恋往昔和虚构未来这两条途径使被压抑的欲望获得满足,表现出乌托邦式的审美取向,以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统治模式和趋于异化的社会语境相对峙。
“伊托邦”是进入21世纪后日益显豁的理论关注和文学研究的新维度。电子传媒时代的来临和赛博空间的生成,使得“伊托邦”成为接续乌托邦和恶托邦发展轨迹的新现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媒体艺术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委员会主席威廉·J·米切尔在其《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2001)一书中提出“伊托邦”的概念,认为“伊托邦”是一个中性词,特指提供电子化服务、全球互联的当代生活和未来城市,既非充满美好而浪漫的社会想象色彩的乌托邦,亦非蕴含着抑郁、怀疑、厌惧、绝望的黯淡情绪的恶托邦。米切尔教授的《伊托邦》是“了解正在出现的网络社会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的一部“充满奇思异想的纲领性著作”,“代表着一种看待未来以及严肃认真地对待历史、永恒与未来之多种交汇的重要方式”。该书的“序幕:城市的挽歌”引用麦克卢汉1967年的一个预言:“城市除了对旅游者而言仍是一个文化幽灵外,将不复存在。”米切尔认为,比特(bits)已经将城市摧垮,传统城市模式无法与网络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共存,“以网络为媒介、属于数字电子时代的新型大都市将历久不衰”[2] (p1)。这就是我们无法后退、别无选择的抉择——伊托邦。这将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共存的关系。
米切尔的《伊托邦》关注传媒的变化对历史与人生的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和革命性的意义。其开篇分别叙述了三个哀悼者的“悼词”:第一篇悼词的关键词是“水井”。作为古老荒凉的社会聚落村庄的社交中心的水井,因供水管道的出现而边缘化。人口增长了,村庄也扩展成为市镇,但村民们已经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水,不必再聚首水井边,新颖现代的场所如广场、咖啡馆、市场取代了水井的社交功能。第二篇悼词的关键词是“壁炉”。作为北方家庭在冬天“惟一的光源与热源”的壁炉,因管线(电线和供热管道)的铺设而边缘化,壁炉熄火(除非节庆时作为一种怀旧的娱乐方式才点燃),家庭成员开始分散活动,“老祖母变得百无聊赖,脾气暴躁,不久就搬出家门”,住进附近有空调的疗养院去了。“壁炉周围再也无法成为社会的粘合剂了”。第三篇悼词的关键词是“佛祖讲经”。作为以前佛祖讲经圣地的菩提树下和佛祖圆寂后藏经的寺院,因“书籍的大量印刷和文字的广泛传播”而边缘化。信徒们不必围坐在菩提树下或长途朝圣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关于佛祖的信息。经历市镇化、电气化和信息化后的伊托邦时代,受地点和时间制约的使大众维系在一起的旧式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裂痕,“今天,无所不在的通讯网络、智能机器、智能建筑,与供水、废物处理、能量传输以及交通运输系统相结合,构成一个不分时间、无论地点的全球化互联世界”。大约从1993年开始以万维网为标志的、由异类数字精英所引领的这场数字革命,其意义并不小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人们熟悉的体制和生活正在产生极为深刻的变化。[2] (p11)尽管米切尔试图从客观中立的立场描述这种伊托邦的方方面面,他一方面驳斥技术必胜论者美好的乌托邦遐想,另一方面也否定人们关于恶托邦的担忧,说不要“认为数字革命必然会像其他革命一样,再次带来肮脏的权力和特权”,但是,文明的进化与异化实在是世界历史这枚徽章的两面,认同与差异的互动、黑格尔哲学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德勒兹思想观念之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憧憬“距离消失、空间终结”,一切都呈现出虚拟现实特征的伊托邦是朵美好纯净的出水芙蓉,但同时也要充分警惕可能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新的污染。
人文主义——乌托邦与恶托邦文学的精髓
欧阳灿灿
通观西方乌托邦小说,在其对未来的令人激动的描画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人文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在恶托邦文学中扭曲怪异地折射出来。乌托邦与恶托邦文学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植根于其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核。
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在古希腊时代,它的原意是“修辞”,指为培养演说家所进行的教育。该词后来指体现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四种基本因素:言说的自由;法律的准则;城邦的政治自由;个体作出自己道德与政治决定的权利。[5] (p109)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内涵深化,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以人性否定封建教会神性的思想体系和武器。在其后的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中,19世纪现实主义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都渗透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关键词之一,人文主义内涵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对人的关注,包括对人性、人的存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等的关切与思考。无论是憧憬美好未来的乌托邦,还是批判和警示社会历史负面发展的恶托邦文学,都贯注着人文主义精神。
乌托邦传统源远流长,从古代希伯来先知对未来的勾画到后来世界文学中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模式,都可以发现许多极具人文精神的思想因素与措施,如弘扬理性、提倡人文教育、主张人人平等自由、实施优生计划等。乌托邦思想家、文学家们对人类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相信自然世界与人的思想可以按正确方法加以改造,尤其把教育视为塑造完美人性、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培根的《新大西岛》堪为例证。
恶托邦文学都给乌托邦传统注入了新的人文主义内涵,形成了新的艺术表现方式。与乌托邦作家乐观主义的正面憧憬不同,恶托邦作家忧心忡忡地关注社会历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他们对人类、社会、自然等关系作出了新的反思与批判。大多数乌托邦作家倾向于从总体意义上看待人与世界,突出人的集体性,而恶托邦作家则强调人的多样性、个体性,要求把人从神圣的总体性、普遍性中释放出来,他们尤其是对泯灭个性、戕害人性的极权主义统治深恶痛绝。这在奥维尔《1984年》中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表现。恶托邦作家还对传统上关于理性和科技的看法进行了反思。因为科学技术似乎并未如乌托邦作家所愿,带来人性的完善和精神的自由,相反给人类的发展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例如在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中,先进的科学技术讽刺性地成为了牢牢地控制个体自由、导致人的“非人性化”的有力工具。恶托邦作家极为担忧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可能带来的环境恶化的可怕后果,他们不同程度地表露了重新审视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在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反思的关系上,恶托邦的出现似乎是对乌托邦的一种反拨,但两者在本质上具有思想上的内在一致性,这就是对人、人性、人的存在境遇和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注。因此说人文主义是乌托邦与恶托邦文学的精髓。或许可以借用一个摄影学的比喻,乌托邦是正面显示图像的彩色照片,而恶托邦则是看起来丑陋不堪的黑白负片,但是它们实际上只是从不同维度反映着同一实体——社会想象中的人。
在恶托邦小说中几乎都存在一个人文主义者式的人物,例如奥维尔《1984年》中的温斯顿,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中的约翰,当代著名的加拿大女作家玛·阿特伍德《女仆的故事》中的奥弗雷德,等等。
一言以蔽之,在乌托邦与恶托邦作品中,共同蕴含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即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怀,对真善美伦理价值的不懈追求,对扭曲畸变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不满与警示,以及不怠于现状而不断提升自己的超越精神和创造精神。
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中的“乌托邦”传统
张群芳
在世界文学中“乌托邦”有着悠久的传统,直到“乌托邦”得名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小说后,人人平等幸福、个个安居乐业的乌有之乡或理想社会图景才得以定形,成为世人心向往之的洞天福地。
虽然我非常佩服乌托邦乃至恶托邦文学的作者们的洞察力、想象力和批判精神,但是,我更加震惊于他们那几乎毫无例外的男性中心主义。他们都是具有启蒙警世精神的知识精英,但是,却仍然摆脱不了千百年来男权制思想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乌托邦文学中关于妇女的描写。深受柏拉图影响的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从整个城邦的利益出发,提倡与《理想国》相同的公妻制:“女子初次与男子性交而不受孕者,便被配给另外一个男子。如果多次与男子合欢而仍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没有权利进入公共食堂和寺院。”[7] (p31~32)安德里亚在《基督城》里也毫不掩饰地说:“女人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生儿育女。”[8] (p129)莫尔虽然在其著名的《乌托邦》中主张一夫一妻制,但也明确规定:“丈夫管教其妻子,父母管教其儿女,倘使过失重大,则由官方处罚,以资儆戒。”[9] (p238)莫尔不但规定妇女在某种情况下仍然隶属男子(如新郎与新娘裸体相对,以便丈夫选择关系自己一生幸福的妻子),而且还力图维持家长制的两性家庭关系,如要求女子在结婚之前严守贞操,严格禁止通奸或妻子要求离婚,等等。至于后来的乌托邦作品如培根的《新大西岛》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家长制家庭结构。总体而言,莫尔为“乌托邦”定名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主流的乌托邦文学虽然对理想社会进行了繁复的设计与构思,但是它们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并无太大的区别。妇女总是被定位在生儿育女、管理家务的角色上,总是与“性”联系在一起,潘多拉和夏娃的女性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男性心头,因为从她们开始,西方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文化确立了一种基本的性别定势:女性总是与无知、愚昧、罪孽相联系。
其次,我们来看恶托邦文学的代表作《1984年》对主要女性的处置和态度。在乔治·奥维尔的笔下,女性只是一种“性”的存在。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沦为政治木偶,表现出性冷淡,温斯顿与她结婚十年来,在床上只要“一碰到她的身体,她似乎就立刻畏缩僵硬起来。搂着她有如搂着一个有关节的木偶一样”。奇怪的是,她却要求温斯顿每周例行公事般地进行一次房事,“她甚至给这件工作起了两个名称,一个叫做‘制造一个孩子’,另外一个叫做‘我们对党应负的义务’”。在大洋国,“惟一被公认的结婚目的,是为了党而生儿育女。性交被认作一种好比灌肠那样的例行公事的小手术”。而温斯顿貌似叛逆的女友朱丽亚实际上只是“从腰以下才是一个反叛者”。
奥斯卡·王尔德曾说:“一幅没有乌托邦景色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瞧,因为它舍弃了人类永远向往的境遇。”但如果这里的“人类”仅仅是" man" (男人),那它又如何值得我们永远向往呢?
恶托邦与科技的意识形态功能
邓与评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但也是人类美好的乌托邦情结遭到强烈质疑和否定的时代。在物质文明空前进化、技术理性高扬的同时,大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小说家们对权力政治支配下的技术进步,以及它所带来的人的精神的全面异化表现出了普遍的关注。他们以恶托邦的文学形式预测和描绘了这种极权统治下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进步的结合所导致的异样景观,对传统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加以解构,对人类未来的可能出现的恶托邦前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对技术政治社会中人的存在危机发出警示。
乔治·奥维尔《1984年》所描绘的恶托邦“大洋国”,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国家,也是一个高度极权化的国家。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弥漫在国家的每一个领域,其话语依托强大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电幕和窃听器牢牢地宰制着一切,极权统治的象征“老大哥”的形象与声音无处不在,通过巨型屏幕和广播影响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极权政治的工具思想警察无孔不入,监视和抓捕任何有精神独立和异己思想的人,国家机器动用科技含量极高的设备对思想犯进行令人发指的惩罚和洗脑,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道,窒息了人类的自由天性。恶托邦文学旨在提醒人们:技术进步与极权统治的结合,使传统乌托邦恬美和谐的牧歌终结,社会想象的诱人幻象破灭,灾难性的恶托邦宛如噩梦一般萦绕不去。
文学领域所描绘的技术政治现象应当与理论层面的深刻反思相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对近代工具理性的社会批判可资借鉴。马尔库塞曾经强烈批判过科学技术反人性的一面,他不无偏激地用一个等式来表达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技术进步=社会财富增长=奴役加强。他认为科学技术带来了生活方式、劳动方式的改变,给人类改造自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科技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包含了对爱欲和本能的压抑,成为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作为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认为它消除了人的理性批判力量,从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人应该是双向度的人,既有技术理性力量,同时也应当具有理性批判精神——这是一种否定性和颠覆性的力量。在奥维尔的《1984年》中,这表现为主人公温斯顿对党魁“老大哥”和极权统治之下的社会及人的存在方式合理性的怀疑和否定。马尔库塞认为科技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因为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与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
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可谓功不可没,但问题不在于科技是什么,而在于谁在掌控科学技术!当科技成为技术政治,成为高度极权化的意识形态使用的工具和手段之时,它可能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恶托邦式的灾难,从而使伊托邦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恶托邦的延续。
由此看来,在乌托邦—恶托邦—伊托邦的三个维度上,科学技术都是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传统乌托邦文学往往借助科学技术营造社会想象的美好幻象;而恶托邦文学则更多地对科学技术作了政治寓言和意识形态的解读。在上述的现代小说家和思想家的视野中,科学技术的中立性这一传统认识遭到了质疑和否定。科学技术本身是带有意识形态话语特征的,因此应当警惕科学技术与技术政治的畸形结合,避免奥维尔式的恶托邦梦魇在人类的未来世界里变成可怕的现实。
比较视野中的伊托邦
杨丽英
在20世纪进入尾声,新世纪的足音清晰可闻之际,美国学者威廉·J·米切尔在其《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一书中,提出了“伊托邦”的新概念。他认为在当今数字信息时代,人类所处的空间不仅仅是真实存在的物理与地理的场所,还包括了虚拟真实的赛博空间,即一个以电子媒介将全人类链接在一起的网络世界。他把这种提供电子化服务以及全球互联的城市称为“伊托邦”,并认为它是中性化的实体。
在笔者看来,米切尔教授关于伊托邦的中性化界说可以进一步商榷。虽然“伊托邦”(E-topia)颇为确切地与我们当今所处的E—时代相吻合,令人联想起后历史、后地理的赛博空间和拟像时代及其种种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与此前的乌托邦、恶托邦概念相比较,伊托邦是否可能成为纤尘不染、遗世独立的高科技“神话世界”?
就伊托邦本身而言,它存在着乌托邦与恶托邦的双重悖论特征。
一方面,中性化的“伊托邦”概念实际上具有明显的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性质。它貌似公允的立场使人很容易幻想存在着一片高科技的“净土”,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极大的增长,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数字虚拟世界中演绎着伟大的现代神话,它突破传统乌托邦的时空束缚,隐匿或遮蔽了年龄、性别、种族、阶级、身份……使得人类无差别交流的“大同世界”得以真正地实现,从而为我们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化未来世界。
另一方面,伊托邦的现实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乌托邦神话,成为恶托邦的逻辑发展。数字化存在方式的伊托邦并非纯粹指向未来,它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无法逃离当今社会复杂矛盾的现实关系。当我们在奥斯维辛之后和五月风暴以来的语境下认真审视“伊托邦”之时,可以发现其所蕴含的恶托邦的意味。电子传媒时代的数字世界以其虚幻性、娱乐性麻醉人们的文化批判意识,高科技文明的美好前景似乎向人类许诺,贫困终将消逝,一切差别终将弭灭。但是从实质上看,光明纯净的世界表象之下可能隐匿着汹涌可怕的暗流,冠冕堂皇的游戏规则中可能蕴含着福柯式的权力话语,在某种意义上,伊托邦是一种鲍德里亚式的“完美的罪行”。
无论是乌托邦、恶托邦还是伊托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境遇不断审视和反思的结果。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言,人被宣称是不断探索他的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的价值就存在于他的这一审视中,存在于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标签:乌托邦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伊托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