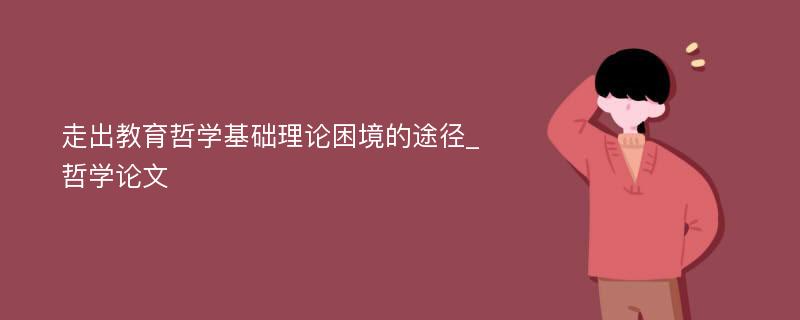
走出教育哲学基本理论困境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理论论文,路径论文,困境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33(2010)03-0005-06
教育哲学研究虽然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重视,但是对于许多基本问题,迄今仍然处于探讨阶段,远未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本文在揭示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困境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可能性、建设性的解决路径,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困境一:学科属性定位的“单边性”思维倾向明显,“理论贯通性”不足
何谓教育哲学?从学科归属关系看,教育哲学应归属于哲学还是教育学?教育哲学究竟是哲学的子学科,还是教育学的子学科?长期以来,围绕教育哲学的学科归属定位问题,学界展开了广泛、持久的争鸣。各种观点归结起来,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种:其一,教育哲学属哲学范畴,是哲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学科,比如吴俊升先生就曾鲜明地提出:“把哲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方面,便是教育哲学。教育哲学当和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一样,同是应用哲学,不过应用的境地各不相同罢了。”[1]在郎特里(Rowntree,D.)编著的《英汉双解教育词典》中,也将“教育哲学”界定为哲学的应用学科,教育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其内涵一是建立有关知识、认识与作为制度化社会活动的教育的思想体系;二是澄清教育概念的含义。近年来,前者(如在柏拉图、康德、杜威的著作中所见)已不如后者(如在彼德斯〈Peters,R.S.〉的著作中所见)受到重视。”[2](P346-347)其二,教育哲学属教育学范畴,是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子学科之一,是从哲学的特殊视角出发来研究教育活动,着眼点是哲学,学科的落脚点和归宿仍是教育学。“教育哲学与其他教育科学有着相同的目的,但在处理教育问题时,它却有着另外的最终目标,并运用了特殊的方法。”[3](P34)应该说,以上两种观点呈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学科归属思维倾向,分别在哲学、教育学领域影响较大。其三,教育哲学既属哲学范畴,同时亦属教育学范畴,本质上具有双重属性,是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依笔者管见,第三种观点才更接近教育哲学学科属性的本质,只不过紧跟的问题是:如果将教育哲学定位于一种交叉学科,那么,二者的交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交叉?是外在的相加还是内在的有机结合?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又该如何交叉?等等。本文试图在依次分析以上三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作为“科学之王”的哲学位于人类智慧金字塔的塔尖,包容着众多学科。许多学科知识体系,尤其是社会科学诸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都从哲学那里寻求基础性理论根源以及自身存在之合法性的证明依据。社会科学“旨在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的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世俗的知识。”[4](P96-97)这种来自经验的性质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通常意义上,它应该指称一套较完整的相对独立化的知识体系。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哲学最早产生于1894年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将德国哲学家洛孙克兰茨的著作《教育学的体系》翻译成英文,并更名为“教育哲学”。应该说,从诞生之时,教育哲学就与哲学有着难以割断的学科渊源联系,并带有很强的哲学理论在教育领域具体演绎的意味。此种观念长期统治和困扰教育哲学的学科归属定位,导致教育哲学研究呈现出刻板、僵化的模式化特征,尾随哲学的发展亦步亦趋,处于徘徊不前的尴尬状态。许多研究成果都循着这样一种固定思路:首先将有关的哲学观点作为预设前提摆放出来,然后再挪移到特定的教育领域中进行所谓的应用性“思考”。深究起来,大多并未将二者有机结合,而只是在做表面层次的粘贴,甚至为了追赶时髦,迎合热点,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哲学观点生搬硬套过来,结果往往给读者以如坠云雾,不知所云之感。恰如某学者所忧虑的:“当下的教育理论话语,夹杂着一些‘新’的概念与命题,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仍然不过是哲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幽灵’。在当今的学术场域及学科架构中,就理论地位而言,哲学及社会科学的理论似乎要高于教育学理论。”[5]在笔者看来,如果仅仅将教育哲学定位为“用哲学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单纯把哲学观点作以教育学的演绎,或者将教育与哲学机械“捆绑”式的研究观念极易导致研究视野的狭窄和短浅,从而束缚教育哲学自身的建设性和持续性发展。究其原因有二:第一,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之下进行的,只不过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因而没有必要再重复强调教育哲学是“用哲学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第二,如果将教育哲学定位于哲学理论在教育现象中的应用,为教育研究提供预设前提,这样的做法最大的弊端是可能导致“原则在先”。它内在地包含一个假设:哲学的命题具有“先在”的正确性,变化的只是应用领域的不同。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育与其他学科结合如哲学而生成的新学科,并不是直接的演绎关系,哲学命题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教育理论命题的正确性。”[6](P9)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教育哲学划归到教育学学科体系中,又极易产生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关系理解上的疑惑,具体表现为教育哲学与其母学科——教育学,与其平行学科——教育原理、教育史(尤其是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等相互混淆、内容严重重复的问题。为了躲避对哲学的过分依附性,教育哲学在竭力联系教育实践,挖掘教育问题的同时,又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失去了“哲学性”或者“哲学味道”。难怪有学者慨叹:“现在的教育哲学‘哲学’味还不够浓,因而在今后要加强教育哲学与哲学甚至其他学科的‘对话’。”[7]因此,只有深入变革此类观念,我们才能更为理性地继承哲学的理论遗产,并为教育哲学的研究准备一个可靠的基本前提,进而重新理解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教育问题的实质。
综归以上探讨,我们得出关于教育哲学学科属性的相对科学的定位:教育哲学是应用哲学与理论教育学双重属性的辩证统一,是两门学科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产生的,其性质是介于哲学和教育学之间并兼备二者属性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它一边连接着哲学,另一边则又必然连接着教育学,这种关联哲学与教育学的“双边性”,决定着它既属于应用哲学范畴,同时又属于教育学的高端学理范畴。笔者认为,只有这样的属性定位,才更符合教育哲学本身的理论诉求。所以,应坚决摒弃一味强调归属于哲学或者教育学的“单边性”的片面化思维模式,大力加强一种“理论贯通性”。这里所说的“理论贯通性”,不仅意指教育哲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同时还应当满足对于教育学领域中诸多“平行”关系学科的理论贯通,从而使教育哲学学科内的哲学思维、教育思维得以全面地体现和贯彻,这也是教育哲学摆脱目前浅层次的贫困、迂回状态,进而朝着更为丰厚、坚实的学理化、哲理化方向成熟迈进的必然需要。尤其应明确的是,教育哲学并不是哲学原理的简单移植和推广,不是外在于教育学的先验原则的罗列,而是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其目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形成一种关于教育的确定性、普遍性知识,而是以人的生活世界中所呈现出的教育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鼓励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帮助人们透过纷繁的教育现象认识其背后深藏的理论与现实关怀。教育哲学的内容和体系既不能过于哲学化,也不能过于教育学化,而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形成教育哲学特定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理性,教育哲学指导人们不断从现象趋向本质,从个别趋向一般,从现存趋向应当,从异化趋向合理。教育学科双重属性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哲学和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在二者动态、交叉的综合层面上,确立自身的研究方向,前瞻性地指导教育实践活动,推动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困境二:研究对象“泛化”、“外向化”问题严重,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
众所周知,一门学科能否自立于科学体系之中,能否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教育哲学,不论将它理解为人类就特定教育问题而展开的智力活动,还是将它作为人类对教育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它的基本任务或者功能无疑应紧紧围绕“教育是什么”这个本源性问题展开。然而,这一基本任务的完成,也并非易事。即便教育哲学能够提供一个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争议较少的关于教育的定义,我们也不能乐观地认为教育哲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教育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教育的表层现象世界的梳理,还应该是对教育的根源世界的揭示,更应该是对教育的意义世界的构建。但就目前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却令人堪忧。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研究对象“泛化”问题 当下有相当数量的学者高估教育哲学的价值和作用,过分夸大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将本属于哲学本体论的问题以及教育学原理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问题都塞到教育哲学中,贪多求大,追求所谓完整性、系统性,甚至将一般性教育思想误作教育哲学思想妄加评判,教育哲学俨然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教育大全”。这种做法既降低了教育哲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危及其学科地位的合法性。笔者认为,教育哲学必须首先能够自我澄清针对的对象“是”什么,“不是”什么,自己的独特研究范畴究竟在何处,从而确证自身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的真切性。
2.研究对象“外向化”问题 纵观目前教育哲学的研究现状,基本上以介绍、阐释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思想为主,解析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成果则数量较少,大多混杂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著作里,定位并不准确、鲜明。诚然,西方教育哲学资源对中国教育哲学研究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但教育哲学研究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综合的领域,忽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对当代教育哲学的积极意义,是对中国教育哲学宝贵历史财富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将造成“个性化”教育哲学理论的难产。这也是中国教育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路单一、视野窒碍、重复投入等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况且,还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众多教育哲学思想产生的渊源、教育哲学研究主体的学术背景各异等诸多复杂性影响因素,极易产生水土不服、对接不上、产量不多、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在学习西方优秀教育哲学思想的同时,我们决不应忽视本国教育的客观状况。只有正确处理好“外向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凸显中国教育哲学的“中国”内涵,才能使研究对象更加丰富、现实、有特色、有个性,形成中国教育哲学民族化、国际化的气质品相。
那么,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如何圈定教育哲学的研究域限?笔者认为,只有通过“本体论”问题的追问才能实现人对于其生存的教育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并为更高层面的理想性存在状态指示方向。教育哲学必须着力研究本体与基础问题,将厘清教育哲学的研究范围、对象、层次、方法等作为首要目的,明晰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原理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域限,探寻自身独特的价值、功能与作用。教育哲学追询的问题不仅关乎当下的教育生活,而且是对人的理想性生存状态、样式的期许。如此具有规范性、指示性的期许可以被称为是教育哲学的“本体论”承诺。教育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并不针对具体某个教育现象,也不针对具体的个别的某个教育者或受教育者,它具有前定性、预设性、普遍性、永恒性。正如黄济教授所言,教育哲学是“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8](P16)它重新厘定了哲学与智慧、教育与人生的关系,使教育从知识传承的认识论转向了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探求,并与哲学的本体论相联系,从而实现了对“教育—人生”问题的全新阐释。王坤庆教授指出:“在现代教育哲学中,人们最大的分歧恐怕是在教育目的观、教育价值观等一系列根本的教育问题上。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才?是受过教育、掌握系统知识、受过专门训练、具有良好道德精神面貌的人,还是透彻理解生活、具有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的人?实际上,这既是教育目的、教育价值的选择问题,也是教育哲学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在这些根本问题的引导下,人们试图重新认识教育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教学’、‘训练’、‘陶冶’、‘师生关系’、‘德行’、‘生长’、‘发展’等。”[9](P90)
笔者认为,教育哲学的本体性问题与逻辑主线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层面:
在哲学层面,教育哲学立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形上追求,它内在地关注人性、人权、历史、现实与未来,并浸润着哲学所特有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它的本体论问题是“人·教育·思维”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其逻辑性核心命题是:第一,人是什么?人类生活为什么需要教育?教育对个体的生命延展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二,是否存在教育的共同理想图景?理想的教育何以可能?人的全面发展理念蕴含着什么样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教育在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之间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第三,人能认识世界和自身吗?人思维能力的提高与教育有何关联?教育着眼于扩展人的知识还是提升人的智慧?等等。
在生活层面,教育哲学反对近代理性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传统,反对将人的教育问题仅仅纳入到认识论领域,而是强调深层次地追问人的存在,并代之以人的生成意义构架,从而具有存在论的表述特征。它真挚地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存在价值与发展趋向,既关注个体的生活,也谋求社会群体的相互依存和团结。基于此,教育哲学生活层面的本体论问题是要厘清“生存·教育·存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逻辑性核心命题是:第一,人的“生存”与“存在”有何“质”的区分?哲学为人的日常生活所必需吗?哲学所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导具有怎样的实际价值?第二,教育的目的究竟是指向人的“生存”还是“存在”?教育是人“存在”的必要途径吗?第三,教育如何关涉人的美好生活,从而使人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等等。
总而言之,教育哲学只有明确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并沿循特定的逻辑主线,才能在保持自身“个性化”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的同时,为进一步拓展更广阔的研究空间提供可能性。
困境三:与教育实践对接不利,难以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导力”
英国教育家卡尔认为:“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做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10](P559)
然而,教育哲学作为指导教育实践的“思维图式”之一,却在当今的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中面临边缘化的危险,它所探讨的课题似乎越来越与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无缘,更难谈及对当下的教育实践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导力”。众多研究者单纯追求教育哲学的形上性、超然性,游离于生动活泼的教育生活世界之外,关于教育实践的思考,已经沦为教育理论思考的附属物、陪衬物,无法真正反映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呼声。我们认为,所谓“理论指导力”不仅应当是指它对于国家宏观教育政策、教育法规的指导能力,而且还应表现为对具体教育实践的强有力的引导、调控、协调能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似乎并非是教育哲学的直接任务,但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评析,以确定其正确与否及其可行性如何,则是教育哲学应有之义。教育哲学应当从‘象牙塔’里走出来,面向实际,为回答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服务。”[11]笔者认为,教育哲学只有生存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才能获得自身发展与成熟的力量。而若想提升教育哲学的“理论指导力”,可以尝试加强以下两大联盟的沟通:
1.教育哲学研究者与哲学研究者的联盟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进步的主要途径是杂交而专业化,大多数专家都并不处于所谓的学科的核心而是在外延地带,与其他学科的专家保持者接触。他们在边境地区又借又贷。他们是杂交的专家学者。”[12]积极加强与哲学研究者的联盟,是教育哲学向深广发展尤其是朝着学理化、哲理化方向提升的必然需要,是打通教育哲学与哲学的学科阻隔状态、形成二者良性互动机制的必然需要,也是促进两个学科研究者思想交往、融合和升华的必然需要。
“教育哲学家没有理由要像胡塞尔创立现象学那样从事于技术现象学,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为心理现象学家所熟知的办法。我们着手研究像希望、信任或信念之类的事物并且系统地对这些术语使用的场景加以区分,以便我们能够把握要研究的事物或者经历这一事物的主体的本质或基本特征。”[13](P78)哲学的基本品质是批判,但“价值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他者的单纯否定与驳斥,它更应是一种立足于自身发展的价值意义上的“解蔽”与“超越”。它激发人思维的自主意识、怀疑意识和创新能力,从而实现哲学理论的普遍性与特定教育问题的特殊性的具体统一,主体价值目标与客体运动规律的具体统一以及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具体统一。通过与哲学研究者的交流对话,能为教育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基础与契机,不断激发研究主体的创新勇气与自我超越意识,在坚守自己教育阵地的同时,秉持理性批判的态度,以借鉴性而非移植性吸收为圭臬,来提升对教育的“思考力”和创新能力,开辟教育哲学发展的新空间。
2.教育哲学研究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联盟理论来源于实践,归根结底又要回到实践中去发挥其“理论指导力”。教育哲学研究者只有脚踩理论与实践这两艘船,才不会蜕变为实践的“应声虫”,被实践界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才能使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升华为动态的行动指南,从而才会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以杜威为例,诺丁斯指出,杜威在探讨教育问题时,“总是从可被观察和反思的物体和事件开始:儿童的活动、睿智的行动的作品、兴趣对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在民主的背景中富于创造力的个性品质的发展、模仿背后可观察到的(或者至少可容易推断出的)动机因素。杜威认为现实主义者的、理念主义者的和实用主义者的等形容词所蕴含的系统的立场阻碍了人们对于实际事务的清晰思考。”[13](P50)然而,在目前的教育哲学研究群体中,却出现了一种不良“分级”的倾向,即以自身学科“形而上”特征为自傲的资本,将教育实践活动打上“形而下”的标签,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充满理性思辨意味可以凌驾于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之上的“科学之科学”,进而对后者采取轻视甚至贬低态度。显然,这种态度对于教育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其实,教育哲学与教育实践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如杜威所言:“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而“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14](P347)教育哲学指导实践的方式是通过改变思维模式的形式完成的,它内化于教育实践者的行动中,为教育实践纠偏、指向。教育哲学研究者须在关注“纯粹学术问题”的同时,紧紧依托教育实践部门,走出书斋,走进课堂,将更多目光投向教育实践活动中存在和发生的现实问题,与教育实践工作者形成亲密团结的研究联盟或共同体,及时给出理论解释和方法建议并得到相应的反馈信息,从而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只有如此,才不至于使教育哲学研究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同理,教育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也应摒弃对“形而上”教育哲学的拒斥态度,积极提升自身的哲学理论素养,力争找到与教育哲学研究者平等对话的机制,为教育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完善输送新鲜营养,使二者均获得健康、和谐发展,而这无疑有待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关注与努力。
以上,我们对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主要面临的三个基本理论困境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三者并不是相互独立与彼此分离的,而是有着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困境一,着力于揭示和批判教育哲学的学科属性定位的“单边性”与“捆绑式”思维方式,强调了教育哲学的“理论贯通”的基本学科特性与研究原则;困境二,重在分析当前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泛化”、“外向化”问题,并围绕“本体论”诉求进一步明晰了教育哲学研究的逻辑主线,并将学术研究的境界提升至对“教育—人生”之大课题的全新阐释上;困境三,则通过对当下教育哲学研究领域中一味追求形上玄思、严重脱离生活实践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试图为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天然”鸿沟开辟出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
收稿日期:2010-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