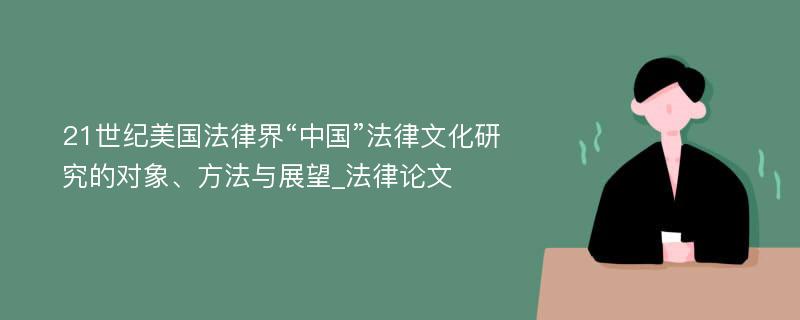
21世纪美国法学界“中国”法律文化研究评析:对象、方法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国法论文,中国论文,前景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3)02-0014-08
自中国传统文化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向西方传播以来,历经百余年,已在西方英语世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汉学研究,也产生了一批如李约瑟、费正清、史华慈等西方汉学大家。在英语语系西方汉学传统中,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也自是具有一席之地。如1810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副使司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之子小司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即将《大清律例》译成英文出版[1]。然而,早期中国法律文献的英译多为处理现实中的中西法律纠纷,以功利性为主旨,文化性的研究还远未形成声势,但此时也逐渐出现对中国法律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努力[2]。此种现象自民国有所转变[3],像庞德这样与中国较有渊源的学者,业已有意识地提出西方对中国法律的研究应以“比较法和历史为基础”此等真知灼见[4]。当代以来,西方英语世界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中国法律的文章屡见不鲜①。即使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学界依然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中国法研究[5],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杰罗姆·柯恩(Jerome A.Cohen)、安守廉(William P.Alford)等至今依然活跃于美国的中国法研究领域。
在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代表的译注丛书使国内学界对西方的汉学研究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在法学方面即包括中国法专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与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同时期,《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这本收录了以美国学界中国传统法律研究的译文集,成为中国法律学者案头间管窥异域中国传统法律研究方法、文献和论题的重要参考。该译文集《编者序言》即指出该文集的对象正是“对于中国法律史具有共同的学术兴趣的学者间正在进行的国际对话”。诚然,相互平等、理解和尊重才能达至对话,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中西文化交流乃至碰撞,却难寻此种对话的前提与成果。20世纪最后20年对中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崛起也好、发展也罢,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在世界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在此历史阶段系统研究同时期美国学者异域眼光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相互了解,互通有无,更能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断为世界所认知。
时针飞转,转眼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过去,在学界逐渐接触并开启中美乃至中西法学研究特别是法律文化交流30年之后,以美国学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是否气象一新,对中国传统法律研究的关注点落在何处,值得我国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分析。
一、研究对象的获取方法与数据
本文以“中国”(China/Chinese)为关键字,以2000年至2012年为时间段,从Heinonline法律期刊数据库中遴选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以“中国”为关键字进行搜索,不仅仅将论文限定于中国法律研究的专题范围内,更能体现外国学者将“法律”与“中国”这两个概念相关联与对应时,其学术关注点定位在何处,从而明了美国法学界中国法律问题研究的热点问题。
毋庸置疑,若要对美国法学界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现状有一个巨细无遗的系统了解,将这十几年间所发表的中国传统法律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甚或书评“一网打尽”,逐一分析梳理,抽象出其规律,总结出其特点,自是一个至臻完善的理想结果。本文则试图通过以点概面的努力,通过分析此期间美国法学期刊中所刊载的以中国传统法律为主题的论文,通过一个侧面反映21世纪以来美国学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状。
按照上述思路,自2000年至2012年间,以“China”为主题关键字搜索到的论文共计为2698篇,以“Chinese”为主题关键字搜索到的论文数目文共计为802篇。其中,美国学者②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③的文章共计15篇④。
二、数量分析中的学术史简析
从数量上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成果所占美国学界中国法研究的比重并不大⑤,算不上美国中国法研究的一个重镇。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美国法学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却几乎未曾中断,显示其强韧的生命力。美国学者陆思礼(Stanley B.Lubman)教授将美国中国法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1960年代:探索月球的另一面(Exploring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on);1970年代:开拓前沿(Exploring the Frontier)和1980年—2000年:开垦未知的森林(Exploring the Uncharted Forest)。在陆思礼教授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法律是“一种可被称作‘政治—法律’型的法律体系,因此研究几乎无从下手”[6]。鉴于当时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民事法律作为研究对象,西方法学界对当时中国现行法律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集中于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描述性(descriptire)研究,即使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美国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研究对象。[7]
诚如陆思礼教授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一篇回顾西方中国法研究的文章中所预言的那样,“对中国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法律制度与中国社会的互动这样一个话题,留给富有耐心的西方学生洞悉中国法律的希望。”[8]随着中美建交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此种期望变成了现实。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法学界发表的以中国为主题的论文何止千计,虽绝大多数都实用主义的关注经世致用的当代部门法,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也顽强地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逐渐从经济层面走向文化层面,从商品输出逐步跨越到文化输出,何尝不会留给有耐心的学者更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期望。
三、对“中国法治”主题的关注及其原因分析
关于从传统法律文化角度论述“法治”(rule of law)问题与中国的论文几乎占了总体研究成果的三成,这构成了最近十几年美国法学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显著区别于20世纪中国传统法律问题的研究范畴。[9]与此相呼应,《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所收录的12篇论文中,仅有一篇关于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法治问题的论著。在Heinonline数据库中,1980年—1999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国法治问题的论文虽有十余篇,从传统法律文化角度展开论述者凤毛麟角,其主要内容多为当代中国如何实行法治[10],并且多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实法律问题挂钩,显示出对中国法律问题研究极强的现实性⑥。而这种现实性其实恰可解释为何21世纪以来美国法学界重视以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研究中国的法治问题。
美国学者麦凯拉·塔克(Micaela Tucker)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热衷于法治问题做出了如下的解释:“真相其实是,以法治为目标的改革与全球化的政治进程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关于实行法治的努力就是西方试图解决因国与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而伴生的希望与焦虑。”[11]显然,在全球化的经济与政治浪潮中,采取统一的法律标准与术语,减少法律壁垒,最终获益的无疑是逐利的西方国际资本。因此,西方一直试图以法治这一纯粹的西方概念体系为标准建立一套通用的法律准则。在这方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多种关于法治的概念,目的就是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边进行投资,一边培育出能够孕育法治事业的沃土”[12]。
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至少是在经济领域建立了能与西方法律制度相容的“字面上”的法治,因而使在法律制度层面分析法治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从前。西方关于中国法治问题的研究由此则走向了“历史深处的忧虑”:“当前对全球化的焦虑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谁的世界观将会占上风。推行法治的努力毫无疑问是一种保障西方世界观将会占上风的努力。确实,法治的美国支持者完全有焦虑的理由。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弹性以及其长达5000年的历史,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西方被中国所融和。”[13]
目前的图景是,中国作为一个西方视野中的“他者”正在难以阻挡的试图分享制定规则的权力,虽然现阶段还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但中国毋庸置疑的巨大文化潜力却能够使西方认真思索,中国法律文化是否与西方所推行的以法治为标签的法制体系南辕北辙,中国法律文化是否不仅能拒斥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法治,更能取而代之。这些问题只有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才能够得出答案。
四、学术与教育背景影响下的研究范式分析
因选取以法律期刊为主的数据库,因此文章主要出自美国法学学者之手⑦,且多为20世纪90年代获得法学学位并开始其教育生涯,显示美国法学界中青年学者中出现了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新生力量,如埃里克·奥茨(Eric W.Orts),马克·莫达克-特鲁然(Mark C.Modak-Truran),提姆·鲁斯科拉(Teemu Ruskola)等。这些法学学者虽然从事甚至将主要学术精力用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之中,但依然讲授传统意义上美国职业法学教育的主要课程,如合同法、宪法以及货物销售法等。因此,在涉及中国传统法律问题的研究中,其视角多是法学的,如对中国传统法治问题的探寻其着眼点则是法治这一典型的法学理论概念体系,而提姆·鲁斯科拉教授所著的《概念化公司与亲属: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法与发展理论》一文则更具代表性。其采取比较法的分析方式,通过公司法概念与理论的研究,从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及其产生的家族企业(clan corporation)中找寻中美公司之间的共同之处,在法律多元化的基础之上探讨中美公司法与家庭法等在全球化影响下如何发展[14]。因此,美国法学学者在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问题时,容易倾向于从当代法律问题出发,而这些问题往往是西方法学体系中的问题,中国传统更多的作为一种法学体系下异域的对比和解释。
然而,如果将眼光投射于整个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则呈现出多种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的学者各据所长,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角度以及研究进路各具特色,不断丰富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成果。比如历史学教授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以小说家的笔触,采取一种“大叙事”的格局透过一个巫术大案(这种案件本身的神秘性与异域性即是吸引西方关注的极好素材)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透过不同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从而以一个地方性案件勾勒出了一部中国清代乾隆时期的社会史[15]。黄宗智教授所推动的“新法律史”运动则以对中国古代档案特别是清代档案的娴熟利用,不再局限于对古代中国典章制度、律令体系的文本化研究,促使法律史的对象从纸面上的法向现实中的法转向,强调对“实践”的重视,将法律史与文化史和经济史相结合,勾画出一幅置身于社会文化史之中的法律图景,展现了历史社会法学的面目[16]。上述研究方法在西方历史研究包括法律史研究中的运用并不鲜见。黄宗智教授的研究透出法国年鉴学派开辟的总体史研究方式的痕迹⑧。而与《叫魂》相似,美国法律学者南希·沃罗奇(Nancy Woloch)围绕穆勒诉俄勒冈(Muller v.Oregon)一案[17],从宪法史直至社会史深刻刻画了美国19世纪80年代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法律全貌;而史坦利·库特勒(Stanley I.Kutler)教授则通过描述查理桥(Charles River Bridge v.Warten Bridge)一案[18]的历史过程,围绕该案剖析了美国18世纪中期关于合同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法律取舍的历史背景。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则能发现风格迥异的中国传统法律研究方法,“日本学者史料周详、论证缜密的风格,美国学者新颖活泼、视野宽阔的特色,法国学者老汉学的遗绪”,这在《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19]。该书中各国学者在研究中所运用的分析模式引人深思,如以“时空场”:时间—空间分析模式研究中国法律史这一由中国历史(该书中具体指清代)为特定时间延续的时间轴与中国这一地域概念上的空间轴共同绘制出的特定对象,社会法学中“关系”概念下如何运用“人的关系”提升到法律世界的宏观政策层面以及包括西方中国法律史研究在内的“边缘”与“中心”的基本立场问题。[20]
然而,问题也由此产生。这些研究方法与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其意义自不待言,但是他们本身也构成了一种“他者”:首先他们是作为一种异域的研究被引入;其次,这也是法学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进路。无可否认,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何况法律史本身即包含历史、法律并能轻易容纳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史学和社会学等而言,法律史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研究素材,套用其既存的研究方法,只是研究对象与法律挂上了钩,并能不断利用新方法对既有的老问题进行新探索,产生新的研究成果,能够不断为法学研究提供极好的借鉴与启发。如果剥离那些新鲜而又稍显陌生的概念,逻辑严密而又有些繁琐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各种“ism”的相互争鸣,法律文化问题终归还要回到法律问题的范畴,在法学中开花结果,既利用不断推陈出新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在尘埃落定后提供具有更多法学意义上的解释。如果将法律或曰法学看成是一个人,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等看成另外的人,法学之外其他学科对法学包括对法律文化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法律这个人与人群中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关系等问题;而法学研究之于法学这个拟制的人,则更像是医学之对于人,研究的是法学之人机体的内在机理。因此,即使是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与概念,依然能够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法学观点,例如,比较法学中的“法系”概念的产生;以法系概念为基础,武树臣教授通过对秦“改法为律”的分析,利用“法律样式”中所包含的判例法、成文法、混合法这些典型的法律概念,将中国古代法归为混合法的类型。[21]鉴于西方法律体系与法律话语的不可逆性,也产生了以西方现代法学体系和法律语言诠释传统法律文化的努力,为法律史研究增添了更多法学色彩,为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增加了一种研究路径。⑨总之,不同研究视角方法下的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等,均能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在不同学科内开花结果,而相互间的借鉴,博采众长,特别是逐渐摸索出中国式的法律文化研究模式,则能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精彩纷呈。
其实,以法律史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研究自身先天的带有跨学科的特征,这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天然得比多数部门法研究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多学科研究手段的运用无疑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的研究局面,随着不同核心观点的逐步确立,从而有可能在中国法律文化领域逐步产生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学派,而这正能不断确保中西之间平等的对话。
五、是否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分析
西方汉学研究包括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往往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分析中国这个处于边缘的“他者”。西方中心主义曾在美国汉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Cohen)指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存在三种方法:“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传统—现代”(tradition-modernity)、“帝国主义”(imperialism),而这三种方法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Western-centric)。⑩此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这一西文著作引入的过程中往往弥漫着一种本土化的东方主义态度,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只是一个‘他者’,在分析中依旧显露出所谓西方普世性法律解释方式的话语霸权。而事实上,如果其意图仅仅是为了说明中国自成体系的法律制度本身,则始终无法走出为西方话语做‘注脚’的地位。对‘法的本土资源’的探寻依旧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遂而,由材料出发,并进而用理论加以必要而合理的解释,就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究。而如何找到合理兼容中国本土思路与西方研究路径的文本,就变得颇富吸引力”[22]。确实,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无异于透过希腊人的眼睛看中国。因此,西方学界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局限,如柯文教授指出,对于中国的研究应该以中国为出发点,将研究着眼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23]。我们还要看到,尽管“欧洲的分析范畴对西方人搞明白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性既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充分的”,但无可否认,源于欧洲的西方文化体系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世界,并通过“西学东渐”促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由于“欧洲思想已经成为每个人的遗产并影响着每个人”,在西方对东方研究中并不是要完全将西方思想置之脑后。西方研究东方法律的做法不是完全抛弃欧洲—美国相延续的法律理念,而是将这种法律理念和范畴当成一种地方性的资源[24]。
美国学者在21世纪以来论述中国主题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问题中,不断显示出将西方理念“本地化”的一种立场。例如,“任何地方的法律文化均是本地化的”[25],西方则“需要探寻能够与中国背景相适应的其他的法治概念”[26]。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法律文化的理解和对法治问题的现实解读,对于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直颇受诟病的负面现象——“关系”及其与“法治”的关系也催生了新的阐释:“西方要探索为什么法治的推崇者需要避免通过简单的翻译‘关系’这个词语来更好地理解它。法治不是解决中国法制挑战的灵丹妙药。(中西之间的)平衡将会取代西方的霸权成为法治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全球性影响中生存下来的关键。”[27]
然而,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西方学者毕竟生长于西方话语体系之下,假设其完全抛开西方立场与思维,则只是长着西方面孔的中国人而已。因此,即使采取“中国中心观”的美国学者也还是西方人,只不过是在“中国的西方人”(Westerner in China)。无论美国学者采取西方中心或是中国中心的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其分析方式多半是西方的。另一方面,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即使是其语言本身,在较长时期内将会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强势思想,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表述成为西方的现代性。在法学领域,似乎还难以改变由普通法和大陆法所统治的法学体系。因此,西方学者难以完全放弃其西方立场,特别是西方预设的以现代性等为代表的评判前提,在西方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难免会出现削足适履,即以西方理论之履削中国问题之足。
但是,随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加深,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西方对中国的分析中增添了更多的平等与尊重(现阶段更多的是重视大于尊重),逐渐改变完全以西方理论自上而下的审视中国传统,以西方之现代解构中国之落后的态度。因此,出现了一种程度上大大削弱和妥协的“西方中心观”的体现(认为西方完全放弃这种价值观还为时过早)。例如,法家思想传统中被认为是残酷与负面的,但肯尼斯·温斯顿(Kenneth Winston)教授所著的《中国法家思想的内在道德》一文,以朗·富勒所建立的法治八要素为依据,详细论述韩非的法律思想与形式主义的西方法治的契合,从而指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能一味地进行抛弃与批评。[28]
在对法治问题的论述中,美国学者虽依然将“法治”这一“难以理解的、复杂的”[29]“西方概念”[30]。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论预设,娴熟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但已非简单地将中国问题套到西方的框框之中,承认法治概念的局限性,承认与理解西方与中国的差异(从而最大限度上避免了不平等性),探寻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融性,只是这种交融性依然建立在西方的理念与分析基础之上。
以马克·莫达克-特鲁然教授对中国法治问题的分析为例。在他看来,法治本身是“极易受文化因素影响的一个概念”[31]。“向(美国之外的)国家推行法治,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西方制定的法治的前提条件是否与其他文化存在的先决条件共存”[32]。更何况即使在西方,“学者们在法治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式的理想这一观点达成了一致,但却在艰难的确立其核心内容并在识别为数不少的不同法治种类”[32]。在面临这种困境,特别是解释法治如何能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互协调时,马克·莫达克-特鲁然教授的解决方案所依赖的依然是西方的思想支持。他利用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过程哲学中“终极的美”(telos of beauty)即是“存在于多样性中的同一”(unity-in-diversity)这一观点,指出与传统西方自然法传统下的法治理想不同,“过程哲学下的自然法所支持建立的法治概念,能够兼顾类似中美差别这样的文化差异”[33]。这是因为,“终极的美这一理念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每个社会独特的处境将会决定哪种情势能够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中将终极的美达至极致。……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把如传统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所指出的那些一成不变的实体权利和情势收入囊中。因此,必须不断修正实体权利和法规,从而促使当下社会环境能够达到的最为理想的社会完善性得以实现”[34]。虽然马克·莫达克-特鲁然教授未对中国法治到底是什么做出结论(鉴于法治概念本身存在的争议,也难以做出这一结论),但是这种拒绝将法治的内容固定化,特别是西方化,而把法治本身看成是有差异的发展过程,并没有简单将中国的法治作为西方的一个“他者”,反而为中国法治走出自己的特色并为世界所接受提出了无限的可能。
结语: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走出去”与现实关怀
综上所述,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学者特别是法学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律问题中具有现实关怀的研究视角,典型代表即是将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等当代问题相结合;以西方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中国传统,并在不断地弱化西方中心观的分析立场。
美国学者对中国和美国的理解均在不断地修正之中,西方不再是一贯正确的唯一标准,即使在西方视角下,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被越来越被发现蕴含着更多的正当性,这也同时出现了一个机遇与挑战:中国学者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更多地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输出到西方,使西方更为透彻和不带偏见地了解中国传统,甚至有一天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思想是解决西方问题的一条道路。
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终要“走出去”。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方面,中国学者的优势自不待言(11)。在文化对话与交流逐渐成为趋势的今天,单向的从西到东的文化运行轨迹显然无法适应中国影响不断增大的现实,中西之间双向交流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愈发凸显。
另一方面,美国学者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其着眼点在当代与比较法的视野,希望能从传统中解答当代问题,因为“从历史实际的视野来看,中国今天的法律明显具有三大传统,即古代的、现代革命的和西方移植的三大传统。三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现实;三者一起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形成一个有机体,缺一便不可理解中国的现实”[35]。这也提醒我们,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不仅仅着眼过去,更可以放眼现在与将来。
期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将会呈现一种中西互动,历史思索与当下关怀兼顾的繁荣景象。
附录:2000-2012 Heinonline中国(China/Chinese)主题下美国学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论文汇总
1.Stanley B.Lubman,Study of Chines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Reflections on the Past and Concerns about the Future,Wash.U.Global Stud.L.Rev.1(2003).
2.Winston,The Internal Morality of Chinese Legalism,2005 Sing J.Legal Stud.313(2005).
3.Teemu Ruskola,Conceptualizing Corporations and Kinship:Comparative Law and Development Theory in a Chinese Perspective,52 Stan.L.Rev.1599(1999—2000).
4.Mark C.Modak-Truran,A Process Theory of Natural Law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26 Penn St.Int'l L.Rev.607(2007—2008).
5.Micaela Tucker,"Guanxi!" - "Gesundheit!" An Alternative View on the Rule of Law Panacea in China,Vt.L.Rev.689(2010—2011).
6.Eric IV.Orts,The Rule of Law in China,34 Vand.J.Transnatl.L.43 (2001)
7.Qiang Fang & Roger Des Forges,Were Chinese Rulers above the Law:Toward a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from Early Times to 1949,44 Stan.J.Int'l L.101(2008).
8.Randall Peerenboom,Let One Hundred Flowers Bloom,One Hundred Schools Contend:Debating Rule of Law in China,23 Mich.J.Int'l L.471(2001—2002)
9.John O.Haley,Law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A Framework for Analysis,27 Mich.J.Int'l L.895(2005—2006).
10.Teemu Ruskola,Law without Law,or is "Chinese Law" an Oxymoron?,11 Wm.& Mary Bill Rts.J.655(2002—2003).
11.Kevin.C.Clark,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and General Workings of Chinese Mediation Systems:What Lessons Can American Mediators Learn?,2 Pepp.Disp,Resol.L.J.117(2002).
12.Dominiek Delporte,Precedent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Agreements in Ming China(1368-1644).Insights from the " Classified Regulations of the Great Ming," Book 13,21 Law & Hist.Rev.271(2003).
13.William P.Alford & Chien-Chang Wu,Qing China and the Legal Treatment of Mental Infirmity:A Preliminary Sketch in Tribute to Professor William C.Jones,2 Wash.U.Global Stud.L.Rev.187(2003).
14.Hayden Windrow,Short History of Law,Norms,and Social Control in Imperial China,7 APLPJ 244(2006).
15.Randall Peerenboom,X-Files:Past and Present Portrayals of China's Alien Legal System,2 Wash.U.Global Stud.L.Rev.37(2003).
收稿日期:2013-01-09
注释:
①以Heinonline所收录的美国法学期刊为例,自1900—1949年期间,以“China”为标题关键字的文章为521篇,以“Chinese”为标题关键字的文章为276篇。而1950年至今,两类文章的数量则分别为5472篇和1718篇。
②这里所说的美国学者包含在美的华人学者。
③“法律文化”一词1975年由美国著名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其所著《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中提出,他所指的法律文化是指“持续不断作用于法律的社会力量(social force)”,“社会总体文化中促使社会力量有利于法律和与法律相对立的部分”,Friedman Lawrence M.The Legal System: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5:15.在弗里德曼看来,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法律问题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法律制度和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Neil J.Smelser & Paul B.Balte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M].New York:Elsevier,Pergamon Press,2001:8625.本文分析对象所指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63.具体而言,其学术成果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指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及不限于仅对我国当代各部门法进行研究之外的学术研究。
④这里未包括国内学者在国外发表的论文。
⑤作者以同样的搜索方法对Jasotr数据库进行搜索,符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文章也并不多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黄宗智教授所著的Whither Chinese Law?,发表于Modern China,Vo1.33,No.2(Apr.,2007),pp.163-194。其中文译文《中国法律的现代性?》发表于《清华法学》第10辑,2007,67-88页。
⑥在这些与中国相关的论述法治问题的文章中,涉及传统法律文化者仅为收录于《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一书中高道蕴教授(Karen Turner)所著的《中国早期的法治思想》一文(Rule of Law Ideals in Early China[J].Journal of Chinese Law,1992:1)。
⑦此处的法学学者主要是指获得法学学位者。
⑧关于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方法,参见李铁、张绪山.法国年鉴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评价[J].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1):31-35.
⑨如郭建.中国财产法史稿[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该书以大陆法物权法体系对中国传统财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台湾学者戴炎辉则以现代刑法语言与理论展开了对《唐律》的研究,参见戴炎辉.唐律通论[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陈惠馨.法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戴炎辉先生的相关研究谈起[J].法制史研究,(4):127-161.
⑩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该书译者代序——“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对美国汉学研究中曾经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做了分析。
(11)例如,台湾学者张维仁先生发表的Classical Chinese Jurisprud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一文(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2009-2010(2):207-272),突出显示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阐释的全面性和深入性。
标签:法律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法治论文; 法律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法律论文; 法治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