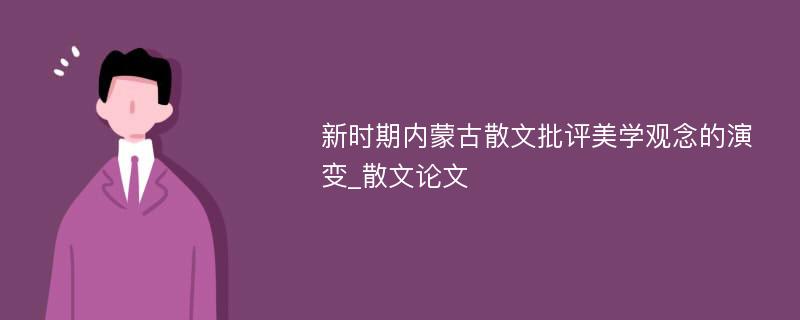
新时期内蒙古散文批评的美学观念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蒙古论文,新时期论文,美学论文,散文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0)05-0107-06
散文批评作为散文创作与散文理论的中间环节,它促动着散文的创作与散文理论的生成。进入新时期以来,内蒙古散文创作与散文理论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散文批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散文批评范式的转变直接反映并影响散文创作美学观念的转变。
纵观新时期内蒙古散文批评,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内蒙古散文批评在遵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如注重对散文内容、情感真实性评价的基础上重视散文所表现出的民族、地域特色。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内蒙古散文批评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散文批评在社会经济发展及散文创作的影响下发生了转变,不再局限于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在保持对散文真实性、民族性评价和引导的同时,开始注意到散文的审美形式批评,并在批评实践中借鉴多种西方文艺批评方法,如心理学批评、文化批评等,为散文批评打开了新的局面。
进入新时期以后,内蒙古文艺批评活动扭转“文化大革命”中文艺批评的残局日渐繁荣起来。1980年孟和博颜在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谈谈评论工作》的讲话。1981年,《民族文艺论丛》(汉文)、《金钥匙》(蒙文)先后创刊,有了专门的评论园地。1984年,内蒙古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成立,对文艺批评队伍的现状做了调查,接着创办了全国公开发行的《民族文艺报》。由此,文艺批评活动在内蒙古空前高涨,理论界对于文艺批评原则和批评标准的探讨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内蒙古文学批评重要的时代表征。1981年奎曾撰文指出,文艺批评要从题材内容、思想倾向、社会功用和效果等方面来考虑作品的政治价值,具体指出了文艺批评的评价原则。此后,许多理论家、评论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相似的探讨。随同内蒙古文艺批评的总态势,散文批评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此时期内蒙古散文批评主要呈现出以下两点特征:
(一)坚持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强调真实性美学原则
新时期初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内蒙古散文批评主要是秉承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王先霈在《文学理论批评原理》一书中介绍说:“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1](7)体现在散文批评中,就是注重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强调散文要纪实,要表现真实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并注重对散文作品所引起的社会功用和效果的分析评价。在众多的文学创作模式中,散文是一种重在写实、篇幅短小、不拘格律、形式多样,反映现实生活及创作主体情感的文学样式,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艺术特征。散文的文体特点决定了真实是散文的灵魂,著名作家周立波在论述散文特点时曾说:“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家们要依靠旅行访问、调查研究来积蓄丰富的素材;要把事件的经过、人物的真容、场地的实景审查清楚了,然后才能提笔伸纸。散文特写绝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2](1)在新时期散文批评的第一阶段,真实性是散文批评的首要标准,美学观念的第一要义,《内蒙古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创作素描》一文中引用刘锡庆的评语说明,20世纪80年代散文创作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是这个时代忠实可信的记录,是这个时代浸透真情的讴歌。”[3]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内蒙古散文创作非常活跃。随着散文创作的繁荣,这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散文评论文章,如《真切、真实、真挚——读散文特写集〈晚餐〉》《真实而有意境——评〈大漠情思〉的艺术特色》《李全喜散文的本土意义——〈哲里木散记〉漫评》,等等。散文批评主要是以真实性作为衡量的标准,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从散文文本的内容、题材、情感、思想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肯定了内蒙古散文作家对于生活和情感细腻生动的艺术体验。如贾融在评价周彦文的散文集《大漠情思》(1983年第8期《草原》)时,就将真实作为散文创作的灵魂所在,“《大漠情思》最突出的特点是真实。我觉得,真实而有意境,正是中国散文的传统,也是中国散文能立足于世界文坛之所在。”“在谈论《大漠情思》这部集子时,有的同志认为,周彦文的散文有意境,但太实。我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4]由此可见,贾融在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同时,结合散文文体自身的特点,重视散文创造中的真实性,并将其提升到散文灵魂的地位。纪实是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模式,也是散文真实性的直接体现。在《李全喜散文的本土意义——〈哲里木散记〉漫评》一文中,贾羽着重评论并肯定了李全喜散文的纪实性,文中引用玛拉沁夫序中评语,“他的作品纪实性强,报告文体多,也是由于这种直观感受激发他创作热情的缘故。”[5]他在分析李全喜散文视角不断转换的特征时也一再突出了作品的真实性。比如他在批评中写到“所谓‘普通百姓的视角’是作者对于家乡的时常都有可能激动的现象能够客观如实的反映。李全喜站在一位草原儿子的视角上,真实的记录了故乡的一切。”“如果从作品的真实性价值、艺术价值与民族性价值这一意义上来看,李全喜作品的价值是较全面的。”[5]散文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门类,它的真实性不仅体现在对于客观生活的纪实性表述上,也体现在创作主体情感的真实性上。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有一句名言:“艺术就是感情”情感性是散文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刘英建的评论文章《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歌——评高文修的散文集〈只有香如故〉》时指出:“散文写作,离不开感情;没有感情的散文,会味同嚼蜡。高文修深悟此道,加上本身感情的丰富,就形成了他的散文在‘神’不散方面的一大特色。”[6]情感的真实成为批评家评论散文真实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正如锦贻在批评文章《真切、真实、真挚——读散文特写集〈晚餐〉》中所说:“情意深、境界高,言旨兼美,文情并茂,也是这本散文特写集的一个特征。发自内心的真切感情是造作不出来的。源于生活的真实画面是臆不出的。基于人民的真挚语言是杜撰不了的。这正是我读这本集子感受最深之处。”[7]此外,在《散文创作真实性刍议》中,评者明确指出现实性、真实性是散文创作的生存发展之路,指责“也有的散文作品现实性不强,题材面不够广泛,回忆性文章多,山水游记多,风物掌故多,而且写过去的多,与当前的现实生活无关宏旨,不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这样的作品缺乏生命力。我们应该摒弃这样的创作方式,努力使散文创作具有真情实感。”[8]从中可以看出,此阶段批评者大多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要求散文创作要注意其内容的真实性,这体现了以真为美的散文美学观念。受这一观念的指引,散文创作的地域民族特色同样为批评家格外青睐,在他们看来,内蒙古散文的真实性与其民族性密不可分。
(二)彰显地域性民族性特征,追求民族化美学风格
关于内蒙古文艺民族性的讨论早在建国初就已经在内蒙古文坛展开。1950年至1951年,《内蒙古日报》和《内蒙古文艺》连续发表文章并召开座谈会,讨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由此成为内蒙古文学批评界一个热门话题不断延续。1962年7月奎曾在《草原》上发表《内蒙古文学的民族特点与地区特点初探》,形成了文艺的民族特征的又一次讨论。文艺民族性问题的探讨被文化大革命中断后,20世纪80年代又成为内蒙古文坛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新时期的蒙古文艺批评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对文艺民族性坚持不懈的追求。这一地域性文艺批评标志折射出内蒙古文艺创作的品貌,与内蒙古文艺的审美形态有着内在的统一性。[9]张锦贻在《从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谈起——文艺民族化问题漫谈之一》中也指出了文艺作品的民族化问题:“文艺作品是否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主要的根本的,还在于它的内容是否反映了民族的生活,民族的性格、心理、感情、品德、精神,以及风格、习惯等,有一种本民族所特有的风味。”[10]1988年,布赫在自治区第四次文代会《祝辞》中就文艺的民族特点问题再次阐明:“我们的文艺及其自然地要在总体上体现全国思想文化的共性,同时也必然在共性中体现个性,反映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再一次肯定了内蒙古文艺的民族性问题。
体现在散文批评上,批评家将民族性特征作为重要的声没标准,引导散文创作的民族性追求。比如,邢莉《闪烁着民族精神的人文景观》对苏尔塔拉图散文的题材评价时指出:“但是无论描绘什么,我们都感到他的散文创作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的衔接。不论是渗透在文章中的道德文化精神、人格价值志趣,抑或散文中的审美追求,都体现着这种久远的文化积淀。”“广袤的草原茫茫的沙漠,记载着祖先光辉业绩的历史遗迹和优美的传说,还有这子孙万代生生不息的土地,这各民族之间生死相依的纯厚情谊,都使他获得了燃烧的激情。”[11]在这里,批评家看到了民族文化作为作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深深渗透到作家的血液之中,成为其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成为其散文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李全喜散文的本土意义——〈哲里木散记〉漫评》中,贾羽特别关注到李全喜散文创作地域文化描写中表现出来的民族风格:“‘作品里展示的哲里木风貌,历史变迁以及人民的喜悦与忧伤;变革与希望确实是情浓畅述,墨重尽染。’而李全喜散文所具有的这些特色,我觉得无不来源于生他养育他的哲里木的厚爱与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全喜的散文又具有了鲜明的本土意义。”[5]对于民族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文中写到:“能够给作者带来永恒魅力的,只有草原变化无穷的风光与草原人民追求真善美的业绩。”[5]又如,在子皿的评论文章《一帧诱人的〈绿色请柬〉》中,子皿以形象的笔法分析了《绿色请柬》中对于蒙古族生活地域的自然景色、生活习俗以及民族气质的描写。在分析评价散文写作的同时,也将读者带到了草原生活的优美、新奇之中。评者认为,草原的景色、风俗、风貌的描写也为作品带来了新鲜的气息、神秘的美感以及强烈的吸引力。“正因为情之所钟,所以大草原的任何景色在作家的眼中都是那么的美。这种美无疑是融合了客观美和作家主观感受的情绪的美,所以,大草原的《晨曲》才那么美妙,大草原的《黄昏》才那么神秘。”[12]地域、民族特色是内蒙古散文创作的最大特征,特殊的地理风貌和民族气质在为内蒙古作家提供表现题材的同时也赋予了内蒙古散文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由此而成为内蒙古散文批评重要的美学标准。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语境的宽松,内蒙古散文创作与批评活动非常活跃,大量散文作品与批评文章先后涌现,散文创作与批评进入了繁荣的新阶段。但是由于批评视野相对狭窄,批评方法相对贫乏,造成散文批评模式相对单一,内蒙古散文批评还缺乏具有美学与诗学高度的评析。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以来,内蒙古散文批评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打破传统社会历史批评一统天下的模式,开始关注散文创作中的形式特征,并在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心理学批评、文化批评等批评模式,散文批评的美学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着力阐扬散文形式美学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内蒙古散文创作呈现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一些散文仍然坚持传统的创作思路,但是在形式上有了一定的新意。批评一方面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来立论,同时注意到对散文形式美的关注和阐释,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开始向审美形式批评模式转变。比如在《听阿拉善的风声诉说》中,评论者对于散文中独特的写作形式进行了评价。“《爷爷的牧场》则用小说写作的形式描写大漠生态的历史和现状,写得很细腻悲情,是作者近年来散文写作手法的一次突破,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13]散文是一种开放的文体,各种行文结构都可以在散文中出现。在惯用的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之外,评论家关注到其他艺术表现方式带给散文文体的影响。在《震撼、思考与希望》中,李廷舫指出:“但我敢肯定:刘志成肯定是唱着信天游长大的,所以他的散文行文建构,一旦用信天游做脊梁骨的时候,那篇散文里总是充满深沉而悠长的韵律,而深沉悠长的韵律里的起伏跌宕,总惹得读者情不自禁地与其共鸣。”[14]诗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根本的特征,也是文学产生永恒魅力的根本所在,散文当然不例外。文学的诗性美学特征离不开特定的形式,获得了这一美学观念的内蒙古散文除了在行文建构方面追求创新外,在写作视角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这一形式美的特征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如李晓峰在《生命存在的另一种仪式里》一文中敏锐地发现创作者借助主体对象化来审视自己和他人:“需要指出的是,在安心的散文诗中,作为诗人的安心并不总是以主体的‘我’与世界进行对话,同时,她还经常把主体对象化:……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安心如他者般审读和思考着苦难、幸福、痛苦这些人类母题,执著于‘缘’的浪漫想象。在主体对象化的过程中,安心不仅审视他人,同时也在生命的高度上,冷静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及其生命中的苦难和彷徨,这使安心的散文诗从个体生命走向人类命运,完成了由人到人类的质的飞跃。”[15]在写作视角的新颖之外,安心散文通过大量使用意象,为散文赋予了独特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当然,上述的一切,在安心的诗中都是通过具体的意象传达出来的。从诗学角度而言,安心的散文诗的意象大都是清亮而透明的,宛若晶莹柔润的碧玉,给人一种清纯明澈而又华贵雅洁的质感。”[16]多样化的写作手法为内蒙古散文创作打开了新的视野,丰富了散文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同时也促使着内蒙古散文批评向新的审美范式转变和发展,确立了散文诗性意味评价的美学观念。
(二)着力散文批评模式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散文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创作趋势,与此相携,散文批评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审美指向。心理学批评、文化批评等西方文学批评方法陆续进入内蒙古散文批评领域,开始了批评模式的变化。
对于心理学批评王先霈在《文学理论批评原理》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如是界定:“心理学批评是一种汲取心理科学的研究成果,立足于文学作为精神活动的特殊性,对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和包含的心理现象以及读者的欣赏心理进行分析的方法。”[14]
在内蒙古的散文批评实践中,评论家大多是从作者的苦难意识、宗教体验等方面进行评析。如李廷舫在评论散文家刘志成的作品时指出,作者“《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待葬的姑娘》、《裸袒的渴意》等篇,都无不是他对陕北贫困农民生存状态的写照,是作家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是强烈的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的表达,是他悲天悯人地为乡土、乡民的不幸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呐喊。都是在心底里沤制,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1]又如在《西北大地的岩石与鹰》中,北城对于刘志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苦难意识评论到:“可以说,苦难意识形成刘志成散文风格最有血性的主动脉。苦难是文学的主题,苦难和崇高永远是文学所要表达的极境。而刘志成所表现的苦难,又非个人琐碎得失的‘苦难’,而是基于人类的大苦难,表述对人本身的深刻的哲学思索和终极关怀。”[16]苦难意识作为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融汇在散文创作中,并成为这一时期批评家关注的焦点。耿瑞的评论文章《苦难体验的宗教意味》中,进一步对刘志成散文中所表现的苦难意识做出了新的解读。文中写到:“此际,可见刘志成的个体生命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大雪迷茫中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立于比同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的归宿感。”“刘志成散文中透露出的这种由于在现世无法找到精神家园的归宿而只能形而上的‘上下求索’最终在人类的梦想世界中找到它的归宿的省悟而呈现出的宗教意味,是现代散文生命体验的最高形式——宗教体验。”[17]如上评论,体现出散文批评的生命美学意识的觉悟。
文化批评是20世纪后期至今内蒙古散文批评所运用的另一种重要的批评视角。针对现代工业文明对草原文明的挑战,许多作家在缅怀草原原始古老的生态文明的同时,力图以文学的方式呼吁民众保护日渐消失的草原文明和生活传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少数散文创作中表现出这种民族自省意识,并为批评家所意识和关注。对此,一些文学评论者曾撰文指出,20世纪80年代新的“草原文学”,着重表现了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撞击中草原生活的社会变革,具有明显的忧患意识和悲怆精神,提出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给读者启迪和警醒,这同改革开放的大潮是分不开的。黄薇在其《城市化进程中的蒙古族小说——自省小说分析》中也指出城市化对民族自省意识的影响:“世界上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在于文化的模塑,是文化改变了我们的先天赋予。在城市文化的迫力下,城市蒙古人已经变成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了。”“‘城里人’的身份和职业、城市的派头和举止,又使他们有了许多自命不凡,自觉不自觉地对牧区的落后、闭塞、艰难产生了自然的拒绝。城市的另一种价值判断导致他们对传统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重新的裁定。他们的一切都已在城市中被改变。”[18]城市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草原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最终背离草原文明的优秀传统。20世纪始,民族自省意识已经成为内蒙古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小说批评中的文化意识在散文批评中也有着比较充分的体现。李晓峰在评《天马行空式的奇思玄想——郭保林“草原系列”散文漫评》中论到:“他的某些哲思明显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在《抒情的乌梁素海》中,他欣赏着这片内陆湖泊的古朴、宁静与原始,不禁为现代文明对这里的侵犯和吞噬担忧。他惊呼‘现代文明虽然离这里很远,但它那双充血的眼睛已盯上了乌梁素海,它已闻到了这里的原始气味。不知哪一天它会一下子扑过来,张开巨大的贪婪的嘴巴……’这种既明知现代文明需要去开发古朴蛮荒,又希望保留那古朴与蛮荒的矛盾心境,是现代人中文化层次较高者的一种普遍心境。”[19]在其他的散文批评中,这种对于草原文明危机所呈现出来的民族自省意识也有表现。莫名在《包国晨散文艺术特色》一文中指出:“包国晨最近几年散发在全国各报纸杂志的几十篇作品中,尤以短诗《白桦泪》为代表,在这首短诗中,集中体现出了诗人对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的焦虑、哀婉和痛心疾首的厚重情感。”[20]民族自省意识是内蒙古作家在散文创作中对于新时期草原文明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的自然表现,而散文批评则从文化的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做出了具体而深刻的阐释,表明生态美学意识参与到内蒙古散文批评之中。
应该指出,尽管20世纪中后期以来,内蒙古散文创作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散文批评也从过去的单一模式向多元化迈进。但是不可否认,新时期以来内蒙古散文批评观念和批评形式仍然趋于落后和保守:当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进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多元化的探讨时,内蒙古散文批评在整体上仍困守着单一的现实主义原则,有相当的滞后性,对散文作品缺乏深入的读解能力,难以发挥对创作的引领作用。再与区内的小说批评、影视批评比较,散文批评也显得萧条和呆板,乏有灵动、厚重的美学批评,难以与散文这种灵活多变、善于表现人性灵的创作相对应,也无法适应读者在批评中深入领会散文意蕴的审美需求。内蒙古散文批评的这些症结,需要美学观念的不断更新,需要多种批评方法论的滋养,更需要用文学诗性心灵认知把握散文世界。文学批评家首先应该是鉴赏家,对散文批评而言,尤为如此。
标签:散文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草原风格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刘志成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