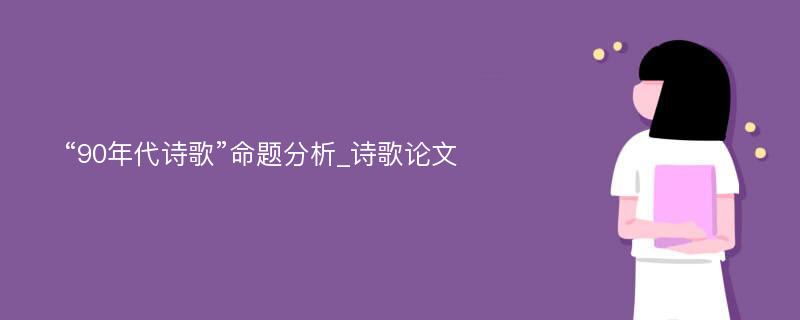
“1990年代诗歌”命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命题论文,诗歌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当代诗歌研究者和当代诗歌序列编排者来说,“1990年代诗歌”(由于对1990年代诗歌的命名是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的,所以当时的命名者就直接用“九十年代诗歌”或“90年代诗歌”这类指称;到了2000年之后,也有研究者继续沿用这些指称,但更多的是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或“20世纪90年代诗歌”这样的表述,本文采用的“1990年代诗歌”是对后者的简称或缩称,其意义完全等同于20世纪90年代所用的“九十年代诗歌”或“90年代诗歌”)在表面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通识性诗学命题。通常地,诗歌言说者和诗歌史叙述者用它来指认和命名自然时段的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这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真的存在具有诗学内涵的“1990年代诗歌”。事实上,尽管用自然时段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现象命名的情况十分普遍,而且大多是恰当的,但用物理层面的“1990年代”来直接称呼20世纪90年代诗歌却是“无理”和“无效”的,也就是说,任何所谓“90年代诗歌”其实都无法笼络和统摄、代表和标识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话语实践。由于对缺乏诗学指归的“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采纳和运用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自明”(命名者自己明白其所指)性,因而在诗歌言说界和诗歌史编排界造成了极大的理论混乱,甚至带来了关乎诗歌和诗学“话语权”的争端和战火。
一、用时段命名文学(诗歌)现象的惯常性、合理性
对于任何文学现象,一旦要加以描述和言说,要进行文学史编排,就必然要对其命名和指称。最到位和精当的命名当是那种能直接标识出对象的核心特征(或精神内涵或艺术质地,如反思文学,如象征诗派、非非诗派,等等)的命名。不过,常见的一类命名方式是,称谓本身并非该文学样态特征的直接概括,而是要么是以该文学样态所产生的时段、地段(如三十年代文学,如孤岛文学、晋察冀诗歌,等等)来命名,要么是以该文学形态的主体(如红卫兵诗歌、大学生诗群,等等)来命名,要么是以该文学类型“栖身”的社团、杂志(如新月诗派、“他们”诗派,等等)来命名,要么以是该文学派别书写对象的类属(如知青小说、文化散文,等等)来命名,当然还有这样的命名,其所指可能是交叉、重叠的(如美女小说,既指代着写作主体“美女”,也标示文学书写对象“美女”;解放区文学,既指代着文学所处地段“解放区”,也标示出文学书写对象“解放区”)。不管是哪种,因为名称的指代物的特征规定、制约着能纳入其“名下”的文学事实的特征,所以此称谓也就间接、隐在地传达出由其命名的文学对象的特征了。“1990年代诗歌”无疑属于以文学样态所处时段的名称命名的一类。的确,以时段命名文学样态的情况在文学史叙述和文学研究视阈中比比皆是,“五四文学”、“二十年代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等等,便是中国新文学领域中一些以时段命名的典型文学类型。
中国古典诗学有“本乎情性,关乎世道”的说法,著名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也明确提出:“诗歌不是没有时间性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而不是跳过。”① 的确,任何文学创作形态,从根本上说都与特定时代有着必然的关系,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以时代(时段)命名诗歌就应该有其逻辑上的正当性。任何命名都是为区别和划界而为之的,对文学的命名自然也是为区别和划分出不同的文学样态。既如此,当以时段为文学命名时,这时段就当是文学时段而非物理概念意义上的自然时段,也就是说,之所以能用某个时段来为此时段的文学命名,是因为这个时段的文学有某种足以与其他时段文学相区别的特点,从而可以将它作为一个“阶段”看待。打开既存的文学史,不难发现,那些用来给文学命名的时段通常都是给社会命名的时段,而给社会命名的依据往往是政治,以及政治意义层面的经济、文化等,这就造成了给文学命名的时段一般都是政治色彩的所谓“时代”——有时干脆就以特定时段的时代主题命名该时段的文学,如“文革文学”、“五四文学”,等等。所谓自然时段,习惯上指的是从0到10年、或0到100年、或0到1000年……这样的可以用整数表示的时段,最常见的标识方法是“X十年代”、“XX世纪”等在文学史叙述中,似乎并不乏以这样的自然时段命名和标识的文学样态。但当仔细体认,却可以看出,这样的自然时段是因为与文学时段——常常也是政治时段——对应、契合了的缘故,也就是说,是因为恰好在这个时段出现的可以用来代表该时段文学样态和特征的主导和主流文学,也足以区别、独立于其他时段文学的缘故。无视文学话语实践的、纯粹用自然时段命名该时段文学的文学名号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因而是“无效”和“非法”的;只有当该自然时段出现了的确在该时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态,而该文学样态又的确有着能区别、独立于其它时段文学的独特性时,假自然时段之名呼此时段之文学才是“有效”和“合法”的。在此情形下,自然时段之名只是此时段文学的符号、代码,在其之下必然内隐有能主导此时段文学的独特状貌和质地。
二、“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无效性”
“1990年代诗歌”,外在来看,显然是用作为自然时段的“1990年代”来为20世纪90年代(1990-1999年)的诗歌命名的,命名者的意图自然在于力求把1990年代的诗歌纳入这一指称之下——只有如此,它才能超越自然时段层面而上升为文学和诗学意义的命题以获具文学史价值和诗学有效性。通过上面的分析,“1990年代诗歌”要能成为文学和诗学命题,1990年代诗歌必须满足这样三个条件:第一,有能代表和反映1990年代诗歌整体状况和业绩的主导、主流诗歌存在;第二,该主导、主流诗歌具有能独立、区别于1990年代之外的其他时段诗歌的特质和品格;在此基础上,第三,1990年代诗歌相较于现代汉语诗歌整体或者“1990年代诗歌”命名者所确立的作为参照系的诗歌年段而言,发生了明显的“中断”和“转型”。显然,在上述三个条件中,相对于中国新诗,尤其是相对于设置为对照物、甚至对立面的1980年代诗歌,1990年代诗歌所出现的“中断”和“转型”实实在在、显而易见因而被所有“1990年代诗歌”命名者们把捉、捕获到了。我们既可以在程光炜等诗歌史家的阐述中发现其意识,也可以在欧阳江河等1990年代诗歌见证者、亲历者的叙说中得到对其的认同,前者如“较之当代诗歌的任何一个阶段,现今(1990年代——引者注)的写作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无例可援的”②,后者如“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③。
这种“中断”和“转型”,当是需要急于为1990年代诗歌命名的内在原因。问题在于,是不是只要有了“中断”、“转型”,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个90年代”(唐晓渡语)诗歌呢,1990年代诗歌能够满足上面列举的另外两个条件吗?所谓出现了“中断”和“转型”,指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出现了新质和创生性元素,而这种新质和创生性元素又是此前或已有的诗歌名号包容不了的。因此,对1990年代诗歌写作理想化的命名,应该是对发现到、把捉出的具有新质和创生性的诗歌写作进行命名,从而标识出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中断”和“转型”所在,进一步展现出1990年代诗歌的独立性和区别性价值意义。而要直接以“1990年代诗歌”命名20世纪90年代诗歌,从理论上讲,命名者发现到、把捉出的新质和创生性就必须是在1990年代具有主导、主体性的新质和创生性,或者说,这种新质和创生性必须是在1990年代居于主导、主体地位的诗歌写作所具有的。然而,1990年代诗歌写作却是个人化的、多元化的,复杂性、差异性构成了其基本生存景观。在这样的景观中,新鲜、奇异遍地开花,但花色品种各各不同,没有哪一款成为了1990年代诗歌新质的主导或主体,也没有其中任何一款的诗歌成为了足以代表1990年代诗歌的诗歌样态:“90年代诗歌的小团体虽然已经解散,但内部的分歧却在加剧。试图从整体上去把握主流或主导倾向,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④ 因此,这从命名学(命名的需要、依据)上说明,有效、精当的“1990年代诗歌”命题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一来,从“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纷纷上马可以看出,这些命名者都只不过是在1990年代诗歌场域中搜捕一类附着了某些新质的诗歌写作,然后将这些新质本质化、普遍化为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主导、主流新质,将这类诗歌写作指定为1990年代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诗歌写作,“隆重”推出他们各自的“1990年代诗歌”命题。
的确,任何一个“1990年代诗歌”命题都负载、拽拉着一种特定类型的诗歌样态和作用于这类诗歌的新质和创生性元素,而同一个“1990年代诗歌”往往是作为徽标别在不同的新质及其作用的诗歌身上的。“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同名不同实,其实也反过来说明1990年代诗歌新质和创生性元素的多样化、差异性。瓦雷里在谈到象征主义时说:“我们称之为象征主义的统一性并不在于美学上的一致:象征主义不是一个流派。相反,它接纳了大量流派,甚至最背道而驰的那些流派,我说过:美学使他们产生分歧;伦理学将他们连结到一起。”⑤ 似乎也可以说,“1990年代诗歌”也不是一个流派,它也接纳了大量流派,把1990年代诗歌连结到一起成为“1990年代诗歌”的也不是美学而是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就是所谓“中断”、“转型”,就是所谓“新质”和“创生性”。不过,细究起来,这样比照是不合适的,因为确定“象征主义”文艺的毕竟是“象征主义”这一有着内涵指归的“伦理学”,而确定“1990年代诗歌”的只是有着外延牵连而无内涵所指同一性和确定性的“新”和“创生”。既然如此,从学理角度看,所谓的“1990年代诗歌”就只能是一个徒有其表(自然时段)而无其里(诗学指归)的空壳命题了。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伪命题”实质,姜涛有着清醒的体认,“‘90年代诗歌’是一个有些含混的说法……并不针对整个90年代这个历史时段,也没有穷尽当下写作的全部现实”、“‘90年代诗歌’并不是一个包揽全局的大命题”,其原因在于,“当下诗歌现实仍是‘巴尔干化’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诗人群落占有着不同的知识结构,秉承着不同的观念和理想,甚至是在不同的时代里写作。”⑥ 同样,洪子诚“它基本上是为了有助于对诗歌现象的描述而做出的段落的划分。这一划分,虽然多少带有诗歌史‘时期’的意味,却并非严格的时期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它带有近距离观察时,作为一种时间尺度的‘权宜’性质”⑦ 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也表达了对“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不肯定、不信任。
诗歌言说者、命名者在言说和命名1990年代诗歌的同时,其实也在言说、命名他们自己,表达了他们对于1990年代诗歌的把握、认知和观念、意识。因为没有真正的“1990年代诗歌”存在,所以只要仅仅搜刮到1990年代诗歌的碎片、截取到1990年代诗歌局部的人都可以首先名其为“1990年代诗歌”,然后指其为1990年代诗歌。这样,既然此“1990年代诗歌”非彼“1990年代诗歌”,“1990年代诗歌”之间“撞车”事件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势所必然了。这里有必要提及1990年代末期诗界那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对于这场争论本身,诗界内外,甚至包括介入者自身,似乎都是持批评、排斥、蔑视或讥嘲态度的,大都把它归于“在大众消费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1990年代,诗人们出于“诗歌崇拜”和“文化英雄的自我想象有关”⑧ 的内讧或“对诗歌象征资本和话语权力的争夺”⑨ 的诗歌政治斗争之列。客观地说,就这场争论本身而言,是有其必然性,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尽管采用的某些方式、投掷的某些语言是“非诗化”的因而似乎有不足取的地方。因为,从根本上说,这场争论正是不同“1990年代诗歌”命题“撞车”的表征。其实,“知识分子写作”者的“1990年代诗歌”与“民间写作”者的“1990年代诗歌”两者既在外延上互相覆盖不了也在内指上互相代表不了1990年代诗歌。更何况“知识分子写作”也好、“民间写作”也罢,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只是“在与80年代的区分与反差中组织起来的自我想象”⑩ 和无谓的话语建构,都还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着的。因此,无论哪一个试图标榜为1990年代诗歌,都不仅是对两者中的另一个、而且是对所有其他“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遮蔽”、“压抑”、“埋葬”,更进一步说,是对20世纪90年代诗歌“真相”的“抹煞”(这些“具有高度尖锐性质”的词汇正是那场争论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语词”)。既然如此,有争论倒是正常的,而没有争论则是不正常的了。如果要说价值和意义的话,这争论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为哪一方夺取了权力、讨回了公道,而在于为20世纪90年代诗歌澄清了事实、还原了本真,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不存在“1990年代诗歌”,“1990年代诗歌”命题不成立!
三、由“1990年代诗歌”命题带来的理论混乱
20世纪90年代诗歌园地里,拥有各自新质和创生性元素的诗歌类型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那些“逮住”任何一类就名之为“1990年代诗歌”的诗歌言说者、诗歌史叙述者,其意图主旨在于凸显、指认其为20世纪90年代主导、主体诗歌并由此代表20世纪90年代诗歌。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捕获”、“抓持”还是命名、指认的过程中,他们都会将价值判断、态度立场浸透进新质、创生性元素(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一些)以及对应的诗歌中。总体说来,对各自的新质、创生性以及由此而定的“1990年代诗歌”,把持者和命名者基本投递了两种对立的价值判断和态度立场:一种是认可、肯定、推许,另一种是排斥、否定、贬抑。这就涉及到评价规范、参照标准的选取和确定问题了:“我们在估价某一事物或某一种兴趣的等级时,要参照某种规范,要运用一套标准,要把被估价的事物或兴趣与其他的事物或兴趣加以比较。”(11) 尽管不同“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具体所指和涵盖物不一样,但它们却都是基因于“断裂”、“转型”后的新质和创生性元素——当然它们并非同一而是不同的——而成立了的,所以能够说明的是,那些不同新质的把持者和不同“1990年代诗歌”的命名者选取和确定的评价规范、参照标准,要么也是“中断”和“转型”了的新质、创生性的,要么就是还没有“中断”、“转型”的“传统”、“历史”的。
要求规范、标准“中断”和“转型”的主张,以及在诗歌理论话语中对新质、创生性标准、规范的践行,在1990年代诗界有着强大声势:“既有的关于诗歌本质的界定,既有的关于诗歌审美的标准,既有的关于诗歌写作的规范……在90年代看来,就有狭隘和陈腐之嫌”(12)、“纵观九十年代的先锋诗界……让诗的审美标准,处于‘被迫’中的修正,一种更具包含的诗歌和评鉴尺度正在形成。”(13) 操持“修正”价值标准和批判依据的人,对他们各自的新质以及藉此命名的“1990年代诗歌”自然褒扬有加并极力鼓动、倡导,如王家新之“90年AI写作作把中国诗歌推向了一个更为成熟、开阔的境界,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建设所达到的水平,都是以前不能相比的”(14)、陈晓明之“我同意这种观点,即认为90年代的中国诗歌经历过青年诗人的精神升越和语词锤炼,已经使汉语诗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5);持“传统”、“历史”的标准和规范的人可能不像前者那样直接、明确地主张、倡导,但却是把它化入自己的思想、意识中去评判、指点诗歌事实的。既然标准和规范是采自于“传统”、“历史”的诗歌,而裁决的是新质、创生性的诗歌,即它们的“1990年代诗歌”,结果自然是对其否定、批判和贬抑了,如郑敏之“今天我们有些所谓‘先锋’诗人以丑陋的形象和扭曲的语言塞在诗中……使诗歌发展再度陷入新的迷茫”(16)、孙绍振之“自从所谓后新潮诗产生以来,虽然也有新探索,但是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新诗的水平并没有全面的提高。相反,给我的印象是,有点江河日下的样子”(17),并因此要“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上述两种评判倾向可以简单描述为:前者(王家新等)是用他们指定并命名的“1990年代诗歌”否定、抵制“1990年代诗歌”之前的诗歌样态(主要是“1980年代诗歌”——当然,它也只是“1990年代诗歌”命名者的话语建构,因而与“1990年代诗歌”一样,也是面目各异的),从而确认、阐述他们的“1990年代诗歌”命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后者(孙绍振等)则是用“1990年代诗歌”之前的诗歌样态否定、排拒他们指定并命名的“1990年代诗歌”。
关于对“1990年代诗歌”(其实是这一命题拖累的诗歌)的判断和评价,只要稍加留意,便会发现许多怪异因而引人发笑的现象。其中之一是,不同的“1990年代诗歌”命名和言说者,所持的是同样的标准和规范,但由于考量和评判的是不同的诗歌类型——尽管它们都被指称为了“1990年代诗歌”,因而对“1990年代诗歌”给予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态度立场。这同时也说明了,同一种标准和规范,由不同的“1990年代诗歌”确立和命名者运用时,可能是新质、创生性的,也可能是传统的、历史的:如果这种标准不同于评价、判断与他们设定为“1990年代诗歌”的参照面、对立面的诗歌类型的标准,则是新质、创生性的标准;相反,如果这种标准是延续、继承于评价、判断与他们设定为“1990年代诗歌”的参照面、对立面的诗歌类型的标准,就是传统、历史的。
最典型的是,诗歌写作的“及物性”和“历史化”可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诗歌打量者、言说者中间带有“通约性”的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一些人,如王家新、程光炜等等,是用“及物性”、“历史化”去肯定、彰显他们的“1990年代诗歌”的,因为他们指定并命名为“1990年代诗歌”的是那些“以个人的方式介入时代复杂的生活层面,从而呈现了与时代的相互交错、也相互冲突与抗衡的复杂关系”(18) 的处理和应对现实生存经验的诗歌。他们之所以把此类诗歌指定为“1990年代诗歌”,正是因为它们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他们确定的参照域)的“纯诗”和“不及物”写作(这是它们指认的“1980年代诗歌”)具有“历史化”、“及物性”这些新质、创生性元素,从而可以区别、独立于“1980年代诗歌”。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王家新们看来,“1990年代诗歌”“中断”、“转型”于“1980年代诗歌”的标志就在于“及物性”和“历史化”,因而它成为了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新质;相应地,他们提出了评判诗歌的“及物性”和“历史化”标准,自然,相对于评价和判断“1980年代诗歌”写作(“纯诗”写作)的“非历史化”、“不及物”标准,他们的“及物性”和“历史化”标准就是“中断”和“转型”了的新质和创生性标准了。用“新质”和“创生性”标准去评价、判断“拥抱”该“新质”和“创生性”的“1990年代诗歌”,肯定是“赞誉有加”的了。而另一些人,如孙绍振、温远辉、林贤治等等,选定并命名为“1990年代诗歌”的却是“光凭文字游戏和思想上和形式上的极端的放浪”、“披上后现代文化哲学的外衣”(19)、“不指涉当下,或者与当下生存相乖悖,在所谓的哲学命题下肆意涂抹”(20) 的诗歌类型。“与现实脱节”、“非历史化”、“不及物性”是他们对这类诗歌的“质”的提拎,而之所以视之为新质,则是参照、对比于(作为诗歌精神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诗歌、1980年代朦胧诗而言的。在判断标准和评价规范的选定问题上,他们不是像王家新们一样与时俱进,而是延续、承接着评判“现实主义”传统诗歌、朦胧诗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也就是“及物性”、“历史化”的传统的标准而非“不及物”和“非历史化”这些新质、创生性的标准。用“历史化”、“及物性”这一传统、历史的标准去评价、判断与传统、历史“中断”“转型”了的“非历史化”、“不及物”的新质、创生性诗歌,当然只能是“被拒绝、被排斥、直至死亡”(21) 的预言或曰“咒语”了。关于这个问题,程尚逊曾客观指出:“相比于八十年代人们对诗歌的理解,九十年代关于诗歌成就的说法,完全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肯定者认为它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并对这个时代的特殊性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而否定者则认为它完全蜕变为诗人们对语言的把玩,根本没有承担起诗歌反映时代的责任。”(22)
注释:
① [乌克兰]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M].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② 程光炜.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J].山花,1997,(3).
③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④ 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A].陈超.最新先锋诗论选[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⑤ 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M].段映虹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⑥⑨⑩ 姜涛.可疑的反思及反思话语的可能性[A].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⑦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⑧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2) 臧棣.假如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写些什么……[A].肖开愚等.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3) 陈仲义.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估衡[J].当代作家评论,2004,(6).
(14) 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5) 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A].陈超.最新先锋诗论选[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6) 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A].见陈超.最新先锋诗论选[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7) 孙绍振.后新潮诗的反思[A].杨克.1998中国新诗年鉴[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18)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9) 孙绍振.后新潮诗的反思[A].杨克.1998中国新诗年鉴[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20) 温远辉.现代诗歌的进入方式[A].见杨克.1998中国新诗年鉴[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21) 吴义勤、原保国.远逝的亡灵[A].见杨克.1998中国新诗年鉴[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22) 程尚逊.从几个说法谈起[A].见孙文波.语言,形式的命名[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