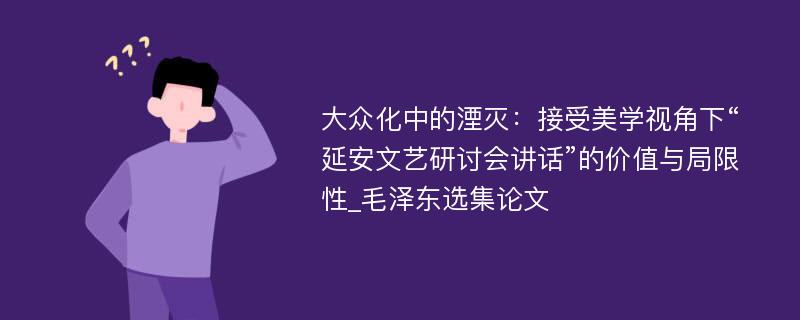
在普及中湮没——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价值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会上论文,角度看论文,美学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积极或消极的),也因此一直备受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接受美学产生以来,一些中西方的学者开始探讨《讲话》的接受美学意义,然而他们往往只是从时代与战争的角度来述其局限性,缺乏纯理论式的细致探讨,这显然是偏颇的。因此,本文将联系《讲话》发表的前后状况,从接受美学内部的两大研究理论(接受研究、效应研究)角度来探讨之,希望得到一个较为公允的论述结果。
一、从接受研究角度观其价值与局限
接受美学内部包含两大研究方向,即接受研究与效应研究。接受研究的重点在对读者的研究,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将读者放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读者决定了本文这一“半成品”的最终完成。从这一角度言,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毛泽东的《讲话》是接受美学的一个源头。(注: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在《讲话》的“结论”部分的开头,毛泽东指出: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这里肯定而明确地反复强调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将群众放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对于此,以往研究者们往往总是从政治革命及当时的时代需要角度来论述之(当然,这确实是重要的方面,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毛泽东愈来愈发现,工农大众才是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力量,文艺必须帮助和促进对于工农大众觉悟的唤醒)。但是从文艺界角度而言,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早已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来个年头了。抗战开始以后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充分认识到民众的极端重要性。楼适夷尖锐地指出“文化人应该觉醒,把文化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内,在今日的新形势下,已经是一种不可自恕的犯罪,没有普遍的大众的基础,决不能有真实崇高的文化。”(注:《纪念五四为大众的文化而战斗》,《抗战文艺三日刊》,第1卷,第3期.)南桌亦说得更为精彩:“现在正是‘文艺大众化’发展的空前良机。因为大众喜欢活生生的‘英雄’,现在正是‘英雄’出世的年头,大众喜欢‘传奇’意味的东西,现在则正是‘传奇’的时代。”(注:《关于“文艺大众化》《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此类论述十分之多,然而这场讨论并没有吸引工农大众,或者说,这场讨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当时作家还没有真正地走到工农大众中去,其产生这样的讨论只是在于“教育”他们,“启发”他们,只是把他们作为“教育”、“启发”的对象。这时的作家与读者仍存在一种意识上的不平等这也就谈不上“作家”、“作品”、“读者”三者关系的融合了。
而在《讲话》中,毛泽东则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对象问题,之后立刻引发出以前“大众化讨论”未曾涉及的大众化的途径与方法问题,即作家要看清大众,了解大众,真正地走到接受者当中去: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确是第一位的工作。
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851页.)
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研究理论所强调的正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接受者,强调对于个案的分析,毛泽东这里对于大众身份的确定及对其地位的提升无疑与姚斯的理论暗暗契合了。并且,与先前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相比,他明确地给创作者提供了如何了解人民大众的途径与方法,强调了一种非居高临下式的融合,这是难能可贵的。更进一步说,姚斯接受研究中的接受者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有一定审美经验与欣赏能力的读者,这种前提的假定性使得姚斯的接受研究遇到了绝对以读者为中心的极端主义风险,缺乏对于创作者在本文接受中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认识,或者说,几近于忽视了作家创作时对于将来读者的接受所能起到的和所会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毛泽东讲话中则不然,认识到作家创作对于接受者的重要作用,他详尽地指出了当时大众的状态:
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普及的东西比较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即这时的受众层次是十分低的,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创造出“真正有用的作品”。这是从接受者角度给创作者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于创作者与本文之关系的关注,这是姚斯在建构其接受研究时未深刻注意到的——即在不断的接受中,使受众层次不断提高,即受众层次并非先天性的处于较理想化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研究应该注意“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注:《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03页.)即对于群众(接受者)自身必须有现实的认识,而不能只是一厢情愿。但是,结合当时所处的抗战形势,正由于革命的需要,“普及工作”被迫不及待地提到了面前,即作家必须将文艺创作变成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去“雪中送炭”。这即属于功利性的接受观,是以此应付另外的一件事,也许只是为了奔走呼号,也许只是为了抄录摘用,这些又都离开了接受本身。
《讲话》中强调:
……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这种情况下,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他实际上已经抽走了接受者的主体的意识活动性(当然对于当时根据地的大部分工农兵而言,这种主体性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及受教育程度等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他想提供给工农兵的实际上即是一种精神上的激愤。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都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想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追求的是急切的煽动效果,先前强调的在审美经验的不断积累中提高接受者层次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因此,虽然毛泽东《讲话》注意到了作者与本文之间的关系对于接受者的影响,但是仍然走向了绝对以接受者为中心而忽视创作者的歧途,与姚斯的因对于读者水准的假定性而致的偏差正好“异曲同工”了。也正因此,作者的地位便在这场“普及运动”中被湮没了。本应由作家——作品二位一体模式过渡到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模式的理想又一次破灭,创作者在消失,作家实际上沦为了写手。
二、从效应研究角度观其局限
伊泽尔的效应研究正是从姚斯接受研究这一薄弱环节出发,强调“反馈信息”使作品由“半成品”走向“成品”的作用,强调作者与本文之间的关系对于接受过程的影响,“空白”、“空域”是其关键词汇。所谓“空域”指的是本文中各不同部分和形状应该互有联系,尽管本文自身未作如此说明。“空域”是本文不易觉察的联结点,它们在划出各个部分的要点和场景时,同时也在怂恿读者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是对于作者的高要求——一种预见性的不动声色的怂恿。作家在构架作品框架的时候,实际上是必须高于读者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虽然注意到了创作者与本文关系的重要性,却最终没有走向伊泽尔所建构的“效应研究”理论的方向呢?
毛泽东《讲话》中始终强调作家与大众的统一: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二者统一起来。(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可以想见,当时大众接受层次之低使得这种“统一”从美学角度而言,只能使作家于其中湮没,这是与强调文学艺术作品须与由其审美价值属性构成复调和声的接受美学相悖的。而中国文人历来的“济世”传统更使得这种局面得以顺利出现。这在上文所述的楼适夷尤其是南桌的言论中表露无遗,他们完全沉浸于民众身上的浴血奋战、义无返顾地牺牲精神之中了,他们虽然意识崇高,使命感炽热,但却忽视了对作为读者群体的人民大众的深刻研究与把握,读者已不再是其作品的读者,而成了一种模范与榜样,作家自己最终走向了自我否定和自我谴责的境地。
其实早在新文学革命时期,许多文艺先辈对于这样的状况已有了一定的认识。茅盾在一篇署名“玄”的文章中说:“中国一般人看小说的目的,一向是在看点‘情节’,到现在还是如此,‘情调’和‘风格’一向被群众忽视,现在仍被大多数人忽视。这是极不好的现象。”茅盾还十分严肃地提出,“若非把这个现象改革,中国一般读者鉴赏小说的程度,终难提高。”(注:《评〈小说汇刊〉》,《文学旬刊》第46号,1922年7月1日,转引自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鲁迅先生亦言:“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他,却自己……”(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然而,似乎时代永远不会让你有完美的结果,以前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虽然关心了接受者却并未仔细分析之,未去寻找走向他们的正确途径。而毛泽东《讲话》虽然系统分析了大众接受者,却又在时代与革命的“压迫”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是在此种情况下,统一的主题、创作模式便趁虚而入并被欣然接受了。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2页.)
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2页.)
可见毛泽东在将以往“大众化运动”理论进一步深入与系统化的同时,虽然他亦强调文学是艺术的,但最终走向了文学是革命,完全服从于革命的这一极端。不管其政治意义如何,从完整的接受美学理论角度而言,这都是不容许的。绝对的“概念灌输式”或者说是“煽动迎合式”的普及代替了“艺术式”的潜移默化,这也就无法带来任何接受者主动性的自我升华效果。毛泽东一度强调的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注:参见《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867页.)也就只能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文人作文,农夫握锄,本是平平常常、出乎自然的事。如果意别有在,有意为之,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戴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注:《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作家身份始终只能是一个主体性的创作者,而不能沦为号召下的“写手”,倘若如此,本文中必须由创作者留下的“空白”、“空域”便荡然无存了。这一点可以从《讲话》发表之后的“赵树理现象”略见一斑。
赵树理称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创作是“文坛文学”,并立意打破这个“高于地面”的“坛”。赵树理的小说,每一部都会“引起群众的欢迎,群众把赵树理看成是自己人;把他笔下的人物看成是自己周围的人。”(注: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可以说,虽然这是一种精神生产,但却缺乏更多的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欣赏、审美价值,只是一种对于群众乐于故事口味的迎合。作家自己的地位沉沦了,即如题目中所说的,只能是被湮没。
三、综述
由上述论述可见,对于毛泽东《讲话》,我们完全有必要从接受美学自身两大理论方向来分别考察之,只有如此才可以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即毛泽东一方面注重并仔细分析了作为接受者的大众的状况,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有利于文学作品的被接受,有利于对于知识、文化、思想等的普及,并与姚斯的接受研究暗暗契合。但同时《讲话》由于过度地从阶级立场、革命需要角度出发而完全偏向了大众,忽视了作为创作者的作家。与完整的接受美学理论的另一研究方向——效应研究相对照,无疑这又是其很大的局限,导致作家最终的被颠覆,沦为写手。然而无论如何,这是那个时代所无法避免的,正如接受美学所强调的,政治、时代、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不仅始终影响接受者,而且也自始至终地影响作为普通一分子的作家的思想及其创作。(注: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⑨《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标签:毛泽东选集论文; 延安文艺座谈会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接受美学论文; 文艺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毛泽东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