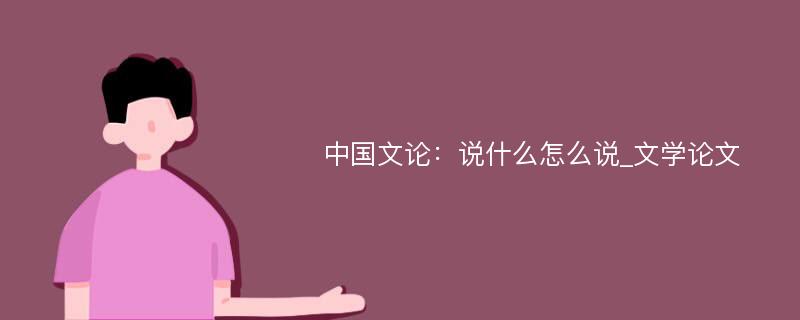
中国文论:说什么与怎么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说什么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其言说的过程及其结果大体上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说什么”与“怎么说”。欧阳修《代人上枢密求先集序》:“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言以载事”而“事信”属于“说什么”,“文以饰言”而“言文”属于“怎么说”。
“说什么”与“怎么说”构成了全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论,理应同时关注这两个问题。古代文论说什么?古代文论说得太多了。仅就“创作发生”这一具体话题而言,古代文论就说了许许多多:孔子有“诗可以怨”,屈原有“发愤以抒情”,司马迁有“发愤著书”,钟嵘有“感荡心灵”,刘勰有“为情造文”,韩愈有“不平则鸣”,欧阳修有“穷而后工”……不惟创作发生,举凡文学创作以及整个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论都有自己的“说什么”。
“中国文学批评史”(或曰“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伊始,就一直格外关注“中国文论‘说什么’”。从周秦诸子到清季学人,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到《人间词话》的“词以境界为最上”,历朝历代的文论家和文论著述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所说的在今天还有没有(或能不能)用?这些问题是学界最为关心的。古代文论的“说什么”当然是很重要的,它直接构成中国文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传统。但是也应该看到,古代文论的“说什么”因其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有些内容在今天已失去了作用和价值;或衍为空泛(如“文以载道”),或成为常识(如“物感心动”),或无处可用(如“四声八病”),或无话可说(如“章表书记”)……
毋庸讳言,中国文论传统形态的“说什么”,相当部分的内容在今天已经失效或部分失效。比如儒家文论的“教化说”,在由文学自身的边缘化所导致的文学伦理教化功能之弱化的今天,早已成无的放矢之论。又比如,泛文学语境下的尊体和辨体,随着诸多“文体”在文学史上的消失而使去了或“尊”或“辨”的必要。还有,中国文论有着极其丰厚的抒情理论,而在这个叙事至上,尤其是图像叙事几成霸权的时代,抒情理论还有多大回旋余地或阐释空间?正是因为中国文论的“说什么”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部分失效,导致了文论界的“失语”焦虑:而“失语”焦虑又催生出文论界对中国文论“说什么”的过度研究,以至于将“说什么”(文论话语之建设)视为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枢机或关键。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讨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至今未见显著成效,个中缘由固然非常复杂,而我以为过分关注中国文论的“说什么”进而将其视为实现现代转换的惟一支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界对中国文论“说什么”的过分关注,还有着历史的原因。先秦儒家文化主张“言之有物”、“辞达而已”,反对“巧言令色”、“以辞害志”。先秦儒家对理论言说的要求,重在“说什么”(说的内容是否符合礼教仁义),而非“怎么说”(有无技巧,有无修辞等)。这种思维方式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便是非常重视“怎么说”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仍然要程序式地谴责“采丽竞繁”、“言贵浮诡”。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对“说什么”的过分关注,直接影响了对“怎么说”的必要关注。关于“中国文论‘说什么’”的研究,其界域之广博、论述之深邃、成果之丰厚,已经到了《文心雕龙·序志》所言“马郑诸儒,弘之以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的程度。相比之下,对“中国文论‘怎么说’”的研究,就显得是“泛议文义,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二)
若寻根索源,则不难发现一件很有意味的事:古代文论的“怎么说”问题与古代文论是同时诞生的。先秦是古代文论的滥觞期,要研究“先秦文论”,恐怕先得弄清“先秦文论‘怎么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先秦”部分共选录八家:《尚书·尧典》、《诗经》、《论语》、《墨子》、《孟子》、《商君书》、《庄子》、《荀子》。这八家或是文学作品,或是史书,或是子书。与后代文论(如《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相比,先秦文论没有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或专篇,因而也不能够独立成体、集中系统地讨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先秦文论怎么说?寄生地说,随意地说。所谓“寄生地说”,是指先秦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批评文体,只能寄生于当时各种体式的文化典籍之中,在非文论的文体框架内议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如庄子“三言”中的文论阐释)。所谓“随意地说”,并非随心所欲或随随便便,而是指先秦文论的论者“随”自己或儒或墨或道或法的文化思想之“意”,旁及文论话题(如《论语》所录孔子师徒之“因事及诗”和“因诗及事”)。
先秦文论的寄生性与随意性,在“怎么说”的特定层面,从源头上铸成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形成后世文论文体的开放性与多元化,以及话语方式的审美性与艺术化。中国文论的言说,既然一开始就寄生于各种非文论文体,久而久之,文论言说就淡化了文体意识,或者说,文论言说可以在论者所青睐所选择的任何一种文体的框架内展开。即便是在文体意识与文论意识均已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依然根据自己的文体爱好而不是文论应有的文体要求,来选择文论言说的文体样式。比如陆机和刘勰,都有自觉的文论意识和辨体意识,陆机著有《辨亡论》,刘勰著有《灭惑论》:《文心雕龙》还辟有“论说篇”,释“论说”之名,敷“论说”之理,品历代“论说”之佳构。这两位深谙“论说”之道、擅长“论说”之体的文论家,在讨论文学理论问题时,却舍“论说”而取“骈”、“赋”。陆机和刘勰的这种选择既非个别亦非偶然,它是文学自觉时代的文论家,对文学理论批评之诗性言说的自觉体认。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仅在“论文叙笔”和“割情析采”时关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怎么说”,甚至在“征圣宗经”时亦不忘彰显圣人著经时“怎么说”。南北朝之后,唐宋诗论讲究诗格、诗法、诗式、诗体,如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皎然《诗式》,以及宋代梅圣俞、苏轼、欧阳修等人,均从刘勰的“怎么说”理论中吸取了不少思想及方法①。
如果说,先秦文论是寄生地说,随意地说:那么六朝文论则是骈俪地说(如《文赋》、《文心雕龙》)、意象地说(如《诗品》)。唐宋以后,文论言说干脆采取了与文学(诗歌、笔记小说等)完全相同的文体和语言方式:抒情地说(如《二十四诗品》以及大量的论诗诗)、叙事地说(如属于“说部”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等)。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不能是批评,正如批评不能是文学。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批评文本之中,“批评”可能是“文学的”或具有“文学性”:“文学”可能是“批评的”或具有“理论性”。前者如钟嵘的《诗品》,自觉的批评意识和独到而深刻的批评见解,凭借着极具文学性的文字出场,其想象之丰富、取譬之奇妙、性情之率真、语句之优美,完全可以读作文学性散文。后者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分明是二十四首四言诗,既有《诗经》四言的方正典雅,又有汉魏五言的自然清丽,还有晚唐七言的哀婉幽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司空图的“诗画”或“画诗”其实是在深刻而系统地言说着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文学的风格和意境。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说的是二十四种诗歌风格或意境,也是二十四种文论范畴。当司空图用“景、境、人、情”皆备的诗性叙事来表述他的诗学范畴时,他实际上揭示了中国文论诗性言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文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中国文论的理论体系,由历朝历代的诸多理论范畴所构成:而历朝历代的文论范畴,其形成有一个共通的特征:不是出于书斋的玄想,而是出于对经验的叙述或归纳。比如刘勰,对《文心雕龙》中的每一个理论范畴都要“释名彰义”。论“神思”,则谓“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论“风骨”,则曰“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论“体势”,则云“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不惟“神思”、“风骨”、“体势”这类创作论范畴,即便是“道”这种具有本体论和本源性的元范畴,刘勰对它的释名彰义也不是逻辑的、思辨的,而是经验描述和归纳性质的。《文心雕龙》之原“道”,大谈“日月叠璧”、“山川焕绮”、“云霞雕色”、“草木贲华”……“道”作为中国文论的元范畴无疑有着纯粹的形而上意味,但“道”这个字在古汉语中的原初释义却是实体性的。《说文》:“道,所行道也。”道就是道路,经验世界中实体性的“道”有着诸多特征或规定性,如道之两端,道之边限,道之走向,行道之方等等。这些经验层面的义项,在历史时空中逐渐发生了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转变。由“道之两端”而有“本源”、“本体”、“终极”之义,由“道之边限”而有“准则”、“规范”之义,由“道之走向”而有“运行”、“规律”之义,由“行道之方”而有“技艺”、“技巧”、“技法”之义……凡此种种,从不同的层面构成“道”的丰富内涵。徐复观在谈到《庄子》之“道”时指出:“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② 因而可以说,中国文论由人生经验而归纳出的理论范畴,是最具艺术精神的。
中国文论的“怎么说”,不仅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而且以其言说的具象性、直觉性和整体性,揭示出中国文论在思维方式上的诗性特质。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论的“怎么说”?首先,要从原始时代的诗性智慧、轴心期的诗性空间、原始儒、道的诗性精神以及汉语言的诗性生成之中,探求中国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源与文字之根;继之,要在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及生存方式等不同层面,阐释中国诗性文论的特征、成因及理论价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将古代文论的“怎么说”,创造性地转换为当下文论的“怎么说”,亦即从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传统之中发掘并吸取具有现代价值的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
(三)
中国文论之关注“怎么说”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文化根荄是自周秦诸子以来的诗性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我们看周秦诸子时期的中国文化典籍,无论是诗歌体的《道德经》还是寓言体的《庄子》,抑或对话体的《论语》和《孟子》,它们所言说的,是关于人类、自然、社会以及文化、文学、文论的理性思考;而他们所选择的言说方式以及支撑这种选择的思维方式却是诗性的。
以《庄子》为例。《庄子》的“寓言十九”,其诗性言说既是文化的也是文论的。《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天下》有“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何为“寓言”?《寓言》篇自谓:“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谋。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父之誉子,诚多不信,故须藉外论之;直言其道,俗多不受,亦须藉外论之。故郭象注曰:“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陆德明释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③ 相对于庄子欲明之“道”而言,庄子的“寓言”是“外”,是用以寄寓己意的他者(他人和他物)。道是不可说的,或者说是不可直说、不可己说的,必须“藉外论之”,这个“外”就是寓言,就是虚构性或文学性言说。何为“重言”?借重先哲时贤之言也,属于庄子诗性言说中的对话部分。《人间世》、《大宗师》借重仲尼与颜回的对话讨论“心斋”、“坐忘”,《知北游》借重老聃与孔子的对话讨论虚静等等,均属《庄子》寓言中的“重言”部分。衡之于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标准,《庄子》诸多的重言(对话)完全不同于语孟的对话,前者依然属于庄子的诗性言说。当然,“重言”之中的老子、孔子、颜回等,都是真人,他们所讲的那些道理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更是真谛,所以庄子要说“以重言为真”。这是一种虚构的真实,或者说是诗性的真实。何为“卮言”?自然无心之言也,属于庄子诗性言说的曼衍风格④。郭象注“卮言”曰:“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从之,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⑤ 因物随变,顺任自然,无心之言,新异日出,是为卮言。《庄子》三言,合而言之,是庄子诗性言说的总体特征:分而言之,“寓言”是对诗性言说的质的规定,“重言”是庄子寓言的对话方式,“卮言”则是庄子寓言的独特语言风格。庄子寓言的诗性言说方式及语言风格,与庄子寓言的思想内容一样,对后世文论的诗性言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整部《庄子》而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数字表述是准确的;但具体到《庄子》33篇中的某一篇,诗性言说(寓言、重言、卮言)的比例并没有这么大。比如内篇的《齐物论》,虽然也有寓言(如狙公赋芧,朝三暮四)、重言(如瞿鹊子问乎长梧子)和卮言(如“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等诗性言说,但大部分篇幅(或者说主体部分),庄子是在思辨地说,逻辑地说,故《文心雕龙·论说》称“庄周《齐物》,以论为名”。《齐物论》中的“论”(哲理性言说),颇为著名的段落有:“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等等。不惟《齐物论》,《庄子》内篇的其他6篇亦可见哲理性言说。庄学界一般认为, 《庄子》内篇是比较可靠的庄子作品。据此可以说,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具有很高思辨水准的哲学家,他完全有能力思辨地说、逻辑地说(就像他在《齐物论》中已经做过的),完全可以用《天下》所说的“庄语”(庄重严正之语)来言说本身就具有形而上色彩的“道”。
然而,庄子更多地选择了寓言、重言和卮言,选择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选择了“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一言以蔽之,选择了诗性言说。我们知道,庄子的语言观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庄子·天道》篇“轮扁语斤”的寓言,不厌其细地申述“意之所随者(道)不可以言传”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道理;但是,庄子这位“知者”倘若真的“不言”,他如何能将这个道理讲得清楚?他人及后人又如何能知晓这个道理?所以,主张“不言”的庄子又不得不言。关于庄子的这一悖论,后人有多种解释,却大多不能自圆其说。在此,我们试从庄子“三言”之诗性特征的角度略作辩说。
庄子论“道”是接着老子说的,故在“道不可道(说)”这一点上与老子一脉相承。但是,庄子的“道”与老子的“道”又有很大的不同:老子将形而上之道落实到治国教民,以成“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庄子则将形而上之道转化为心灵之道,通过“朝彻”、“见独”、“心斋”、“坐忘”以成“真人”“至人”或“神人”。而庄子的所谓真人、至人、神人,不是一种生物性或社会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的或心灵的存在。说到底,庄子是在用《庄子》的三言(诗性言说),精心地建构一个心灵的世界。在庄子那里,语言对于“道”是无能为力的,而语言对于由“道”转化成的心灵世界却是大有可为的。庄子欲将“道”转化为心灵世界,则须先作两个层面的超越:一是超越尘世,一是超越语言。“处昏上乱相之间”的庄子,无时无刻不在想超越这污秽混浊的尘世:“得意忘言”的庄子,无时无刻不在想超越这不能传意不能诣道的语言。超越尘世,超越语言,最终是要建构一个清洁虚静的心灵世界,建构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诗性世界。庄子藉什么来超越尘世,超越语言?庄子又拿什么来建构心灵世界, 建构诗性世界?语言。除了“语言”,庄子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庄子在物质世界(包括语言世界)之外所精心建构的,其实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一个诗性言说的世界。这就是庄子明知“知者不言”却不得不言的最为深刻也是最为真实的原因。
徐复观在论及庄学精神与南朝山水画之关系时指出:“没有人会在活生生的人的对象中,真能发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生命中的世界。庄子所追求的,一切伟大艺术家所追求的,正是可以完全把自己安放进去的世界,因而使自己的人生、精神上的担负,得到解放。”⑥ 同样是追求“可以完全把自己安放进去的世界”,南朝的画家和画论家选择了最能体现庄学精神的山水画,而庄子选择了最具诗性特质的“三言”。徐复观说“由庄学精神而来的绘画,可说到了山水画而始落了实”⑦;我们同样可以说,由轴心期诗性智慧而来的中国文化的诗性言说,到庄子的“三言”而始落了实。唐志契《绘事微言》:“山水原是风流潇洒之事,与写草书行书相同,不是拘挛用功之物。”中国文化及文论的诗性言说,犹如绘画中的山水画和书法中的草书行书,“不是拘挛用功之物”,“原是风流潇洒之事”,其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灵魂和生命的诗性世界。这个世界是在诗性言说中生成的,言说者凭藉着自己的言说建构了这个世界,因而能在这个世界中作逍遥之游,申齐物之论,养生命之主,全德充之符,宗大道之师……
庄子的哲学及文论同样包含“说什么”与“怎么说”问题。庄子说什么?说“道”;而“道”又不可说,故庄子哲学的“说什么”反倒变得简单了,因为说什么也无济于“道”,故“说什么”也就不是十分重要了。庄子怎么说?前面讲到,庄子有两套言说方式:思辨地说与诗性地说。《庄子》是哲学,理应思辨地说,庄子也完全能够思辨地说。但哲学家庄子却选择了“寓言十九”,选择了诗性地说。庄子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很难也很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庄子的“怎么说”。因而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怎么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
一位美国汉学家如此描述《庄子》的“怎么说”:“大多数看似自相矛盾的段落、不依据前提的推理、看起来转弯抹角的或纯粹幽默的文学参考,包括运用或有目的地误用历史人物以及像孔子这样的哲学上的论敌作为对话者……”庄子为什么要这样说?论者指出:“目的都在于使读者的分析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沉默,并同时加强读者的直觉的或总体性的心力功能。在削弱和麻痹心灵的分析思考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庄子》展示了大量光辉灿烂的语言技艺和文学手法”⑧,让分析性沉默,让诗性苏醒,这是庄子的“怎么说”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所体现的艺术精神。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庄子的“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给中国文论以深刻的启示和巨大的影响。
(四)
中国文论的“怎么说”,因其对中国文论之独特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的承载和表达,有着较强的超时空的生命力、实现现代转换的潜在活力以及针砭现代学术病症的疗救能力。
前面谈到,庄子明知“言”不能诣“道”却还是要言,其真实而深刻的用意是要用独具诗性魅力的“三言”,建构起一个超越尘俗的精神世界以安顿自己疲惫的心灵。受庄子“怎么说”的影响,中国文论何尝不是如此?刘勰明明知道“论说”与“骈体”的区别,对六朝文学的“俪采百字之偶”亦颇有微辞,可是他偏偏选择偶俪繁缛的骈体文来阐释他的文学理论。为什么?“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孤寂落寞的刘勰,要用他的美文,用他独特的诗性言说,建构一个可寄放心灵的“文”(语言)的世界。青年彦和如此,暮年表圣亦然。唐末司空图,这位耐辱居士、休休亭主,远离朝廷远离尘世,用二十四首四言诗,用抒情、叙事、比兴、象征等艺术手法,在空山旷野之间栽种文论绿树,在衰世浊尘之外建构心灵家园。不惟彦和、表圣,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史,该有多少文论家在用自己的诗性言说建构诗意的家园!
在这个被称为“高科技”或“技术化”的时代,中国文论的诗性家园恶乎在?“文变染乎世情”,因“世情”之故,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大体上走了一条从政治化、哲学化到工具主义、理性主义的路径,诗性言说的理论传统基本上被中断。在20世纪西方文化的巨大阴影之中,中国文论的“说什么”与“怎么说”被立体地消融掉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我们说的是别人的“说什么”;从“精神分析”到“本文分析”,从“细读”到“误读”,我们用的是别人的“怎么说”。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界热衷于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怎么说”,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这些新方法“拉郎配”式地引进文学理论。结果怎么样呢?没几年便“尔曹身与名俱灭”了。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文学理论中的科学和逻辑的思维方式,而是反对那种科学化倾向,反对那种科学至上、逻辑唯一的态度(这种倾向或态度本身就是“非科学”的)。“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⑨,对文心的探幽索微,对文学的深识鉴奥,更多的是一种描述(discribe)而非仅仅是规定(prescribe)。文学理论是诗性与逻辑性的统一,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理应建立在她自己的诗性传统之上。
中国诗性文论的“怎么说”,依次包括言说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三个层面。支撑中国诗性文论之言说方式的,是中国诗性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陆机以赋论文,刘勰以骈文析文心雕文龙,杜甫以七绝论诗,司空图以四言描述诗歌风格和意境……既是对文论言说方式的自觉选择,更是对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自觉选择,是深受中国诗性文化熏染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文论诗性传统的形成而言,诗性文化是重要的精神根基和人文素养。且不说道家的自然与超迈、道教的神秘与浪漫、玄学的清虚与冲淡以及禅宗的般若、顿悟等等,本身就是典型的诗性文化,即便是以“事功”见长的儒家文化,其实也并不乏诗性特征。孔子忧道传道,热心救世,却也神往于沂浴之乐,醉心于韶音之美。海德格尔曾不厌其细地解读荷尔德林的两句诗:“人们建功立业,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⑩,借这两句诗来状写《论语》中的孔子也是颇能传其神的。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学理论,铸成其诗性内质便不足为奇了。
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的人们,也在“建功立业”,却并不能够“诗意地栖居”。文学这片本该是最富诗意的绿洲,却在遭受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侵袭。刚刚摆脱“政治奴婢”之地位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一转身又要去做金钱的臣妾。文学批评的主体与对象,已沦为甲方与乙方,财迷迷,慌张张,没有了人格,更远离诗性。对于这种后工业时代的流行病,我们以为,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无疑是一剂良药。21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该吸纳中国诗性文论“怎么说”的传统。在高科技时代,技术理性或科学主义成为主宰性标准。表现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则是非诗意的栖居和唯理性的思维,导致文论话语的艰涩、干涸和板滞。文学批评常常远离文学作品,在一个丢失了上下文的虚空之中,毫无目标地抛掷新术语新名词的炸弹。文学理论则是无视本民族的文化语境,热衷于为各种进口的“主义”或“流派”作着似是而非的诠释:或者似懂非懂地盯着外来的文论“蓝图”,随心所欲地搬动着本民族的文论“部件”而建构着沙滩上的理论“大厦”。这种“大厦”既缺乏内在的精神支撑(中国文论的“说什么”),更没有外观上的“好看”(中国文论的“怎么说”)。
当代中国,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大多集中在高等院校,由于对高校教师在职称评聘、业绩考核和学术奖惩等方面越来越严格的“数字化”管理,使得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学术研究成为一种越来越“规范化”或“模式化”的文字制作。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文学理论批评的“怎么说”,无论是文体样式、话语方式抑或语言风格,均趋向单一、枯涩甚至冷漠。古代文论那种特有的灵性、兴趣和生命感受被丢弃,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所特有的开放、多元和诗性言说的传统亦被中断。毋庸讳言,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并不太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然而,就文学批评这一特定领域而言,我们是否做过这样的比较:一篇书信体的《报任安书》或《与元九书》胜过多少篇核心或权威期刊的论文?一部骈体文的《文心雕龙》或随感式的《沧浪诗话》又胜过多少部国家级或省部级出版社的巨著?在文学批评的研究及写作领域,我们需要吸纳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否则,我们的文学批评则难逃如彼归宿:或者是西方学术新潮或旧论的“中国注释”,或者是各种学术报表中的“统计数字”,或者是毫无思想震撼力和学术生命力的“印刷符号”或“文字过客”。
百年回首,方知诗性传统之可贵,方知古代文论“怎么说”之值得研究。中国文论诗性传统在20世纪初的断裂,从一个特定的维度导致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丢失,导致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以及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疏离。要在新的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可行性路径之一是清理、总结、承续诗性传统,并揭示出这一传统的现代价值。创造性地承续已被中断近一个世纪的诗性传统,既能为连接古文论与现代文论找到一条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纽带,也能为建设中国文论寻求传统文化的资源和根基。
注释:
① 参见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第20—23、34—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30页,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③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4册第947—948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 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第728—72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4册第94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⑥⑦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135、153页,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⑧ [美]爱莲心著:《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第2页,周炽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⑨ 黄庭坚:《寄晁之忠》。
⑩ 成穷、余虹、作虹译:《海德格尔诗学文集》第191—20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二十四诗品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寓言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齐物论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诗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