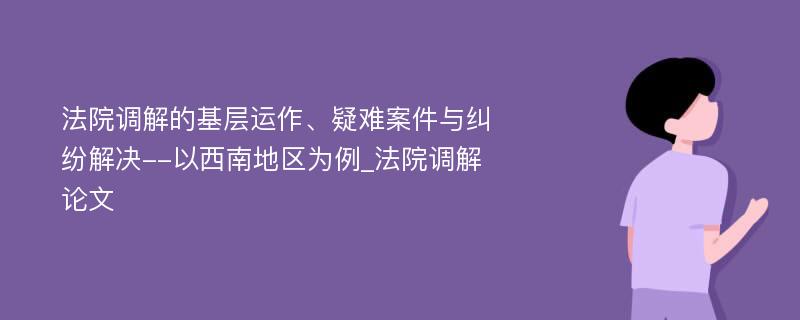
法院调解、难办案件与纠纷解决的基层运作——基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南地区论文,难办论文,中国论文,基层论文,案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自2008年起,中国大陆的宏观司法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的治下,中国法院系统被要求重新回归“群众路线”。①在具体制度安排上,“法院调解”被再次放置到了异常突出的位置,官方将这一政策变革概括为——“大调解”。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大调解时代全国法院系统的平均调解率已近达到68.15%。②然而,此“大调解”政策自其颁布之日起,便引发了法律实务界与学术界的批评和激烈争论,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③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Jerome A.Cohen)认为此项改革是对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主导的职业化倾向的司法改革的全面背叛,是“以‘民主’为幌子的‘群众路线’(Mass Line);是明显地倒退到了将法律当作‘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过去。”④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则认为,在过去十年: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导向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突出审判和审判方式改革,强调法官消极和中立,律师扮演积极角色……这种司法模式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基层社会,缺乏适用性和有效性,在宏观层面需要适度调整。有鉴于此,从宏观层面看,我认为能动司法和大调解的实验和推广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⑤ 其实,自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⑥从一种思想理念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时开始,调解与法治,正义与规则,威权与民主,司法传统与社区传统,纠纷解决中的霸权与政治等,此间的争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就从未停止过。⑦而之于当下中国,法治尚未定型,司法尚且不彰,在此情况下强调用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冲突,这也自然会构成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西方学理与中国语境在多层论域内的冲撞。虽然,今日大调解的热潮已在渐渐退去,但刻下中国的大部分纠纷依然正在通过法院调解予以解决,这使得我们在概念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关于调解的争论即使是有价值的,也是不足够的。一些更为直接的问题应该被回答:例如,法院调解机制是如何运作?是否适用、有效?有何优点与缺陷?对其缺点如何克服与修正?正如葛兰特(Marc Galanter)教授指出的:“我们可以期待关于司法调解的系统知识及其制度措施的快速发展。但是这样的知识(发展)需要我们发展出适当的工具(措施)能对司法调解之过程及结果的质量予以评价。”⑧——而这些对调解过程与结果质量的认知,只能通过深深地扎根纠纷解决的过程本身,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才能获得。对于中国调解而言,相关的经验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非常缺乏的,⑨这是现有调解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缺漏。值得一提的是,经验研究并不先验地肯定或否定研究对象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在通过“在场”的体验与观察(定性)或调查与统计(定量)来寻找和评估这种合理性是否可以建立的真实理据。 除了经验研究的缺乏,现有研究的另一个明显缺陷还在于,它们都是笼统地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或者作为中国的整体发言。中国被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全实体,而所有的学术研究是以整个中国为论域来展开和论述的。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以及地理与人口的多样性,中国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在统一的民族国家表层下多元现实共存、相继的复杂论域,其异质性在省际甚至在一个省区内部都是非常显著的。⑩裴宜理也指出,应该将中国研究看作一个尚待完成的由区域研究所构成的学术拼图,而非“树木—森林”的关系,这将更有利于准确地理解中国现实。(11)所以,诸多社会科学都已相继指出,将中国作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在方法论意义上存在重大失误。而在法学领域,这种尊重区域差异,在方法上强调或重视由“区域”构成的论域限制,并对研究结论有效性抱有必要的“区域节制”的研究作品是罕见的。本文是在这一方法论起点上对中国法院调解进行研究的,所以本文着眼于中国西南一隅的基层社会,故而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个案的谨慎拓展(Case Expansion);不是普范性的,而是区域性的。 在本篇文章中,笔者会首先介绍案件的内容、处理过程以及案件嵌入的西南中国基层法院之社会生态,接下来将对由本案所体现的法院调解的利弊予以分别讨论,然后得出相关结论。在结论部分,本文还就“失败个案”问题作出方法意义上的讨论。 二、案情 (一)案例一:一个穆斯林村落的继承案件 1.案件基本事实 案件发生在西南中国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具体而言是一个回汉杂居的城郊接合部。(12) 甲与乙是姐弟,都是穆斯林,曾共同居住在同一个镇上。大约40年前,甲外嫁到了临村并从家里搬出。在所有的兄弟姐妹逐渐搬出老宅之后,乙,这个家族最小的儿子继续与父母居住在祖宅中。虽然其他子女也曾承担了一些赡养父母的工作,但乙承担主要的义务。20年间,父母相继去世,乙及其家庭独自居住在祖宅中。2009年,乙想要拆除祖宅另建新房,这个计划遭到了甲的反对,她主张自己对该房屋也应享有继承权,故乙不能单独对祖屋予以处置。(13)然而,乙主张根据民间习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故这位姐姐不享有继承权;乙同时主张自己在赡养父母方面尽到了主要义务,自己理应独享对祖屋的继承权。该村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试图调解,但最终失败。随后,甲将乙诉至法院。 2.案件处置过程 显然,法官需要面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在理论意义上,有很多文献对这种冲突关系作过讨论,但在这里,笔者更加关心的是法官是如何处理和克服这其中的为难,这种由法律多元所制造的现实两难。除了两套规则系统的冲突,在这里,法官们还要面对由于追求“人民满意”的政治要求所带来的压力。在操作层面,如果法官严格贯彻《继承法》,换言之,法官将民间习惯完全视为无效,那本案的原告将不会满意这样的判决结果。(14)相反,如果法官只是迁就民间习惯,这将导致在判决上的明显违法,以及被告方的不满。在西方社会,当事人是否满意不会被法官当作判决的一个重要考量;然而在中国,法官需要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和满意,这是因为在近年司法群众路线中,对所谓“作人民满意的法官”的日益强调。(15)在具体政策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级法院系统,“要努力实现调解结案率和息诉服判率的‘两上升’,实现涉诉信访率和强制执行率的‘两下降’。”(16)在地方法院内部,往往将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些要求转化为具体实际的考评标准和奖惩细则,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满意度。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谨慎而小心地处理这种困难案件,不仅要保证法律的公平,而且需要考虑政治的正确以及自身利益的不受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调解其实构成了处理该案的一种很好的选择,它不仅能提供给双方当事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而且也避免了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的正面冲突。就这一案例而言,法官也有足够的理据劝说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问题。对于原告,法官可以告诉她被告承担了主要的赡养父母义务,以及对外嫁女不再享有继承权的习俗,促其调解;而对于被告,《继承法》中男女平等的原则也会成为劝说其接受调解的理由。但遗憾的是,由于被告人的固执,法院调解最终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被迫回到了判决的轨道,而需要为这个困难案件提供一个实际的判决,并面对一方当事人有可能因为不满而申诉、上诉甚至上访的风险。(17) 在庭审程序结束后,法官开始琢磨如何判决。在最后决定作出之前,法官带着书记员重新回到纠纷发生的村落,向村、镇领导和人民调解员咨询此案的处理方式。在村镇领导的办公室,法官实际上完成了多次有目的的访谈。具体咨询了诸如此类案件有没有先例?如果独占房屋的一方需要给对方补偿,到底多少金额合适?在这个过程中,书记员记录下他们的访谈内容,在采访的最后,法官将笔录交给受访的官员和调解员过目、签字。当法官写判决书时,这些访谈的材料并被法官归在了卷宗中,这些地方性知识和建议被用于合法化法官最终的判决。虽然这些访谈资料并没有直接被引用在判决中,但它们实际被法官当作“证据”加以使用,不是案件事实的证明证据,而是法官如是判决的证据。在策略上,法官预估到任何一种判决都可能引发某一方当事人的不满,这些“证据”实际上是为二审法官准备的,在这里法官借助了行政与社区力量来合法化自己的判决以规避上诉时被认定为错判的风险。 在解决纠纷最终产生判决的过程中,法官使用了他的“在地智慧”,广泛地调动了法律和从地方权威那里收集的地方性知识以决定这一难办案件中正义的方位并尽可能地去规避风险。坦率地说,法官的策略运用是创造性的,但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权威,也就是这些村、镇干部愿意为这样一个判决背书?事实上,这些地方行政领导完全可以拒绝法官访谈,完全可以拒绝在笔录上签字的请求。其一,这不是他们工作的范畴,村、镇干部及人民调解员没有义务去处理司法问题;其二,“依法治国”或者“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是政府官方话语和政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8)无论在现实中贯彻程度如何,这无疑可以成为他们拒绝在法官访谈文字上签字的“漂亮”而正确的理由。然而,这些地方官员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与法官是“熟人”。用法官的话,“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平日里,这个生存社区里的交集已经在他们之间积累了足够的了解与信任——地方干部也了解,如果有需要,法官也会帮助他们——这未必是一种友谊,而是一种在特定的互动模式与自利本性所建构的共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法院(法官)与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关联,诸如“政法委”或“综合治理办公室”之类的制度连结,也是日常的、生活的、个人关系层面的。所以,地方官员们签字的笔录不仅构成了支撑该案中法官判决的证据,也构成了法院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证明。 (二)案例二:一个由于政府拆迁而引起的纠纷 1.案件基本事实 丙和丁签署了一个大面积厂房的租赁合同。在合同签署时,有风声说房屋所在的这条街有可能要改建拓宽。丙,房屋的房东,为保证合同的稳定性,承诺如若遭遇拆迁,拆迁的费用将补偿给承租人,遂双方顺利签署合同。两年后,政府果然开始一条新路的建设项目,丙出租给丁的房屋属于征收的范围。丙由于拥有大面积的房屋,故在拆迁过程中和政府多次协商,并达成一致,愿意搬迁,同时获得了较高的补偿。(19)此时,丙拒绝将补偿款支付给丁,认为补偿的款项都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丁由于不满丙没有履行当时的合同约定而拒绝从即将拆迁的房屋中搬出。由于房屋的产权人丙已经和政府达成了拆迁协议,政府无法接受因为承租人丁的拖延而使整个新路建设的工期落后。所以,政府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责令丙立即清空房屋,履行已经签订的拆迁协议。与此同时,丁也向法院对丙的违约行为提起了告诉,两件案件被法院合并审理,最后用调解方式予以解决,丁同意立刻搬走,同时他也获得了12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原先丙、丁之间的租赁合同也宣告废除。(20) 2.案件处置过程 实践中,行政权力将难办案件交予司法部门解决的现象并不罕见。论及此事,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说: “政治人物可能将权力让渡给法院,这种方式可以混淆责任。无论是在民主还是威权体制下都会发现将棘手问题交给法院解决是有好处的,这将有利于保障精英阶层的共识,将公众的不满转移到别处,允许不满的公民有一个发泄的平台,也就保障了统治政党的合法性。”(21) 尽管中国的法院系统受制于政府,但法院一般并不愿意帮助政府处理房屋拆迁纠纷。一位法官告诉笔者,他们并不喜欢处理与拆迁有关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有可能将被拆迁者与政府的矛盾转移到法院。引用另一位法官的话:“我们不想被愤怒的拆迁群众包围,更不想成为政府的替罪羊,遭受抗议、游行甚至暴动。”换句话说,如果这类案件不能被恰当地处理,当事人可能对法庭比政府更为憎恨,并将法院看作政府的“同谋”,认为法院通过生产法律术语与大词来欺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能会采取某些极端手段,诸如自焚和杀戮,来报复和对抗法院。这种情况将不仅影响司法人员的升迁,而且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法院,如同其他所有的组织,一定包含有某种程度的自利,因此拒绝审理与拆迁有关的案件其实是明智的选择;而且基层人民法院的级别(副县级)高于镇政府(乡镇级),所以即使拒绝也没有太多的行政压力,完全可行。 另外,在法律上,中国的基层法院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不接受拆迁纠纷的受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22)换言之,法院也有充分的法律理由拒绝受理该起拆迁案件。然而,法院最终没有拒绝,因为镇政府与法院已经在长期的日常互动中建立了相互关系,和前一个案例相似,法院愿意在政府需要的时候予以援助,这也许不仅因为政治与制度安排上的连接,也因为生活中的互动——他们是熟人。 三、辩证理解运作中的法院调解 (一)法院调解的正面功用 1.扩大了法院的受案范围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院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拒接受理和拆迁有关的案件。不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地方法院也会出台一些司法意见限制当事人类似的诉权与法院的受案范围。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曾出台文件,将13类案件拒之门外。这些案件包括集资纠纷案件、非法“传销”活动而引起的纠纷案件、因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决定、体制变动而引起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计划划转过程中的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等、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的纠纷案件,但是直接支付给个人,未经集体经济组织安排发生的纠纷案除外,等等。(23) 然而,在上面陈述的案件中,法官却受理了这个拆迁案件。在技术上,他们对民事诉讼与民事调解作出细微的区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该规定可以被解释为,法院不能通过受理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处理拆迁争诉,但并没有明确禁止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的适用。在这里,民事诉讼与民事调解被区别开来,通过这个细微的区别性解释,法院调解使得这个拆迁案件可以被法院处理,当事人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无独有偶,在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与林权有关的诉讼也被认为是法院“不予受理”的范围。例如,在地方司法实践中,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规定: “以下纠纷不属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应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处理:(1)因林地被依法征收,对被征林地、林木补偿标准不服的;(2)因林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属不清发生争议的;(3)林地合法流转后,受让人私自改变林地用途,承包人请求对其进行处罚的。”(24) 然而,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中国西南地区的法院,在遇到林权相关案件时,也会通过法院调解的折中方式予以解决,使得林权纠纷最终能够被法院处置,尽管处置的方式不是诉讼。事实上,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正如一些学者强调的,中国目前正处在纠纷高发期。纠纷的种类、层次,涉及的当事人皆多样而复杂。(25)根据2010年《中国法治发展蓝皮书》,由于失业、社会两极分化、金融危机等原因,大量的社会冲突开始涌现。(26)其中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当今中国大量发生的刑事与群体性纠纷。(27)对于此,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也在其工作报告中确认,从1978年到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数量增加了大概20倍。(28)所以正常而言,越来越多的案件需要法院提供纠纷解决的途径。然而,由于政治与司法改革的滞后,(29)“法院正越来越多地通过不作为来处理复杂与敏感的案件:案件被拒收或被搁置。”(30)而与此同时,在肖扬主政最高人民法院的十年(1998—2008),调解是被专业化取向的司法政策所抑制的,调解并没有发挥其最大的功效。正如贺欣与裴文睿所言,“除了正式的第三方的商业调解,各种调解的受欢迎程度直到最近才止跌回升。例如,民事与经济案件通过司法调解解决的数量从69%和76%下降到了2001年的30.4%。”(31)然而,“非诉讼纠纷解决的程序可以适应具体的需要,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不同程度的调试。”(32)基于纠纷解决设计(Dispute Resolution Design)的理念,非诉讼纠纷解决可以创造不同的构架来处理常见的、系统性的纠纷,能够被运用于处置最一般与最不一般的冲突。(33)因此,对中国当下的司法体系而言,法院调解成为一个尚未被充分开掘的“富矿”,特别是考虑到它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所体现过的超凡的纠纷解决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法院调解能够给很多纠纷当事人提供一个法律的、官方的救济,这些人如果通过诉讼途径,很有可能被法院拒绝或什么也得不到。“聊胜于无”,虽然推进法院调解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并不能被看作制度性的革新,也无法解决现有司法体制中的种种结构性问题,但从一个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法院调解确实回应了一部分紧迫的社会司法需求,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冲突,用一种不同于诉讼的官方路径解决了人们的纠纷。无论如何,解决纠纷也是法院的一项基础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法院的受案范围以及权力被扩大了,这是法院调解给社会带来的益处。 2.善于处理困难案件 诺斯曾提到,在缺乏社会流动性、由大量熟人所构成的社区中,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如调解,会很好地运作。(34)然而对于一个由大多数是陌生人组成的城市,制度化的、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如诉讼,将会成为主导性的解决纠纷的方法。(35)这样一个理论似乎预设了社会的复杂程度与纠纷解决模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对于简单的社区,调解能够使用;而到了复杂的城市情境,调解的适用性将会受到明显的限制。然而,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进化范式显然过于简单,因为影响一个纠纷解决机制适用性的原因是复杂的,外部情境(context)仅仅是多个影响因素中的一个。例如,这种城市—农村,诉讼—调解的二分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多中心纠纷(multi-center dispute)的存在。在前面提到的继承纠纷问题中,调解明显是一种更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因为调解本来就善于处理家事问题;(36)但更重要的是,调解可以帮助法官处理这种多中心的复杂案件,并避免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避免不合适用诉讼处理的冲突进入诉讼途径。 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区域发展具有巨大的不平衡性,区域文化与社会生态具有异质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习惯、习俗、民族传统、文化规训、禁忌与国家法长期并存,并有可能产生竞争与冲突。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状况产生了一种复杂、困难的纠纷类型——多中心案件。“多中心案件”这个词是富勒(Lon Fuller)从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polycentric”的概念挪用过来的,富勒认为,有一些案件在本质上就不适合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予以解决,因为在这些案件中,存在彼此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状结构”。富勒认为: “我们可以通过想象一个蜘蛛网来想象这种情况。拉动蛛网的一端将会给整个蛛网造成一种复杂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拉力上使用两倍的力量,将有可能产生的不是简单的两倍的张力,而会创建一个不同的复杂而紧张的模式。这肯定会发生,例如,如果翻倍的拉力导致的一个或多个脆弱的线索折断。这是一个‘多中心’的情况,因为它是‘多中心’——每个交织的节点都是一个独特的分配的复杂张力的中心。”(37) 虽然富勒没有直接谈及上述这个穆斯林继承案件中的法律多元问题,但他却启发我们去看到在“多中心案件”中,“诉讼裁判(adjudication)无法恰当的引导当事人去理解纠纷的多重面向(multifaceted)……对抗制程序会简化很多冲突,因此,很多法庭处置的案件不过是其最终解决纠纷前的一个步骤而已。”(38)对于富勒而言,传统的诉讼裁判在面对多中心案件时是有困难的,这样的状况一旦出现,就要求法官使用非正统的方式,如调解,或者要求法官对“问题加以改造以使之能够适应诉讼裁判的处置程序和标准。”(39) 在中国,考虑到国家之广大,国情之复杂,区域差异与异质性之深刻程度,却有很多并不适合通过传统的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裴文睿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富勒的观点。在谈及中国的司法状况时,裴文睿说:“中国司法化程度有限的重要原因在于法院并非是处理很多在中低收入国家生成的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的最好的平台。正如在一些财富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法院(及其机构)都是相对羸弱的。更进一步,很多现实问题无法以司法裁决的方式予以处置——但就法院而言,它们常常连有效与可执行的救济都提供不了。”(40)在西南中国,这种法律多元的状况非常多见。处于中国的转型时代在转型时代,西南中国有大量的人口迁移,这构成了现有社会高度流动性及其与传统社会的张力。由于多元族群与文化形态的并存,国家法对社会的介入存在独特的境况与挑战。例如,在云南,著名回族学者纳麒就认为:“由于自然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云南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和落后的状况下,而以农村为主体的回族聚居区的封闭性和落后性更显突出,这对回族社会生活造成的最真实、最直接的后果是,云南回族社会比之发达开放地区的回族社会更完整、更全面地保存和坚持着传统的伊斯兰教准则和习俗。”(41)所以,在文化多元的地域,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家,多种共生的秩序、习俗、价值与制度都构成了对国家法的挑战与法律多元、多中心纠纷等问题。在这种情境下的调解适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熟人社会中的适用性问题,在世界版图的意义上看,这是一个外生文明在进入本土文明、产生文明杂合状态后,一种秩序紊乱与竞争状态中的纠纷化解之道。 如前所陈,有一些学者相信调解主要适用于那些发生在特定社区或者特定群体内部的纠纷,在很多情况下,纠纷的解决接近于某种程度的道德判断。(42)然而,依循Fuller的思路,调解的适用大大超过了传统社区这一限定,它能够为多中心与复杂纠纷的解决提供一种可行的制度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法院调解是一种在西南中国解决此类纠纷的理想方法。 除此之外,法院调解处置复杂案件的成功经验也会对争端解决的制度设计产生建设性的作用。根据门克尔-梅多(Carrie Menkel-Meadow)教授的研究,“很多重要的人类社会的变迁都是通过冲突中的努力争取而得到的,这些经验会改变人类的制度安排,人际关系以及理念”,(43)并“通过建立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来维持社会作为个整体系统的稳定。”(44)换句话说,法院调解在处理复杂案件中所积累的经验可以被学习并被有关机关制度化。对此,范愉教授就指出,ADR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可以积累纠纷解决的经验,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勾勒和定位权力、义务在新型纠纷、全新语境、复杂状况中的具体界限。(45)这些经验在我们重新设计与建构社会法律体系,或订立新的法律时可以成为重要的参考。对于中国来说,这为解决“多中心”和复杂的纠纷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现实制度安排及与社会现实细微互动的具体情境。“因此,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的探寻可能被理解为一个更准确的定位裁判的位置的问题,或者在连续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定位司法裁判的更合理方位。”(46)基于这些经验,司法机关可以找到一个现实的和具有语境性的,而不是理论和理念化的路径,来制定纠纷解决领域的规则与法律。 (二)法院调解的负面问题 1.对个人权利的损害 由于允许在“法律的阴影下讨价还价”(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law),法院调解有可能对正义产生损伤。而这种情况在上面拆迁的那则案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与调解不同,司法裁判具有“……‘明显的朝向过去的取向。’它们解释与评估法律原则,过去的行为和事件,已然造成之权享(entitlement),建立的义务和诉求。”(47)然而,法院调解的终极目标是找到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妥协结果,然后让当事人延续他们从明天开始的新生活。所以,调解更多是面向未来的: “当人们第一次出现在调解的办公室,他们想做的都是去谈论过去……继续的讨论过去不可避免地让调解员扮演了法官的角色。寻找一个解决方案要求将关注的重点移向未来,因为解决方案在未来才会出现……调解员没有兴趣讨论或评估关于过去的抱怨,而会将纠纷当事人的讨论重新定位对未来的期望。”(48) 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合法与非法通常被认为是纠纷当事人和调解员不应该过分关注的内容。毕竟,“决定过去谁是正确或错误的这是法官的工作,而非调解员。”(49)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调解会较少地关注成文法的规定。说到法院调解的本质,苏力教授就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去坚持所谓的“依法调解”,因为调解并不是一个司法裁判的过程。苏力说: “要想促进调解的发展,就必须适度摆脱法条的约束,放松对调解的‘依法’要求。第一,调解可以依法,但着眼点不是依法,而是调解成功。第二,从社会角度来看,背离了法律的调解不一定就不公正,相反可能丰富对法律的理解,创造新的法律。第三,在不关注是否依法的调解中,法律仍然在起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始终会成为调解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第四,调解中只要求作为调解者的法官不能从中谋利、有意偏袒一方,调解结果基本公道,距离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不能差距太大或过于迁就陈规陋习。”(50) 但从法官的角度看,他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来调查事实,维护正义。(51)根据中国的法律,“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也是法定的法官职责。在上文提到的拆迁案件中,出租人为了最大化其利益,声称租赁合同不再有效,需要修正合同内容。纯粹从技术上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房屋出租方可以主张由于客观情势相较于原合同签订时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基于此,他可以提出对原合同内容进行修正的要求。(52)而事实上,所谓的客观情况较之合同签订时确有变化,因为房屋出租人获得了比一般住户更多的补偿。然而,这个原因他无法公开说出口,并提供相关证据。这是因为在拆迁时,补偿标准对于所有统一地区的住户而言应该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该房屋出租人还会获得更多的补偿呢?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负责拆迁的部门和官员同意给他更多补偿?是否有“猫腻”或腐败在“桌子底下”发生?有其他违法行为吗?在法院调解过程中,因为这些问题都关乎过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以求快速地达成合意,案结事了。因此,那些在同一区域居住的住户的利益和权利就有可能受到伤害,他们对这个不公平的补偿并不知情,因为发生在调解室中的谈判与调解过程是保密的。在这种情况下,该案的解决包含了对不公正的容忍,在解决纠纷的同时有可能牺牲了第三方或者其他公众的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对正义可能的漠视在“调解优先”和“和谐社会”的大气候下能够被正当化,政治上是正确的。相反,如果该案走入司法诉讼渠道,它可能导致严重的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如果主审法官将该案导向诉讼,就有必要让出租人一方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在多大程度上补偿高于正常的情况以至于造成了显著的情势变更,导致了合同的无效。然而,这些问题都是很难在法庭上当众讲明的,因为很多具体的谈判、博弈与利益交换都是出租方与拆迁部门在桌子底下完成了(53)。所以,如果这个案子用诉讼处理,在证据方面会遇到非常尴尬的状况。更进一步讲,如果该案通过诉讼处理,案件将被公开审理。(54)那么,这个并不公平的补偿将会被公众了解,这有可能引发公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愤怒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这样的解决结果将会是非常糟糕的,法院和法官会被认为是制造了纠纷,而非维护了和谐。 事实上,这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私人过程产生了公众效应”(55)的案例。在一些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调解过程也可能对第三方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56)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交易行为可以将其产生的所有成本和利益全部内部化(internalize),则政府没有必要对交易行为进行干预。但是,如果交易行为产生的利益与成本无法内部化,为了防止这些外溢的部分对第三人可能造成的损害,外部公权力就有可能介入干预。从某种角度看,公权力的干预有时就是法院与法官的司法介入,他们应该保证案件不会对无关的第三方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在这个拆迁案件中,法院调解的使用恰恰是正当化了那些对第三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所有居住在该拆迁区域内的居民的权利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因为补偿的金额并不公正。然而吊诡的是,这个不公正补偿的后面,有法院的“正义背书”。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是:如果纠纷中可能产生明显的外部性(externality),法院调解的功能可能被异化。调解可能被利用来粉饰、遮掩这些不良行为,而这种粉饰、遮掩在“大调解”的政策框架下很有可能被正当化,因为“大调解”就是追求案结事了。这种结果主义导向的政策可能让法官更加能动地追求和解的现实结果,但也可能忽略方式方法的正当、法律规范的捍卫以及当事人的权利。 2.上诉审的消失 由于法院调解在一审案件中的大量使用,二审案件(上诉审)有可能急剧减少。即使有部分案件进入上诉程序,他们有可能被二审调解所消解而不会形成上诉审的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 “大力做好再审案件调解工作。对历时时间长、认识分歧较大的再审案件,当事人情绪激烈、矛盾激化的再审案件,改判和维持效果都不理想的再审案件,要多做调解、协调工作,尽可能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对抗诉再审案件,可以邀请检察机关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对一般再审案件,可以要求原一、二审法院配合进行调解;对处于执行中的再审案件,可以与执行部门协调共同做好调解工作。”(57) 因此,这种“大调解”的制度安排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制度紊乱,毕竟上诉审对于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特别是一个大国的司法体系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贺卫方教授曾对此作过非常清晰的梳理: “法院分上下级的功能有二:一是为不满意一审判决的当事人提供一个独立的重新审查机会,以增进司法决策的审慎和公正;二是通过上级法官对下级法官判决中法律解释的审查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所辖范围内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不必说,最高法院的主要功能之一乃是确保全国范围内的法制统一。要实现通过司法的法制统一,各个上诉法院之间需要就法律解释建立某种协调机制,更需要对最高法院的功能加以界定,重要的是,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作为一般法院处理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而只审理那些具有法制统一意义的法律争议。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本身也必须受到自己已经作出的法律解释的约束,不可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以确立法律解释的可预期性。”(58) 中国是一个大国,内部蕴含有大量的不平衡,异质性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法治的统一就显得格外重要。没有了上诉审,对于基层法院差异的、多样的、不规范的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就无法有效地予以管控和检查,这也就很难确保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也只有在司法体系里发生的对法律的辨认与适用才能为当事人在面临类似处境时提供一种事前的可预期的指引规则。(59) 四、结语 即使在这个被调查的西南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社会的异质性与社会价值的多样性依然存在。城市的居民,乡村的居民,少数民族居民,他们差异化的价值与习俗共存,社会转型依旧任重道远。西南中国某市的这些社会现实催生了涉及法律多元问题的“多中心”案件的产生,这使得强制、僵化地适用国家法变得愈发困难,需要一种灵活而机动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在地”设计。确实,如果纠纷中涉及了彼此冲突的基本政策目标与价值理念,无论最终的判决为何,司法裁判在适用时都会显得非常困难。更不要说这样的案件判决在执行上,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至少极端困难。(60)因此,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法院调解扩大法院可受理案件的范围,并且擅长处理在这种多元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多中心”难办案件。在这个意义上,法院调解对于所调查的城市社区是具有适用性的,它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了更有效的司法救济与具有灵活性的纠纷解决方案。 然而,由于当下中国的调解政策过分强调其实用与政治功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社会不稳定的“应急反应”,从而缺乏系统的设计与全面的考虑。虽然实现正义与解决纠纷都是法院的基础功能,两者也有重合的部分,但在宏观司法政策上对两者不同的偏好确实有可能将当事人带往不同的方向。在今天的中国,法院系统的核心任务就是处置纠纷,案结事了;在这样一个以纠纷解决为核心导向的司法政策下,法官有可能将调解泛滥地用于并不适合调解的案件中,并忽视正义。事实上,纠纷当事人、调解员以及纠纷的特点与性质都会对法院调解的适用性与有效性产生影响。对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其实“心知肚明”,在2010年颁发的司法解释中,它明确指出: “科学把握当判则判的时机。要在加强调解的同时,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注意防止不当调解和片面追求调解率的倾向,不得以牺牲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代价进行调解。对当事人虚假诉讼或者假借调解拖延诉讼的,应依法及时制止并做出裁判;对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方案显失公平,勉强调解会纵容违法者、违约方,且使守法者、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受损的,应依法及时裁判;对调解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投入的成本与解决效果不成正比的,应依法及时裁判;对涉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或者对形成社会规则意识有积极意义的案件,应注意依法及时裁判结案,充分发挥裁判在明辨是非、规范行为、惩恶扬善中的积极作用。”(61) 所以,确有不少类型的案件是不适合用调解解决的。但由于“政治挂帅”,上面这些最高人民法院明知的规则在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以,当下中国法院调解法予以规制的重点,应该是坚决地排除一些调解不应适用的案件类型,这样的案件法院系统不能用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一个现实的改革起点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明确重申对法院调解的适用限制,对于那些不适宜用调解解决的案例,在纠纷解决方式选择时,应该坚决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排除调解的适用。至少应该让法院系统遵守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发布的上述不适用调解的司法规则。这样的限制可以有效地防止调解的泛滥,并避免由于过分追求调解率而导致的上诉审的消失。 最后,由于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运作的高度关联,政府与法院之间的合作会加强。例如,中国各个地方所成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办公室”就是其中的例子。依据有关说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 “根据全国社会治安状况,研究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供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对一个时期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出部署,并督促实施;指导、协调、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重大措施;总结推广实践经验,表彰先进,组织有关部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研究,探索和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维护社会治安的新路子;办理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有关事项。”(62) 在实践中,除了政法委,法院与其他有关政府部门也会被一道地安排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办公室”的制度框架中来。一般而言,法院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在面对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时,需要和政府部门协同合作,解决问题。所以,“大调解”政策和对纠纷解决的强调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审判独立。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不应该被夸大和意识形态化。正如前文中谈到的,地方法院深深地嵌入地方社区与中国的政治、司法结构中。所谓的“大调解”政策,作为一种应急的技术性制度安排,不可能改变中国地方社会的基本风貌,也不可能刷新中国的基本体制结构。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共生与依赖早已有之,并非由“大调解”政策到来而来,也不会随“大调解”的政策消退而去。因此,即使有影响,笔者认为“大调解”政策对审判独立的影响也应该是有限的,至少需要更细致、更精微的经验研究数据予以支持。 除了上述这些政策建议外,本文还无意间触及了一个方法论的“角落”,即我们在个案研究的选择时,应该也留意那些“失败的个案”。理由很多——第一个原因,也许有些浪漫。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琳娜》的开篇中写道:“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用社会科学焦躁干枯的语言来重述文学巨匠对社会生活具有洞见性的这个理解——托尔斯泰也许是在说:失败的原因,是一种离散的、分立的,难以“一言以蔽之”的,需要个体识别的状态。他用文学家的敏觉视角提示我们,成功或者幸福具有规律性的本质特征,反而是失败或者不幸才能更生动地曝露人类命运的偶然、社会机制的复杂,以及存在方式的多样。这种判断在广袤的思想史丛林中并不罕见,孔子在《论语·里仁》一章中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伦理角度理解,无外,这是一句儒家劝世的叮咛教诲,但如果从社会科学的立场出发作以阐释,孔子也是在讲两种不同的经验类型,成功的与失败的;并提示后人,如果同时关怀这两个类型,将会更加立体地、复合性地成全我们对世界差异面向的理解——正向的经验,让人“齐”,(63)其内在统一的规律性价值能提供向往、标准、参照;负面的经验,则让人“省”,它可以提供理论研究者一个更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反身立场。所以,个案的价值是可以在正、负两个坐标系统之中都作出精彩的标定。本文中的两个个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失败”的调解——一个是调解因受到阻却而无法发生,一个是调解隐匿真实而可能削伤正义。但“失败”调解个案,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参与观察失败的个案,珍惜失败的个案,力求理解失败历程,并对散碎的失败状态进行必要的归纳,这也可使智识得以积累与发生。而这个面向,即“面对失败的个案”,大概我们法律经验研究者经常忽略的问题——也许不仅是法律经验研究,法律教义学的重点很多时候也是所谓“伟大的判例”,(64)就是那些“成功”地改变社会生活的法律事件;由此,失败的叙述被遮蔽、被取消、被浪费。 第二,如果我们从交叉学科的视野出发,关心失败案例就非常普遍了。也许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失败造成的伤实在太痛,很多成功与失败的对照,实在刺目地让人无法回绝。例如,为什么很多国家的社会转型成功了,而很多国家没有?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民富足而康乐,而很多国家没有?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保持经济的持久增长,而有的国家没有?为什么有的政策可以有效地被贯彻、履行,而有的则没有?是的,在政经的大坐标里,很多失败甚至比成功还要显眼,在全球的成绩单公示之时,那些失败“差等生”的“父母、亲友与师长”一定会无比关切地询问:“我们家到底怎么回事?”而现实中,却也有好事者对全球各国的各种政经表现作出评价,一个直接的但让人感到不愉快的评价来自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与美国“和平基金会”共同编制的失败国家指数(Failed States Index)(65),这个指数赤裸裸地曝露失败与成功的显在距离,并指引我们去思考造就这些差距的理据。作为局外人,失败也许只是一连串的数据、排列,是需要久久滑动鼠标才会看到的位于统计底部的名目。而对于亲历者,失败就是入骨的痛。因为失败所致的痛苦,以及对比所致的困顿催生了理解国家的失败、理解政策的失败、理解历史的失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基本问题意识。(66) 第三个原因,关注田野中的“失败个案”(在笔者上面的研究中,就是指注意一些没有调解成功的个案),可以提高调研效率,优化田野过程。很多有经验的学术同仁都会同意,富有成效的田野工作很多时候需要运气。在进入田野前,我们总是太期待精彩的密集迸发,但很多时候,正好相反,现实是重复、乏味、平庸、琐碎的,其似乎所能呈现了的也只能是毫无新意的累赘而劳乏的生命状态。这种观察视角的困顿,除了缺乏对细碎问题中的意义可能性的敏感,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将所有的视域都聚焦于对“成功”个案的期待,与此同时便忽视了有价值的不成功个案。好的、具有价值的不成功的个案可能已经在身边,却因未被学术检视而消逝。理解成功的个案可以创造好的经验研究,理解个案的失败,也可以。 第四,关注“失败个案”涉及一个学术人的人文关怀。法律学术对现实的介入,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学科,也许其目的包括了(虽然不仅限于)让制度下的个体更为富足康乐、更为和洽自如,这是法律学术的应有之义。我们的田野参与,我们的学术进步,不仅只是为人类的智识增长出力,也应该福泽更多的被学术的目光打量过的地方。追逐成功是本能,多数人只向胜利者致敬。所以关心失败的个案,是一种力图改变现状的善良与勇敢道义力量,是一种不被现实赎买的达观与抗议精神,是一种对失败者,落魄、孤独、无奈、彷徨的同伴的照看。这是一种闪耀的学术慈悲。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的所有论述及结论仅对西南中国负责(也许在某些中国的欠发达地区也有相类似的状况),本文的结论不能,也不应该被普遍化成为对中国整体的解释或结论。本文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的发达地区,如北京和上海,是否有解释力,还需要有进一步的学术接力与实证研究。 注释: ①See Benjamin L.Liebman,“A Return to Populist Legality?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Legal Reform” in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Perry (eds.),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65-188. ②胡云腾:《“数说”调解》,载《人民法院版》电子版,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3-03/11/content_59561.htm,2013年3月13日访问。 ③ZHANG Xianchu,“Civil Justice Reform with Political Agenda” in YU Guanghua ed.,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Change and Challenges (New York:Routledge,2010),p.253. ④Jerome Cohen,“On the Three Supremes”,载http://blogs.law.harvard.du/guorui/2008/10/23/jerome-cohen-on-the-three-supremes/,2011年3 月30 日访问。 ⑤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6页。 ⑥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可简称为ADR,中文常被译作“非诉讼纠纷解决”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是指“除了诉讼以外处置纠纷的一种方法程序。”具体而言,ADR包括协商、调解、独立调查员、迷你审判、诉前会议、仲裁、案件管理、租用法官等形态。详见Albert K.Fiadjoe,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 Developing World Perspective (London:Cave ndish,2004),pp.19-20;亦见Richard C.Reuben,“Public Justice:Toward a State Action Theory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May 1997)83(3) California Law Review 577,580,footnote 3。 ⑦关于这些争论的一个粗略的文献综述,可以参见Chapter 4:The Debates around Civil Justice and the Movement Towards Procedural Innovation in Simon Roberts and Michael Palmer,Dispute Process:ADR and the Primary Forms of Decision-Mak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nd ed.,2005),pp.45-78. ⑧Marc Galanter,“‘...A Settlement Judge,Not a Trial Judge:’ Judicial Med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Spring,1985) 12(1)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13. ⑨XU Xiaobing,“Media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Towards Common Outcome”(2003) Unpublished JSD 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School of Law,p.9. ⑩Tony Saic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3rd ed.,2011),p.9.一些体现这种区域差异的数据,可以参见HU Angang,“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WANG Chaohua ed.,One China,Many Paths (London; New York:Verso,2003),p.222。 (11)Elizabeth J.Perry,“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State-Society Relations”(1994) 139 The China Quarterly 704,712-713. (12)本案是笔者在西南中国某省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的,案件事实与过程来源于笔者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观察、访谈以及最后的调解协议。本案的当事人及主审法官均同意笔者获取和使用本案的事实数据,但为了保证匿名,与纠纷参与人身份有关的可识别信息在叙述中均已省略。 (13)根据《继承法》第3条第2款,遗产包括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第9条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第10条规定了遗产的继承顺序: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第13条第3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所以,即使被告在赡养父母时承担了主要义务,并不能在法律上排除原告对房产的继承权。而根据《物权法》第93条,“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据该法第97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14)法官几乎不敢这样去做,因为当地无论在历史还是近代,发生过多次严重的回汉冲突。 (15)2007年12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上强调:“维护人民权益,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目的。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载http://www.taiwan.cn/sy/rdxw/200712/t20071225_507440.htm,2013年3月15日访问。200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讲话中指出:“实现由知识型培训向知识能力并重型培训转变,提高年轻法官熟谙民情、了解民意、消解民怨的综合能力。”http://www.court.gov.cn/xwzx/rdzt/rmfg/rmfgyw/201003/t20100304_2300.html,2013年3月15日访问。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载http://www.court.gov.cn/qwfb/sfwj/yj/201008/t20100811_8489.htm,2013年3月15日访问。 (17)根据笔者的调查,在不少西南中国的基层法院内部都存在明确、细致的绩效或积分机制,如有涉诉上访发生,相关法官在绩效上被严重扣分,这将对法官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18)Benjamin L.Liebman,“A Return to Populist Legality?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Legal Reform” in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Perry (eds.),Mao's Invisible Hand: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68. (19)根据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3之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至于补偿标准,第24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70680.htm#sub5454986,2013年3月15日访问。但这些规定较为抽象,具体的补偿数额,并没有清楚的标准。在省、市一级政府关于拆迁赔偿的规定,也只是相对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具体的赔偿标准。在实践中,同一个地区的赔偿数额应该一致,但由于不同的谈判能力和具体情况,对于不同的被拆迁户,赔偿数额在具体实践中会有不同,甚至明显的差异。 (20)本案是笔者在西南中国某省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的,案件事实与过程来源于笔者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观察、访谈以及最后的调解协议。本案的当事人及主审法官均同意笔者获取和使用本案的事实数据,但为了保证匿名,与纠纷参与人身份有关的可识别信息在叙述中均已省略。 (21)Randall Peerenboom,“More Law,Less Courts:Legalized Governance,Judicialization,and Dejudicialization in China” in Tom Ginsburg and Albert H.Y.Chen (eds.),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9),p.187. (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载http://law.baidu.com/pages/chinalawinfo/5/96/fab4e56fc7ac7563361dc46bb3c76e91_0.html,2013年3月15日访问。 (23)Benjamin L.Liebman,“China's Courts:Restricted Reform”(2007)21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1,27,以及《新京报》的新闻报道,载http://news.sina.com.cn/c/2004-08-12/12133382459s.shtml,2013年3月31日访问。 (2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林权民事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2010年第9期),载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lgs/s/2593/content-401468.html,2013年3月31日访问。 (25)胡联合、胡鞍钢、王磊:《关于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载《探索》2007年第6期,第105页。 (26)参见李林:《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7)Dali L.Yang,“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olitical Discontents in China:Authoritarianism,Unequal Growth and the Dilemma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2006)9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43,152-153. (28)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工作报告》, 载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3/17/content_11024682.htm,2011年3月13日访问。 (29)SONG Jianli,“China's Judiciary:Current Issues”(2007)59 Maine Law Review 141,147. (30)Benjamin L.Liebman,“China's Courts:Restricted Reform”(2007)21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1,27. (31)Randall Peerenboom and Xin He,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Patterns,Causes and Prognosis (2009)4 East Asia Law Review 1,25. (32)Henry Brown and Arthur L.Marriott,AD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Sweet & Maxwell,1993),p.17. (33)Andrea Kupfer Schneider,“The Intersection of Dispute Systems Desig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2009)14 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289,289. (34)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Winter 1991)5(1)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7,99,103. (35)同上注,第104页。 (36)参见Yolanda Vorys,“The Best of Both Worlds:The Use of Med-Arb for Resolving Will Disputes”(2007)22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 871,871-872。在许多法域,与家庭事务有关的纠纷是由一个专门的法律机构像家庭法院,来解决的。例如,在日本,由于传统文化和家事纠纷的特点,家庭纠纷将由家庭法院系统来处理。在这个家庭法院中,有法官、家庭问题的专家,以及社会工作者共同工作,他们可以帮助双方冷静下来,和平地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调解往往是首选。家庭法院一直被视为日本第一代司法改革中一个巨大的成功。笔者感谢日本中央大学的Stao Nobuyuki 教授分享这一信息。更多关于日本家庭法院系统的细节信息,参见Hiroshi Oda,Japanese Law (London; Dublin; Edinbur gh:Butterworths,1992),pp.73-75,以及 Taimie L.Bryant,“Family Models,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 and Family Law in Japan”(1995)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 14(1)1。 (37)Lon L.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1978)92 Harvard Law Review 353,395. (38)Herbert Jacob,Justice in America:Courts,Lawyers and the Judicial Process (Boston:Little,Brown,4th ed,1984),p.12. (39)Lon L.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1978)92 Harvard Law Review 353,401. (40)Randall Peerenboom,“More Law,Less Courts:Legalized Governance,Judicialization,and Dejudicialization in China” in Tom Ginsburg and Albert H.Y.Chen (eds),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9),p.190. (41)纳麒:《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42)Philip C.C.Huang and You Chenjun,“Mediation and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Law”(2009)3 China Law 2-7. (43)Carrie J.Menkel-Meadow et al.eds.,Dispute Resolution:Beyond the Adversarial Model (New York:Aspen Publishers,2005),p.7. (44)Lewis Alfred Coser,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Free Press,1956),p.34. (45)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 (46)D.Paul Emond,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Ontario:Canada Law Book,1989),p.4. (47)Roger Cotterrell,The Sociology of Law:An Introduction (London; Dublin; Edinburgh:Butterworths,2[nd] ed,1992),pp.211-212. (48)John M.Haynes and Stephanie Charlesworth,The Fundamentals of Family Mediation (Sydney:The Feferation Press,1996),pp.13-14 and also Stephen K.Erickson and Marilyn S.McKnight,The Practitioner's Guide to Mediation:a Client-centered Approach (New York:Wiley,2001),p.25. (49)同上注。 (50)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13页。 (51)Philip Hamburger,Law and Judicial Dut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03. (5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之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53)也许在实际中,搬迁补偿在某一范围内的上下浮动是一种惯例,但这种行为仍然是不公正的,是法律需要去检视的而不是去背书的内容。 (54)《民事诉讼法》第13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55)See Andrew T.Guzman,“Arbitrator Liability:Reconciling Arbitration and Mandatory Rules”(2000)49 Duke Law Journal 1279,1284. (56)See James A.Wall and Timothy C.Dunne,“Mediation Research:A Current Review”(2012)April Negotiation Journal 217,233. (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第12条,载http://www.court.gov.cn/qwfb/sfwj/yj/201008/t20100811_8489.htm,2013年3月30日访问。 (58)贺卫方:《统一之道》,载http://test.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9495,2013年4月1日访问。 (59)Vicki Waye and Ping Xion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tion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 in China”(2011)6(1)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Article 2,2. (60)Randall Peerenboom,“More Law,Less Courts:Legalized Governance,Judicialization,and Dejudicialization in China” in Tom Ginsburg and Albert H.Y.Chen (eds.),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9),p.187. (6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第12条,载http://www.court.gov.cn/qwfb/sfwj/yj/201008/t20100811_8489.htm,2013年3月30日访问。 (62)参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114/64136/88838/5999186.html,以及玉溪维稳:http://www.ynda.yn.gov.cn/ynszfwyh/3892517452931661824/20090615/19130.html,综治维稳的基本信息:http://baike.baidu.com/view/2938302.htm,2013年4月2日访问。 (63)《说文解字》界定“齐”为“禾麦吐穗上平也”,就可以理解为一致、齐平,一种标准的内在统一。 (64)苏力教授在评论本文时指出,其实大量的研究都在研究所谓是“失败案例”——上诉审是一审的失败,而上访则可能隐含着司法公力救济的失败,这是对“失败案例”的一个广义定义,可以提醒我们更多的关心问题而非修辞。但这种广义定义和本文在方法论意义上强调“失败案例”有微妙差别。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失败案例事实上是突出了田野过程的“去目的性”,或者再次强调扎根理论的一些基本价值,即抛去一些过于强硬的问题意识和预设,而是反身而诚,有可能浸泡在田野中,在意那些碎片的、不成功的、非戏剧性但却在日常中弥散的田野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凝练和萃取质性研究的精华养分,并提炼成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在全过程的意义上体认田野现场的发生历程,即使那些并不耀目或显在的关于上诉审或上访的案例过程,那些其中的小瑕疵、小障碍、小局限,那些不成功或庸碌的浅白过程,都可以成为值得被学术关注的对象,被赋予学术价值。 (65)例如,这是2013年的排名,载http://ffp.statesindex.org/rankings-2013-sortable,2014年11月26日访问。 (66)例如,美国著名批判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的著作《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和践踏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就是一本检讨美国是否能够通过政治干预而改变失败国家命运的书。标签:法院调解论文; 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法院论文; 司法确认制度论文; 司法调解论文; 拆迁律师论文; 法制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