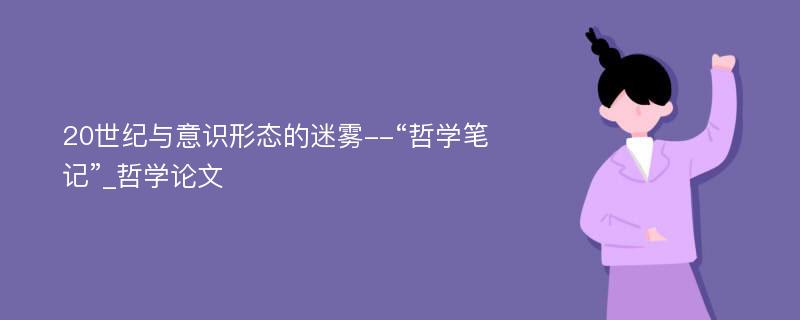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与意识形态迷雾——哲学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迷雾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即将谢幕的二十世纪百年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内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曾经笼罩着极左思潮的迷雾,意识形态的执偏与纷争更是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唯物主义的断章取义地进行“绝对真理”的一厢情愿的确认,以及对唯心主义同样断章取义地进行“极端谎谬”的一厢情愿的定性,成为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思想界与理论界的主流思想。甚至在那个时代曾有人肩负起了唐吉诃德的使命——用唯物主义征服世界,给自己在哲学王国里筑起天朝大国的威严,期待着有一天让所有的偏离了自己阵营的哲学命题最终都皈依自己。
要理解哲学,就要理解哲学的全部,要理解它的正面与侧面、目标与过程、现实与背景,而不能从庞大的哲学论证中归纳出一个囊括了全部意义的结论。实践表明,这个所谓的囊括了全部意义的结论,往往是人的主观臆断,然后以这个主观臆断而以讹传讹。哲学对人的价值就是哲学本身所展开的意义,哲学是很崇高的东西,而我们一些人却把它理解得象加减法一般容易,试图让全体人民都来捧着哲学,分享与智慧为友的乐趣,这看似对哲学的推崇,实则是把哲学嘲弄了。在德意志民族的土壤里曾经培养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爱因斯坦、来布尼茨等哲学大师,这些哲学大师又以他们深邃而辉煌的思想熏陶了德意志民族理性的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哲学已经缺欠了许多,我们缺乏逻辑,所以人们的观点总是千锤百炼般的顿悟,却无法用三段论广阔地展开,我们的哲学依据的是直觉,句子精致,意味无穷,但又众说纷纷,一部伟大的《易经》(没有作者),神秘得如同黑洞,足以把中国人都引入迷宫,为解开一个卜卦而绞尽脑汁,花了那么大的心思,最后还是众说纷纷。是《易经》太深刻了,还是中国人的理性蜕化了呢?从哲学史来看,中国式的哲学家首先是伦理学家,哲学一发生就试图指点人们的生活,哲学是相当世俗的。许多学者都承认,中国人崇尚的是实践理性,这是一种油滑又聪明的解释,但仅此已把西方的思维和东方的智慧区分开了。我们不可否认,哲学在实践中要表现出功利性,哲学在它的童年时期就有济世的传统,纵然它曾在象牙塔里作过暂时的停留,哲学的功利性不是哲学存在的唯一理由,但的确是哲学存在的一个理由,要不,哲学的存在难道是为了让人伤透脑筋吗?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哲学可以不顾一切,跃入人间和一些琐碎而具体的现象打成一片,我们的悲剧就在于试图把哲学变得可操作,试图把哲学道理用自己浅薄的才智解释得通俗易懂,完全把哲学公式化、政策化,哲学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从哲学的童年起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就陷入了恩恩怨怨的论争之中,许多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蓦然发现,两唯之争并没有给各自带来什么益处,他们都没有能力让人们只相信其中一方,倒是不少有识之士渐渐从这旷日持久的论争中解脱出来,开始认清了各自的破绽。从两家开始对垒的第一天起,物质和精神在人的思维中被分裂了,唯物主义者声称在它们的帐下,世界统一了,可实际上他们却表现出对精神的病态般的歧视、敌视。这样,在唯物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死寂的、冰冷的。物质和精神在观念中的分裂,是唯物唯心之争造成的,当唯物、唯心两大阵营能握手言和时,物质和精神从观念和现实中才能得以白发重逢,而这时的哲学又正好和宗教成了一家子,所不同的是,哲学研究坎坎坷坷,而宗教自始至终都认定了“色心不二”的深刻而又简单的道理。(汤因比深切地呼唤并预言,下一世纪将是宗教来拯救世界,因为,世界的发展是令人担忧的,在现实中,经济(现代化)与伦理竟是那样不可调和。宗教的使命是想使二者统一起来)。
可以说,哲学正在从总体上由旧的形态向新质转化,并且在转化过程中痛苦地否定自己建立起来的价值,它既是救世主又是平民,它既要拯救人类也要拯救自己,哲学这种自我意识使其正在逐渐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共注的价值,这对于消解低层次的意识形态的纷争,消解哲学流派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割据状态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哲学形态: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没有任何理由回避一些全球性的主题,如胡塞尔所说“当人类的命运成为儿戏,生活受到巨大的危机威胁之时,哲学发挥着救世主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哲学必须把一些问题放在一边,提出能够指导历史生活的问题”。布莱顿大会的主题是“对人的哲学理解”。这表明哲学经过漫长的逻辑历程又回归到人本身,人是哲学真正的家园,人最典型的体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完美结合。二十世纪末最深刻的困境是人类自身,人与物的对立危及了人的生存,而人的贪欲的肆忌发挥又加剧了危机的提前到来,因而,对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发展的关注是任何哲学流源都无法否认的,或许在这个层次上,哲学是共性的,统一的。在低层次上,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上试图统一哲学对现实的解释的做法,是哲学异化的表现,而这正是哲学百年来的困惑。
二
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应是包含神话、道德、习俗、哲学、艺术等等,而发展的结果往往是其中的某一个要素垄断了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的代称,并且用这种意识形态规定、假设了世界存在的理由和前景,这便意谓着意识形态的发展更加远离意识形态本身,这种具有“霸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含着某种难以弥合的缺憾——无法完整地理解世界的丰富多彩。人是意识形态的创造主体,意识形态天然地接受人的检阅和选择,而发展的结果是意识形态规定了人的生存和命运。人们相信并甘愿接受意识形态的召唤、激活、安慰,甚至是欺骗,这是人的悲剧。仅仅是意识形态选择人,便意味着在这个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物质力量,当这种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时,意识形态对人的选择具有了强制的色彩,这就导致了三种结局:首先,意识形态的操作者是人,是一部分人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左右另一部分人,因而,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的结合亦即人与物质力量的结合,这样,意识形态往往是人格的象征,意识形态挟带着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私欲和利益,意识形态造成的对人的伤害实质上是一部分人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对另一部分人的伤害。其次,人是创造意识形态的主体,由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的结合显得意识形态异常强大,强大到意识形态异化为形式主体时,当意识形态对人进行单方面的选择时,就意味着死人抓住了活人。再次,意识形态与物质力量的结合扭曲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使意识形态工具化,以物质力量为动力而使意识形态以“终极信仰”和未来理想的诺言使现状变得可以接受或忍受,而这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以正宗而自居,另一方面沦为一种附庸品。意识形态成为物质力量的代称,所有偏离正宗意识形态的其他意识形态都将被抑制、摧残,以维护其正宗的地位。而意识形态一旦陷入这一困境,即成为保守的意识形态,并竭力维持其一元存在的优势,以便享有对社会、对世界唯一的解释权,想必在这种社会里苟活着的人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人,人们不必运用创造性思维,而是用重复性思维,按照意识形态提供的行为标准和思维框架局部地理解世界,这时的理解只能提供无聊的朝歌,不能使思维的水平有半点长进,甚至还陶乐其中。这样一来,一旦社会发生巨变,意识形态刻化的假设的世界和世界的本来面目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这就会导致:一方面意识形态不能从社会巨变中清醒过来,从而借助物质力量本能地维护享有的特权,另一方面,信仰、理想、价值等发生深刻危机,人们从内心已摈弃了意识形态的一元结构对人的制约,但因原有的意识形态还没有放下虚伪的臭架子,还依赖着物质力量在正襟危坐。于是为了免遭伤害,更多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心态和意识形态开玩笑,他们都在公开场合正儿八经地念一通纯而又纯的美丽词藻,而在行动上却早就把它抛到九霄之外,而意识形态身边除了一帮如同意识形态一样僵化的帮腔者和侍奉者外,其余的人都心照不宣,而实质上意识形态除了唯一能显示出野蛮和暴力的物质力量外,一无所有。
让我们再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就是物质力量的化身。在一些政治本位制比较严重的国家,一切学术问题、思想观点都必须与之兑换。我们一方面觉得意识形态那样持久地制肘着人们,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软弱得可怜,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性,人们一谈到意识形态问题,总是以政治与意识形态相关性取代其独立性,在现实中,意识形态常常丧失自身和政治合为一体,成为政治的小妾。政治意识形态化显得政治温温尔雅,而事实上,政治在任何时候都是强力的象征,意识形态政治化使意识形态不可自拔,失去了对政治提出责难和忠告的勇气,从而使政治一意孤行,沿着一条自以为正确无误的路子扭着意识形态走下去,而这时的意识形态不是皈依于政治,就是被政治逼着,悲切地为政治唱牧歌。这样又导致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同时陷入迷雾之中,直到走入深渊,而政治依旧是政治,正如政治家所言“政治没有纯洁性可言”。
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意识形态的职能表现为(1 )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并加以论证,这种论证从来都应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的,一旦是单方面的论证,就是意识形态的失职;(2 )监测政府对方案的执行,并对执行情况作出评价,意识形态在这里凭借的是良知和真理,而不是其它什么,它的责任是对事实的公开,而不是对现象的掩饰;(3)制造或创建新思想来解释世界、现实。 这是意识形态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理由。但当意识形态政治化后,它的一系列的社会功能就不能正常发挥,政治失去了第二种忠诚的辅助,把意识形态一古脑地编入自己的番号下,使其失去了除自身以外的清醒判断,以政治判断作为社会运行的准则,很容易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引向灾难。
意识形态是反映现实的(当然也超越了现实),现实的复杂多样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复杂多样,这也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属性,在一个常态下的集权国家里,从表面上看好像有一种国家哲学作为统一思想的基础,其实这只是写在官方文件中的,人们的生活依据主要是传统的价值和现实固有的法则。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显得毫不奇怪,意识形态的复杂与多样并不可怕,意识形态的复杂多样是客观存在的,它对社会从正和负两个方面上发生影响,有时,腐朽、保守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机体起负向作用,但决不能因其具有负向的一面而试图消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代之以青一色的意识形态。“国家应该容忍这种哲学原则,而且我也不曾见过,有任何政府因为这样放纵的原故,致使其政治利益有所损失,哲学家一般并没有大的热枕;他们的学说也不能十分迷惑一般人民,我们如果要限制他们的推论,那一定会危及于科学,或危及于国家,因为这样慢慢就可以一般人所十分关心的那些方面准备好杀戳和压迫的道路”(休谟),意识形态的多样化还直接导源于利益集团的多样化。作为实体存在的全民、股份制、民营、合资、独资企业等都是合理的,那么从这些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也应是合理的。事实表明,在专制气氛浓重的国家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受到压制,在开明的社会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得以宽容,在开放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得以自由地生长。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的丰富多彩反证了世界的丰富多彩。
三
让我们投注一下这样三个概念:目标→运行→结果。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想本身,目标的制定依据两个要素:历史和现实,也就是说由历史和现实作参照才确定了某个目标,也就是说目标的制定依据的是客观的标准。实际上目标本身孕含着三个要素:历史、现实和未来,目标本身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的总结预知了未来。实际上未来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也好,作为一种存在状态也好,都还没有真正参与到目标中,只是目标推测了一种未来,甚至创造性地发挥了未来,这说明目标本身带来某种假设性,目标不是纯客观的东西,目标中包含着大量臆想,这些主观的因子既构成了目标的一部分,又是扭曲目标的内在因素,这是目标永恒的缺陷,必须对目标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有明确的认识,对目标寄于过高的希望将会导致目标在现实运行中惨败。因为一切东西都不是看其设想得如何,而是如何使这些设想在实际运行中与设想的逻辑大体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存在着两条线:一条是目标本身提供的论证逻辑,一条是目标在运行中的现实逻辑。这两条路子有没有吻合的可能呢?有,但只能存在于人的想象中,而决不会存在于现实中。目标不是运行在真空中,目标运行在充满了个性的和意志的社会中,这些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既是促成目标实现的因素,又是扭曲、阻碍目标实现的因子。就目标与结果而看,目标运行的结果与目标所预言的结果之间,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1)现实运行的结果与期望的结果是毫不相干的。(2)与期望的结果相近的结果。(3)与期望的结果差距较大。(4)与期望的结果完全重合,这样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与结果之间不可能是全等关系,结果往往偏离了目标,或者是说,目标往往是在目标的推进过程中偏离了目标本身,这时候,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对现实的关注上,应该灵活地调适目标与现实的距离,而不应该死守着既定目标,以不变应万变,还自以为把握住了大方向而没有迷航。目标只能提供某种尽可能精确的论证,在实践中不能象计算系统一般控制实施。我们的错误就在于为了目标而牺牲了现实,由于对现实的漠视,反而恶化了现实,使目标的运行缺乏必要的现实基础,目标所预示的美好的前景与现实的分裂越来越大,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目标本身并不是全能的、一劳永逸地指点人们的生活,现实却时时刻刻困绕着人们的生活,人的幸福的远景或许是目标所预示的,但与人休戚相关的幸福却是现实所提供的,也是现实中丢失的。人们已意识到,关注现实不会牺牲目标,只能优化现实,有利于目标的调整和实现,为了目标而牺牲了现实就等于牺牲了人本身,而我们为之奔走、为之奋斗的目标难道不正是为了人的幸福吗?二十世纪早期曾诞生了一批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首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时,目标是动力,现实才是真正关注的东西。在这批先驱者之后的几代人成为目标主义者,他们首先是目标和理想的守护人,其次才是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与目标总是有所抵触,他们便总是站在目标的一方,总是目标主义者。这是这几代人深刻的悲剧。总想用目标来鼓起人们的巨大热情,来推动目标的实现,实际上把人们培养成一个以目标为中心的目标主义者,而名义上他们因承的是先驱者的路子,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恰好与先驱者相反。在即将逝去的百年历史中,曾经诞生一批巨人。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颂扬他们,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那个时代具有了更加沉甸甸的份量;另一方面,有时候也有一些非常平庸的历史发展的段落,在平庸的时代里,也只有那些平庸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推崇的是巨人,而不是平庸的人。平庸的人总是以平庸的方式来浅薄地理解世界,如果让平庸的人掌管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他以平庸的才智加于人身上。他依据的是政治权力,而他还误以为他比别人高明多少。他缺乏思想、才能,只有职位供给他的权力,他不能拯救自己,岂能统领众生?他唯一的能力是用权力来维护目标,其实是在维护自己,他压根儿都不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有一个永恒的结论:人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人的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讲为了满足欲望的实现,而且欲望是个无底洞,不可能能够实现,一个人获得了一个需要的满足,马上会引发更大的需要和欲望,需要的满足,意味着实现了某种利益,成为某种既得利益者,得到某种利益,便不可能让其放弃这种利益享受,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出,如果一个政治家不具备巨人的心灵,即使具备了巨人的心灵,也很难摆脱那种利己的本性,何况是那些平庸的政治家呢?当他的处境受到危险时,他俨然以一个目标的维护者而自居,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这恐怕是人之本性,也是政治行为的本质,因为,透过附加在人性上的众多“形式”壳,我们发现,一切纷争,一切幻影,一切所谓的深奥的东西都导源于人性的困惑之中,政治行为其实并不复杂,它只不过是人欲的扩展罢了。
四
我相信,用一个基本观点把全部哲学切分为两大对立面的方法和思维都是粗糙的,也是粗暴的。而且我认为这种对哲学在最高层次的分割是在低层次的对立思维的影响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过去我们总是把西方现代哲学等同于唯心主义,似乎只要沾上了唯心主义就意谓着作了一只徒劳的探索。而用实践的观点来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原因很简单,唯物与唯心不只是停留在头脑中,尤其是体现于行为之上。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实践。
可以说,我们一直忍受了理论上的一个巨大的误会:那就是,竭力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仿佛它可以一劳永逸地指点人们正确无误地走下去,而实际情况却是,在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一直弥漫着一种严重的唯意志论的迷雾,过分推崇人的革命性和能动性,过分地搞理论崇拜,对思想家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判断肆忌发挥,脱离一定的现实基础,违背最起码的人性常识对人进行思想改造,企图使所有的人都皈依于一种模式、一种思想,从而在一种思想的引导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种巨大的意志的整合,然后从事那些宏伟的事业。可那些热衷于“唯意志论”的唯物主义者从开始行动的第一步起就蜕变为货真价实的唯心主义者,而这些唯物观只停留在思维和口头语中的唯物主义者的奋斗成果的见证,就是至今依稀可见的埋没在败土荒草中的、锈迹斑驳的炼钢炉。
唯物主义者们口头上一直在念叨对理论和思想要“灵活应用”,另一方面又死守着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把一种思想搞得金壁辉煌,而且总是以这一种思想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一切。这就令人想到圣经和神学院。我们把一种思想奉为圣经,若大的一个国家如同神学院,你需要的不是理性,而是虔诚,首先是相信和接受,而不是批判和选择。理论界的极度的、不负责任的奉迎,导致了民众肤浅的无批判的从众。政治没有制衡必然导致专制,思想和理论的一元化就可能使其作茧身缚,在一种没有竞争、没有参照系的环境里畸型生长。所有的所谓的“理论家”都拥戴一种理论并为之涂脂抹粉,不仅兆明该理论必将枯萎,也表明理论工作者理论品格的丧失。诚然,有人会把责任推及给政治上的强压,但这并不能解释问题之根本,何况还有人要依仗理论作威作福,乱棍打人。政治上的蛮不讲理,也与理论上的放纵和谄媚分不开。与理论为伍的人们,一定要明确自己作为社会中特殊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他们的天性就是对真理,对知识价值的追求,以及是社会的良心所在,而决不能屈服或迎合某种政治上的急功近利的需要,不能仅靠注释别人的思想而活着。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一种思想、一种理论的本性在于能给予我们启迪,而不是种瓜种豆的工具,一种理论的诞生是以一定的时代和现实作为背景的,对于产生这个理论的时代,理论将显示出其革命性和现实指导性的一面,但这个时代一旦过去后,面临新的时代和现实,理论本身会分化,甚至丧失现实指导意义;一方面理论指导了现实,另一方面新的时代又呼唤新的理论,无疑这个新的理论是新的形态,是对旧理论的否定,仅仅意识到理论的现实指导性会导致理论的庸俗化,理论生存价值在于其超越现实的一面,而这种超越性又孕育着对现实的某种投注,不管在任何时代中,总是存在一些共同的、悬而未解的问题,一些为许多时代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所谓理论的超越意义还在于它阐释了这类问题,既然这些问题古老而常新,那么论证过这些问题的理论就富有现实意义,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就对现实中发生的事有时具有发言权。但是试图以一种不变的观点锢守着一种理论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对理论的修修补补绝不是对其爱护。能够指导这个时代的理论,就是一种创造性发展了的理论,可它一旦创造性地发展了,它就是另一种理论形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