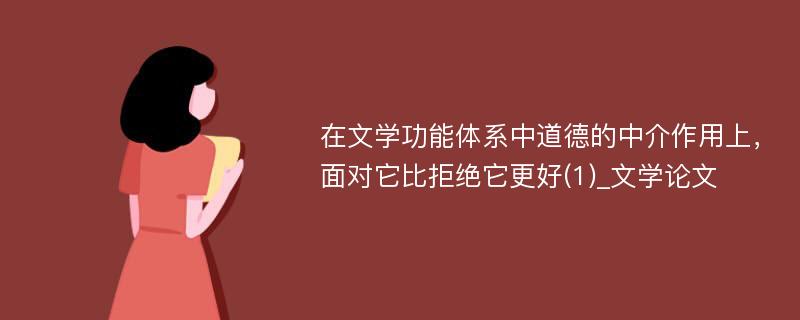
与其排斥 不如面对——论道德在文学功能系统的中介作用(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介论文,作用论文,功能论文,系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学复杂的多元化功能系统中,按照审美功能和宣传教育功能的两分法,道德教化功能,本属于非审美的方面。虽然在社会生活中,道德同别的意识形态门类一样,受着政治的调节,但在文学活动中,它却很像是起着某种中介环节的作用。由于这种中介作用的发挥,就使它对于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其它非审美功能来说,都显得相当重要。一方面,当各种非审美的因素进入文学作品,完成审美的转化,并成为作品的内容要素时,多数都要经过道德的中介,首先使自己变成可以由善的尺度进行衡量的东西,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审美判断的对象;另一方面,当作品中的各种内容要素,通过审美的渠道,在鉴赏的过程中作用于读者的精神世界,并进而影响他的社会实践时,道德也往往要起中介的作用。道德之所以能够在审美和非审美的转化、衔接关系上,起到某种中介作用,其理论根据在于美善叠合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事实。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应该认为在文学的功能系统中,除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审美特质之外,道德因素比其它任何功能因素都要远为重要得多。
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向来为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重视、所强调。据说俄皇尼古拉一世的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自己人好算帐》发表之后,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施林斯基——施赫玛托夫公爵就命令莫斯科教育区的督学召见这位剧作家,要求“对他这样开导开导:一个天才的崇高而有益的目的,不仅在于把可笑和丑恶的事物加以生动的描绘,而且还在于给它公正的谴责,不仅在于漫画式的讽刺,而且还在于传播崇高的道德情操;因而也在于把善和恶加以对比,把那些能使心灵高尚的思想和行为与那些可笑和犯罪的事物加以对比;最后,还在于确立一个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来说是如此重要的信念,那就是恶行在现世要得到应有的惩罚。”(见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译本,第217—218页。)
善和恶作为道德范畴,作为伦理判断的标准,是变动的、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赋予善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会截然对立,然而在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这一点上,却多数是一致的。比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那位教育大臣大约要早两千多年以前,亚里斯多德所讲艺术的教育、净化、精神享受三种功能,其教育功能,就主要是指伦理道德,而且摆在首位。后来培根认为“诗所给予的是宏达的气度,道德和愉快。”(《学术的进展》,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卷,第268页。) 狄德罗也说:“只有在戏院的池座里,好人和坏人的眼泪交溶在一起,在这里坏人会对自己所犯过的恶行表示愤慨,会对自己给人造成的痛苦感到同情,会对一个正是具有他那样性格的人表示厌恶。当我们有所感的时候,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感触总会是铭刻在我们心头的;那个坏人走出了包厢,已比较不那么倾向于作恶了,这比被一个严厉而生硬的说教者痛斥一顿要来得有效。”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期望:“倘使一切模仿艺术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倘使有一天它们帮助法律引导我们爱道德根罪恶,人们将会得到多大的好处!”(《论戏剧艺术》,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卷,第350页。)
强调文学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在中国,有着比西方更为久远和更为深刻的传统。中国的礼乐文化,源远流长。礼作为一种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和关于这个制度的观念,是政治的,但作为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际等级关系,以建立防止越规作乱的行为规范,则又是道德的。也可以说,礼是一种借以维持宗法血缘等级制度的政治道德。至于乐,从“乐以和之”的古老观念看,它辅助着礼,并被礼的精神所渗透,它通过潜移默化的审美作用,调理人的情感,从而导向宁静,并最终影响人际关系使之趋于和谐。可见,在礼乐文化中,乐和礼的结合点,正是道德。正因为“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记》、《礼记》,卷37。)所以,《乐记》才成为《礼记》这部书的重要部分之一。
《礼记》是重要的儒家经典;礼,是儒者理想的政治境界和道德境界。创始于三代,精致化于两汉的礼乐文化,主要由历代儒者所继承,所发展。它深入到人们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积淀于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礼乐文化的核心精神,其实主要是伦理的。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它着重于人格的熏陶和理想人格的建造,使之在礼的规范下,敬业乐群,行不逾矩。孔子是很重视乐的,徐复观就从他的习乐和乐教思想中看出了深层的伦理涵义。他说:“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要由技术以深入于技术后面的精神,更进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这正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的过程。对乐章后面的人格的把握,即是孔子自己人格向音乐中的浸沉、融合。”(《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自古诗乐一体, 所以孔子的乐教思想也同样渗透在孔门诗教之中。《毛诗序》中所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如果从读者接受关系来考察,显然是着眼于个体理想人格的塑造的。
礼乐文化中的伦理精神,不仅体现于儒家的乐教、诗教之中,而且成为其整个文学艺术功能观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后世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早萌生于勾栏瓦舍之中,后来在明代的文人手中达到高度繁荣的话木小说,本是一种与产生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都会生活的繁荣分不开的艺术样式,就其功能而言,带有很强的娱乐性和消遣性,然而,原其作者的初心,无不有一种强烈的劝善惩恶的伦理动机。以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而论,单看书名,就标出了很强的道德意味。他在《喻世明言》的叙里说,这类通俗小说可以“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绿天馆主人叙》,见《中国话本大系·古今小说》附录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647页。 )豫章无碍居士为《警世通言》所写的《叙》中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六经《语》、《孟》,谈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上、为劝善之家……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见《中国话本大系·警世通言》附录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为什么历来人们在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上,在鉴赏实践上,会特别强调道德教化作用呢?这是因为,道德不是别的,它是人的社会行为的规范、原则和标准。它协调着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社会行为无论是否自觉,都是由一定的道德原则来制约的、调整的。但是,道德对人的约束,多半是行为主体的自我约束,它不像法律那样来自外部的强制。虽然一种道德原则,被多数社会成员所遵循并约定俗成之后,也会形成社会舆论,这种舆论当然对行为主体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压力,但即便如此,也不具备如法律那样的外部强制机制和外部强制效力。所谓“道德法庭”,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如果这里也有对邪恶的审判台的话,则主要是当事者个人在良心上的自我审判,如托尔斯泰《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那样。不过在托尔斯泰那里不叫“道德法庭”而叫道德的自我完成或自我改善。
文学的描写对象是人、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的广阔的精神世界。它常常把隐藏在人们行为后面的隐秘的内在动机,善的、恶的、崇高的、卑下的都合盘托出。这就必然会涉及道德领域,涉及对这种行为及其动机的道德评价。鲁迅在论及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时候,曾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411页。)无论是洁白下的罪恶,还是罪恶下的洁白,其着眼点都在道德方面。完全脱离了对人和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就很难有文学的创作和欣赏。
在美学史上,也有对文学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家,克罗齐便是。他说:“加给艺术的目的,如把人们引向善良,使人们憎恨邪恶,纠正或改善风俗习惯等等,都是道德学说的派生物;在对下层阶级的教育中,要求艺术家给予合作,去加强人民的民族性、战斗性,去传播勤劳朴素的生活理想,这也是道德学说的派生物,这些事情是艺术所作不到的,正像几何学也做不到一样。”他甚至说,道德学说的美学家是要让艺术给苦药“裹着糖衣”,是要它“在为神圣教堂或道德服务时,扮演高等妓女,即教会的妓女。”但是他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无法把他的上述观念贯彻到底。他发现,就在他的祖国意大利的历史上,但丁、塔索、巴里尼、阿尔菲爱里、孟佐尼和马志尼都是站在他的观点的对面的,于是不得不作出理论上的让步:“正是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艺术的道德学说过去现在将来都一直是有益的。”“这种学说毕竟也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从艺术在道德范畴之外这点来看,艺术家当然是既不在道德的这一面,也不在那一面;然而,艺术家既是在道德的王国里,那么只要他是人,就不能逃避来做人的责任,就必须把艺术本身——现在和将来都不是道德——看作是一项要执行的使命,一个教士的职责。”(《美学纲要》,见《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5页。)克莱夫·贝尔也遇到了类似于克罗齐的矛盾。他在其名作《艺术》里,专立一节讨论艺术与伦理的问题。他从自己“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基本定义出发,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自身,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只有心理的愉快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好或善。”(《艺术》,中译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76页。)因此,他反对任何外加的艺术目的:“任何要为艺术寻求其它道德上的理由,任何要在艺术中寻找达到其它目的(而不达到好的心理状态)的手段之举动,都是一个傻瓜,或者说是一个头脑发昏的天才人物的错误举动。”他和克罗齐一样,把话讲得很绝。然而,绕来绕去总也把问题说不清楚,最后还是得出了一个他并不愿意得出的结论:“从艺术角度判断,唯一与艺术相当的性质是艺术性。从艺术是达到善的手段来判断,别的其它性质都不值一提,因为没有别的其它性质能与艺术相提并论,没有其它性质有如此的道德价值。因此,在达到善这一目的的手段中再也没有比艺术更好的手段了。”(《艺术》,中译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9页。)克罗齐和贝尔,从反对艺术的道德目的、道德教化功能,到不得不为它们留下一定的位置,这甚至比提倡艺术的道德功能的那些人都更能证明艺术创作和鉴赏中伦理因素的重要。如其徒劳无益地排斥它,不如勇敢地面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