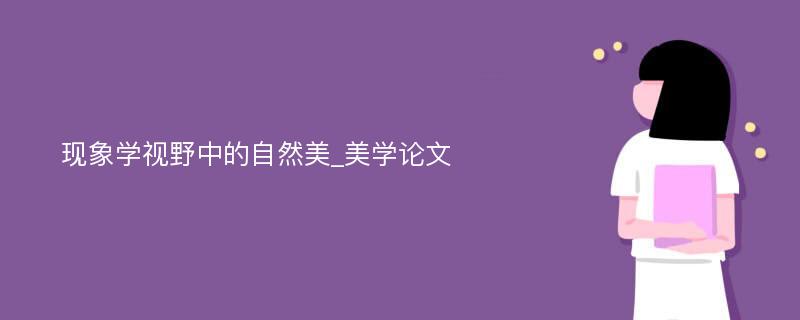
现象学视域中的自然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现象学论文,自然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象学美学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在杜夫海纳的相关论著中,因此,我们就把焦点集中在他的身上。现象学从美学的角度对自然对象进行探讨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只有自然的审美对象才真正体现了人与自然,即主体与客体之间那种真正的密切关联的关系,如杜夫海纳所说“有关审美对象的思考一直偏重于艺术。……如果这个经验(指的是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从现象学看来是最清楚不过的话,从本体论方面来看就不清楚了。(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他认为,作为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是被制造出来的,在这个对象身上打下了艺术家的人性烙印,这样的审美对象是一个准主体,而“这丝毫不能保证主体与客体有根本的亲密关系”(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因为“仍然是人在向他自己打招呼,而根本不是世界在向人打招呼”(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因此有必要探究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即人与自然的最亲密的关系。
第二,当代美学的主要缺陷在于:“虽然如此注意于在艺术家身上揭示出类似那个建立科学的自我的一种先验的自我的活动,但它却逐渐忘记了自然产生美这一点。”(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这是因为“人类只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产品、自然的儿子,才是这个自然的关联之物;自然对人类说话,给人类许多他显示自身的图像,以便人类能够谈论它。……只有人类才提出目的,这是因为他自身就是由一种只有在自己身上才能被认识的力量当作目的而产生的。因此,艺术响应自然发出的这一召唤,艺术在表现自然所孕育的那些世界时表现自然,它赞颂自然。”(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杜夫海纳认为,以往的美学理论在美的创造过程中,只片面强调艺术家的能动性,而忽视了自然的作用。美的创造离不开艺术家,同样也离不开大自然,两者缺一不可,为了矫正以往理论的偏颇,杜夫海纳着力从自然的角度论述自然在美的创造过程中所处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第三,审美经验体现的是人与对象之间的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而人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自然向人类现出真身,人类可以阅读自然献给他的这些伟大图像。……创造的自然产生人并启发人达到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哲学偏重选择美学的原因,因为这样它们可以寻根溯源,它们的分析也可以因为美学而变得方向明确,条理清楚。”(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美学比哲学、科学更具本源性、初始性,对自然的审美经验的探讨有利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自然的审美经验》中,杜夫海纳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自然对象?第二,自然对象审美化的条件;第三,自然的审美对象与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相比所具有的特征;第四,自然的审美对象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下面我们就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论述。
一、自然对象的界定及审美化的条件
在杜夫海纳的对象系列中,可分为“自然的”与“人工的”两大类,所谓“自然的”指的是没有打上人性烙印即未经人力改造的对象,如日月星空山川湖海等等;“人工的”指的是由人所“制造”出来即“人化”了的自然对象。人工的对象又可分为两大类,即艺术作品与实用对象,前者如文学、绘画、音乐、电影、雕塑等,后者如能指对象、使用对象、技术对象等等。杜夫海纳所说的自然的审美对象指的是什么?“这里的审美对象不再由艺术作品来提供,而是由一个自然的物体来提供——所谓‘自然的’是针对‘人工的’而言,如一片风景或一个生命体。”(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
在明确了杜夫海纳所界定的自然对象的确切含义后,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即自然对象如何就可以变成审美的对象,是不是所有的自然对象都可以审美化?杜夫海纳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自然对象都可以审美化。那么,区分自然对象美与不美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对这个问题传统美学并未提供多少有益的理论,如他所说:“不幸的是,在有关自然的审美性质问题上,几乎没有专家,也没有传统”(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不过,尽管杜夫海纳此言并非空穴来风,但讲得过于绝对,比如在二十世纪之前,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代表人物博克与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康德都有关于自然的审美性质的论述,再者,从《自然的审美经验》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本人在这一问题上受到康德的深刻影响。到了二十世纪,美学的主要走向是以艺术作品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鲜有关于自然美的理论实际情况只是大体合乎西方美学的实际状况,如英国的R·W赫伯恩在写于1963年的《自然的审美欣赏》一文中也发出了类似于杜夫海纳的感叹:“当代美学著述绝大部分关注的是艺术,极少有关心自然美的。”(注:[美]M·李普曼编:《当代美学》,邓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赫伯恩在文章中对人们缺乏关注自然为何美的热情这个原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科学将自然分解为一系列的材料与现象,使人们很难从整体上把握,同时自然的神秘感也在科学的解说下消失殆尽,这无疑增加人们对自然的审美欣赏的迷茫与困惑。另一方面,自然对象自身所限,例如自然对象的难以控制性、多变性及不确定性等促使人们把注意的目光集中到了艺术作品上。)但是,前苏联与我国在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讨论中都把自然美放在重要位置,因此,杜夫海纳所言并未涵盖世界美学的整体特点。对杜夫海纳的这一观点则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关于自然审美性质的理论从整体上未能超越传统,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还是要么从对象的角度要么从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杜夫海纳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有意运用意向性理论来破解自然对象何以就美这一令人困惑的理论难题,在活动与关系中来探究自然美的奥秘。
自然对象何以才能美?首先,非审美的自然对象就是那些没有意义的、平庸或无味的东西。他所说的平庸不应看作贬义词,它与无意义的东西的含义是等同的。平庸与伟大即小与大相对,而确定大小的最高尺度是感官:“当审美对象呈现于感官时,感官就是最终的裁判者。……不管从多远的地方去看山,山也显得大,不管从多近的地方看一茎小草,草也显得小。”(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
其次,非审美的对象就是不能具有隐喻性的对象,换言之,自然对象的美与不美取决于它能不能在精神空间取得意义。这里所说的精神指主体的感觉力,依赖这种感觉力,情感往往从自然对象中读解出的是伟大和深刻:“非审美的对象,就是那种不能具有隐喻性的对象,不能说出那些在情感的支持下精神可以获得‘含糊不清的话’的对象。因为精神在这儿不是别的,只是感觉力,是根据事物出现在感性之中的当时所呈现的外形与这些事物进行交流的能力。……这种交流不要求理解力做中介,而是通过感官直接进行的。”(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
再次,只有当自然是无人性的对象时,它才是表现性的,它才成为审美的对象:“不能审美化的东西不再仅仅是无意义的事物,而是那些人工的、任意的、专断的、自然中所有显得不自然的事物。”(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33页、第33页、第33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33-34页、第39页、第40页、第40-41页、第42页、第44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1页、第43页、第48页、第50页、第51页、第49页。)因此,“不管自然人化与否,只要它是具有表现力的又是自然的时候,它就成为审美对象。而且,只有当它是自然的,它才是具有充分表现力的。因为它自身的必然性还必须有所显示。”(13)如落日的余辉并不服从画家用于调色板上的规律,林间的风声并不服从音乐的和声等,艺术作品的必然性不同于自然对象的必然性,自然的色彩显示的只是一种物理的必然性,如石头年久生成的色彩,艺术的色彩则是一种精神的必然性,在自然中必然性自己表现自己,必然性就是自然的完满。
概言之,只要自然对象具备了非平庸性、隐喻性与表现性这三个条件时,即自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客观属性与主体本身的某种精神特质相契合时,自然对象就成了一个能够被人审美欣赏的对象。从整体来看,现象学美学各家在某些方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都把美理解为一种价值,比如,盖格把美学界定为一种价值科学,美学是一种研究审美价值的学科,英伽登自六十年代起,就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对审美价值的研究上,此外萨特、海德格尔等也持大致相同的立场。如果说,受胡塞尔影响并有所创造的英伽登与萨特把这种价值关系统一于欣赏者的审美意识即审美想象中,海德格尔把这种关系统一于存在之中,那么,深受梅洛·庞蒂影响的杜夫海纳则把这种关系统一于审美知觉之中。对杜夫海纳来说,美既然是一种价值,那它必然就会在一种关系中见出,这是因为,价值关系说到底是一种意义与需求关系,一种情感意义与情感需求,对象本身应具有某种客观属性,而欣赏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又需要对这种属性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在这种境况下,一种意义关系即价值关系就建立了起来。因此,自然对象的美既不能单单归结为客体的客观属性,不能单单归结为主体的主观精神特质,它是两者互动作用的产物,体现的是一种价值与意义关系而非实体关系,无论这种实体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
二、自然的审美对象的特征
杜夫海纳在完成了对自然对象审美化条件的论述后,进而探讨了自然的审美对象的特征。为了突出自然的审美对象的显著特征,他以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作为参照系来论述。
首先,自然的审美对象是由一个非人工的、自然的物体来担当的,它所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在感召人,通过人来显现自己的真身。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是一件人工制造品,有创作者自己的人性烙印,是一个准主体,它所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在向人打招呼。
其次,从感性的角度来看,自然的审美对象的感性是大自然自身所创造的,而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的感性则有人的创造成分。前者的感性形式没有后者那样纯粹、严格与稳定,具有一种开放性与非恒常性,后者的感性形式则具有封闭性与持久性,例如自然光线与云彩的多变和画中光线与云彩的不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恰如杜夫海纳所说:“艺术品能激起无缘无故的感性,这无缘无故的感性有其自身的结构与逻辑……而自然对象则激起世界的各种感性面貌,这时,感性面貌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思议性便成了主要效能,无须人们去试图在其中寻找一种事先考虑好的组织的严密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欣赏落日余辉而对邮政局挂的月份牌上的落日却感到厌恶的缘故……我们接受自然感性的自发性和丰富多采,但在艺术感性中却不能容忍。”(14)
再次,从审美对象与它的周围环境的关系看,自然的审美对象是活生生的自然物,与它的周围环境紧密连接在一起,处于真实的时空之中,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则从它的周围环境独立出来,如绘画需要画框,戏剧需要舞台,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的世界不是真实的、自然的时空,而是“虚拟”的时空。
最后,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看,由于自然的审美对象与它的周围环境融合在一起,知觉主体很难把自然的审美对象完全中立化,对象中的非审美的东西时时都在吸引着他,如田野对农夫、协和广场对出租司机就构不成纯粹的审美对象。因此与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相比,“存在于自然对象之中,就象存在于世界上,我们被拉向自然对象,因而又受自然对象的包围和牵连。因此,审美意向性不那么纯,它更指向自然,它针对的对象属于自然。”(15)
三、自然的审美对象所揭示的意义
杜夫海纳特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的审美经验是艺术的审美经验的穷亲戚,也不意味着,把自然审美化后,人们通过艺术就会看到自然。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揭示的情感特质偏重的是人的意义;自然的审美对象所揭示的情感特质偏重的是自然的意义,“艺术不是通过气质所看到的自然……自然也不是通过文化所看到的艺术。谁去通过牧歌听鸟叫呢?”(16)也就是说,当自然未经人化时,最经常呈现的就是那些与伟大和崇高相关连的方面,秀丽则是崇高缩小了的表现,是一种减价了的崇高。崇高这个词最早源于郎吉弩斯,他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论述的。真正从美学的角度来阐释崇高则始于博克,后在康德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博克和康德分别代表了对崇高解释的两个方向即客观论与主观论。在自然的审美性质这一问题上,以夏夫兹博里、哈奇生、赫加兹、博克等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认为自然对象之所以美,原因在于自然的形状、外观。具体到崇高这一范畴,博克认为,自然的感性性质如体积的巨大、力量、空无、无限等使人感到一种可恐怖性但又不危及人身安全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康德接受了博克的部分观点,但又不满博克纯粹从物体的感性特质角度论述,他转而从主体的角度,从精神的角度来论述产生崇高的原因。杜夫海纳对传统的两种方法都不满意,他在前面曾简洁地指出,自然对象如果不具有隐喻性就不可能产生美,言外之意强调独立的感性自然无所谓美与不美,强调与人的关联。在此,杜夫海纳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康德的崇高美学思想,认为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性质从根本上消解了自然的感性特质,自然在康德的主体性哲学中成了现象,自然失去了自己本真的面貌。杜夫海纳认为,崇高的诞生既有赖于自然的感性,同时也依赖于主体的精神心理,因此,崇高是一种关系活动中的产物,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对象或者主体。本着这一美学原则,杜夫海纳对康德的崇高进行了修正:“我们不说:‘真正的崇高仅存在于判断者的精神之中,而不存在于产生这种素质的自然对象之中。’我们说:真正的崇高存在于这二者之中。……自然把我自己的形象反射给我……它的风暴就是我的激情,它的天空就是我的高尚,它的鲜花就是我的纯洁。”(17)
此外,杜夫海纳还特意论述了“自然的”与“人工的”的联系与区别。他说,尽管艺术作品是人工制造,但并不意味着艺术品象似人工的,相反,真正的艺术即自然。因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带有自然的外表,在其作品中非但不抹去而是强化自然的标记,它遵循自然的规律存在,如罗曼式拱顶表现了重力,因而整个建筑物与风景协调一致,艺术作品与自然浑然一体而无损于自然。“审美效果应归功于谁呢?……自然之所以能从审美的角度看,那是因为它能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同样,我们现在想说:自然只有在通过一件艺术品辐射性地呈现于自身中而审美化时才是审美的。”(18)
那么,从本体论角度看,对自然的审美经验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杜夫海纳的实在论立场,是他反对胡塞尔先验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努力。在他看来,自然是感性的存在,人也是感性的而非纯粹意识的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的审美经验中,情感向我们揭示了存在的完满”(19),“审美经验在这里(指自然)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没有象在艺术作品面前那样纯。但在它使我们进一步与事物浑然一体并不许可作同样完全的还原方面,它又更接近于普通知觉。还原在这里所能做的,就是宣称它自己的不可能性,产生对世界的信仰,而不是取消这种信仰。存在并不单单是人和事物的共同命运,人和事物并存。人愈深刻地与事物在一起,他的存在愈深刻。然而审美知觉额外增加的东西,就是肯定人与自然的一种共同天性。因为,这时自然对我说话,我听得见它。它比艺术对我说得少,但至少它告诉我它自己的必然性。”(20)“在这世界里,人在美的指导下体验到它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又仿佛体验到一种先定和谐的效果,这种和谐不需要上帝去预先设定,因为它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然’”(21)
四、简要评价
杜夫海纳在写于1955年的《自然的审美经验》一文中重新提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他特殊的理由:从审美经验领域看,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他整体理论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本体论领域看,通过审美经验这一特殊的领域,反对传统唯心主义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唯心主义的自然理论,强调人是自然的儿子,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所激起的审美经验给我们上了一堂在世界上存在的课。”(22)重新确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所应处于的实际地位以及自然如何向人显现,而唯心主义恰恰颠倒了这种关系。二十世纪美学理论的一个偏颇就是片面强调艺术家的创造性,往往忽视了自然在美的创造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杜夫海纳《对自然的审美经验》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对此进行纠偏。美的创造既离不开艺术家的天才与灵感,更离不开所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这两者的有机融合才能创造出美与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