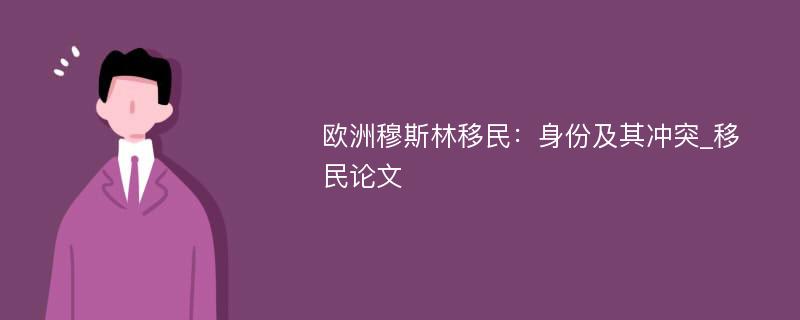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身份认同及其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移民论文,冲突论文,身份论文,在欧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11月13日,由“伊斯兰国”发动、法国个别极端穆斯林移民参与、造成100余人遇难的“巴黎暴恐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使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及其融合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主要是来自西亚和非洲地区。在德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招募客籍工人时期的土耳其;在法国,主要是来自前殖民地的马格里布国家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英国,主要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在西班牙,主要是来自摩洛哥。因此,来自西亚和非洲的穆斯林成为欧洲国家穆斯林族群的主体组成部分。在欧洲国家的外来族群中,因穆斯林移民持续不断的迁移和出生率居高不下,穆斯林移民族群已成为第一大外来族群。但由于族群、宗教、文化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穆斯林族群并没有很好地融入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成为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相隔离的“平行社会”和“边缘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的二代和三代穆斯林,自小生活于上述国家,并且获得了欧洲国家的国籍,是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但21世纪以来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法国《查理周刊》枪杀案等系列恐怖主义事件,实施者多为在欧洲出生、具有欧洲国家国籍的穆斯林移民,可见,欧洲穆斯林移民在个人身份、族群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3个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认同紧张与冲突。当2014年“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在中东崛起和发展壮大时,欧洲国家不少穆斯林参加到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恐怖主义“圣战”中。2015年11月,法国的个别穆斯林也响应“伊斯兰国”的召唤,直接参与了“巴黎枪击爆炸案”。对此,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他们为何没有融合到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中?为何背弃自己的国家,而实施危害自己同胞和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为何参加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的所谓“圣战”?这实质上涉及西亚北非裔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出现冲突这一核心问题,也是观察当下欧洲国家应对中东难民潮问题及西亚非洲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视点。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只有数篇论文从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的视角论及。本文拟从移民社会学的视角,从个人身份、族群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3个层面,论述欧洲国家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及其冲突。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个人身份认同及其冲突 身处欧洲国家基督教文明主流社会中的穆斯林,无论是出生在伊斯兰国家、后来移民到欧洲国家并最终没有加入欧洲国家国籍的第一代穆斯林,还是出生在欧洲国家、从小就生活在欧洲国家,甚至获得欧洲国家的国籍而成为欧洲国家公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他们都能够感受到:在个人身份上,他们与欧洲国家本土社会成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冲突。“我究竟是谁?”,这是困扰欧洲穆斯林的首要问题。 欧洲国家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早期成长和生活在伊斯兰国家,即使后来移民到欧洲国家,并一直生活在那里,依然改变不了其对祖籍国的深厚情感,而且多数第一代穆斯林移民没有加入所在国家的国籍。因此,尽管第一代穆斯林移民已经成为欧洲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社会层面的意义上被视为欧洲国家的人,如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但在教育、就业、工作和生活的微观层面上,第一代穆斯林一直是以外国人的身份被主流社会标注的,在上述领域备受歧视与排斥。在穆斯林移民的个人心理上,他们也是以自己是外国人的身份进行定位的。与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不同,第二代、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从小就接受西方国家的教育、生活在欧洲国家,他们绝大多数已经获得所在国的国籍,因而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在法律和政治意义上,他们就是所在欧洲国家的公民,但不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公民。①正如亨廷顿所说,欧洲穆斯林与欧洲原住民有着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他们“对上帝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种种关系有不同的观点,而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阶级的相对重要性亦有迥异的看法。”②这就决定了欧洲穆斯林在文化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与欧洲原居民有着根本不同。 在文化意义上,穆斯林移民并没有真正融合到欧洲国家主流的基督教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之中,而是依然生活在伊斯兰文化的氛围中。对于穆斯林移民而言,伊斯兰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或是一整套信念和崇拜方式,而是一个包括僧俗的、总体一元化的生活方式,它涵盖了从婚丧嫁娶到法律和经济等一系列的文明,而且已经被当地民众认同为民族文明。”③正因为如此,多数的穆斯林移民在婚姻上仍选择在穆斯林族群中通婚。如果当地的穆斯林男人没有合适的穆斯林妇女,他们就会选择原祖籍国的穆斯林姑娘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移民欧洲国家。“这些新娘基本上来自落后、偏远的农村,对西方社会一无所知。据《国际论坛报》的报道,荷兰70%、丹麦90%的穆斯林从‘过去祖国’娶妻生子,有7万多名生活在法国的穆斯林妇女被迫接受强迫性或父母包办的婚姻关系。”④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穆斯林移民与欧洲国家主流文化融合的难度,也进一步造成穆斯林移民与欧洲国家主流文化的隔离。亨廷顿曾著书提到,“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⑤ 在社会层面上,他们处处感受到欧洲国家主流社会在教育、就业、职业升迁等方面的排斥,由此成为与外来移民一样的外国人。基于伊斯兰文化以及欧洲国家对穆斯林移民在教育方面的排斥等原因,穆斯林移民、即使二代、三代受教育程度远低于欧洲国家的本土居民。受过高等教育的穆斯林极少,多数拥有中学或中学以下学历。仅以德国为例,德国穆斯林70%仅有中学或中学以下的学历,取得高等学历的仅有5%,而在德国受高等教育的穆斯林平均比例为19%。⑥在就业方面,二代、三代穆斯林的就业状况与其受教育程度较低紧密相连,多是从事较为低端、艰苦、待遇较差、收入较低的行业。在职位的升迁上,尽管二代、三代的穆斯林已经获得欧洲国家的国籍,在公民身份上就是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但在实际的工作职业生涯中,他们的肤色、种族、服饰以及文化象征等因素,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欧洲国家的原居民一样享有同等待遇。正因为如此,一些二代、三代欧洲穆斯林对欧洲国家主流社会有着排斥与反叛情绪。 与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相比,二代、三代存在着更为严重的个人身份认同危机,他们更渴望融入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欧洲国家、接受这个国家的主流教育,而且在政治意义上就是这个欧洲国家的公民,但社会现实中,主流社会给予他们的排斥和歧视让他们备感屈辱,这与自己属于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是互相冲突的。同属国家公民,仅仅因为是一名穆斯林,就成为二等或三等公民,而不能充分享受这个国家的文明发展成果,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内心中的个人身份困惑日益剧增。“我究竟是谁”的疑问,充斥在欧洲穆斯林心中。正如祖籍国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穆斯林阿玛尔·迪布所说:“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经常对我说我是穆斯林。可是他们不告诉我穆斯林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是乡下人,没有上过学,自己也不清楚穆斯林的含义。长大之后,我成了我们那个地方唯一的北非人。只要问我姓甚名谁,就能知道我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尽管我并不觉得有人搞种族主义,歧视我。我是谁?我是什么人?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感到,我应当有自己的根源,有自己的传统;然而,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我都找不到。在学校里,历史教科书上有一页讲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但仅此而已;至于阿尔及利亚历史、文化等等,书上一字未提。”⑦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答案就是,一方面,穆斯林属于欧洲国家的公民;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于本土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是平行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之外的属于穆斯林群体的“外国人”。这就是欧洲穆斯林在个人身份认同时遭遇的悖论与冲突。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族群身份认同及其冲突 在社会学、民族学研究领域,族群认同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概念。在当今世界,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族群的认同、冲突和对立,已经成为一个涉及国家与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问题。从历史上看,尽管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早在近代就出现了最早意义上的传统民族国家,如法兰西、德意志等,但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大量来自前殖民地的穆斯林进入欧洲国家,逐渐改变了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相对单一的民族结构,而成为多族群国家。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穆斯林族群已成为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最大的外来族群。 “群体的身份认同来自其集体记忆和共有知识,而穆斯林群体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其原来的社会环境,就比一般人更为迫切地面临重新确认身份认同的问题。”⑧对于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进行族群识别,我们可以从少数族裔和宗教信仰两个基本方面作为切入点。 从少数族裔的视角来看,在欧洲国家,尽管穆斯林族群已成为欧洲国家第二大族群,但仍属于外来族群,而且与欧洲国家的主流族群相比,依然属于少数族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整个穆斯林族群中的跨越国界的族群。跨界族群一般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历史上同一族群由于跨境而居,将可能走向分化,最终将发展成不同的族群。”⑨正如马戎所说:“在非洲,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划定的国界把一些原属于同一族群的人口分别划归到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政府的统治之下,国界两边的族群社区会按照不同的社会制度、族群政策和文化导向而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被国境分开的两部分也就逐步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的族群。”⑩另一种结果是,由于该族群有着自己长期信仰的宗教,而且缺乏更深刻的国家认同,因而他们依然在宗教、文化和心理上属于同一族群。正如弗雷德里克·巴斯在分析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穆斯林族群时所说:尽管他们有国界分割,但由于“他们遵循该族群作为正统穆斯林的礼教习俗而一直自视为同一族群。”(11)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正属于跨境族群的第二种结果。从族群的视角来看,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将自己视为广大的穆斯林族群的一部分。 从宗教信仰的视角来看,宗教在形成和巩固欧洲国家穆斯林族群的族群识别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中,‘族群’与‘国家’这两个层次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认同层面,前者偏重于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民族-文化),后者偏重于与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民族-国家)。”(12)就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而言,共同信奉的伊斯兰教发挥了族群识别的重要作用。在欧洲国家,不管你来自什么民族,也不管你来自哪一国家,只要信奉伊斯兰教,那么,你就是属于穆斯林族群的基本成员。尽管在穆斯林族群的认同体系中,血统、语言、地域政治共同体(国家)、宗教等共同参与了穆斯林族群的认同,但起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其共同信奉的伊斯兰教。正是在伊斯兰教的宗教旗帜下,不管你是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的穆斯林,还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这些人在欧洲国家就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族群身份——穆斯林族群。其中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是跨境的非伊斯兰国家的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如法国穆斯林、德国穆斯林、英国穆斯林等等。正如马戎所说,“一旦一个族群、一个部落信仰了某个宗教,当这个族群或部落的成员与其他宗教的族群或部落交往时,宗教就成为群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在族群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也会成为引发和加强其成员族群意识的媒介,成为族群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逐步注入本族民众的感情因素,成为族群政治动员的工具,成为族群的社会与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13)欧洲国家对其境内的常住穆斯林的标识,正是以伊斯兰教作为重要标识因素的。 对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而言,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这一族群身份与伊斯兰教宗主国的穆斯林身份,甚至是宗教激进主义的极端穆斯林身份有时是相互冲突和转化的。它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他们是欧洲国家穆斯林还是祖籍国穆斯林的身份冲突。就国家归属和社会联系而言,第一代穆斯林移民对母国怀有深深的归属情感,并在家庭中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母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社会联系中,第二代、第三代穆斯林则在清真寺中,感受到与欧洲国家主流宗教基督教截然不同的伊斯兰教教义的熏陶,尽管他们在欧洲国家出生和长大,但在他们内心深刻感到自己与其他欧洲原居民的不同,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族群,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母国也有强烈的归属意识。但当他们真正来到父辈的祖籍国、自己所向往的母国时,他们却找不到母国的归属感,因为在母国看来,他们已经不是本国的穆斯林,而是真正的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了。正如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乔治·尼尔逊所说:“在政治意识和社会联系而言,前两批移民对自己的母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子女在具有强烈归属意识的家庭中长大。比如归属于印度、归属于摩洛哥等等。因此,当这些年轻人来到父辈的国家时,他们深感自己成了陌生人,也深感自己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成了英国人或荷兰人。”(14) 二是他们是欧洲国家穆斯林族群身份与极端宗教教徒身份的紧张与冲突。毫无疑问,作为最大的外来少数族裔的穆斯林,他们在欧洲国家不同于其他少数族群,其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伊斯兰教对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行为、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伦敦地铁爆炸、马德里地铁爆炸等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尽管是极少数穆斯林所为,但对整个欧洲穆斯林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在欧洲国家,上至政治精英,下至社会民众,普遍对欧洲穆斯林保持警觉,并持有更大的排斥心理。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能否真正成为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成为欧洲国家极大的政治疑问和社会疑问。正如乔治·尼尔逊所说:“穆斯林能不能成为英国人?一个人能否既是穆斯林又是欧洲人?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一些欧洲国家的伊斯兰团体带头起来反对多国部队对伊拉克采取的行动,这就再次引发了辩论。有人提出‘既然他们是英国人,就应当支持英国军队。他们对国家忠诚可靠吗?’”(15)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日益成为隔离在欧洲国家主流社会之外的“平行社会”和二等公民。对于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而言,他们同样是欧洲国家的公民,同样“拥有社会权利,同时对社会怀有期盼。”但现实是,一方面,在自己所在的欧洲国家无法得到应有的权利,无法实现自己的期盼和承认。另一方面,“从父母那里获得文化认同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不是一回事。”于是,“他们便设法寻求新的东西,许多人由此转向伊斯兰教,转向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有些年轻人甚至转向了极端伊斯兰组织。(16)正是在伊斯兰世界和极端伊斯兰组织中,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得到了全面的确认。由此,当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号召他们向西方世界发动“圣战”时,这些欧洲国家的少数穆斯林,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和从属于国家的族群身份——法国穆斯林、英国穆斯林、德国穆斯林的欧洲国家族群身份,而认同极端宗教和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的身份。他们要么在自己的祖国——欧洲国家,制造恐怖主义袭击;要么离开欧洲国家,奔向阿富汗、叙利亚战场,参加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所谓“圣战”。显然,他们在欧洲穆斯林的族群身份与极端宗教的教徒身份认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紧张与冲突。尽管参与极端伊斯兰教和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的欧洲穆斯林也就数千人,这与上千万欧洲穆斯林相比,只是沧海一粟,但由于其源源不断的产生,并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与西方文明的“圣战”中,因此,欧洲国家对整个穆斯林族群的政治情感认同与信仰认同,从整体上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及其冲突 种族或族群的认同往往受到国家、权力和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通常是紧密联系的。一般情况下,“脱离政府行为以及国家组成之意识形态所发挥作用的政治过程,则不能得以领悟”族群认同的真谛。因为“族群的产生和族群的认同鲜明地与国家和国家建设的政治进程相关联。”(17)“对于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而言,必须确立国家作为民族成员归属层次中的最高单位,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所必须坚持的价值共识。因为民族认同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依附性,而国家作为满足个体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具有逻辑和理性上的至高性;在政治实践中,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族群或族群成员能够离开国家而独立生存,无论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依赖的意义上,还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概不例外。”(18)对于今天的欧洲国家来说,已经不再是相对意义上单一族群或民族国家,而是多族群、多民族的国家。在多族群的欧洲国家中,一个相对是主体的原著族群,其他是非主体的族群。在非主体的族群中,既有原居民的少数族群,也有从境外迁移而来的外来族群。但无论哪一种族群,都存在着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由于其所信仰伊斯兰教的关系,因而保持着更多的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面临着更严重的国家认同的紧张与冲突问题。 欧洲国家的政府深知,对于有伊斯兰宗教信仰支撑的穆斯林族群,最终目标是应实现其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不同的欧洲国家对于穆斯林族群采取了不同的移民融入模式,英国采取了多元文化的模式,法国采取了共和同化模式,德国采取了拒斥与融合模式,以实现穆斯林族群在欧洲国家的国家认同。限于篇幅,仅以法国为例。法国采取了共和模式,该“模式根植于法兰西文明对于普遍主义哲学的推崇,是法国在少数人政治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融入政策模式。这一模式的要点:一是在于个体的公民身份而不是群体的、社群的;二是在于公域内对不同于国族的语言、文化、历史等的不承认。”(19)另外,法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一个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共和国,保证所有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论出身、种族、宗教信仰”。正因为如此,生活在法国的二代、三代的穆斯林移民,天然地获得了法国的公民权,并被赋予政治认同的义务。法国研究共和模式的专家多米尼克·什纳贝就认为,公民和外国人有权在私域内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特性,如民族特性、文化、宗教,但这不能成为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20)正因为如此,法国穆斯林就可以轻松地摆脱血缘、种族、族群、祖籍国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而获得法国的国籍,从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国的穆斯林要比其他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更容易得到国家政治与法律层面的认可。也是这个原因,“在欧洲范围来看,相较于其他国家,法国移民(尤其是北非穆斯林移民)对国家认同度、融合程度最高,对基督教和犹太教最为温和,对伊斯兰极端教最少同情,认为伊斯兰与现代社会并无冲突,穆斯林精英群体也存在共识:伊斯兰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是兼容的。”(21) 但问题是,欧洲穆斯林移民获得了欧洲国家的公民权,而成为欧洲国家的公民,是否得到了与欧洲国家主流族群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利与社会承认?是否就意味着在族群、宗教、祖国的认同上,与欧洲国家原居住的公民有着同样的认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法国的穆斯林族群,特别是那些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为例,尽管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由于实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使这些法国穆斯林轻松成为法国的公民,享有与其他法兰西公民同样平等的权利,但实际上,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只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所设计的,为保护他们被认为或自认为“国民”的人不受少数民族(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或外来族群)的影响的制度性障碍。“在他们看来,那些移民所要求的公民权是基于现代性所具有的同样的自由原则基础之上的,但这些原则只是使统治精英(白人)的权利合法化。从这个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似乎给那些为消除阶级、种族、性别和文化上的不平等而战并希望享受与统治集团同等权利所谓少数民族提供了一个机会,不过这种想法似乎太幼稚了。”(22)“欧盟基本权利署在2010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穆斯林群体通常在人口拥挤的贫民区居住,高失业率、贫困与恶劣的居住环境成为穆斯林生活最主要的特征。”(23) 只要我们看看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内的少数族群最关心的受教育、就业、居住、社会参与、社会生活的糟糕状况,就会清晰地发现:法国的穆斯林族群完全不同于生活于法国的原居住公民。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没有正式的工作,或即使有一份工作,也是临时的,或是较为艰苦的,是法国白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他们获得的收入也远低于法国白人。有些年轻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工作,他们无法参与社区管理和城市管理、进入法国主流的社会生活,而是生活在伊斯兰教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伊斯兰世界——法国主流社会的“平行社会”和“边缘社会”。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歧视。“他们没有被围墙隔离,可以自由的行动,可以说流利的法语、英语或者德语,但是他们仍然被周围的人所拒绝,从而使他们变成了失去社会和文化根基的孤独个体,忍受着‘去疆域化’的痛苦。”(24)“在个人的基本权利无法通过正当途径来实现的时候,在备受压迫中长大的孩子,反而可能会展现出高度侵略性、颠覆性的性格特征。”(25)法国的穆斯林青少年正是如此,他们作为法国的公民,却无法享受到像白人公民同样的社会权利,于是,他们通过焚烧汽车、打砸抢公共设施,来反抗主流社会的歧视和压迫,来表达对法国政府和社会的不满,以此追求自己作为公民的尊严和平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往往是社会中沉默的少数,他们在主流社会的视若无睹中承受苦难,却很少能够通过文明、和平的途径来主张权利。在这种时候,暴力成为一种对话的方式,它能够以最极端的方式,强迫多数人正视现实中被忽视或被默认的不公正(26)。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法国主流社会和民众将穆斯林族群进一步视为法国的“内部敌人”和“破坏性的力量”,这更加深了法国政府和民众对法国穆斯林族群的成见和排斥。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和欧洲国家发生的系列打着穆斯林旗号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后,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明显地存在着将穆斯林族群“敌人化”的倾向,突出表现在将穆斯林族群犯罪化和伊斯兰教信仰犯罪化。正是基于这样的依据,法国的穆斯林经常遭到法国警察毫无根据的搜查、被当作恐怖主义的嫌疑犯遭到未经指控的拘押。(27)对法国穆斯林来说,在自己的祖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等方面无法体验到国家公民的荣耀和尊严。于是,一些法国穆斯林便转向伊斯兰教、甚至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希冀通过“重新伊斯兰化”,找回自己的族群归属和尊严。由此,少数穆斯林听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召唤,成为恐怖组织的成员。 解释欧洲国家的少数穆斯林是如何从欧洲国家的公民转变为欧洲国家的敌人这个问题,我们依然需要从社会成员的认同体系中寻找根源,其中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根据人们各自生长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不同熏陶,“人们头脑中居于不同层面上的群组认同意识会表现得十分不同,某一层面上的认同意识会强化,而其他层面上的则会弱化。各个层面所包含的政治、地域、文化、血缘等等构成认同意识的内涵的组合情况会各有不同。”(28)正如罗森斯(Roosens)所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认同层面等级体系……这个等级体系可能随着时间而转换或变化,在一定的场景下,某个层面的社会认同会比其他层面更加显著。”(29)对法国穆斯林后裔而言,尽管法国的共和主义的移民政策模式,自然赋予了他们以法国的国籍,从而解决了穆斯林的政治公民身份问题,但由于其不分种族、地域、宗教信仰和文化不同,因此,这种穆斯林政治公民身份的解决,掩盖了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法国的穆斯林并没有实现与法国的基督教文化的宗教认同,而依然保持了相对封闭的伊斯兰教文化认同,甚至在祖国的记忆中,依然是那个遥远的伊斯兰国家。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族群意识、历史记忆、族群身份和宗教文化认同基础之上的法国穆斯林,他们的国家认同就缺乏坚实的根基。在宗教和国家两大认同要素中,法国穆斯林往往以宗教而非国家因素认同自己的集体身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点。“比起基督教徒,穆斯林更习惯于首先以宗教而非国家来界定其集体身份。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法国四国的穆斯林中,将公民作为首要集体身份的比例远低于本国的基督徒,而将宗教当作首要集体身份的,在差距最小的德国,穆斯林是基督徒的两倍(占比分别是66%和33%),差距最大的西班牙居然接近5倍。”(30)对法国穆斯林来说,他们有两个主要的身份,一个是宗教信徒身份,一个是国家公民身份。显然,就重要性而言,宗教教徒身份要远远重要于国家公民身份。所以,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的时候,法国的穆斯林更愿意将其视为宗教战争,而每当发生宗教危机和宗教战争的时候,宗教认同要比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强烈得多。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法国穆斯林移民反对西方国家对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的战争,甚至个别人直接响应伊斯兰极端宗教和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号召,在自己的祖国发动恐怖袭击,或者奔赴伊斯兰国参加对西方文明的所谓“圣战”,从而实现了由欧洲国家的公民到欧洲国家的敌人的根本性转变。英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状况也大致相似。 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量穆斯林移民欧洲国家,只有不足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招募外国劳工进行经济与社会重建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体系瓦解的六七十年代和战后局部战争诱发的大量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的后冷战时代。尽管欧洲国家特别是穆斯林相对集中的西欧国家,如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保留其宗教文化的前提下,采取了促进其社会融合的政策,但由于主观上欧洲穆斯林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封闭性和客观上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排斥,欧洲穆斯林并没有实现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真正融合,而是成为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并行、并被割裂在外的“平行社会”。因此,欧洲穆斯林在身份认同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内在冲突。在个人身份的认同上,欧洲穆斯林及其后裔尽管因取得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国籍而完成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的国家认同,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完成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认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因而依然自视和被视为外国人;在族群身份认同上,欧洲穆斯林族群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的族群组成部分,但属于外来少数族群,由于宗教认同在族群身份认同上的重要作用,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将自己视为广大的穆斯林族群的一部分,少数穆斯林甚至认同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上,由于欧洲穆斯林的后裔多数已获得欧洲国家的国籍,因此,获得了欧洲国家的公民权和国家公民政治身份,但欧洲穆斯林更愿意以伊斯兰教信奉者作为首要集体身份,而非国家公民身份。少数认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穆斯林,在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号召他们参加对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圣战”的时候,放弃了欧洲国家的公民身份,成为欧洲国家的敌人。由此看来,一方面,欧洲穆斯林的个人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公民认同及其冲突表明,当代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比第一代穆斯林移民,在个人身份、族群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上,存在着强烈的不确定、迷茫和疏离感,因此,他们更迫切地需要明确的身份建构。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需要重新审视多元文化政策,因为从实施效果看,多元文化政策并没有实现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内的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政治融合。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相继宣布本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31) 进入2014年特别是2015年以来,受中东变局溢出效应的影响,数以百万计的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及北非国家的穆斯林难民,其中也有来自“伊斯兰国”的叙利亚籍、埃及籍等国家的恐怖分子,纷纷冲破欧洲国家统一的边防线而进入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面临着穆斯林移民更为艰巨的融合任务和恐怖主义袭击的严峻形势,由此,形成了欧洲的难民危机(32)。欧洲国家的少数穆斯林不断参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发动针对自己所在的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行为或参与“伊斯兰国”所谓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圣战”。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族群的合理身份建构依然任重而道远,欧洲穆斯林族群的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融合之路依然漫长而艰巨。 从欧洲国家的移民融合政策层面来看,欧洲国家也需要进一步反思其实施半个世纪的多元文化模式的局限性。多元文化模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促进了包括穆斯林少数族裔在内的社会融合,穆斯林族群也在欧洲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它也默许了少数族群与主流族群的不平等状态的合法存在。实际上,作为少数族裔的穆斯林族群,从一开始就因为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没有实现与欧洲国家本土主流族群的平等。也就是说,穆斯林“移民少数族裔有外在于自身的、源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话语的劣势,这种不平等应通过以分配性正义或者补偿性正义为理念的制度性手段进行纠正。”(33)正如罗尔斯所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注意那些天赋较低或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34)正因为如此,创新多元文化模式已成为欧洲国家政府的必然选择。(35)针对信奉宗教、融入主流社会困难重重的少数族裔,欧洲国家的政府需要制定出更加有效的移民融合政策,实施更有利于促进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措施。只有实现了穆斯林族群在欧洲国家身份认同的合理建构,穆斯林族群才能更好地融入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欧洲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繁荣。 注释: ①胡雨:《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边缘化还是整合》,载《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90~95页。 ②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p 22-49. ③储殷等:《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0页。 ④胡雨:前引文,第90~95页。 ⑤[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⑥Jocelyne Cesari,"Securitization and Religious Divides in Europe",Submission to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itizenship and Security 6th PCRD of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⑦[法国]阿玛尔·迪布:《我是穆斯林,我还是法国公民》,载《科技潮》2000年第7期,第92~93页。 ⑧储殷等:前引文,第1~20页。 ⑨梁茂春:《“跨界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越边境的壮族为例》,载《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40~53页。 ⑩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11)Fredrik Barth,"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in Fredrik Barth edited,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9. (12)马戎:前引书,第73页。 (13)马戎:前引书,第628页。 (14)[英国]乔治·尼尔逊:《欧洲穆斯林要求承认》,载《科技潮》2000年第7期,第91~92页。 (15)[英国]同上文。 (16)[英国]同上文。 (17)陈志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23~32页。 (18)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19)刘力达:《高认同与高冲突:反思共和模式下法国的移民问题及其政策》,载《民族研究》2013年第5期,第11~22页。 (20)Dominique Schnapper,La Communaute des citoyens,Paris? Gallimard,1994,p.100. (21)German Marsc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Transatlantic Trends,Imimgration,Washington,DC.,2011,p.29.转引自:刘力达:前引书。 (22)[西班牙]亚历山大·科埃略·德拉罗萨:《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载《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5期,第37~44页。 (23)储殷等:前引文,第1~20页。 (24)方长明:《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与反思》,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5~20页。 (25)储殷等:前引文,第1~20页。 (26)[美国]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屈平、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27)参见李瑞生:《评西方反恐实践中的“敌人化”穆斯林》,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4期(下),第243~249页。 (28)马戎:前引书,第73页。 (29)Roosens & Eugeen E.,Creating Ethnicity: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Newbury Park:Sage Publications,1989,p.16. (30)储殷等:前引文,第1~20页。 (31)张娟:《恐怖主义在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页。 (32)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其影响分析》,载《德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41~53页;方华:《难民保护与欧洲治理中东难民潮的困境》,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4—19页。 (33)刘力达,引前文,第11~22页。 (34)[美国]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 (35)宋全成:《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欧洲多元文化面临严峻挑战》,载《求是学刊》2014年第6期,第185~191页。标签:移民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穆斯林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法国生活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