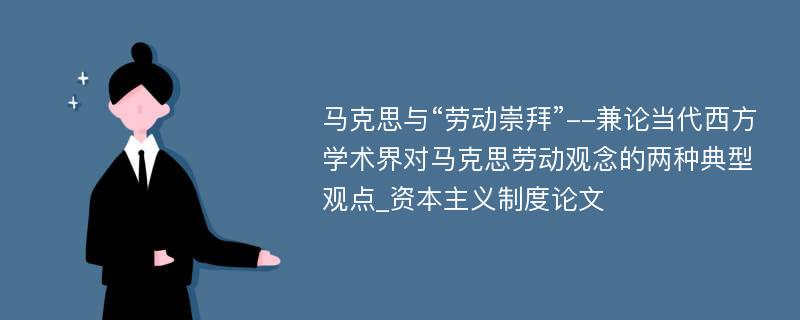
马克思与“劳动崇拜”——兼评当代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两种代表性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两种论文,学界论文,代表性论文,崇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5)04-0001-06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劳动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是与马克思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路径分不开的。自亚当·斯密把经济学的劳动概念提升到社会思想的层面上加以肯定性的解读之后,这一概念的内涵与理论角色便不断地被刷新与修改。黑格尔被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所鼓舞,敏锐地看到了劳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背后的需求体系正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精神与自然相协调的场所,因而摒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二元论,走向了以绝对精神的“劳动”过程为主线的哲学体系。如果说在斯密那里,社会思想被沉降到了经济学的层面上加以解读,那么,在黑格尔那里,经济过程是被提升到政治的层面上来加以实现的。沿着这一线索,我们要问的是: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又是放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的呢?按照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解释,似乎马克思的哲学是被拉回到经济学的层面上来加以实现的,因为它把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人文意蕴以及社会发展的内涵都简约到了经济学具体劳动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的层面上。这种理解既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真谛,同时也被当今学界的很多学者所放弃了。但问题似乎依然存在:到底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层面上的劳动概念?
一
当今国外学界在此问题上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定马克思是通过劳动概念的一个维度即具体劳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使用价值,来反对劳动概念的另一个维度即抽象劳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交换价值的内涵的。鲍德里亚、德里达等人就是持这种观点。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用使用价值的优先性来反对资本主义抽象的交换价值,其思想的一个致命缺陷是:没看到人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其实也是由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维度所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支持着资本的狡计。它说服人们相信自己是因为出卖劳动力才被异化的,由此认同于这样一种更激进的假设,即他们作为劳动力可能被异化了,而他们的劳动力作为创造价值的力量是‘非异化’的”(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By 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31.)。鲍德里亚进而还认为必须要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来加以彻底的批判(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By 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43.);德里达的观点也与此相类似,所不同的只是他对马克思观点的批判采用了另外一种思路。在他看来,像马克思这样用“准超验”的使用价值来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交换价值的思路从表面上看的确很诱人,“如果人们保留使用价值,那么物品的诸属性(这将是属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会总是极具人情味的,并会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令人放心。它们就会总是关联着当属于人、属于人的属性的东西:或者与人的需要相适应,而这恰恰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再不就是人类活动的产品,而人类活动的目的似乎就是想让它们满足他们的需要。”(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但德里达马上指出,这种思路是不正确的,因为从来就不存在游离于交换价值之外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的意思似乎是,物的使用价值是完整无损的。使用价值就是物的本身,它是自身同一的。和资本一样,幻影就开始于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因此它指的仅仅就是幽灵‘进入舞台’。在此之前,在马克思看来,它还不在那里,甚至也不是为了使使用价值处于游荡状态。但是,所谓的前一阶段的确定性,亦即这一想像的使用价值,确切地说,一种被彻底纯化的走向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的确定性究竟来自何处?……如果无法确证这种纯粹性,那么,人们就不得不说,那幻影在所说的交换价值之前,在一般价值之价值的起始处就已经出现了,或者说商品形式在商品形式之前,在它自身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0页。)德里达把这种状况称为“原始的卖淫”。据此,他指责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层面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带有准超验的“弥赛亚主义”特性的“驱魔姿态”,并说真正的幽灵其实是无法驱赶的,马克思思想的失误就在于没有看清“幽灵”的这一特性。
第二种观点认定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始终没有超越具有纯粹必然性的过程历史观。这种观点尽管不认为马克思是用使用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的,但它依然对马克思的劳动观点持批判态度,因为在它看来,马克思尽管的确是站在包括交换价值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批判思路的,而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状态下劳动过程的描述也的确是很深刻的,但问题是,马克思劳动观的整个理论层面是很初级的。汉娜·阿伦特等人就是持这种观点。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所关心的只是人的劳动能力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分离,即劳动产品的异化,但问题是,劳动过程所置于其中的整个世界都是异化的,马克思显然是在接受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方式的前提下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在她看来,马克思没有看到,“劳动社会”的出现恰恰是与现代的过程历史意识的产生相吻合的,这是因为,劳动社会正不断地放任自己无限制地去扩大物质生产,因而使人越来越走向劳动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不自由,从而使历史越来越具有必然性。马克思之所以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抱着“一种机械论哲学的幻想,认为劳动力和其他一切能量一样永远不会消失,如果它没有在艰苦的生命活动中消耗掉,就会自动地滋养其他‘更高级的’活动”(注: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133.),殊不知,如果我们不能摆脱劳动的必然性,那么,上述这种劳动过程的发展只能表现为我们消费欲望的无休止的增长,直到我们的生命被吞噬为止。所以,只有彻底摆脱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劳动过程,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二
上述两种观点的一个共有弊病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真正语境及内涵。鲍德里亚等人的第一种观点显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历史底蕴。应该说,马克思在其理论生涯中从来没有试图用使用价值及其所代表的具体劳动的维度,来反对交换价值及其所代表的抽象劳动的维度,即使是在其早期的《1844年手稿》中也是这样。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尽管还没有展开现实历史性的批判逻辑,但他对异化劳动(可以被理解为与后来的交换价值概念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的批判是站在体现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之基础上的,而不是劳动的一个维度即具体劳动的基础上的。经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就更加站到了社会历史性的维度之上,《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就是一个例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上述这一点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在此手稿的“货币章”及“资本章”的开头部分,马克思由于要贯彻在《导言》中就已确定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阐述方法,因而还没有详细展开在交换价值批判方面的历史性线索,还只是就货币及所代表的交换价值在拜物教方面的内涵展开了批判。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此时的交换价值批判方面,马克思也不是从使用价值的维度来展开的,而是一般性地站在人的特性的被否定的层面上来展开的,“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页。)。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其实在“货币章”写作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了上述这种从“抽象”的层面所展开的对交换价值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是必须要加以进一步推进的。在研究完货币的职能之后,马克思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在整个“货币章”的阐述中,商品还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但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是被生产出来的,因此,“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马克思马上就转到了“资本章”的阐述中。而且,在开始“资本章”的阐述后不久,马克思就通过反问“是否应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这一问题,而把自己的思路明确地界定在凝聚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辩证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层面上。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不是一种简单的等价物,脱离了使用价值的维度是无法理解这种劳动的真实内涵的,因为它恰恰是由于其独特的使用价值才使其具有交换价值的。于是,在马克思的思路中,劳动便转化成了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概念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道路上已经从经验历史主义的道路,走向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这一概念一出现,马克思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即工人所创造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转化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转化成了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也就是说,原本属于工人这一主体的东西,现在已经转化成了资本这种客体所具有的东西。这一思想质点为马克思把自己的思路推进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层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一条社会历史性的批判思路很自然地被牵引了出来。从此以后,在整个《57-58年手稿》的主导思路中,马克思就都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展开对资本这一交换价值发展的最高形式的批判了。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鲍德里亚等人对马克思的理解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阿伦特等人提出的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尽管从表面上看承认了马克思思路中的历史感,即看到了马克思是从劳动的历史发展中来审视拜物教的批判问题的,但它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看到马克思思路中的这种“历史”并非一种经济发展史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把哲学下降到经济史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而是把经济提升到哲学的层面上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的思路中,劳动发展史背后所支撑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内涵,即“社会的个人”的实现的历史。能否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关系到能否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57-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一点实际上是讲得很清楚的,只不过在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注意到马克思的阐述方法所带来的文本表述上的特点罢了。依照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阐述方法,在相对“抽象”的“货币章”和“资本章”的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正面阐述不是很多,其原因在于这一层次的论述还不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具体”过程。而从“资本章”的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开始,由于已经较为贴近资本主义的现实“具体”,因而马克思对直接生产过程与人本身的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就明显增多了。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注:《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把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视为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两个方面(注:《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把科学视为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维度(注:《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马克思脑海中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个人的异化及其社会的个人的实现。在其理论生涯的早期阶段,即《1844年手稿》阶段,他直接把这种最基本的问题转化成了“理论”问题,而没有经过现实社会生活的“中介”,这使他的理论线索明显具有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特征。经过其中期思想的转变,马克思实际上找到了把上述最基本问题经过现实社会生活的中介而表达出来的理论方式,这一理论就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57-58年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来说,劳动概念的内涵已经全然不同于它在《1844年手稿》中的意思,它所要承载的是一种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中既包括个人的异化经过现实社会生活“中介”之后的表达形式,即雇佣劳动,又包括“社会的个人”在现实社会生活层面所表达出的内涵,即能够体现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内涵。“劳动”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路中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正像他在《导言》中所说的,“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阿伦特等人指责马克思陷入了劳动拜物教并因而无法把自己的思路提升到人的自由活动的层面,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学者没有看到马克思“劳动”思路所矗立其上韵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哲学思路,而只是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思路。这就大大降低了马克思劳动思路的理论高度。与《1844年手稿》时期相比,马克思此时实际上并没有抛弃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理想,他所做的只是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马克思关注“劳动”,关注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并不意味着他就不关心人的自由活动的实现了。恰恰相反,即使在他关注现实劳动的时候,他脑海中所想着的依然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理想的实现,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旦转入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研究,就很快从一般性的“劳动”概念转入了具有社会历史内涵的“雇佣劳动”概念的原因,因为他必须要研究雇佣劳动所承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来科学地证明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实现的必然性。在阐述个人在未来的自由活动时,马克思事实上也用了“劳动”的概念,“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由于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象在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因此,可以断定,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在基本思路上显然是不可能与所谓的劳动拜物教同流合污的。
三
当然,我们也承认,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在论证劳动层面上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时,在某些地方可能有些简单化,譬如,他认为单是科学的发展,就足以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解体,因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在《57-58年手稿》的某些地方的确是从这一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的崩溃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18页。)。应该承认,马克思这里的确受到了当时普遍流行的把科学与人类自由解放中的进步力量简单等同起来的启蒙思想的影响,而没能注意到后来被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抓住的科学与工业相互纠结并成为一种统治力量的问题(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8页。)(在马克思当时,科学与工业的纠结事实上还不明显);又譬如,马克思在阐述一旦工人群众自己占有了自己的剩余劳动就必然带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增加时,的确没有对工人的物质需求的不断膨胀的可能性加以太多的考虑,在他看来,既然资本的发展已经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了一个最低的限度,那么,一旦工人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他们就必然会把这种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使个人在艺术、科学方面得到发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222页。)。马克思这里的确可能受到了由亚当·斯密演绎出来的苏格兰历史学派关于人具有节俭之本性的说教以及卢梭的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需求是有限的观点的影响(注:参见(法)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杨祖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对上述两点所谓的“缺陷”,也必须全面地来看待。
就第一个“缺陷”而言,我们必须看到,这是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篇中所展开的论述。马克思在整个《57-58年手稿》中是非常彻底地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阐述方法的,他的理论阐述被推进到某一个理论层面,他就会严格地就这一理论层面的内容来展开理论演绎。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事实上还没有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现实,像一般利润率等概念还没有出现,因此,可以把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性的论述指认为他在谈到某些具体问题时的一些思想发挥,而且这种思想发挥还是严格地被限定在已经被推演出来的理论层面之内的。马克思上述从科学的解放功能的角度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性的论证,就是他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层面上论及与必要劳动时间相对立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时所展开的思想发挥。这不应该被指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性论证问题上的最终观点。否则的话,当我们把审视眼光前推到“资本的生产过程”篇中时,我们还会发现马克思对此问题的更为简单的证明,他只是指出了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的“倒置”(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性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性而没有展开更多的说明。这实际上是因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资本的生产过程”层面上所出现的剩余价值等概念是不会直接出现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之中的,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灭亡性的最终证明应当在“资本章”的最后一篇中才能加以完成,前面所做的分析更多地是在“科学抽象”的意义上为最后的理论阐述奠定基础。事实也是这样,当马克思转入“资本章”的第三篇即“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篇(相当于后来《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他很快就采用了一种新的论证方式,即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导致的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角度,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和必然灭亡性的证明,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指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页。)。因此,仅仅从科学(生产力的一个维度)的解放功能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从历史性的生产关系的角度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性的证明,本身是一种简单化的结果。
就上述第二个“缺陷”而言,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思考得其实要比阿伦特等人深刻得多。阿伦特等人之所以得出工人的消费欲望会无限制地膨胀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他)们沿袭了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进程时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从物的生产和人(主体)的生产的角度来剖析资本的神秘化进程,而没有对马克思思路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即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线索给予足够的重视。这里的,个重要理论质点是:能否看到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的根本特性在于其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性,而不是其作为单独的个人的一些欲望、信念或文化上的特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条中对这一点早就有过论述。如果在缺失了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线索的前提下,只从物的生产与个人的生产的角度来剖析资本的神秘化过程,那就很容易得出资本关系在获得全面胜利的结论,因为按照这种以抽象个人为基础的理论思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行动主体必将被“生产”得越来越符合资本发展的需要。这其实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时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在异化中“感到很自在”的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39页。)。遗憾的是,这种思路即使在最近几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依然很普遍,哈特、奈格里在其著名的《帝国》一书中是这样阐述的(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理德在其《资本的微观政治学:马克思与当代的史前史》一书中也是这样阐述的(注:参见Jason Read,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Marx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沿着这种思路,作为“阶级”而存在的工人必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作为“大众”之一份子的工人,即作为单纯个体而存在的工人。如此一来,工人当然会越来越遁入到资本为其设置的圈套之中,他的消费欲望也当然会像阿伦特所讲的那样无限制的膨胀,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的个人”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左派政治理论家要想“发话”,也就只剩下提出一些不痛不痒的乌托邦式的解放议程了。
其实,马克思在其思路中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并把它十分明确地界定在资本的“外部生活关系”的层面上。在马克思看来,仅就这一层面而言,相互对立的因素的确不是资本和劳动,而是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是处在简单流通关系中的各个个人,是处在商品所有者即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中的各个个人,但这毕竟只是资本的外部生活关系,而问题的关键是要进入到资本的“内部有机的生活”关系之中。这后一点恰恰是马克思在《57-58年手稿》及其整个后期经济学手稿中论述的重点,正像他所说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5页。)也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工人尽管在外部的生活关系的层面上也有可能会被资本主义的拜物教观点所束缚,也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会去追逐物质欲望,但由于资本的内部有机生活的关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因而,随着资本不断地把其本质凸显出来,工人必将既在现实实践又在观点和思维方式的领域起来反对资本的局限性,“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某种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这是马克思断定工人在推翻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之后不会再去追逐物质欲望,而是会把自由支配的时间放在发展人的自由个性上面的根本理由。因此,在《57-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阐述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一问题时,即使有可能没有明确地排除亚当·斯密和卢梭的上述观点的影响,但这并不是马克思阐述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过分强调显然是不合理的。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科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