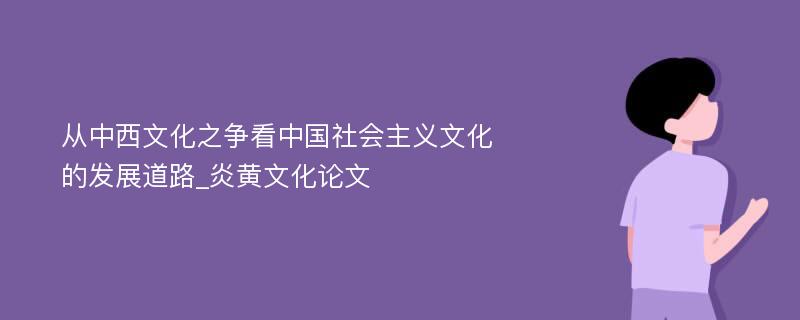
从中西文化之争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看我论文,之争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建设新文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国人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其间有关争论,始终没有中断。经过一百多年的争论与反思,人们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逐渐由“左”、右极端走向理性和客观。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十五大报告中这一崭新的科学论断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回顾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 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代中西文化之争的历史回顾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成果,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文化输出国,自我中心意识很强烈。中国人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为“中央之国”,而周围世界则是“四夷”。明朝时期来华传教的利玛窦以一个欧洲人特有的视角,对中国人这种心态作了如下描述:“因为不知道地球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注:《中国札记》第1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直到明末清初,华夏文化总能成功地应付各种挑战,以一种强势文化的面目出现。尽管那时中西文化也存在交流和融合,但并不存在大规模中西文化论争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之威向中华大地直驱而入,中西文化直接正面交锋,在以强大的器物为载体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文化节节败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中国文化路在何方,就成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思考的中心问题。
如同一切面临着近代西方挑战的民族一样,渴望富强的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这种选择无疑与中国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能力有关。中国人最初只承认“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而意识形态优于西方诸强。产生这种心态也很自然,因为中国的儒家思想的确有资格与西方思想相比较,但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技术实力却无法比较。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服气与对西方工业化骄人成绩的被迫服气,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将工业化看作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并且容易使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将现代化视为技术层面变迁的过程。至于制度及意识形态变迁,则是以后的事情。
1、“中体西用”的模式。1861年1月,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的初衷并非要对付洋人,而是为了安抚洋人,其首要目的则是为了平息发捻,解决朝廷的心腹之患。但历史的进程,往往会出现意料不到的结果,办洋务带来的许多问题都触及到传统,由此引发了守旧派的不满。应该承认,当时朝廷内外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吸取教训,他们并不赞成“师夷长技”。堂堂中国人学习夷人的奇技淫巧,岂不是奇耻大辱。面对洋务派的种种变革,守旧派总是予以坚决的拒绝。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郑观应、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他们以采西学、图自强为武器,主张变革社会,走近代化的工业道路。守旧派以张盛藻、倭仁、刘锡鸿、于凌辰、王家壁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孔孟之道,以封建的纲常伦理为武器来反对洋务。双方围绕着是否向西方学习,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争论,如有关成立同文馆之争,海防之争,铁路之争等等。巨大的阻力,使得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只能寻找折中的道路走,于是“中体西用”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提了出来,提倡“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注:薛福成《筹说刍议·变法篇》。)“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注:冯桂芳《校颁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西文化第一次论争以中国文化为“本”,西方文化为“用”而告终。
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战争的惨败使得洋务运动的丰功伟绩“灰飞烟灭”。两千多年一直是“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的中学一败于“西夷”,再败于刚学了一点“夷体”的“东夷”,举国震惊。如果说败于“西夷”,中国人还能勉强接受,那么败于“东夷”,国人则难以面对。人们无法想象,强大的大清帝国居然被一个初兴的岛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只能以赔款和割地来苟且偷生。甲午一仗,彻底毁灭了中国人刚刚树立起的一点信心,人们心理严重失衡,更为严重的是,崇洋媚外之风就此盛行。
2、改良和革命。痛定思痛, 上层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终于看到了隐藏在“奇技淫巧”现象后面的政治制度,于是酝酿出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他们主张仿效西方建立一种“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反对封建的君主专政制度。继而维新变法兴起。维新人士从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强入手,大力提倡“新学”、“西学”,极力宣传“天演论”、民约论,宣扬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创建中国的新文化,“破除千百年自尊自愚的恶习”。这次,维新派要动真格了,守旧派的反对也就格外激烈,由此引发中西文化第二次论争。在这场论战中,维新派拿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做衡量的标准,以“西学”为武器,托古为名,改制为实,主动地向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观念发起了挑战。他们生气勃勃,发表了大批鲜明的观点,给封建主义伦理纲常以狠狠的打击。守旧派也不甘示弱,毫不妥协,他们指责康梁是“托改革,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注:《翼教丛编》序。)。顽固派守旧分子叶德辉甚至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豚之足贵,断不以有康有力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不安”。(注:《翼教丛编》卷一,第11页。)为了阻挠维新,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但不管他们怎样变换恶毒的词句来攻击变法,其武器仍是孔孟之道。从四十年代反对“师夷长技”到九十年代反对变法维新,守旧派多次反复祭起封建纲常这一法宝,充分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基础的雄厚。
可惜戊戌变法最终为顽固派绞杀。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断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上层资源。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只有走暴力革命这条路。果不其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汲取改良失败的教训,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形式上终结了儒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可革命的果实被篡夺,一度出现的文化生机又被扼杀了。在尊孔读经的招魂幡下,中华大地上相继上演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丑剧。
3、五四文化启蒙。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办。以陈独秀、 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凭借着广收并蓄的与“中学”时有冲突的“西学”知识,以及一颗颗赤子之心、报国之心,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彻底的反封建专制及其政治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一恢宏的运动极大地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真正终结了儒学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国外的思潮源源不断地输入,在中国激起了主义的狂潮,什么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柏格森思想、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纷纷而至,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引发了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争。当时的中国,在文化模式的选择上主要存在三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即马克思主义派,西方文化派,东方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派,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为代表,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西方文化派以胡适、吴稚晖、丁文江、陈序经为代表,主张彻底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东方文化派,以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为代表,主张儒家文化的返本开新。三方围绕着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劣,科学与人生观等问题,展开了空前的争论。论争愈演愈烈,持续数十年,余音未了。“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中西文化之争就此告一段落。
纵观这段历史,其实是中国人不断学习西方,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从承认“技不如人”到喊出“打倒孔家店”,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一步步深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曾把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求近代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器物技术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制度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维新变法;第三阶段,从文化心理上感觉不足,遂有新文化运动。这个总结可谓很有见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人选择了西方最杰出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有了先进的批判武器,人们对中西之争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四十年代如是说:“从前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有名词上的改变,这表示近来人们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以前所谓西洋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吃亏,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注:《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25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认识的深化,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逻辑的必然。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充分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二、对近代中西文化之争的几点反思
1、关于文化的一元与多元
“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相一致,只能是被看作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解文化形成的原因提供了指导线索。从本质上讲,文化即“人化”,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及自身社会环境而创造出来的非自然事物。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导致了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及谋生方式的不同,因而引发了人群组合方式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区域文化。由此可见,人类文化是多源头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区域有着各自的传统。当然也正是由于文化是“人化”这一原因,人类文化才能有着本质上的共性,文化的共性就在于人类的统一性。文化的内在统一使得不同的民族、区域文化可以相互沟通、交流与融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有个性也有共性,这就是文化一元与多元的关系。人类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种一元与多元的统一中前进的。
回首近代文化论争中的不同流派,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还是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尽管他们的文化取向截然不同,但隐藏在分歧主张的背后却有基本一致的思路:一元文化观。显然,主张儒学复兴的人无非认为人类文化只有一个起源,其演化发展也只能是一种模式。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长期统一繁荣、和谐安定,而西方文化又暴露出很多弊端,那么,人类只有走“儒学复兴”的路才是合理的,不仅中国这样走,而且西方也必须这样走。梁启超不是这样大声呼吁吗?“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拨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同样,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认为,唯有西方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才是文明大道的主流,因此,我们要全盘西化,向着西方的道路走。比如胡适就认为,各民族的文化的演变发展,实质上走的是同一条路,“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注: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二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很明显,两派在文化观念的基本思路上,都是一元文化观,认为人类文化的演化只能是单一的文化路径,在众多的文化模式中,唯有一种是正宗的,正确的,其余的一概是变形的,不正确的。他们只看到文化的共性,而忽视了文化的个性,不承认每种文化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的一面,从而把文化的共性绝对化了。
2、关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文化的产生、发展脱离不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产生、演变的,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时代性和民族性两种属性。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而言,其时代性与民族性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民族性寓有时代精神,时代性寓有民族特色,两者共同构成文化的生命系统。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冲击,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一张力在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儒学复兴派之间针锋相对的论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自由主义西化派以时代性为基本依据,认定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已落后于时代。他们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现实表现的层面,将中国近代的落伍归结于文化的落后,从而将中国文化中的一切异于西方文化的民族特质视为缺失。比照作为人类文化现代化之样板的西方文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这样,“今日的第一要务是造就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踏地的去学人家”。(注:胡适《请大家来照镜子》,《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一卷。)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全盘西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而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则以民族性为根基,以民族性为最高价值尺度。在他们看来,保守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如果丢掉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那么,即使在中国建成了所谓的“现代文化”,那也已经不再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其缺失,但仅仅是“事”之问题,即表现形态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即文化之根本精神的问题。因而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是“圆满俱足”的。基于这样的立场,文化保守主义者指明了一条与文化激进主义者大异其趣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儒学复学”,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认为此举不仅可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且可以救西方文化之自毁。正如后来新儒家大师牟宗三所宣称的“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岂图制造自己而已哉?亦所以救西方之自毁也。故吾人之融摄,其作用与价值,必将为世界性,而为人类提示一新方向。”(注:《道德的理想主义》第4页, 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
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中,正是以文化之民族性为基本立足点的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与以文化之时代性为唯一价值尺度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构成了直接的理论对立面。尽管双方的主张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但终因各执一端,而陷入片面。其实,在文化系统中,就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而言,应该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时代性是内容,民族性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中国文化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时代性和民族性缺一不可。
3、关于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
系统论认为,事物作为系统而存在,各有其特定的结构性和内部诸要素间的彼此相关性。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自然有其整体性与可分性。说它是整体的,是因为任何文化都是完整而独立的统一系统,它内部的各个方面都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部分只是整体意义上的部分,离开整体即无部分可言,各个部分有机地建构在一起所以才成为一种统一的文化;说它是可分的,是因为一种文化既然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就一定包含多个要素,多个层面,比如人们通常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文化的器物层面,文化的制度层面,文化的价值层面。这些不同的层面,虽相互依存,但也各自独立,表现为文化结构系统的可分性。不仅如此,例如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同样也反映出文化的可分性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说文化不可分,那么这种文化就是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文化的整体性和可分性本身是不可绝对相分的,离开可分性的整体性是抽象笼统且不能认识的整体性,离开整体性的可分性是一种没有内在联系从而也是不能有机建构在一个系统里的可分性。所以,整体性与可分性本身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如果将其人为的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那就是对文化本身的否定和破坏。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一个文化体系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彼此密切结合,不能相互脱离的,有些则是彼此牴牾、相互矛盾的;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是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体系之中。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如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等。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文化整体性和可分性的辩证关系。
而在近代中国文化选择史上,笼统地谈文化整体性者有之,绝对地说文化可分性者亦有之。这些都是由于不能具体地把握文化的可分析性,所以往往陷入要么只讲整体,要么只言可分。如近代中国的西化派,否认了文化的可分性,只承认文化的整体性,所以才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洋务派则将文化的可分性人为地夸大和绝对化了,以致于破坏了文化的整体性,所以才有了外在的文化选择和细枝末节学习西方的失败记录,这两者都是从各执一端的思路上走向文化选择的歧路。
三、文化建设必须走综合创新之路
鉴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所谓综合创新,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那么,自然是“综合”,就不是根据某一家,某一派,某一国,某一方的文化来构筑自己的文化体系,而是博采众长,兼融并包,共冶一炉,熔而铸之;自然是“创新”,就不是“模仿”、“照搬”、“套用”,而是在综合的基础上,经过辩证的分析、鉴别,进行一种新的创造。“综合”不是为了综合而综合,也并非仅仅是兼收并蓄,而意在“创新”。而要创造出一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文化体系,就必须综合,必然博采百家。“综合”与“创新”两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毫无疑问,“综合创新”的提出并非是某一专家、学者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反思并深入地总结近代以来围绕文化论争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而提出来的,自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
早在明朝末年,国人接触“泰西之学”之初,徐光启就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注:《明史·徐光启传》。)此后,提倡从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入手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张,在后世一直不绝于耳。如万期同的“兼通中西之学而折其衷”,(注:万斯同《送梅定久南还序》。)魏源的“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注:魏源《海国图志后叙》。)王韬的“天下之道其终也由异而同,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孙中山的“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蔡元培的“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述,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注: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杨昌济的“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共冶之”。(注:《杨昌济文集》第2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些前辈学者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会通和融合中西文化的真知灼见。尽管他们还没有摆脱中西二元和中国本位文化思想的束缚,但毕竟表现了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高瞻远瞩的文化观。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文化的古今中西又一次大论争中,张岱年先生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文化的“综合创新论”这一概念,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硬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注: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第399 页,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方克立先生把它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十六字诀。(注:方克立《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至此, “综合创新论”作为一种文化主张在形式上逐渐定型,在内容上日趋完备,在文化建设中逐渐显示出其优势所在。
从会通超胜说到综合创新说,这中间凝聚着无数先进中国人的智慧和心血。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文化变迁,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走综合创新之必要性。举凡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在我们采纳、吸收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我们都要以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态度,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辩证的综合的再创造。总之,我们要打破时空的限制,打破画地为牢,此疆彼界的做法,采取全方位的学习,筛选,借鉴,吸收的方针,综合而后创新。这种创新的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按“蔚蓝色”文明模式建构的文化,它必将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充满民族特色而又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一直是高度重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8—70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如何发展文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6页,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从时间上来看文化在历史上的演进就是“古今”,从空间上而观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就是“中外”,由此毛泽东拒斥了“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在概念上犯了错误。因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十分正确,为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扫清了思想障碍。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这一辨证综合的文化观,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提出了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时代大旗,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
1997年9月,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艺术。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第 4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这段话深刻地总结了近代以来前人在文化建设上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对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走综合创新之路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兴,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和庄严的使命。我们坚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富强,政治的民主,我们必将迎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必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