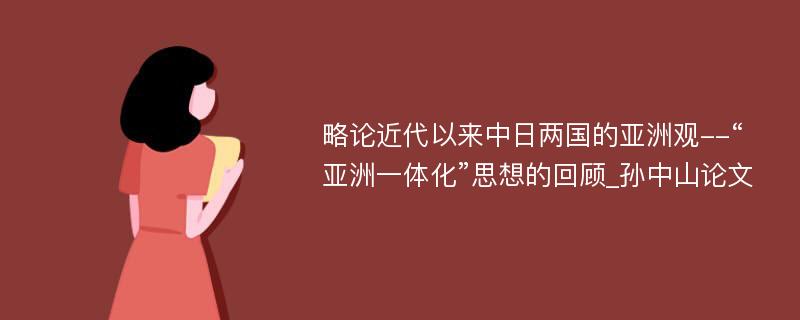
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近代论文,中日论文,思想论文,观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洲应该“寻求共赢、促进发展”。当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已越来越清晰,正在从概念逐步变成现实。通过睦邻、安邻、富邻的务实外交,中国与亚洲人民一道努力促进这个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合作、安全合作和政治合作。亚洲的发展潜力是可实现的和可持续的,亚洲有能力创造共同繁荣。亚洲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希望。因为历史文化渊源的近似性,亚洲国家对本地区具有深深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历史是现实的背景,现实是思想的实现。当我们今天以热诚之心讨论亚洲一体化的时候,有必要作一次“思想考古”,回顾历史上亚洲人的“亚洲观”,以了解亚洲现状的“思想背景”。又因为中日同是亚洲大国,梳理中日历史上的亚洲观,认识其源流,明晰其本质,辨别其同异,就显得十分重要。冈仓天心、井上圆了、大川周明、桂太郎等人是日本历史上所谓“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而章太炎、孙中山则同样显示了对于二十世纪亚洲前途的深切关注与期待。将他们的思想作对比性的排列,或可为今天“亚洲一体化”增添有益的思想历史的话题。
一、近代日本的亚洲观
1.冈仓天心的“亚洲觉醒”论
对文化亚洲主义产生卓越贡献的是冈仓天心等人。冈仓天心原名觉三,生于横滨,著名的美术评论家与思想家。1880年东京大学毕业后入文部省。1886年被派往欧美考察西方美术。1890年创设东京美术学校,为校长。他主张国粹,致力于日本绘画的民族化与近代化,与当时活跃一时的国粹主义者产生深刻的心灵沟通。他在《东邦的理想》等书中提倡文化的亚洲主义。他的这本书写成于印度旅行的途中,特殊的写作环境使本书表现出对亚洲命运的深切关怀。
他在所著《亚洲的觉醒》中表现强烈的文化亚洲主义思想。他说,“儒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缩影,其本性是自制的与非侵略性的”。儒教是“亚洲之心”,亚洲人因学习孔子之教,将热爱劳动的道德神圣化。孔子与他的弟子,教人以淳朴家长制的道德,并主张这个世界谦让与调和。以后佛教传入,又使“自制”的观念得以强化。孔子主张“种族宿命”思想,对于这种宿命要努力去遵行,不可以有所超越。显然冈仓天心将孔子诠释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希望遵从孔子之道,使亚洲脱离战乱,走向和平。冈仓还这样说明儒教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原本是一个岛国,因儒教与佛教的影响,与邻国一道,自制自律,在岛国狭小的领域里,遵从着自己的宿命。”
他承认西洋曾教给日本许多有益的东西,“然而不可忘记给我们真正的灵感之源的还是亚洲的精神。正是亚洲将古代的文化传播给我们,植吾以更生的种子。在亚洲的有数的孩子中间,我国可以毫不惭愧的说,我们确实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应当为此而高兴。”
他承认日本是亚洲的孩子,具体而言是在接受儒教思想的乳汁哺育后成长起来的民族。他觉得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日本,日本是亚洲最好的孩子,是将儒教思想领会最佳、运用得当而达极旨的民族。他也为亚洲的前途与命运担心,觉得作为东洋一隅的日本,其国民正在努力应付随近代社会而来的种种“急务”,且还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但其对于未来是自信的,因为日本已经从昏睡中起来。但印度与中国还在昏睡之中。假如此两国不醒来,亚洲纵然有日本一枝独秀,也终为长夜无见黎明。他说:“‘亚细亚的长夜’曾经使我国昏睡不醒,……知识长进与社会的进步在无感觉的空气中窒息。”
他指出,亚洲的长夜源自于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犯,愚昧的游牧文化使中国文明进化受阻。他对蒙古统治亚洲的历史深恶痛疾,表现了他独到的亚洲进化史观。他说:“亚细亚的颓废源发于蒙古人对亚洲的征服,这是一个极大的惨祸。当我们想起因蒙古袭来所带来的文明的黑夜,我们将更觉得支那与印度的文明是如何的熠熠闪光。”
他呼吁西方应该了解东方。西方能从广阔的领域与众多的渠道了解情报,但今日还是对亚洲抱着极多的误解,这使冈仓天心感到痛苦。他责难西方说:“他们还是怀着着人种的偏见,自十字军时代遗留下来的对东洋人的种种漠然与嫌恶,依然在支配着他们的心。”在他看来,即使他们中间的有识者,对亚洲复活的内面意义以及亚洲的终极理想还是抱着极大的猜忌。他道出了自己写作《日本的觉醒》一书的目的:“正因为当今的西方人对东方亚细亚还处在懵懂无知的状态,对日本的现状与将来有着种种的异论,所以我要对这一切议论做一一的说明。”(注:冈仓天心:《日本的觉醒》,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4页。)
2.井上圆了的“文化亚洲”论
宣传亚洲文化主义的还有井上圆了。井上生于1858年,新泻人。从小习汉学,同时也习“洋学”。他23岁进东京大学学习西洋哲学,就此立志将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1887年创建“哲学馆”,现为日本东洋大学。1904年在东京中野开辟“哲学堂公园”。说来井上还与中国有生死之缘,1919年在中国大连讲演中突然中风倒地不起,时年61岁。
他读的是西洋哲学,但对印度佛教有皈依之感,同时对中国古代哲学寄于深情。他认为,无论东西文化,都蕴藏着同质的哲学内涵。其外在表现虽异,但沿着不同的曲折山路,同可攀上人类精神的顶峰,在那里都可以迎接到照耀人心的哲理曙光。在他建立的哲学堂中,同时祭祀释迦牟尼、孔子、默罕默德与耶稣,表达自己的世界一统观,重视亚洲的哲学方法与理想。井上生活的年代,日本流行“日本主义”。他主张将日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结合,并将思想的侧重置于亚洲主义。他原来设想办一所大学,起名“日本大学”或者是“日本主义大学”,但1896年后,他的想法起了变化,决意将要办的大学定名为“东洋大学”。
不能否认,井上“亚洲主义”思想中还有着不少“大日本主义”的内容。甲午战争后他认为改变日本命运与形象的时候到了。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的强者与东方的霸者。日本今后所思考的不应仅是日本自体,且要与自己的国际地位相符合,在学问的领域里做亚洲的“领路人”。他设立“东洋大学”,其旨所在为“掌握东洋学术的全权”。
3.大川周明的“亚洲复兴”论
大川周明(1886-1957年),日本山形县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1926年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学位论文《特许殖民公司制度的研究》,获法学博士学衔。曾入满铁的东亚经济调查局为调查科长。1932年创立“神武会”,倡导“国家改造论”,鼓吹侵略思想。战败后,列为A级战犯,公判中因精神病而释放。其著作有《日本文明史》(1921年)、《复兴亚细亚的诸问题》(1922年)、《复兴印度之精神根据》(1924年)、《日本精神研究》(1927年)、《亚细亚建设者》(1940年)、《近世欧罗巴殖民史》(1941年)等。
他重视儒教在亚洲的作用,以为亚洲本具有“以精神自由为特征的”贵重文化价值。近代以来,亚细亚无奈成了西方殖民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忘记或因“怠惰”,失掉了这份精神财富。由此原因,亚洲的社会变得无序与非组织化。他主张日本发挥“亚洲先进国”的作用,确立亚洲的道德主体,以复兴亚洲。
他主张亚洲应该有宗教。他在《东洋的道与南洲翁遗训》中说:“日本人具有回归自然的精神,为此首先注意到的是语言中没有‘宗教’这个概念”,即使印度与中国的词汇中也同样“无适当的概念可以对应。”
他分析日本没有“宗教”概念的原因:“宗教、道德、政治三个方面,是人的实践生活。这三方面在西欧乃是次第的分化,各成自己的领域,各有自己的发展而具规模。东洋未见这样的分化。”东亚是将“人生一体性地把握。三体涵容而求精神生活全体的规模。”他主张将中国的“道”弘扬起来。“其道为天、地、人之道。即人与天地正确对应的总原则。用一句话说,即为道。”他又说:“人对天的关系为宗教,对人的关系为狭义之德,与志同道合者的关系为政治。”他明言:“中国儒教阐明道德之旨。其乃一个教系,将宗教、道德、政治合而为一”,“儒教至少可以说不是西欧概念中的宗教,但也不是伦理学与政治学,不是其中之一,而是它们的总和。”(注:大川周明:“安乐门”、“东洋的道与南洲翁遗训”,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现代日本思想大系)9,筑摩书房,1970年,第311页。)
竹内好在《大川周明的亚洲研究》一文中说,给予大川周明最大影响的是北一辉。大川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北一辉思想深处有大亚细亚主义做指导。在价值体认上,开始是儒教,其后又有佛教。他在《回忆北一辉》一文中说:“北君将刊《纯正社会主义》,出版社选定为‘孔孟社’。如若了解北君,对此应予以重视。由此可知北君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北一辉20岁前后主张将孟子的王道表现于近代。当他皈依于法华经……又主张将‘无上道’的思想表现于近代。正因为如此,北一辉拒绝了所有热心的诱导,而将马克思主义呼为‘直译的社会主义’,决不与其共进退。”他说:“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是法华经的行者。是故北君终日诵读法华经,独居之时常在读经三昧中度过。”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大川周明最终从文化亚洲主义者变为亚洲侵略主义者。他的亚洲复兴之路,不是“亚洲提携”,而是亚洲“解体”及对亚洲的侵略。
4.桂太郎的“亚洲解放”论
桂太郎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他第三次组阁的时候,对孙中山表示亲近。他约孙中山密谈,谈话中“两人都可以说是做到了推心置腹”。(注: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桂太郎临死时说:“我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注:戴季陶:《日本论》。)桂太郎死后,孙中山感叹地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大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
戴季陶著《日本论》,论两国政治家取得感情上的沟通,基础不在学术理论,也不在国家思想,“而在共求东方民族复兴”。戴季陶记录桂太郎与孙中山会见时如下的言论:
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在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势力尤其是军国主义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主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
桂太郎认为: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却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俄国,急是救了,然而以后的东方可能由英国独霸。英国的海军力非日本所能敌,英国的经济力也非日本之所及。日俄未战,当设法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结果既已分明,日英同盟的效用也就结束。英日两国将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在于日德同盟,对英作战。打倒英国的霸权,东方乃得安枕,日本乃得生存。如此紧要的问题,非独日本一家的问题。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的压迫之下,一旦解除英国的武力压迫,经济压迫问题也迎刃而解。
他说: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界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访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俄都讨论对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笃,连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时有半点漏泄,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
应该说,当时孙中山对桂太郎的意见是抱首肯态度的。所以桂太郎才说:刚才听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做侵略中国的拙策。给大陆以绝对的保障,而全力发展美澳,这是日本生存发展的正路。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
他又说:
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孙中山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注:戴季陶:《日本论》。)
桂太郎(1847-1913年)是长州藩出身的军阀,1901年至1903年之间连续三次任日本首相。他早年留学德国,志在日本建立德国式陆军。曾经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战后任台湾总督。任首相期内,缔结日英同盟,发动日俄战争,捏造“大逆事件”,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晚年策划建立新党同志会,筹备时死去。
桂太郎与孙中山的谈话,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一,俄国与英国是亚洲的共同敌人。其二,俄国与英国相比,俄国是亚洲“最急”的敌人,英国是亚洲“最终”的敌人。其三,宜先联英战胜俄国,尔后打击英国,最后解除西方对亚洲的压迫。其四,日俄战争之后,俄国的威胁已暂缓,日谋与德联盟,以取胜英国。其五,说服孙中山“日中联合”,形成日中土德奥联盟与英国对抗。作为交换的条件,日本在道义上支持孙中山反对袁世凯专制。
读戴季陶《日本论》可知,桂太郎所想的是驱逐俄英美势力,最后独占亚洲。尽管他保证“决不做侵略中国的拙策”,承诺“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甚至以理想主义口吻描绘美景:“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但他明显的民族自私思想也溢于言表,坐在桂太郎身边的孙中山、戴季陶自然明晓。不过,当时孙中山、戴季陶的处境是,面前有一个十分具体的敌人,这就是袁世凯。革命派迫切要做的是先打倒袁世凯,然后争取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所以当桂太郎说出“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这样的话后,孙中山与戴季陶便权宜地将桂太郎引为友人。然而,桂太郎表面保护亚洲利益,实为独占亚洲的阴谋思考,也引起孙中山、戴季陶的警惕。
二、近代中国的亚洲观
1.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做了他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孙中山演讲开头就说:
今天大家定了一个问题,请我来讲演,这个问题是大亚洲主义。我们要讲这个问题,便先要看清楚我们亚洲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想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便已经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像希腊、罗马那些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我们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来,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种种文化,都由于我们这种老文化发生出来的。(注:孙中山:“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演讲词”,载曹锦清编:《民权与国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以下未注者皆与本注同。)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本质上说是文化亚洲主义。亚洲是一个文化统一体,共同的文化纽带将它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确信亚洲应该联合,可以联合,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联邦。他为亚洲的古老文明感到骄傲。虽然孙中山说西方文化也由东方传去,有点偏颇,但表现出孙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评态度。他强调一切新文化都由“老文化”推演而发生。亚洲是世界上著名的“老文化”源地,对其应持自信与积极的态度。
在演讲中,孙中山承认现代亚洲落后了,但这不能成为亚洲妄自菲薄的理由。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亚洲的衰弱已走到极点,正面临一个转机的关头。他对率先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寄予希望。他说“日本是亚洲的头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三十年前废除了与西方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他说:“日本在世界上赢得了地位,这是亚洲人的骄傲与榜样。中国、印度等所有的亚洲国家将步日本后尘,一起向帝国主义争自由,亚洲是充满了希望的。”(注:同上。)
孙中山对日俄战争给予肯定。他说,日本的胜利,给周边国家以震动。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使日本的影响传遍世界。他使亚洲“欢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
他说,亚洲与欧美现在存在着冲突,这冲突是军事的,也是经济的,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他说:
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
孙中山说,中国与日本乃至亚洲的文化说到底,是“王道”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则是“霸道”的文化。表面上看,欧洲文化好过亚洲,但他们的文化仅“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是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一言概括之,是霸道文化。他说世界上除了欧洲霸道这种坏文化之外,还有一个好文化,就是亚洲王道文化。亚洲文化“好过霸道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专门感化人而不去压服人,让人怀德,而无须让人去畏威。孙中山感慨地说,世人都去相信“霸道”文化,“王道”文化处在被排挤的状态。西方用霸道文化欺压东方,是亚洲日甚一日陷于衰落的最大原因。
分析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其最强调的是亚洲有一个大主义,有一个大精神。所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就是亚洲的大文化主义与大精神主义。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就是中国的儒教思想。他主张将这个大主义与大精神作为亚洲灵魂与亚洲发展发达的精神基础。他说:
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亚洲的灵魂,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
孙中山发表此演说的时候,中国已经过“五四”运动,已经过东西文化论战。由孙中山的言论看,他似乎没有和“五四”以后胡适等人的文化批评主义站在一起。想必他是不赞成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理论的。追问其思想本原,说他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更恰当些。不过他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他主张对中国与亚洲传统抱接续态度但绝不反对民主与科学。他的一生说明他是中国20世纪初将民主思想付之于实践的最勇敢最坚决的斗士。他对中国实现科学化也竭尽其力。所以他有如下的话:
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
孙中山主张亚洲应该有发达的军事科学,他表彰日本在这方面的实绩:
近来亚洲国家学欧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军制造,海军驾驶,不必靠欧洲人,日本的陆军制造,陆军运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亚洲东方一个完全的独立国家。
孙中山说亚洲既有她的大精神与大文化,同时又有了自己的军备与武力,那就要促使亚洲去做一件大事,即将亚洲从欧洲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让亚洲的每一个国家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诚如孙中山所说: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
孙中山将亚洲的独立寄托在亚洲的联合与互相支持。他说目前在亚洲有一个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正在澎湃发展。这种思想潮流涌进的结果使亚洲团结起来。他希望亚洲各个争取民族解放国家之间要有“亲密的交际”与“诚恳的感情”。亚洲“联络”起来,亚洲全体独立就为期不远了。
孙中山在演讲最后对日本提出希望。他说中国与日本,至今还不能说是已经真正的“联络”起来了。亚洲的王道思想,亚洲民族求解放的独立精神,是亚洲,是中日团结联合的思想基础。什么时候亚洲团结起来,中日团结起来。亚洲就会取得全体的独立,王道思想就会最终战胜西方的霸道思想,亚洲的曙光就会出现。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2.章太炎的“文化一体”论
1894年以后,章太炎参加革命,开始读日本书。1897年2月,在《时务报》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以俄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章太炎到日本之后就有印度志士钵逻罕、保什来访。“二君道印度衰微之状与其志士所经画者,益凄怆不自胜”,同时也询问中国情况。章太炎又曾与张继一起拜访幸德秋水。在章太炎等人的努力下,结成亚洲和亲会。(注:幸德秋水的家中,存有章太炎给张继的一封信,曰:幸德秋水先生:拜启明日午后一时,往贵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弃。章太炎 张继二十六日《民报》社。)亚洲和亲会首次集会在青山印度会馆保什的住宅。第二次集会在东京九段下一所唯一神教教会中。与会者除中日印三国的代表外,还有越南、菲律宾等国志士参加。(注: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1907年四月,章太炎发起由中国、印度、日本与朝鲜等国人士组成的“亚洲和亲会”。章太炎受命起草《约章》,有汉、英、日三种文体。
约章规定:
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者、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凌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会中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故各宜以亲睦平权之精神,尽相等之能力,以应本会宗旨。无论来自何国之会员,均以平权产睦为主。现设总部于东京、支那、孟买、朝鲜、菲律宾、安南、美国等处。
参加亚洲和亲会的,除去以上各国外,还有缅甸、马来西亚、朝鲜等国革命志士。日本会员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森近运平、竹内善朔等人。中国人员则有章太炎(炳麟)、张溥泉(继)、刘申叔(师培)、何殷振(震)、苏子毂(元英,汉名曼殊)、陈仲甫(独秀)等人。
从对章太炎思想的观察,可知他当时有亚洲提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亚洲文化一体论之上的。章太炎将中国与日本、印度三国关系,比喻为一把扇子,中国是扇骨,印度是扇纸,日本是系扇柄的扇绳。在章太炎看来,亚洲是在儒教与佛教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文化区域,在近代同时都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章太炎对于这种冲击,未抱全盘否定的态度,问题在于西学东渐,亚洲文明正走向瓦解与衰败。这使章太炎产生紧张与难抑的文化忧思,希冀通过亚洲亲和,互勉互尊,既收西学养分又使亚洲文明大劫获生,更新发展。在中国、日本与印度三种文明中,他最担心的是中国与印度的文明,此两种文明相对日本文明,后者已见转型成功的希望,而前者吉象难寻。他不无遗憾的说,现在“亚洲”扇子的扇骨与扇纸正在朽烂。如若依然无动于衷,亚洲的败亡将指日可待。他承认日本这条扇绳,即日本的现代文化正通过自身努力,脱出危亡境地,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作为扇绳的日本”非但没有担负起拯救它的使命,相反对东方实行侵略,破坏着“亚洲之扇”——亚洲的文化。这使他痛心疾首,惋惜万分。
自然,章太炎的文化一体化思想与日本的民间亚洲主义有相通之处,同将西方侵略视为最大的危险。他写《五无论》与《国家论》,论云:“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其殖民统治“酷虐为旷古所未有”。(注:李润苍:《章太炎与中日文化交流》。)章太炎的大亚洲主义还有革命目的在内,希望借亚洲(主要是日本)之师,排满兴汉,复兴中华。故他在亲自所书的亚洲和亲会的《约言》中强调:“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为此,章太炎的亚洲观从其主题来看,一为文化保种,二为民族保种,保亚洲文化之种,保亚洲民族之种。
三、史为殷鉴,当今“亚洲一体化”历史借鉴
以上,我们对日本历史上“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冈仓天心、井上圆了、大川周明、桂太郎等人的思想作了探讨,同时也对孙中山、章太炎的亚洲观作了介绍。事实告诉我们,一百年来中国与日本已具备各自的亚洲观,此为今天“亚洲一体化”,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中日提携”、“中国不可轻”、“亚洲联合”等思想,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日本思想界,其特点是主张中日协和,共同反对西方军事与经济的侵略。尽管这样的思想具有“合纵联横”的“战略”意义,可称之为“战略亚洲主义”。然而它毕竟有别于“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理论,且因源生于民间,对亚洲合作终归有利。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与亚洲观,应避免全盘否定的“一抹黑”做法,将右翼论调与民间思想作区别对待,是应取的态度。
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日形成以儒学为主体的近似的文化国情。文化认同,将产生协作共存的“协和”体认。井上圆了、冈仓天心等人是文化亚洲主义的代表,其“主义”的根底与中国文化有关。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章太炎的“文化一体”论,既对军国主义理论保持警惕,作尖锐批判,也对中日近世以来文化“同源”的情况作高度评价。中国与日本至今遗存而续的文化底蕴,为当下亚洲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心理基础。
回顾历史也清醒地看到,近代以来尽管民间人士勾画出中日友好、亚洲合作的美好图画。然而理想终究未得实现,枪炮的轰鸣遮掩了和平的祈祷。侵略理论甚嚣尘上,民间思想最终破产。
因为右翼思想的影响,日本近代以来存在以下错误论点:一是“日本中心论”。认为日本最早进入现代化行列,有理由成为亚洲中心。如果实现亚洲“合作”,必以日本为“中心”,为主导;二是“日本解放论”。认为近代以来,亚洲沦为欧美殖民地,日本“进出”(侵略)邻国是为了“解放亚洲”。三是“脱亚论”。在亚洲唯日本臻“富强”之域,亚洲诸国落后愚昧,不配作日本的朋友,乃是日本的“恶友”。日本应脱离“恶友”,脱离亚洲。如此“理论”还有很多,流毒至今,是阻止当前亚洲合作发展的精神障隔。
是的,与欧洲相比较,亚洲“经济一体化”步履艰难。人们从各方面寻找问题的起因,沉思而不得其解。然而,假如把视线投向历史,或许可以寻觅症结,发现希望,从根源上找到21世纪亚洲一体化的前进之路。
标签:孙中山论文; 戴季陶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章太炎论文; 日本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