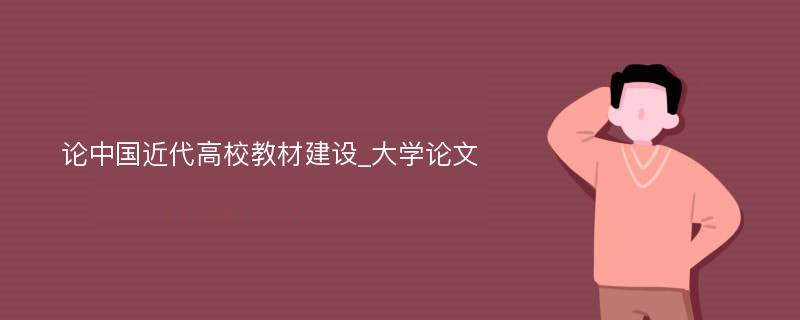
中国近代大学教材建设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教材建设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3-0081-05
大学教材是指用于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教科书及参考书,是高校教育活动赖以开展的基本资源。大学教材建设一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和课程变革的重要内容。近代大学教材历经编印讲义、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到本土化教材的发展历程,并呈现由民间自主编印到国家统一出版的趋势。目前,学界对于近代教材、教科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基本上集中于中小学层面;同时,尽管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对于近代大学课程及其基本要素的教材研究却并不充分。总的来说,近代大学教材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史料进行整理爬梳,以探求中国近代大学教材的发展轨迹及其变革的规律,为当前的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提供历史的镜鉴。
一、近代大学发展初期的讲义授课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开始起步。在学科内容上,传统的“四部之学”向近代的“七科之学”转变。很显然,传统的教学材料和参考书籍无法适应新的教学之需。因此,教材建设便成为初创的大学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近代高等教育肇兴之时,教材问题便引起了晚清学部足够的重视。学部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分门别类地详载了我国专科以上学校课程,对于教科用书作了如下规定:“现定科目之中学各书,应自行编纂;西学各书外国皆有教人课本,宜择译善本讲授。”[1]此处所言外国主要是指日本,因为当时大学教学科目系参酌日本模式设置。学部鼓励采译善本讲授,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采译善本编成讲义。时人有论:“我国当初兴学校之时,教育家不可多得各种教育新书,亦均未有善本,于是有出洋留学根本湛深之教员,或自东洋译成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诸书,或自西文译成地理、历史、理化诸书。既未有华文印本,则不得不用油印讲义以发给学生,随编随印随讲。”[2]115时人所论揭示了大学讲义授课的背景和缘由。限于中外教育交流的规模和编印出版的力量,讲义便成为大学授课可资凭借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各类学科率皆按课授以讲义,以辅教师口说之所未备,以供生徒退息之所谴修”,讲义“积有岁时,粲然成卷帙”。[3]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其编印讲义之风依然盛行。北大要求文、理、法、商、工各门课都应发讲义,而且要求教师对讲义常作修改,因此讲义稿件要连年重印。当时,北大出版部的主要任务即是印刷讲义,正如有的学者回忆的那样,“印刷本校教授的讲义是一大宗”[4]。不惟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诸多课程均采用讲义教授。一些著名学者如吴致觉、陶行知等皆曾编印讲义授课。囿于时局动荡及教育经费缺乏保障等因素,不少教授的自编讲义没有付梓出版,因此难以完成对教材的系统编译及出版工作。
毋庸讳言,讲义作为时代的产物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为传播西学、服务大学教学科研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讲义的弊端也很明显,“国内各大学之授课悉凭教授编制讲义,不仅各异其是且学生缺乏参考书籍,不易从事比较研究。”[5]有人曾于《教育杂志》上撰文逐条指陈其弊:“其一,讲义之编译时间仓促,多不免割裂支离之处;其二,或全抄某书而节去其扼要之处,或删节前段而采用后段文气不连贯,或讲员节去其略深奥之初致失其本真;其三,学校聘请书记和印刷工膳写真笔版、油印讲义耗费不赀;其四,讲义所用纸张油墨之费不可胜计;其五,每日所发之讲义堆积如山,日久稍陈旧则漫漶破碎不可复用或错落缺失补印维艰,终将付诸一炬。此五者,大抵有损害于学校,而阻教育之进步者也。”[2]115该文所罗列的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各界对讲义授课的不满,讲义作为权宜之计逐渐受到了质疑和指责。
由上述内容可知,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际,国内大学教材匮乏,大学教师只好参照国外特别是日本大学各科教材,自主编译讲义充当教育教学资料。这种举措既为各科授课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作为非严格意义上的教材,讲义的编印体现了近代大学发展初期教材的非规范化特征。
二、外文原版教材的引进与使用
如果说讲义自身的弊端还只是激起社会各界不满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外教育交流的深化则促进了大学教材的正规化建设。
20世纪2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1925年全国有综合性大学和专门性大学共47所,大学教职员3 762人。大学数和教职员数分别是民国初年的11倍和16倍(民国初年全国有大学4所,教职员229人)。[6]大学之外,还有涵盖法政、医药、工业、农业、商业、外语等类型专科学校58所。从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算起,在经历三十年之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已经初具规模,这在客观上要求课程与教材适应其发展状况。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中外教育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亦得以拓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美教育交流取代了中日教育交流成为主流,留美学生逐渐超过留日学生,从而带动了美国教育思想的不断输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教育理论、大学制度及教育革新实践的影响日益加深,一场新的教育改革运动在伴随着对西方教育理念的吸纳和教育制度的借鉴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更广层面上催生了对西方教育教学的具体内容,包括课程、教材的移植与推广。
在此新形势之下,北京政府颁布的《大学校令》、《国立大学条例》等有关大学章程条例,均明确要求大学教学方式及课程设置全面效仿美欧各国著名大学。1915年,交通大学(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堂”)课程设置以美国同类专科为蓝本,教材直接购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成套教科书,并聘请外籍教师以英文讲授。1917年,时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瑮在其提出的《改订理科课程方案报告》中拟订的课程设置也是以欧美著名大学的课程为参考。私立大学引进教材则更甚,当时著名的私立大学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都是教材引进的典型。[7]这种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各大学十分普遍,据当时执教于中央大学的物理学家施士元的回忆:“当时没有中文教材,只有英文参考书”。[8]20世纪20、30年代,许多大学的理、工、医、农各科继续采用外文教科书,并指定外文参考书;文科中的外文系科与经济、政治等科,凡涉及外国事宜皆用外文书。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理科课程大部分就选用世界各国的科学新成果,例如物理系选用的《近代物理》课程是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教材;效仿美国办学模式的清华大学,其西学部课程诸如世界地理、数学、化学、卫生、图画、音乐等,甚至修身课也都用英文教本。[9]不仅如此,据某些学生回忆,“由于绝大多数课程采用美国的教科书,教授讲课写文章也常常夹着几个英文名词以显示其学问,连中文、历史方面的许多教员也是如此。”[10]
对于外文原版教材如此风靡的缘由,1925年寿勉成撰文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因无适用之中文课本;其二,因西人之著作较优于我国人之著作;其三,因各大学教授多自英美留学归来,教中文书或不如教西文书之为易;其四,因近来各校学生对于留学生之批评多以其英语之流畅与否为标准,故采用西文课本,易以迎合学生之心理;其五,因采用西书并以英语教授之,为学生他日出洋便利计;其六,因我国统计不发达、名词不统一,下手著书殊不容易;其七,因处今之世不能不晓英文,而用西书讲英语,即所以助进学生之英文智识;其八,因教授与学生言语每不统一,故不如以英语代之。”[11]151从其分析来看,外文原版教材具有质量优良、利于学习英文、方便教师授课等优长之处。
外文原版教材自有其优长之处,但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为人关注。其时海内学者“夙以高级学校用外国文教授,效率低劣为憾”[12]。近代科学家蔡翘曾忧心忡忡地谈起科学教材的现状:“国内大学之科学教材类多采用外国课本,且尚有一部分学术竟至用外国语讲演而不以为怪,此不特滑稽可笑,抑亦万分可怜。盖一个独立国人民而不能对其本国听众用自己文字及语言表达思想,天下可耻之事殊有甚于此者,谁令为之,谁负其责,我辈从事科学教育者宁不惭愧耶?”[13]蔡翘的话表明了一个有责任心的科学家的态度,他清醒地认识到外文原版教材存在的严重问题,即直接从西方国家照搬使用无益于学术独立。因此,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呼吁使用中文大学教材的声音便见诸报端杂志。有学者通过中西比较的方法,指出大学采用中文教材有四方面的好处:“(甲)教育效率得以增加也。其一、因读中文书快而读西文书慢;如以读英文书之时间读中文书,其时间之节省自不待智者而知;其二、因能读中文者多而能读英文者少,今能以中文为科学之演述,则国人得科学智识之机会自必加多。(乙)教育之经济得以增也——买西书因贵,而以银洋买西书更贵。(丙)教育之体统得以保全也。夫国有一国之文字,即一国有一国之书籍,亦即一国有一国之学校,俾得发扬文化保存国粹。(丁)留学之结果可以较优也。”[11]1511931年4月27日蔡元培在《申报》上发表了《国化教科书问题》一文,将采用中文教材提升到国化教科书的高度。他指出大学教科书采用外文原本教材“是不得已的过渡办法”,并明确提出大学教材要尽快实现中国化,“除开外国文学一项,其余各种科学都应该来用中国文做的教本。”[14]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外文原版教材的引进及使用成为这一时期大学教材建设的显著特点。外文原版教材的引进相对初期的讲义编印而言,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不仅促进了大学各科教材的正规化建设,也促进了大学课程、教法及教育理念的全面革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大学在同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越来越感到迷失自我的困惑。缘此,大学教材的本土化建设便被提上日程。
三、中国近代大学教材本土化探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趋于稳定的时局为大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大学各项制度逐步完善,教育学术渐趋独立发展,大学教材建设进入了本土化探索的新时期。
此时,一大批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他们对西方当时的学术发展及大学教学状况有较为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其中不少学者已能跟踪世界前沿研究,并努力探索中国教育学术独立发展的道路。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并在多所大学开设新课程,编译的教材因而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教育部关于职称评定的规定对于大学教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30年,教育部规定教授与副教授的晋升要将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综合考虑。具体而言,要取得教授和副教授的职称,需要有发表独创性的著作;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需要5年教学经验并且在得到最后学位后发表过独创性的著作,才有资格晋升为正教授,需要3年的教学经验才能晋升副教授,其他条件与教授相同。这样的规定,促使大学教授和副教授重视科研,并将其研究成果或学术著作及时出版,因而该时期学术著作数量增长较快。学术著作多为学者的研究心得,其要点一般也曾以讲义的形式在课堂上讲授过,因此,学术著作出版后多用作教学用书和教学参考用书。
近代大学教材的本土化探索,首先是自民间开始的,国家默许民间出版机构自主编印,政府负责对其审查。自30年代起,近代诸多出版机构在与大学和学术团体合作的基础上,推出系列大学教材。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大学丛书”水平最高、影响最大,为众多高校所选用。商务印书馆首先从征集国内外大学课程表着手,据此拟定大学应有科目草案。1933年1月,商务将《大学科目草案》交送“大学丛书”委员会审查,各委员对于编辑方针的拟订、院系的更动、新系的添设、科目的增删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商务在参照各委员建议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并将《大学科目草案》更名为《大学丛书目录》。《大学丛书目录》以普通大学各院系应有之科目为编印的依据,即根据各院系的科目情况有针对性地准备书稿。商务版“大学丛书”先后出版325种,涵盖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等8个学院737个科目,各学科的用书均初具规模,其中很大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大学各学科的奠基之作,“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自编大学教科书的基础。”。[15]这套丛书不仅内容适合各学院系使用,而且降低了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使得每个学生拥有和使用中文大学课本成为可能,既避免了制作和使用讲义的诸多烦琐,又克服了购买和使用外文教材的种种弊端。更为重要的是,由教材进而课程进而教法势必带来一系列变革,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规范化发展。
“大学丛书”包括译著和编著两种类型。其中,译著先后共出版129种,大多为国外学术研究的力作,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从学科上看,涉及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许多门类。从选收的类型上看,除选入大量西方著作外,也收入了日本学者的代表作,如关一著、马凌甫译的《工业政策》,园正造著、萧君绛译的《群论》,原歌定二著、刘肇龙译的《水力学》等。从编译者的选择看,多为留洋归国学识丰赡的专业学者,如李四光、丁燮林、任鸿隽、罗家伦、何炳松、秉志、傅统先、杜亚泉等,他们既熟悉专业领域国外的研究状况,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可以通过教学研究的积累将其成果编译出版,商务以丛书的形式策划出版这些译著,从而实现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导入国内的初衷。教材中国内学者的著作共196种,皆为一时之选,有些著作更堪称学术精品,如王力的《中国音韵学》、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金岳霖的《逻辑》、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陈鹤琴的《儿童心理之研究》等。各领域知名教授通过著书立说将他们多年教学科研的成果系统化,从而促进了学术的交流与繁荣。商务版“大学丛书”的意义在于以民间力量参与大学教材出版,促进了近代大学教材的发展与繁荣。
20世纪40年代初,教育部开始加强对大学课程及教材的统制。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所编大学教本虽多,却未能遍及所有科目,且抗战期间经费的困难状况影响了原有的出书计划。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政府力量从事大学教材的审查编印。部编教材命名为“部定大学用书”,凸显其权威性和统一性。“部定大学用书”的编辑出版是与教育部整理大学课程紧密相联的,1938-1940年间教育部相继整理并颁布了各学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和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在此基础上,1939年教育部设立部定大学用书编译委员会开始从事大学教材的统编工作。至1947年共完成编译大学用书约250种。虽然部编大学教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编印大学教材的自由,不利于大学教材市场的发展和业务的竞争,但在战时经济萧条和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由国家统一组织规划有利于解决大学教材的匮乏问题。而且,部编教材根据当时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借鉴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的出版经验和组稿方式,博采众家,编译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课程的科学化和教材的统一化。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教材建设在近代历经编印讲义、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到本土化教材的发展历程,并呈现由民间自主编印到国家统一出版的趋势。近代大学教材发展所呈现出的这种特点既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又受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当前,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大学教材建设显得尤为迫切。中国近代大学教材建设的历程无疑会为之提供历史的镜鉴,这不仅由于当前大学教材依然存在着讲义、外文原版和自主编著等类型,而且近代大学教材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困惑,诸如引进与原创(国际化与本土化)、审定与国定(多样化与标准化)等选择,依然为现今所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