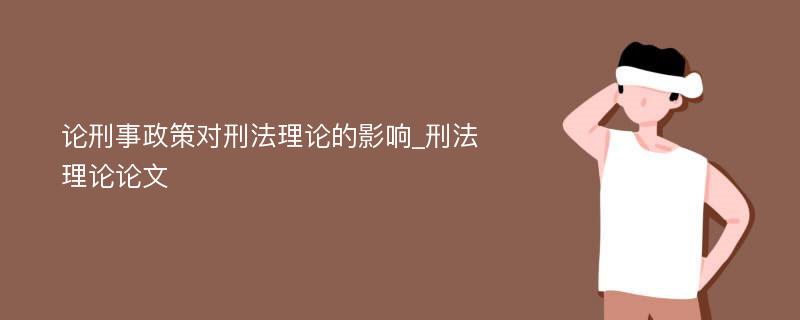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刑事政策定义的不同解读
“刑事政策(Kriminalpolitik)”一词,18世纪末便在德国被使用,但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始自德国学者Feuerbach(1775-1833)1803年的刑法教科书,①后来由H.W.E.Henke②和Liszt等诸多学者推广,逐渐形成了现代刑事政策学。大陆法系刑事法学关于刑事政策的定义尽管表述五花八门,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二定义说”和“三定义说”。③英美法系刑事法学中并没有大陆法系刑事法学意义上的刑事政策这一术语。因此,在一些著名的英美法律词典——如美国的Black's Law Dictionary和英国的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中,都没有关于刑事政策的专门词条。但是英美刑事法学者经常使用criminal policy或crime policy以及penal policy。不过,他们所探讨的criminal policy或crime policy一般是指犯罪学意义上的对策,而penal policy一般是指刑罚学(penology)意义上的罪犯矫正政策。故而学者们认为,英美刑事法学中的刑事政策,其含义就是“criminal(犯罪的)”与“policy(政策)”相加,再加上“刑罚政策”。英国南安普顿(Southampton)大学法学院教授Andrew Rutherford曾经指出:刑事政策包括刑事司法程序从警察到监狱体系的所有环节——所有关涉与犯罪作斗争以及保护公民不受不公正或压制对待而与犯罪斗争的一切措施;刑事政策也重视以往被忽视了的犯罪被害人问题,总之,刑事政策涉及预防犯罪(更恰当地说是减少犯罪)的方方面面;因此,刑事政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刑罚与刑事司法问题,它涵盖了社会针对犯罪现象所做出的全部特定反应内容。④如此看来,英美刑事法学中的刑事政策,其含义大体上与大陆法系刑事法学中广义的刑事政策概念相当,与Liszt主张的“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原则的总和”⑤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的刑事法学中,关于刑事政策的定义,学者们历来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所谓刑事政策,就是指社会公共权威综合运用刑罚、非刑罚方法与各种社会手段预防、控制犯罪的策略”;⑥也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⑦还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是指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对因此而牵涉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⑧此外,还有学者明确主张“犯罪对策就是刑事政策”。⑨前述关于刑事政策的见解各有其理,但是本质上并未超出大陆法系刑事法学关于刑事政策的“二定义说”和“三定义说”的范畴,只不过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在笔者看来,如果在刑事法制的范畴内探讨刑事政策定义,当选择狭义的刑事政策定义为宜。这是因为,广义的刑事政策涵盖了所有与预防和控制犯罪有关的公共政策,如果学理上选择广义的刑事政策,不仅刑事法学者无力胜任此一意义上的刑事政策研究,而且还会使刑事政策本身与其它社会公共政策混为一谈,⑩从而丧失刑事政策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而最狭义的刑事政策仅仅将特别预防作为其目的,严格将刑事政策的调整对象限定为犯罪者或有犯罪危险者(可适用保安处分者),因而把刑事立法和一般潜在犯罪人排除在刑事政策的考量范围之外,显然不符合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出于此种考虑,笔者将我国的刑事政策界定为:所谓刑事政策,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等部门(11)根据我国国情和犯罪状况制定或运用的预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矫治犯罪人的各种刑事对策。笔者所主张的刑事政策定义仍然属于狭义的刑事政策定义,它主要涉及国家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三大方面。本文正是在此一定义上探讨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
二、刑法学说史的考察:刑事政策思想决定刑法理论走向
当下,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刑事政策与相关刑事法律科学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但是,就刑法理论而言,刑事政策与之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究竟有何影响?却鲜见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这正如德国学者Lothar Kulen教授所言:“这个所谓的崇尚自由的刑法理念到底与刑事政策,尤其是与现代刑事政策有何关联?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依据的,因为政策正是致力于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来实现特定的目标,特别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同时,刑事政策正是试图通过公布(Erlassen)刑法来实现这一点。”(12)不难理解,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二者都涉及犯罪与刑事处罚,从某种角度来看,刑法理论中很多问题,诸如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犯罪论与刑罚论等问题,实际上也是刑事政策问题。
在Criminal Policy Making一书中,Andrew Rutherford教授在其“导论”的第一句话便道破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微妙关系。他说:“刑事政策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确定刑法的边界,包括那些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能有效的辩护理由。”(13)据此,刑事政策就决定了刑法与刑法理论的基本走向。其实,一部近现代刑事政策史,就是一部近现代刑法理论史!
1791年《法国法典》(French Code)(14)在欧洲大陆率先采纳了“威慑原则”(the principle of deterrence),并深刻影响了德国刑法理论研究与刑事立法,威慑论在德国很快流行起来。(15)在18世纪晚期,德国刑事法学研究异常活跃。特别是围绕刑事责任根据与刑罚目的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乃是von Crolmann(1775-1829)(16)与Feuerbach这两位学术友人之间的论战。当时关于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解释就是自Aristotle(384 BC-322 BC)以来,Baron Samuel von Pufendorf(1632-1694)第一个以独立而科学的方法思考并论证了的“道义责任论”(moral responsibility)(17)和Immanuel Kant(1724-1804)法哲学思想中的意思自由论(the freedom of will)。事实上,道义责任论的法哲学根基乃是“道义自由”(freedom of morality)或“道义自由论”(the theory of moral freedom)。(18)道义自由论认为:人具有独立自主地进行道德选择和决定的能力;道德选择和决定的自由是道德责任的前提,所谓“决定作恶的是我自己,想去行善的也是我自己”(萨特语)。(19)Kant法哲学中的意思自由论与道义自由论一脉相存,认为人的道德意志是独立的、绝对自由的,从而进一步为道义责任论提供了强大的法哲学理论支持。意思自由论的基本思想乃是:人具有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而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的能力;人能够在其自己的意志支配下选择为善或者为恶;滥用自由的行为侵害社会或他人,表明行为人选择了恶,这就违反了道德规则,因而行为人具有道德的过错或具有道德上的应受非难性。换言之,每个人的意志乃是自由的,即每个人具有选择其行为的自由,而犯罪正是行为人在其意思自由的前提下对行为选择的结果。既然行为人具有意思自由,他可以选择适法行为,而他偏偏选择违法行为,因此这就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
Crolmann与Feuerbach都不赞同意思自由论。Grolmann认为:人之所以犯罪,是由其危险性格决定的;刑罚不应当针对犯罪人的意思自由,而应当针对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应当特别注意行为人的个人性格;刑法与道德相互间没有什么关系,刑罚也不可能改善犯罪人的道德水平;那些违反法律意志的人,将来还会以相同或者相似的方式违反法律;刑罚应当指向犯罪行为显示出来的犯罪人的性格,犯罪人现在实施的犯罪可能预示了其将来可能实施的罪行——即:判断犯罪人是否将来会重复已实施的犯罪,更多取决于行为人的个人性格以及具体案件的特定情况。因此,犯罪人的永久性格可以作为确定其刑罚适用的因素。应当贯彻这样的规则——犯罪人的违法倾向越大,他应受到的处罚就越重;而违法倾向的程度,可以根据犯罪人违法行为所侵害的权利(法益)性质来加以判断。基于以上分析,Grolmann坚决主张“特别预防论”,其基本思想是:作为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的反应,刑罚的根据就在于——针对那些犯罪人,法制政府有权进行压制(威慑),这种压制甚至包括消灭犯罪人;运用压制犯罪人的威慑方法能够使犯罪人回归社会,这里所说的压制方法就是刑罚;刑罚的目的就在于防止犯罪人将来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尤应指出的是,Grolmann与Feuerbach一样,对刑事法律制定怀有崇高敬意,认为刑法典只能根据现实社会中大多数犯罪的一般情况和原则,确定哪些人是犯罪人以及什么行为是犯罪。(20)
Feuerbach一方面反对意思自由论,同时他坚决反对Grolmann的特别预防论,而主张“一般预防论”(general deterrence)。他认为Grolmann的特别预防论的致命弱点在于“选择了行为的纯粹可能性(危险性格)作为处罚根据,而不是把真实的违法行为作为处罚的根据”。在法哲学意义上,Feuerbah与Kant都试图为刑法寻求一个永恒的支撑点,但是Kant力主“意思自由论”,试图在其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以上天的名义或通过永恒审判的绝对真理等方法来阐释刑法问题,而Feuerbach则倡导“一般预防论”,将刑法奠基于地球上(尘世)立法者的权力之上,认为刑法乃是人性卑微冲动的结果——地球上立法者的权力与人性的卑微冲动允许某种精确的制度设计,刑法正是这种制度设计的产物。他否定刑罚是国家发动的根据假设的道义自由进行的道义报复。他指出:“推定道义自由需要刑法,这是绝对自相矛盾”;刑罚乃是一种市民处罚(civic punishment,即世俗的、为了国家的目的而发动的区别于道义处罚的处罚);刑罚奠基于明确宣告的法律规定,从犯罪人角度看,刑罚的合理性在于通过刑罚方法威慑进而促使犯罪人自愿服从;从国家角度看,刑罚的合理性则在于通过威慑的方法,阻吓犯罪和防止犯罪的可能性,而刑罚威慑的最终目的就是避免侵害权利(法益),即防止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实体权利受到犯罪侵害。在Feuerbach看来,人类行为显然受着人类意志的支配,而人类意志是一种纯粹感性动机的产品或混合物,为了使人类感性动机纯化,法律必须尽可能地严格和明确;防止犯罪是国家的功能,但是通过直接的物理强制(physical compulsion)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因此,国家可以通过对那些可能犯罪的人进行威慑来采取心理强制(psychological compulsion),而且,这种威慑必须充分有力,否则不会有效。Feuerbach这些学说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制定、颁布完备的刑罚法规,将罪刑关系清楚昭示于天下,使每个国民都知道什么是犯罪,犯罪后将有什么后果。此即“心理强制论”(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coercion)或“通过法律恐吓的威慑理论”(the theory of deterrence through threat of law)的精髓所在。(21)
为了实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刑法哲学思想,Feuerbach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实践。由于受法国18世纪后期刑法改革的影响,德国维尔兹堡(Würzberg)大学教授Kleinschrod(1762-1824)受命起草巴伐利亚(Bavaria)刑法典,并于1802年出版。但是,Kleinschrod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普鲁士总邦法》(General Prussia Landrecht)(22)刑法部分的旧套路和精神,刑法立法体系混乱,用语含糊不清,因而受到Feuerbach的尖锐批评。在论及刑法立法时,Feuerbach一针见血地指出:一部刑法典不是概略纲要,而应当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在其自身内部必须协调,它必须以精确的定义和独特的明确适用规则统驭整部法典;刑法典决不能追求经院哲学家似的矫揉造作和所谓精细明白体系;聪明的立法者不会以演绎的方法来立法,也不会使用哲学的和学究式的表达方式来立法,立法者应当把哲学精神展示在自己深广的立法观念中,而不是表现在虚幻的哲学语言中,立法者应当使用充满智慧的、清楚而崇高的民众语言,其简明的立法用语与其正确而精致的思想相协调,能够被所有民众理解,立法者所确立的刑法原则应当深思熟虑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基础。(23)
Feuerbach对Kleinschrod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的批评以及发表的关于刑法立法的高论不仅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引起了巴伐利亚当局的高度关注。1805年,巴伐利亚司法部长任命Feuerbach重新起草巴伐利亚刑法典,最终孕育了德国刑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13年5月16日《巴伐利亚刑法典》!这一时期,Feuerbach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草案可以视为实现其刑事政策思想(特别是刑法立法政策思想)的伟大实践。他的很多重要刑事政策思想和刑法理论均通过该刑法草案体现出来。特别是关于罪刑法定主义、一般预防思想、犯罪构成要件、限制和约束法官裁量权、刑法立法体系等奠定现代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基础的学说,都包含在其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中了。Feuerbach起草的刑法典基本上为1813年《巴伐利亚刑法典》所接受(虽然不是全部)。该法典“以表达清晰、值得所有立法者敬重而著称”,其划时代意义在于:确立了罪刑法定主义并明确废除了类推定罪;彻底废除了法官无限制的裁量权,确立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明确规定了加重处罚和减轻处罚的法律原则;仿效法国刑法典犯罪分类,将犯罪分为“刑事犯罪”(crimes)、“轻罪”(misdemeanors)、“违警罪(transgressions)”;明确规定总则条款适用于所有“刑事犯罪”和“轻罪”,而“违警罪”则由专门的《违警犯罪法》(Code for Offenses against Police Supervision)去调整;刑法分则条文力求清楚描述构成要件,体现了Feuerbach关于“立法者规定的每个罪行包括了特定要素,这些特定要素乃是定罪的唯一标准”的思想。(2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陆法系刑法学说史上以Grolmann与Feuerbach等人为代表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有关刑法与刑罚的论析,本质上应该已经属于近现代刑事政策的思想了。事实上,费尔巴哈最初所使用的“刑事政策”就是指的基于其“心理强制说的刑事立法政策”,(25)而Feuerbach 1805年受命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草案,正是其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检验。完全可以这样认定:正是Feuerbach等先辈贤达的开拓性研究,为现代刑法及其理论奠定了刑事政策思想根基,而Feuerbach等人的刑事政策思想从此决定了现代罪刑法定等核心刑法理论的基本走向。及至当代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说信奉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抑或“结果无价值论”还是“行为无价值论”,莫不取决于其刑事政策立场。
三、行为价值学说辩证:刑事政策立场决定刑法理论选择
就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而言,关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的对立与争论从未止息。鉴于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实际上乃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延续或另一种表现形式,(26)故本文仅以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对立来说明刑事政策立场对刑法理论选择的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行为无价值(Handlungsunwert)与结果无价值(Erfolgsunwert)深深受到了德国刑法学家Hans Welzel(1904-1977)刑法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对于Welzel论证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法哲学背景却无人论及。1909年,德国无意识(unconsciousness(27))哲学家E.von Hartmann(1842-1906)的哲学名著《价值学纲要》(Grundriss der Axiologie,“Outline of Axiology”1909)出版,该书首次系统论证了价值哲学体系,从而标志着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的第三大哲学体系——价值论的诞生。价值论本来就是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哲学学说,它主要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以及人的行为对个人、社会的意义。此后,作为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潮,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迅速而广泛地被应用于伦理学、法学、美学、认识论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正是在此种背景下,Welzel在1936年发表了重要的刑法哲学著作——《刑法中的自然主义与价值哲学》(Naturalismus und Wertphilosophie im Strafrecht,1936),其中,Welzel运用价值哲学的基本理论,对刑法学的行为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了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概念。
Welzel从其创立的目的行为理论出发,认为“对行为不应只作为因果过程来把握,而应该和该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起来加以理解”;(28)“不法”并不是引起利益(法益)侵害的因果事实,(29)“不法”存在于目的性行为的价值关系中,从价值哲学角度来看,刑法的价值评价对象乃是(有)目的(之)行为,其价值内容体现在行为目的性中行为人对刑法规范所设定的禁止和命令的态度;(30)如果行为人遵守刑法规范设定的禁止和命令,即行为人没有实施不法行为,则行为人的适法行为就因为符合法的价值而具有价值;如果行为人基于反规范的目的,违反刑法规范设定的禁止和命令,即行为人实施了不法行为,则行为人反规范的不法行为就因为违法性而不符合法的价值,因而行为人之行为就是无价值的,这种不法的无价值行为就是犯罪。以行为的有无价值(是否符合法的价值)作为判断是否不法或犯罪的学说,被称之为“行为无价值论”。按照同样的逻辑,Welzel把客观主义主张“不法(犯罪)是利益(法益)侵害”称之为“结果无价值”,而以是否发生侵害结果作为判断是否不法或犯罪的学说则是“结果无价值论”。
经过70多年的研究发展,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已经十分成熟,并成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关于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可分为:(1)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和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彻底贯彻规范违反说,认为只有行为无价值决定违法性,结果是偶然的产物,仅仅是客观的处罚条件而已。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认为,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同时都对违法性有影响,事实上,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同时加入了部分行为无价值论的思想,主张折衷的犯罪论(违法论)。(31)德国的刑事司法判例与刑法理论主要持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以下略称“行为无价值论”);(32)(2)结果无价值一元论与结果无价值二元论(二元违法论)。结果无价值一元论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利益(法益)侵害或侵害利益(法益)的危险,判断行为是否违法,只能根据行为人之行为是否造成了实际侵害结果,这就是考察行为人之行为是否造成了对利益(法益)的实际侵害或侵害危险;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要素具有辅助意义,只能作为是否存在责任的判断根据。结果无价值二元论认为:只有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联系起来考虑,行为才具有作为人的行为意义,在判断行为是否违法时,应当把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要素作为评价资料,行为人的主观要素既对结果无价值(法益侵害性)有影响,也对行为无价值(规范违反性)有影响。(33)日本刑事司法判例与刑法理论主要持结果无价值二元论(以下略称“结果无价值论”)。
当前,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区别主要在于:(1)关于排除违法性事由的一般原理,结果无价值论和法益衡量说(34)有关,而行为无价值论与社会相当性说(35)有关;(2)关于主观的违法要素,结果无价值论由于将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质作为重点,因此,原则上不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相反地,行为无价值论则肯定包括故意、过失在内的主观违法要素;(3)关于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如正当防卫意思),结果无价值论主张不要;相反地,行为无价值论则主张需要。(36)从上述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在有关违法性认识上存在重要区别,因此,信奉或坚持结果无价值论或行为无价值论就会得出不同的违法或犯罪结论。这里仅举数例:
第一,关于不能犯未遂。德国刑法典第22条规定:“行为人已直接实施犯罪,而未发生行为人所预期的结果的,是未遂犯。”第23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由于对犯罪对象和手段的认识错误,在性质上其犯罪行为不能实行终了的,法院可免除其刑罚,或减轻其刑罚。”(37)德国刑法典实际上体现了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据此,不能犯未遂原则上仍然应当被评价为“无价值”或“不法”,只不过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件事实裁量“免除其刑罚”。换言之,在行为无价值论看来,不能犯未遂本质上也属于犯罪,只是在价值判断上可以免除刑事处罚。而且,德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对象不能犯的某些案件仍然认为具有可罚性。1952年,德国曾经发生了所谓“胡椒袋案”(行为人准备用袋装胡椒粉迷住送钞员的眼睛,并守候在轻轨车站,行为人还发动了用以逃跑的车辆在轻轨旁等候,但是由于被害人没有到来而致未遂)。对于此案,德国学者和司法界均认为不应当免除对行为人的处罚。(38)这和德国奉行的与行为无价值论一致的主观的未遂理论(39)完全吻合。但是在结果无价值论看来,可能正好得出相反结论——对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特别是绝对不能犯)的场合(如把尸体当活人而开枪击中或把白糖当砒霜投放他人饮料中的“杀人”),因为不可能造成法益侵害的事实发生,因而主张不存在结果无价值的事实,故不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40)
第二,关于偶然防卫。所谓偶然防卫是指行为人在毫无防卫意思的前提下实施了某一行为,而这一行为碰巧(偶然)满足了正当防卫的客观要件。例如:甲喝酒致醉,在回家的路上,见到女青年乙。甲上前抓住女青年乙,并扯破了乙女的上衣,意图强奸。乙女挣脱逃跑,甲紧追不舍。此时丙驾驶一辆汽车正好撞上甲某,致其死亡,乙得以逃脱。对于此一案例,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行为无价值论强调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即成立正当防卫,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防卫意思为前提,换言之,行为人“只有对自己的行为作为正当防卫被允许这一许可(许容)性的认识才是主观的正当化要素。如果不存在这一认识,就意味着是出于违反规范的意思而实施行为,因而具有行为无价值论上的违法”。(41)所以,在行为无价值论看来,前述案例不成立正当防卫,行为人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罪责。然而,结果无价值论一般主张“防卫意思不要说”,认为即便行为人没有防卫意思——对其处于正当防卫的状况并无认识,也可以成立正当防卫。因为结果无价值论特别强调法益侵害,故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符合正当防卫要件,便具有防卫效果,所以认为偶然防卫也可以阻却违法性。
第三,关于以非法方式实现权利保护。所谓“以非法方式实现权利保护”是指以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保护行为人自己的某种利益,例如,以抢劫的方式实现行为人自己的债权等。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甲与乙做中药生意时相识,乙欠甲78万元并出具了欠条,乙与甲约定1997年10月25日付清货款人民币78万元。期满后,乙未给付货款且下落不明,甲经多次追讨未果。1999年9月,甲得知乙仍在做虫草生意,即与丙商定,由丙假装卖主,通过中介人张某联系与乙进行交易。同年9月17日,丙携带虫草样品,通过张某联系让乙看货。乙与丙见面看货,双方商定由乙以每公斤8800元价格收购丙的虫草并于同年9月21日在一农家小院交易。9月21日上午,甲和其亲友、债主10余人到乙与丙约定的见面地点设伏等候。15时许,乙与朱某、陈某等人携带现金人民币55万元驾车到约定的交易地点后,甲带领数人到现场,出示乙写的欠条要其归还欠款。乙声明所携货款是别人的,甲要求对方出示相应的凭证未果后,即对乙进行威胁并打其两耳光,强令司机打开车门,甲从汽车内搜出现金人民币55万元。让乙点数后,甲给乙写了一张“收到55万元还款”的收条,又令乙写下“还欠甲23万元货款”的欠条一张。(42)
对于本案的处理,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行为无价值论看来,甲和乙之间虽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甲要实现自己的债权,必须采取合法、有效的途径或方法。甲对乙采取威胁和暴力手段,强行将乙汽车上的55万元钱款拿走,尽管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但是这种以抢劫的方法来实现债权的行为本质上严重违反了刑法规范,即已经触犯了刑法作出的禁止或命令规范,因而具有行为无价值性质(不法性),(43)构成抢劫罪。但是结果无价值论则认为,由于本案中甲实际上是抢回了属于自己的55万元钱款,也就是说,本案没有发生真实的法益侵害,所以客观上并不存在结果无价值,因而甲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本案的第一审法院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二审法院却推翻了一审法院对甲的定罪,宣告甲无罪。(44)这表明两级法院事实上分别采取了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不同理论立场。
毫无疑问,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早已发展成为十分精致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很难说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甚至很难说哪一个比另一个更加科学。刑法学上的很多成熟学说都是如此,如关于共同正犯本质的“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实行行为共同说”、“共同意思主体说”等均有其科学合理之处,但是不同的共同正犯理论确认的刑罚处罚范围具有明显的宽窄差异。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审判或者刑法学主流学说选择何种理论,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立场的价值选择——即取决于一个国家刑事政策关于公正(正义)的诉求与定位。从刑事政策立场来看,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都是为“不法”或违法乃至犯罪界定范围,或者说都是为如何确定刑罚处罚范围划定界限。但是一般而言,行为无价值论的处罚范围要大于结果无价值论的处罚范围。国家的刑事司法审判代表着国家的刑事政策立场,而国家刑事司法判例(在中国,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刑法判例)的刑事政策立场往往会引导或决定刑法理论的研究发展方向。(45)日本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流行行为无价值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结果无价值论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及至近些年来“行为无价值论重新复兴”的发展势头,(46)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日本刑事政策立场的变化所致。
四、结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相互作用
Liszt曾经指出:“刑事政策给予我们评价现行法律的标准,它向我们阐明应当适用的法律;它也教导我们从它的目的出发来理解现行法律,并按照它的目的具体适用法律。”(47)不难理解,Liszt的这一论断说明了刑事政策对刑法制定、刑法适用乃至刑法解释的决定性意义。刑法学以研究刑法立法、刑法适用和刑法解释为基本内容,所以毋需赘言,刑法理论当然会受到刑事政策的深刻而决定性影响,“刑法学向刑事政策靠拢”(48)就成为刑法学(甚至刑法立法)研究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应当指出,强调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决定意义,并不意味着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就不具有反制作用。事实上,刑法理论同样对刑事政策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影响力。这不仅因为近现代刑事政策思想正是发端于刑法学说的发展过程中,而且还因为刑事政策思想与刑法理论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刑法理论中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死刑存废的学说、社会防卫理论等等,其本身既是刑法理论,又是刑事政策思想,而这些刑法理论无论是对当代刑事政策的制定还是对刑事政策的推行,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所谓“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Liszt语),正好说明了刑法乃至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制约意义。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国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各类暴力犯罪案件频频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有效地遏制犯罪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决策层及时提出了“严打”、“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然而,由于此一刑事政策过分突出其政策效用而忽视了刑事政策应当受到刑法制约的属性,导致“严打”、“从重从快”脱离罪刑法定轨道,因而受到刑法理论界的尖锐批评。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法理学角度看,“严打”与罪刑法定精神相背离。(49)更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批评“严打”、“从重从快”刑事政策存在严重缺陷。(50)正是那些立足于罪刑法定刑法理论立场的善意批评,促使我国“严打”、“从重从快”刑事政策现在变得更加理性,并催生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彻底改变了“严打”刑事政策片面追求“惩罚”而忽视“宽容”或“谦抑”的政策导向,是更为科学、合理且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政策。中国的情况令人信服的说明了刑法理论能够影响甚至推进刑事政策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注①;张甘妹:《刑事政策》,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印行,第1页。[日]森本益之等:《刑事政策学》,戴波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德国19世纪重要的刑法学家,著有《刑法理论之争》(Ueber den Streit der Strafrechtstheorien,1811)、《刑事法与刑事政策手册》(Handbuch des Criminalrechts und der Kriminalpolitik,1823)等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他反对绝对报应刑论,但主张修正了报应刑论。
③“二定义说”认为,刑事政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犯罪、镇压犯罪为目的所为的一切手段或方法;狭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犯罪、镇压犯罪为目的,运用刑罚以及具有与刑罚类似作用之诸制度,对犯罪人及有犯罪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刑事之诸对策。“三定义说”则认为,刑事政策有广义、狭义、最狭义三种:广义的刑事政策系指国家以预防、镇压犯罪为目的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与方针;狭义的刑事政策系指对犯罪者或有犯罪危险者,以预防、镇压犯罪为直接目的所采取的国家强制对策;最狭义的刑事政策则是指对各个犯罪者、犯罪危险者以特别预防为目的而实行的措施,如刑罚、保安处分等。从上述两类刑事政策定义可以看出,“三定义说”与“二定义说”基本类似,只是“三定义说”的“最狭义说”把特别预防作为一项独立的刑事政策内容。由于广义的刑事政策定义有包罗万象之嫌,即它把一切可能与犯罪学意义上之“犯罪”有关的公共政策统统纳入刑事政策范畴,从而可能使刑事政策被淹没在无限宽广的公共政策之中,因此,大陆法系的刑事法学者多选择“狭义的刑事政策定义。”
④Criminal Policy Making,edited by Andrew Rutherford,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97,"Introduction".
⑤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⑥侯宏林:《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⑦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⑧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⑨王牧主编:《犯罪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页。
⑩我国有学者否定刑事政策本质上属于公共政策,参见李卫红:《刑事政策概念误区种种及矫正》,载《刑事法学》2008年第5期。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刑事政策本质上就是公共政策的一种类型,但它有自己的特殊性。关于此一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章有阐释。
(11)此处所说的“司法机关等部门”,是指法院、检察院和对犯罪嫌疑人有侦查权以及对犯罪人有监管、刑事执行权力的机关。
(12)[德]诺沙·库伦:《刑事政策的原则》,陈毅坚译,谢望原等主编:《中国刑事政策报告》第3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708页。
(13)前引④。
(14)1791年《法国法典》实际上是一部刑法典。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刑”(Sentences),包括刑法总则及具体刑罚方法(死刑、劳役等)、累犯的加重处罚、缺席审判者的刑之执行、影响刑罚性质和期限的罪犯年龄、对犯罪的追诉期限以及被定罪人的回归;第二部分标题为“犯罪与刑罚”(Crimes and their punishment),包括犯罪的定义与分类,具体将犯罪分为针对公共利益的犯罪和针对个人的犯罪两大类。此外,还规定了处理共犯等的规则。刑法学说史认为,该法典对欧洲大陆国家刑法立法有重要影响,它是法国1810年刑法典的前身。参见Carl Ludwig,von Bar: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Law,Rothman Reprints,Inc.,1968,pp.321-322。
(15)参见Carl Ludwig,von Bar:A History of Continental Criminal Law,p.325.
(16)德国法学家,其1798年出版的刑法教科书(Lehrbuch)被视为德国刑法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坚决反对报复性刑罚,为推动德国刑法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17)前引(15)。
(18)有必要说明,有些学者认为是Kant的意思自由论为道义责任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就本人考证,此一结论似乎与学说史实不符。即道义责任论最初基于道义自由论而不是意思自由论,尽管意思自由论与道义自由论基本思想相同。
(19)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6页。
(20)前引(15),p.326,pp.427-428。
(21)前引(15),pp.428-434。
(22)亦可译为《普鲁士国家的普通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ur die Preussischen Sttaten,ALR)。
(23)前引(15),pp.328-330。
(24)前引(15),pp.330-331,p.431.
(25)前引①,[日]大谷实书,第7页注①。
(26)日本学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古典学派(客观主义刑法学)和近代学派(主观主义刑法学)的对立形式发生了变化,逐渐向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对立转变。参见[日]增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27)德国哲学家Hartmann用以说明终极实在性质的用语。他认为,无意识是宇宙的基本原则,是无所不包的存在的基础。它有两个互相关联而不可归约的属性——意志和理念。与此相应,它也具有两种功能:作为理念的无意识,深藏于自然的背后,它在理智的进步中展现自身;作为意志的无意识在人的生存中展现自身。两者统一于同一个无意识之中。
(28)[日]山口厚:《日本刑法学中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金光旭译,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29)当时德国盛行客观主义刑法学的“因果行为论”,而Welzel不赞同该理论而主张“目的行为论”。
(30)参见王安异:《刑法中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31)参见前引(26),[日]增根威彦书,第87页-88页。
(32)日本有学者认为,“现在在德国,仍然主张引起法益侵害的事实不过是客观的法益处罚条件而已的观点,或者说主张仅以行为无价值就能说明可罚性的基础的观点。”参见前引①[日]大谷实书,第182页。但是,著名德国刑法学家Roxin教授明确指出:“一个杀人的行为是由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共同组成的,在这里,两者必须在一种通过由归责理论更详细表示的关系中相互支持而存在。”[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第213页。Roxin教授这里主张的显然是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33)参见前引(26),[日]增根威彦书,“译者序”。
(34)所谓法益衡量说,是指即便行为人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行为,但是该行为引起的法益侵害小于其所保护的利益或等于其保护的利益时,可以阻却其违法性。
(35)行为无价值论所主张的违法性阻却的理论最初是目的说,即行为人之行为如果是为了正当目的的相当手段,则可以阻却其违法性。现在,行为无价值论则采用社会相当性说作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所谓社会相当性,是指以社会一般人为基准,判断某一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具有通常性,如果行为人之行为具有一般人日常生活之通常性,则可以阻却违法性。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36)前引①,[日]大谷实书,第182页注[1]。
(37)《德国刑法典》,徐久升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38)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39)主观的未遂理论源自主观犯罪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意志在犯罪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从行人的角度出发,行为人违反法律的禁止或命令时,在这些违反了受保护的规范的行为中,就已经存在着刑法上的重要不法。就未遂而言,是否对法益造成具体侵害,或者是否有侵害的危险,都不重要。参见前引(38),[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书,第254页。
(40)不同国家刑法立法及其理论对不能犯未遂的价值判断有很大不同。英国《1981年犯罪未遂法》第一条第(2)款规定:“即使事实上犯罪是不可能的(即不能犯,引者注),一个人也可以被认定为本条规定的犯罪未遂。”参见《英国刑事制定法精要》,谢望原主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这表明,英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不能犯未遂采取了类似于德国的行为无价值论立场。
(41)前引(35),[日]西田典之书,第128页。
(42)参见唐亚南:《债权人非法讨债不应以侵犯财产罪定罪》,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7601,2008.11.20。
(43)行为无价值论的重要根据乃是规范违反说。这一论点完全符合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即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不法侵害,原则上只能采取法律救济,任何人不可采取私力报复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即便是法律认可的正当防卫、紧急避嫌以及自救行为,也必须符合法的精神。当今世界两大法系都认同这一点。
(44)前引(42)。
(45)对此,最直观的说明就是“许霆案”的判决表明的刑事政策立场对我国刑法学理论的影响。关于许霆案定性,刑法学界有多种论争:有人认为是盗窃罪,有人认为是诈骗罪,有人认为是信用卡诈骗罪,还有人认为是侵占罪等,但是最高法院2008年8月核准“许霆案”以“盗窃(金融机构)罪论处”,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特别减轻程序”对许霆判处5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的这一核准所代表的刑事司法政策立场无疑决定了我国刑法学主流学说今后对类似案件持“盗窃论”的理论选择。
(46)前引(28)。
(47)[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8)[日]前田雅英:《刑法学和刑事政策》,黎宏译,谢望原等主编:《中国刑事政策报告》第一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26页。
(49)参见朱艳英:《罪刑法定与我国的‘严打’》,载《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2期。
(50)参见侯宏林:《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第308-3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