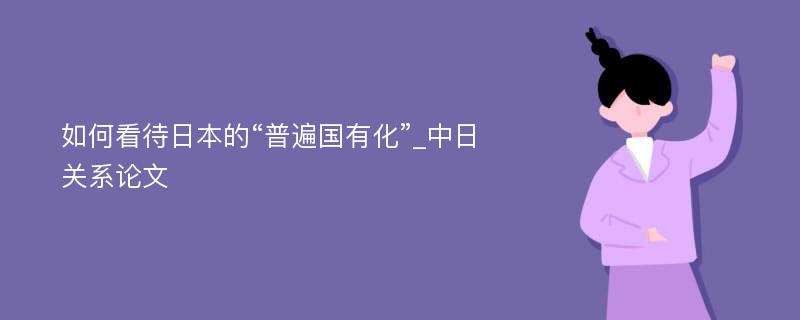
如何看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如何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是对中国安全与发展影响最大的邻国,中日关系在中国推动多极化与稳定周边的外交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实际已超出外交范畴,涉及包括国内社会在内的综合安全问题。如何准确把握日本的变化,并就对日政策做长远筹划,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
不普通的“普通国家”
过去10年,日本充分体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失重感。冷战结束之初,日本在经济上与美欧成鼎足之势,世界旧格局的瓦解又为其外向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活动空间。经济能量政治化的冲动,促使日本雄心勃勃地勾画起“日美欧三极主导”的世界秩序蓝图,并为此要自我改造成为“普通国家”。但始料未及的是,冷战的结束同样在日本国内引发剧烈震荡,政治领导力的削弱与经济低迷相互掣肘,恶性循环。
但剖开时局的表层,在政坛动荡不居、经济有景无气、外交做而难为的背后,日本国家战略取向的主线清晰可辨。久困思变,民族主义浪潮在这个国家的再度兴起,不光是折射出长期淤积的困顿感,而且恰恰也为进行中的重大调整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战略平台。对内全面改革、对外积极做为,成为自桥本以来历届内阁的共同追求,而最终目标都是要变日本为“普通国家”。
桥本的“六大改革”、小泉的“新世纪维新”,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对内,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重点首先放在经济、金融领域,尝试尽快自拔于结构性、制度性缺陷的泥潭。对外,从修改法制这一关键入手,自我松绑,加紧向国际政治、安全领域渗透。从《联合国和平合作法》到《周边事态法》再到最近的《恐怖对策特别对策法》,这一“整军三级跳”过程,前两跳相隔7年,而最近一跳不过两年有余。自卫队“走出去”的门槛越来越低,范围越来越宽,动作越来越大。
小泽一郎1993年出版综合论述国家战略的《日本改造计划》,率先使用了“普通国家”一词。其内涵一是否定传统的协调型政治模式,建立两大保守政党制,二是否定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茂路线”,修改宪法和防务政策,做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
由于一些因素的存在,日本的“普通国家”论特别是在其对外意义上令国际社会格外关注。首先,它有违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这一点当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取向与强化日美同盟的具体政策相结合时表现得尤为清楚。日本学界在总结日本的战争教训时曾说,日本在二战中错误地选择了落后于新殖民主义时代的旧游戏规则,现在,日本看来要再次落伍。其次,与日本自身政策更具关联性的是,由于它一直没能处理好历史认识问题,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其“普通国家”化也就格外令人担忧。
全面评估日本
近年来的日本给人一种焦躁之感,这首先反映了它主观愿望与差强人意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剧烈冲突。日本外交有“联合国中心”、“日美基轴”、“亚洲一员”等多种提法,由于借推动安理会改革实现政治大国梦的策略总体收效不大,90年代中期以来“联合国中心”有所淡化。日本转而侧重于日美双边同盟的强化与“自强”,但这不可避免地对其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造成冲击,使“亚洲一员”外交受挫。日本面临一系列的战略两难,“普通国家化”的道路注定艰难曲折。
日本要背靠日美同盟获取战略优势的意图很明显,但强化日美同盟并不能解决其所有的安全问题,相反势必引起周边反弹。在美国以利己均势为目标、战略威慑为重点、抑强扶弱为原则的亚太安全战略中,日本属“体制内国家”、地区内首席盟友,美日同盟是“基石”。但事实上,日本对同盟的稳固与持久缺乏自信,日美关系固有的脆弱性并未随军事合作的强化而消除。
日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美国的对日观只需看看10年前美国传统基金会乔治·弗里德曼等著的《下一次美日战争》便可一目了然。所以,日本实际更专注的不是导弹防御系统,而是要把独立开发出的军事侦察卫星早日送上天。同样道理,日本恐怕永远难以成为美国“在远东的英国盟友”。日本领导人强调日美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同盟”,这多少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近年来,日本以美国为范本的改革无不折戟沉沙,除政界亚洲派势力的抵制外,更多是验证了日美政治风土和文化历史的差异。在美国“文明冲突论”者眼里,日本也确是一个文化上的异己分子。亨廷顿说过,“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与美欧不同”,美英、美加、美澳这些伙伴之间“拥有同种文化、可协商解决问题、能相互信赖”,而世界上“再难找到像美日两国这样文化差异如此悬殊的国家了”。
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似近而远”,这起因于日美同盟,起因于日本外交安保政策上的种种动作,起因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今天的日本已经与和平宪法、“专守防卫”相去万里,政策与法理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威信并没有随“国际贡献”的扩大同步提升。小泉首相近日在就上述新法案与宪法的关系回答质询时干脆坦白:“我承认这确实是暧味。如果要追究其清楚的法律一贯性和明确性,我将穷于答辩。”从更深层次看,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的国家,百余年前力主“脱亚入欧”的精英们曾对其亚洲“恶邻”做过令人不齿的描述,但是日本的政治自负缺乏文化与心理支撑。用亨廷顿的话说,日本是一个“国家与文明圈在外延上等同的独特国家”,大和文明的影响所及仅止于列岛之内,无法在亚洲文明圈内发挥领导作用。战后日本靠的是经济,而一旦经济上不再独领风骚,马上就有一个如何调整心态、与邻国平等相处、在亚洲保住位置的问题。
对华关系是日本与亚洲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它大国多边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的快速发展成为日本要“有所做为”的口实,但也正是基于同一原因,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日本都充分“体认”对华关系的重要性。日本经济结构的国际属性极强,海外安全至关重要,在安全上有特殊的战略脆弱性。若干基本因素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会日益突出,但也不可能采取全面对抗政策。对日本而言,所谓的“中国威胁”尚未像冷战时代的“苏联威胁”那样已经固定化、格局化。在中美日“三角”中,由于中日均把发展对美关系置于首位,中日关系作为中美、日美关系变量的一面往往表现得比较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关系就绝对属于被动、从属地位。日本与美强化同盟,既是出于“普通国家化”的阶段性需求,也是中日关系发展不畅的结果。中日与中美在地缘、经济、历史、意识形态及民族心理诸方面的差异,决定了日美对华利益、政策的差异。
中国如何应对
近年来时起时伏的摩擦揭示出中日关系面临的两大突出难点:一是缺乏政治互信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关系、深化合作的瓶颈。二是如何重筑合作模式,扩大合作亮点,强化战略支撑。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是:同处战略上升期的中日两国,在各自构想的地区及世界秩序中以何种方式、给对方以什么位置。随着支撑中日关系的力量对比、地缘战略、外部环境、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等各方面的变化和调整,在“苏联威胁”消失后仅以经济合作与特定情结为支撑的关系框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无法再继续有效规范关系的实体。
中日关系正在经历的变化带有空前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直接构成对旧有模式与政策思路的历史性挑战。对中国而言,对日政策如何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如何在稳定周边与推动多极化之间把握平衡,将是新世纪最富挑战性的外交课题之一,而其中关键在于着眼全局、沉着冷静、准确判断、占据主动。
惟此,改善关系方能避免成为权宜之计。中日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摩擦从某种角度看有其必然性。与差异与摩擦本身相比,能否妥善处理差异与摩擦往往更为关键。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深化合作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前提是彼此认清共同利益,相互认可和尊重对方的战略利益。中日的共同利益首先在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当是考虑保障自身安全利益的重要选择,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须以区内战略力量间关系的稳定为前提。日本有制造紧张气氛以整军经武的一面,但同时它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中也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战略利益。
总之,形势的客观变化要求政策思路的同步调整,对日政策的评估应以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指针。我们可以先从一系列的设问及其解答开始:21世纪,我经济发展可资利用的主要外部资源及由此决定的主要合作对象在哪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来自日本的阻力作用是明显存在的,但它是不是最大的?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角度看,日本的政策取向构成促进而非促退因素,但作为邻国的日本的“极化”对中国又将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