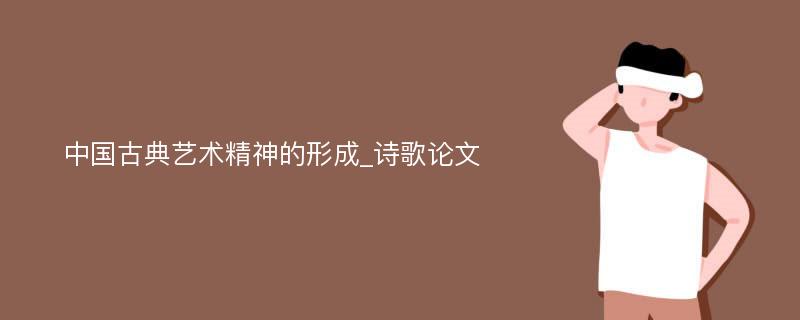
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典论文,精神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文学观念的演变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在他看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所谓“子学时代”,这是个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而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界便日渐形成了定于一尊的正统思想观念和依经立论的思想方法。冯友兰先生相信此后两千多年中,不仅儒家,其他如道家佛家等哲学流派,也同样是依经立论,依据现成的经典进行思维和判断。引申开来讲,直到现代的思想界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学色彩。
这种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划分,看起来似乎有点简单,但一般说来同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认识是吻合的。可以说自汉代以来,文人们对圣人和经典的权威地位的无条件尊崇便成为传统。因此用“经学时代”来概括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应当说大致上是不错的。但与传统的经学联系密切的文学是否也可以这样概括呢?人们往往认为当然也可以。自儒家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和把《诗》列入“六经”之伦,《诗经》便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无上的位置。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时,也总是把孔子谈论《诗经》时所说的“兴、观、群、怨”等观点和《尚书》等经典中的“诗言志”等说法作为中国诗学的早期经典,甚至如朱自清先生所说“开山的纲领”看待。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的传统诗学当然也同其他学术一样属于“经学”传统。
如果用这种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认识来解释传统经学中关于文学的观念,显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这样的观念也是中国早期诗学的观念,还不是十分有说服力。事实上,在经学兴起并以伦理教化的观念解释《诗经》的汉代,诗歌的创作与接受活动并非都是以伦理教化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勾勒诗歌发展史时指出,汉代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也有“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的继承《诗经》传统的作品,但总的说来,从意图、趣味到形式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雅润”到“清丽”,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再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尽管每一代文人都在谈论《诗经》的伦理或政治教化意义,但一代代的诗歌创作却是“华实异用,惟才所安”,依作者的兴趣与才华而转移。关于诗歌创作追求的演变,钟嵘是这样说的:“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注:钟嵘:《诗品序》,《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他所描绘的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从《风》即《诗经》的传统蜕变出来的过程。这种蜕变的动机与教化无关,只是为了“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了使诗歌有“滋味”而已。
从刘勰和钟嵘的说法来看,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是从四言转变到五言、从“雅润”转变到“清丽”、从“取效风骚”转变到“有滋味”,而这个过程显然与以教化为中心的观念相去甚远。这种差别说明,在两汉时期人们的心目中,《诗经》与一般的诗歌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已成为儒家的经典,因而关于《诗经》的认识基本上属于经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与欣赏活动中,人们对诗歌之类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有一种不同于经学的观念。经学化的《诗经》同非经学的诗歌创作与欣赏实践已出现分立之势。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解释为:“自从采诗制度废弛而诗歌亡佚,《春秋》之作就取代了诗歌的职能。”(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这意味着《诗经》与采诗制度废弛后的诗歌是不同的。采诗制度废弛后并不是不再有诗歌了,只是不再有对诗歌进行整理删定的工作,这些诗歌也就不再被用来进行社交应对和教化;《诗经》与《诗经》之后的亡佚诗歌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前者成为政治或伦理教化的附庸,后者则变成了个人的自发行为;由此而产生了诗歌观念的差异: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者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而《诗经》之后的诗歌创作观念所体现的却是作者自发的趣味需要与形式冲动。“诗经之学”与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之间出现了差异。
人们之所以把两汉文学理论整个归结到教化附庸的观点上去,显然是因为这种经学化的观点在经学昌盛的当时具有重要影响。而另一方面,尽管两汉时期的文学创作很繁盛,但诗歌创作意识与观念却带着强烈的自发倾向,作为创作观念体现的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传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尽管已经有了许多优秀作品,有了许多关于诗歌创作与欣赏的看法,却还没有一种理论把它们像对待《诗经》那样使之成为文学的经典和理想。汉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呼唤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成熟。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历史上较早的一篇关于文学问题的专论文章,就体现出这种时代的需要。曹丕在这篇专论中一方面盛赞当时文学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优秀作家辈出;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时的许多文人对文学的认识还为个人的偏长和偏见所囿。他认为这时应当有能够审己度人、公平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的理论著作和理论家“君子”对文学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他提到了文学的内在根据(“文以气为主”),也强调了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重点内容还是对作家风格的评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这些研究实际上开了后来《文心雕龙》对不同文学风格和范式研究的先河。
曹丕之后,东晋陆机的《文赋》更具体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问题。陆机在《文赋》的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写作《文赋》,是要总结如何写作的规律。但他也知道,写作的有些内在的奥妙是难以用语言说明的;他所能做的,实际上是示人以取则之径:“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所以在《文赋》的第一段就讲“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前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章应当是有感而发;但在他看来,有感是不够的,还要“取则”,即要有学习的典范。《文赋》各节讲的都是如何写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从优秀作品的范例和自己写作的体会中总结出来的范式:“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从《典论·论文》到《文赋》,关于文学的理论逐渐成熟,形成了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为准则的典范观念。
陆机之后的另一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他写作《诗品》是因为面对着文学活动的繁荣与无序而产生了想要为文学寻找规范的强烈愿望。钟嵘在批评诗歌时指出:“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也就是肯定了诗歌批评应当是有规则、有标准的。他所标举的标准就是在《诗品序》中提到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如果说陆机试图确立写作的典范,那么钟嵘所做的则是建立批评的规范。这些行为都已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风尚。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与传播活动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文学自身的典范和标准。从《世说新语》中士人们相互之间对文学作品的批评褒贬到《文章流别》、《文选》等文学作品选集的出现,都是这种评价活动的表现。而在理论建设中最能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当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对文学提出的原则是“宗经”,听上去是个经学的口号,但实际上他对经典价值的解释可以说完全文学化了。他在解释宗经的具体内涵时提出了六义,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些标准中所涉及的对文章内容的要求如“情深”、“风清”、“事信”、“义直”等等,都是一般化的概念,与作为儒家经典的具体伦理意义无关;更多的方面则是对于文章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的要求。
刘勰标举六义的真正动机在于匡正文学创作中“文体解散”之弊。在他看来,文学的问题不是遵循哪一家哲理的问题,而是缺乏文学自身的规则典范的问题。六义与任何一家哲学无关,其实是一套文章风格范式。他心目中的规范不仅仅是具体写作意义上的范式,而是本原意义上的规范,即“道”。刘勰在谈论“道”时并不关心与“文”无关的其他内容,他所要“原”的“道”是与“文”密不可分的概念。“道”将天地之文与人文统摄在一起,从而为文学规定了根本的性质。可以说《文心雕龙》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将经学的道统转换成了文学的“文统”,建立了文学经典的观念。他的“六义”说就是为将经学的经典转换成文学经典而提出的标准。只是在刘勰这里,树立文学典范的意识不是针对具体作品的品评意识,而是确立一种普遍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心雕龙》的确是在开创古典主义的理论观念。
“古典主义”是个外来语,在文艺思想史上人们最早是把古罗马时期的文艺思潮称为古典主义。古罗马的文艺思想就具体内容而言或许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古典主义却可以借用来很恰当地描述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等人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一位学者把古罗马贺拉斯(Q.Horace)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概括为三条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和合理原则。(注: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其中合理原则可以认为是一般性的普适的理性原则,合式原则是针对艺术创作而言的具体要求,而借鉴原则是使得合理与合式的观念获得客观标准的典范性观念。总之,这三条原则将文学的理想理性化、规范化和现实化了。这就是古典主义的根本意义,不仅适用于古罗马的文学精神,也适用于后来的法国古典主义以及近代的其他古典主义艺术思潮,实际上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古典主义艺术精神。
在批评家看来,古典主义往往意味着对典范、法则的过分推崇和对个性、创造性和天才的漠视,因而似乎是艺术观念平庸化乃至僵化的标志。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这种对典范、法则的推崇,为文学艺术经验的积淀和理性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代的人们关于艺术理想的普遍性和优秀作品价值的永恒性信念就是古典主义观念的产物。曹丕和刘勰希望自己关于文学的研究使自己获得不朽的价值,也正是基于这种古典意识。
二、宋元以来的文学典范意识
唐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繁荣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给宋代文学的创作以极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关于文学的议论和批评中。宋代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与前几个朝代都不同的特点:柳开、王禹偁的古文,潘阆、林逋等人的晚唐诗派,杨亿等人的“西昆体”,这些诗文流派的创作与主张尽管各不相同,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就是都以学习唐代的某些作家或某一流派的创作为目标。明人张綎在《刊西昆诗集序》中说:“杨、刘诸公倡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注:《四部丛刊》影印明本《西昆酬唱集》卷首。)在他看来,不仅标榜学唐的人在学习、效法唐人的创作,即使没有标榜学习某种唐诗风格的人其实也没有脱离唐代创作的影响。
宋代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诗话”这种表达文学观念的文体。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广义的“诗话”可以包括各种各样关于诗歌的理论批评或其他言论,因而应当从钟嵘的《诗品》算起。但真正以“诗话”之名标目的著作只能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始。欧阳修自己在《六一诗话》中称,这本书是“集以资闲谈”的。钟嵘写作《诗品》的目的很清楚,既是给古今诗人一个定评,也是为时人的批评立一个标准,因而可以说是一部很严肃郑重的著作。《文镜秘府论》所摘引的那些《诗格》、《诗评》之类比起钟嵘的《诗品》来当然要显得自由随意一点,但同样有实在的目的,就是指导帮助诗歌创作。相形之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专门把围绕着诗歌的闲谈搜集整理成书,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即以闲谈的形式表达关于文学的见解,这就使得这本书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了。
那么,闲谈式的诗话于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究竟有何意义呢?我们试选几段看看:
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盖在水北,去河南府十余里。岁时朝拜官吏,常苦晨兴,而留守达官简贵,每朝罢,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
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如此耳。……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注: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264-266页。)
这几段都是典型的闲谈随笔文字,随意挥洒、涉笔成趣,却看不出有什么微言大义或实用的教诲。以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者们比较重视的是有理论价值的格言警句,而往往忽略了这类闲趣文字。上引第一段文字中虽然提到了几句歪诗,但意不在论诗,而是讲述有关的世情民俗,所以历来不入文学思想史研究者之眼。然而细细品味一下就可以领悟到,这些闲谈实际上涉及的是当时诗歌活动的一种文化氛围。“卖花担上看桃李”之句不仅描绘了当时京城官僚士大夫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揭示了有些文人诗歌创作背后的一种与现实生活疏远、隔膜的趣味基础。“正梦寐中行十里”云云则不只是写实,同时也是表现了一种富于机趣的通俗趣味。第二段文字通过蛮布弓衣上织绣的诗句说明了梅尧臣的名气、影响之大,同时也是在提示当时文学传播活动的一些特点。第三段谈论的是文学创作本身的事,但不是理论分析或阐释,仍然还是闲谈。这些关于一字阙文的议论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理解诗歌的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即对唐代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崇拜。总之,这种种闲谈和逸闻琐事构成了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创作、接受诗歌的语境。一首诗歌的意义其实就是由这种语境提供的。当欧阳修称他写《六一诗话》是为了“资闲谈”时,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使诗歌的意义、价值得以增殖的新的文学活动方式。
唐人的《诗格》、《诗评》、《诗式》之类论诗的著作,宽泛地说也可以称作“诗话”。但它们与宋代以《六一诗话》开头的讲话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唐人主要谈论的是如何作诗,而宋人的诗话则更多地关注起了如何读诗的问题。比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有这样几段:
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又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
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王平甫云:“庄宅牙人语也,解量四至。”吴僧《钱塘白塔院诗》曰:“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余谓分界堠子语也。(注:《历代诗话》上册,第303页。)
白居易的诗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常常被人们当做不用华丽字眼而自有富贵气象的精彩诗句,但陈师道在这里的评价却另出手眼。他并不是说这两句诗不好,而是用了一种不同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他注意到这两句诗所描绘的景象是从外部、从远处观察的印象,因而说这是“看人富贵者”的话。这里对诗句的评价是基于一种特殊的分析方式,不是对诗句本身的修辞、形象等方面进行分析,而是从作者在叙述时所处的视角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是一种精微的体验,表明分析者对诗歌的鉴赏、品味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显然,诗话虽属闲谈,表达的却是宋代文人对唐代以来文学艺术成就更进一步的认识。在这种欣赏品味的基础上,宋代逐渐形成了更自觉地学习典范的意识。宋人对前人诗文的分析评价或可商榷,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言论体现了宋人对文学典范学习的自觉意识和分析的深刻、细微程度。
宋代文学观念发展历程的最后一站应当说就是严羽的《沧浪诗话》。《沧浪诗话》与《六一诗话》以来许多诗话都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是一部“资闲谈”的随笔,而是像《诗品》那样专门研究诗歌理论问题的专著。严羽写作《沧浪诗话》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解决对宋代文学创作与观念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的问题。江西诗派学习唐代文学典范讲的是法,而严羽却认为唐诗的真正妙处恰恰在于没有可以捉摸的法则,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辨析作品风格家数的能力并非像他自诩的那样高明,因而今人郭绍虞反讥他“未遇盘根而利器已变成为钝器”。(注:《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到严羽对唐人尤其是李杜的态度所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他在《诗辨》中总结诗歌的艺术特征时说: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在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其中实际上包容了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文学观念。他所说的诗之九品是九种典范风格,也就是对文学典范艺术价值的认识;而他说的起结、句法和字眼这三种用工途径则体现了从规范或法则方面进行学习的要求。这些观点都与江西诗派重视诗法的观念关系十分密切。他所说的所谓诗的极致——入神,黄庭坚也曾提出:“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从这些方面来看,严羽虽然自称是取江西诗派心肝的刽子手,实际上还是受到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观念不少影响的。
那么,就上面所引的这些观点来看,严羽与江西诗派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说,就是“入神”二字。黄庭坚讲“钩深入神”,是说要有自己的独到深刻的见解而不为人后。但严羽的“入神”指的是诗歌创作中的最高艺术境界。显然,在严羽那里唐人尤其是李杜作为文学典范,具有了与江西诗派等人所学习的典范很不相同的意义。在黄庭坚看来,李杜(他主要欣赏的是杜甫)为后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学习范式和可供吸取的现成创作资源;而对于严羽而言,李杜所启示的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终极境界。他不像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等人那样去把李杜当做实用的典范去学习效法,而是将其变成了一种艺术境界、艺术理想来膜拜。
对于宋人来说,唐代文学无可置疑是至高的艺术典范。不同的文学流派,往往以唐代不同风格、流派的文学作品作为学习效法的典范。这固然说明唐代文学的伟大成就为宋代的文学典范观念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基础,但同时也说明宋人的典范意识还是一种与个人趣味直接相关的个人意识,还不足以形成刘勰所说的那种“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的普遍的典范标准。严羽所不满意的,正是这种只凭个人趣味出发学习效法、而没有高下之别的实用典范意识。他讲大小乘、讲第一义之悟,都是为了确立一种与实用典范意识不同的典范观念。《诗辨》中最为人们注意的说法之一是所谓“别材”、“别趣”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他提出这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别材别趣作为评价文学典范的标准,从而与黄庭坚等人所注重的有法可学的典范观念区别了开来。由这种别材别趣生发开,便产生了他所说的第一义之悟的内容——兴趣、气象、入神……,典范变成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
可以认为,宋人关于文学典范的观念到了严羽这里,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从形而下的、实用意义上的“诗法”即经验范式,转变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形而上的精神气象和境界。经典文学不再是具体的学习样板,而是升华为令人景仰、膜拜的精神境界。继严羽之后,在明代前后“七子”对盛唐诗歌的推崇中,在竟陵派对所谓古人“真精神”的奇特会心中,乃至清代王渔洋等人对唐诗神韵的精微体察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升华为精神境界甚至神秘偶像的古代文学典范。这表明,文学典范观念从“实”到“虚”的这种升华过程在后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中得到了继承,并形成了明清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影响巨大的古典主义思潮。
三、明清时期的文学典范意识
严羽的观点应当理解为宋代学习、崇拜文学经典的文学观念发展的逻辑结果。到了明清两代,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开始,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古典作品的问题。在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中,有一种日益走向深入细微的趋势。明初的方孝孺在《苏太史文集序》中谈到庄子、李白和苏轼的诗文时说:“庄周之著书,李白之歌诗,放荡纵恣,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彼其学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于神,故无所用其智巧,而举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苏子之文犹李白之诗也,皆至于神者也。”
方孝孺应当算是个道学先生,他在谈论文学时一般讲的不外乎经世致用之类的大道理。但他在谈及具体的古典作品时,口吻却变为批评家特有的深奥玄妙,谈论的是“默会于神”、“至于神”之类的话头,使我们不由得想到严羽的“入神”。方孝孺自己对古典文学的鉴赏力究竟如何是个问题,至少从他对文学的一般看法来说他不能算是道地的鉴赏家。因此他对庄子、李白和苏轼的艺术成就的评价,有几分真正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就不免显得可疑了。但正因为如此,才说明对古典文学审美特征的精微认识已不是个别人的特殊眼光和趣味。方孝孺的情况有点像严羽,他自己的创作才能与他对经典作品的认识似不相称。我们会发现,这种不相称在后来对经典文学的谈论和学习中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换句话说,经典作品将越来越变得高不可攀。
自明代中期起,以“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前七子尤其是李梦阳对古典文学的态度较拘泥于尺寸古法,似乎与我们所说的对古典作品审美特征认识的精微深细化趋势不大吻合。但他也知道,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依照他所说的古法制作成的,是气、色、味、香融为一体,“一挥而众善具”的浑然天成之作。这种看法同样表明对古典文学作品认识的深化。
明代文人对古典作品尤其是唐代诗文的精深解读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其典型代表就是晚明的竟陵派。他们认为一般人所学的古典作品还远不够深奥,只不过是“极肤极狭极熟者”。钟惺在《诗归序》中称,他们要求的是“古人真诗”:
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
他们对古典作品的理解的确是过于穿凿了一点,难怪钱谦益说他们“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70页。)事实上钟惺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所求之难及。他在《与高孩之观察》中说:“夫所谓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何以言之?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他在评价相传为伯牙所作的《水仙操》时,用一种击节入神的态度惊呼:“寂寞二字,微矣微矣!”似已到了言所不追、语固知止的入微境界。显然,这样一种境界使他不得不生出“心知诗中实有此境”而“下笔未能如此”的感喟来。对经典作品的接受便越来越从对前人创作的学习转向了静观性质的鉴赏。
对经典艺术作品的感受越来越细微,经典作品就变得越来越神圣高卓,其结果便是离创作学习的可能越来越远。这一发展趋势从明代影响到了清代。清代对经典作品感受最为精微的当数王渔洋。他的“神韵”说可以说是将严羽以来对唐诗等经典作品中不可言传的韵味的感受和研究推到了高峰。他论诗推崇的是“色相俱空”的冲淡境界,而且将这种境界的创造更进一步神秘化:“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注:王士祯:《诗友诗传录》,《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有人看到王渔洋自己的诗稿时发现,他本人作诗却不是那么伫兴而就的,倒是多有涂乙,显然是经过了反复斟酌修改。实际上不仅是要经过反复斟酌修改,他的许多神韵小诗几乎是从王、孟、韦、柳一路诗风中脱卸出来的。可以说在王渔洋那里,对经典作品的欣赏感受与学习创作之间的距离更加拉大了。
明清时期,文学经典在文学活动中的意义比过去更为突出,对经典作品创作规律和作品特征即文法的研究也发展到更深入的程度。明初高启在论诗法时提出的对诗歌进行艺术评价的标准是“格”、“意”、“趣”三个方面。(注:高启:《独庵集序》,《四部丛刊》本。)与唐代人喜欢谈论的“十七势”、“十四例”之类法式不同,其中没有什么实在具体的东西可供学习,毋宁说是一些具有较高概括性的观念范畴。“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这是把对诗歌艺术特征的分析区分成三个层次:“格”是形式的整体特征,可以说是评价作品的最直观层次,也是确定一个作品基本格调的层次;“意”是情感内蕴,是作品的内在意义层,也是一部作品感染、打动人的内在源泉;而“趣”则是作品中所透射出的作者的灵感和独创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特殊魅力。这三个层次的观念显示出高启对文学审美规律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层。
明中叶的谢榛谈论诗文时提到的概念是体、志、气、韵(注:谢榛:《四溟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41页。),与高启所说的格、意、趣有相似之处:“体”近于高启的“格”,“志”近于“意”,“气”与“韵”的准确含义当然不同于“趣”,但也是与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关。这里可以看出明人进行艺术作品的描述和分析思路的一个特点,是比前人更注重使用抽象概念进行较全面、宏观的概括。这种研究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清代叶燮的《原诗》对诗歌艺术特征进行的全面系统的概括与理论抽象。事实上,叶燮用理、事、情三方面来概括作品的意义,用才、胆、识、力四要素来概括诗人的主观条件,这样的分析研究思路与高启、谢榛等明人的分析论述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谢榛还谈到诗有四格,即兴、趣、意、理。他集中谈论的是诗歌作品的内在意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谈到了“趣”。关于诗要有“趣”的说法,或许可以从严羽所说的盛唐人论诗惟在“兴趣”这个说法中找到源头。严羽所说的“兴趣”究系何指是个问题,因为他说来说去,总归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别材”、“别趣”。我们只能设想他的“兴趣”是相对于宋人的读书穷理而言的审美意蕴,显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而对于明人来说,“趣”这个概念具有了特定时代文化所赋予的意义。从谢榛用以说明的例句“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来看,似应指尖新脱俗的意趣。主张性灵的公安派袁宏道关于“趣”的解释是童趣,这与推崇古典的谢榛所说的“趣”当然不同。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谈论传奇创作时主张重“机趣”。他在解释“机趣”时说:
阳明登坛讲学,反复辨说良知二字,一愚人讯之曰:“请问‘良知’这件东西,还是白的?还是黑的?”阳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点带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词,则离合悲欢,嘻笑怒骂,无一语不带机趣而止矣。(注:李渔:《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他在这里解释的趣或者说“机趣”,更近似于当代人所说的“脑筋急转弯”式的机智。这些对“趣”的理解和解释虽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出自个人天性、见出灵气才称得上有“趣”。当关于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涉及像“趣”这样的概念时,就不再能机械地靠对法式的研究和学习来解决问题了。
明人胡应麟说:“汉唐以后谈诗者,吾于宋严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献吉得一法字,皆千古词场大关键。第二者不可偏废,法而不悟,如小僧缚律;悟不由法,外道野狐耳。”(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他要求将“法”与“悟”结合起来,而“趣”正是需要通过“悟”才能把握的东西。叶燮则将胡应麟“法”与“悟”的区分变为“死法”与“活法”之分,而“活法”所论之理、事、情则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注:叶燮:《原诗》内篇,《清诗话》下册,第587页。)由于有了“法”与“悟”、“死法”与“活法”之别,对文学创作规律或法式的研究变得复杂了。明代另一学习古典的文学流派“唐宋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唐顺之曾用唱歌奏乐之法来说明文法的不同层次,他认为一般人可感知的法就是“气有湮而复畅,声有歇而复宣。阖之以助开,尾之以引首”这些基本规律。然而“最善为乐者”虽然也不离这些基本的法,却“使喉管声气融而为一,而莫可以窥”,成为无法之法。这才是明清人心目中文法的最高境界。(注: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荆川先生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那种“莫可以窥”的无法之法意味着对经典作品仅靠学习来把握是不够的,还得靠个人的灵感和悟性。这样一来,自唐宋以来对古典作品创作方法的学习就变成了对古典作品深层意蕴的神悟式释读。这表明,对古典作品意义的理解越来越向个人主观体验的方向发展。以主观体验甚至臆度的方式释读经典作品,这种风气直到明末仍不绝如缕。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以评点“六才子书”著名的怪才金圣叹。金圣叹批评《离骚》、唐诗、《水浒传》、《西厢记》乃至释讲佛经易理,多有出人意表的奇谈怪论。赞者称颂他的批评灵心妙舌、透发心花;批评者则认为他的观点牵强附会、怪诞不经。其实在金圣叹对古典作品的释读中,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着。他在《水浒传》中对许多人物性格的分析的确是独具只眼、妙笔生花;而他在《通宗易论》中硬把孔子与如来拉在一起,不能不说是生拉硬拽的奇谈怪论。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对古典作品的理解和解释都带有明显的个人体验色彩。个人体验的主观性使得他的批评的客观准确性无法得到保证,因而造成了精彩深刻的分析与牵强附会的误读并存的矛盾情形。
一般说来,清代文人的学风与文风比明人要严谨实在。清代的学者们对古典作品的释读和研究比起明代来更严谨科学,但并未因此而忽视了对作品审美意蕴的体验。清初学者王夫之研究诗歌艺术特征的方式,虽然看上去不像竟陵派或金圣叹对古典作品的释读那么主观偏激,但在重个人体验而不是普适的推理和客观标准方面却是一致的,以至于后人往往批评他的这种带有主观倾向的释读“不免堕入空虚一路”(注:王闿运:《湘绮楼说诗》,《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7页。)。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对《诗经》中诗句的解释,可看做这种体验式释读方式的出色例证。比如他在解释“周南”中的《芣苢》时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在解释《汉广》时说:“终篇忽叠泳江汉,觉烟水茫茫,浩渺无际,广不可泳,长更无方,唯有徘徊瞻望,长歌浩叹而已。”这两首诗不但篇幅短小,而且内容更简单,主要是一些重复的叠句而已。像这样的诗句如要从字面强解,那就不免会成为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种将“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解作“香蕉一,苹果二,大鸭梨一”的迂腐经生了。(注: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方玉润的解法如他自己所说,是平心静气的“涵咏”,也就是在想象中设身处地地体验。金圣叹在小说批评中把这种体验方式称作“动心”,是指作者在构思小说中生动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时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方玉润在释读古诗时也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正是这种设身处地“动心”的体验,使明清人对古典作品中审美意蕴的理解比宋人胶着于字义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对古典文学释读和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贯穿历史的艺术精神,一种始终活在一代代人心灵深处的审美需要。这种深藏在文学文本背后的活的精神,只能通过读者的个人体验来获得。它实际上是读者与仍然活在作品背后的作者之间的一种心灵沟通。这正是谭元春所说的古人“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的那种阅读境界。(注:谭元春:《诗归序》,《谭友夏合集》卷八,台湾伟文图书出版公司影印本。)随着这种体验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古典作品的价值不再仅仅是文学创作中学习、效法的样板和工具。对古典作品的欣赏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了。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所总结、提炼出来的传统文学审美范畴“意境”,可以说就是古典作品释读中体验意识发展成熟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境”理论的主要功用不是指导诗歌创作,而是对古典作品释读欣赏经验的总结,是对后来的一代代古典文学接受者提示的体验式阅读的门径。古典主义的文学思潮就这样逐步从创作转向了接受。
标签:诗歌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诗品论文; 新古典主义论文; 经学论文; 历代诗话论文; 沧浪诗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