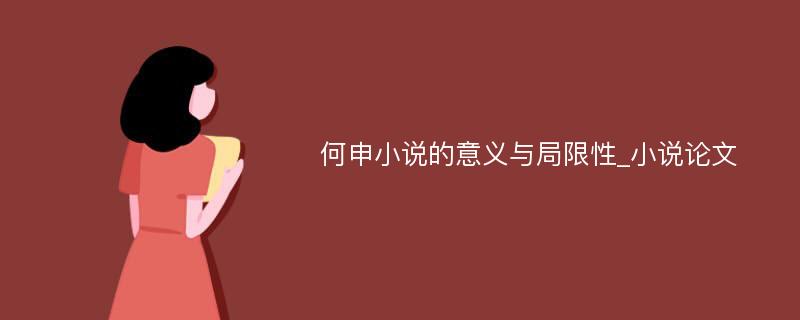
何申小说的意义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1-0113-07
一
读何申的小说,我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20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柳青说的一句话:“要 想创作,就先生活。”我想,何申对这句话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理解。何申不是那种凭 灵感、靠才气进行创作的作家,他之成为作家,不是根源于他有什么过人的天赋,而是 塞北山乡的生活打造使然。
与其他作家不同,何申虽然有过短暂的武侠小说写作经历,但是很快,他选择了一条 植根于生活的创作道路。他把生活作为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可靠根基和取之不尽的创作 源泉。他从事创作之前,就已经深深扎根于燕赵大地塞北山乡之中,积累了丰富的写作 素材:
十多年里,结合本职工作,每年去一些乡镇,我也就走个差不多了。于是,闭上眼睛 ,我就能想起哪个乡镇的大门朝哪开,大门里的房子是啥样,房子里的人这时节大概正 忙什么……当然,还能想起县城里、山村里、农户家里的人和事……
这无疑是我小说创作的源泉[1](P425)。
生活的确十分慷慨,生活燃烧了作家的创作热情,生活也成就了作家的创作技巧。所 以,拿起笔来的作家何申,总是念念不忘生活的厚爱:
我拿起笔来,心里就放不下我身边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也许我跟他们同喝这一地 方的水太久了,也许我注定要为他们的欢乐和痛苦而动心,现实就是这样,我已经写了 三十多部中篇(侦探小说除外),两部长篇,还有数十部电视连续剧,所有这些作品都没 有离开这块土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2]。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我们作家的基本功。练好基本功,写作才能根底硬、路数准、 思路宽、素材多、人物活,作品才能吸引人,才能解除闭门造车的苦恼。
深入生活不能蜻蜓点水,不能当局外人,而应该有一股真诚,要亲身去参与。
现实生活的人物是活灵活现各具特色的,为我们作家提供了最好的模特,如果我们不 用最佳的模特去绘画,画出来的人物就难免苍白无力[3]。
享受过生活馈赠的何申,又以生活的忠实记录者的身份参与到生活中来。他叙写生活 ,坚持了一条严格的写实风格,这里所说的“写实”,当然不是指机械地照搬生活,或 纯客观地记录生活。他以同情、欣赏和参与者的身份融入到他所熟悉的生活中。他把笔 触深入到当前我国农村最为基层的领域。写农村、写基层,是何申小说特殊性之所在。 所以特殊,是和当前文坛比较而言。我们不少作家热衷于写都市、白领、夜生活、婚外 恋、武打、凶杀等作家并不一定熟悉的生活,取材撞车、叙述雷同、远离尘嚣、不食烟 火、拉大了与生活的距离,制造了文学与生活的疏离,读者也因此而疏离了文学。何申 小说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创作倾向的矫正和抑制,它以自己的创作而不是宣言昭示作家 对当下生活的关注,在高度个体化的文学创作里,表达对生活应有的敏感与热情,也唤 起了人们对一度被淡忘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一古老命题的当代理解。因此, 何申小说在当今低迷的文坛里,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言说价值。
何申对基层生活的叙写,表现为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追求原生态的展示,把生活 的泥土气息和各色人等的真实情状不加掩饰,和盘托出。应该说,他追求的是鲁迅先生 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境界。其二,大量而集中。写基层生活并 不始于何申,但何申对基层生活的叙写大量而集中。何身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生活在村 、乡、县的最为基层的干部、农民(“热和系列”表明何申创作题材的拓展),这构成了 何申小说一个独特的风景,具有鲜明的取材个性。其三,超越了当下小说在塑造人物上 的理性负荷。他笔下的人物较少受作家理念的制约,作家面对人物,既不溢美,也不掩 恶,实现了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从俯瞰式视角向平视的视角的转变。何申小说里的人物 往往瑕瑜互见,美丑共存,高大的又是渺小的,崇高的也是平凡的。生存,是潜藏在何 申小说里的一个虽然朦胧却异常顽固的声音,制约着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因为 要生存,就有了县委书记傅桂英碍于亲情而向不正之风的认同、妥协(《七品县令和办 公室主任》),副县长郑德海看似智慧的化解矛盾的方式(《穷县》),和农民范老五面 对他从没有见过的金钱时有违常态的行为方式(《穷人》)。《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 作为一乡之长,在新年将至的腊月里,还为拿到小流域项目找县里的有关领导,虽说不 上殚精竭虑,却也一心为公,以至于在大年初一还想着那些吃不上饺子的民工而把自己 过年的饺子送到了医院。但他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也想在这个七家乡干上 个一两年再调回县城,为能调回县城也不得不送礼,走后门。小说这样写,增添了可信 性,避免了概念化。当有的作家随意挥写,任性地捏合人物,让人物成了作者某种观念 的传声筒时,何申小说里的人物以其鲜活的生命气息让读者感同身受,缩短了读者与小 说的距离。
有人说,何申的作品缺乏应有的道德判断,作者有意无意迁就了他笔下人物的缺陷, 甚至把缺陷当优点一样放大、展示。我不这样认为,小说不是道德说教,作者也不是全 能的上帝,作家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地跳出来,对他小说里的人物给予道德上的臧否。小 说有自己的叙述逻辑,作家在小说叙述面前有时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何申对他笔下人 物的处理,是服膺了生活的定性的。
二
何申小说具有强烈的认知价值。他的对于基层农村生活的叙写,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我 们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感悟。现在有人耻于谈论文学的认知价值,认为文学的认知 价值与高尚的审美活动相对立。这个看法并不能成立。文学的认知价值是优秀文学作品 的重要属性,读者在享受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审美愉悦的同时,也能获得对生活直观的认 识。排斥文学作品的认知价值,是否定文学作品之于人生多方面的可能与启示。当然, 文学的认知价值有自己的特点,它不是道德的说教,也不是抽象的演绎,而是融入在小 说里的人物形象、故事情景里的。何申小说认知价值的主调是,他以形象的方式展示了 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复杂多样、千姿百态的现实景观。既展现了现实的惰性像无形 的绳索对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束缚,也写出了这些人在艰难抑郁的生存环境里顽强地伸 展理想的热情与豪迈。《穷县》一开头,就突出了穷县青远县年末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青远县常务副县长郑德海本想住进医院避开年末难关一段时间,却因县里的主要领导赶 巧都不在家——县委米书记在县里屁股没有坐热就随团到国外访问去了,县长傅桂英本 想上个项目为县里办点好事却又被人家骗走了50万,没法在县里呆下去了,眼下到区里 为自己男的和孩子联系工作和学校去了,管政法的苗书记回老家忙丧事去了,文教书记 到地委党校学习去了,宣传部长又因车祸导致脑震荡正在家里休息……。呆在床上的郑 德海就坐不住了,不得不去主持全面工作。面临的却又是令人尴尬的局面:企业不景气 ,财政空虚,老干部因工资晚发、医疗费报销不了要上街游行,倒闭厂的职工成天到县 委大院请愿请求给碗粥喝,申报贫困县的工作还要开展……。小说着力写出了穷县面对 困境时的无奈、困惑和挣扎,也写出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郑德海面对种种复杂 的人际关系练就的既老练沉稳、雷厉风行,又狡黠圆滑的性格特征。《县委宣传部》以 地区文明办来县里检查工作为缘由,把一个县委宣传部所遭遇的种种尴尬给揭示出来。 袜子厂女工因没有领到工资而到地区行署上访,整个县税收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包书 记整治封建迷信活动竟被打破了头,县文明办主任收到在海外打工的女儿寄来的一万元 钱,竟以为女儿在外卖身而受刺激因而卧病。小说对人物所置身的艰难滞重的生存环境 以及人物在这种环境中所生成的狭隘、卑微、乃至变态的性格特征,也有着很好地揭示 。
何申不是那种廉价的感伤式的作家,他对他笔下的人物在同情、了解的基础上,也写 出了存在于这些人物身上的某些愚昧、落后与偏见。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历史惰性和封闭 的保守的地缘文化对人的牵制,急于脱贫致富奔小康、享受物质文明过程中所滋生的新 的问题,再一次把教育农民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中篇小说《良辰吉日》写调到城关镇任 书记的李德林在农历八月十五这个良辰吉日里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堪称转型期困扰 中国农村发展的种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真实写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但富裕起来的农民又面临着新的困惑,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富裕以后该怎么办。与 此同时,由于天灾人祸,一部分人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何申以敏锐的知觉,艺术地揭示 了当前农村由贫富分化而在人物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新的问题。《穷人》里的故事似乎有 点荒诞,农民范老五,面对从天而降的两万块钱捐款,竟然不知如何是好,出了一系列 洋相。接受捐款的仪式上,当村长在背后捅他一下,提醒他说些感谢的话时,小说是这 样写的:
范老五把钱往紧抱:“说啥?”
村长又捅他一下:“感谢的话。”
范老五低头瞅瞅钱:“那话咋说来着?”
村长又捅他一下:“使劲想。”
范老五被捅疼了,扭头说:“想就想呗,瞎鸡巴捅啥呀!捅折了腰我咋干活?”
全场人都笑了,这一笑倒把范老五的紧张劲儿松下去了不少,脸上的肌肉能动了,于 是便有了笑脸,嘴唇子吧哒两下,好像要说点题上的话了,他这一动,摄像机照相机话 筒也都动起来,不成想范老五吧哒完嘴又没反应了,眼珠子又直勾勾地瞅着远处他家住 的那条沟。
读到这里,每一个读者是会忍俊不禁的,在这笑声里,掺杂着酸楚和苦涩。就像人们 读《阿Q正传》,在笑声里包含着眼泪。当女记者问范老五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起了什么 作用时,憨厚得近于愚昧的范老五竟然这样回答:“我的作用当然很重要,这仨崽子都 是我做出来的。”生存的压力,生活的磨难,把一个善良的农民从外观到心理严重扭曲 了。读到这里,读者对农民的命运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何申小说的认知价值还体现在,他以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身份,写出了他笔下的 人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里顽强地伸展理想的热情与豪迈,这使何申作品增添了若干温馨 与亮色。这在长篇小说《多彩的乡村》有非常鲜明的表现。《多彩的乡村》堪称中国20 世纪90年代北方农村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作为新形势下成长起来的有觉悟、有能力、 有远见、有点子的主人公三将村村长赵国强,踏实务实、锐意进取,不畏权势,不谋私 利,敢于打破传统陋习,冲破重重阻力,带领三将村村民摆脱困境,初步实现了小康目 标。从赵国强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新人新面貌。
三
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叙事是对生活经验的组织,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该是一个叙 事的高手。何申小说的叙事,坚持了忠实于生活这一基本原则。他不像某些先锋作家那 样,执意切断与生活的联系,在对语言的偏执中建立起叙事的迷宫,以此来颠覆读者的 经验,制造文学与读者的疏离。何申心里始终装着读者,更关心转型期我国农村的现实 问题。在他看来,小说哪怕能给人们“提供点素材”,或帮助人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 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人情世故或其他什么有意思的事”,或“为农民群众办点好事,也 为农村工作出点主意”,也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了。所以,何申 写小说,并不精心构筑叙事的逻辑,“完全是放下文章的腔来说话”,追求一种本色、 自然、贴近民众的叙述效果。为此,何申小说主要采取了全知的视角,以顺时序的叙述 结构展开故事,故事跟着叙述走,叙述跟着生活走,实现了叙述与生活的合一。现代小 说叙事理论把叙事分为全聚焦模式、内聚焦模式和外聚焦模式三种。在第一种模式里, 叙述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他的人物的身份处境,既 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活动空间非常之大。第二种模式又称为“人物视点式”,叙述者 与叙述对象叠合,叙述者借对象的意识、感官展现特定时空中人物的心理及其所折射的 人和事;第三种模式叙述者对于故事的掌握达到最低限度,叙述者隐身,以此达到减少 叙述干预的目的。三种叙事模式各有特点,不宜笼统抑此扬彼或扬此抑彼。何申小说叙 事主要采用第一种模式。他很少采用第一人称介入的主观型叙事模式,也不采用隐藏叙 述行为的第三种叙述模式,而是采用全聚焦客观性的叙述方式。如《穷县》,从青远县 常务副县长郑德海年末面对的一系列头疼事写起,在时间的延宕中,逐一展开对人物所 置身的生活空间及其人际关系的叙写。《村民组长》讲述的也是农民奔小康的故事。先 从村民组长黄禄想着手解决村里几件事入手,作者以全聚焦客观性叙述的方式,真实记 录了黄禄对这些事件解决的方式,也深入到内心,写出了黄禄遭遇一系列问题、事件时 的所思所想。这种全聚焦客观性的叙述方式,帮助作者在有限的篇幅里迅速聚拢矛盾, 展开故事,又使小说包含较大的生活容量。当然,这种叙述方式作者用得多了,也会带 来新的问题:一是叙事雷同,缺少变化,久而久之,形成模式,会制约作者的创新。二 是有可能使故事松散,不利于情节推进和对人物的性格刻画。
何申小说叙事的另一个特点是富有画面感的场景作为叙事要素进入小说文本。画面本 来是造型艺术的叙事要素,造型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区别,在于造型艺术诉诸视觉,具有 强烈的直观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的审美需要,因此造型艺术是 最具有大众化的一种艺术形式。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特性决定了小说不提供可视 的、定向的画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不具备唤起画面感的美学效果。因为小说语言 唤起人的想像,读者在想像中可以浮现出相关的画面。何申善于用语言创造富有画面感 的场景,从而使他笔下的生活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可以说,富有画面感场景的营造是 何申实现其写作意图的基本叙事策略。何申小说的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性格都 是在这种画面感的营造中展现出来的。我们看《多彩的乡村》,这是一部在何申创造道 路上具有关键意义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再一次显示了何申对塞北农村的熟悉,和营造 富有画面感的场景的能力。小说第一章,写儿女、女婿为六十六岁的德顺老汉过生日, 把要出场的人物一一推出。这一章的描写,画面感极强,小说借人物的身份、语言、动 作构置生活场景,推动画面运动,展开故事情节。德顺老汉的朴实倔强,大儿子、副县 长国民的文弱善良,二儿子三将村村主任,小说的主角国强纯朴厚道,大女婿、身为乡 长的孙国权的风风火火、直来直去,二女婿、三将村最有名的冒尖户钱满天的狡黠圆滑 ,以及三女婿孙二柱身上所特有的农民习气,都具有一种给人以宛若在眼前的视觉性效 果。这一章可以说是一幅多姿多彩、富有动感的塞北农村生日宴图。小说通过这张生日 宴图,联系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为在广阔的背景里伸展这张生日宴图奠定了基调, 显示了作者在写作长篇小说时清醒的构思意识。而这,恰恰是以往何申小说最缺乏的。
《多彩的乡村》叙事开合自如,抑扬有度,不同时空富有画面感的场景在叙事链条上 的组接,构成了小说既轻松舒缓又紧张跌宕的节奏,从而使叙述具有饱满的张力。钱家 大院的争吵,洪水发作后三将村被淹的景象,社教运动来临以后围绕钱家财产,赵国强 与社教组长、也是他的嫂子的黄小凤的正面交锋,为见到电力局长,高秀红挺身而出, 勇拖轿车的场面,钱满天高息存储引发的三将村村民骚乱,赵国强面对李光田父子对高 秀红施暴时的挺身而出,以及德顺老汉面对金聚海等人企图推倒大棚强行征地霸道行径 时以生命之躯的抗争,都是极具画面感和冲突性的场景。这些叙事单元对小说的审美意 义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以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叙事的单一 、平淡,产生了节奏。有了节奏,也就有了小说的生命和元气。其三,也是更为重要的 ,是实现了小说叙事的视觉转换,打通了接受者的心理通路,消除了读者阅读上的障碍 ,缩短了小说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获得愉悦性的美感。可以说, 何申小说的大众化,通俗化,可以为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所接受这一审美旨趣的实现, 与作者的这种叙事策略是分不开的。
何申小说的叙述也在不断地丰富。早期的作品叙述单一,缺乏节奏,基本上是叙述者 在讲故事,后来手法就灵活多了,不仅有叙述者的叙述,也增添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对话 、景物描写。如景物描写,这是以往何申小说较为缺乏的,但在长篇小说《多彩的乡村 》里,景物描写为小说增添了灵动的氤氲,成为烘托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一笔。我们看 :
夜色很美,一轮圆月高高悬着,融融的月光透过脱去叶子的枝丫,尽情地涂抹在静静 的路上。爆竹不时的从什么地方响一下两下,很响,偶尔还有带哨音的花窜上天空,叭 的一下炸开,闪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满满的向下滑动,照亮了一片天空。
这段描写,诗意极浓,对于烘托赵国强与高秀红俩人在特定环境里的心境,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这种描写,在何申以往小说里是很难见到的。恰到好处的景物描写,是何申 小说突破被有些评论家称为“太实、太滞”的局限应努力的方面。
四
何申小说的不足:缺乏对材料的精细组织和审美感悟,给人的印象是作者较多对实在 生活场景的展示而缺少对意蕴世界的发现。也许作者过于依赖生活的馈赠、过于相信生 活本身的力量,以至于作者没有清醒的选材意识,缺乏与生活的必要的距离,把小说等 同与生活了。当我们通读了何申小说以后,一个难以驱遣的认识,是小说的文化底蕴不 够。小说的文化底蕴当然不是作者人为赋予的,作家不能为了文化底蕴而牺牲现象的丰 富性。何申小说无疑具有浓郁的塞北山乡气息,他的小说是从一个侧面了解改革开放以 来农村生活的缩影,具有不可替代的“这一个”的特点。但是,读完何申小说以后掩卷 沉思,我们发现小说除了留给我们几个回味起来还算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外,就再也发现 不了更多的东西了。仿佛在一个嘈杂、热闹的集市上走了一遭,看见了各色人等,当时 挺兴奋、挺开心,但过去之后很快就成了过眼烟云,没有太深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与 作者缺乏对生活的审美开掘、对材料的精细组织有关系。
何申的有些小说还有编造重复的毛病。如《年前年后》写到了李德林趁于小梅不在家 到县医院做生育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李德林那些东西里没几个能存活,作者通过这一笔 写于小梅与马大肚的不正当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笔,有助于情节的发展和对人物尴尬 处境的揭示。但是,在《乡镇干部》里,作者又写到了原二道河小马乡长为达到与妻子 离婚的目的,一块到县医院检查,结果倒查出了小马乡长有问题,离婚目的没有达到。 而在长篇小说《多彩的乡村》里,孙二柱为要小子,非让县医院把媳妇那结了扎的输卵 管给接上,闹出许多笑话。三篇(部)小说,虽说叙述内容不尽相同,但读过这些小说的 人,是不难感受到作者大体相似的故事框架和较少变换的叙述策略的。这不能不说是小 说的大忌。说明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断地超越自己,该是多么困难的事。
何申小说的语言富有塞北山乡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和他笔下的生活一样浑璞 、粗糙却又鲜活、生动。但是,从文学语言特殊的美感效果角度看,何申小说的语言仍 然有太实、太浅,缺少个性化的毛病。如人物语言,在《多彩的乡村》中几个晒太阳的 老头与冯三仙的对话就让人觉得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像是一群小青年在跟冯三仙逗嘴, 哪像农村里的老者在说话?
一次座谈会上,何申曾经谈到河北省作家的一个特点:写实,不搞形而上和追求形式 。这个概括也许准确,但是,在这种概括里我却感觉到某种对作家来说也许是致命的东 西。即小说精神性的匮乏和艺术形式的粗糙。精神性是小说的灵魂,小说缺乏穿透心灵 的力量,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审美品位。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既具有诉诸人的感觉经验 的实在层次,又具有诉诸心灵经验的心意层次,不仅如此,它还具有超出人的感觉阈限 ,蕴涵着普遍的人生精义的超验层次。小说的本质不能不是形而上的。形而上在这里不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要求,是一个小说家超出“在场”应有的智慧。而 这,恰恰是我省许多作家不具备、在骨子里也强烈拒斥的(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也许 铁凝和阿宁是个例外)。因为“不搞形而上”,所以小说往往拉不开与生活的距离,而 停留在浅表的层次上,给人以太实、太滞,缺少意蕴的印象。
台湾作家李昂曾经谈到过大陆作家形式感的薄弱和作品形式的粗糙问题。我认为这是 异常尖锐却十分切中要害的批评。形式的粗糙在何申的小说里是有一定的表现的。他自 己曾说:“像我这样业余写作的,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文学中的较深的内容,只 是肚子里有不少老杂事,写出来哪怕是给人们提供点素材,终归也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另一篇谈创作经验的文章里,作者也谈到了为了保持生活的新鲜感,往往顾不上沉淀 就写出来了。抱着这样的态度写小说,形式上的粗糙也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当前许 多作家潜意识里依然奉行内容在先,形式在后,内容决定形式,题材决定小说价值的观 点。在认识文学性或评价文学作品时,往往极力张扬文学作品所选题材的支配性价值, 忽视甚至根本忽视小说之为小说的特殊性。我认为,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中,形式绝不是 可有可无的工具,在一定意义上说,形式是文学艺术的本体,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是 审美形式的创造;文学艺术的价值,也主要是其审美形式的价值。这绝不是什么形式主 义,因为在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中,形式与内容是如此互为整体,难以割裂!用黑格尔 的话来说,即“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 形式是文学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物化形态,是文学作品意蕴的承担者,作家创造了一种形 式,也就发明了一种心灵的语言。凭着这形式,作家的精神性存在成为永恒。可见,无 论是从哪个角度说,讲求形式是对文学特殊性的尊重;不讲求形式,是降低了对文学的 要求。
何申小说的上述缺陷,与作者的文学观念有一定联系。在作者看来,小说是生活的一 种补充,是认识生活的形式,与生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他自己曾说:“像我这样业 余写作的,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文学中的较深的内容,只是肚子里有不少老杂事 ,写出来哪怕是给人们提供点素材,终归也是件有益的工作。”在另一篇谈创作体会的 文章里,何申说得更明白:“当人们通过我的小说对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人情世故或其 他什么有意思的事了解得更深入细致了,那这些作品或多或少也能算经受了一点历史的 考验吧。”[4]显然,在何申的创作理念里,小说与生活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小说 如果能帮助人更深入细致地了解“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人情世故”,“为农民群众办点 好事,也为农村工作出点主意”[5],也就算达到了目的。这显然是降低了对文学的要 求。
但是,作家也许并不太清楚,小说的意义不在于近距离地关照生活,回答并试图解决 生活里提出的问题(如帮助农村工作做点什么等)。小说是对存在的追问,在对存在追问 的同时达到对生存经验的启示和敞亮。从生活到创作,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植过程,而是 一个充满主体性的创造过程,包含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诗意的眷注和理性的透视。小说 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新的书写,可能性构成了小说的价值指归。米兰·昆德拉谈到小说的 功能时曾经说,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只有当您割断了与您的生活相连 的脐带,并开始探寻生活本身而不是您自己的生活时,小说才能真正地充分发展”[6]( P82)。重温米兰·昆德拉的这段话,对作家的创作是有启示的。也许何申对他所置身的 生活太熟悉、太有感情了,以至于作者反而不能有效地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导致创作对 生活过分依赖,而睿智的洞见和深刻的发现不够;何申笔下的小说是鲜活的、本色的、 毛茸茸的,但又是不够深刻、缺乏心灵的震撼力的。他做到了对他所熟悉的生活素材的 组织和文字传译,却较少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的创造性的转换。何申以一个 基层文化工作者的道德良心、社会关怀,与他所不能忘怀的山乡共脉动,从而为这块贫 瘠而又富饶的土地唱出了深情的颂歌。但是,作为小说家的何申,我们有理由对其提出 更高的期待,而作家自己在经历了一段写作的过程以后,也应该对自己的创作有所反思 。毕竟,小说还是要当作小说来对待。
五
这些年,以何申、谈歌、关仁山为代表的河北省的“三驾马车”,曾引起文学界的热 烈的讨论。这是河北文学界的骄傲,因为不论是来自赞扬还是来自批评,甚至来自热烈 的赞扬和猛烈的批评,都有助于文坛对河北省创作的关注,有助于不同文学价值观的碰 撞、交流和渗透。
在众多的关于“三驾马车”的评论中,我以为郑法清的概括是有代表性的:
他们似乎在不约而同地闯荡着一条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创作的新路。他们很看重生活 ,绝不把自己关在四角的天地里去主观臆造和随意组合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故事; 他们很关心时代,从不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去搞那些无谓的自我情绪的宣泄;他们心中 不忘人民,笔下所写,全是老百姓关心的人和事,字里行间流动着老百姓的思想和感情 ;他们很有社会责任感,敢于直面人生,大胆触及矛盾,对于真善美的事物,他们热情 讴歌,对于假恶丑的东西,他们无情鞭挞,并在讴歌与鞭挞之中呼唤人类灵魂的净化、 精神的升华与新时期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在当前有些人热衷于情爱性爱的渲染 ,迷恋文字游戏,甚至以隐私或秘闻去换取钞票的时候,他们选择这样一条积极的、向 上的现实主义创造道路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7]。
郑法清的这段话,我以为既代表了从肯定的角度评价“三驾马车”的多数人的意见, 也点明了对“三驾马车”肯定性评价的历史契机和现实根源。正由于强烈的关注现实和 当下的品格,唤回了人们对一度被淡忘了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一古老命题的 当代理解,给久违的文坛注入了一些清新的气息,“三驾马车”才被认为是文学中的现 实主义“新浪潮”、“冲击波”。而“肤浅的现实主义”、“泡沫的现实主义”等评价 也同时出现。面对同一文学现象,何以会产生如此相反的评价呢?我以为,个中原因根 源于文学观念的差异。在不同价值立场和知识背景的理论家、批评家那里,对现实主义 的理解并不相同。有人强调文学关注现实、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 有人强调文学家的主体力量,强调作家关照生活时应有的批判精神、人道精神和超越精 神。我以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其实,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向任何一极的 倾斜都可能带来文学的失重。文学粘滞于生活,依附于生活,必然导致文学精神的匮乏 ;而切断文学与生活的联系,使文学远离尘嚣,不食烟火,也会导致文学功能的弱化, 和文学价值的衰退。在生活与文学、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之间,在历史的 定性与终极指向之间,文学应该以自己可能的形式使之保持一个饱满的张力。从这个角 度看“三驾马车”,我们在肯定其关注当下、贴近现实、反映现实和分享艰难的正确的 创作道路和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有理由对“三驾马车”提出一个根植于对文学特 殊性理解的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我们的作家可以而且应当具有超越了单纯同情和欣赏 之上的理性审视的眼光,应有的人文关切和忧患情怀,以及基于小说家这一社会角色而 锻就的文学的道德感与责任心。在文学史的长河里,衡鉴一个作家、一部文学作品的艺 术成就,绝不是看文学家选择了什么样的题材,提出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作家对社会 人生负怎样的责任,以及责任的高低贵贱,轻重大小并不依照他所选取的题材来划分。 怎样的组织他生活,怎样讲述他的故事,怎样拥有他面对存在而昭示的生存智慧,这一 切无疑是对一个小说家最为迫切的追问。在这里,我想起了河北省作家铁凝在中挪文学 研讨会上的发言,与何申君共勉:
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责任,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着理解 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 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还有同情 心、良知、希冀以及警觉的批判精神——[8](P230)
在这段谈论文学家责任感的文字里,我们不是分明感受到文学家承担责任、分享艰难 的特殊性与可能的方式吗?
收稿日期:2001-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