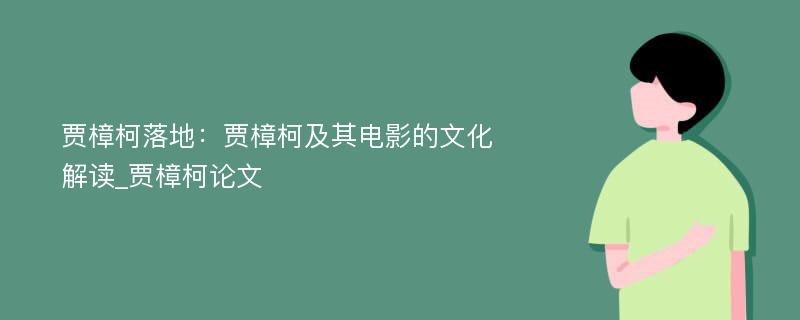
走出地下的贾樟柯——对贾樟柯及其电影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下论文,文化论文,电影论文,贾樟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贾樟柯,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文化 结构中,他本身具有着文化精英的身份。但是,从1995年开始贾樟柯就在现有的国家电 影体制之外从事独立电影生产,这种边缘状态又使他具有着艺术先锋性。而当贾樟柯及 其电影频繁地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时,大众传媒在第一时间内将他加工成为消费文 化的时尚新鲜元素,使贾樟柯和他的电影成为一枚新的小资标签。2004年,中国电影改 革,贾樟柯获得了正式的导演身份,并于同年成为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正式回归文化主 流。如果将贾樟柯的经历看作一个文化事件,对它的解读将使我们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去 探讨中国电影的发展。
一
周宪在《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化是一个共时多元并存的结构 :即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元并立的结构。比较来说,主导文化是一个重要 的文化力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一种体制的文化,或政治文化对审美文化的制约。精 英文化相比之下是一种弱势文化,但它仍具有一定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先锋性;而大众文 化则与西方大众文化有更多的表面相似点[1]。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化的扩张,西方与 东方文化的对抗与同化在日益加剧。可以说,贾樟柯及其电影始终处于这种中国当代文 化三元结构和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重重交织中。
贾樟柯的电影无论是拍摄方式、拍摄手法还是拍摄内容、拍摄理念,都对传统学院式 、体制化的电影构成了冲击。早期作品《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 是用电视摄像机拍摄的,成本低,拍摄自由度、随意性强,与利用专业摄影机拍摄电影 的导演相比,他更像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他的电影人物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边缘人 (打工青年、小偷、少年抢劫犯……),他们痛苦、困惑、矛盾、无奈,与主流电影从正 面建构现代化的光明历程不同,贾樟柯的电影更多从阴暗面描述了这一历程中的社会个 体心灵与精神的痛苦转变;他的演员大都是非职业演员,没有技艺娴熟的演技派,也没 有光鲜亮丽的偶像派。他以纪实手法再现着平民的生命状态和生活轨迹,以一种近乎是 原生态的影像颠覆着传统戏剧性的电影表达方式。而更为突出的是,贾樟柯以他自我表 现的、个人化的小叙事,拆解着主流电影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宏大叙事。可以说, 从一开始,贾樟柯和他的电影就被中国当代主导文化边缘化了,无法在体制内获得一个 合法的身份和名称。因此,只能以独立电影、地下电影等诸如此类词语对其加以命名。
除了“独立电影人”,“文化先锋”也是一个贾樟柯无法摆脱的身份。“先锋”是与 现代性紧密相关的西方概念,“这一概念明显的军事内涵,恰好指明了先锋派得自于较 广义现代性意识的某些态度与倾向——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遵从主义的颂扬,勇往直 前的探索,以及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对于时间与内在性必然战胜传统的确信不疑,(这些 传统试图成为永恒、不可更改和先验地确定了的东西)”。[2]“先锋派是或者说应该是 有意识地走在时代前面。这种意识不仅给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加上了一种使命感,而且赋 予他们以领导者的特权与责任。成为先锋派的一员就是成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尽管 与以往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不同,这个精英阶层投身于一个完全反精英主义的纲领, 它的终极乌托邦目标是所有人民平等地享受生活的所有福利”。[3]以上是西方学者对 “先锋”作的说明,但是它并不能完全用于对贾樟柯“文化先锋”的解释,因为在这个 概念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曾被称为“先锋”而如今成为精英文化代表的第五代电影人的影 子。虽然不同的时代赋予了两代电影人共同的先锋称号,但其“先锋”的意义与最终走 向却完全不同。
第五代电影人早期的作品是具有鲜明的先锋性的,大胆地进行艺术实验,追求与传统 不同的艺术观念,具有“忧患意识”和“终极关怀”,但他们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 对启蒙、民族、反思、历史等现代性宏大叙事进行重新书写,因此他们以文化领导者自 居,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并不能“投身于一个完全反精英主义的纲领”。之后,第五代 电影人尝试了许多市场化、商业化的拍摄,先锋性有所减弱,但都因为不能摆脱这种精 英意识而无法完全被大众所接受。与此相比,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人具有更彻底 的先锋性,他们以自己的电影实践反叛第五代类似父权的电影表达方式,他们无意政治 的反抗、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个人化地书写着平民的生存状态,虽然他们都是精英阶 层的一员(贾樟柯等大都接受过正规电影学院的教育),但却有着反精英的意识,其最终 目标也是对普通人生命与体验的尊重。也许,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更应被称为“后先锋” 。正因为有了贾樟柯等人,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鸿沟有了被填平的可能 。
贾樟柯的电影在中国的电影学院及电影圈内放映,并不受欢迎,他的《小山回家》甚 至曾被认为是“粗糙”之作,这也许是他对当代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反叛造成的。那 么,这是否意味着他是大众文化的代表呢?
二
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探 索科学、民主、现代性是这一时代的文化主题。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意识 的增强,物质的极大丰富,使人们在看到了现代化辉煌成果的同时,也在个体精神与心 灵上经历着痛苦的蜕变。成长在这个时期的贾樟柯及其第六代电影人,他们身上同时纠 缠着两种不同的艺术观:先锋与平民。先锋的思想气质使贾樟柯等非常不适应已有的电 影体制与传统,不喜欢主旋律式的歌颂或批评,反对精英式的启蒙与反思,他们主张个 人自由的话语权力,关注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而正是因此更具有了大众性的潜质。
贾樟柯及其电影潜在的大众性与他的先锋性一样复杂,具有着与西方所定义的“大众 文化”既相似又不同的涵义。“大众文化”是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与市场经济的 兴起、大众传播媒介的繁荣紧密相关。但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意义有两种不同的解 释:一种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麻痹、消磨大众意志,盲目消费,追求快感,抹 杀个性,推广平庸。一种是伯明翰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为民众的,具有颠覆即定霸权秩 序的能力。贾樟柯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采访时说,大众文化是影响他重要的 东西,在上高中的时候他一直看录像,尤其是那时非常火爆的港片,不断接触到现代流 行文化:喇叭裤、烫发、邓丽君的歌曲等等,这些后来都成为他电影中的主要影像。19 98年,贾樟柯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的文章,将 DV电影的概念引入中国,而此时DV这种现代科技的产物正开始在中国市场上热销。不久 ,他第一部利用这种数字技术拍摄的电影《任逍遥》入选戛纳电影节。一时之间,DV影 像在大众中间迅速流行,在人们看来原本神秘、复杂的电影拍摄过程变得简单、自由。 可以说是贾樟柯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对于电影不太专业的人,通过看片,不断地 DV实践,不用进入电影学院,不通过体制,依靠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进入神圣的电影王国 。于是贾樟柯以他的小影像颠覆着固有大影像的权威,使大众可以分享到那曾牢牢掌握 在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手中的话语权,他的“DV精神”鼓舞了一批批的热血青年。可见 ,后一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在贾樟柯的身上具有明显的表现。
然而,大众文化还具有一个特点,“假如文化商品或文本不包含人们可从中创造出关 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的他们自己的意义的资源的话,它们就会被拒绝,从而在市场 上失败。它们也就不会被广为接受”。[4]也许是因为贾樟柯以一种先锋的方式表达他 的平民关怀,大众只热衷于他的那种DV拍摄而舍弃掉了那些“看不懂”的平民史诗,于 是,大众文化将贾樟柯式DV拍摄的先锋性彻底抹平,使它变成了展示大众心情故事的娱 乐方式。
在“大众文化”中常常有一群“领跑者”,在西方主要指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 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崇尚特立独行,追求享受,但却沉浸在自己的 精神与物质世界中,是消费文化的代表。在中国,与之相对应的是白领阶层,更流行的 称呼是“小资”,他们是时尚的制造和传播者,其身上具有更多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 那种大众文化特征。“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 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5]这样 的结果就是:“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自己的死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阔 抵消了它的独特性”。[6]因此,“小资”们喜欢贾樟柯,因为他的先锋性是区别一般 、平庸的新鲜元素。于是,诸如《城市画报》、《新周刊》、“e龙网”这些以打造新 新人类、小资生活为宗旨的大众传媒纷纷把焦点对准了贾樟柯,而看他的电影也就成了 证明“小资”文化生活品位的一枚光鲜亮丽的标签。就这样,大众传媒与“小资”合谋 把贾樟柯由电影导演变成了一个概念和符号。这样的“大众文化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 步展开,在相当意义上是一个消费社会原则和世俗享乐主义扩张的过程,日常生活的意 识形态的胜利,使得主导文化的崇高和精英文化的规范都失去了以往所具有的震撼力量 。”[7]在中国,“小资”阶层以下还包含更多生活在底层的普通民众,但是由于这些 人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更无法对先锋式地展现他们生活、心灵、精神状态的贾樟柯电影 产生共鸣。
可以说,贾樟柯及其电影的先锋性与平民性,尴尬地处在中国特有的主导文化、精英 文化和大众文化中间。中国在现代性进程当中所形成的复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 化结构使贾樟柯及其电影被不同的文化不同程度地吸收、利用、改造、排斥,但无论如 何,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力量他是应该被我们的时代加以肯定的。
三
贾樟柯的电影很少在国内公映,在市场上即使有盗版光碟,数量和品种也很有限,对 于这样一个国内罕见作品的电影人,他是如何被大众所认识的呢?
当贾樟柯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时候,对于许多外国人却是再熟悉不过 了,他和他的电影频繁地出现在一个个国际影展上,获得了多个令中国电影人非常羡慕 甚至愤怒的国际称赞与大奖。于是,大众传媒将获奖的“喜讯”不断传到国内,国人震 惊了,开始认识了这个传奇般的贾樟柯。这样,一个不被国家体制承认的独立电影人, 依靠在国际电影节上的辉煌赢得了自己生存的权利。
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电影希望走向世界得到国际的认可,更准确地说是西 方的认可,而“获奖”则是认可的最好标志。但西方一直以自己的文化标准与尺度来衡 量着中国电影,这种后殖民主义文化造成的残酷事实就是:文化身份认同的错乱。当中 国电影逐渐走向世界的时候,却丧失了自己本土的话语权利。“‘声音’表明其拥有自 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他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 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8]这样,我 们只能以“沉默的他者”(福柯语)身份来认同西方的标准,当人家说“这部电影是好的 ”以后,我们纷纷随声附和,自己不再有清醒的判断。而贾樟柯的电影之所以频频在国 外获奖,是他地下拍片的行为与小叙事、个人化的电影表达方式在西方看来是一种反抗 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志,其影片中反映的小人物的生命状态则是展现了“‘东方’褪去了 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成为一位‘灰姑娘’”[9]后的空虚、失落、痛苦的色 彩。这对于贾樟柯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被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所利用。而他的最初理想 是想逃出各种意识形态的控制,进行属于个人的自由表达。然而,有一件事是可以令贾 樟柯感到的欣慰的,那就是他身上的那张获奖清单使他具有了一定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 本,帮助他得到了中国导演的合法身份,从今以后“可以从容地拍电影了”(贾樟柯语) 。
“资本是一种权利形式……个人能够积累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也就是说, 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生活可能性或机遇……”[10]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态:经 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并且资本可以转换。专业院校的学习经历是贾樟柯的文 化资本,由此获得的精英身份是他的社会资本,但是此时的资本还很有限,并且他从事 的独立电影生产不能被资本起作用而依赖的场(这里指现有的电影体制)所接受,无法获 得充足合法的权利。但是,贾樟柯的电影不断地得到国际赞誉和大奖,如1997年《小武 》获得第四十八届柏林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2000年《站台》作为唯一一部华语电影 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并于2001年被《电影手册》评为世界十大影片;《任逍遥》参加了 戛纳电影节正式竞赛片,而这些电影节则以坚持艺术的原则而闻名世界,具有着鲜明的 精英主义立场和权威的评判标准,尽管商业前景与市场影响远远不如好莱坞、奥斯卡, 但也正因此显出“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就这样,文化资本积累带来的社会资本的增加 使贾樟柯得到了成正比的利润:不仅获得了大众崇拜的掌声和喝彩,更是得到了国家体 制的认可,合法导演的身份与中戏教师的头衔使他完全走出了地下,接下来就是获得投 资(经济资本)拍摄首部地上电影《世界》。也许我们无法预测这部电影的票房如何,但 贾樟柯毕竟向市场迈入了第一步。
对于来到“地上”的贾樟柯,有人担心他能否保持独立的艺术先锋性不向市场妥协, 有人则认为,如果《世界》仍坚持前三部作品的风格则不可能真正进入主流电影市场— —大众,这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上:电影是为艺术还是为大众。但我 们实际看到的是,先锋与平民、西方与本土、艺术与市场这些看似矛盾的因素,总是同 时在贾樟柯的身上悖论式地存在着。也许,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恢复电影的本来面目 :电影就是电影,它是一种公共文化,既属于中国,也属于西方;既属于公众,也属于 个人。因此,不要再把重大的文化责任强加到每一部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身上,这样我 们就会平心静气地看待那些西方的奖项与评价,冷静地思考中国电影的发展;我们的电 影人也不要以艺术的神圣来排斥大众手中选票,因为没有人可以声称电影是他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