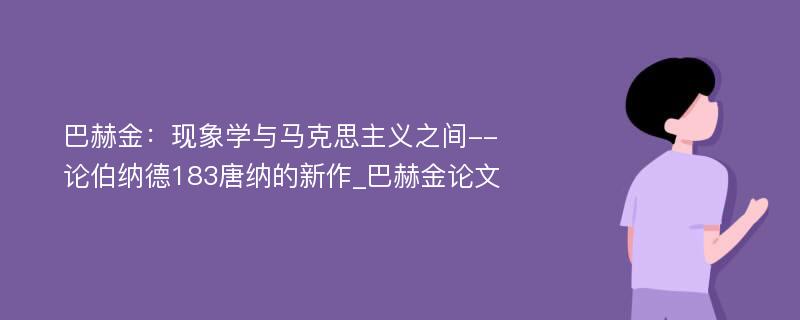
巴赫金: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评伯纳德#183;唐纳尔斯的新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现象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作论文,尔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赫金自60年代在西方被“发现”以来,引起了哲学家、思想家、文论家、语言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由于其思想的深邃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其著作中学科涵盖的广泛性,巴赫金被各家目为同道知己。释家蜂起,各具识见。其中荦荦大者有“对话的巴赫金”(托多罗夫),[①]小说理论家的巴赫金(莫逊与爱默逊),[②]“马克思主义的巴赫金”(希培德与海希考普等),[③]“建筑术的巴赫金”(卡拉克与霍奎斯特)[④]等等。但我们立即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学者们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巴赫金的思想最终归于一个统一的名称之下,尽管这种努力或多或少地总是在对“对话理论”的探究下进行。
然而“兼容”工作总显得捉襟见肘。正如卡拉克和霍奎斯特所承认的那样,“由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较为完整的形象永远无法转化为一个单一的、确定的巴赫金。事实上,试图一劳永逸地描绘出轮廓分明的‘真正’的巴赫金形象将会全然不顾他的全部主张,这样一种威严的造型可能具有专横的意味”。[⑤]
美国学者迈克尔·伯纳德·唐纳尔斯无意做一个“专横的造型者”。针对各种想把巴赫金合而为一的努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努力必然失败。原因有二:一是在巴氏著作里贯穿了两种主导思想,它们泾渭分明,却又各行其道;二是巴氏本人从来就未能也未曾打算将它们融为一体。这两种思想主流就是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巴赫金就穿行于这两种哲学思想之间。[⑥]
伯纳德·唐纳尔斯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巴赫金研究新作《巴赫金: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中。该书于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分七个部分:形式主义的问题;新康德哲学与巴赫金的现象学观;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寻找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本;科学与意识形态;科学、实践与变易;巴赫金知识问题与文学研究。这七个部分可归结为对三个大的方面的论述:一、巴赫金的现象学观;二、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观;三、建立巴赫金范式的“唯物主义修辞学”(materialist rhetoric)的可能性。
伯纳德·唐纳尔斯认为巴赫金理论中的这种二元现象,在他与俄国形式主义的论争中表现得很清楚,在其日后的理论发展中也一直清晰可辩。他的现象学观大体源自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后又经胡塞尔等人发展了的新康德哲学;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则强调了语言的解放性。[⑦]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对象上是不同的。现象学研究人类个体认识客体的方法,研究个体怎样对艺术作品作审美判断及个体意识的结构和性质;马克思主义则研究人的社会构成以及意识形态在这些构成中的作用。根据现象学的观点,巴赫金提出人的主体是在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中定义的,他要探索在语言创作中这种关系被表现出来的方法,他要发现语言符号怎样被内在化(interiorized),且最后又怎样在主体的相互关系中被重新使用。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表现在他对含有意义与价值的社会话语的特点与形成的求索之中,在于对语言和符号怎样产生了主体的知识(knowledge)及其知识的社会构成的研究之中。
一、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伯纳德·唐纳尔斯认为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他与形式主义的论争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他提出,巴赫金一方面赞成形式主义者将文艺学引回被忽视了的文本上来,将文学研究中的话语研究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又批评了形式主义只重视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技巧,而忽略了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材料建构了这种文学性的问题。在批评的基础上,巴赫金主张在文学研究中突出意识形态的丰富性和深度,把它作为意义的理据凸现出来。当然,文艺学不是社会学或政治学,它应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但这个对象的确立不应将它与其它对象的联系割裂开来,否则就成了难以理喻的东西。巴赫金一贯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它以语言建构,而语言是包围并创造了人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赫金否认形式主义者提出的“诗歌语言”的存在,认为诗歌语言仅仅是普通语言的一个方面。对诗歌进行语言方面的研究也只是研究诗歌的方法之一。无论从哪一方面研究诗歌都不能离开它产生与接受时的具体社会话语环境,正如杰姆逊所言,文艺批判要“永远的历史化”。[⑧]而形式主义的失误正在于此:它将审美客体与所有其它话语分割开来,仅囿于对客体作语言分析,而不把它放在社会话语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文学研究的历史方法讨论具体的社会环境怎样在作品形成的独特时空里建构了作品,使它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要历史性地了解语言,除了对写作具体语篇的人进行分析外,还必须对语篇产生的独特时空进行分析,这种社会评价使语篇的实践存在及其语义现实化。它超越了词、语法形式、句子及所有的抽象的语言确定性,它限定对这些语言要素的选择,也限定了对形式和内容的联系的选择。巴赫金认为,尽管可以用各种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但彻底的审美分析是少不了这种社会批评的。伯纳德·唐纳尔斯引用巴赫金的话说,如果社会批评能对那些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能决定话语及其形式的直接变化的东西加以研究,那就更深入更富有成效了。[⑨]
伯纳德·唐纳尔斯注意到了巴赫金对言语(utterance)和日常语言的区别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在巴赫金的著作中,言语与日常语言不同,它已成了被社会赋予了意义与价值的语言符号。因此,文学创作就不是简单的对语言形式的选择,而是对意义与价值的判断、选择、组合。所谓诗歌中的“陌生化”现象只是诗歌内涵中某些社会评价的互抗成份在起作用。在《小说话语的史前史》一书中,巴赫金指出,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农民、皇族、商人—每个群体都使用着具有相同词汇、词法、句法等的相同语言材料,但与“民族语言”都有着不同的关系。在《文艺学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中,巴赫金接着说:“同一词的不同语调在每个群体之中差异极大,在同一语法结构中,语义与文体组合也大相径庭,当话语成为一个具体的社会行为的时候,同一个词占有截然不同的层位。”[⑩]既如此,重要的不在于语言的性质,而在于它的社会功用。
形式主义者潜心于“诗歌语言”,忽视了诗歌语言与广泛、复杂的社会语言的紧密联系,忽视了它只是这种超美学语言(extra-aesthetic language)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事实,因而成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巴赫金的矢下之的。
伯纳德·唐纳尔斯总结巴赫金的“首要规则”为:所有语言都只是意识形态材料的一部分,人凭借这些材料对世界作出决断。文学语言既有别于“日常”语言,同时又受其影响。这就为文艺学家们怎样走近文学指明了一条道路。(11]
二、巴赫金的现象学观探索
伯纳德·唐纳尔斯认为巴赫金的现象学倾向亦在同形式主义的交锋中显露出来。他引《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和《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等说明巴赫金在试图阐明物质内容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时着重研究的却都是单个主体如何对审美客体进行审美观照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考察物质环境怎样决定了社会交往,从而对美学语言进行研究。巴赫金在批评形式主义对语言性质和审美客体的结构概念模糊时,提出要建立一种“艺术语言创作的美学”。(12]
巴赫金认为美学创作就是艺术家将各种材料—不仅是语言—进行组织以指向某种意向的活动。(13]他以雕塑家塑造雕像的活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雕塑家使用材料进行工作,这种材料也许是大理石。但使塑像成为审美物的重要因素不在于其材料是大理石,也不在于雕塑家和审视者如何对雕像有了认知,重要的是:
雕成的像从美学上说是人与他的躯体的有效形式:创作意向和审视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而艺术家和审视者与作为一尊确定的躯体的大理石之间的关系则只是次要的、衍生的。它受某种客观价值的首要关系支配—在这里,它受活生生的人的价值关系支配。(14]
大理石人形是“外在作品”,而审美客体则是材料与指向作品的意向活动的总和。
伯纳德·唐纳尔斯又引巴赫金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文指出该文是巴氏最具有“现象学”倾向的文本之一。在该文中,巴赫金认为是人的认知活动将艺术内外的审美活动统一起来。(15]
巴氏把人的审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认知层次,这里的认知,是指在先科学思维的概念里找出早已组织好的实在。换句话说,就是在不考虑对象与其他人的价值关系,也不考虑由于认识了对象的组织而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去发现对象,也就是找出胡塞尔所谓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那些对所有人的认知都适用的概念。其次是伦理层次,包括对某些事件或对象作出认知理解的反应后而可能采取的行为的范围。最后是审美层次。这一层次使认知理解与伦理行为达到完美的实现。巴赫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审美活动,就是通过将已被认知和评价的现实转换到另一价值层次,使它从属于一个新的整体并在其中重新定位,从而使这个认知与伦理的统一体获得形式的活动。这一活动使现实个性化、具体化。但这个完成的审美形式却正是指向先前的认知与评价的。[(16]
巴赫金还认为形式主义缺乏一种普通美学理论,造成了对“内容”定义的混乱,使描写“对象的材料”(如新闻报道的语言)和“对象的内容”(如作品描写的现实,人们可借此获得认知,它不是语言符号的直接重合)的区分变得困难。他还区分了“内容”与“审美对象”。“内容”不带有观察者或作者的审美完成活动,能脱离审美对象而被谈论,因为它不带观察者或作者的价值判断。内容可被释义,而审美对象则不能;与此相同,意识形态的材料能被释义,被分析,而审美对象则不能。(17]
伯纳德·唐纳尔斯指出巴赫金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证了各种语言的相互作用,并揭示了出现在语言及其它意识形态的材料中的各种困难与矛盾(《小说话语》,《小说话语的史前史》,《陀氏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等);另一方面他又以现象学的方法讨论了建构成话语的单个主体间的关系(《艺术与应答性》,《语言类型》等)。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材料形成了人,这一思想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现象学”著作里都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主体—不管是作为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实体—的实际物质生存环境与语言的这一功能相脱离。巴赫金在《内容问题》一文中不惜篇幅论证了人的脑力活动是如何使日常活动审美化的;在《作者与主人公》中又论及人类主体是如何通过对语言的内在化继而又对其重新使用而建立起来的。但伯纳德·唐纳尔斯指出,对我们这个社会化的,有形的宇宙作出“应答与描写”是与以物质方式改变它根本不同的一种活动。尽管巴氏指出了形式主义混淆内容和材料的问题(既文本的意识形态材料和作品的语言),他在总体上也没有很好地区分语言和意识形态材料,犯了与形式主义同样的错误。(18]
伯纳德·唐纳尔斯的观点是:语言的内在化和语言的对话化交谈能改变人的认知,但这种改变并不能自动导致已经改变了认知的主体改变其生存的物质环境。比如,一个穷学生能与“贫穷”这个字眼进行对话,却不能使他的贫困处境通过对话而得到改变。
巴赫金与形式主义的遭遇使他处于二难境况。他一方面要建立一种语言哲学,这种哲学将提出言语不与语言形式的审美对象相脱离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又得提出一种方法,能对这种对象的审美特性与人的认知能力联系起来加以研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方法论使他处于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之间。(19]
三、“唯物主义修辞学”:关于知识的获得
伯纳德·唐纳尔斯指出,一方面,巴赫金肯定超语言事件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对能否超语言地建立对这些事件的知识表示怀疑。我们赖以认识世界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又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建立起关于物质生产力的科学知识?科学被看成是主体获得关于物质存在的知识的方法。但由于主体只能通过语言进入物质世界,那么我们又岂能在获得知识时避免意识形态的成份渗入其中呢?巴赫金认为这种渗入不可避免。因为我们虽然可以使语言对话以辨认出它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者说它的“先前的生命”,但这并不能使我们看出语言的意识形态的羁绊从而摆脱它。
超语言现象是存在的一历史的力量,经济的运作,行星的运动,地球引力,热力等等都是。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客观上是怎样运行的,除非我们凭借语言。比如我们知道有树在某处的森林里静静地倒下,这个事实除非我们亲眼所见或与人交谈了解到,否则是无从知道的。而交谈是语言行为。(20]巴赫金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得来自对客观事件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了某一事件,并且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去认知的,这一切都发生在语言的层次上。这个知识不能逃离我们在有关语言中的定位。因为我们不用这种独特的方法去认识事物,也总会有别种符号关系会将我们拉入到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我们总是用某一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去认知,纯客观性是没有的。总结巴赫金的上述思想,唐纳尔斯认为巴赫金的观点是:语言包含了真正的社会世界。
巴氏语言理论中的现象学的一面表明,要进入语言的物质环境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环境就隐藏在语言之中。闭口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避开这个难题的一种方法,但最终它会将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转为由此而产生的可能的知识所具有的价值问题。
唐纳尔斯认为巴氏的唯物论是最能产生可行的语言理论的,但这种唯物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现象学起点。因为正是这个起点提出了两种认识:肯定的(必然的)和可能的(或然的)知识。现象学认为可能的知识只能通过阐释学获得,肯定的知识则通过科学获得。这个模式的两个领域并不相容:科学家研究科学,读者研究阐释。唯物论的观点则认为这两个领域并行不悖。事实上,二者都提供了进入同一世界的途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媒介:科学家通过可重复的过程检验可观察得到的材料,而阐释学则在独特的环境下检验可能的信息。伯纳德·唐纳尔斯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摇摆于唯物论与现象学之间。
关于巴赫金的言语(utterance)理论,伯纳德·唐纳尔斯指出对它的研究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即语言层面和历史层面。因为在言语的社会结构里,确实存在独立于思想的事实(reality),但我们从中获得的知识并不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知识的获得通过语言的中介。巴赫金说:“文学分析是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一个分支,它同科学一样运作。”(21]然而,科学地分析非语言现象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些方法起着修辞作用,因为他们总是蕴藏于意识形态的结构之中。科学知识只是近似性的,我们只能设法不断完善对某种已知现象的描述。“修辞的”或中介的知识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但它又明显地受由物质和语言构成的环境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对言语本身进行语言的及历史内容的分析。
鉴于巴赫金处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事实,伯纳德·唐纳尔斯指出,那些想以现象学或马克思主义来组织概括巴赫金思想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将巴赫金的著作对话化也不可避免地扬此抑彼,不符合巴赫金思想的实际。了解巴赫金著作中的这种两重性,能使我们认识到他的著作何以充满了矛盾、张力和魅力,从而不去试图将他的著作一统化,而是将注意力转到如何更好地吸收其精髓,利用它提出的新视角对语言、文学以及使用语言的人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新的问题,探索新的答案。这是伯纳德·唐纳尔斯这部新作的贡献之一吧。
注释:
①See Tzvetan Todorov,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al Principlc(Minne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②See Gary Saul Morson & Caryl Emerson,Mikhail Bakhtin:Creation of aProsaics(California:Stanford UP 1990).
Morson和Emerson的“prosaics”一词有二层含义。第一层泛指文学理论,尤指小说理论,故不采用“诗学”(poetics)一词,而用“prosaics”代之;第二层则远远超出文学理论的意义,而指一种思维形式,它强调日常的、一般的、平凡的事物的重要性。Morson与Emerson认为巴赫金的著作中这二层意义俱在。在第一层意义里,巴赫金有其独特的创造;在第二层意义上,他师法了列夫·托尔斯泰和维特根思担等(见该书16页)。
③See Kcn Hirschkop,"Bakhtin,Discourse and Democracy",in New Left Review 160.6(1986).Also see Bakhtin and Cultural Theory.ed.Ken Hirschkop and David Shepherd(Manchester:Manchester UP,1989).
④See Katerina Clark and Michael Holquist,Mikhail Bakhtin(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1984).
⑤Clark/Holquist,op.cit.p.10.
⑥Michale Bernard-Donals,Mikhail Bakhtin: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Cambridge UP,xii-xiii).
⑦M.Bernard-Donals,op.cit.pp.1-3.
⑧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 HH UP.1981),pp.9.
⑨M.Bakhtin,Dialogic Imagination,ed.Michael Holquist,trans.Caryl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U of Texas P,1981)p.7.
⑩(21)M.Bakhtin M/P.N.Medvedev,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Scholarship,trans.Albert J.Wehrle(Cambridge:Harvard UP.1985),p.123,p.3.
(11)Michael Bernard-Donals,Bakhtin: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Cambridge UP.),p.11,
(12)See M.Bakhtin,Art and Answerability.ed.Michael Holquist.trans,Vadim Liapunov(Austin:U of Texas P.1990).
(13)(15)(17)(18)(19)(20)M.Bernard-Donals,op.cit.p.12,p.14,p.15,p.16,p.17,p.165.
(14)(16)同(12),p.265,pp.275-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