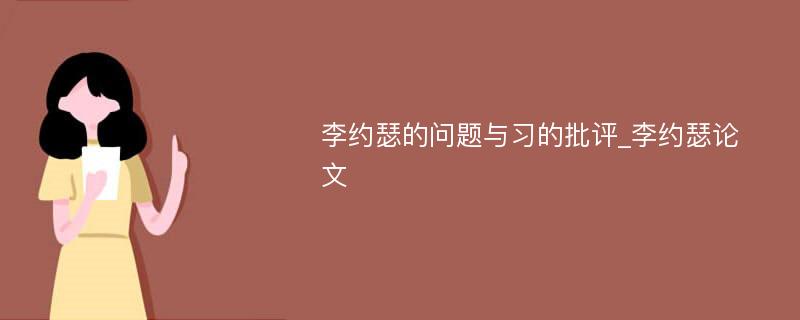
李约瑟问题和席文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时,提出两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为先进技术起步而将自然假说数学化的现代科学只在伽利略的时候崛起于西方?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应用自然知识于人类需要方面大大领先于西方?席文对李约瑟的两个问题做过分析,他指出,第二个问题中的自然知识不是第一个问题中的科学,不能在逻辑上引发第一个问题。他说:“中国(过去)有各种‘科学’;却并没有科学。”有些人只看了席文这后半句就连篇累牍地反驳,但是所举出的事例仍然摆脱不了席文前半句“科学”的窠臼。这些“科学”不能像在欧洲那样形成哲学整合,从而导致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发生科学革命。席文提出,现代科学在发展时留下的欧洲烙印太强,不能认为科学革命在全球别处均有可能。李约瑟也很早(至迟1956年,即提出第二个问题之前14年)就说出了中国古代“尽管有这些成就也未能使中国科学达到伽利略、哈维和牛顿的水平”(注: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此后简称SCC),Vol.11,P.496,J.Needham。)这样的话,并且对其原因有所探讨。在研究原因时他对中国思维方式的不同、传统经验技术与纯客观科学的区别、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与现代科学不可分割的关系,虽均有提及,但予以淡化,这就使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引起了席文的批评,在中国更引发了所谓“李约瑟难题”这个无事生非的误会。实际上,这三种因素对于解答他的上述论断很有裨益,下面试做一说明。
(一)中国思维从生命出发,追求道德内省,即牟宗三教授所说的intensional mentality,儒、道、佛三家都离不了这个范围;而西方思维从自然出发,追求对自然的客观分析认识,即cxtensional mentality,基督教义更是除上帝外都一问到底。太注重内省道德思维出不了外延思维的民主政治和科学(注:已故港、台牟宗三教授1983年在《中国哲学十九讲》第二讲第42页上说:“中国文化以前两三千年在intensional truth这方面表现得多,……extensional truth出不来,……所以从五四以来一直着重这个问题。……如果你有extensional mentality,那么科学才能生根。假如我们没有extensional mentality,那么科学永远进不来,民主政治也永远进不来。学科学还容易点,学民主政治就更难了。”据说李约瑟晚年承认,对某些关键性思想意识因素他未遑研究,而这些思想政治因素可能导致了中国在科学技术成就上赶不上西方国家(George Basalla,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P.175,Reprinted 199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李约瑟可能指的是中国欠缺extensional mentality。)。席文指出西方思维总问Is it true?而中国终极关怀的是Is if morally improving?
(二)中国传说远祖无不是工匠,《考工记》说技术是“圣人所为”。这在古文明中是突出的,它可以解释李约瑟的第二个问题。但技术始于打造石器,本与圣人无关,后来在儒家重视生命的思路下,认为民众没有安定生活则无法治国,于是技术便被赋予了强烈的价值取向,与价值中立的纯客观“爱知”自然知识有原则区别。中国古代技术也就在这种价值取向(即李约瑟所说的应用自然知识于人类需要)的驱动下获得了高度发展。这种发展与科学的推动无关。科学推动技术的重大影响始自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注:G.Basalla,Ibid.p.28)李约瑟没有澄清两者的区别(注:SCC各卷涉及的例子大半是中国传统的empirical技术成就,尽管李约瑟在该书Voll.11,P.29上在引用了胡适一段话后说"There was no room for science,therefore,only technology,And in these passages Hsun Tzu,though exhibiting Legalistleanings,crystalised the position of all subsequent Confucians";更明显的例子是李约瑟在“世纪科学的演进”这篇文章图1中(《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P.213)画出中国于公元800年左右“科学”水平比欧洲高,但他举出的例子却是机械钟等技术。),也没有指出中国古代凡是重大技术进展都是中央政权强大的结果,而价值取向淡薄的科学都成就于政权分裂的先泰(甲骨天象记录)、魏晋(刘徽)、宋元时代(四大数学家),或由个别视科学功名如敝屣的人(李时珍、徐霞客、朱载堉)特立独行取得。
(三)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以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为先导,伴随新大陆航线的开通和海上贸易,使新兴资产阶级起非常革命的作用,建立超越国界有法律保障的技术性格,即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材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和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这些“技术性格”使与李约瑟合作研究资本主义的黄仁宇认为,如能排除资本主义的掠夺侵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正性,则对20世纪某些地区而言它还是现代化的同义词(注: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PP.31,33,270,311,493。)),这令欧洲国家国力大增,许多大学设立从数学上分析自然的新课程,注重实验方法,建立研究院。科学知识的大量普及更为先进技术奠定了基础。它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P.29-32。)近年来休莫克勒(J.Schmookler)通过大量调查数据说明,推动科学发明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市场购买力。他的说法当然也还存在问题,(注:见George Basalla Ibid,P.113。虽然在同书P.115上Basalla也说到市场购买需要并不能完全解释科学发现为什么有规律地连续出现,但是他忽略了科学价值中立,况且现代技术改革往往是跨国、跨学科多项科学发现共同促成,当然不能有规律地回应市场需求。)但他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
李约瑟既然在第一个问题中将现代科学限定为“为先进技术而对自然所作的数学假设”,又认为欧洲科学在科学革命后明显地超越了中国科学,然而他对资本主义与科学革命密不可分的关系避而不谈(尽管他很早就强调了中国重视水利农业集权的官僚主义与欧洲沿海城邦重商背景的不同(注:SCC,Vol.11,P,338。)),加上他一再强调科学的“世界范围起源律”(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科学技术史通论》P.20,《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就予人假象他可能在对第二个问题的叙述中找到现代科学。事实上他找到的都是否定的意见(注:例如在SCC Vol.11,P.130说到科学与民主不可分的关系,P.496说从来没有达伽利略、哈维和牛顿的水平,P.543说这种(中国的)科学只能停止在纯经验的水平上,P.576说没有文艺复兴来把中国科学从经验的昏睡中唤醒等,都说明中国发展不出现代科学。),提到否定意见时又零碎低调,就难怪有些未能仔细阅读他著作的人(如牟宗三)产生了误会,指责说:“尽管英国那个李约瑟写了那么一大套书讲中国科学,可是它究竟并没有发展成现代的科学。”(注:牟宗三同书PP.14、42。牟的指责对李约瑟不公平,那不是李约瑟写作三十几大册SCC的原意。李约瑟从来无意写出中国可能在16、17世纪独立发展出Cartesian-Newtonian现代科学来,而是想表明中国传统的科学对现代科学的影响。并且说明以中国的聪明才智,完全可能发展出适合辩证有机思想的另一种先进科学来(SCC Vol.11,P.583)。席文指出,如果李约瑟第一个问题是明知故问的“启发式(heuristic)”问题,那也只在一开始时有用,陷入过深会含混不清。对李约瑟猜想中国可能会发展的另一种先进科学的说法,本文作者认为历史有辩证必然性,不能归纳设想另有可能道路。既然欧洲在16、17世纪资本主义和科学革命时发展出了Cartesian-Newtonian科学,就无法绕过它走另一条道路,只能充分掌握发展它,我们再也不能像李约瑟所说的“让垂死的原始科学理论死揪住未死的道德哲学不放”,SCC Vol.11,P.279。)
风物长宜放眼量。李约瑟的“世界范围起源律”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和今后可持续的发展上可以说是心胸博大的,譬如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对欧洲文艺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天人合一”学说更是今后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但是这条“百川汇海”的规律不能单独混淆到近几百年现代科学的发展上。16、17世纪爆发的科学革命既然发源于西方希腊的“爱知”自然哲学,与欧洲整个经济、社会和哲学翻天覆地的革命密不可分,那就不能撇开质变,将其与革命前受到过的empirical东方技术影响相混淆,而只能干脆承认科学革命的爆发地是欧洲,现代科学领先的地区是西方。
李约瑟渊博的生物胚胎和化学知识对待有些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确独具慧眼,不仅能从1909年A.Windaus制备类固醇性激素的皂化、升华工序联想到中国公元前2世纪就造出了秋石(注:《中世纪对性激素的认识》,《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PP.1052-1053。),而且预见到21世纪科学上主要是生物科学世纪,可能最现代的“欧洲”科学有负于古代中国有机自然观者良多(注:SCC,Vol.11,P,505。)。但是历史证明牛顿的机械宇宙观是绕不过去的。中国人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补这一课。李约瑟也指出没有打下牛顿的基础就瞎捉摸爱因斯坦世界观是不行的,沿这种跨越式道路发展不了科学(注:SCC,Vol.11,P,543。)。
反观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类似欧洲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缺乏数学假设和实验,缺乏分析和哲学整合的零星自然知识,大都人文价值取向极强,是被李约瑟归属为“文明”的经验技术。虽然有些客观知识如甲骨星象纪录,还有些做了大量实验及数学计算(注:1993年,我在京都会议之隙问席文,明代朱载堉在乐律上做了那么多实验,计算结果达百余页,算不算科学?他愣了一下,说这不一样。我想他指的那是个别杰出的成就,影响不大,没有从统一的哲学思想出发形成风气引发科学革命。周昌忠《西洋科学方法论史》PP.359-361也谈到现代科学发现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反对现有收敛思维、对之形成发散思维张力的结果。),但谈不上可证伪的理论,更未能推动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因此直到1922年,梁启超旅欧回国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科盲”,他因而大声疾呼(注:任公的原话是:“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了,太窄了。且不说那些鄙厌科学的人都把它看作器用、末技,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的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呼吁的实际是:没有“德先生”,就谈不上“赛先生”。(注:李约瑟注意到民主与科学的关系,在注11(SCC Vol.11,P.130)谈到过。)
收稿日期:2001-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