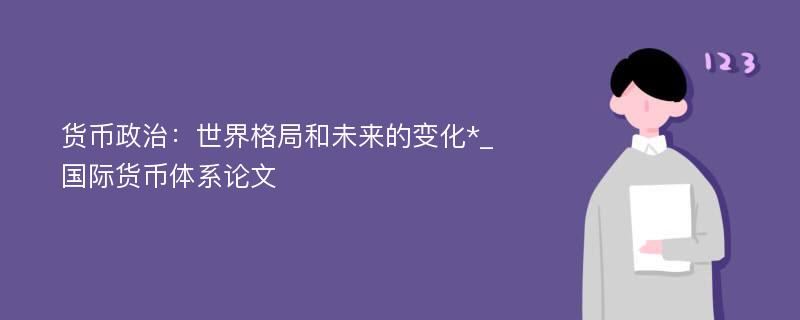
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格局论文,政治论文,未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4-0010-15
地理历来是“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因而人们习惯于以地缘的视角观察和解释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然而,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世界格局的演变突破了原有的地缘框架,出现了一些足以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因素,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币缘和币缘政治。币缘原本是指货币与人们生产、交换及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全球体系出现以前,各经济体在空间上相对分隔,建立在一国或区域货币基础上的货币关系,本质上是国家内部或区域内部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全球体系的基础,币缘就成为了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而币缘政治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币缘政治是币缘的核心,是左右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杆。用币缘政治的框架去诠释历史和现实,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变化的先兆。
一 货币本位:世界体系的基础
现实承续着历史,要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必须对现代世界体系演进成型的过程有所了解。据世界体系理论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看法,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存在着许多的帝国,彼此间亦存在着长距离的贸易,但作为第一个具有政治、经济、文明三个层面的历史体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则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①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认可“世界体系”的概念,却对沃勒斯坦等人所持的“欧洲中心论”抱着完全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正起源是白银资本以亚洲为轴心的全球大规模流动。在弗兰克看来,在1400-1800年的全球发展中,货币扮演着重要角色。周游世界各地的货币以中国和印度为轴心推动着世界转动,不断大量供应着血液,润滑着全球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② 经济史家们估计,从1493年到1800年在殖民统治下的300多年时间里,美洲生产了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70%的黄金,在这些总量超过13.7万吨的白银中,有超过6万吨运往了中国。③ 贡德·弗兰克进一步分析道,以白银为主的贵金属流向东方,说明存在着商品的反向流动。欧洲通过在美洲开采的白银,保持了与亚洲主要国家间规模巨大的交换活动,得以进入当时由亚洲主导的世界体系。④
其实,中国货币体制中并无近代西方的本位货币概念,早期是“谷帛为币”,继而是铜铁铸钱。低价金属铸钱能方便应对日常琐细而频繁的劳动交换,适宜作为小规模交换的商品经济的工具。⑤ 而金银等贵金属则是当做价值尺度、赏赐之物,一般不流通。⑥ 在唐朝和宋朝,白银在与西域的交流中偶尔显露出世界货币的职能。⑦ 到明朝正嘉时期以后,特别是万历年实行“一条鞭法”后,银可以折租税、计粮价、折俸钞,因而获得了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⑧ 可见,中国经济从明朝开始出现的货币化趋势,对白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作为贵金属,白银比铜铁价值高,比金数量要多,便于运输而更具经济性;同时银也比大明宝钞之类信用货币更加可靠,因而最适宜进行高价值、长距离、大规模的跨国商品交换。从“漫长的16世纪”开始,在亚洲、欧洲、美洲之间以白银为媒介展开了大规模贸易,这导致了以白银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⑨ 依托着白银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葡萄牙和西班牙换取了香料和殖民财富,荷兰人拥有了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和银行,而英国从西印度积累的资本促进了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支持蒸汽机和纺织技术。⑩ 同时,这些资本还资助了欧洲国家间的大大小小的战争,(11) 从政治上推进着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资本主义核心区控制边缘地带的金字塔式的国际秩序。可以说,正是白银资本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商品大交换,积累起仰赖于世界贸易的商业资本,进而催生了导致工业革命的产业资本和现代科技体系,方才导致了欧洲的后来居上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
从币缘政治的角度观察历史,我们更容易发现,世界体系的建立需要有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就是这些基础的最重要的部分。国际货币体系是各国关于货币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安排,其中最关键之处就是确定以什么作为交换和储备的介质,即确立什么样的货币本位。此外,才是经常见诸报端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和汇率问题。也就是说,能否确立各国也包括跨国市场普遍接受的货币本位,是国际货币体系能否确立的关键,而国际货币体系又是世界体系的根基。因此,谁控制了确定货币本位的权力,谁就控制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权,也就掌握了世界体系运行的杠杆。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控制者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能够将这种认识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可叹的是,当时处于有利地位的中国明清朝代的统治集团者并无任何金融意识,也没有包括对货币本位重要性的认识;可怕的是,由于他们忽略了以银——这种本土缺少的资源作为货币本位所蕴藏的巨大风险,(12) 把关系国家存亡的金融命脉置于他国手中。历史惩罚了无知者:1630年后的美洲白银短缺,使明王朝迅速败亡;而由英国开始的世界金本位制浪潮,又最终导致了实行银本位制的清朝的垮台。(13)
与葡萄牙、西班牙甚至荷兰相比,英国是白银体系中的“插班生”。然而,它们依靠在1696年牛顿担任皇家造币厂厂长时重铸了英镑并确立了与黄金的固定比价,靠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领先于世界的货币思想,靠纳尔逊护卫的海上安全屏障,以几代人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对银本位的颠覆。1816年,也就是在英国领导神圣同盟打败拿破仑后的第二年,英国立法实行金本位制,采取以国家铸造金币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本位货币自由流通,把白银作为辅币。随后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效仿,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以英镑为主导的金本位制时代。在货币本位制上,先知先觉的英国人得到了历史的最高奖赏,就是世界霸权。
作为拥有更多黄金储备的国家,英国实行金本位制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铸币税,还可以通过维持金银之间有利于黄金的比价关系,用汇率杠杆进行财富转移。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银行可以在金本位体制下自主发行远高于黄金储备的英镑银行券,以支持英国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英镑-金本位”加上固定汇率制,构成了新型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贵金属+信用货币的体制,支撑了英国的海外投资和战争,实现上百年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成就了英国的全球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经济遭受重创,英镑霸权再无力维持。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标志英镑主导的金本位体系退出了历史舞台。(14)
与银本位与金本位制混混沌沌的权力交接相比,金本位制之间的权力易手则是巅峰对决。靠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支撑,美国以“怀特方案”拆散了约翰·凯恩斯(John M.Keynes)关于战后货币体系重建的构想。在1944年,美国人选择了以“双挂钩”为特色的金汇兑制: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仍然是金本位加上固定汇率制。所不同的是,美元取代了英镑的位置。随着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世界体系的霸权也落入美国手中。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当得知英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迫切需要美国的信贷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英国不撤兵,英镑将会在投机压力下变得一文不值。英国最终在美国货币杠杆下屈服了。(15) 其后的历史多次证明,币缘不仅是一种经济金融的关系,更是一种政治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国家间军事的较量。
币缘的核心是币缘政治。与发端于主权、视国家为空间生物、认为地理环境是国家政治行为基本因素的地缘政治不同,作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的过程。从币缘政治的角度看,支配当代世界体系包括国际政治的主导力量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获利主要通过流水线和贸易的时代不同,金融资本获取利润的方式主要依靠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巨量衍生金融工具,其主要政治目标也成为在于已有利时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于己不利时则修改或改造金融秩序。币缘政治更关注于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货币因素,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新范畴,其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币权长期被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世界性金融机构所独占。应该承认,在1945-1970年的25年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表现十分卓越——在全球经济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增长。(16) 然而,以一国货币充当全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存在着致命缺陷,即所谓的“特里芬悖论”。(17) 历史的真实进程显示,与学者预计的悖论相比,冷战的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导致的巨额军事开支才是压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更重要也是更直接的原因。(18) 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出于保护自身财富而加紧用手中的美元兑换黄金,这一夹杂着国际间经济政治多种要素的博弈,也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沉重打击。在多种压力下,尼克松政府选择了放弃金本位。这其实是美国转嫁危机的一种主动选择。(19) 美国人丢掉了“金汇兑制”,却得到了“美元本位制”。
尼克松把国际货币体系引入了信用货币或纸币时代的轨道,开创了金融史上的新纪元。这是货币史上历史性的一跃。从此,货币不再是一块由金或银制作、其重量和纯度由国王或总统或国家以其权威进行担保的硬通货了。(20) 在各国间进行交换的货币,只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纸币或电子符号。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牙买加协议》确定实行浮动汇率和黄金非货币化,并允许多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字面上看,牙买加体系是多元货币体系,而实质上是以美元为本位的信用货币体制。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美元本位制”就是“美国帝权”—— 一种与大英帝国“自由贸易权”类似的“非领土的权力”。(21)
对美国来说,获得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的地位,就可以向世界提供超量美元和各种债券以及足以淹没全球的金融衍生品。这种摆脱了实物锚定的货币体系,允许金融机构凭空创造具有货币功能的金融产品,使金融资本可以操纵各种金融市场,从而奠定了金融资本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使美国可以金融创新的方式攫取制造业国家和资源类国家的巨额财富,建立以债务国美国支配所有债权国的反常规的新型世界秩序体系。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同样正确。38年来,美联储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美元和货币性短期流动资产,美国的货币存量(M3)广义货币增加了20倍,引发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危机,美国为支持超前消费和多次战争欠下了11万亿美元的国债和50万亿美元由政府信贷担保的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金等债务,(22) 美国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期货市场累积了巨大的系统风险……这些因素的积累使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本质上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元本位制的危机。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它与发生在17世纪和19世纪的银本位制危机、1929年和1971年的金本位制危机一样,(23) 是国际货币体系本位制的危机,是撼动了世界体系基础的大危机。既然我们都知道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现行世界体系的基石,那么美元本位制危机就将引发导致全球金融体系震荡的激烈冲突。指出这一前景,不是对形势没有信心,而是要正视并防范可能到来的冲击。认清这一点,或许可以使我们汲取教训,不会再次受到历史的惩罚。
二 国家身上的金融化烙印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是人们用于概括过去30年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三个主题词。(24) 其实,“全球化”不过是世界体系的别称,而“新自由主义”则是偶领风骚的时尚意识,真正能够体现这个世界本质变化和现状的就是“金融化”。在一定意义上说,金融化是推动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深层因素。
关于金融化,有着不同层次的不同认识。有的学者把金融化局限在金融体系内部,认为金融化是指由于无数金融工具爆炸式增长导致的资本市场型金融体系逐步主导银行型金融体系的过程;有的则认为金融化是生产模式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的过程;(25) 更综合的看法是,金融化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政治学概念,它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金融化是食利者阶层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增强的过程。(26)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金融化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趋势,它体现在金融强国不断利用金融工具和货币体系去支配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以保持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简言之,所谓的金融化,就是金融逐步主导经济,进而影响政治和社会乃至左右国际关系的过程。
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金融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国家的侵蚀,最突出的就是使国家利益的金融化。国家利益的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国家利益概念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却又存在最多争议的概念,为了避免陷于无谓的争论,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视为包括物质和精神等多种要素组成的整体框架,看看金融如何影响并改变了这些国家利益的要素。
金融化改变了国家安全的外在形式与主要内涵。以往国家安全主要体现在空间安全上,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外敌的入侵。在金融化时代,危及国家和颠覆政权的威胁更多地来自金融危机的冲击。据近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危机将转化为银行危机,而银行危机又将转化为财政危机,随之可能导致政府危机和爆发社会总危机,导致政府垮台。(27) 从1970年以来,全球至少发生了15次引发广泛危机的金融崩溃事件。(28) 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有多个国家破产或瓦解,许多国家陷入民众上街、政府倒台的社会危机之中。即使在金融上强大的美国也时刻提心吊胆地提防着可能致使美元崩溃的金融攻击。(29) 毫无疑问,如今的国家安全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安全,金融化不仅增加了国家安全的新方向,亦成为其新的焦点。
财富是国家的另一项重要利益。在金融化之前,国家财富的主要形态是土地、资源、物产和商品等有形物质,现在国家财富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货币、债券、股票等金融化的财富。尽管金融化的财富本质上只是资源的倒影,但却容易被转移和剥夺。因为这些金融化的财富往往由国际储备货币来计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已知的外汇储备的最新统计,其中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61%,欧元占27%,余下的主要为英镑和日元。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调整汇率等多种手段造成本币贬值以实现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占。(30) 特别是开放的金融市场和现代信息手段为迅捷地在国家间转移财富创造了条件。财富在今天,既不是亚当·斯密的“一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的年产量”,也不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任何可以带来收益的东西(资本、土地和劳力)”,而是“可买卖的获得满意的手段”。(31) 这种抽象的、脱离了泥土气息和流水线喧嚣的财富——金融资产,可以在一瞬间离开一个国家,只留下混乱和贫穷。在金融化时代,国家完全可能出现铜墙铁壁犹在而财富尽失的现象。
主权独立是国家基本利益。如今,虽然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仍然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但是除了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却无法完全掌控自己国家货币的汇率、利率和发行量,并因此承受着国际货币市场波动带来的汇兑损失和金融风险。更何况在金融危机时受援国家要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渡的部分国家主权,平时各国中央银行则必须跟随美联储升降息的消息采取相应措施,这些都说明控制供给货币体系的国家对其他国家主权范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国防政策都具有超出武力之外的控制力。就像有的国家财长所说的那样,“我只是我们国家的半个财长,另外半个在华盛顿”。(32) 更重要的是,货币资本的全球流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赢利方式,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不断消解着国家的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使国家只能按照金融资本的分工去扮演产业链上的指定角色。
除了国家利益金融化的趋势外,金融化对国家力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国民精神和政府素质等因素的影响,而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国家力量的主要部分。(33)
作为在世界上占据一定空间的行为体,国家无可置疑地对所属空间拥有主权。然而,欧洲国家颠覆了它们最先倡导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框架——在欧盟国家之间主动放弃了彼此的国家边界,建立了一体化市场,统一了货币,签订了可以使人员、物资跨国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欧盟现象模糊了传统主权国家的空间边界,对地理历来是国家力量根基的观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实欧洲国家之所以让渡国家主权,这与应对美国和美元的压力直接相关。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必须联合才能在这个充分金融化的世界上成为有分量的成员。以欧洲为榜样,许多地区也在或快或慢地推进经济一体化和货币整合。有趣的是,每遇到一次全球性危机,这种区域整合的进程就会加快。尽管世界其他地方没有欧盟走得那么远,但却趋势一致。
另一个与地理有关的现象是“以土地经营权换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近50年里建立了总量不容小觑的经济特区或开发区,这种由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推动的“空间支配权转移”现象显示,地理因素稳定性正在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所撼动。此外,在金融市场支持下发展起了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互联网和航空航天技术不仅使世界经济连为一体,也消解或降低了地理因素在国家安全上的作用。以往难以逾越的山脉、海洋在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太空平台和网络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屏障作用。尽管地理因素对战争成本和制约军事力量使用仍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但与马汉、麦金德时代相比,地缘因素的作用却已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立国的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巅峰时期,美国制造业占到世界制造业份额的40%。当时的美国金融主要是为需要大量资本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直到1966年,据美国的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只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34) 而到现在,与生产流通有关的金融交易量不到1%。从1995年到2007年金融利润在美国企业总利润的占比中膨胀了300%。(35) 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向国外转移,大量传统工业企业纷纷进入金融服务业,美国最著名的工业企业通用电气公司在2009年的报告中称:过去10年来,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收入来源于金融服务。(36) 金融化把所谓“新自由主义盒子”扣在美国经济之上,全面推进“全球化”、“小政府”、“弹性劳动力市场”和“摒弃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37) 膨胀了虚拟经济,压制了实体经济,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削弱了国家力量。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多次呼吁美国的再工业化。然而在金融资本集团的全力阻击下,这种呼呼只能止于呐喊。
为战争融资一直是组建国家的首要推动力。(38) 即使在当代,国家依然摆脱不了为战争融资的宿命。对战争如何影响已经金融化的国家,最经典的就是斯蒂格利茨和比尔米斯关于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影响所做出的分析。他们的重要贡献不是发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花费了“3万亿美元的战争”,也不是全球性的金融市场使国家很容易筹得战争费用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打酱油的钱可以用来买醋:弥补美国巨额赤字的贷款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战费”。他们的关键结论是,这场发生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迫使美联储降低利率、增发国债,导致美国赤字扩张、经济减速,从而引发了2007年底发生的次贷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战争的经济代价需要美国几代纳税人来偿付。(39) 金融化使国家易于透支,这可以使它们能够维持庞大开支的军事力量和进行天价战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40) 发生在美国的危机证明,金融化是国家力量所在,也是灾难所在。
此外,对于厌恶风险的金融资本来说,非对称的军事力量造成的伤害可能造成资本的“羊群效应”。于是一个很小的跨国组织可以对拥有世界最强大军力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安全威胁和经济破坏。尽管军事力量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充当着终极法庭的作用,然而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金融化使国家更脆弱。
与国家利益形态和国家力量变化相应,国家行为也出现了变化,这可以在国家领导人的行为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翻检一下近年来各国特别是大国领导的峰会新闻——不论是全球性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还是地区性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欧盟领导人峰会——都不难发现,尽管各国首脑仍会谈到控制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等一些政治、军事问题,但他们谈论更多的或更感兴趣的显然是经济议题。大国、小国的领导人似乎全成了国家的首席执行官(CEO)。他们专注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关注吸引投资,开辟市场,在他们出访团队中更多的是企业家和金融家。最近,他们又关注于利率调整、汇率变化、股市涨跌、流动性过剩与不足、赤字与盈余、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QE2)的影响等,金融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国家领导者视野的中心,日益成为“首脑级”的高政治话题。
除了对国家的影响以外,金融化通过创造全球舞台新的主体,扩展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首先是那些可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金融机构,它们可以操纵大宗商品价格,也可以玩弄股指或期指,还可以通过发布国家信用评级来引起市场震荡,造成国家经济基本面大幅波动和投融资环境的变动,对国际政治可产生重大影响。2008年俄格战争后,石油价格剧烈波动,使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大影响,这无疑对俄罗斯当时正趋强硬的外交立场起到了牵制作用。此外,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更多也更直接地介入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从2011年年初以来发生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局动荡中可以看出,这些利益诉求复杂的非政府组织如果与富可敌国的金融力量相结合,就可能成为力可敌国的政治力量。例如,给美国和多国政府造成不小麻烦的维基解密,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一家德国的基金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化在国家身上留下了金色的印记,开启了国际关系金融化的过程——币缘政治逐步走上了国际关系的前台。
三 未来的焦点与走势
认识未来世界格局变化,关键在于抓主要矛盾。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阐释,人们不难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货币的本位制,对世界体系即世界基本秩序的建构与稳定运行具有重大意义。正是由于美元本位制的危机,使二战以来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遭到质疑,危机冲击了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撼动了国际秩序的基础。
危机当头,各国固然需要协调政策应对眼前的挑战;但是人们心里清楚,现在也需要对危机后的世界秩序进行设计与安排了。与经常成为新闻事件的核武器试验或是偶尔成为广泛议题的气候变暖相比,国家间的贸易争端、汇率升跌、货币增发与贬值、主权债务等才是决定世界之舟航向的洋流。由于国家利益的高度金融化,金融杠杆左右着全球资源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未来国际关系的矛盾将会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展开,其焦点是——恢复原有的秩序还是改革旧秩序?其本质是一个币缘政治问题。
2011年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谈道,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的遗留,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弊端,与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已不适应,未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亦难以应对大规模金融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和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因而,需要进行改革。(41) 中国的看法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震动。(42) 显然,作为至今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仍然希望能够恢复和维持已经深陷危机的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曾经从改变银本位制、金本位制而获得过世界主导权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比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更加清晰地知道,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变最终将改变整个世界。
恢复还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利益。处于原有体系中不同地位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态度,即使西方国家因其利益的差异,意见也各不相同。目前,全球的货币利益主要由美欧两家分享,但份额差距很大。由于欧盟国家已经组成了内部贸易量占到70%的欧元圈,希望通过限制美元资本的扩张、缩小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欧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份额。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鲜明地表达过必须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意愿,但他们只是希望按照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对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改造。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帝国那样严密的政治实体,而是一个“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经济实体。(43) 不同的金融资本集团控制世界经济体系运行,控制全球资本投资、产业分工和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分配。在利益高度金融化的今天,美元、欧元金融资本集团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无疑会弱化美欧间传统同盟关系,使大西洋两岸的“表兄弟”彼此渐行渐远。
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矛盾——有着严重的贸易顺逆差,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明特征,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对美国传统大国地位构成了挑战,美国则支持台湾当局使中国继续分裂。此外,中美两国间还存在着历史的夙愿。可是从币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实际上处于美元圈体系的中间地位。这首先是一个水平空间的概念——环太平洋地区就像一个“美元湖”,囊括了中国的主要市场、主要贸易伙伴、主要外汇储备的来源和投资的去处,也包括资源产地和通道,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空间。然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立体空间,反映出产业结构中的垂直分工——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元体系中占据着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基础端是提供资源的国家,而作为消费—金融大国的美国则处于美元体系的高端,一方面它消费着中国制造的大量廉价商品,另一方面还需要中国提供大量的净储蓄——即从资本项下流入美国购买各种金融产品的贸易盈余。前者保持了美国低廉的物价,保障了高失业率下美国社会的稳定;而后者则是美国得以长期维持赤字财政和主要的生财之道。在美国的主导下,环太平洋地区逐渐形成了由消费国家—制造国家—资源国家构成的“美元币缘圈”。美国的职责是维持这个体系运转并从中获利,过去30年,中国在这个“美元币缘圈”体系中实现了发展。于是,两国间形成了奇特的“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44) 这是中美“斗而不破”的前提。以传统框架无法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同样令美国人感到困惑,“利益攸关方”、“中美国”、“两国集团(G2)”等名称,就是美国官员和学者之间试图概括的中美关系命名竞赛的部分成果。
不可否认,在币缘圈的产业分工链条的上、中游之间难免存在着利益冲突。作为制造业国家,中国希望争取商品定价权,希望保证贸易盈余投资的安全,作为大量资源的用户,中国也希望有一定的资源定价权,买什么什么就涨、卖什么什么就跌的情况对中国显然不利。在目前的体制下,美国既控制着商品定价权,又通过大宗商品的金融市场对资源价格进行控制,还要通过发行货币和金融衍生品占尽金融利益,这种两头通吃、赢者通吃的旧制度,肯定会受到制造业国家、资源国家及欧洲这样的消费-金融国家的反对。所以,不管美国愿意与否,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恐怕不改不行。然而,与欧洲不同,中国现在并不希望彻底拆散美元币缘圈,或者掀翻“美元湖”,中国目前还没有分享全球金融利益的能力与意愿。那么中国要什么呢?其实,中国的目标有限,就是雅尔塔体系中曾经允诺中国的那部分安全势力范围和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利益。这就是中国战略学者所说的“地区性守成”。(45)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正处于上升期的国家要“守成”尤其不易。其一,“成”果并未入我囊中,还需争取。其二,刚刚重返大国俱乐部的中国,尚不能敏感地去感受自己的战略或策略的调整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尚不会“守”。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其他大国出牌后再决定如何出牌。
2010年,在东北亚和南海地区先后出现了紧张局势,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以经济合作为基调的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日韩关系发生偏转,领海、领土的传统争端成为西太平洋区域的主导话题。对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大国心深如海,其行为背后自有复杂的动机。如果我们尝试以币缘政治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从2010年1月1日启动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货币互换以及随后中、日、韩三国总理商议三国自由贸易区和货币互换,东亚地区加快区域经济和货币整合的步伐,无疑将瓦解环太平洋地区“美元湖”。而这正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美国必须重返亚洲,以遏制美元体系中的这种“分离主义”倾向。在曾经与美国同舟共济的欧洲人看来,美国是一头大象,它有意或无意地屁股一歪就可能打破平衡或改变格局。可能在国务卿希拉里看来,正与美国“同舟共济”的中国也是一头大象,而这头大象似乎也正有意无意地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强国习惯用肢体语言传达信息,受到挤压的中国要理解背后的信号。
需要看到的是,国家吹响的常常是音调不定的号角。这是因为在任何时候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代表着不同人群的各个利益集团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和采取不同的行动。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资本逐渐式微,表现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金融资本的膨胀。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商品交易额为15.77万亿美元,而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700万亿美元。(46) 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已经成为这几十年间美国国家利益的主导力量。在金融化时代,国家需要世界性的大金融机构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资本,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配合,仅靠政府信用难以实现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融资,获得推进经济发展、改革福利政策和进行军备竞赛及战争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金融机构也将失去对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影响力。这种国家与金融机构相互依赖关系的长期互动,就形成了与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47) 相似的权力中枢——“金融—政治联合体”,如果用地理概念表述,就是“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资本集团受到重挫,“金融-政治联合体”受到削弱。以“改革”为旗帜而成为总统的奥巴马,在国内和国际的政策上开始改弦易辙,强调就业与再工业化,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更多关注着产业资本集团和一般民众的利益。然而,金融资本仍然是美国利益的主导者,它需要维持稳定的美元币缘圈,需要中、日、韩等国持续的净储蓄的流入。因此,在环太平洋地区需要保持可控的紧张,既要防止日、韩的离心倾向,巩固美日、美韩间的同盟关系,同时,又绝不能把中国驱向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因为美国很清楚,以目前亚洲地区的政治文化生态,亚元圈还是遥远的海市蜃楼。但如果让中国与欧洲进行整合,就可能在欧亚大陆甚至是欧亚非大陆上形成巨大的非美元币缘圈,这不论是从地缘还是从币缘来说,都是美国真正的梦魇。对美国来说,欧元构成的外部制约可能与其产生核心利益相冲突,而美元币缘圈内部利益和权力分配是“共生体”内转移支付式的利益调整。因此,两个赌场争利的美欧矛盾将难以调和,甚至有激化的前景。(48) 而在同一币缘圈内部的美中之间将难有战争,只有强硬的讨价还价,(49) 包括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同理,欧元圈也需要中国等制造业和资源类国家的加入,在这些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却有着让权力回归平衡的共同利益。对币权的角逐,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的格局。
可以预见,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适应变化的世界格局,已经成为未来大国间政治的焦点。用币缘政治的框架分析主要大国在焦点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有利于我们预见世界大势的发展。更具实践意义的是,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博弈中,我们就知道能够做些什么和不做什么——积极参与其中的改革,而不是取而代之的革命。
[收稿日期:2011-01-28]
[修回日期:2011-03-16]
注释:
①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页。
②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③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134、139页。
④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导论,第5页。弗兰克更想证明的是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 000年,而不是像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者以为的那样只有500年的历史。
⑤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
⑥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⑦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37、307页。
⑧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83、488页。
⑨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前言,第13页。弗兰克提到,他初稿的标题是《亚洲霸权下的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
⑩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78页关于“博尔顿和瓦特曾得到贷款”的相关内容。
(11) [英]尼亚尔·弗格逊著,蒋显璟译:《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1700-2000)》,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2)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13)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第129页。
(14) 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5)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郭学堂等译:《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7页。
(16) [美]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著,贺坤、贺斌译:《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7) 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其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由于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地位。各国为发展国际贸易,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导致美元在海外不断沉淀,这使美国将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作为国际核心货币应保持币值稳定,这要求美国须是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的悖论被称为“特里芬悖论”。参见[美]罗伯特·特里芬著,陈尚霖、雷达译:《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8) [美]赫德森著,嵇飞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272页。
(19) 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译序第1页。
(20) [英]约翰·F·乔恩著,李广乾译:《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页。
(21) [美]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2) [美]彼得·D·希夫、[美]约翰·唐斯著,陈召强译:《美元大崩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77、150页。
(23) [美]本·S·伯南克著,宋芳秀、寇文红译:《大萧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24) [美]约翰·B·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第9页。
(25) 约翰·B·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第9页。
(26) [美]戈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金融化与世界经济》(序言),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7期,第14页。
(27) [美]理查德·邓肯著,王靖国等译:《美元危机:成因、后果和对策》,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28) [美]约翰·B·福斯特等:《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1期,第7页。
(29)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1年2月1日文章:《金融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2月3日第4版。
(30)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31)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世界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页。
(32)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赵绍棣、黄其祥译:《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章。
(33)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34) 王建:《大变革时代的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35) 约翰·B·福斯特等:《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1期,第7页。
(36) 希勒尔·蒂克廷:《今日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11期,第9页。
(37) 托马斯·I·帕利:《金融化:涵义和影响》,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第17-19页。
(38) [英]尼亚尔·弗格逊著,蒋显璟译:《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39)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琳达·比尔米斯著,卢昌崇译:《三万亿美元的战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文版序,第2页。
(40) 《老子·五十八章》。
(41) 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2011年1月18日消息,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42) 马丁·尔夫:《中国为何不爱美元?》,载《金融时报》,2011年1月18日,FT中文网站,http://www.ftchinese.com/。
(43)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路爱国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44) 郭震远:《美国对台政策开始又一次重大转折》,载《中国评论》,2010年1月号,第18页。
(45) 张文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载《领导者》,2007年第5期,第26页。
(46) 王建:《货币霸权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47) 1961年艾森豪威尔的卸任演讲,参见美国《新闻周刊》于2011年2月20日刊发的文章《无根据的影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军工联合体》。
(48) 王建:《货币霸权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49)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译:《转型中的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标签:国际货币体系论文; 世界格局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白银投资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白银美元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白银论文; 货币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