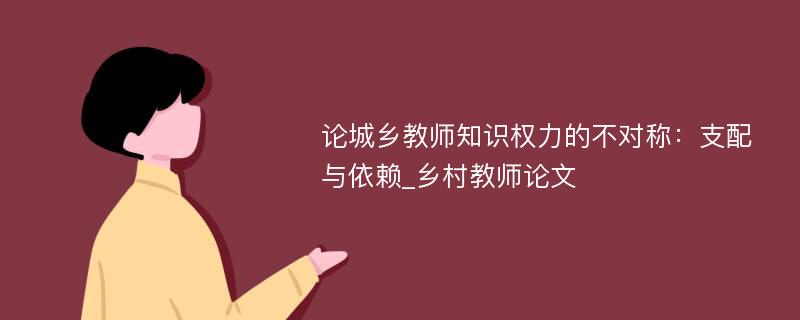
论城乡教师知识权力的不对称性:支配与依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权力论文,教师论文,知识论文,不对称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知识生成机制的不对等性 知识生成是指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个体化经验的过程。它不是教育研究者和学术权威的专利,而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基本权利。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的价值与意义更加深远了,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知识已经成为关键的经济资源,而且是竞争优势的主导性来源,甚至可能是唯一来源。”[1]随着科学哲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价值性,知识的生成受权力、意识形态、政治信念等因素的影响。[2]这就意味着,教师的知识总是打上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情境的烙印,他们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建构、体验与个人性质,这样的知识比客观知识更为单纯、深刻与生动。传统上,教师一直是知识生产的重要群体,在教育生活中,他们将“成人”(成就他人)与“成己”(成为自己)统一,原始性地呈现教师教学人性,自由地生成自我知识[3]。古代教师融知识生产与教育实践于一身,如我国的孔子,既从事教育实践又进行教育知识生产。西方最早的职业教师——“智者”,也是一边云游四方,授徒讲学,一边对教育问题进行思索,形成独特的教育思想。按理说,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育实践者,他们与乡土自然、乡土文化互动,其知识与城市教师的相比,具有一种乡土气息,也更生动、灵性与形象,具有一种生命意蕴。伟大的教育学家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苏霍姆林斯基等,虽然清贫一生,但他们却勤勉不辍,潜隐笃定,归纳反思,生成了系统的教育知识,为人类创造了宝贵的知识财富,谁说这不是一种生命的积淀呢?由此可见,乡村教师也是知识生成的重要群体,我们不能无视其知识生成能力。 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教育学术的制度化与技术化,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逐渐分离,教育知识生产成了教育研究者的专利。城乡教师在知识生成机制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性,知识权力对乡村教师进行支配。现今的知识生产机制,存在这样一种误区:“研究是纯学术人员与科学家的特有领域,教师只是他人研究过程中的旁观者、研究对象与研究结果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参与者。”[4]对于现有的知识生产者而言,他们拒绝多样性的知识,而追求知识生产的繁、难、高、深,他们否认底层教师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贬低或忽视教育实践者的知识和个人经验。因此,乡村教师在教育研究者和城市教师的知识面前永远都是“被指导者”。这样,乡村教师在知识的生产上,丧失了创造的权利,放弃了自己的想象与创造,也失去了知识生产的关系、土壤与营养的根基。他们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边缘,逐渐沦为他人知识的附庸,失去了知识创造的信心与自我价值的肯定。他们的生活丧失了生命的属性,沦落为一片荒原,了无生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权力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权力。城乡教师,在知识生产上,就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 二、知识表达机制的不公平性 知识表达机制即知识话语权利系统。乡村教师不是超然,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他们的中心工作是教育活动,而教育活动又是以知识为前提,以知识为载体,以知识为目的的活动。作为教育活动组织者的教师,他们的教育教学活动,无不是在一定知识观的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所言”“所想”“所行”无不是对知识观的表达和言说。[5]我们应该充分尊重教师的知识话语权,特别是乡村教师的知识话语权。因为“叙事者才是话语的掌控者,叙述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才是他希望表达的真实内容”[6]。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你的情境——你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你认为什么事重要,什么值得去了解,情境也决定你想要描述和解释的理论/故事”[7]。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掌控者,他是站在乡村教育的位置,结合其历史文化和生存境遇,来看教育和世界的,其位置、历史、境遇和角度具有独特性与一次性。而且,知识是个体自我世界的表达,具有个人性。知识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具有了独特的内涵与意义。因此,我们要充分尊重个体的知识权力,维护个体的知识话语权。这既是人本精神的真谛,也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充分重视了个体的知识本性。 然而,我们发现,乡村教师越来越被边缘化,也越来越失去知识话语权。他们在表达自我的过程中,总是受知识体制与技术力量的支配与干预。现在,很多学者在探讨乡村教师的问题时,他们有意或无意地,给乡村教师贴上“低素质者”的标签,认为乡村教师的素质普遍低下,应该加强乡村教师的“知识供给”,以提高其各方面的素质。但是,乡村教师真的是“低素质者”吗?他们真的需要各种外在的“知识给予”吗?这些专家学者真的深入到乡村,了解过乡村教师吗?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他们根本没有给乡村教师说话的权利,而只是依靠自身的专家地位,一味地凭借自己的纯粹理性,甚至想当然,盲目地制定计划,提供方案。他们在制定教师评价标准、实行课程改革,实施各种教师培训计划,以及各种教育政策时,很少深入底层,聆听乡村教师内心的声音,很少与乡村教师深入平等地交往与对话,很少给予乡村教师真正的知识表达权利。就改革和评价的结果而言,乡村教师仅仅是“政策的执行者,秩序的服从者,课程的操作者,方法的消费者……他们很容易矮化为一个仅仅从事非创造性劳动的雇工,僵化为一个只是观赏既定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愚化为一个贬损自身灵魂的思想附庸,堕化为一个维护错误观念的文化保安”[8]。 三、知识选择机制的不自由性 乡村教师的知识选择,主要是指在已有的知识文化中选择一定的知识进行传播、再造与创新。雷蒙德·威廉姆斯说:“从哲学、真正的理论和各种实践史的水平和角度来看,有一个我称之为选择性传统的过程……选择总是关键的,从过去和现在的整个可能领域里进行选择,某种意义和实践被当作重点选出,而另外某些意义和实践则被忽略和排除。”[9]乡村教师自主选择知识,就是选择自己认为对人有重要意义的知识,及其相应的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教师作为教育专门人员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对乡村教师的尊重与信任。乡村教师生活和工作的地区具有独特性,其教授的知识既要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又要与现代化的知识内容保持联结与融通。一方面,这能满足学生服务乡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这也要求教师选择现代化的内容,促使乡村学子在知识获取中,实现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结,从而促进乡土社会的现代化。 但是,他主性却是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特性,也是中国乡村教育必然具备的特性,这一特性集中反映在乡村教育的教学和管理上。管理学意义上的人、财、事三权几乎从来没有属于过农村,尤其没有属于过学校的直接主办人和教学的直接参与者——校长和教师,也就是说,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一直被动地处于权力组织的边缘化位置[10]。而乡村教师的知识选择,就更具有他主性,正如麦克·F.D.扬所说,知识是社会控制的产物。特别是在阶级社会,知识就是一定阶级权力控制下的产物,是一定社会主流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11]弗莱雷说“教育即政治”,而阿普尔也认为,课程是社会主流阶级权力、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体现,是“官方知识”、“法定文化”。课程知识,不仅仅是一个分析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更不是一个纯粹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12]其实,“历史上发生的某些具体事件,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而这种制度也使压迫者使用暴力,使人非人性化。这种状况迟早会被压迫者起来反抗,与那些造成他们不完善的人进行斗争”[13]。一定程度上,国家与教师就是一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在强制意识形态下,许多时候,乡村教师必须放弃自由的知识选择权,而迎合意识形态的潮流与要求,“设计教育课程内容的出发点必须是当前的、现实的、具体的,并能反映人们意愿的情景”[14]。因此,教育的价值取向、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手段等,就应该产生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在当前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建构。 知识选择不自由,会导致乡村教师逐渐失去自我。如果乡村教师长期摒弃自己的知识选择权,那么就会丧失自我的本性,就会遮蔽其作为专业人员的内在的生命悸动,就会放弃自己的历史与生存的文化养料,最终成为“他者”的附庸。 四、知识共享机制的缺乏 知识共享是指知识在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转移,是知识拥有者将其本身的知识外化、提供出来,而知识需求者通过各种沟通方式与知识提供者互动以获得知识的过程。[15]知识是一种独特性的资本,它可以重复使用,而不会因此而消耗其价值,甚至可以说,知识的使用范围越广,其价值和影响力也就越大。基于知识的这种特性,知识共享也就成为知识管理的关键。[16]然而,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是,知识共享的重要动机之一,是超越知识的“利己主义”。工业社会以来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意识形态,使得众多教师都深信知识拥有量与自己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教师的教学业绩和专业发展与知识拥有量成正比。因此,在学校教育中,拒绝知识分享,分割知识的整体性质与学术成员之间的封闭保守等情况,似乎普遍存在。知识分子们已经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沦落为地地道道的“知识利己主义者”。他们深信,凭借自己拥有的而别人没有的知识,就是拥有了在学校中立足生存以及专业晋升的砝码。在职称评定等教师业绩考核与竞争中,可以占有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基于知识带来利益的考虑,他们不愿意将知识分享给他人,缺乏知识共享、交流与互补意识。城市与乡村教师,虽然同属教育系统,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他们分居两端,联系甚少,缺少对话,知识未能共享,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共享机制。 教师劳动的时间、空间与活动特征,使其失去了共享知识的时空结构与可能。劳动时间长,教几门课程,空间主要限于办公室与课堂,已经成为乡村教师生存处境的基本生存影像。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欣赏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更遑论其历史与乡土文化的优势,并将其中的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历史传统与人文景观融入到自己的教学中去。缺乏知识共享机制的严重后果是,一方面,在教师与家长、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逐渐割裂中,乡村教师越来越孤立无援,成了生活中孤独的漫步者;另一方面,他们在追赶城市教师的艰难文化苦旅中,与城市教师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联系,他们愈是渴望现代化知识,就愈沦落为现代化旅程中的流浪者。他们无法依赖自己、依赖环境,也很少有社会资源对他们给予援助。他们是孤立的,脱离环境而生活,俨然一个脱离父母的孩子。印度哲学家奥修说,你无法依赖,你也无法独立。在自身资源缺乏的基础上,乡村教师之间以及城乡教师之间都不能分享知识,分享经验,而都只是将眼光投射在自身,久而久之,城乡教师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教师知识分子的身份越来越消弭,其心灵失落感也越来越强烈。 五、“他者”对乡村教师的规训 这里的“他者”,是指乡村教师以外的教育专家,包括大学教育专家、城市中小学教育专家与技术官僚等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比乡村教师拥有更多的知识话语权。乡村教师作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是乡村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奋战在教育的第一线,亲身经历和体验着教育实践。他们与城市教师一样,是受过专门的教育训练,通过专业资格考试的专业教师。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教师是一门专门的职业”,教师是专业人员,在工作中具有较高自主性,他们不受监督,在教学要事上能够自主决定。实际上,任何知识,均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个人对实践问题的反思,并跟随实践问题的解决不断发展,这样的知识才有生命力,才能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所以,知识是实践的、开放的、融通的、科学的。历史上,教师在学生、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场所的设置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自主权,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专家。[17]教师专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在于教师教育的程序设计,也不在于知识发展的理性逻辑,而在于个体在自己的生存境遇中找到自我的学习、选择与发展方式。任何外在于主体的知识设计,只会是对自我内心世界与精神自治的入侵与横蛮摧折。 然而现在,乡村教师并没有被视为教育专家。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被“他者”支配,并逐渐对“他者”形成了知识的依附。就教师的专业发展而言,我们不能否认,理论界对其内涵众说纷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模式指手画脚,而一线教师也在自身专业发展进程中迷失自我。[18]这些“他者”对乡村教师的支配,是以客观知识为工具的。在客观知识的规训下,乡村教师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异化为教育政治的“犬儒”,教学的“机器”,生活实践的“背叛者”,农村教师不再是乡村里的“熟人”和“精神领袖”……而最终成为了村落中的“陌生人”。[19]在现代化的狂澜中,乡村教师的存在呈现象征性、区隔性、原子性等特征,即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完全局限于主体外部的技术力量设计的范畴之中,乡村教师的责任、权利、义务、意识与行动被局限在与专业性有关的事件上,具有浓烈的强制与规训意味。[20] 乡村教师对“他者”的依附,表现在自我价值的迷失。在这种背景下,客观知识及其积累和传播方式,支配了乡村教师的专业化过程。乡村教师逐渐沦为客观知识的奴隶,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潜能、历史经验与生存环境,其独立人格被遮蔽,特殊性被忽视,乡村知识分子角色被消弭。在客观知识的标准下,乡村教师的教学水平劣于城市教师,在这种差距怪圈中,他们缺乏主体意识,自我选择意识薄弱。“事实上,任何人所掌握的只不过是科学知识的一个微小部分,无论他对这一小部分知识掌握得有多好,都不足以直接评判科学的有效性和价值。”[21]因此,尽管一些“专家学者”标榜科学,但是“现存的科学意旨是辨认一个叫做‘科学’题材的有效权威,但是他并不是最高权威”[22]。我们越来越认清,教育专家们越来越具有古代巫师的性质,他们的理念体系,无法与教育现场切合,他们的信心、知识与理论体系是脆弱的,他们的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是危险的。而基层的教师,他们的经验与艺术是可靠、安全与实在的,能够指导其教育实践,并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教师的教学经验、技术、生活、学术、道德没有任何界限,教师的沉静、低调、不抛头露面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与学术贞操,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人格,乡村教师的这种人格是不容干涉的。所以,乡村教师不能在“专家学者”的阴影下迷失自我,必须坚守自我,相信自己,否则他们将生活在一个无我的宇宙图画中,不能创造和维护科学价值。他们的精神空虚、自卑、被动与无奈,他们厌倦居高临下的空疏和无情却有逻辑的知识体系,只希望从形而上学层面回到事实本身。 从其本质而言,城乡教师的知识及其权力的支配与依附关系,是客观知识对教师的支配,以及教师对客观知识的依附。然而,由于乡村教师在知识权力上处于不利地位,客观知识对其支配程度更为严重。所以,正如福柯所言,“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3]。因此,乡村教师知识权力的旁落是城乡教师不均衡的重要原因之一。自古以来,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就是一个永恒而又复杂的话题,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张力。它们既彼此渗透,又相互冲突。我们从知识权力的角度,分析其如何使城乡教师走向不均衡,旨在为解决城乡教师不均衡提供一点线索,也为权力者提供一个反思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