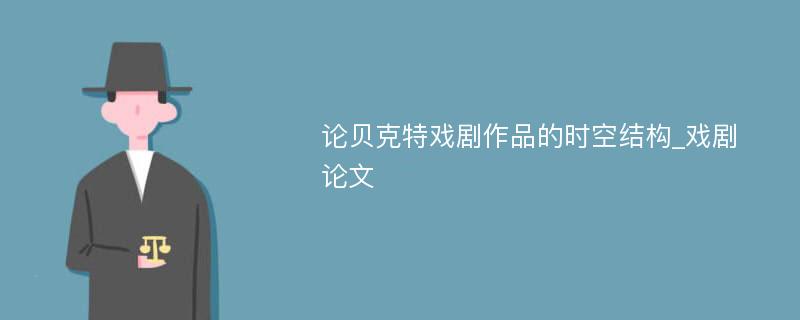
试论贝克特戏剧作品中的时空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戏剧论文,时空论文,结构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53年《等待戈多》初演成功,直到70年代中后期,贝克特在戏剧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继续探索了20多年。“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处境”是贝克特一直致力于表现的主题。为了表现这样的主题,贝克特采用反传统的戏剧手法,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尤其是在时空结构上,贝克特打破了传统戏剧中的时空概念,试图以新的时空结构模式表现作品的深刻内涵,让他的戏剧作品“向着观众内心深处说话”[①],以激发观众从无意义中体味出意义,使他们有意识地面对当代世界的荒诞以及人类自身的悲剧性处境。对这样的时空结构作深入细致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诠释贝克特的戏剧作品,而且可以使我国的戏剧工作者拓宽视野,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从而丰富和提高我国的戏剧创作与理论水平。
一、贝克特剧中时空结构的基本特点
苏联美学家T·斯列布霍夫在《艺术作品的时空机制》一文中指出“艺术作品的大厦建筑在艺术时空这块基石之上。艺术中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是艺术形象的思想和情感的载体,而且是作品的结构系统的枢轴。”[②]传统戏剧中,时空机制具有组织结构成份、统摄其它结构因素的功能。传统剧主要讲述一个故事,它通过逻辑严密、顺序连贯的情节安排在观众头脑中留下完整缜密的印象。由于情节发展是在井然有序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传统戏剧的时空观念很强,对时间和空间有明确的限制。从观众欣赏角度来看,剧中明确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是“具象”的表现,否则,时间不清、地点不明,给观众的印象也是模糊不定的。
贝克特的戏剧作品则彻底打破传统框框。它们既无意于叙述一个完整的离奇曲折的故事,也没有描绘某一具体时空下的社会生活及日常琐事,而是着重表现人物荒诞的生存状态和混乱的思维状态。因此,贝克特的剧作既没有严格的外在逻辑关系,也缺乏连贯的情节。没有情节也就无需提供情节发展所需的时间和空间。纵观贝克特的戏剧作品,可以发现其作品中的时空机制具有如下特点:
Ⅰ.时间:模糊、循环、混乱
传统戏剧作家往往把舞台时间当成结构的组成部分,竭尽全力巧妙地安排剧情以使观众完全沉浸于发生在特定时间内的具体事件中,贝克特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经常让剧中人物直接面对时间并且不断提醒观众舞台时间,从而使时间与剧情脱节。《等待戈多》一剧中弗拉季米尔不断地发问:“咱们这会儿干什么呢?”[③]《残局》中幕帷初启,克洛夫就不耐烦地宣称:“结束了,已经结束了。”[④]为了打发难捱的时间,贝克特剧中的人物尝试各种毫无意义的活动,例如空洞的谈话、滑稽的动作、无聊的游戏等。不难看出,舞台时空在贝克特的剧中是一片需要填补的空白,人物频繁地直面时间,观众被频繁地提醒时间,也就是被提醒生存的意识。只有当人的生存成为一种枯燥无味的负担时,时间才显得空洞,才会被人们反复地感觉到。时间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处理与贝克特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完全一致。
除了让人物直面时间,贝克特还让他们直接评述时间。《最后一盘录音带》中的克拉普抱怨说:“这一年过得糟透了。”[⑤]《快乐的日子》中的温妮也对“今天并不比昨天更好,明天也不会比今天更热,怎么会这样。”[⑥]产生了疑问,最终她不得不承认“时间的此刻同彼刻无甚区别。”[⑦]不可否认,传统戏剧作家有时也让剧中人物直接评述时间,《麦克白》中,洛斯在得知邓肯被谋杀的消息后叹道:“你看上天好象恼怒人类的行为,在向这流血的舞台发出恐吓。照钟点现在应该是白天了,可是黑夜的魔手却把那在天空中运行的明灯遮蔽得不露一丝光亮。难道黑夜已经统治一切,还是因为白昼不屑露面,所以在这应该有阳光吻遍大地的时候,地面上却被无边的黑暗所笼罩?”[⑧]在洛斯的口中,时间仍是具体的、现实的,尽管黑夜遮住白昼象征麦克白弑君纂位的罪恶。然而贝克特剧中的人物对时间所发出的议论已不单纯是具体的提示,同时含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在更深层次上对人的生存状态发出疑问,因而成为作者探讨的主题。
贝克特剧中的时间经常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舞台提示从不明确“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和日期:《等待戈多》初始于某一天的黄昏;《快乐的日子》发生在未知的正午时分;《最后一盘录音带》演现于“未来的一个深夜”……。贝克特剧中的人物也没有能力认准时间,在他们的思维里时间是模糊不定的。《等待戈多》中,爱斯特拉冈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或者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五?”[⑨]同样,他也记不清楚与弗拉季米尔的会面到底是在昨天,还是在更久以前。幸运儿认为自己的年龄可能是“十一”也可能是“六十”。在波卓的眼里,出生与死去是发生在“同一天、同一秒”的事。《快乐的日子》一剧中的温妮,每时每刻处在耀眼灯光的照射下,已失去了对时间的确切概念,只能空洞地重复着:“又是美妙的一天。”[⑩]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舞台时间,贝克特的剧本一方面晦涩难懂;另一方面,解除了舞台时间的限制,贝克特反而可以以虚代实,充分调动观众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使作品包容更多的艺术含量,同时也暗示了“生存状态的荒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
为了与循环的剧情相呼应,贝克特剧中的舞台时间也是不断循环、不断重复的。《等待戈多》的第一幕始于某一天的黄昏。第二幕的舞台提示只有简单的“第二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几个字。《残局》是独幕剧,不可能象《等待戈多》那样在幕与幕之间形成舞台时间的循环,但是在该剧中时间是由断断续续的片断组成的。每一轮片断的结束又是新一轮片断的开始,正如汉姆所说:“开始就是结束……时间的终点包含于开始之中……”。[12]
贝克特剧中的时间还是混乱的。传统剧中时间一般按年代顺序线性发展,过去的事件往往通过人物的回忆得以再现。这种再现的回忆有时会改变人物处境,引起人物之间的冲突,有时甚至导致人物命运的重大改变。中外名剧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玩偶之家》里,娜拉为给丈夫治病曾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这段往事的再现在娜拉夫妇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最终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在曹禺的《雷雨》中,鲁妈的回忆使周萍和四凤意识到他们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残酷的事实最终造成了三个年青人的惨死。贝克特的剧中当然也有人物回忆。《残局》里的老夫妇纳格和尼尔就曾回顾了他俩共骑一辆双人自行车户外郊游的美妙经历;《快乐的日子》里的温妮也时时回忆自己的一生……但是,贝克特剧中人物的回忆既不推剧情的的发展也不导致任何冲突。事实上,人物何时何地回忆过去以及为什么回忆过去显得无足轻重,回忆只是人物打发时间的手段之一。同时,贝克特通过人物混乱的回忆打破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顺叙、倒叙、插叙”的传统叙事模式,使舞台时间交错、回旋。在贝克特的剧中,回忆与现实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由现在到过去,由过去到现在或将来的突然转换使得贝克特剧中的时间显得混乱不清。《最后一盘录音带》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例子。该剧描写年逾六旬的克拉普在“未来”的一个深夜一面聆听自己三十年前的录音,一面为自己的现在录音以便留待将来再听。舞台上自始至终出现的只有克拉普一个人,他是通过与录音机里放出的声音的对话来完成全剧的。剧中,克拉普运用录音机使正在录制的自己现在的声音与他30年前录下的39岁时的声音交替出现,互相映衬。有时克拉普通过重放录音,使自己现在的声音与过去的声音融合起来,例如克拉普听着录音机里放出的声音:“今天我39了,健壮得——(他挪了挪身体,坐得更舒服些,把其中一只纸盒从桌子上碰掉下来,他咒骂着揿下停机键……然后把磁带倒到头,打开放音键,恢复原来的姿势)今天我39了,除了原来那些弱点,我健壮得很。”[12]有时,克拉普又通过一个动作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例如在“真难相信那时的我竟会是那么一个毛头小伙。那嗓音。基督啊!还有那抱负!(克拉普附和着磁带里那阵短暂的笑声)还有那决心(克拉普附和着磁带里那阵短暂的笑声)……以一声——(短促的笑)呼喊上帝的声音终止。(克拉普附和着磁带里那阵长时间的笑声)”[13]这一段磁带录音中,克拉普的笑使他现在以及30年以前对更早时的自我看法取得了一致。
Ⅱ.地点:模糊、抽象、充满象征意义
就表面来看,贝克特剧中的地点很少变动,完全符合亚理斯多德提出的“悲剧情节不应该同时在两个不同地点发生”的要求。然而,与模糊不清的时间一致,贝克特剧中的地点也同样是模糊不定的;同时它又是极其抽象,充满象征意义的。首先,在言语符号的表现上,无论是从舞台提示还是从人物对话中观众都无法得知贝克特剧作发生的具体地点。在贝克特的早期剧作中有时会出现表示某一地点的专有名词,例如克拉普在39岁生日时提到“至少在10年或12年以前……我想那时我仍然和比安卡一起住在凯德街”。[14]69岁生日时他又希望能“在晨霭中带着一条母狗再次驻足克罗干”。[15]但是,这样的名词既不是剧情发生的地点也无法向观众提供任何地点信息。其次,舞台上其它非言语因素的应用使得剧中地点更为扑溯迷离。传统戏剧中,即使不借助人物语言,观众也能从舞台布景、道具或演员服装等戏剧因素中推测出剧情发生的具体地点,然而贝克特剧中人物服装只起到遮蔽身体的自然作用而看不出任何民族、时代等社会特征。舞台布景的运用消除了舞台具体的空间感,使舞台显得荒诞离奇,给剧作笼上了非现实的气氛。贝克特的剧中舞台场景极其简约:《等待戈多》中的道具只有一棵树;《快乐的日子》的舞台场景是“一片晒枯的草地,中间形成山冈”;《残局》发生在几乎空无一物的室内,仅有的道具是一把轮椅、两只垃圾筒以及墙上反挂的一幅画;《来来往往》中只有一小块供演员表演的长方形空地……。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贝克特甚至抛弃了有形的物质道具而借用人体部分作为舞台布景。在《那时》一剧中,一个白胡子老人的头颅“被悬挂在舞台中央十英尺高的地方”聆听自己的声音,在《脚步》一剧里,舞台中央一束光下只有一双女人的脚在来回走动;在《不是我》中,全黑的舞台中央悬挂着一张嘴,里面传出一个老妇人喋喋不休的声音……。综上所述,贝克特的剧中,简约、抽象的舞台场景营造出虚幻不定的舞台空间,使贝克特的剧本产生了无限的象征意义。由舞台场景造成的直喻效果对观众和评论家而言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贝克特时空结构的具体运用
在艺术形式上贝克特有意淡化了语言的表意作用而强调了戏剧的直观因素,一切着眼于舞台效果。也就是说,贝克特通过运用舞台场景、灯光、声象效果等戏剧因素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使观众不再把上述戏剧因素当成可以忽略的辅助背景,而是迫使观众深入思考它们所包含的主题意义。具体说来,贝克特主要是通过以下手段来表现作品的时空结构的。
Ⅰ.布景和道具
乍看,贝克特剧中的舞台场景好似荒诞不经,但实际上却有所指向,寓意深长,在表现时空机制方面,布景和道具有时被用来暗示时间的循环不止。《等待戈多》中,第一幕里的枯树在第二幕中长出了几片绿叶。显然,这一道具的变化并不暗示希望的来临,因为直到剧本结束狄狄和戈戈苦苦等待的戈多仍然没有出现。道具的这一貌似忽然的变化实则暗示了流浪汉等待时间之长,也许从冬等到春。日复一日,狄狄和戈戈在同一地点等着戈多的到来,但每一天他们得到的除了失望以外还有一句始终未能兑现的口头许诺。对剧中人物而言,等待成了期望和失望相互交替的循环仪式。在无穷无尽、一成不变的等待中,时间失去了意义,它只是更长的等待、更多的折磨的代名词。类似的时间的循环也出现在《哑剧Ⅱ》中。舞台上一条长方形木板上摆放着ABC三只口袋,它们的排列顺序依次从CBA变成CAB,然后又变成CBA。如此的变换程序很容易使人想起一只永不停止来回摇晃的钟摆。
有时贝克特剧中的道具暗喻了空间的不确定。如《残局》中的舞台布景很难使观众得出确切的空间所在。有时,当汉姆宣称“这间房间以外是死亡”时,或者当克洛夫说透过窗子看到的只有“零”时,观众仿佛觉得这个舞台空间就是整个世界,剧中人物只能生活在这个狭小的舞台空间里;但有时抽象、简单的布景又使观众得出相反的结论,即这个舞台空间只是一个暂时的虚假空间,“一个空泛的洞穴”。[16]
也许贝克特剧中最能通过道具的运用体现时间概念的作品是《最后一盘录音带》。在这个剧中,贝克特首次把录音机和录音带作为道具,观众通过录音机里放出的声音窥见克拉普的过去经历,了解他的现在状况,得知他的未来计划。但是,克拉普对道具的随意使用打乱了时间顺序,使过去、现在融合在一起。此外,为了逃避现实的孤独,克拉普宁愿沉湎于回忆。剧中他三次聆听自己年青时泛舟湖上甜蜜而忧伤的爱情故事。这三次录音分别出现在剧本的中间、后半部分及结尾处。三次重复把整个剧本分割成两大部分,舞台时间也就在这两部分之间往复,从现在到过去、从过去到现在、再从现在到过去来回摇摆。
Ⅱ.灯光
在灯光的运用上贝克特经常采用明暗对比法,把舞台分成明暗两个空间,与其说如此的灯光效果可以使观众心无旁鹜地集中观看演员的表演,倒不如说是为了直喻主题。既然贝克特剧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反映人的孤独,那么舞台上的大片黑暗地带则成了表现人物孤独心理的最直接有效的直喻形式。为了逃避孤独,贝克特剧中的人物无路可走,只能局限于一小方光亮地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舞台上的照明地带成了人物唯一能生存、逗留的空间。《最后一盘录音带》的舞台提示表明“只有桌子和近旁笼罩在一束强烈的白色灯光下,舞台的其余部分则隐在黑暗中。”走进黑暗,克拉普与现实相联系,或喝酒,或吃香蕉,或取分类帐,或拿字典……;走出黑暗,克拉普倾听着录音带——他记忆的代用品,印证着以往对自我印象的评价。因此,舞台灯光不仅照亮了物体,更照亮了克拉普贮存于录音带中的自我意识。灯光在克拉普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在光亮中,克拉普可以重回过去,能够沉湎于以往的回忆;在黑暗里,克拉普则只能回到现实中,陷于孤独状态。由此,与其说克拉普是在光和影之间走动,还不如说他在过去与现实间穿梭。与《最后一盘录音带》相似,在《来来往往》中灯光也把舞台分成两部分。Flo,Vi和Ru这三位妇女中的每一位每一次从长椅一端走进黑暗,又从另一端进入光亮区,这来来回回的走动,以及相应的排坐顺序的依次变换,使观众清晰地看出时间的流逝。
除了采用明暗对比法之外,贝克特在有些剧中采用恒定不变、强烈耀眼的灯光使整个舞台笼罩在光亮下,例如在《快乐的日子》一剧中,整个舞台笼罩在一片刺眼的灯光下,仿佛是在永无止境的正午时分,只有间歇的铃声象征性地把时间分成白天和黑夜两部分。尽管温妮一再强调“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但眩目的灯光使时间胶着静止,“又一天”实际上只是温妮的想象。对于温妮来说,真正的快乐是能在黑暗中闭上眼睛不再忍受强光的刺激,不再被刺耳的铃声吵醒。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对温妮来说仍是奢望,只要灯光不灭,时间就静止不动,她就只能忍受这无情的现实。
在《呼吸》一剧中贝克特对灯光的运用又有所创新。贝克特通过光度的强弱变化模拟了人生历程。剧始,一簇微光照在舞台中央的垃圾堆上。几秒钟以后灯光渐亮直至最亮。5秒钟以后灯光渐弱,最后回到开始的状态。短暂的间歇以后灯光的变化模式又重新开始。这样,在全剧35秒钟内,贝克特向观众展示了人出生、发展、辉煌、衰弱、死亡的过程,演示了人类世代繁衍的行为。
三、时空机制的象征意义
文学作品无论采取何种写作方法,其本质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作家所理解的世界图景和人类状况。贝克特生活的20世纪是一个极其复杂矛盾的时代。一方面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和力量空前强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人的物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政治经济危机使世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社会震荡不定。二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不仅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激发、加深了种种社会矛盾。震惊之余,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怀疑日深,对社会的看法日益悲观,许多人产生了没落感伤、悲观厌世的情绪。与时代背景相呼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的批评更为激进。在文学领域,作家们不仅在道德意义上而且还在社会和人类生存的本质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怀疑和否定。自19世纪末期开始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帕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弗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现代文学开始向内转,更注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人的无意识领域,对人性的完整、人的存在价值和终极意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探索。
作为一个对时代变化高度敏感的作家,贝克特不能不对现代文明及其它危机作出反应,也不会不对人类生存的困境进行思考。事实上,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贝克特在作品中也试图回答“我是什么?”“时间和空间是什么?”“思维和物质是什么?”等问题。然而,理性思考的结果却只有失望。在贝克特看来,世界是荒诞的,人对生存其中的世界、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人在生活中丧失了自我,因此人的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为了表达非理性的内容,贝克特采纳了与之相应的混乱的艺术形式。在具体操作上,贝克特通过运用灯光、舞台布景等戏剧因素,以独特的时空结构模式为切入点,使舞台画面含蕴了丰富的思想和情感意义。恩格斯说过“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谬的事情。”[17]在贝克特的戏剧作品中,贝克特不再把时空结构当成戏剧内容的叙述者与承载者;恰恰相反,模糊、抽象的时空结构使得舞台上的一切都无法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网络显现出来。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也就显得虚幻、荒诞。同时,脱离了具体的时空情境,人物形象变得抽象、空洞。在贝克特的剧作中,人物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他们从遥远的过去走向未知的未来,完全失去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也失去了对自身背景和确切身份的认可。在如此混乱的世界里,人只能产生错位的感觉,也会因为寻找不到自我而产生痛苦,这正是贝克特要突出的主题。
笔者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时会出现曲折、坎坷,甚至出现倒退,但是发展和进步永远是历史的主流,决不能因为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而否认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贝克特对世界、对人类的悲观看法难免失之偏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贝克特的论调是悲观的,他笔下的世界没有未来,没有理想,到处充满了荒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贝克特对人类完全丧失了理想和信念。恰恰相反,在多年不懈的艺术实践中贝克特形成了日臻完善、独具一格的艺术形式。正是用这种反传统的艺术形式贝克特具象地反映了他深刻的思想内容,这种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写照是富有历史深度的。同时,在他全面否定的背后隐藏着最激进的追求,在凄如挽歌的低沉语调中,也大都激荡着对人类的救赎之情。正如辛格所说:“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悲观并非颓废,而是对救赎人类的一种强烈的热情。”[18]正由于贝克特勇敢地直面人类的不合理,并且采用新颖独特的形式把这种不合理表现出来,因此,1969年贝克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学院的吉耶洛致辞:“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19]这可以说是对贝克特剧作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最恰当的评价,准确抓住了贝克特在剧作结构上不断创新的艺术本质。
注释:
① 《荒诞说——从存在主义到荒诞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1992,第17页。
② 《论莎剧时空结构的基本模式与功能》,《外国文学研究》,武汉,1991年第一期,第42页。
③ 《荒诞派戏剧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80,第14页。
④ [11] Endgame,Fabre & Fabre,London,1970,第12、26页。
⑤ [12] [13] [14] [15] 《最后一盘录音带》,《国外文学》,1992年第4期,第190、191、192、192、197页。
⑥ ⑦ ⑩ "Happy Days",Grove Press,New York,1970,第12、8页。
⑧ 《麦克白》,《莎士比亚全集》,卷八,第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⑨ 《荒诞派戏剧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80,第12页。
[16] "Presence and Repetition in Beckett's Theatre",Cambridge 1989,第1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1页。
[18] [19] 《诺贝尔奖文学的现代人类文化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第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