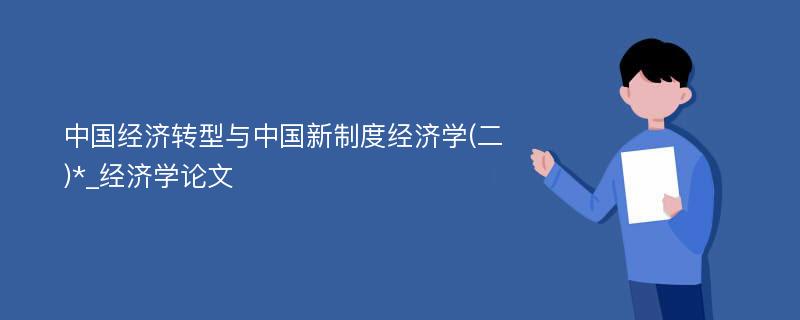
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之二论文,经济学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过渡过程中的企业、市场、国家及其它
3.1 改革主体的确认与过渡过程中政府的作用
在对渐进过程进行分析时,自然会考虑改革的主体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大多采用了林毅夫(1994)早期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即把制度变迁按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另一类是社会成员自发进行的诱致性变迁,前者来自于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强制地设计和推行某种制度安排;而后者是因为制度选择集合、技术、制度服务的需求及与其他制度安排的协调性的改变产生了制度不均衡,从而进一步产生了获利机会,人们为了利用这些获利机会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林的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是新制度经济学早期常用的制度供求分析框架的具体化,因为强制性变迁可视为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时的供给主导型变迁模式,而诱致性变迁可视为需求导向型变迁模式。后来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采用了这一说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至少在改革的某一段时期内是如此,一种原因在于政府的直接参与能够化解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和官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即所谓“诺思悖论”)(杨瑞龙,1993,1994,1997,1998);另一个原因在于财政压力迫使政府直接改变现存制度安排(张宇燕,何帆,1997);第三个原因在于改革的方向、速度、路径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改革过程中社会效益的增进是以核心领导者能获得更多的效用为前提的(胡汝银,1992)。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看法还体现在战略观上,如前所述,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4)等等。但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命题得不到经验的强有力支持,周其仁(1994)在全面剖析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时指出,改革前农村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导致农民的不满以及政府自身的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作局部退却,从而使农民有了一定的“局部退出权”(即政府对家庭经营和集体工副业的默认)。到“整个80年代,国家在确认了包产到户体制之后,农村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就是在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推动下承认农民自有资源的私产制度”(周其仁,1994)。裴小林(1999)也指出,改革前后一直不变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正好作为渐进平稳转轨的一个载体。也就是说,政府从主动介入农村管理转向只保留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而默认农民在此前提下的制度创新。因此,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实质上是农民与国家的一个长期交易过程,国家的财政压力和政治压力促使其消极退出,而不是主动的进行制度创新,即农民的退出权是农民自己争取来的,这意味着表面上的政府主导型改革实际上不过是政府对自发的民间改革的确认而已。张维迎(1995b)也证明, 国家与企业之间实际上是通过谈判来逐步界定双方的权利。陈凌(2000)则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地区经济绩效的差异问题,他认为,这种差异只能从制度的内生性和创新性的层面上来解释,即特定的地方性知识内生出特定的地方制度结构,同时又不断的以创新的形式加以扩展,整个过程实际上正好说明了哈耶克的自发的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改革的交易观而非主导观也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杨晓维(1996)的成都自发股票交易市场案例、陈郁(1996)对1986—90年间的上海股票交易的实证分析、孔径源(1996)的股份合作经济案例,杨瑞龙(1999)的江苏昆山自费经济开发区案例、黄少安(1999)广东三茂铁路公司案例、刘守英(1999)的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变迁个案、张军(1999)的温州民间金融机构案例及张曙光(1999)的山东惠民小市场案例等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同样一个道理,即一旦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退却,其他社会成员就有能力通过自发地制度创新来捕捉潜在的获利机会,而如果政府试图获得先动优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占有这些机会,就可能伤害自发的制度创新本身。换句话说,只有当政府和社会成员通过平等的交易来实现互惠性制度变迁时,才可能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内在统一,也即走上一条改革成本最小的路径。
3.2 经济组织的性质
突出过渡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其实是在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交易为基础的改革观在承认政府的作用的前提下,强调市场才是更基本的制度安排。市场表面上是人们交换的场所,实际上确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Hayek, 1988),市场化就是这种合作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所谓合作,就是要在承认每个人的平等的契约权利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制度规则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具有了立宪功能,即所有当事人都有权参与制度的形成(唐寿宁,1998a, 1998b), 这意味着合作秩序的形成与扩展是建立在所有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基础上。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强调的改革的交易观的本质,即这种观点突出了制度创新的一致同意基础,也相当于否认了单方供给制度的可能性。
从改革过程的实际经验看,作为规则的秩序的形成与政府的恰当定位有关。在联通公司案例中,盛洪(1999)发现,电信市场的竞争规则的形成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政府为了公正行使裁决功能,不得不停止直接介入电信市场,而转向依据规范的司法制度间接实施管制,另一个原因在于,企业间自发的市场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这些规范同时约束着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并可能最终被提炼成法律条文。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可以直接掠夺其它经济主体的利益,也可以通过间接引导形成与其它经济主体的合作格局。成功合作的秘诀“不在于政府积极地站在前面充当主角,制造市场,而在于紧紧追随个人的寻利行为,并沿着它的方向,根据它的需要,为其清障铺路,提供服务,给予保护,加以引导”(张曙光,1999)。如果政府试图扮演积极的角色,就可能损害合作秩序本身,例如,山东惠民政府大市场要灭民间小市场案例(张曙光,1999)、天津鸡蛋价格管制案例(陈宗胜,1999)及温州民间金融案例(张军,1999)等都证明,政府不恰当地把手伸向市场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当然,关于政府的消极作用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老话题,只不过中国的改革案例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已。从另一个角度看,改革过程中政府是否还有其它的作用?杨瑞龙(1999)和黄少安(1999)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在过渡过程中是相当活跃的,江苏昆山自费经济开发区的建立及广东三茂铁路公司的组建都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有关,在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假说中,地方政府是改革中期主要的制度创新主体。这似乎部分地否认了张曙光等人的结论。揭开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对地方政府的性质和行为本身的认识。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复杂关系类似于一个“大家庭”关系,其中中央扮演“父亲”,地方扮演“子女”,地方政府和企业一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这是两者功能重合的一面,两者的区别在于,地方政府还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而企业则是一个生产单位,因此,地方政府的许多行为已经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张曙光,1995)。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必须与当地的企业一起追求当地的经济增长,并和其它地方政府竞争,这种共同的利益关系把地方政府和企业、社区紧密相联,共同作为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力量。这种家庭结构在追求经济目标时相当于一种“M型”组织结构(Qian and-Xu,1994), 当出于某种原因中央退却时,地方政府便乘机填补空位,从而使得事实上的分权结构合法化,造成一种中国式的“经济联邦主义”。对地方政府来说,当地的经济增长已经不是副业,而是主要的工作,此时地方政府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个企业家,它把一个地方当作一个大企业,通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实现本地的发展(周业安,1998)。可见,正是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制度创新。
中央政府的被动和地方政府的主动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奔格局(樊纲等,1990),分权化及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客观后果是加速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但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后果具有两重性,它既可能促进又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这与每个地方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官员的能力有关。实际上,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建设在很多方面带来了不良后果,樊纲(1996)等人的经验研究显示,地方政府的非规范公共收入占总公共收入的一半以上,所谓“三乱”及官员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福利,所以才需要对政府恰当的定位。
除了对政府和市场的认识以外,国内的学者还就企业、家庭等经济组织的性质进行了讨论。企业的性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国内的争论只不过是国外争论的延续,焦点集中在对资本所有者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的确认(注:争论主要集中在崔之元(1995),张维迎(1996)、周其仁(1996)及杨瑞龙和周业安(1997)之间。张认为企业的本质是资本的所有权,而崔等人分别从公司法、人力资本及产权的经济性质等角度论证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本质。)。如果经济学是面向现实的,那么就不能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推导上,而是要回答为什么现实的企业经常表现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企业的契约性质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承认契约本质就必须承认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致同意,也就必须承认企业决策只是利益相关者各自的声音的汇集。不过,中国的各种企业制度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导致有个性的一面。张春和王一江(海闻,1997)通过对乡镇企业的性质的思考发现,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不是个人自由约定的结果,而是政府主导作用下的产物,因为乡镇政府拥有广泛的资源控制权,可以通过这种特权来获得产权。但是,从群众的角度看,这种产权的部分让渡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如同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只是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强权掠夺行为是如何产生和制约的?理论上仍不清楚,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以契约观为基础的国家理论。
除了企业等组织外,有关家庭的制度结构不能不分析,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家族色彩较浓厚。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家庭是一个产权主体(张曙光,1998)或是一个治理结构(陈凌,1998),如果一个社会的信息流以规范信息为主(注:所谓规范信息是指主要通过文字交流的书面的、正式的信息,反之则是非规范信息(陈凌,1998)。),那么市场和等级等标准治理结构就被广泛运用;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规范,信息的交流就只能依赖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此时家族式组织就是有效的。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中国的社会信息结构属于不规范型,那么有效的治理结构就是家族式组织和企业间交往形成的战略网络(陈凌,1998)。利用信息的规范程度来对经济组织作比较静态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常用方法,不过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动态的制度演进过程中,信息流是怎样决定演进路径的?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模型,也许可以模拟中国各种特殊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网络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作用不仅仅如此,以威廉姆逊为主导的新组织理论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假定前提,即正式的契约法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不存在摩擦,所以当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等导致契约不完全时,关系等隐契约或非正式契约安排就自动弥补契约法的不足,此即所谓“私了”机制解决关系契约问题更有效的结论的来源。但刘世定(1999)不完全同意上述结论,他认为经济活动是嵌入人际关系中展开的,在一定的人际关系背景下,签约前的人际关系存量会影响到交易特征;并且人际关系的多元性和对其控制的有限性也会带来它与文本合同的摩擦,这意味着同一种合同治理结构可以嵌入不同的关系结构,就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导致不同的结果。另外,关系结构对文本合同的影响是双重的,即可能改进合同法体系的不足,也可能带来合同的软化。刘的理论给我们带来了新视角,新制度经济学中往往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分开讨论,这种方法尽管比较方便,但也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而基于这个互动机制,我们就可以看出,先前的产权派和林毅夫等市场派及李稻葵等的产权模糊论的争论实际上是看到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前者注重正式合同关系,后者强调非正式合同关系,至于两者的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还不清楚。
四、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
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旧体制的性质及其向新体制过渡的过程的性质,但这不等于说国内的学者们就这些问题达成了共识,也不等于不研究与制度有关的其它问题。事实上,除了前述成果外,许多学者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只不过在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这面大旗下,有些观点、甚至方法论上都差异很大。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学者对依据本土改革经验的研究前景是乐观的,盛洪(1995)试图在中国传统和现代经济学精神的内在一致性上构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一个学派的形成可以立足于某个理论“内核”,然后发展出自己的“保护带”,比如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等;也可以直接对现有主流理论的“内核”的修正,比如交易成本经济学就是用有限理性代替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内核。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对本上改革经验的直观认识的结合上发展而来,整体上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些理论直接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在修正主流经济学的内核的基础上研究改革问题,比如早期的盛洪、刘世锦等人即是如此。有些理论则直接援用激励理论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对新古典范式的认同及必要的保护带的修正来看待改革中的各项制度,比如林毅夫、张军及张维迎等人的研究。还有一些理论采用了国外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有些涉及内核的修正,有些则仅仅涉及保护带的修正,如樊纲、唐寿宁等人的研究。有些理论则广泛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果,也涉及到对理论内核的修正,如后期的盛洪、樊纲、张曙光等人。另有一些理论混杂着新古典范式和交易成本经济学范式,如杨瑞龙等。不同范式的运用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中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一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是范式之争,而不是观点之争。
在方法论上,国内学者基本上达成了默契,就是认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只有张字燕、胡汝银、早期的樊纲等试图以利益集团为分析单位来说明改革中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实际上,政治经济的互动的背后可能是个人为了改变其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而作出的投资决策的结果(唐寿宁,1998),这意味着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可能会得到更本质的看法。方法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部均衡分析本身带来的,因为偏好等外生因素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可能是内生的,而这种互动关系必须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才可能理解(汪丁丁,1996)。如何建立中国的制度变迁一般均衡模型也许很有意义。
更重要的也许是,对改革现象的直观认识导致了一些学者认识到过程的重要性以及过渡过程中多重均衡存在的可能,这种自发的违背新古典理论内核的行为可能导致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可能与制度演进主义的内在精神相一致,也就是可能生长出一种演进主义的观点(注:汪丁丁(1994)、周业安(1998,2000)、陈凌(2000)已经试图把演进主义的一些原理运用进来。)。从制度演进论的角度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这就要求采用动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普遍采用的比较静态分析,并且在动态的演进过程中,可能出现多重均衡,即人们可能找不到最优的制度安排,但可能发现若干同样有效的次优安排,这已经为中国经济学者所强调。他们还认识到路径依赖非常重要,并自觉地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对改革过程带来的影响。制度的自然演进暗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事人在特定的交易环境中从事有利于自己的交易,这一过程本身可能内生出特定的制度安排(田国强,1996),这意味着把制度视为外生的变量是站不住脚的。制度的内生性还暗示,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卖际上要从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自愿交易的过程中去理解。在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可能非连续或离散的变化会发生(柯荣柱,1997),这种离散特征意味着一个渐进过程包含了僵持或倒退。当然,从一个较长时期看,制度的演进过程可以视为连续的,这种连续的变化来自个人知识差异性为基础的分工及制度知识的可遗传性。问题在于,制度的演进是不是必然导致效率的改进?诺思(1994)已经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回答了一项低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不过,还有其它一些原因,比如公共决策程序滥用于私人物品交易领域,导致不利的制度安排被选择(盛洪,1995)。但仅仅正式的制度安排是不够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隐含前提是等价关系(即契约关系),而现实的演进过程中经常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等价关系,此时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就非常重要(茅于轼,1998)。实际上,文化因素等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既可能带来制度“锁定”,也可能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
制度演进过程中,当事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新奥地利传统持消极的当事人观点,而新熊比特主义和凡勃伦传统又持积极的当事人观点,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在分析地方政府和社区成员的制度创新行为时,隐含的假定制度创新者是熊比特式的企业家,即制度变迁卖际上是一个制度企业家的制度创新过程(周业安, 1998),或是制度企业家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过程(张曙光,1999:4),并且制度变迁过程中,当事人的边干边学可以改变制度知识的分布,从而影响到变迁路径(陈郁,1996)。然而,这种熊比特式的分析会忽视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自然演化,也很难理清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更。对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
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现象做了广泛的研究,无论是对企业、市场及国家等专门的制度安排的性质,还是对制度创新和变迁过程的性质,我们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这些认识的逐步深化有助于中国今后若干年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但也应该看到,目前国内的研究水平与国外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差距,有些差距还很大,这一方面是国内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水平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所内含的弱点。中国的改革经验给本土的学者们提供了潜在的机会,我们在提高自身水平的同时,恰恰可能弥补主流理论的一些不足,进而有机会提高中国经济学家的声音,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派”。
注释:
*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杨瑞龙教授、唐寿宁博士、张曙光研究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谢意,但文中观点由本人负责。
**盛洪(1996)做了有关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理论综述,但从近几年的发展看,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经远远突破了过渡经济的研究范围,故必须从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全面把握近十年对制度的起源、制度创新、企业、市场和国家等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因此,所谓的“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特指中国经济学家(主要是大陆的或在大陆活动的经济学家)以中国的经济转轨为研究背景对制度问题的探索。虽然称其为一个流派还为时过早,但终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研究特色。
标签:经济学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