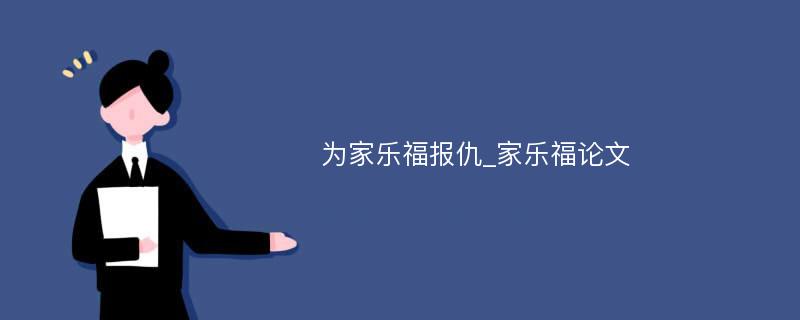
为家乐福“申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乐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01年开始,有关供货商与超级终端就“通路费”(包含进场费、上架费等各项需要交纳给零售商的费用)或是市场话语权之争日渐激烈。其中,每每有所征讨,几乎都能从中找到跨国零售业巨鳄家乐福的身影。
作为世界零售业榜上的亚军,作为受益于“通路费”而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已经赢利的外资零售商,家乐福并不乏有做主角的时候。
2003年6月,因不满对方在进场费上的盘剥和经营风险转嫁上的“无赖”,以洽洽、阿明、正林等知名炒货品牌为会员的上海妙货行业协会,发动了一次至今余温犹在的“上海炒货暴炒家乐福”事件,这再次将家乐福推向了中国供销矛盾舞台的中心。
到目前为止,虽然已以炒货企业恢复向家乐福供货,双方摒弃前嫌、握手言和而暂告谢幕,但对于关心供销关系,供货商生存和零售业发展的一些人士来讲,却再度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质疑国际惯例的意义何在?
家乐福在回应上海事件中的炒货协会时,曾一如既往的坚称收取通道费是国际惯例,认为进场费等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自己只不过是将这种方式移植到了中国。
而供货商们则认为,在家乐福刚刚进入上海的时候,收费并不高,有很多费用都是在供应商大量涌进的1998年之后才增加的。言下之意,“国际惯例”只不过是家乐福的傲慢托词,是它坐地起价的强盗式逻辑。
我们很难判断争执双方孰对孰错。但首先,供销双方在追逐最大化赢利上的钻营,是企业的天然使命;其次,具体通过何种途径达到最大化的赢利,这不单是一个企业经营理念上的问题(如以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为赢利途径的沃尔玛模式与家乐福向供货商盘剥利润的不同),更与当事双方在市场的生物链上处于什么样的环节、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有重大的关系。如此看来,在买方市场中,供货商(尤其是广大的中小供货商)受制于销售环节,向强势零售商“称臣进贡”也是符合逻辑的,更何况,家乐福还是强势零售商中的世界强者,即使仅以中国为限,其去年110亿元的销售额在国内零售业中也是凤毛麟角,难有比肩者了。
这为“国际惯例”做了很好的诠释。因为,所谓惯例往往指的就是游戏规则,所谓规则,除了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的法律法规外,就是强“欺”弱、大“吃”小的商业通则了。由此说来,所谓讲究双赢的商业伦理,在合作中就存在让步与妥协,就存在一方多赢一方少赢甚至不赢与亏输。在商业社会中,这只不过是强者“亲民的幌子”,是弱者“画饼充饥”的美好愿望。
如此而言,家乐福是在按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行事。而在一定程度上,供货商们强烈质疑家乐福的“国际惯例”,尽管能够博得媒体等力量对弱者的同情和呐喊助威,能够引起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供销问题关系的重视并早做立法、立规,能够促使一帮同病相怜的供货商们形成统一战线,平衡自己在与家乐福争执中的不均等势力,但就供货商们的根本出路来讲,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也就是说,只要供货商们还舍弃不了家乐福,就会存在一场天平难免倾斜的持久博弈,它们也就难免不受家乐福国际惯例的“制约”。除非供货商们能够在品牌上自强,或是在销售渠道上减少对家乐福等超级终端的依赖,或是供货商的联盟足够令家乐福屈服,也抑或是供货商们能够等到反家乐福赢利模式的大型零售商越来越多,并能够相对家乐福形成足够的竞争,真正威胁到其生存,使它不得不低下头来将所谓的“国际惯例”逐渐抛弃,并考虑如何与供货商形成更紧密的战略联盟关系。
盘剥供货商的原罪来自家乐福?
在沸沸扬扬的上海事件中,受尽“国际惯例”水涨船高、变本加厉之苦的供货商们的冤述引出了这样一个话题:正是家乐福将无休止地盘剥供货商,收取通道费、转嫁经营风险的赢利方式率先带进了中国,才导致了国内零售业的纷纷效尤。
按这种逻辑推断下去,家乐福就是国内零售商向供货商收取“通路费”的始作俑者,是致使“通路费”在国内零售业大行其道的原罪。但,这种论断站得住脚吗?家乐福是否真是第一家在中国境内收取进场费、上架费等各种通路费用的零售商,暂且无法考证,但将原罪的帽上盖在家乐福头上,却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的多数零售商,或主动或被动,大多都有急功近利的心态。面对日趋惨烈的竞争态势,在优化供应链、提高服务及经营管理水平、减耗增效,以及增强竞争能力的“内功”非一日可成的情况下,只得频频使出早已惯用的价格战。
但这无疑使进销差价所带来的“原始利润”消耗殆尽,而以“内功”赢利的途径又培育不成,妄图以自有品牌架起的赢利天空也没能撑得足够成熟。在此情况下,以那些或为生存,或为时不我待的圈地扩张,或为圈线,或目的兼具多者的超级终端们而言,还有什么比将手伸向上游的供货商来得更切实际呢?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先行赚取“通路利润”的家乐福,中国本土的零售商都不会让供货商的日子好过。更不用说在中国的商业文化中,也一向充斥着“此路是我开”和“雁过拔毛”的强盗逻辑。
由上可见,家乐福是始作俑者和原罪的观点很难站住脚。如若非要找出一个原罪,那也是零售商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原始竞争手段的擅用,以及供货商自身的孱弱。
这个道理,供货商们并非想不通,但是,它们为什么非要将盘剥供货商的原罪加在家乐福的头上呢?
下面的内容,或许能让我们一窥供货商们的复杂心态。
家乐福能弄垮一个行业?
为了说明家乐福是如何盘剥供货商的,上海炒货协会的成员们计算出了一组数据:家乐福的“通路费”占到了供应商在家乐福销售额的35%左右。正是因为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才导致了上海炒货行业协会最大的11家常务理事企业在家乐福卖场几乎全部亏损,其平均亏损率高达10%以上。亦由此,一些人表示出对家乐福等超级终端可能弄垮一个行业的担忧。
应该说,这种担忧是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但似乎又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姑且不说供销双方需要走到一起才能合作——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也不说拥有40个卖场的家乐福能在一个企业的销售额中占到多大的份量,就算是中途有人要撤伙,也可有法依法、有约依约的退出。
但就家乐福与炒货企业的这般供销关系,对许多供货商来说,却并非是说撤就撤这么简单的。
其一,由于缺乏合理的渠道规划和精耕细作,过于依赖大卖场销售能力等原因,许多供货商在大卖场的销售额通常都占到了其市场总销售额的45%-60%。这使供货商们很难割舍开那些一再做非份之想的大型零售商。就家乐福而言,其遍布全国约40个大卖场(含新近开业的杭州家乐福)也有着惊人的吐纳能力,这足以成为诸多供货商重点客户中的重点。如阿明瓜子、家乐福的销售贡献占到了其全国销量的4%左右。
其二,家乐福是供货商的“世界杯”,无论是展示宣传还是销售,抑或是通过家乐福这个跳板走向世界,其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对一些供货商来说,假如不置身其中,甚至意味着没有能够挤入主流渠道。
其三,家乐福只有一个,而可以取代自己的供货商却有很多。在销售渠道缺乏多元化支撑的情况下,退出家乐福的中小供货商们,岂不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抢占自己的市场份额?
其四,身陷其中,常年亏损,心有不甘。仍以出品阿明瓜子的三明公司为例,其产品在全国销量位列前茅,但就是在家乐福赚不到钱,进入家乐福6年间,投入2000多万元,换来的却是平均每年亏损100多万元。既然如此,三明公司为何不趁着“上海事件”退出家乐福呢?因为“前几年投入的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了”。
这些就是上海炒货行业协会成员为什么会由当初的集团撤货,到暂时停止供货,再到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胜利就恢复供货的主要原由。当然,其中的忿忿不平、骂骂咧咧、分分合合却也是难免的。
这就是矛盾的供货商:明知道自己是在“背着金子撵贼”,却仍要打得头破血流的前赴后继往里挤;明知道自己的渠道缺乏合理的多元化和精耕细作,却仍要高度依赖风险集中的大卖场,忽视了对中小终端的开拓和维护,以及其对差异化多元销售渠道的谋求与创建。
由此可见,即使一个行业真的因家乐福而垮,那也是“灭秦者秦也”!
说明了什么?
家乐福与炒货企业的供销纷争以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矛盾,除与其原本互为依存的伙伴关系和势强势弱的商业位置等有关外,其中还充斥着时下一些供销双方的心态问题。
如,家乐福们动辄就变本加厉地盘剥和以撤柜清场相威胁,而炒货协会及其它们的会员们也总以停止供货相反击,它们之间的相互倾轧,其间不乏浮躁。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新近成立的中国零售商专业委员会(又有称供货商委员会,是一个代替政府相关部门行使一些职能,意在规范供销行为,调解供销纠纷的组织,隶属中国商业联合会)的某君向我提及的一件逸事:该君向某供货商协会会长征求一些如何处理供销关系的意见,那位会长却对他讲:“我们500多家供货商能和零售商打架,你们能吗?”供销关系已经到了这份上,多少都能体现出供销双方目前的浮躁心态。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无论是供货商们,还是家乐福们,实则处在了一个是进而“临渊羡鱼”,还是退而“海阔天空”,又或者是向左走、向右走的十字路口。具体应该怎么走,则可能对双方在各自领域的竞争能力,以及今后双方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就单词“Carrefour”法文意为十字路口的家乐福来讲,是否应该调整自己的赢利理念,以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势成水火”的供货商们改变关系形成联盟,这更有可能影响到它在中国零售业及其世界零售业版图的格局。
标签:家乐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