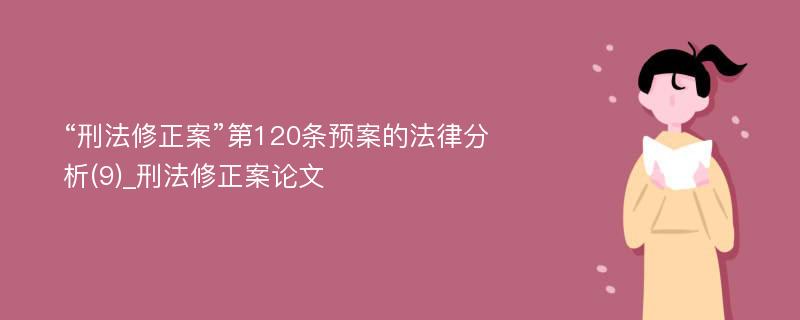
《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前置化规制的法理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正案论文,探析论文,法理论文,刑法论文,规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3-0041-13 近年来在我国连续发生的天安门金水桥、昆明和新疆火车站,以及乌鲁木齐早市爆炸事件,揭示出我国反恐怖局势骤然升级,以威胁无辜平民生命要挟国家,意图达到政治目的的恐怖活动呈现事件常态化、后果严重性的趋势。目前我国针对东突恐怖活动采取的反常态化的刑事前置化模式和非常态的刑事追责政策,都体现出新惩罚主义提倡的刑罚前置化的苗头。《刑法修正案(九)》将具体恐怖犯罪的预备或预备的预备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意味着将实行行为之前的预备或抽象危险行为与从事具体恐怖暴力的实行行为视作具有等价的违法和有责性。将前置行为与实行行为等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发法益保护前置化的正当性问题。支持前置化的论者认为强调法益保护的抽象化与前置化、严厉化,均是现代刑法的特征,①并通过处罚未遂犯、危险犯和预备犯等规范和加大处罚力度予以实现。②然而法益保护前置化因其天然的扩张性,很容易面临其特殊的刑事措施和严厉的立法取向与刑法谦抑性相背离,违反法治和人权保障的理念的质疑。本文将回溯我国反恐立法和司法历程,说明前置化规制的现实法律基础,旨在分析前置化规制背后的法治理念和根据。 一、反恐刑事规制立场的回视:立法突破与司法扩张 (一)反恐规制概况 1.立法特殊保护阶段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反恐决定》),规定了恐怖活动定义、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名单的认定主体、冻结程序等;2013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特殊侦查措施、辩护权的限制行使和诉讼参加人特殊保护等涉及反恐的特殊内容。 2.司法急速扩张阶段 2014年5月,我国公布实施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部门关于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对传播含有破坏民族团结、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内容的音视频的严重情形予以刑事追究。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于2014年9月9日联合出台《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不仅将制作、传播、发送、传递暴恐音视频行为扩张解释为犯罪,同时以类型化的方式将意图造成恐怖活动但尚未证实具有具体恐怖活动意图的行为入罪。如培训恐怖分子、持有或通过其他方式宣传带有恐怖极端思想等行为,分别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论处。然而,通过运用体系、文义等解释方法,尚难以将以上行为类型分别归入各罪。 3.立法探索调整阶段 《刑法修正案(九)》在沿袭《意见》入罪思路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扩张的几种行为类型单独立罪,以避免司法认定存在的类推解释之嫌。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宣扬、煽动类:以制作资料、散发资料、发布信息、当面讲授或音频视频、信息网络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煽动他人从事恐怖活动、参加恐怖组织;第二,阻碍法律实施类:利用极端思想煽动、强迫他人破坏法律实施;第三,持有、穿戴类: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强制他人穿戴宣扬涉恐服饰、标志的。 (二)不断趋向扩张的立法和司法立场 1.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等价性 回溯反恐立法与司法历程,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反恐法律框架愈加投射出扩张化、严厉化和前置化的规制理念。《反恐决定》将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以犯罪集团处理,意味着集团组织者对所有犯罪活动负责以及适当免除证实集团成员具体犯罪主观、客观内容的证明责任。《通告》显现出将观看、传播暴恐音视频等恐怖活动的预备或准备行为与恐怖实行行为等价的端倪。制作、传播、存储涉恐音视频制造了恐怖氛围,至少客观上起到了教唆、培训恐怖分子的作用,为恐怖犯罪创造条件,属于恐怖实行行为的预备。《意见》则更为激进和深化,将意图从事恐怖活动或以多种方式宣传极端、恐怖思想的行为定罪处罚。其蕴含的司法意旨是将煽动类犯罪的前置或准备行为规定为实行犯。宣扬、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行为与煽动本属于两个独立的行为。两者联系在于,一是前者往往为后者的实施创造条件(当意图从事恐怖活动时),而一旦解释后者包含前者则意味着扩张。二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与后者的预备行为不同的是,前者既可表现为与后者独立的前置行为,也可表现为与前后阶段无关的,与后者并行的行为。笔者认为,意图从事具体恐怖活动的前者,实质上应属于为预备行为实施的“准备”行为。③而尚未证实有从事恐怖活动意图的,则无法成为有目的的形式预备犯,而可能成为独立于实行行为的实质预备犯。《刑法修正案(九)》则统一将不需证实具有从事恐怖活动意图的宣扬恐怖思想的行为入罪,不失为立法层面上大的突破。 2.主观要素的推定 《意见》推进了“明知”证明规则与实体法的衔接。一是证明责任的转移。基于同案犯或其他证人证言证实“明知的”,由行为人承担证明责任,如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可推定“明知”。二是基于前行为推定本次行为的“明知”。曾因恐怖、宗教极端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处罚的,并不能对传播、传递做出合理解释的,认定为“明知”。《刑法修正案(九)》没有对证明“明知”作具体规定,但对明知他人犯罪的推定规则有所突破。将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的严重情形予以入罪。《刑法修正案(九)》在证明行为人“明知”方面仍需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由于“明知”属于证据采纳、事实认定方面的推定规则,其在尚未出台新解释之前,《意见》中对“明知”的推定规则应可予以参照。 二、反恐刑事规制的保护法益 (一)恐怖犯罪的行为及侵害法益 1.价值冲突目的和复合性动机 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暴力犯罪,制造出恐怖气氛,以达到某种政治、宗教或者其他社会目的,是恐怖主义犯罪区别于其他刑事犯罪的核心特征。其行为的反人类性和目的的特殊性,不仅投射出恐怖分子对无辜生命的蔑视,更反映出其对立与敌视维持社会运转的基本伦理秩序规范的态度。 (1)基于表达价值冲突的目的 行为无价值论基于规范违反说的立场界定不法内涵。根据行为无价值论,犯罪行为的不法内涵取决于犯罪行为本身的反规范性。④结果无价值论者罗克辛认为,“法益是在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者目标设定。……这个法益概念包含了已经被法(Recht)事先发现的状态以及同样由法才能创设的遵守规范的义务”。⑤可见,虽然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在刑法根据是法益还是规范上有争议,但都承认行为违反了规范。以东突为代表的恐怖分子即具有明显的与社会价值观根本对立、极端敌视法规范的特征。导致人们形成冲突的有“物质性原因”和“价值性原因”,即由于信仰或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相较可通过物质条件改善或阶层间的相互妥协而予以缓解的物质性冲突,价值性冲突却更危险和难以根治。当某个阶级或阶层对这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或者对这个社会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价值准则和制度体系产生了动摇,那么,它就会威胁到这个社会的“生存”。⑥这种基于道德、宗教或政治信仰,发生价值偏离的犯罪人,会对社会制度和法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怀疑、敌视、甚至是仇恨情绪。他们与社会整体对行为人行为的意义识别产生巨大背离,认为自己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是对抗不公平社会的正义行为,是值得被信仰和献身的高尚行为。对此类因信仰、价值偏差的犯罪。有学者认为属于价值性冲突犯罪,需要采取有别于一般刑事规范的手段才能得以抑制。⑦ (2)夹杂利他利己的复合性动机 分清不同行为人的目的和动机的出发点在于:因人身危险性的不同,在运用具体程序和判定行为人刑事责任承担时可有所区别,以更好地实现刑法的机能。目前我国恐怖活动呈现出组织性、长期性特征的,主要是打着宗教旗号、意图分裂国家进行恐怖活动的东突组织。其组织、领导、参加者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冲突犯罪人的特征。从我国对恐怖活动的定义来看,排除了出于个人目的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暴力犯罪,仅指有组织性、带有政治目的,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暴力犯罪。除英雄主义之外,不排除存在借助外来势力的资助和组织系统的扩散以企图实现个人对权力、物质欲望的动机。换句话说,既有完全价值冲突的犯罪人,也有无视社会法规范以实现社会目的和个人动机并存的犯罪人。 存在复杂动机的犯罪心理与一般犯罪心理并无太大差异,其反抗情绪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社会化管理对预防此类犯罪人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成长在闭塞、落后环境下的犯罪人往往易接受来自不良信息的诱导和迷信思想的蛊惑,如“死后上天堂即可有享不尽的美食等”诱惑性言语、被披着宗教外衣鼓吹所谓民族独立、分裂国家言语“洗脑”,认为通过恐怖活动可以实现个人享乐动机。然而,出于愚昧动机与信仰动机的犯罪人在行为危害性的犯罪成立要件方面并没有区别,只是量刑和程序上因不同的人身危险性而有所区别,且在社会管理政策上需有不同对待。原因是尽管出于愚昧动机,但对暴力恐怖活动及为以上行为创造条件、准备工具的行为性质和后果危害明知,对行为的后果如威胁个体生命安全、制造恐怖气氛以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后果明知。不管出于愚昧抑或信仰的动机,其明知的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具有构成相应犯罪要件的正当性。 2.侵害超个人法益的反人类行为 由于恐怖活动行为方式的残忍性、攻击目标的任意性和反社会的目的性,决定了其反人类的行为特性。其行为不仅造成不特定人群生命财产的损失,也造成了对社会基本秩序的不信赖感。人们对日常生活、伦理秩序能否保持稳定不再感到信任,而是时刻感受到身处破坏和威胁的不稳定状态。恐怖活动不仅破坏力强,其行为反复发生和难以根治是难解的问题。价值性冲突犯罪对社会的反抗精神已经根深蒂固,非用物质改善或一般价值观的灌输甚至保安处分措施能得以矫正。国际社会对因政治理念不同而采取的暴力行为,是否属于恐怖活动颇有争议,“但在任何情况下,……针对平民的攻击应视为恐怖主义罪行”。⑧当然学者也承认,当国家仅仅为威慑平民投降而以他们为轰炸目标时,……当它旨在恐吓更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臣服时,反恐本身也能够成为恐怖主义。⑨况且,从恐怖主义犯罪实际情况来看,不乏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支持、资助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甚至直接参与、实施恐怖活动的情形。如何应对、处理复杂的恐怖活动,不至于将中间层推向敌对势力,考验着各国立法者的智慧。 不可否认,以反恐名义针对平民的暴力也是恐怖主义,但却不是因此放任恐怖主义的理由。采取法定手段以克制理性的态度对恐怖主义进行规制,是承认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犯罪有别于传统犯罪这一基本事实的应有立场。恐怖主义是针对不特定无辜平民的生命,以达到威胁国家安全目的,其侵害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安全和整体社会秩序。由于价值型冲突犯罪人对社会制度的极端敌视甚至是仇视,而恐怖活动表现出的有组织性、危害后果反复发生的因素,严重威胁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根本违反了基本法规范和社会秩序。当社会综合治理措施和现有刑法体系在其面前无法完全发挥效能时,采取特定立法和司法立场具有必要性。 (二)恐怖犯罪前置化规制的保护法益 行为侵害的法益不仅包含物质性的保护对象,也包含精神化的保护对象(例如个人的名誉、自由、恐惧感等)。由于精神上的法益侵害可以通过被影响或者改变的对象呈现出来或者被具体化,所以能够以客观形式体现出来,进而能够被证明。⑩恐怖犯罪带来的不仅是暴力侵害结果或侵害结果的抽象危险,还直接带来严重的恐惧感和对社会产生的无秩序感等精神化危害。宣扬、存储类行为突出表现了以上精神化危害。之所以将精神化危害作为规制对象,是由于行为对具体暴恐行为起到教唆、煽动、传授的帮助作用。这些客观作用和可证明的对法规范的敌视能够将行为与暴恐实害展现出密切关联性,并显现出对暴恐实害的抽象危险。《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的行为因具备以上条件而予以前置规制。 从刑罚前置化的根据来看,不论结果无价值论者还是行为无价值论者,都承认行为侵害到保护法益,不同之处在于对违法根据的看法:行为最终侵害是法规范还是法益?外在表现为惩罚的是行为还是结果?两者都承认行为是具备刑事可罚性的前提,处罚的界限标准是危害行为与保护法益的关联性。区别在于,行为无价值论者坚持前置化行为已经能够证明行为人敌对法规范的主观因素也是前置化根据之一,进而合理限缩违法性的界限。尤其是在司法的定量与主观证明阶段,其限缩作用和谨慎态度将显得更为突出。 不论预备犯抑或危险犯的处罚依据都需遵照前置化规制的行为与危害后果关联性的原则。不可否认,预备或危险犯的行为与危害都是有距离的,“‘危害’的范畴被抽象危险犯的概念所延展,致使刑罚干预的危害结果包含了距离实害结果较为遥远的侵害,这就使得‘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出现了分离”。(11)但前置行为仍显现出了与法益侵害的联系性。从犯罪构造角度看,刑罚的轻重是按照行为与立法者想要避免的危害后果的距离远近以及严重性的大小逐级加量的。由于只要一着手实施实行行为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或许可以说前置化就是对实行行为的判断。(12) 体现恐怖、极端主义思想内容的物理载体在社会中宣扬,至少已经造成社会不特定大众的恐惧感,破坏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安定感和秩序感。利用暴恐音视频来宣扬恐怖主义、煽动恐怖活动的预备行为能够显现出侵害重大法益的抽象危险和敌视社会基本伦理秩序的主观态度。如制作暴力恐怖、极端宗教内容的行为客观上会对具体恐怖犯罪起到教唆或帮助作用,已经显现出侵害重大法益(如不特定人的生命、人身和整个社会秩序的安全)的抽象危险,也反映出行为人对社会基本伦理秩序的敌视。《刑法修正案(九)》拟制的预备犯罪一通过“宣扬”恐怖极端主义或“煽动”恐怖活动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中的“宣扬”和“煽动”行为应为客观条件而不是目的要素。只有从客观上起到宣扬恐怖极端主义、煽动恐怖活动的作用,且能够证明其主观敌对法规范时,才能显现出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以触动刑事处罚的神经元。 三、前置化规制的法理依据 (一)前置化规制的内在暗合:有待商榷的敌人刑法 否定对恐怖犯罪采取特定立法和法律适用立场的观点,其背后源头在于忽视现代刑法所面临的犯罪有别于传统犯罪这一基本事实。由于价值型冲突犯罪人对社会制度的极端敌视甚至是仇视,当今社会综合治理措施和普通刑法体系在其面前是无效用的规范和制度。采取特定立法和司法立场在应然和实然层面均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明晰、正当的特殊理论要比正当性缺乏、无制度约束的实务滥用要好的多。 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以其保护规范适用为出发点,主张将实施恐怖犯罪、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性犯罪以及其他危险犯罪的行为人视为敌人,不给予其市民对待。(13)讨论敌人刑法之前提是,不因“敌人”之敏感词汇,放弃理性辨识敌人刑法的机会,进而不加选择地接受市民刑法内部依然存在的非法治规制手段。除去异议颇大的人格体问题的争论,对恐怖犯罪采取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根据在理论来源方面会与主张对恐怖犯罪人采取特定刑事手段包括前置化规制、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等的“敌人刑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基于对全社会基本规则蔑视的特殊人群的行为造成超个人法益的严重侵害后果的危险状态,致使立法者有理由采取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措施。虽然由于敌人刑法的“敌人”与“敌人刑法”概念分别与主张人人平权和保障人权的法治国概念似乎存在对立,一提起敌人刑法的概念,面临的大多是质疑,(14)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敌人刑法越来越与现行的特殊刑法存在暗合之处。为了厘清似乎存在两者间的纠葛之处,需要识别敌人刑法争议的根源、匡正敌人刑法的误解并加以理性辨识,以完整认识前置化规制的法理基础和依据。 与敌人刑法相对的概念,是传统刑法认可的具有法律性的市民刑法。市民刑法又是与法治国相对称的概念。(15)明确敌人刑法和市民刑法的不同,可以防止施政者随意动用敌人刑法措施来对待市民犯罪。市民规范对市民犯罪人及未犯罪的普通市民均同样有效。所不同者仅仅在于,刑法规范的有效性之于犯罪的市民是现实的,而对于未犯罪的市民则是观念的。违反了市民刑法的市民犯罪人虽然破坏了社会规范的现实性,但是并不能通过剥夺其人格体的资格来恢复社会的同一性,市民犯罪人尚是社会定义的人格体。(16)但敌人刑法则不同,简而言之,市民刑法在于维护规范的效力,敌人刑法则是在抗制危险。(17)反对者声称敌人刑法缺乏法律性。但实际上敌人刑法是为了不破坏市民刑法。(18)它是将本不属于市民刑法精神所包含的内容,以较为规范的形式与市民刑法分列出来。因此敌人刑法不是一个理念,而已经是规范,具有法律性特征。在危险丛生的现代社会,与固守在既有的启蒙原则框架内不同,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大胆地承认了对启蒙原则的突破,这其实是在缩小恣意的敌人思维的规则领域,将游离或隐藏于我们法律体系的那部分敌人政治和敌人警务收编到法治国框架下来处理,从而减少这些散杂在我们法律体系中的敌人刑法可能带来的对法治国的破坏,这未尝不是一种维护法治国的方法。(19)也许也更能理解雅科布斯之所谓“一个清晰明确的敌人刑法,比起在整个刑法中四处混杂着敌人刑法的规定,以法治国的角度言之,是较少危险的”。(20) 1.围绕“敌人刑法”的争议 雅科布斯教授认为,在确定的犯罪领域中,将持续偏离法律而不再能提供认知性的最低保证的人定为非人格体,这也便是敌人。(21)支持者认为在承认现有法律体系缺陷的前提下,通过区分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市民刑法和敌人刑法,从而减少而不是消灭这种缺陷的四处蔓延,使法律体系严整清晰,同时也成为一种在风险社会中维护法治国的“以战止战”的必要方法。(22) 综合来看,反对敌人刑法的观点在应然层面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敌人刑法理论与法治国原则存在内容上的互斥性;二是循环论证问题。在实然层面有司法的任意性和程序保障缺失的担心,主张强调法治国的包容性,运用保安处分、抽象危险犯等概念预防、惩治恐怖犯罪。 2.匡正 (1)应然层面 第一,法治国的矛盾。反对者认为,敌人刑法最大的问题在于跟法治国的天然矛盾。对于Jakobs来说,刑法的目的不是法益保护,而是保护规范适用。从纯粹的规范角度来看,法规范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得到适用,规范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它必须被遵守。(23)规范违反说从来不否定犯罪行为侵害法益的属性,只是认为行为的根本属性是违反了规范。但反对者认为前提是规范本身具有可信任度,敌人刑法对敌人界定存在不明确性的致命伤。笔者认为,如果在国家主权论范畴内,观点没有疑问。但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国家就应该依照与之订立的契约来惩罚他。国家如何能够突然取消某人的成员资格,在与他订立契约之后否定他的订约能力,认为他不具备理解契约的能力,否定其法律人格?那是因为,恐怖行为是在有选择的情形下选择了背离整体社会价值的行为,故无法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其违反基本的法规范,对根本契约不仅不予以遵守,且行为已威胁到社会整体契约的存在,这时无法用一般法规范来惩治。而敌人刑法确实有防御危险的功用:通过限制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权利保障,取消刑讯逼供的禁止,可以高效率地控制危险源,避免对法益更大损害,维护基本社会规范。反对者认为,对犯罪分子或恐怖组织的培训教育,没有存在真正可罚性的行为,甚至连直接的未遂也不能得到证实,只是刚刚被计划。虽然恐怖组织的存在对社会是“弥散的威胁,潜在的不安全影响”,但在市民刑法体系内同样可以讨论对公共安宁、公共秩序或者对法和平的侵犯。市民刑法不以惩罚犯罪人的危险性为目的,而是要惩罚接下来发生的公共安全的侵犯,这只能表明在犯罪预备中“刑罚比例递减的前置化”。(24)然而敌人刑法惩罚的并不是对公共安全的侵犯,而是应被震慑且首先应该被排除的危险。犯罪行为的前置,并不是将对外部的破坏性犯罪化,而是通过把行为人内部状况解释成对法益的危险,从而将完全不存在问题的态度犯罪化。 第二,循环论证问题。反对者认为,敌人刑法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25)从规范学的角度考虑,循环论证是指概念之间的互相证明,它既不能产生新的内容,也不会排除旧的内容。但是通过动用刑罚,行为人的意义表达被否定,规范的标准性解释模式地位被巩固,社会的同一性被维持。在这个过程之中,既产生了新的对规范效力的证明,又排除了不合法的意义表达,怎么能说是循环论证呢?如果仍然理解为循环论证,法益论亦是一种循环论证。(26)正如说惩罚犯罪是为了保护法益,那么保护法益又是为了什么呢?规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也即维护保护法益。 同时,反对者对敌人刑法的三段论逻辑提出了质疑。反对者认为敌人刑法遵从三段论逻辑:大前提=法治国需要前提条件,小前提=当今西方法治国现实性前提条件之不存在或被动摇,结论=法治国在当今时代存在缺口,须为敌人刑法所补充。但其小前提就有疑问,逻辑推理结论不具有可靠性。(27)笔者认为这实际牵涉到实然层面,实然状况是现有刑法框架尚不能预防恐怖犯罪或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所以敌人刑法的逻辑小前提是具备的。具体论证将在实然层面予以论述。 (2)实然层面 一是法治国的困境。反对者认为,应对法治国体系下丑陋的裸露之处的办法并不一定要从法治国外衣之外另寻一块布料,建构一个新的体系,即所谓的敌人刑法。(28)而是通过增强法治国体系的包容性来解决棘手问题,如保安处分与改造处分领域,则敌人刑法的概念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危险性、习惯犯、危险消除等概念已经足够说明问题。笔者认为,现有保安处分所针对对象和防卫措施恐怕难以适用对社会基本规范敌视的人群,而危险犯的设定是新惩罚主义的重要表现,从我国立法层面看,现代刑法中保安处分的处罚对象是适用恶习的短期刑期或通过教育来感化的群体,但对于价值冲突类型犯罪并不适用,他们因内心的信仰,确信即使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也是为实现正义的手段,将其行为正当、甚至高尚化。从实体而言,现行法治国框架下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设定总是会受到诸如破坏罪刑法定、客观主义和破坏法益的指责和质疑。在抽象危险犯被严格限定的情形下还不能达到惩治和预防价值冲突类犯罪的目的。从程序而言,即使适度适用敌人刑法,实行特殊的证据、侦查规则和对辩护权限制等措施也是不能被现行法律框架所包容的。 反对敌人刑法理念的论者认为因偶发性的恐怖事件作为实然因素,运用敌人刑法并不能成功消除危险。原因在于这一功用也将被它本身自造的危险——在正常社会散布对社会成员资格性的怀疑,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市民而大大抵消。(29)然而,如果没有有别于现有法律框架的规范,在预备犯未被类型化的情形下,运用法律技术手段和抽象危险犯理论同样会面临行为样态的不明晰、破坏罪行法定原则的指责。恐怖犯罪破坏力极强,又具有偶发性,法益侵害的危险日趋迫切,但预防和压制犯罪颇有难度。如果不将处罚恐怖犯罪的特殊刑事政策常态化,恐不能压制和惩治日益猖獗的恐怖犯罪。实际上,雅科布斯认为敌人概念基本上具有保护性功能,消除其危险性。 3.前置化规制与敌人刑法的疏离 威胁人类安全、制造恐怖气氛的恐怖暴力违反了基本社会秩序要求,但不明确的刑事政策则更令人生畏。执行者不明确执行方向因而采取过于极端手段,也可能这些手段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作为实现其政治企图的工具,进而将部分无辜人群牵连,激发社会人员投入恐怖组织的怀抱,进而一同排斥、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如“911”后,无正当理论支撑下的非正当程序设置,致使不断面临实践中被滥用暴力逼供的指责,而美国也并没有因此得到证据方面的多少好处。故而,应以科学严格谨慎的理念作为反恐刑事政策和立法理念的指导,实现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立法和适用的明确化和稳定化,以切实实现与国际社会法治国理念、制度的契合。 (1)尚未成熟的“敌人刑法” “敌人刑法”理论同样存在可能的危险,一旦解读不当,国家与社会必双受其害。刑法应当是“带哨的皮鞭”。(30)一旦皮鞭上的哨子在理论上已经被缴械,皮鞭在实践中伤人就可能具有必然性。 首先,敌人的界定问题。一是非人格体的认定。虽然Jakobs认为敌人是通过行为举止、职业生涯或与组织的结合关系,“可推知地、持续回避了法”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别的如宗教或沐浴,对自由社会来说,他至少是当下不可教化的敌人,是公众之敌。通过提供确实可信的、对将来法忠诚的保证,重返市民状态的道路始终是开放的。对存在思想犯罪而尚未外化的人群冠之以非人格体,因而被市民社会隔离的做法而起的争议,Jakobs似乎并没有更明确的反驳之词。为敌人刑法辩驳的斯特凡·希克亦言,“将完全不存在问题的态度犯罪化,行为人刑法与法治国理念格格不入,也就是说行为与结果(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的关联太过疏离,距离太遥远的行为人也纳入”敌人范畴,是现行法治难以接受的。危险性的习惯犯也是不赞同的,Jakobs暂时只是在着重强调它的效力,且作为疑难问题而提出,他并没有去问及它的实施。其本人不是描述敌人刑法概念,或完全批评,而是在规范性使用它。(31)二是敌人范围的问题。因价值性冲突导致的其他犯罪,是行为人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之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实施的以杀人、放火等方式报复社会的行为。(32)从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第2条恐怖活动的定义来看,制造恐怖活动的目的是危害公共安全、制造恐慌以胁迫国家机关。对恐怖活动的定义排除了个人目的。雅科布斯界定敌人为“与现实社会对立的人”。但就我国对恐怖活动的定义来看,并未因动机的不同而作区分。如何看待对社会不满?是否要将物质利益的冲突纳入到敌人刑法范畴,将把反抗家庭暴力、索要工资、不满政府某项规定或者行政处理行为而产生的针对小范围内不特定人群的故意杀人等行为纳入恐怖主义范畴内。从主观来看,行为并不以制造社会恐慌、威胁国家机关为目的,仅是意图表达不满情绪,由于诉求没有合理疏通的渠道,渴望以极端方式引起重视,解决其诉求,采取的过于极端的暴力行为或传播企图实施暴力活动的信息,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恐慌情绪的,也适用与恐怖犯罪相关的罪名处罚。三是人格体回归社会问题。还有偶发性与一直对抗基本社会规范的区分问题。对于偶发性恐怖活动的行为人,如何认定其具有一直对基本法规范敌视的心理态度?如何认定偶发性就有一直敌视市民刑法的心态需要刑法考量,尤其对于没有将暴力恐怖行为发端于外在的情形,如仅观看、存储涉恐音视频或者基于对宗教理解有误,客观上破坏了法律实施的,是否具有从事恐怖活动的目的。敌人刑法似乎并没有将偶发性心理因素的行为人纳入敌人的范畴概念中。 其次,未明确暴力取证的界限。恐怖犯罪尤其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恐怖犯罪,是价值选择性犯罪。当暂时排除人权保障因素时,通过刑讯逼供来获得嫌疑人口供不见得能取得意想的效果。但现有法治国下的刑事程序要求控辩双方权利的平等。为保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弱势”一方的辩方,赋予辩方更多的个人自由方面的保障。但与其他犯罪不同的是,司法机关此刻面对的是强大、狡猾的恐怖犯罪集团整体力量和顽固的反人类个体,被赋予更多权利的辩方恐怕并不是处于“弱势”地位,有时反而更甚。当个体自由和社会安全产生严重对立时,如何取舍两者利益,是立法者必须迫切面对的问题。适当地限制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是平衡两者利益的应然选择。 (2)对敌人刑法理念审慎客观的考量 敌人刑法视域中的犯罪属于价值性冲突犯罪,即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实施诸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和因价值性冲突导致的其他犯罪。不可否认,在规范学层面,敌人刑法在设立目的和方向把握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合理性因素,且在功能层面,敌人刑法也符合了现实需求。但面对敌人刑法的不成熟以及现行法治国现状,尤其是我国正处于坚决纠正刑讯逼供的情势而言,全面接纳敌人刑法很有难处,但吸收其合理因素或概念以完善市民刑法是可行的。正确对待尚未完全成熟的敌人刑法的理性态度应是:一方面支持者通过规范教义和实证体验进行修正、明确敌人概念及超常规的刑事程序,吸收其合理因素以完善市民刑法中前置化规制的依据;另一方面基于司法任意使用和丧失人权保障的担心,需严格限制敌人刑法的适用,以预防冤假错案和保障最基本人权。 (二)前置化规制的现实契合:实质预备犯与抽象危险犯 从现实角度考量前置化规制的法理依据,首先面临以下问题:法律拟制的前置行为属于类型化的实质预备犯抑或抽象危险犯?解答此问题的意义在于通过讨论两者的区别,驳斥将恐怖犯罪一律划归为预备犯,进而排斥预备犯正当性的论说,而论证前置处罚的正当性及处罚边界。对《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前置化规制的行为,不免面临刑事处罚根据的质疑:从文义解释角度来看,难以将利用涉恐图书资料、音频及其他物品以宣扬恐怖、极端主义或煽动恐怖活动的行为归入恐怖犯罪的实行行为,将其理解为预备行为或预备的预备可能更具说服力。梁根林教授认为,该条之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实质是为其后预备实施的恐怖犯罪的预备行为。(33)那么将预备行为的再预备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视野的根据无非在于,行为与侵害法益的相关联性。具体而言,预备行为已经显现出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和敌视法规范的不法意志。至于行为性质问题,难以想象将预备行为理解为具体危险犯,其行为本身特质是否能够显现出足以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的客观现实性是存在疑问的,在造成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范畴内考量更具有合理性。 学界对预备犯超过应予处罚边界的质疑更多倾向于抽象危险犯。预备行为虽然是为了实行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尚未着手实行构成要件行为,既不能确切地表征行为人对法规范的违反与敌对意识,也不能自证行为人意图通过构成要件行为实现结果无价值。就预备犯的可罚性根据而言,有学者指出:“不管预备行为所可能侵害的法益有多么重要,在还没有办法确认一个人是否果真存在有不法意志的情况下就以刑罚相应,恐怕是对于人毫无节制的工具化。”(34)有学者认为预备犯有着难以确定行为起点和终点的困境,以及主观目的难以证明,使得其往往受到处罚边界存在模糊性、处罚依据存在非正当性的质疑。(35)也有学者认为预备犯与法治天然相悖,不具有类型化的限定性,很难确立预备行为统一的认定标准,而行为与结果之间出现分离的抽象危险犯则有一定优势。(36)从以上质疑可以看出,对涉恐行为确定刑罚前置化手段的归属亦是一种证明正当性的方式。 就抽象危险犯的特性而言,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将在社会一般观念上认为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类型化之后所规定的犯罪,就是抽象危险犯。”(37)大冢仁、山口厚、冈本胜等学者也持此观点。(38)德国学者Roxi认为:“抽象危险犯罪,是指一种典型的危险的举止行为被作为犯罪而处于刑罚之下,不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出现一种危险的结果。”就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而言,“行为对象的侵害不再是作为刑事可罚性的条件来要求的,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即根据这种行为所具有的客观或者主观倾向,是以损害一种法益为指向的”。(39)可见,行为的主客观与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间的关联性发挥着边界控制的功能作用。 就预备犯的根据而言,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对预备犯的处罚依据有不同看法。现在通行的二元论集合了两者观点,将法益侵害的结果和敌对法规范的主观因素相结合,认为当“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与实行行为有着内在的主客观联系,已经足以显现出其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并且明显违反正常社会生活规范,足以表征行为人敌对法规范、法秩序的不法意识,因而才能被界定为预备行为。这种目的论的限缩实质上起到了例外处罚预备犯的效果。(40)根据二元论的表述,预备行为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才能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第一,预备行为与法益侵害的联系;第二,预备行为要显现出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第三,预备行为可以证明行为人敌对法规范的主观因素。尽管两者同为刑罚前置化手段,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抽象危险犯与预备犯却在刑罚处罚界限上达到了相交点:预备行为的主客观要能体现出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 毋庸置疑的是,抽象危险犯与预备犯同为刑事前置化的手段,两者的分割界点并不明显。如果说预备犯有不具类型化的限定性,则抽象危险犯也并不具有天然类型化的特征。两者在本质上即违法根据是行为与法益的关联性上是一致的。预备犯发生在实害行为的前移阶段。抽象危险从根本上源于某些行为所具有的法益侵害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既是一个规范的或者说拟制的范畴,也是具有客观经验和科学法则作为支撑的。同为前置化手段的预备犯的处罚评价标准亦是行为与重大法益的关联性,只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包含法律拟制的行为)才能展现为规范违反性或法益侵害为内涵的客观不法。运用法律拟制技术与抽象危险犯原理,将具有法益侵害抽象危险因而具有刑事可罚性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了实施特定其他目的的犯罪行为,行为人只要故意实施了类型化的预备行为,均认为实现犯罪既遂。(41)继而,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载体的行为产生了煽动、组织具体恐怖犯罪的抽象危险,其侵害法益是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基本秩序,具备刑法例外干预的必要性。如将尚未证明预备行为与具体恐怖犯罪的主体有共谋或有独立从事具体恐怖活动目的预备行为,以形式预备犯归罪可能会有更多诸如主观目的难以证明和行为的非外化性特征方面的质疑,且也确实会造成某些司法困境。而对具备抽象危险性的预备行为进行必要的刑法干预,也满足了当代刑法干预必要性和谦抑性的双重要求。如国外立法把出入恐怖主义犯罪训练场所、对已知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公开播送恐怖分子的言论等规定为独立的犯罪。(42)可见,将具备抽象危险的实质预备犯予以刑事规制,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 四、余论:《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刑罚前置化的边界 只有从客观上起到宣扬恐怖极端主义、煽动恐怖活动的作用,且能够证明其主观敌对法规范时,才能显现出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以打开刑事处罚的门楣。《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前置化规制的处罚边界需要遵循行为是否显现出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和敌视法规范的原则。即使法律拟制的行为,也不宜一律作为恐怖犯罪的实行犯处罚,处罚边界的作用不可忽视。 《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新增了五种罪名,相应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如何适用是司法者当前迫切面临的问题。笔者以利用图书、涉恐音视频宣扬、煽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行为样态为例,拟进行浅显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新增了“以制作、散发资料、发布信息、当面讲授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和“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样态,从文义解释角度出发,制作音视频,通过网络或者散发、发布甚至是当面讲授、解释图书、音视频内容的行为是可以被制作、传播的行为方式所容纳的。因此,“利用暴恐音视频宣扬、煽动恐怖”的行为方式可以被制作、传播、传递和持有暴恐音视频行为所容纳。 对制作涉恐图书、音视频或其他物品的行为需要在量上加以限制,以显现出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状态:一是制作涉恐图书、音视频数量及次数。如考虑制作光盘的张数,录音、录像带盒数,图书数量,以制作DVD、VCD、CD母盘的张数作为定量标准。利用互联网制作恐怖信息并传播的,因其范围的不特定和影响力的不可控性,只要我国网民可接触、下载,以汉语或内容针对对象的语言传播,传播内容涉及民族问题、社会制度和国家安全的涉恐音视频、图文资料的,则不论次数、数量即可考虑入罪。二是被处理次数。如因制作涉恐图书、音视频被刑事处罚过,考虑到主观故意及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可不再考量次数和数量限制,予以治罪。另外,对于涉恐图书、音视频内容并未明显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仅有歪曲宗教、民族事件等事实内容,无法证明敌视法规范的主观内容,宣扬恐怖主义或煽动恐怖活动意图的事实不明的,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传播与制作涉恐图书、音视频及其他物品的行为样态表现不同,对保护法益的侵害程度存在些许差异。第一,就传播方式而言,传播在汉语中是一个联合结构的词,其中“播”多半是指“传播”,传具有“递、送、交、运、给、表达”等多种动态的意义。因此,不仅散发、传递、发送涉恐图书、音视频及其他物品的行为被“传播”这个大概念所涵盖,当面讲授内容的行为方式亦可被“传播”的文义内涵所包括。第二,就传播工具而言,传播的中间介质分为两种:“传统图书、标志物及音视频介质如VCD、CD”和“网站、网页、论坛、电子邮件、博客、微博、即时通讯工具、群组、聊天室、网络硬盘、网络电话、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网络应用服务”。传播的方式也可分为“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图书、音视频及其他物品”以及通过网络传递方式“登载、张贴、复制、发送、播放、演示”。由于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和迅速性,宣传内容的易得性,其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制作行为所侵害的保护法益程度无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甚于后者。同时,国内恐怖主义滋生在闭塞、落后的人文环境更适宜通过传统方式方法传播极端、恐怖思想。通过图书或CD、VCD等存储介质手法及其他标志物品宣传恐怖活动内容的,在构成要件的起刑考量上比照制作涉恐图书、音视频的定量因素考虑。根据传播次数、数量和是否被处理过来综合判断其主观恶意和情节轻重问题。在制作图书的册数,录音、录像带盒数,制作DVD、VCD、CD母盘张数,制作标识物品数量和被处理次数方面进行堵截处罚的考量。第三,就中介传输服务者而言,根据《意见》规定,网络传播有以下方式:建立、开办、经营、管理网站、网页、论坛、电子邮件、博客、微博、即时通讯工具、群组、聊天室、网络硬盘、网络电话、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网络应用服务。以上方式涵摄范围较广,为规制中介传输者提供了法律适用空间。反观《刑法修正案(九)》则没有明确规定。“通过音频视频、信息网络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煽动的”主体和行为样态是否包括犯罪主体为中介传输服务者及其传输行为呢?笔者认为,从立法意旨、处罚依据和反恐必要性来看,是可以包括中介传输者的。第四,就主观因素的考量来看,偶然散布涉恐图书或音视频,且图书、视频内容体现煽动、传授意图不明显的,排除行为人心理意志因素上还未达到希望或放任破坏社会秩序和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程度,而是出于好奇、出风头等动机,无法证明行为人有敌视法规范的主观内容的,不应纳入前置化规制。 非法持有涉恐图书、音视频及其他标识物的行为对保护法益的侵害不直接和明显,也难以证明主观故意,故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将更加审慎。《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规定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情节严重”的,才予以入罪。可见明知是涉恐图书、音视频及其他标识物予以存储的,不排除出于好奇的动机,行为人没有危害社会秩序、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目的的可能;且即使当行为人有恐怖活动目的,因为害怕或悔改情绪没有转发、传播,或参与恐怖活动实行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根据预备中止犯、未遂中止或准中止规则,作为刑罚减免理由,不予刑事处罚或减轻处罚。对于存储大量涉恐图书、音视频或其他物品,数量超出日常生活可理解范围,尚无其他证据证实其存储有正当理由的,应认为其有主观故意,或者经行政处理过,其主观恶意明显的,可予以前置化规制。 《刑法修正案(九)》第120条未明确将传递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行为作为行为样态。就毒品犯罪而言,从制作、传递到贩卖和持有都有独立罪名。参照以上规定,是否可以说明除共谋外,单纯传递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行为不构成犯罪呢?所谓单纯的传递行为,是指在明知被传递物品性质情形下,对被传递方无“煽动”或“传授”的意思联络、且与具体恐怖活动犯罪人无共谋下的传送行为,如光盘等介质的运输、传送。笔者认为,从立法目的和体系解释方法的角度,应将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而单纯的传递行为作为犯罪行为处理。所谓举重以明轻,“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予以入罪,传递行为并不比前者危害性轻。就具体适用而言,可将该行为纳入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行为样态更为妥当。明知是涉恐图书、音视频及其他物品而传递的行为,对恐怖活动的泛滥和实施有着加功作用,相对于制作、传播行为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是恐怖活动犯罪的边缘行为,在起刑考量上高于制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定性考量。传递是动态的、短期产生变化的持有状态,传统的持有是相对静止状态的持有,将其纳入非法持有的行为类型,具备“情节严重”情节才入罪,符合文义解释、立法本意和法理根据。 就“明知”的认定而言,参照毒品犯罪和《意见》的明知认定规则是司法解释出台前较为可行的操作办法。如结合其一贯表现,具体行为、程度、手段、事后态度以及年龄、认知和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等综合判断。再犯或曾被处理的,同案犯供认或证人指证的,行为人辩解不具有合理性的,依据其行为本身和认知程度,应可认定为明知。认定有罪需要符合证据规则,如果其他多名知情人陈述简单粗略,不能相互印证的,则不能定案。在证明力方面,应该是共犯或目击证人,而不是传来证据;就证明标准而言,不要求明确知道从事恐怖活动,而是知道、认识到、意识到行为性质及后果的“可能性”即可。 从立法扩张依据到司法适用阶段,不论所保护法益有多重要,立法者和司法者运用扩张解释甚至前置化手段规制预备行为,总不免面临违反刑法谦抑性、罪刑法定原则的质疑。扩张立法和理性限缩的技术运用考验着立法及司法者处理现实问题的智慧。同样,祛魅的手段和方式是否符合刑罚目的和刑法原则,也需要遵循立法原旨和理论根据的司法定量和证明规则来得以进一步实现。 注释: ①[日]生田胜义:《行为原理と刑事违法论》,信山社2002年版,第19页。 ②[日]高桥则夫:《刑法保护の早期化と刑法の界限》,载《法律时报》2002年第75卷第2号,第16页。 ③张明楷教授指出,由于犯罪预备是犯罪,而为了实施犯罪预备行为所进行的“准备”又不是犯罪预备,故应将“为了犯罪”理解为“为了实行犯罪”。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页。 ④参见[日]曾根威彦:《刑法学的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⑤[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⑥参见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7页。 ⑦参见姜涛:《价值性冲突犯罪及其立法策略展开》,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期,第8-12页。 ⑧《反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联合国文件A/59/894(2005)。 ⑨Richard Jackson,The Study of Terrorism after 11September 2001:Problems,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Political Studies Review,Vol.7,No.2,2009,pp.1171-1184. ⑩Tariana Vargas Pinto,Delitos de peligro abstracto y resultado,Editorial Aranzadi,SA,2007,p.92. (11)参见Bernard E.Harcout,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in Vol.90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 Criminology,pp.109-194. (12)Alejandro Kiss,El delito de peligro abstracto,Buenos Aires:Ad-hoc,2011,p.41. (13)Günther Jakobs,Kriminalisierung im Vorfeld einerRechtsgutsverletzung,ZsWt 97(1985),S.751-783. (14)从以下文献中可看出论者对敌人刑法否定的态度。刘仁文:《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第54-59页;王莹:《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第126-142页;闻志强:《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5期,第20-22页;万毅:《“敌人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国两制”立法模式质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81-83页。 (15)雅科布斯在《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中提出了市民刑法和敌人刑法这组对立的范畴。其后又发表《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恐怖主义分子作为法律上的人格体?》和《敌人刑法?——关于法律性条件的考察》集中论述他的敌人刑法理论。具体参见[德]雅科布斯:《行为责任刑法》,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以下。 (16)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第612页。 (17)许玉秀:《“刑事法之基础与界限”——洪福增教授纪念专辑》,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8页。 (18)林立:《由雅科布斯“仇敌刑法”之概念反省刑法“规范论”传统对抵抗国家暴力问题的局限性》,载台湾地区《政大法学评论》2004年第81期,第34页。 (19)参见何庆仁:《对话敌人刑法》,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7期,第69页。 (20)参见蔡桂生:《敌人刑法的思与辩》,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第608-609页。 (21)参见前引(15)雅科布斯书,第39页。 (22)转引自前引(20),第163页。Vg.lManuelCancioMeliá,Feind "strafrecht"? ZSWt 117(2005),S.268; Jochen Bung,FeindstrafrechtalsTheorie derNormgeltung und derPerson,HRRS 2/2006,S.63. (23)Jakobs,Feindstrafrecht?—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Bedingungen von Rechtlichkeit,HRRS 2006/8 (24)参见[德]斯特凡·希克:《作为调节性观念的敌人刑法》,谭淦译,载《刑事法评论》(第35卷)2014年第2期,第54- 55页。 (25)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0页。 (26)参见前引(19),第97页。 (27)参见前引(14)王莹文,第137页。 (28)参见Greco,Ueber das so genannte Feindstrafrecht,GA 2006,S.109. (29)参见前引(14)王莹文,第140页。 (30)[法]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31)参见前引(24),第52-53页。 (32)参见前引⑦,第6页。 (33)参见梁根林:《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困境与突围——〈刑法〉第22条的解读与重构》,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175页。 (34)参见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35)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维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王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36)参见王永茜:《论现代刑法扩张的新手段——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和刑事处罚的前置化》,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6期,第127-129页。 (37)[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38)[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39)Kratzsch,GA1989,56.转引自前引⑤,第18页。 (40)结果无价值的一元论立足于法益侵害或法益侵害危险的犯罪结果对行为进行不法评价,只要预备行为对实行行为内在的主客观联系已经足以显现出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的,应予以刑事处罚。对于尚未显现出对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的预备行为,则应排除在刑事处罚之外。一元行为无价值论则更强调通过行为人对法规范与法秩序的敌对意识对行为进行不法评价。将那些明显违反正常社会生活规范、足以表征行为人敌对法规范、法秩序,并与实行行为有着内在的主客观联系的,为犯罪的实行创造了便利条件的行为界定为刑法处罚的预备行为。参见前引(34)。 (41)高巍:《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及正当性基础》,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第73页。 (42)姜涛:《恐怖主义犯罪:理论界定与应对策略》,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81页。标签:刑法修正案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法律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冲突规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