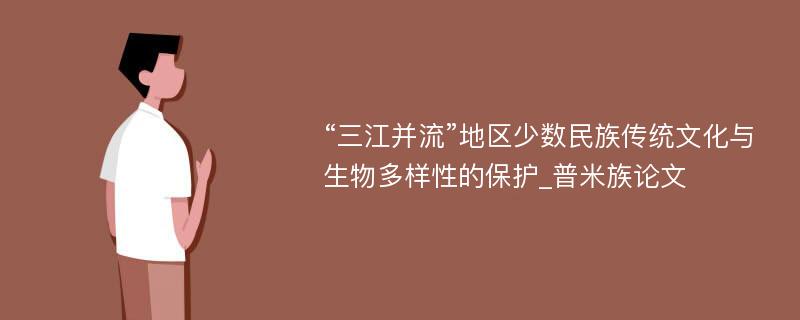
“三江并流”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生物多样性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13(2004)02-0042-06
2003年7月,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表决通过将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一地区,确实是一块神秘的土地,它独有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早已引起世人的关注。滇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有着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其中与自然、地理的关系特别密切。同样,生物多样性也与自然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复杂的地形、地貌、气候,滇西北动植物世界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因此可以说,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滇西北大地上诞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谁也离不开谁,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共同维护滇西北的生态平衡。研究两者的关系,分析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正负面影响,进而探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对策,对于保护滇西北生态环境,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生产方式——大自然,我们的工具
当我们考察传统文化对生态的正面影响时,着眼点是从传统的生产方式中剥离出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居住在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的少数民族,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对千百年丰富的实践认真思考,总结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以此指导自己的生产活动。
1.粮林混作,土地轮歇,平衡生态环境
独龙、怒、傈僳、白(勒墨人)等民族属于生产方式较为原始的民族,长期刀耕火种,年年砍树开荒,对森林形成威胁。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些民族的聚居区生态环境并未恶化,独龙江等地至今仍保持较高的森林覆盖率,实为一个奇迹。奥秘何在?在于实行一种粮食作物轮歇地上种水冬瓜树(学名桤木)、漆树的林粮间作和休耕管理方式。由于砍烧大片森林,刀耕火种的土地第一年肥力足,但以后逐年锐减,更带来水土流失,威胁人居环境。人们通过实践认识到,在轮歇地上种水瓜冬树、漆树等,可以增强地力、恢复生态。
以独龙族为例,长期以来喜种水冬瓜树、漆棕、桃树、李树、龙竹、金竹等树种,其中水冬瓜树的面积最大,数量最多。每当春季来临,他们就到山中和河滩采集水冬瓜树苗,背回村放置入水沟或水田中,清明前后再移栽到轮歇地中。开出的荒地,第一年砍树烧光后,灰烬多、肥效高,种植产量较高的玉米;第二年肥力减退,只能种苦荞,同时间种水冬瓜树,形成粮林混作系统;第三年在水冬瓜树苗间再种一年小米或稗子;第四年补种水冬瓜树苗后便不再种粮食,土地进入丢荒地闲期。5年以后,水冬瓜树高可达8米,直径可达15厘米,新一轮的刀耕火种又可以进行。独龙族大量种植水冬瓜树后,克服了刀耕火种的弊端,制止了水土流失,保护了独龙江一带的生态环境。
2.梯田系统,保持水土,保护森林
刀耕火种农业在滇西北仅存于小部分地区,绝大多数地区早已固定耕地,停止轮歇,停止砍树烧荒,由原始农业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在山区,耕地固定之后,如果停留在坡地种植方式阶段,仍旧不利于水土保持,不利于生物多样的保护。在千百年的山区开发中,滇西北的白、纳西、彝等民族,建立了一套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梯田农业系统。他们采取种植梯田这一农耕方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在不断满足日益提高的人类生活需求的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在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和它们大大小小支流的河谷地带及附近山地,在碧罗雪山、怒山、云岭、横断山的千沟万壑中,各民族都开辟出众多的梯田。
一般是先将荒坡辟为台地,种植旱地作物。几年后,土地慢慢熟化;同时,开挖沟渠,从远处引来山泉,把台地改为梯田。在山区造梯田,田埂必须保证不渗漏田水,因此田埂坚固耐用。每年要铲修田埂一次,防止老鼠打洞,避免杂草丛生。在高山处,山地陡峭,梯田的田埂既高且厚,不易坍塌;低山处,坡度和缓,田埂虽然矮一些、薄一些,依旧能保住水土。以梯田、水源、水沟为主构成的梯田农业,与滇西北山区自然生态构成一个和谐的系统。
3.合理用地,谨慎狩猎
根据立体地形、立体气候,各民族充分发挥自然优势,合理利用土地,为保持生物多样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高海拔地区,如迪庆藏族自治州,普遍种植的粮食是耐寒、热量高、营养丰富的青稞以及高原经济作物。高山草甸牧场特有的优良牧草,虽然看似矮小,但牦牛吃了以后产奶质量大提高,这些牧草受到藏族牧民的保护。在中海拔地区的荒山坡地,玉米、荞麦、小麦、红薯、马铃薯、旱谷、杂豆以及桃、李等果树广为种植。而在下半山和河谷平坝地区,水稻成为粮食作物的当家品,甘蔗、芭蕉等亚热带水果也在一些地区生长。这种合理利用土地、气候条件而形成的立体农业系统,实质上也是一种生态农业。
狩猎在滇西北山地民族中是一项传统的生产活动。在历史上很长时期,狩猎获得的食物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动物蛋白。但并非如有的人想像的,为了获得更多的猎物,滇西北民族滥捕滥猎。独龙族的生产水平不高,狩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有着比许多民族更重要的地位。但比起那些生产更发达、工具更先进的贪婪的人们来,独龙族对狩猎的“适度”有着超常的理智和清醒的认识。他们向动物界索取食物,但绝不过分,绝不做竭泽而渔、伤天害理的事,在狩猎上采取一种十分克制的方式。
在迪庆高原,藏族佛教寺院周围十几里的山林中,不准砍树狩猎。因此,佛寺周围林木繁茂,鸟兽齐乐。野兽出没,伤及附近农民的庄稼,怎么办?也不准猎杀野兽,而是由寺中僧人带领周围村寨居民,每晚在村边燃起篝火,驱赶野兽。老熊来偷吃青稞,也只准敲锣打鼓惊吓,不得用枪打;这样做,既保护了庄稼,又不伤害野兽。还有,人们相信:“谁家下扣子捕猎鸟兽,这家人几代都富不起来,寿延短,还会出残疾人。”因此,杀伤力强的猎枪和钢丝扣禁止使用,林中鸟兽受到的威胁大大减小。以上狩猎方式,反映了藏族和独龙族的思想观念。
总之,粮林混作,土地轮歇的耕作制度,梯田农业系统,“适度”的狩猎方式,都渗透着滇西北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必须建立和谐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朴素的,又是深刻的。
二、生活习俗——大自然,我们的朋友
滇西北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上形成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凝聚了他们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进程的经验和智慧;其中包含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的丰富知识。普米族说:“普米族是森林的朋友。”十分形象地表明普米族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比起把大自然作为工具的认识,把大自然作为朋友就更深入了。
1.对野生植物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居住在滇西北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小凉山等地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文化科学水平也比较低。但是他们一代一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以勤劳的双手开发山区,以智慧的头脑认识自然,积累了合理利用和保护野生植物的丰富知识。
食物利用。这一带一些地区从事原始农业,粮食不够吃。森林中丰富植物资源,为他们补充了食物之不足。他们从切身体验中懂得,森林是水之源,也是食物之源。
药物利用。在缺少现代医疗条件的年代,各民族只能向大自然求救,到山林中采集草药治病,由此而积累了丰富的药用植物知识。药用植物大量生长于森林中,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药用植物,就是保护人类的健康。这一经验,强化了各民族保护森林的意识。
日常生活品利用。靠山吃山,也靠山用山,各民族广泛利用山间草木:炊爨的能源是薪柴和杂草,起房盖屋用松树,烹饪调味用野花椒、大花八角、清香木,造纸用各种纤维植物,染制土布用染料植物,编织生活生产器具用竹、藤等植物,漆树籽榨出的漆油,更是怒江流域傈僳族、怒族、勒墨人的食用油重要来源,是妇女“坐月子”期间的重要补品。山村经济收入的来源也主要是靠种植或采集野生植物。他们出售药材、生漆、漆油等得到钱,再购回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农具。可以说,各民族的生活须臾离不开大自然造就的野生植物。只有在利用它的时候,同时保护它们,才能保证生活的正常进行。
植物对于各民族的生存意义重大,人们已经不满足被动利用野生植物,而是主动地保护和发展野生植物,这就形成各民族热爱种树的习惯。普米族除了保护好大大小小山头的森林以外,更喜欢在村前村后大种核桃。在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漆树广泛种植。最为突出的成就是种植油桐。20世纪80年代中期,怒江州福贡县种植65969亩油桐,成为云南西部河谷油桐生产基地。当人们在陡峭的山坡大量开荒种粮,怒江州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时,油桐的大规模种植,无疑使生态破坏的趋势减缓了。
2.对生存环境的巧妙适应和营造
滇西北地理复杂,从河谷到山顶形成立体气候带。“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山谷或坝子是亚热带气候,往山上去,依次出现暖温带、温带、寒带;或者说,在河谷一带和坝子里已是夏日炎炎,在中山区还是温暖的春天和凉爽的秋天,而在高山区,则是冰雪不化的冬天。
高海拔地区,气候苦寒,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低;不少地方阴冷潮湿,不适宜于人生活。低海拔地区,气候炎热,虫蛇出没,疾病流行,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这里显然不具备良好的人居环境。而中海拔地区,即河谷两岸的中山区和海拔与此相当的坝区,气候冬暖夏凉,四季如春,宜于人居。由此上山可猎获副食,采集野生植物,下山可以开辟梯田梯地,是理想的居住地。在怒江峡谷的福贡、泸水等县,傈僳族、怒族、勒墨人的村寨绝大多数建在中山区的缓坡地带。村寨之上是森林,那里有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及各种野生植物;村寨之下是旱地,也有少量梯田,那里生长着人们安身立命的粮食。村寨居中,下可以种地栽秧,上可以管护森林,保护水源,采集野菜,猎获野物,十分方便;同时,村寨避开了河谷的炎热和高山的苦寒,减少了疾病。由于山高谷深,田地分散,为节约路途的时间和体力耗费,这一带的人家居住较为分散,一个村的100多户人家分散在若干处山坡上,这既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管理、守护,也有利于山林的管理和保护。
3.对民居村镇的精心设计和建构
民居建筑和城镇的布局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各地不同的地形、土壤、气候对各民族民居建筑、城镇布局、结构造型等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建筑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在建筑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这是适应自然;观风察雨,合理结构,这是适应自然;依山顺势,布局城镇,这也是适应自然。更何况为了生活的需要、村落的安全,必须对水源保护、对山林礼敬,这已成为千百年的传统。
在怒江流域,两岸群山陡峭,难以寻觅适应建盖房屋的平地,利用和扩大使用空间成为生活中的大事。世居这一地区的傈僳、怒等民族在建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千脚落地”房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这种架空楼居式的“千脚落地”房,是干栏式建筑中的一种。由于支撑楼房的底层木柱间距密、数量多,密如蛛网,有的多达160根,所以称为“千脚落地”。这类民居顺坡修建,对原地表不挖土填方,仅依靠立柱的高度将楼面调节水平。民居的构件主要用竹篾或藤条绑扎,或用树杈作支点。楼面以上的墙体用横、竖木杆绑扎成网式承重骨架,内墙以竹席围扎而成。屋顶为悬山式茅草顶或木板顶。为了增加户外面积,傈僳族、怒族还利用悬挑扩大空间,增建阁楼、抱厦。人们使用住房时很注意保护,以延长住房的寿命,从而节约了大量的建房用材。在贡山县丙中洛乡茶腊村,怒族同胞充分利用山区地形,建盖了一幢幢高低不同的“千脚落地”房。它们以淳朴、简明的外观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更以这些凝聚怒族智慧的民居建筑与村后的崇山峻岭和村前万古长流的怒江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迪庆州藏族民居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种是德钦县的“碉楼”,通常是内院回廊形式,二层或三层楼房。房屋的朝向主要背山面水,视野开阔;或是向东、向南,力求阳光充足;西面和北面不开窗或开小窗,以防寒风袭击。民居多为独院式,由居室、贮藏间、畜厩和外廊组成;人畜分层,外廊晾晒衣物或作睡眠起居之用;房屋的平顶是在木梁上铺木楞,其上再铺柴草和粘土,拍打严实,防雨防寒效果好,还可以用来晾晒食物、柴草、衣被,进行家务劳动,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和阳光。建筑材料主要是土木、碎石,就地取材,十分方便。整座民居厚重、朴实。白色的墙、深灰色的门窗、屋顶的平台和村寨中浓绿的古树,与蓝天、白云和远处直插云霄的雪山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水磨房建筑是滇西普米、怒、傈僳等民族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一大创造。在崇山峻岭流下的溪水边,人们挖一个有进出口的大坑,坑边用条石砌好,中心竖一根螺旋柱,柱上设一轮木片做的螺旋桨,螺旋桨的正面水渠口安一条木水槽。中心柱上方建一间盖有木顶的木楞房,并在中心柱顶格部架一层楼板,装置两盘石磨。溪水引入坑后直冲螺旋桨,带动中心柱旋转,再带动石磨转动。磨的上方挂一个装粮食的竹篾漏斗,斗口对准磨眼。磨粮食时,漏斗中的粮食随着水磨的振动缓缓流进磨眼,磨成面粉。在怒江旁的茶腊村,怒族、傈僳族同胞充分利用溪水落差形成的势能,连盖五个梯级水磨房,加工粮食。这样的水磨在怒江两岸的湍急溪流上处处可见。它们节约能源、节约劳力,不污染环境,又方便了群众的生活,更为大自然画面上增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观。
4.对婴儿少年的习惯命名和更名
婴儿的命名和少年的更名是各民族人生中的大事,如何命名、更名,是在各民族的传统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兰坪县的普米族是一个以“森林之友”著称的民族,他们对婴儿的命名和对少年的更名,蕴含了这个民族对动物、植物崇敬的传统观念。
普米族初生婴儿请长辈亲属或族内德高望重的人用普米族语取一个“乳名”,到上小学时请教师或外地学者用汉语取一个“学名”。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期体弱多病、发育不良,需要用普米族语更名一次。无论是取“乳名”,还是成长时更名,普米族都习惯用动植物的名称,如“夸信祖”(栗树)、“新信祖”(青松)、“查尼祖”(野猪)、“翁祖”(老熊)、“兹珠祖”(山鹿)、“斯坦”(麂子)、“此祖”(小狗)、“行祖”(小树)、“酿伴”(小平角牛)等。这样的命名有以下含义:(1)用动物命名,是希望孩子长大后,像牛一样勤劳,像熊一样勇武,像鹿一样灵巧,像狗一样忠诚,像麂一样迅速。在普米人眼里,各种动物都有优点,都值得学习,不能轻易捕猎。(2)普米族相信,树能保佑孩子平安。每个孩子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由父母带着,到林中拜祭一棵树(常常是四季常青、质地坚硬的栗树和松树),向它献上素食和酒,求它保佑孩子平安,并用这棵树的名称作为自己的乳名。因此,“夸信祖”(栗树)、“新信祖”(青松)就成了普米族男孩的通用名。孩子们拜祭过的树,全村人都知道,以后任何人不能去砍,也不能在附近烧火。这无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5.对死者后事的节俭安排
滇西北各民族对大自然的适应、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观念,不仅反映在生命诞生后的拜祭树木,以动植物名称为“乳名”的人生礼仪上,也反映在人死后的丧葬习俗中。当经历几十年风风雨雨,走完生命历程后,很多民族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大自然走来,也要向大自然回归。此时,不应破坏自然,而应该加倍保护自然;不应该厚葬,而应该节俭,避免破费财产、土地和森林。
德钦县的藏族丧葬中有着丰富的适应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的意蕴。在冬天有人亡故,可根据占卜择定的日期对尸体进行火葬或天葬。如果在夏季,则不行火葬,因为人们认为火葬会引起气候突变,影响农作物收成;也不行天葬,因为鹫鹰此季节不会光临村寨附近。夏季的丧葬采用水葬或暂时土葬,待冬季再挖出尸体火化。这样,通过火葬、天葬、水葬,就不占用坟地,保持环境原貌;人们清清白白从大自然来,又清清白白回大自然去。也有土葬的情况,那是为了埋葬患了传染性疾病死亡的人,而且坑要挖得很深,以防疾病传染。在梅里雪山地区,火葬后把死者骨灰收入袋中,埋在地下,诵念经文。第二年到梅里雪山转经时,人们带上亲人的一部分骨灰,在神山的丫口撒开,用以做肥催长神山上的树;还有一部分骨灰撤入澜沧江中,意为向江水作最后的施舍、奉献。从这些葬俗中,不难看出藏族对大自然的拳拳回报之心。
在一些实行土葬的地区,人们设立民族或村寨的公共墓地。由于这是祖灵安息之地,所以这一带的草木不能动,谁割草砍树,就会遭到报复。这样,坟山的植被得到很好保护。在云龙白族和兰坪普米族地区,林木茂盛的坟山与神山一样,郁郁葱葱,共同维持生态平衡。而在怒江、独龙江两岸,山高坡陡,土地极其珍贵,居住在此的怒族、傈僳族、独龙族则不设专门的公共墓地。人们生时在一起,死了也不应分离,远葬亲人于心不忍。因此,亲人死后就葬在自家园地附近,或者自己的田野里,不立碑,不扫墓,过几年后坟墓也就复平,重新种植农作物。福贡县一些村寨的傈僳族把亲人葬于岩石上,这样办有利于防水防腐,是对亲人的敬重,同时也不占用土地。这种岩石葬和不设公墓地的葬俗,都根源于节约土地的需要。怒江两岸土地资源有限,不能让死人同活人争地。在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落后、土地就是生命的年代,如果让死人不断蚕食稀缺的土地,后人何以生存?所以,只能实行上述葬法,以保持生态平衡。而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各族人民一种朴素的理想。这一点,也反映在葬俗中。纳西、怒、普米等民族的葬礼,或念《送魂词》、或念《指路经》,意图是把死去的亲人送回祖先发祥地。在经文中,各民族的发祥地位置、名称是不同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各民族的发祥地都是水草青青、绿树葱笼、牛羊肥壮、百鸟争鸣、鲜花盛开、人兽和睦的仙境。正是这一朴素的理想追求,引导人们在生活中采取各种措施,规范自己的行动,保护大自然。
6.对生态环境的习惯法保护
我国政府已制定了森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按照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滇西北民族传统文化中,也包括了法律的成分。各民族历史早期都产生过自己的习惯法,它们不属于现代意义的法律范畴,但它可视为法律的萌芽。它们反映了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对于调整氏族成员相互关系和维护氏族社会秩序,产生过重要作用。在原始社会中,习惯法不需要也没有专门的法制机关来执行,它是靠全氏族成员的认同而自觉接受和无条件遵守。习惯法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生理、宗教、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了对自身生活环境保护的要求,形成了对森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不成文的规定,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在各民族中,神山、祖先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村寨的水源林、风景林、护道林也是不能轻易触动的。村民们平时自觉服从习惯法的规定,并对那些破坏森林、乱捕滥猎的行为进行监督,报告村社组织按规定处理。村社组织多由有威望的氏族长老负责,他们公道正派,对违反习惯法者,无论尊卑长幼,都一视同仁按惯例处罚。随着社会进步,文字普及,不成文的习惯法在大多数民族中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广布各民族的村规民约。其中,白族和彝族不仅把村规民约写于纸上,还有不少村寨把村规民约刻于石碑上,便于传之后世,代代遵守。
村规民约的这些规定,代代相传,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也构成社会公德、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对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宗教信仰——大自然,我们的神灵
滇西北各民族具有广泛的宗教信仰,藏族几乎全民信奉藏传佛教,基督教在傈僳、怒等民族中广为流行,白族有不少人信奉汉地佛教和道教,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而土生土长、形形色色的原始宗教则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中。宗教作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滇西北自然资源管理、自然景观的塑造、自然环境的保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自然崇拜与生态环境保护
对大自然的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宗教意识活动,最普遍的自然崇拜是对天、山、树、水、石的崇拜,至今仍存在于各民族中。
彝、普米、纳西等民族普遍祭祀神树。通常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神树林,其中多以高大而古老的栗树作为全村崇拜的神树,四周长满松柏,形成一片郁郁苍苍的神树林。各民族有固定的祭祀神树林的时间和方式,都有保护神树林的种种观念和具体规则。例如丽江纳西族,每年正月举行祭天仪式,同时祭祀神林。祭祀时在神林中搭设祭台,台中央插三根树木,中为柏树,两旁为栗树,作为农作物的象征;对它们祭拜,是祈求草木茂盛,五谷丰登。神林是树神居住的地方,也是天神、山神居留之所,因而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随意进入,践踏草木,更不能在里面割草砍树,谁违反规定,将给自己或家人带来疾病或灾祸。在水源林祭祀水源,在山林中祭祀山神,也是居于与此相同的观念,采取相近的祭祀方式。上述崇拜对山林、水源的保护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即使在因政策失误而大规模破坏森林的年代,神树林也得以在传统观念、传统规定的保护下免遭厄运,在被破坏得伤痕累累的千山万壑中留下一片葱绿。
山、水、树、石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物,对它们的崇拜是很具体的。在纳西族中,还有一个抽象化了的自然神——“署”神,对“署”神的崇拜已超越了对具体神灵的崇拜,它是更高层次的自然崇拜,更能体现纳西族的自然观。纳西族的祭“署”仪式延续千百年,至今仍有生命力。无庸赘言,这一仪式及其在纳西族中确立的自然观,对纳西族地区的生态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2.图腾崇拜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腾崇拜是滇西一些民族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是在自然崇拜基础上达到的自然宗教的第二个阶段。人们在众多的自然崇拜物中,选定出若干种被认为是对集团成员最为密切、最亲密、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对象,放在特殊位置上进行祭祀,以期得到它们的庇护和好处。再发展一步,把这些自然物视为同自身集团有血缘联系的亲族,集团内的成员始于他们,它们是每个成员的祖先,因而将它们的形象或名称奉为自己氏族或部落组织的神圣标志,并围绕他们进行各种频繁的崇拜活动。
在历史上,怒族各氏族多以一种动物命名,认为此动物与本氏族成员间有特殊关系。随着氏族组织的日益松弛,图腾崇拜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形式而只遗下一些传说。但是以某种动(植)物为祖先的观念还是普遍存在。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前往匹河乡对怒族进行调查时,人们还能说出自己是哪一个氏族的后代。多年来怒族对自己现实祖先的祭祀比较简单,但对传说中奉为自己祖先的动(植)物却十分敬重,不准猎食这些图腾物,不准砍伐这些图腾树,违反者将受到惩罚。类似的图腾崇拜在怒江中游两岸的傈僳族中也普遍存在,所涉及的动植物种类更多。图腾崇拜对怒江两岸的狩猎活动、采伐活动给予了限制,很多动物免遭驽箭的杀戮,很多树木免遭刀斧的砍伐,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3.藏传佛教影响形成的自然保护区
藏传佛教是内涵博大精深的宗教,是藏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其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和规定。德钦县东竹林寺管委会主任设孜活佛说,藏传佛教保护生态的观念有:(1)动、植物均是有生命的,狩猎、砍树是杀生行为,要进行严格的控制。(2)动、植物多了,家畜与人的疾病将大大减少。这是因为,如果疾病将要流行,山上的动植物首先是一道屏障,它们为人类和农作物挡住病菌和污浊的空气。(3)不能乱砍滥猎。认为砍了不该砍的树,打了不该打的鸟,就不得好报。(4)藏区的神山,多是佛家神山,拜山就是拜神。例如太子雪山,山门是时轮金刚的坛城,坛城的坛主是莲花生大师,这座山的山神是卡瓦格博。人们朝拜太子雪山,其实是朝拜时轮金刚、莲花生大师和卡瓦格博神。在这些神山上,是不准砍树狩猎的。破坏了神山的生态,就会得罪佛,引发泥石流、洪水、地震、干旱等灾害,遭到佛和大自然的惩罚。
居于以上观念,在东竹林寺一带有以下规定:(1)只要能听到东竹寺钟鼓声的地方(远至白马雪山丫口),都不能砍一棵树、打一只鸟。 (2)不准炸鱼,不准捕猎,大到老熊豹子,小到山间小鸟,都不准用枪或其他猎具捕猎。对违反者,不仅要罚款,没收枪支,还要关几天。
藏传佛教不仅是藏族的传统信仰,也在怒、普米、纳西等民族广泛传布。藏传佛教保护生态平衡的观念和规定,也影响了上述诸民族,促使他们更加尊敬大自然,加倍保护家乡的动植物,从而形成一个个以寺院、神山为中心的自然保护区。
以上三个方面,体现了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各少数民族对自然环境长期艰苦探索的精神,记录了他们对自然环境认识逐步提高深化的过程,反映了他们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历程中,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促进自身发展。当然,滇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也包涵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多种因素,对其进行研究,已是另一文章的任务了。
【收稿日期】2003-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