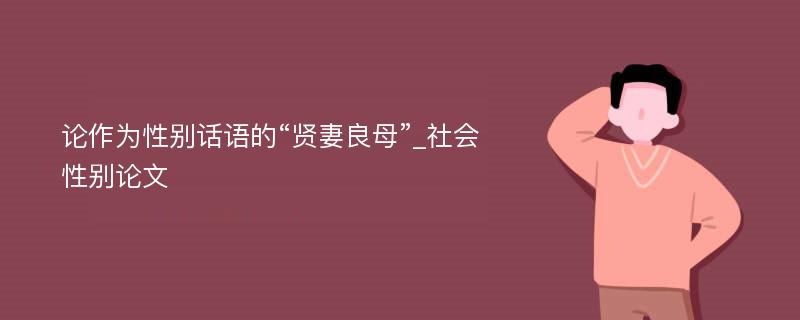
论作为社会性别话语的“贤妻良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贤妻良母论文,话语论文,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0)-01-0109-06
在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在妇女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关注话语。如果话语即权力,那么,解构原有话语即是对原有权力的颠覆。后现代思潮也影响到中国近一时期的妇女研究,比如,李小江的《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注: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兼论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杜芳琴在《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中,对话语生产和流通机制的论述等(注:参见杜芳琴《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国内妇女研究者尝试“模式转换”还刚起步,本文将“贤妻良母”作为社会性别话语来解读,也仅是一种尝试。
一
回顾改革开放的20年中有关妇女问题的讨论,如“女性理想与理想女性”(80年代中后期)、“职业女性角色冲突”(90年代中期)、“女人回家”(90年代中后期),论辩双方虽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但论者均视贤妻良母为传统,既是传统就可继承,亦可抛弃。主张继承者论它是妇女之美德,因此煞费苦心不惜笔墨论说“当代妇女仍然应该争取做贤妻良母,但它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所谓贤妻良母。新贤妻良母即是事业上的强人,又是家庭中的好妻子、好母亲,要两者兼得。”(注:夏华:《试论当代的贤妻良母》,《婚姻与家庭》1986年第12期。)除了“新贤妻良母”外,还有人造出“超贤妻良母”,说是超越以锅台为圆心的平面生活,进入社会、家庭、个人的三维立体人生。(注:冯媛:《今日的中国社会应当怎样要求女性?当代中国职业妇女面临:理想的冲突》,《中国妇女》1986年第5期。)主张抛弃者论它是旧道德,“与男主外,女主内”相连的,为维护旧式家庭结构服务的,是束缚妇女的桎梏,故不宜再用。(注:康强:《试析‘贤妻良母加事业强者’的妇女形象》,《青年探索》1988年第4期。)但论者自知,抛弃“贤妻良母”谈何容易?!
围绕着女性群体意识、角色定位和减轻女性压力所展开的讨论,无一不是改革开放中社会问题的反映。许多论者是积极的女性权利维护者,参与讨论的目的是希望为女性寻找解决当前困境的办法,所关注的是女性在社会中地位和生活质量的变化,他们没有注意自己使用了什么样的话语,以及这套话语的社会性别含义。贤妻良母经过几千年的洗炼,已经成为成熟的性别话语,以上所谈的几次讨论实际上也是在这套性别话语中进行的。
70年代末80年初,是妇女问题的诱发明,作为思想解放的一支劲旅,“知识女性对十分浩劫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妇女特殊命运的反省和对女性角色扭曲的控诉,特别集中表现在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中。解放以来长期压抑的女性意识终于萌发。”(注:李小江:《新时期妇女运动与妇女研究》,《平等与发展》三联书店1997年,第347页。)一时间,女界欣喜“女性意识”的找回,女性能够化妆打扮,充分表达自己的爱美之心了。然而欣喜之后又不得不思考,“女性意识”是什么?海外学者王政敏锐地发现了概念使用所表达的不同意义,历史地考察了中国和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指出,“女性意识”是以自然化的女性为基础来建构的当代女性群体意识,“中国‘女性意识’的建构与西方文化女权主义的努力很不相同,后者是在批判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试图建构女性文化价值观,其锋芒所指是西方文化中的男性内涵。中国‘女性意识’的建构过程主要表现为女性的自律和自我发现,对中国文化中的男性内涵是什么,它的形成与女性内涵有什么关系,男女的内涵是如何形成,怎样改变的,等等,都很少涉及。”(注:王政:《‘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王政认为,“女性意识”仅在80年代给过女性一种解脱和自由感,可社会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大众传媒与广告不断制造各种“现代”女性形象,其基本要素不外乎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笔者以为“女性意识”是宣扬女性阴柔的一面旗子,“贤妻良母”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复归的。
改革伊始,在婚姻家庭中复出的“秦香莲”问题震惊社会,讲述婚姻故事和离婚案的人仿佛都在说:女人要像女人,男人由于女人不像女人而另找新欢,甚至,一些为妇女解忧的人也劝妇女:要像女人,贤慧一些,温柔点儿;改革逐渐深入,职业竞争加剧,职业女性双重角色压力凸现,谁做家务?家务劳动与女性有无天然的联系等问题重新思考;改革深化,下岗人数增加,女性占下岗人员的绝大多数,“女人回家,把就业机会让给男人”作为社会学者的论点提出,引起争论。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多数学者自以为是在两性分工自然的意义上使用“贤妻良母”,用它论证女性做家务自然,对丈夫“贤”自然,对孩子“良”自然,实际上,“贤良”和“妻母”均是社会赋予的,有着明显的历史和时代特征。为了反驳贤妻良母的“自然”,有人不得不说,女人可以“超自然”,做“超贤妻良母”。至此,“贤妻良母”坐稳了它的统治地位。我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前我们用什么思考女人?解放以后的前30年中,“贤妻良母”并未如此主导话语,它是如何隐秘的?
美国学者塔尼·巴娄(Tani E·Barlow)博士感兴趣于中国“女人”话语的研究,她发表了有关的文章,从称谓和概念入手,分析中国社会中妇女观的历史变化,她认为,“话语”中特有的政治文化内涵有作用于历史的一面,比如,她注意到“妇女”这一称谓与革命有关。但为什么不称“女同志”,而称“妇女”?李小江指出,在毛泽东早年的调查报告中,以观察者的身份评价农村女人的生活状况,他称她们是“女子”。日后成为党的领袖时,他称自己队伍中的女人为“妇女”或“妇女同志”,这是为革命队伍中的“女同志”找到的新称谓。(注: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兼论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妇女”这个概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妇女”中包含着“职业的”、“母性的”,也含有“革命的”或“可追随革命的”,其中,“母性的”是“妇女”概念中隐性的但却是重要的表达。我在一篇文章(注:王凤仙:《关于母亲社会性别的思考》,在“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上”(1998年11月)的发言。)里试图指出,“母亲”是“妇女”一词的主要内涵,因为,对年轻的女性可能有“女学生”、“女青年”等词,用到“妇女”时就是已婚的、育有子女的,从二十几岁到七八十岁都是妇女。用“妇女”思考时,两性间的差别是明显的,女性间则没有差异。所以,在解放后的前30年,“贤妻良母”是隐在“妇女”中表达的,或者说,“妇女”所表达的是贤妻良母+革命的+职业的。近20年来,“革命的”表达已逐渐消退,“职业的”情况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甚至产生了怀疑,“贤妻良母”因此开始显现。“贤妻良母”为什么会隐蔽,而不是消失或被消灭?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史》中考证,“贤妻良母”这个名词是清末从东洋输入的,吕美颐也认为:贤妻良母作为概念是1905年左右从日本传入的,它之所以盛行起来,是由于它与中国传统的贤良主义一拍即合。(注: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回顾历史上对“贤妻良母”的论争,我们发现,近代以来,贤妻良母与民权、解放、革命等话语是紧密相联的。比如,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就注意了对传统的贤良主义进行改造,并借此宣扬自己的主张。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写道“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第一次把相夫教子、宜家善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新标准提出来,用以反对“三从四德”,即让妇女从为家庭而生存,变成为善种强国做贡献。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革命者以批判旧世界对妇女的压迫表达自己的思想,陈独秀指出,“三纲”的最大弊病是“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胡适主张,女性要树立“超良妻贤母主义的人生观”。又如,抗日战争时期,争取民族独立、坚持抗战到底的共产党人强烈反对对“贤妻良母主义”的宣扬,反对举出贤夫良父来麻痹人们的思想。罗琼写道:新贤良主义不但让妇女回家,而且让男子回家,关起门来“改善家庭关系”,如果这样的人多起来,只会有利于投降派的活动。
贤妻良母之所以能为革命、民权、解放等话语利用,或者说它之所以成为社会变革时期的热门话题,根本原因就在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最集中地体现为对妇女的压迫,所以,贤妻良母就成为反压迫者最先找到并使用的话语。可是他们不是在社会性别含义上使用的,而是在阶级和民族的意义上使用的。一当革命深入,民族解放,它就可能被抛在一边,被遮弊,或隐现起来。
二
本文将“贤妻良母”作为社会特别话语来解读,即应用社会性别(gender)为分析范畴,看到“贤妻良母”在以往讨论中的话语地位,试图指出“贤妻良母”从来没有被作为两性关系的话语来讨论过。我以为,贤妻良母表达的是“内”与“外”结合的两性生活方式,它包含着: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是家里的(一幅内与外的幸福生活图景);为人妻母是自然的、正常的,不婚不育,是不正常的、不幸的(广告中、医学语言中、村落文化中),贤慧和善良是好女人“好”的必备品德(文学作品中、社会道德中)。
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两性的职责范围有明确的划分——男主外,女主内。所谓“内”是指男性为家长的家族,“外”是指家族之外的经营、亲属、官事、国事等,男性从小被教育关心家庭之外的大事,因为将来他要娶一个女人来照顾“内”务。为什么以男性为家长的家族要让娶来的媳妇主“内”?不能否认,“主”就是要掌握权力,一个在丈夫家生活多年的妻子是有一些权力的。但是这些权力是在一定的规则制度下,按照既定的目标模式争取到的,这个目标模式就是贤妻良母。
她首先认同丈夫家为“内”,自己的父母家为“外”。女孩出生后就被认为是“赔钱货”,因为,养到十几岁就定了亲,二十出头就嫁给了人家。在农村(今天的农村也还沿袭)结了婚的女性要住到丈夫家,婚后一个重要的仪式是“认祖”,就是到丈夫家的祖坟去“告知”这个家多了一个成员,据说,如果不认祖,死后就不能入祖坟。婚后,女性要在丈夫家过年,除夕之夜要同公婆一起吃年夜饭。女性婚后要立刻改口称公婆为“爸、妈”,丈夫则不必叫岳父母“爸、妈”。通过婚后凡此种种的规约,她逐渐地认同丈夫家为“内”,这种认同是她实现目标的基础。接下来,她要做的是:
(1)孝敬公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家庭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妻是配轴。这并不只在封建社会才如此,近现代的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也还是如此。所以,女性婚后的第一课就是侍奉公婆,有研究者写道:“贤妻的字面意义是‘好妻子’,但其实际内容却往往是‘好媳妇’。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贤妻的首要标准,不是体贴丈夫,而是孝敬公婆。……一个女人是不是好媳妇,首先要由公婆来裁决。”(注: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74页。)
(2)相敬如宾和不淫不妒。在夫妻关系为配轴的家庭制度中,男人有男人在外面的事,女人不需要了解;女人有女人在家内的事,男人也不必知道。夫与妻之间如宾,所以有“举案齐眉”之敬。夫妻间可以不表达感情而生育,这对两性的影响是相同的吗?
完全不同。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女人的宿命有五种:正妻(元配)、妾、婢、尼姑和娼妓,对于男人来说,她们各有各的用途,泾渭分明,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注: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男性的情感生活是可以从正妻以外的女人那里获得,贤妻则必须“不淫”,“不淫”不但包括不与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感情或性行为,也包括不与丈夫过多地发生性关系,因为过多的性生活被认为是有损丈夫身体的事。那么,当丈夫提出性要求时,一个贤妻是应该答应,还是应该拒绝呢?拒绝,是“不顺从”;答应,是“不要脸”。所以,贤妻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尽量不在丈夫面前展示女性魅力,当然更不能在其他男性面前展示。当丈夫表示要纳妾时,贤妻不能表现出妒忌,应帮助丈夫,成其美事。(注: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0页。)
(3)教养子女。“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5页。)而对中国女性来说,孩子成为她接受(忍受)婚姻的原因。中国有尊老的传统——养儿为了防老,对女性,子女的意义就不仅在防老,而且在她是否能成为贤妻良母,就是说,她只有成为贤妻良母,她才可能有地位,她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她也才有可能在这个家生活下去。
以家族兴旺为根本的社会,两性为此所承担的责任不同,就妻子而言,第一,她必须能够生育;第二,她要能生儿子;第三,她要教子成材。
在这样漫长的过程中,贤妻良母是不容易达成的,因为良母和贤妻互为基础,相互制约。在这套话语中,女性经由“媳妇”、“某某家的”、“某某的娘”失去了结婚之前的姓名,她被“无名化”了,她们(所有的女性)都是“妻母”;经由“认祖”等一切必须遵守的规范,女性归属到丈夫的家族之中,并确信那里才是自己的家(内),在这里有“妻母”的位置,没有“女儿”的位置。这套话语在说:媳妇生子煞成婆,方能主内。“主内”的权力令人羡慕,比如,她可以受到全家的尊敬,她可以统治家人,包括在外面声名显赫的儿子。
我们注意到,这套话语不是以婚姻为中心展开的,而是以家庭(家族)为中心设计的,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性别歧视制度,但它并不直接表现为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他们相敬如宾),它可能表现为女性对女性的压迫(婆婆对媳妇的要求),也可能表现为生育文化、生存方式对女性的压迫(生不出儿子被外人看笑话,农活没人接替)。由此也提醒我们,是男权文化的家族制度建构了“贤妻良母”,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参加了这个构建,所以,我们反对这个性别歧视制度并不等于反对男人。
三
女性失去姓名(无名化)还不是这套话语的最“成功”之处,它最深刻、最精到的部分在于——它将女性母性化。
我们知道,贤妻良母中,母是根本,母亲被崇拜。母亲崇拜与重视子嗣、崇拜祖先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又与中国古代的生殖崇拜密切相通。(注: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当女性因生育了儿子而受到特别褒奖时,她接下来听到的是“多子多福”,所以她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生,耗尽心血去养,她的生命就在生养之中实现了意义。
在她认同的家庭中,她自己生的孩子是她最亲的人,为了孩子她不惜花时间,也与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有关明清家庭母子关系的研究表明,“一起分担生活的艰辛,在异常严酷、甚至常常是屈辱的境遇中共同奋斗,使母子之间培育起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结。……在明清时代的中国,正如在其他传统社会中一样,母亲是美德和苦难的象征,这一点唯有她的亲生儿女最为理解。儒家的孝道使儿子们可以并且必须在情感上和实际行动上终生铭记母亲的关怀、奉献和不幸遭遇。”(注:熊秉贞:《明清家庭中的母子关系——性别、感情及其他》,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14页。)所以,贤妻良母是有孝道做支持和保障的。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的看法是:在中国旧社会里母子系联的坚强也多少是感情变态的结果。在孝的观念下,社会鼓励着母子的系联。婆媳的争执有多少是爱的争执,我们实在不能加以估计。可以说,没有孝作支持,贤妻良母很难沿袭。
在女性对丈夫家的认同过程中,丈夫的作用远低于孩子。一般女性在婚后1-2年内生第一个孩子,如果夫妻是由媒人介绍,婚前不认识,丈夫又要在外忙,在婚后的一年之内他们相互了解和相爱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孩子的出生就会给初到陌生环境中的女性很大的安慰。如果生的是儿子,女性因孩子得到丈夫家积极地接纳,使她较为顺利地成为贤妻,她就会特别地感谢孩子,也因此更加无保留地把感情投入给孩子。表面看起来母亲爱孩子是自然(生理原因),实际上,她借自己的生理构造(如果她的输卵管和子宫都没问题),靠生育、依赖孩子才得以在家庭中生存,才得以成就贤妻良母,才得以为“人”。所以,如果她爱自己,如果她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那就只有珍爱孩子——自己的骨肉,自己的骨肉就像自己一样。我在一本书里把这称为“女性间接地自我实现”(注:王凤仙:《女人:跪着 站着》,龙门书局1996年版,第109页。)
可见,母性化的过程是以“无名化”为基础的,并通过孝道最终实现的。
母性化中还潜藏着“贤妻良母”的另一个深层目标,就是划分“好女人”和“坏女人”。与婚姻家庭制度并行的贤妻良母产出的是“好女人”,不受家族规范制约者就是“坏女人”。其实,这套话语多用“妻母”,很少用“女人”,原因是“女”在汉字里与许多不洁的字相连,比如“妓”、“奸”等,再者,男人在妻之外所用的女人不能与妻同日而语。所以,“妻”是女中高贵者,能为人妻是福,人母更是不能玷污的,无论“妻”还是“母”,她们都因“人”(男人)而贵。“女”就完全不同了,关于话语对“女”与“妻母”的分离,我在另一篇文章(注:王凤仙:《关于母亲社会性别的思考》,在“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上”(1998年11月)的发言。)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这里着重谈的是母性化与“好女人”和“坏女人”的关系。
当母亲关注与孩子的情感时,她就关心孩子甚于关心丈夫,她与丈夫少谈情爱或不谈情爱时,她就不关注性,忽略自己的性体验;忽略性体验,就“只知生育,不知性快乐”。所以,性对妻子来说就是生育。性虽不快乐,但可以让她做母亲。一旦怀了孩子,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自己就没有性了,丈夫的性可以由别的女人解决。这就是“不淫不妒”。“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女人懂得性的快乐,或者知道如何快乐。母性化的过程中,女性远离了“淫”,远离了“淫”也就远离了“坏”。
在无名化和母性化的过程中,女性获得的称谓是“妻”“母”,当一个女性集妻母于一身时,她的冲突是巨大的,冲突来自男性对“女”的追求和对妻母的需求。女性获得的称谓还有“婆”“媳”,当一个女性为媳后,就发生了与另一个女性的对立,两个女性之间的冲突来自孝道。
“贤妻良母”是界杆,是围栏,在它之内为“好女人”,在它之外为“坏女人”,或至少是“不正常的女人”。无论“妻”还是“母”所表达的均与“女”有差别,“妻母”常与家庭的、温馨的、无私的等词语相联,而“女人”就可以与“贱货”相联。
将“女人”与“妻母”、“婆媳”分离开的是整套社会性别话语——贤妻良母,这套话语支解了女性,因此,女性难以建立自我,难以发展群体意识。
收稿日期:1999-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