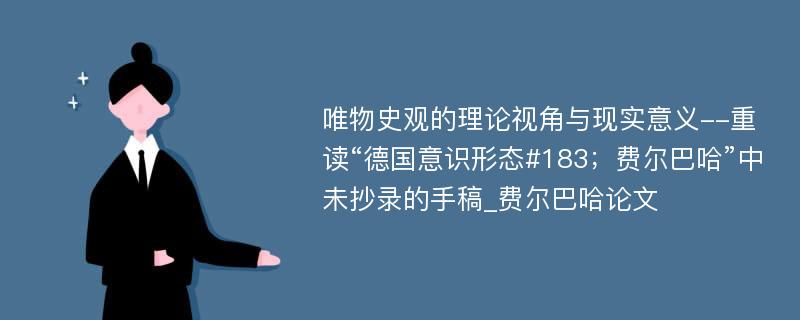
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和现实旨归——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183;费尔巴哈》中“未誊清稿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尔巴哈论文,德意志论文,唯物史观论文,视域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4-0014-07
“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界讨论最多、分歧最大,甚至可以说说法最混乱的议题之一。在相当多的论者那里,其已经脱离了其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其阐释载体—一那些蕴涵深邃但非常散乱的文本,独立而抽象地成为一种可以随意掺杂、涵摄和剔除任何内容的“大口袋”或“大熔炉”。有鉴于此,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追溯其不同阶段的思想运演、具体阐发和论证逻辑,是比原理性的表述更为“鲜活”的思想史佐证、评判依据和发展基础。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其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在现在留存下来的由两个“誊清稿”和三个“未誊清稿”组成的这一章中[1],如果说“誊清稿”只是为了应出版商要求而提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期“样章”,其中由对1842—1845年问德国复杂的的思想图景、理论“事件”的分析而引发的对社会、历史的现实前提及运动的描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和方法的阐发等虽然比较明确,但逻辑较简略和概括的话,那么,在其他三个“未誊清稿”中,在叙述分散的表面背后,“誊清稿”中已经论述过的唯物史观的那些方面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入讨论,而其中未涉及的其他诸多方面则作了详细的阐释或扩展,真正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宽广的理论视野和鲜明的现实归旨。而在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些方面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笼而统之,并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复杂而深邃的思想和逻辑挖掘出来。而这是深化唯物史观研究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拟再次具体而深入地解读和分析这一章中的各个手稿,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论及“未誊清稿Ⅰ”,其他部分另文讨论。
一、人的现实处境及其“解放”的途径
“未誊清稿Ⅰ”的第一自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的第三卷中并未收入,而是作为补充材料放在了中文第一版第四十二卷中。其所分析的是人的现实处境及其“解放”的途径。
人的不自由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获得“解放”?“聪明哲学家”认为是芜杂的“哲学、神学、实体”等遮蔽了人的“自我意识”,是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障统治、左右了人的存在。因此,解决的途径就应该是把那些意识形态形式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把“人”从意识形态构造的“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对人的处境的解释是不对的,因而,对所谓“解放的道路”的指认也是荒谬的。实际上,人从未受过意识形态所构造的“词句”的奴役,如果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寻求人的解放之路,表面上看来煞有介事,其实只是在精神、观念领域兜圈子,而“人”的“解放”并未因此而前进一步。因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人的“解放”是由现实的工业、商业、农业、交往等状况促成的,因此,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还特别加了边注,指出这是“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
既然人的解放是一个复杂、曲折而漫长的过程,除了对现实世界进行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还要根据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理论的批判和斗争,清除诸如“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特别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在历史发展中基本上没什么现实建树,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思想却“被捧上了天”,“词句对德国的意义”非常明显,“它们已经根深蒂固”,从现实方面看,这些“毫无作用的废物”甚至弥补了其历史发展的不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即使只“具有地域性意义”,也必须同这些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二、感性世界·人·历史·自然:超越费尔巴哈的哲学直观
接下来的手稿遗失了五页,使我们无从知道作者的论证思路是如何接续的。以下的分析则极为重要。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P75)这是作者对其把握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及意旨的最重要的表达。“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和“实践”等字眼儿在费尔巴哈的著作里都出现过,他甚至在某些场合也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但“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至多“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概言之,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对“人”、对历史的理解都没有达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高度。
对感性世界的“理解”,费尔巴哈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诚如恩格斯在边注中所指出的,他是“用哲学家的‘眼睛’”,或者说,是戴着“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世界的,这样,他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与他的意识及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与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的症结在于,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2](P76)。
费尔巴哈也谈到了人,但他所理解的人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也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
对世界和人的这种理解,最终导致了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他没有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的生活关系,更不懂得,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人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与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P78)
以这样的视角观照那些漂浮于社会存在之上的意识形式、理论难题及其演变历程,将会获得全新的见解。“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P76)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布鲁诺在《维干德季刊》的文章中坚持“自然和历史的对立”,把自然和历史看作好像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或者好像是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然而,现代工业生产实现和印证了“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如果懂得这一点,那么,“自然与历史的对立”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刻地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其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但其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因此,必须从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变换中看待自然形态的变化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进展。至于费尔巴哈特别谈到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对此,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因此,是“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构成了“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它不仅使自然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促进了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人的直观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发展,塑造了“人本身的存在”。
最后需要指出,“未誊清稿Ⅰ”最后一个自然段在手稿中写在第28页和第29页的右半页,是从《圣布鲁诺》那一章移过来的,是由对鲍威尔的批判接着分析费尔巴哈的历史观,特别是他对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二卷上发表的文章中,费尔巴哈提出了一个概念——“共同人”。他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宾语,认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种纯范畴。在《未来哲学》中,费尔巴哈认为,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
费尔巴哈本来是在对鲍威尔等批判家、理论家的驳难中,为了与其人学思想划清界限而作出这些创设和推导的,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这种理论创构“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但实际上,“既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
三、“原初的历史关系”的因素和意识发展的阶段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正面阐述“原初的历史关系”的因素和发展阶段。
第一个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基本条件。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所谓历史活动的开始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任何历史观的首要的事情就是必经注意到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内涵和意义,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第二个方面是新的需要的产生,即已经得到满足的生活资料的需要本身、满足生活资料需要的活动及已经获得的为满足这种需要而使用的工具等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些新的需要的产生构成了第一个历史活动。
第三个方面是人的生产(家庭),在历史发展过程的开始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出现了,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亦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第四个方面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一定的生产方式或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和探讨。
第五个方面是意识。在考察了上述原初的历史关系的四个方面之后,就会发现,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人具有“意识”和精神。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这种意识并非“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了物质的“纠缠”。这里的物质是指语言。他们把语言解释成“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它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畜群意识”到“部落意识”和“社会意识”,再到“纯粹意识”的嬗变。第一阶段是“畜群意识”。起初,意识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反应,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以外的其他人和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而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即畜群意识。第二阶段是“部落意识”和“社会意识”。后来,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人们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来往。起初是同一部落的成员生活在一起,维护自身的利益,由畜群意识发展为部落意识;之后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人更加意识到交往的重要性,这就过渡到比较高级的社会意识。第三个阶段是“纯粹意识”。当分工使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后,与此相适应思想家、僧侣等出现了,这时人类意识的发展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它是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
马克思、恩格斯也谈到上述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之间的关系,比如不应把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的生产(家庭)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此外,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消灭分工。
四、分工的后果及其前景
由上面的议题,马克思、恩格斯又引申出对分工的论述,这是誊清稿中讨论的继续,着重分析了分工的后果。
首先,分工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分工包含着所有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所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其次,分工导致了利益的冲突。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再者,分工导致了国家的产生。正是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才采取了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共同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表现为虚幻的共同体,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分工决定,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开,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最后,分工造成个体活动与生命本质的“异化”。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自身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当分工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是—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人自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人、不受人控制、使人的愿望不能实现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在这些个人看来,这种社会力量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的,这种力量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那么,分工消灭后的社会活动和个体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人可以按个人的兴趣来决定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人就不会始终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五、异化的逻辑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
接下来的三个自然段是写在原始手稿的右半页的。前两段标有插入符号,后一段没有。
插入的第三自然段是对异化状态的描述:“有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有大量劳动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他们由于竞争而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2](P87)这种状况说明,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其事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插入的第一自然段从“异化—异化的消灭”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及其特征。作者秉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问题的看法,认为现实社会是一种异化状态。有异化就有异化的扬弃和消灭,但这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这种“异化”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第一,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第二,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又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是消灭异化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首先,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普遍的交往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如果未来的社会——共产主义不奠基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那么,其一,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其二,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而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其三,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因此,作者这时对共产主义理解是:“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P87)。其实现的途径是: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插入的第二自然段再次提及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更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即“市民社会”。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承接前面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在近代,其又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据此,他们讽刺当时德国历史科学中的“客观的历史编纂学”学派借用Haupt- und Staatsaktion一词,看重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历史,宣称外交政治高于国内政治,而无视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指出其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
写到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仔细反思了一下到此为止的论述,感到“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而且再次标示需要详加阐发“交往和生产力”,此外,“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深究。
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及其后果
历史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个谜团。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再重复经历历史,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大多数来自理论家、历史学家的描述和解释。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本真的历史过程与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和解释是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是,以往的历史“被思辨地颠倒”了,好像后来的历史是先前的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诸如“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相并列、相关联的人格化的存在。
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2](P88)。这样看来,所谓先前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概念,亦即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所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马克思、恩格斯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历史的发展不是量的积累和同质朝代的更迭,随着时序推进到现代,“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88)。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所具有的世界历史的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可以看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实际过程,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抽象的行为,而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活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活动。
不仅如此,“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还给单个人的发展状态及其前景带来新的特点。在现代,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即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对他们来说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威慑和统治着他们。
显然,历史的更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单个人的发展,最后必然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作者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可以在不同意义上解释,在当时也已经被弄得相当混乱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由上面的阐述得出四个论断:
第一,共产主义革命发生的生产力状况和阶级条件。生产力状况是指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和交往手段的矛盾只能带来灾难、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的阶段。阶级条件是指,社会产生了这样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一阶级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一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其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
第二,共产主义革命的锋芒与实质。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一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praktisch- idealistisch)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因为这些阶级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
第三,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变革。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中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解体的表现。
第四,共产主义革命的全局性。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即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身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七、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唯心主义的超越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作者对自己的历史观进行了明确的概括。这种历史观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其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出发来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之所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将其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一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即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其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具有特殊的性质。
第二,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丝毫不会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如果还没有具备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也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被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以此检视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就会发现,其症结在于,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将其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政治业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历史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与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
表面看来,“未誊清稿Ⅰ”的思路是断断续续、不甚连贯的,但通过对其内容的详细梳理和分析,特别是与“誊清稿”相比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它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都要深入得多。其所涉及的论域和分析深度充分表明,唯物史观根本不是抽象而简单的认识方法和理论教条,而是有着极为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宽泛的思想容量;同时,唯物史观也不是超越一切时代的哲学体系或“绝对真理”,而是有着鲜明的现实考量和未来指向,是批判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论证共产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思想逻辑和理性工具。
[收稿日期]2009-11-05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恩格斯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