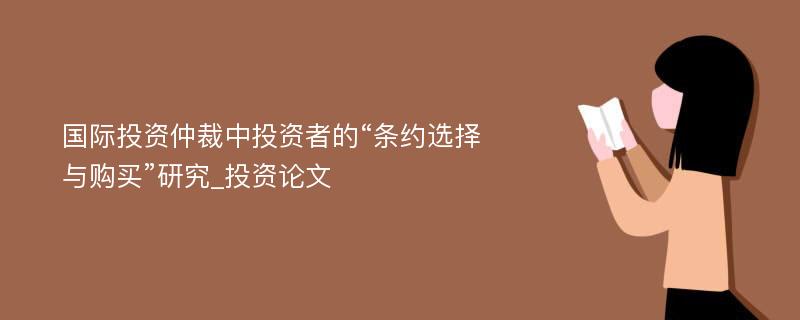
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的“条约选购”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约论文,国际投资论文,投资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早期国际投资条约不同的是,现代国际投资条约①不仅施加了高标准的投资保护义务,还纳入了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仲裁条款。后者作为国际投资条约的“牙齿”②,赋予了投资者就其与东道国间投资争端直接寻求国际仲裁的权利。投资者援引投资条约寻求保护的前提是具有非东道国的某一缔约国国籍,而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间可能并未缔结投资条约或者所缔结的投资条约对于投资者而言还不够有利。为了追求投资保护的最大化,投资者可通过在第三国设立的中间公司③对东道国进行投资,据此“选购”第三国与东道国间的投资条约以寻求保护,这也被称为投资者的“条约选购”(treaty shopping)或“搭便车”行为。
然而,“条约选购”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却始终备受争议,论者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将得出不同的结论。被诉东道国往往极力否定其合法性,认为对“选购”投资条约的投资者给予条约保护不符合条约的目的与缔约国的本意。投资者则认为即使缔约国的本意并不包括对中间公司的保护,但只要条约文本未明确排除,中间公司即有权援引投资条约的实体性和程序性保护。而投资仲裁庭对于“选购”条约的投资者是否有权援引投资条约也并未给出一致的解释。那么,投资者是否可以自由地“选购”任一投资条约以寻求保护?国家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予以有效限制?本文将结合相关投资条约文本与投资仲裁案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国家的应对措施作出评析和建议,以期对我国投资条约实践有所裨益。
一、“条约选购”的途径:第三国转投资与返程投资
“条约选购”的核心在于通过多层级控制关系的运作,从而对其控制链条下公司的国籍身份进行包装。④这种国籍的包装行为,在实践中也被称为国籍构造(nationality structuring)、国籍筹划(nationality planning)或国籍追逐(nationality hunting)。⑤投资者对东道国的一项投资可以经过多个环节,而不同的环节可以构造出具有不同国籍的中间公司。不同的中间公司以及作为该项投资间接股东的最终控制者可能援引不同的国际投资条约对该项投资寻求条约保护。
实践中,条约选购者进行国籍构造的形式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当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间未签订国际投资条约时,投资者可通过在第三国成立的中间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从而寻求该第三国与东道国间投资条约的保护。其二,当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间投资条约未纳入投资仲裁条款或者该条款的范围并不能涵盖某投资争端时,投资者也可通过在第三国成立的中间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从而寻求该第三国与东道国间更为有利的投资条约的保护。其三,具有东道国国籍的投资者为了规避东道国的国内管辖,可通过在其他国家设立的中间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从而寻求该国与东道国间投资条约的保护。前两种情形可统称为投资者的第三国转投资,第三种情形则可称为投资者的返程投资。
从选购的时间点来看,条约选购也可分为事前选购(ex ante)与事后选购(ex post)。事前选购即在投资争端发生之前通过国籍构造将一项投资置于特定的投资条约保护之下;而事后选购即在投资争端发生之后通过国籍构造将投资权益转移至另一国公司从而寻求该另一国与东道国间投资条约的保护。
二、“条约选购”的基础:对中间公司、间接股东的条约保护
(一)投资者国籍的条约标准
投资者是否有权援引某项投资条约,关键在于其是否为该条约某缔约国的“国民”或“投资者”。试图进行条约选购的投资者必须在满足具有缔约国的国籍这一要求后才可能援引其希望的投资条约。而不同的投资条约对于公司投资者国籍的界定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从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文本来看,绝大多数条约都采用了注册地标准(或准据法标准),德国、法国等国签订的部分条约单独或结合采用了住所地标准,此外也有部分条约采用了控制标准或其他混合标准。
根据注册地标准(或准据法标准),依据一缔约国法律在该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具有该国国籍。例如,中国与英国BIT第1条第1款对“公司”作出如下界定:在中国方面,系指在中国领土内任何地方依照有效法律设立或组建的公司、商号或社团;在英国方面,系指在英国领土内依照有效法律设立或组建的公司、商号或社团。注册地标准的优势在于标准的明确性和简易性,依据哪国法律在哪国成立这一事实易于确定;而该标准的劣势则在于投资者与国籍国之间联系的无足轻重,因为在一国设立的公司并不一定在该国开展经营活动或与该国发生其他实质性联系。注册地标准的单一性使得任何在一国成立的公司都可能寻求该国签订的投资条约的保护。⑥
因此,少数投资条约为了限制条约所涵盖的投资者范围,在注册地标准之外结合采用了其他实质性联系标准,比如要求在缔约国开展实质性经济活动或者进行有效管理等。例如,菲律宾与英国BIT第1条第4款规定,缔约国“公司”是指依据一缔约国法律注册或成立,且在该国领土的任何部分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且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
而根据住所地标准,在一缔约国具有住所的公司具有该国国籍。例如,中国与德国BIT第1条第2款规定,非自然人的“投资者”一词在德国方面系指任何住所在德国境内的法人,在中国方面系指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设立或组建且住所在华境内的经济实体。但是该规定并未对“住所”进行明确的界定。“住所”概念的不明确很容易为投资者所利用,因为住所既可能表示主要营业地或公司管理所在地,也可能仅仅表示登记住所地,而登记住所地与公司注册地一般会重叠。⑦在国际投资实践中,一个公司很可能依据A国法律在A国注册成立,其公司管理中心则在B国,而其主要营业地却在C国。⑧
控制标准或者混合标准的出现则是近年来投资条约的一个发展趋势。控制标准的不同运用对于投资者概念的范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该标准既可用来限制投资者的范围,也可用来扩张投资者的范围。而现有的单独或混合采用控制标准的投资条约,多数都意在扩张投资者的范围。例如,中国与瑞士BIT第1条第2款规定,“投资者”包括:“(二)依照该缔约方法律设立或以其他适当的方式组建、且在其领土内有住所和实际经营活动的法律实体;(三)根据第三国法律设立、但为本条第二款第一项所定义的自然人或第二项所定义的法律实体有效控制的法律实体。”该规定第2项的“投资者”虽然需要同时满足注册地标准、住所地标准和实际经营活动标准,但是第3项则另外明确将在第三国设立并由缔约国国民有效控制的法律实体也纳入到投资者范围之内,因而实质上扩张了投资者范围。
而采用控制标准以限制投资者范围的国际投资条约并不多见。例如,日本与新加坡FTA第72条规定,“另一缔约国的公司”是指依据另一缔约国适用法律成立或组建的公司,但是由非缔约国国民所拥有或控制且在另一缔约国未开展实质性商业运营的公司除外。该条款将那些虽在缔约国成立但却由非缔约国国民拥有或控制且在该缔约国未开展实质性商业运营的公司明确排除在投资者范围之外,而且对拥有和控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因此明确限定了该协定所保护的投资者范围,留给投资者进行条约选购的空间非常有限。
(二)国际投资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者”与“投资”
实践中公司的跨境投资一般包括多层级的控制关系,其境外投资也往往涉及多个国家的多个公司,所涉及的公司类型主要包括投资者在东道国成立的当地公司、当地公司的母公司、当地公司的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当地公司的间接股东、中间公司。这些公司要成为特定国际投资条约所涵盖的投资者,需要同时满足该条约对“投资者”和“投资”的定义。一公司如果被认定为特定投资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者”,即有权援引该投资条约对东道国提起投资仲裁程序,而这正是投资者进行条约选购的主要动力之一。
其一,就投资者在东道国成立的当地公司而言,根据注册地标准其具有东道国国籍,因此一般不被认定为投资条约中所保护的另一缔约国投资者。但是,《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ICSID公约》)第25条第2款(b)项允许投资争端当事方作为例外将该公司视为另一缔约国投资者,但前提是争端当事方同意且该公司“受外国控制”。实践中,有部分东道国通过条约、国内立法或投资合同的形式明确同意将当地公司视为另一缔约国投资者。在TSA v.Argentina案中,TSA作为在阿根廷注册成立的公司即依据荷兰与阿根廷BIT第10条第6款对阿根廷提出ICSID仲裁请求,因为该条款规定在东道国成立的公司如符合《ICSID公约》第25条第2款(b)项的条件则应被视为另一缔约国国民。⑨
其二,当地公司的母公司或者公司股东是投资条约下最为常见的“投资者”。母公司或者公司股东对于当地公司享有全部或部分股权,因此其对当地公司投资的形式表现为股份或者其他形式的参股。而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多数都将股份作为投资的一种形式进行列举。例如,中国与荷兰BIT第1条对投资的定义包括“公司股份、债券、股票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参股”。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不论是单一股东、控股的多数股东还是不控股的少数股东都被认定为投资条约下的投资者,而且不同的股东可以独立提出各自的投资仲裁请求。在Camuzzi v.Argentina案⑩与Sempra v.Argentina案(11)中,Camuzzi为卢森堡籍公司,对阿根廷两个当地公司持有多数股份,而Sempra为美国籍公司,对该两个公司持有少数股份,而仲裁庭并不认为所持股份的比例会影响其对两个案件的管辖权。尽管也有仲裁庭对少数股东可单独提出仲裁请求表示担忧,认为可能引发无休止的一连串仲裁请求,但其仍然对少数股东的仲裁请求予以管辖。(12)
其三,间接股东在仲裁实践中也被认定为投资条约所涵盖的“投资者”。一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在母国、东道国或第三国设立一个或多个中间公司,并通过该中间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投资。该投资者即为东道国当地公司的间接股东。在Siemens v.Argentina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股权形式的间接投资也是投资条约所保护的投资,投资条约并未要求在投资和公司最终控制者之间不得插入中间公司。(13)在Waste Management v.Mexico案中,Waste Management是美国籍公司,其通过在开曼群岛的中间公司向墨西哥当地公司进行投资。仲裁庭认为中间公司的存在并不影响间接投资者援引NAFTA提出投资仲裁请求的权利,并指出NAFTA缔约国本可以将仲裁请求范围限制在那些遭受直接损害的公司上,但NAFTA文本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因此中间公司的国籍并不影响本案的仲裁请求。(14)也有仲裁庭认为有必要寻找一个分界点,从而确定那些与受影响的公司之间存在较远关系的间接投资者所提出的仲裁请求是不被允许的,但该仲裁庭同时也承认,这个分界点的确立取决于东道国同意提交仲裁的范围。(15)而多数投资条约在纳入投资仲裁条款的同时并未对不予受理的仲裁请求范围进行规定。因此从投资条约对投资者和投资的宽泛定义出发,间接股权形式的间接投资属于投资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而该间接股东则属于投资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者”。(16)
其四,中间公司在仲裁实践中可独立提出投资仲裁请求。中间公司通常只是投资者进行跨境投资的一个中间平台,因此与中间公司所在国可能并无实质性的经济联系。但是,在仲裁实践中,中间公司援引投资条约提出投资仲裁请求的权利得到了肯定,但前提是该中间公司所援引的投资条约对公司国籍采用注册地标准。根据注册地标准,即使中间公司与注册地国无实质经济联系,其仍然具有注册地国国籍,是注册地国与东道国签订的投资条约所涵盖的投资者。在Saluka v.Czech案中,Saluka对捷克当地的一家公司进行投资,而Saluka是在荷兰注册成立的公司,其由在英国注册成立的野村欧洲有限公司全资控制。捷克政府认为,Saluka是野村欧洲有限公司的一个空壳公司,因此无权援引荷兰与捷克BIT。而仲裁庭认为荷兰与捷克BIT第1条对公司国籍采用了注册地标准,Saluka与野村欧洲有限公司的紧密关系并不影响其本身的投资者地位。(17)
需要注意的是,有部分投资条约将在第三国成立但却由缔约国国民控制的公司也纳入到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者”范围之内。例如,根据中国与瑞士BIT第1条第2款的规定,中国或瑞士的投资者在第三国设立并有效控制的中间公司也可以援引中国与瑞士BIT对东道国提出投资仲裁。当然,如果该第三国与东道国(即中国或瑞士)之间存在单独的投资条约且对公司国籍采取注册地标准,则该中间公司还可以援引该项投资条约对其投资寻求保护。
三、国际投资法对“条约选购”的限制:揭开公司面纱与善意原则
(一)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对“条约选购”的限制
1.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可适用性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为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所普遍接受,该制度目的在于防止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以侵害公司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18)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国际法上的可适用性也得到了国际法实践的认可,例如在Barcelona Traction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国际法中的一定适用是可以接受的。(19)但国际法实践中所适用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功能上与国内法语境下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确定公司的国籍,即在确定公司的国籍时是否考虑公司背后控制者的国籍。(20)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在国际法中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国际投资条约保护领域。当一项投资控制链条上的某个公司援引特定投资条约寻求保护时,须确定是否揭开该公司的面纱以及揭开多少层公司面纱,从而确定该公司是否为特定投资条约所涵盖的“投资者”。但是,揭开公司面纱并不否定该公司在国内法上的权利义务,而仅就投资条约保护的目的否定或者肯定该公司的缔约国国籍,从而否定或者肯定该公司援引投资条约寻求保护的资格。
就投资条约下公司国籍的判断而言,揭开公司面纱的适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投资条约明文授权的揭开公司面纱;第二,条约未明文授权,但仲裁庭依据一般国际法揭开公司面纱。当条约对公司国籍采纳控制标准时,仲裁庭即可依据该标准透过公司面纱考察其背后控制股东的国籍情况。但正如前文所述,控制标准既可用来限制投资者的范围,也可用来扩张投资者的范围。在限制投资者范围的控制标准下,揭开公司面纱的运用在于否定公司的某缔约国国籍;而在扩张投资者范围的控制标准下,揭开公司面纱的运用则在于确立公司的某缔约国国籍。然而,多数投资条约就公司国籍采纳了注册地标准,此时仲裁庭仍可能依据善意原则等一般性规则对公司的股东情况进行考察,从而决定是否揭开公司面纱。
2.第三国转投资情形下的适用
第三国转投资的条约选购者通过在第三国设立的中间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投资。当中间公司依据特定投资条约寻求对投资的保护时,首先要确定是否揭开公司面纱以及揭开多少层公司面纱。在这一问题上,仲裁实践表现出了明显的否定倾向,但同时也认可在公司涉及欺诈或者其他滥用公司人格的情况下有必要揭开其公司面纱。
在Saluka v.Czech案中,Saluka作为中间公司对东道国捷克政府提出了投资仲裁请求。而捷克政府主张:与缔约国没有真实联系且受到第三国公司控制的空壳公司没有援引投资条约的权利,允许他们援引投资条约将导致对投资条约的选购和对仲裁程序的滥用。尽管仲裁庭在裁决中对于这样的主张“表示一定的同情”,但其同时指出其行使管辖权的主要考量因素是投资条约的用语。缔约国本可以在条约中约定将受到第三国公司控制的中间公司排除在“投资者”的定义之外,但荷兰与捷克BIT中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因而仲裁庭无权对BIT中的“投资者”定义作出额外的限制。同时,仲裁庭也注意到在一些情形下有必要透过公司结构去审查其背后的控制者,但是捷克政府并未能证明本案投资者存在“欺诈或者不法行为”,因此仲裁庭拒绝对申请人揭开公司面纱。(21)
同样,在ADC v.Hungary案中,加拿大投资者通过在塞浦路斯注册成立的两家中间公司对匈牙利提起仲裁。仲裁庭认为,在塞浦路斯与匈牙利BIT明确采纳注册地标准的情况下,公司资本的来源以及公司的控制者国籍与该公司的国籍认定没有关联。而且,揭开公司面纱只适用于“真正受益者滥用公司人格以掩盖其真实身份并逃避债务的情形”,而本案并不存在这一情形。(22)
而Aguas del Tunari v.Bolivia案中涉及的投资者关系更为复杂。Aguas del Tunari为在玻利维亚注册的当地公司,在其控制链条上端存在多个层级的中间公司,其中包括若干荷兰籍中间公司,但投资最终由美国公司和意大利公司共同控制。在该案中,Aguas del Tunari援引荷兰与玻利维亚BIT提起仲裁。根据该BIT第1条对“国民”的定义,依据玻利维亚法律成立的公司,如果受到荷兰国民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则该公司属于荷兰的“国民”。仲裁庭肯定了对该案的管辖权,并认为在条约未明确限制的情况下,投资者通过另一国进行投资运作从而获得更有利的税收、公司管理环境以及投资条约的保护在实践中“屡见不鲜而且是合法的”。尽管仲裁庭承认中间公司的运作方式有可能导致公司人格被滥用,而且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况下可以揭开公司面纱,但是其认为从提交证据来看本案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在仲裁庭看来,虽然BIT名为“双边的”投资条约,但是通过对“国民”或“投资者”的宽泛定义,该条约在很多情况下将被第三国投资者用来进行构造或重组投资。而多数BIT中对国民的宽泛定义也表明投资的国籍迁移与条约的目的以及缔约国的本意是相符的。(23)
因此,就第三国转投资的条约选购来看,仲裁实践并不否定条约选购者援引特定投资条约寻求保护的权利,但同时仲裁实践也肯定了揭开公司面纱在少数情形下的可适用性。仲裁庭在决定是否揭开公司面纱时主要考虑是否存在滥用公司人格或滥用权利等情形,但仲裁实践对于滥用情形的认定表现得尤为谨慎。
3.返程投资情形下的适用
与第三国转投资的条约选购不同,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受到了较多的质疑。支持者认为判断投资者是否有权援引投资条约的保护仅需考察其是否符合条约对投资者的定义,而不论该项投资是否最终由东道国国民控制。而反对者认为,国际投资仲裁的目的在于为真正的外国投资者提供救济,而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将原本的国内争端“国际化”,从而规避国内法院的管辖,因此应对其揭开公司面纱,否定其援引投资条约的资格。
在Tokios v.Ukraine案中,Tokios是在立陶宛成立的公司,而该公司的99%股份由乌克兰国民享有。Tokios援引乌克兰与立陶宛BIT提起仲裁。根据该BIT第1条第2款(b)项的规定,依据立陶宛法律法规并在其境内成立的任何实体是立陶宛投资者。仲裁庭通过对该BIT用语的通常意义、上下文并参考其目的和宗旨进行解释后,认为本案唯一需要考虑的是申请人是否为依据立陶宛法律所成立的公司,任何运用控制标准以限制投资者范围的主张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都是不相符的。缔约国本可以采用控制标准或者保留对特定群体拒绝予以条约保护的权利,但在该BIT中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因此,尽管Tokios的99%股份由乌克兰国民拥有,但是仲裁庭拒绝“透过申请人去探寻其股东或者其他对该申请有利益的法律实体”。在仲裁庭看来,Tokios的条约选购行为并不构成对其立陶宛法人资格的滥用,而且,Tokios的设立并非为了获得针对乌克兰向ICSID提交投资仲裁的目的,因为该公司在乌克兰与立陶宛BIT生效的六年前即已经设立,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利用Tokios的公司人格来达到其不正当目的。(24)
但是,作为该案仲裁庭主席的Weil法官对该管辖权裁决表示强烈的反对,其在反对意见中指出ICSID机制的目的不在于允许、更不在于鼓励《ICSID公约》缔约国的国民通过一个现有或者专门成立的外国公司来规避其本国国内法院的管辖和国内法律的适用,其目的在于保护和鼓励“国际投资”。而本案投资争端并非立陶宛投资者与乌克兰间的国际争端,实质上是乌克兰国民与乌克兰之间的国内争端。(25)
同样地,Rompetrol v.Romania案仲裁庭对投资条约下的公司国籍也采取了形式化的文本解释。在该案中,Rompetrol是在荷兰注册的公司,其依据荷兰与罗马尼亚BIT提起仲裁,而该BIT对公司国籍采纳注册地标准。东道国罗马尼亚对于Rompetrol符合《ICSID公约》与BIT关于国籍的形式要求并无异议,但其主张Rompetrol实际上是由罗马尼亚国民控制,因此Rompetrol无权援引该BIT寻求保护。而仲裁庭并未支持东道国的主张,其认为一般国际法中并不存在要求公司与国籍国之间存在“真实且有效联系”的规则,国家可以自由约定采取何种标准以确定公司的国籍。荷兰与罗马尼亚BIT对公司国籍采取了注册地标准,而未对所有或者控制、资本来源或者有效住所作出要求,因此根据条约解释规则,不得对该注册地标准作出其他不同的解释。而且,仲裁庭并不认为对Rompetrol的仲裁请求进行管辖将导致对ICSID机制的滥用。(26)
而在TSA v.Argentina案中,仲裁庭对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者援引投资条约的资格予以了否定。该案中,TSA是在东道国阿根廷成立的当地公司,其由荷兰公司直接控制,但公司的最终控制者是阿根廷国民。TSA依据荷兰与阿根廷BIT第10条第6款的规定,主张其受荷兰公司的“外国控制”,因而应被视为荷兰“国民”。仲裁庭则认为,为确定其是否真实地受到“外国控制”,有必要揭开其公司面纱考察其背后的实际控制者。尤其当公司的最终控制权掌握在东道国国民手中时,仲裁庭有充分理由而且有必要揭开公司的多层面纱以寻求其最终控制者。(27)因此,仲裁庭首先揭开TSA第一层面纱确定其由荷兰公司控制,随后揭开荷兰公司的第二层面纱确定该荷兰公司最终由阿根廷国民控制,进而认定TSA并不存在《ICSID公约》第25条第2款(b)项所要求的“外国控制”,从而否定了TSA在荷兰与阿根廷BIT下的“投资者”资格。(28)这一裁决也得到了Schreuer教授的认可,其认为就《ICSID公约》第25条第2款(b)项的“外国控制”要求而言,最好的办法是将那些最终由东道国国民控制的法人排除在ICSID的管辖权之外。(29)
对比上述三个案件可知,不同仲裁庭(包括个别仲裁员)对于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者是否揭开公司面纱有所分歧,而造成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投资条约对投资者国籍的不同要求。在前两个案件中申请人均为在非东道国的缔约国成立的公司,而在TSA v.Argentina案中申请人为在东道国成立的当地公司,而《ICSID公约》第25条第2款(b)项对于在东道国成立的当地公司特别要求须受“外国控制”。在前两个案件中仲裁庭依据的是相关BIT对公司国籍采纳的注册地标准,而在TSA v.Argentina案中仲裁庭依据的是《ICSID公约》和荷兰与阿根廷BIT对东道国当地公司所要求的“外国控制”标准。
因此,就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来看,仲裁实践并未一般性地确立对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者进行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则,是否揭开公司面纱取决于特定国际投资条约对公司国籍的特定要求。当条约对公司国籍明确采纳控制标准时,仲裁庭将据此对公司揭开公司面纱寻求其背后的控制者国籍;而当条约对公司国籍明确采纳注册地标准时,仲裁庭则倾向于承认条约选购者的缔约国国籍而不考虑其背后的控制者国籍。
可见,仲裁实践并未因第三国转投资或返程投资的不同而对特定类型的条约选购予以特别限制。无论是第三国转投资还是返程投资的中间公司,只要在形式上符合投资条约对投资者的国籍要求,仲裁庭都倾向于将其视为投资条约下所保护的投资者。依赖习惯国际法下的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来否定公司在投资条约下所具有的国籍是很难成功的,条约选购本身并不能构成揭开公司面纱的依据。(30)在注册地国籍标准下,除非具有注册地国籍的公司存在欺诈或者其他滥用公司人格等情形,否则仲裁庭不会对其揭开公司面纱。而投资者欺诈或滥用行为的认定,则涉及对善意原则的解释和适用。
(二)善意原则对“条约选购”的限制
仲裁庭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上的谨慎,源于其对条约选购者的善意推定。通过第三国转投资或者返程投资进行条约选购的投资者只要在形式上符合投资条约对投资者的国籍要求,仲裁庭即推定其具有援引该投资条约的资格,除非东道国能证明该投资者存在欺诈或者其他滥用公司人格等“恶意的”情形。
条约选购的“时间”是仲裁庭考虑“恶意”的关键性因素。在Phoenix v.Czech案中,Phoenix是一家在以色列成立的公司,由捷克自然人Beno全资控制。Phoenix购买了在捷克成立的两家公司,而这两家公司由Beno的家人最终控制。Phoenix援引以色列与捷克BIT提起仲裁,要求捷克对其购买的两家捷克公司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仲裁庭从投资的时间、提起仲裁请求的时间、公司转让的本质、整个投资运作的实质等方面对投资者的条约选购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Phoenix购买两家捷克公司的行为仅仅是Beno家庭内部财产的转移,其唯一目的在于将已有的争端提请ICSID仲裁以寻求救济。Phoenix是为收购捷克公司而专门设立的,在完成收购后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经济活动。Phoenix购买捷克公司并不是“善意的”交易,而仅仅是为了将已有的国内争端转化为可以依据以色列与捷克BIT提交投资仲裁的国际争端,因此不是ICSID体制和BIT所保护的“投资”。(31)可见,在争端发生后通过投资运作进行的条约选购并不能得到仲裁庭的认可。对此,作为本案仲裁庭主席的Stern教授也专门撰文指出,为了获得国际投资仲裁申请资格的“事后选购”并不符合善意原则。(32)但是事前选购则并不构成对ICSID体制和BIT的滥用。
在Mobil v.Venezuela案中,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公司在委内瑞拉进行能源投资,在其投资过程中埃克森美孚公司决定对投资进行重组,通过在荷兰设立新的中间公司并由该公司取得投资的间接控制权。在发生投资争端后,在荷兰设立的中间公司以及由该公司控制的其他中间公司依据荷兰与委内瑞拉BIT提起投资仲裁。仲裁庭在对投资时间、争端发生的时间进行考察之后指出,尽管投资者的投资重组行为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向ICSID提交仲裁的资格,但这是投资者的“合法目的”,只要其所指向的是“未来的争端”。而针对“已有争端”进行的、目的仅在于获得BIT保护管辖的投资重组行为则是“对《ICSID公约》和BIT下国际投资保护体制的滥用操纵”。因此,仲裁庭仅对投资重组之后所发生的投资争端予以管辖。(33)同样,Mihaly v.Sri Lanka案(34)和Banro v.Congo案(35)也涉及投资者的事后选购。在这两个案件中,加拿大公司在对东道国的投资发生争端后,将投资权益转移至在美国设立的公司,试图通过美国公司对东道国提起投资仲裁请求。而加拿大并非《ICSID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加拿大公司无法提起ICSID投资仲裁。两案的仲裁庭对申请人的事后选购行为均予以了否定,并认为在投资争端发生后将投资权益转移至ICSID缔约国国民的做法并不能赋予其援引相关BIT提起投资仲裁的资格。
但是,事前选购与事后选购在某些情形下并非一目了然,从而可能难以确定二者的分界时间点。对此,Pac Rim Cayman v.El Salvador案仲裁庭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这一分界点在于有关当事方已获知某项已有投资争端或者可以预见某项特定争端将很可能发生之时。在该时间点之前,投资者的国籍包装行为通常不构成滥用,而在该时间点之后发生的国籍包装行为则通常可认定为滥用行为。不同案件中由于案件事实的不同可能答案会完全不同。但仲裁庭同时也意识到,这一分界线不太可能是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相反会存在“一个显著的灰色地带”。(36)尽管如此,仲裁庭最终认定本案申请人在将注册地从开曼群岛变为美国之时并未预见到其与萨尔瓦多之间的投资争端,因而认定申请人的国籍变换并不构成程序滥用行为。(37)
(三)小结
总体而言,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对投资者的条约选购行为主要从两方面予以考察,包括投资条约所采纳的公司国籍标准以及投资者是否存在滥用权利或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当投资条约对公司国籍采纳控制标准时,仲裁庭将通过对“控制”用语的解释,揭开公司面纱并对其背后控股股东的国籍情况予以考察。但是,明确采纳控制标准的投资条约仅为少数。
对于采纳注册地标准的多数投资条约而言,仲裁庭通常不会主动揭开某注册地国公司的面纱,除非东道国能证明该公司存在滥用权利或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滥用行为性质的认定,其依据在于善意原则。在投资者被认定违反善意原则的若干仲裁案件中,投资者进行条约选购行为的“时间点”是仲裁庭所考虑的关键要素。只有在投资者已获知某项现有投资争端或者可以预见某项特定的未来投资争端之后,其所进行的条约选购行为才会被例外地认定为恶意的滥用行为。因此,投资者的条约选购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揭开其公司面纱并否定其注册地国籍的依据,除非这一行为发生的“时间点”晚于某项投资争端的形成。
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权利滥用原则还仅仅是一个尚不成熟的评价公司真实国籍的分析工具,依据公司人格滥用原则来否定公司的注册地国籍并非应对条约选购问题的有力措施。(38)揭开公司面纱或者善意原则对条约选购问题的适用并非令人满意的普遍性方案,因为其仅在极其特殊的例外情形下才可适用。仲裁庭就该问题的逐案分析很难实现法律的确定性,最为可靠的方式仍然是由国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予以明确。(39)
四、国家对“条约选购”的条约控制
国际投资条约对投资者的宽泛界定以及一般国际法对条约选购问题的限制不足,使得投资者可以通过构造投资以选购投资条约从而寻求投资保护的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条约选购或者国籍构造本身并不是非法的或者不道德的。(40)有学者甚至据此认为国家遵守投资条约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而不区分其资本的来源地,东道国在BIT下的“双边性”义务已实际转化为对所有投资者的义务(41),或者说已具有了“多边化”特征。(42)但是,正如仲裁实践所反复确认的,投资条约是缔约国之间的特别国际法,缔约国有权在条约文本中就条约选购进行限制,从而避免“陌生的”投资者选购该条约。当然,是否限制以及采取何种模式进行限制则要视缔约国之间的政策考量与利益博弈而定。
(一)限制“投资者”的定义
条约选购现象的存在,其前提是投资条约对于“投资者”国籍标准的较低要求。因此,要求投资者与缔约国间存在更紧密的联系从而限制条约所涵盖的投资者范围是应对条约选购现象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实践中,部分投资条约在注册地标准之外还要求公司在缔约国实际开展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要求其主要营业地或公司管理所在地位于缔约国等。这些额外的要求对于限制条约所涵盖的投资者范围可发挥一定作用,但是投资者仍可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前提下实现选购条约。例如,A国与B国在BIT中要求投资者在一缔约国注册且开展实际经营活动并进行有效管理,而C国投资者仍可在A、B任何一国设立中间公司并由该中间公司向另一国进行投资从而寻求该BIT的保护,只要中间公司在注册地国开展少量经营活动且定期在当地召开董事会等即可满足要求。
与此不同的是,要求投资者在一缔约国成立且须由该缔约国国民拥有或控制则可实质性地限制条约选购的空间。例如,日本与新加坡FTA第72条规定,“另一缔约国的公司”是指依据另一缔约国适用法律成立或组建的公司,但是由非缔约国国民所拥有或控制且在另一缔约国未开展实质性商业运营的公司除外。根据该条定义,第三国投资者在日本或新加坡设立并拥有或控制的中间公司将不是该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者。但是,该定义并未排除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情形,例如新加坡投资者可以通过在日本设立中间公司并由该中间公司对新加坡进行投资,从而寻求该条约对投资的保护。因此,为了同时限制第三国转投资和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缔约国可以在“投资者”的定义中明确:法人投资者是指在一缔约国成立且在该国开展实质性商业活动的公司,但是由非缔约国或东道国国民拥有或控制的公司除外。
但是,实践中缔约国是否采纳上述控制标准或者其他联系标准以限制条约选购,取决于缔约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和政策取向。发展中国家迫于吸引外资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对投资和投资者的宽泛界定,而部分发达国家则希望通过宽泛的投资者定义来保护跨境投资的本国投资者以及增强本国对条约选购者的吸引力。例如,荷兰在其对外签订的98项投资条约中,多数对投资者国籍采纳注册地标准,而且将在非缔约国成立但由缔约国国民控制的实体也纳入到投资者范围之内。荷兰作为投资者寻求投资保护的“条约天堂”,其作用在近年来的投资仲裁案件中得到了体现。根据学者的统计,在现有的ICSID仲裁案件中,荷兰投资者提起的仲裁案件约占10%,而这些投资者当中多数都是所谓的“邮包公司”,其最终控制者或者母公司并不在荷兰,而且其在荷兰并没有实质性经济活动甚至没有任何雇员。(43)
(二)订入拒绝授惠条款(44)
拒绝授惠条款是限制条约选购较为常见的模式。拒绝授惠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缔约一方保留拒绝给予另一缔约方投资者在投资条约项下一部或全部利益的权利。(45)拒绝利益的对象主要包括非缔约国投资者以及东道国投资者两类,即分别针对第三国转投资的条约选购者和返程投资的条约选购者。拒绝授惠条款与限制投资者定义虽然在限制条约选购的效果上相似,但是各自的政策基础并不相同。对投资者定义的限制从源头上将条约选购者从“投资者”的范围中予以排除,而拒绝授惠条款的前提是认可条约选购者在投资条约下的“投资者”地位,但缔约国同时保留拒绝给予其条约保护的权利。因此,拒绝授惠条款的内在政策逻辑可以归纳如下:投资者可以选购条约,而同时国家也有权对条约选购者拒绝予以条约保护。(46)
NAFTA、ECT、ASEAN以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中国(47)等国家签订的部分BIT或双边FTA含有拒绝授惠条款。但是不同投资条约对于拒绝利益条款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以及适用程序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在适用对象上,NAFTA等部分条约同时将第三国转投资和返程投资纳入到拒绝利益的范围之内,而ECT、中国与墨西哥BIT等部分条约仅规定了针对第三国转投资的拒绝利益。在适用条件上,多数条约一般要求东道国拒绝利益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该投资者在另一缔约国未从事实质性商业活动以及该投资者由非缔约国国民或者东道国国民控制(48),其中部分条约对于实质性商业活动和控制也作了规定。在适用程序上,NAFTA、中国与墨西哥BIT等条约要求东道国拒绝利益须“经事先通知及磋商”或“经缔约双方共同磋商”,而ECT、美国与新加坡FTA等条约未对此作出要求。
但是,在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对拒绝授惠条款的适用作出了严格解释,东道国援引该条款主张对条约选购者拒绝利益极少为仲裁庭接受。在Plama v.Bulgaria案中,东道国主张ECT第17条授予缔约国直接和无条件地拒绝利益的权利,而仲裁庭则认为权利的存在与权利的行使不同,ECT第17条下缔约国拒绝利益的权利需要通过向投资者事先通知或者其他形式的宣告予以行使,尽管该条并未明文要求东道国在拒绝利益之前须作出通知。而且,东道国就拒绝利益作出的通知或者宣告不具有溯及力,其只能针对在通知日之后作出的投资。(49)仲裁庭的这一解释将极大地限制拒绝利益条款的实际作用(50),甚至使该条款变得毫无意义。(51)在AMTO v.Ukraine案中,东道国同样援引ECT第17条主张对AMTO拒绝利益。而仲裁庭认为ECT涵盖的投资者包括两类,一类是不得否定其权利的投资者,另一类是可以否定其权利的投资者。当东道国援引ECT第17条对可以否定其权利的投资者拒绝利益时,其须承担证明该投资者存在可以拒绝利益情形的举证责任。而AMTO在ECT成员国拉脱维亚实际开展了商业活动且雇佣了少量员工,因此认定东道国未能证明AMTO存在可以拒绝利益的情形。(52)东道国的举证责任在Generation Ukraine v.Ukraine案中也得到了确认。在该案中,东道国援引美国与乌克兰BIT第1条第2款主张对申请人拒绝利益,而仲裁庭认为东道国未能证明申请人由第三国国民控制。(53)同样,在Yukos v.Russia案中,仲裁庭认为ECT第17条拒绝的利益范围仅限于ECT第三部分的实体权利,而不包括第五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东道国是否援引该条主张拒绝利益并不影响仲裁庭对案件的管辖。而且,仲裁庭对于以往裁决关于通知要求、拒绝利益通知的无溯及力等解释立场也表示认可。(54)
可见,拒绝授惠条款在仲裁实践中的运用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国家能否依据现有的拒绝授惠条款有效限制条约选购仍然存有疑问。尽管有学者对仲裁庭的限制性解释能否反映缔约国的真实意图表示怀疑(55),但这并不能阻止仲裁庭按照自身的理解对拒绝授惠条款进行限制解释。为了防止仲裁庭的限制解释,缔约国有必要在条约中使用清晰的用语以明确拒绝授惠条款的适用对象、条件和程序。具体的调整措施可包括:第一,避免使用“保留拒绝的权利”或“有权拒绝”的表述,而是使用“应予拒绝”(shall be denied)等具有直接或自动适用效果的表述。第二,将拒绝授惠的适用对象明确规定为包括第三国转投资和返程投资。例如,由中国商务部起草的2010年《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第10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对第三国转投资和返程投资作出了拒绝授惠的规定。(56)第三,明确实质性商业活动以及控制的含义。第四,在拒绝授惠条款中或者在概括性的宣告中事先明确将对条约选购者拒绝利益,以应对上诉仲裁裁决对东道国作出的程序性要求。第五,在拒绝授惠条款中明确东道国可在任何时间对条约选购者拒绝利益,例如根据中国与加拿大BIT第16条的规定,缔约国可“在任何时间”对第三国转投资的投资者和返程投资的投资者拒绝利益,且任何时间包括在投资仲裁程序被提起之后。(57)
(三)嗣后联合解释以拘束仲裁庭
投资条约在签订时可能对于特定概念、条约用语有意或者无意地不予以定义或者进行宽泛的界定,而定义的不存在或者模棱两可容易导致实践中适用的分歧。因此,缔约国之间如果通过嗣后的联合解释对特定概念、条约用语予以界定,将可以避免实践中的分歧。
缔约国之间嗣后的联合解释对于仲裁庭具有拘束力。《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即规定,“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予以解释。因此,仲裁庭在对投资条约进行解释时,须将缔约国之间关于条约解释的协定与条约上下文一并考虑进行解释。部分投资条约对缔约国联合解释的效力也予以了确认,例如根据NAFTA第1131条第2款的规定,由缔约国组成的贸易委员会对该条约条款作出的解释对仲裁庭具有拘束力。
但是,由于缔约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政策考量甚至是准备不足,投资条约的缔结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些未经定义的概念或者模糊宽泛的用语。对于这些概念、用语,缔约国之间可能始终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作出联合解释的可能性并不高。
(四)修改或取消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仲裁条款
对于选购条约的投资者而言,援引一项有利的投资条约对东道国提起投资仲裁程序是其选购条约的主要动力。投资者可以选购投资条约的直接原因是多数投资条约对投资者的宽泛界定、拒绝授惠条款的缺位或在规定上的模棱两可,但根本原因在于多数投资条约中纳入了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仲裁条款。缔约国通过该投资仲裁条款,同意投资者就其与东道国间的争端提起投资仲裁程序。
因此,为了应对条约选购现象,最为彻底的方法是在投资条约中限制或取消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仲裁程序。现有投资条约在投资仲裁条款中“同意”提交投资仲裁程序主要包括“概括同意”、“有限同意”和“逐案协商”三种类型。在“概括同意”模式下,投资者可就“任何投资争端”寻求投资仲裁。在“有限同意”模式下,投资者可就东道国同意仲裁的特定投资争端提交仲裁,例如,我国早期的BIT多规定投资者仅可就征收补偿数额争端提交投资仲裁。而在“逐案协商”模式下,投资者须与东道国就特定争端进行协商同意才可提交投资仲裁,这种模式在现代投资条约中较为少见。因此,采用“有限同意”模式可以限制投资者提起投资仲裁程序的范围,而采用“逐案同意”模式或者不纳入投资仲裁条款则赋予了东道国就具体投资争端是否同意提交投资仲裁程序的决定权。
在投资条约中不纳入投资仲裁条款已开始成为一些国家的缔约政策。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其2011年的贸易政策报告中明确表示,在之后的投资条约谈判中将不再纳入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条款。(58)该报告中承认此前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条约纳入投资争端解决条款主要出于保护本国商业的考虑,但考虑到该条款赋予外国投资者相比国内投资者更多的法律权利以及该条款对东道国在经济、社会、环境、健康等方面权力的限制,该政府将不再支持纳入该条款。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政策立场将有效限制澳大利亚BIT对条约选购者的吸引力,因为投资条约中如果没有了投资仲裁条款,那么投资者将失去了可以在国际层面对抗东道国的“牙齿”。
总体而言,不同的应对模式对于条约选购现象的预防效果并不相同。采取何种模式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利益和政策,针对不同的缔约相对国也完全可能采取不同的模式。拒绝授惠条款是当前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应对模式,但该条款的适用在投资仲裁实践中受到了限制,因此有必要予以调整或在条文中对特定概念予以明确。与拒绝授惠条款相比,在定义中对“投资者”的范围予以限制是较为稳妥的方式。而通过嗣后的联合解释以限制仲裁庭在对待条约选购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也是缔约国的备选方案之一,但缔约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将影响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修改或取消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仲裁条款则是缔约国的最后选择,尽管这一方案可以有效限制条约选购现象,但同时也可能降低投资条约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和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五、审慎评估和应对投资者的“条约选购”
投资者为追求投资保护最大化而通过构造第三国中间公司的国籍来“选购”其认为有利和合适的投资条约,这在当前的国际投资实践中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国际法中并不存在规制条约选购行为的一般性国际法规则。中间公司只要在形式上符合投资条约的国籍要求,即为投资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者。
因此,缔约国如果希望对条约选购予以限制,就必须在条约的文本中明确地予以体现。而是否限制以及采取何种模式进行限制则要视缔约国之间的政策考量与利益权衡而定,而且针对不同的缔约相对国也完全可能采取不同的模式。一国在对外签订投资条约时需要综合评估投资条约对外资的吸引力、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对条约选购者的限制、对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对本国政策空间的可能限制等。在当前仍然以大力吸引外资和推动对外投资为主导的政策背景下,东道国对投资者选购投资条约的现象更倾向于有限度的容忍。
中国在其签订的投资条约中,多数规定法人投资者具有注册地国国籍,而未对其作出其他的国籍联系要求或者纳入拒绝授惠条款,因此留给投资者进行条约选购的空间非常大。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有相当的部分是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等自由港进行的对华投资。(59)而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六成的投资流向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60)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面临着第三国投资者通过上述自由港选购投资条约的风险,而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则意味着可以通过上述自由港的离岸优势寻求更为有利的投资条约的保护。因此,对于不同的缔约相对国是否有必要限制条约选购以及如何限制条约选购并不能得出一刀切的结论。
投资者的条约选购无可厚非,但控制条约选购对本国的不利影响至关重要。缔约国有必要在投资条约中明确是否允许以及允许哪些条约选购行为以维护本国及本国投资者利益。尽管目前中国仅有一例被诉案件(61),而中国投资者对外国提起的三起投资仲裁案件(62)也并无涉及条约选购问题。但是随着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迅猛发展,中国被外国投资者起诉或中国投资者起诉外国政府“只是个时间的问题”(63)。中国有必要对其对外签订且已生效的102项BIT(64)以及4项已生效的含有投资章节的FTA(65)进行评估(评估指标体系可包括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环境指标等(66)),并考察投资者在这些条约下可进行条约选购的潜在空间以及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如有必要可积极寻求修改或终止某条约。同时,对于尚未生效或正在谈判中的BIT与FTA,进行事前的条约评估也尤为重要,通过系统的指标评估,可以将投资条约中的权利义务以及条约选购的潜在风险转化为效益和成本,进而作出相应的预案。
①国际投资条约主要包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下简称BIT)以及包含投资章节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FTA),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FTA)、《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ASEAN)、《欧洲能源宪章》(以下简称ECT)、中国与新西兰FTA等。
②A.C.Sinclair,The Substance of Nationality Requirem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20,No.2,2005,p.357.
③中间公司(Intermediate Corporations)这一概念在不同场合也经常被称为控股公司(Holding Corporations)、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s)、空壳公司(Shell Corporations)、邮包公司(Mailbox Corporations)或导管公司(Conduit Corporations)等。
④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情况下,投资者无须通过公司国籍的包装而可径直依据最惠国待遇条款选购第三方条约,但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此种情形都存在激烈争论,本文暂不讨论该问题。参见徐崇利:《从实体到程序: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之争》,载于《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第41~50页。
⑤Mattew Skinner,Cameron A.Miles & Sam Luttrell,Access and Advantage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reaty Shopping,Journal of World Energy Law & Business,Vol.3,No.3,2010,pp.260-285.
⑥UNCTAD,Scope and Definition:A Sequel,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11,p.82.
⑦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German Branch,The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ity of Investors under Investment Protection Treaties,2011,pp.28-31.
⑧OEC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Understanding Concepts and Tracking Innovations,OECD Publishing,2008,p.18.
⑨TSA Spectrum de Argentina SA v.Argentina,ICSID Case No.ARB/05/5,Award./05/5,Award.
⑩Camuzzi Int'l S.A.v.Argentina,ICSID Case No.ARB/03/2,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1)Sempra Energy Int'l v.Argentina,ICSID Case No.ARB/02/16,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2)Enron Creditors Recovery Corp.(formerly Enron Corp.)and Ponderosa Assets,L.P.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1/3,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a.50.
(13)Siemens A.G.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2/8,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a.137.
(14)Waste Management Inc.v.United Mexican States,ICSID Case No.ARB(AF)/00/3,Aard,para.85.
(15)Enron Creditors Recovery Corp.(formerly Enron Corp.)and Ponderosa Assets,L.P.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1/3,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a.52.
(16)Martin J.Valasek & Patrick Dumberry,Developments in the Legal Standing of Shareholders and Holding Corporation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s,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26,No.1,2011,p.55.
(17)Saluka Investments BV(The Netherlands)v.The Czech Republic,UNCITRAL,Partial Award(Mar.17,2006),para.229.
(18)朱慈蕴:《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载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第73~81页。
(19)Case Concerning the 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Ltd.(Belgium v.Spain),Judgment,1970 ICJ Rep.3,paras.56-58.
(20)See,e.g.,Katherine E.Lyons,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Syracu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Commerce,Vol.33,2006,p.523.
(21)Saluka Investments BV(The Netherlands)v.The Czech Republic,UNCITRAL,Partial Award(Mar.17,2006),paras.229-241.
(22)ADC Affiliate Ltd.and ADC & ADMC Mgmt.Ltd.v.Republic of Hungary,ICSID Case No.ARB/03/16,Award,paras.353-359.
(23)Aguas del Tunari S.A.v.Republic of Bolivia,ICSID Case No.ARB/02/3,Decision on Respondent's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paras.245,321,330-332.
(24)Tokios Tokelés v.Ukraine,ICSID Case No.ARB/02/18,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as.38-43,56.
(25)Tokios Tokelés v.Ukraine,ICSID Case No.ARB/02/18,Dissenting Opinion of Prosper Weil,paras.27-30.
(26)The Rompetrol Group N.V.v.Romania,ICSID Case No.ARB/06/3,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as.81-85.
(27)TSA Spectrum de Argentina SA v.Argentina,ICSID Case No ARB/05/5,Award,paras.140-154.
(28)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仲裁员Grant D.Aldonas发表了不同意见,其认为仲裁庭揭开荷兰公司面纱的结论不存在任何依据。参见TSA Spectrum de Argentina SA v.Argentina,ICSID Case No ARB/05/5,Dissenting Opinion of Arbitrator Grant D.Aldonas。
(29)Christoph 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nd ed.,2009,p.323.
(30)Christoph Schreuer,Nationality of Investors:Legitimate Restrictions vs.Business Interests,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24,No.2,2009,pp.525-526.
(31)Phoenix Action,Ltd.v.Czech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6/5,Award,paras.100,135-144.
(32)Brigitte Stern,Are There New Limits on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25,No.1,2010,pp.26-36.
(33)Mobil Corp.and Others v.Venezuela,ICSID Case No.ARB/07/27,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as.190-205.
(34)Mihlaly Int'l Corp.v.Sri Lanka,ICSID Case No.ARB/00/2,Award.
(35)Banro American Resources,Inc.and Société Aurifère du Kivu et du Maniema S.A.R.L.v.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ICSID Case No.ARB/98/7,Award.
(36)Pac Rim Cayman LLC v.The Republic of El Salvador,ICSID Case No.ARB/09/12,Decision on the Respondent's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s,paras.2.99.
(37)该案中可适用的投资条约为《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萨尔瓦多为该协定成员国,而本案申请人的原国籍国英国以及申请人母公司的国籍国加拿大并非协定成员国。
(38)Robin F.Hansen,The Systemic Challenge of Investor Nationality in An Era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ournal of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Vol.1,No.1,2010,pp.81-116.
(39)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German Branch,The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ity of Investors under Investment Protection Treaties,2011,p.51.
(40)Rudolf Dolzer & Christoph Schreuer,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54.
(41)Barton Legum,Defining Investment and Investor:Who is Entitled to Claim?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22,No.4,2010,pp.521-526.
(42)Stephan W.Schill,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17-219.
(43)Roos van Os & Roeline Knottnerus,Dutch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A Gateway to “Treaty Shopping” for Investment Protection b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Amsterdam,SOMO,2011,pp.28-29.
(44)拒绝授惠条款(denial of benefits clause),也译为“利益拒绝条款”或“利益否决条款”。我国2010年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第10条中使用了“拒绝授惠”的用语,本文从之。
(45)漆彤:《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利益拒绝条款》,载于《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9期,第98页。
(46)Michael Waibel,Asha Kaushal,Kyo-Hwa Chung & Claire Balchin(eds.),The Backlash against Investment Arbitration:Perceptions and Realit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0,p.11.
(47)包括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BIT、中国与墨西哥BIT、中国与东盟投资协定、中国与新西兰FTA、中国与秘鲁FTA、中国与加拿大BIT等。
(48)Supra note ⑥,pp.93-94.
(49)Plama Consortium Ltd.v.Republic of Bulgaria,1CSID Case No.ARB/03/24,Decision on Jurisdiction,paras.155-165.
(50)Supra note ⑥,p.98.
(51)Michael Waibel,Asha Kaushal,Kyo-Hwa Chung & Claire Balchin(eds.),The Backlash against Investment Arbitration:Perceptions and Realit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0,p.26.
(52)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MTO v.Ukraine,SCC Case No.080/2005,Award,paras.61-69.
(53)Generation Ukraine,Inc.v.Ukraine,ICSID Case No.ARB/00/9,Award,paras.15.7-15.9.
(54)Yukos Universal Ltd.(Isle of Man)v.Russian Federation,PCA Case No.AA 227,Interim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paras.441-443,456-459.
(55)A.C.Sinclair,The Substance of Nationality Requirem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Vol.20,No.2,2005,p.385.
(56)根据《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第10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缔约另一方的企业是由该缔约方的国民或企业拥有或控制且该企业在另一方境内为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则缔约一方可拒绝给予该企业以本协定项下的利益。而根据该范本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一项投资是由缔约一方的国民或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在该缔约一方进行,且该企业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未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缔约一方可拒绝给予该企业享有缔约另一方的企业及其投资以本协定项下的利益。有关该条文的内容和评论,可参见温先涛:《〈中国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论稿(二)》,载于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9卷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57)中国与加拿大BIT于2012年9月9日签订,目前尚未生效。BIT全文参见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官方网站,http://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acc/fipa-apie/china-text-chine.Aspx?lang=en&view=d,2013年3月10日访问。
(58)报告全文参见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官方网站,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trade/trading-our-way-to-more-jobs-and-prosperity.pdf,2013年3月10日访问。
(59)参见商务部中国投资指南外商投资统计专栏,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wstztj/default.htm,2013年3月10日访问。
(60)参见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jwtztj/default.htm,2013年3月10日访问。
(61)Ekran Berhad v.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ARB/11/15,pending as of 2013.
(62)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Limited and Ping An Insurance(Group)Company of China,Limited v.Kingdom of Belgium,ICSID Case No.ARB/12/29,pending as of 2013; China Heilongjia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 Technical Cooperative Corp.,Qinhuangdaoshi Qinlo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and Beijing Shougang Mining Investment v.Republic of Mongolia,UNCITRAL Case,pending as of 2013; Tza Yap Shum v.Republic of Peru,ICSID Case No.ARB/07/6.
(63)Zhuang-Hui Wu,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for Chinese-Foreign Disputes:Emerging Choices in 2012,International Law News,Vol.41,No.2,2012,p.8.
(64)参见商务部条法司“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专栏: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html,2013年3月10日访问。
(65)包括中国与东盟投资协定、中国与巴基斯坦FTA、中国与新西兰FTA、中国与秘鲁FTA。中国与新加坡FTA规定在投资义务方面适用中国与东盟投资协定,中国与哥斯达黎加FTA在投资义务方面确认双方在中国与哥斯达黎加BIT中的义务,但该BIT尚未生效,参见商务部自由贸易区服务网专栏:http://fta.mofcom.gov.cn/fta_qianshu.shtml,2013年3月10日访问。
(66)参见车丕照:《认真对待条约——写在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载于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8卷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