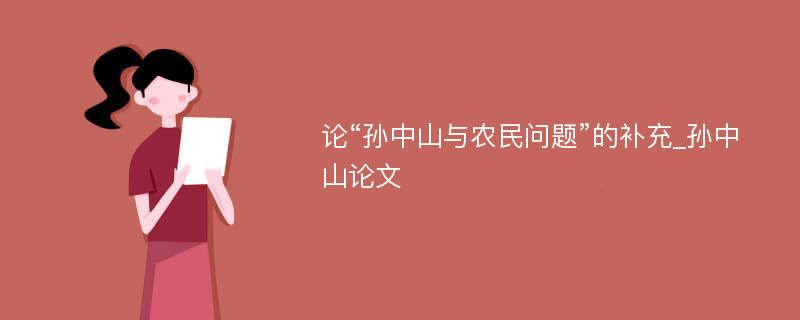
“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6-0014-09
“孙中山与农民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内地学者非常关注并取得很多成果的领域,但对其中某些具体问题仍可商榷、补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谈一些补充看法。
一、早年“贫困农家子”经历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领导改革、革命的政治家当中,像孙中山那样出身于普通农家者为数甚少。孙中山出身于怎样的农家?以往曾有过“贫农”、“农民小生产者”、“富农”、“中农”等不同说法①。对孙中山的家庭状况及早年经历,本师陈锡祺教授以及黄彦、李伯新等学者曾做过调查研究,并在自己的论著中作了阐述②,他们作出的结论是相当谨严的。不过,“贫农”、“中农”等是20世纪中国内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概念,其依据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多少以及有无剥削收入,但即使在1950年代土改时要准确地评定一个农村家庭是什么“成分”往往也不容易,要确切评定历史上的一个农家的“成分”就更困难了。在孙中山出生前后孙家拥有多少土地?具体的家庭收入如何?现在已经不可能找到直接的、可靠的证据(如地契、租约)来说明,基本只是依据后来的口述史料,有不同说法也是很自然的。
孙中山早年说过自己“生而贫”,“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某也,农家子也,早知稼穑之艰难”[1] (P1,18,25)。兴中会时期他回答宫崎寅藏关于平均地权之说得自何处的提问时说:“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需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略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1] (P583)综合各种史料,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躬耕数代”的贫困农家,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如果考虑到孙中山说话的对象和语境,那么,即使是有一些土地的“自耕农”,也可以说是贫困的。
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曾见过孙中山胞姐孙妙茜。罗称孙氏为“耕读人家”,所记孙妙茜讲述家庭状况是“祖父敬贤公,以耕读起家,甚有钱,后以醉心风水,屡事坟工,所费不赀,变卖田地,入不敷出,家资遂耗”;“(父亲达成公)初时家尚小康,以迷信风水,遂致贫苦日甚……”③。所有口述史料都会受时代背景和记录者观念的影响,罗氏有意对孙氏家世及源流作重新建构,且研究方法与结论都大有问题[2],他所说的孙氏“耕读起家”乃是无根之谈。比罗香林稍早去翠亨故居的王斧,所记孙妙茜的说法是“我家很穷,我父亲四十余岁前,完全是一个工人。曾在澳门充当鞋匠,每月工钱四块,一年统共四十八块。后来他又辞了那种职业,回来耕种兼畜牧。田园不过二三亩,但种菜呀,养猪呀,是尽够的”[3]。而钟公任所记孙妙茜的说法是“曾祖父母业农,有田产十余亩,祖父母亦业农(祖父信堪舆学,常游玩山水),其时家境渐窘,曾因急需而变卖多少”;“达成公二十岁以后、三十岁以前,在澳门学做皮革工,卅岁以后回家耕种”;“总理之兄眉公出洋时,曾将仍存之田数亩卖去,以作川资”,钟公任接着写下:“则其时家非小康可知”[4]。
到了1950年代以后,翠亨村的所有口述史料,谈到孙家经济状况时几乎都称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没有土地,只是租种弟弟或祖尝的田地[5] (P59~166)。考虑到在记录口述时中国内地乡村极为重视“贫雇农”、“贫下中农”阶级成分的社会氛围,而口述者本身并非孙家成员,谈的又是百多年前的事,所以,其可信性不能不打折扣。相比较而言,在孙家是否有一些土地这个问题上,笔者更愿意相信王斧、钟公任所记录的孙妙茜的忆述。
翠亨孙中山故居现存的一些文物,可能有助于了解孙中山出生前孙家的经济状况,黄彦、李伯新早就这样做了,本文只是作一些补充。
孙妙茜保存的翠亨孙氏祖尝帐册,记录宗族内部的一些收支④。从道光廿六年(1846年)到咸丰三年(1853年)每年都有“田价银六两六钱正”的记载,这些“田价银”都是前一年就预交的,看来就是祖尝田的地租了。但从头到尾都看不出孙中山的祖、父是承耕这些田亩的人,却有何汉明、孙国贤、孙业贤、黄三交谷或欠谷的记载。显然,尝田的“田价银”及租谷是主要的宗族收入。这些钱也用于借贷生息,借钱者既有族人如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以“息银二分”借了六两)和孙恒亮、孙国贤,也有何、李、陆等外姓人,利息也是公尝收入的来源之一。
翠亨孙氏人丁有限,从道光廿八年(1848年)到咸丰四年(1854年),帐册每年基本上都有“隔年”、“清明”(祭祖)支出的详细记录。在“隔年”、“清明”,孙族都举行祭祀,祭后宗族一起聚餐,每次用米一两斗,还有猪肉(少则两三斤,多则十几斤)、咸鱼、塘鱼、虾米、茨菇、鸭蛋、蔬菜、咸菜、酒、茶等,有时有礼饼,有些年份记有“男孙利市”(红包,只有40文),是给孙家新生男孩的。帐册所记孙族“隔年”、清明聚餐的食物,即使在当日的乡村,也算不上丰盛(都没到提到鸡鸭);但几年间祭祖都没有间断,帐册记载虽简略但尚清楚,至咸丰四年三月宗族“通共存银四十三两七钱四分三”,这笔钱作为一个乡村小家族可以动支的现金,在当时不能说微不足道。宗族有限的基金在族人、乡人有困难时可以借贷;孙中山祖父孙敬贤于光绪廿八年借的6两银子,按期缴交利息,至咸丰五年归还6两本银(孙敬贤本人已于5年前去世);而孙达成恰在这时掌管公尝帐目(帐册有“达成手收”银两的记录),一个家族,按理也不会选一个特别贫穷的成员负责族内收支;综合以上情况,是否可以作如下推测:孙氏家族与孙达成的家庭虽在艰难度日,但还不至于过不下去。
帐册反映的是孙中山出生前一二十年的情况,到孙中山出生后,有几年是孙中山的家庭最艰难的时期:孙达成已经50多岁,体力应该大不如前,几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年长的儿子孙眉出洋去了,为筹集旅费还卖掉家里的田地。孙中山的一姐一兄都在这个时期殇折,应与家庭生活极为困苦有关。但不久孙眉在檀香山逐渐致富,孙家的生活也就改善了。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活了62岁,祖母黄氏活了78岁,父亲孙达成活了76岁,母亲杨氏活了83岁,这在当日的乡村算是很少见。如果经常饥寒交迫,不可能两代都如此长寿。
晚清农民起义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是学者们曾经谈论得比较多的问题。
孙中山曾对宫崎寅藏说过早年听过“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的谈话,于是产生了革命最初的动机[1] (P583)。从20世纪初开始,一再有回忆录提到,孙中山少年时代已经知道太平天国,青年时代即以洪秀全的继承者自命。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内地崇尚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强调孙中山对晚清农民起义的继承。但对以往的一些说法,还是可以推敲一下的。
如果我们看当时产生的史料,那么,不难看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是把太平天国看成是“汉族”反对“满清”的起义,在很多情况下,革命党人还有意地把太平天国的人物士大夫化。1904年孙中山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所作的序言,完全把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汉族人的王朝来看待[1] (P258~259)。真正的太平天国历史,民国以后才逐渐有人研究,而把太平天国称为农民起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以后才有的观念。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他革命党人,当时对太平天国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综看孙中山所有言论、著作,他并没有把太平天国与农民加以联系。
讲到孙中山与晚清农民起义关系时,我们发现,很多口述史料都提及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赞扬,但是,孙中山家乡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几乎没有出自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新会等县的,这个地区即使有人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人数也不会多。而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另一场农民起义——红兵起义则席卷了珠三角。咸丰四年五月,何六在东莞石龙起义,越过番禺、顺德向香山进攻,香山当地的会党、“盗匪”也纷纷响应,尽管我们不知道香山有多少农民参与,但按照历史上一般的情况,数量应该不少。此后十多个月,香山几乎全境都成为清朝官兵、团练与红兵的战场,红兵围攻县城,占领小榄、黄圃、黄角、曹步、古镇、海洲等乡镇,孙中山家乡翠亨附近的南蓢、下栅也发生过战事[6] (卷22,纪事)。这场农民起义对孙中山有无影响?虽然孙中山也经常讲到会党,但从来没有谈过会党发动的这次红兵起义。日后产生的口述史料也没有提及,似乎几十年以后当地人已把这场大动乱完全忘却。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当时产生的一些资料。孙中山的先辈在这场农民起义中有什么遭遇?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直接说明。不过,起义发生时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41岁,叔父孙学成28岁,另一个叔父孙观成23岁(根据口述史料,两个叔父都不在家乡),都正是壮年;他们在战乱后又都健在,孙达成、孙学成还列名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修翠亨祖庙碑记(这个碑记完全没有提及刚刚平息的大战乱)。孙中山的长兄孙眉恰恰生于咸丰四年,孙中山的祖母黄氏、母亲杨氏、婶婶程氏等都是小脚妇女,但她们都安然度过了这场动乱⑤。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肯定:孙达成兄弟没有卷入红兵起义,否则,在清朝官吏、士绅、团练对起义者严厉镇压的情况下,他们不大可能一家都平安无事⑥。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长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贫苦,但尚不至于朝不保夕,从现有的史料看不出他们身上有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孙中山晚年对美国人林白克的忆述,也称孙家的先辈“绝对信仰天子和村中的偶像”,“决不愿违反古训做政治上的叛徒”[7] (P34,156)。因此,笔者认为,孙中山早年“贫困农家子”的经历,对他日后决心改造中国、造福民生有影响,但对他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影响,则不易作出结论。
二、辛亥革命时期对农民的发动
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在近代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内地学术界研究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时无不联系农民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受历史上农民“均平”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土地纲领,是重要和直接的思想渊源[8] (P360~361)。
可能没有哪种农民起义的文献会像《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受到中国内地学术界的重视,对它的内容、性质、作用等问题,学者们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对这个制度反封建的积极意义,都给予高度评价⑦。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实行,甚至它是否被广泛宣传过也可怀疑。当时收集太平天国情报、文件不遗余力的张德坚,在《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后,仍记下“此书贼中似未梓行,迄未俘获”[9] (P253)。这至少反映出,《天朝田亩制度》的实际影响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没有发现多少太平军宣传这个制度或者农民因这个制度参加、支持太平天国起义的记载。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千方百计毁灭其文物文献,一些文献流落国外才得以保存。1924年程演生在巴黎找到一批太平天国印书,其中有《天朝田亩制度》,他把这批印书整理介绍,中国国内才逐渐有人知道[10] (P619)。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亲密同志,都没有在著作中提到过《天朝田亩制度》,只是谈过平均主义的“公仓”(圣库制度)。甚至到了晚年,孙中山在讲到太平天国的赋税、财政时也只是根据一些明显不可靠的传言[11] (P472)。因此,笔者认为,孙中山直至逝世,没有看过甚至并不知道《天朝田亩制度》。至于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均平”的史料,在195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专门整理,知道的人也不会多,孙中山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也没有提起过。所以,要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影响,还必须找到更多直接的证据。
从目前所见的史料,可以断定,孙中山确实认真思考讨论过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冯自由说,孙中山19世纪末同章太炎、梁启超等讨论过中国未来的社会问题与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12] (P144)。梁启超称,孙中山对他说过,“孙文尝与我言矣,曰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之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13] 章太炎转述孙中山的意见是:“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1] (P213)。这些,都是研究者非常熟悉的史料。不少学者讲到,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辛亥革命时期,从讨论、关注农民如何获得土地,到一再公开申明并不是要“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在政纲里完全不提农民—土地问题,是因为革命党人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且害怕因此而把想要争取的汉族官僚、士绅吓跑,同时也怕在这个问题上授保皇派攻击的把柄;革命党人在讲平均地权时只是注重城市土地,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所说的“地主”,主要指工商城市的土地所有者,与日后专指乡村中占有较多土地、依靠地租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不同。笔者同意这些看法,但也想再作些补充。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民的支持和自觉参与,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制定和实行了让农民获得土地的政策,所以,195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学者讨论近代的政治改革与革命时,通常就会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的理论、政策及其实践作为参照。例如,我们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个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纲领,没有分土地给农民,所以无法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孙中山那个时代,孙中山有可能提出这样的纲领吗?就算有,就能够发动农民吗?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是因为其土地纲领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清末以来对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中国共产党还吸收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教训,同时借鉴了苏俄的经验。党的领导人、理论家亲身到乡村进行调查研究,经历过不少失败、挫折才制定出一套可操作的土地改革政策。而宣传、实行这个政策,又依靠初步建立的政权,派出党员、干部、军队深入农村,在一些地区建立起足以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局面后,先进行土改的试点,然后逐步实行、推广到更广阔的省区,最后取得全面成功。
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曾经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武库寻找过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些办法远离时代的要求;引进外国的方法,与中国国情又未免凿枘;当时也没有针对全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科学研究成果可供他们制定政策时作参考。无论孙中山还是其他革命党人,对乡村和农民的知识,大体上只能来自自身的体验,而革命党人当中,与乡村和农民有关系的人很少,更缺乏能够深入乡村的有理论、有理想、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如果有一个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纲领,又有办法向农民宣传,并组织农民实施,这当然有可能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有无可能做得到?地主的反抗以及农民的接受、合作都是问题。以同盟会的动员、协调能力,就算有这样一个纲领也无从实施。太平天国曾经有过一个土地纲领,但洪秀全等人还是宁可用土洋结合、神秘俚俗的上帝教去发动农民。所以,以往对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未免是苛求前人。
孙中山要进行一场推翻清皇朝的革命,自然要发动、依靠相当数量的群众参加,以往学术界也注意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主要通过会党发动部分农民,甚至通过新军与农民取得联系[14] (P320~321)。这些看法,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的。当然,被革命党人发动的人,未必全是躬耕垅亩者,其骨干或积极分子多是乡村的一些边缘群体如流民、盗匪等,他们或是破产农民,或仍在乡村不时以劳力谋生;然而,当社会动荡到了一定程度,或者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就肯定会有大批农民放下手中的农具卷进革命。因此,“农民”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乡村的下层居民。革命党人用什么具体的方法去发动他们?发动的效果如何?这也是本文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辛亥革命中,惠州起义、萍浏澧起义,参加者数以万计,武昌起义后各地民军蜂起,人数更多。考虑到广东的起义与孙中山的关系更为直接与密切⑧,就以广东的例子作些分析。例如1900年的惠州起义,参加者达2万余人,从日后的口述史料看,其中也有不少耕田的农民[15] (P1~19)。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在不到半个月就发动了十几万民军向广州进发,对促成广东“和平光复”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民军,用胡汉民的话说,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16] (P46),列入军政府统计的民军人数曾达到148,400人[17],此外,各县不在广东军政府领取军饷的民军更是不计其数。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拿起武器组成队伍举着革命党的旗帜,或在革命党人率领下投身革命,这是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场景!以往,我们可能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动员农民的程度估计过低了。
革命党人也以革命成功后经济生活的改善来发动农民。孙中山后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不少人说“革命成功,我们大家有平(便宜)米吃”,孙中山认为这句话可以作向群众宣传的材料[11] (P575)。因为珠三角地区大量农田改种经济作物,很多农民都籴米而食,乡村地区更有大量靠出卖劳力为生的人,所以,“食平米”也成为动员乡村下层居民的口号。如在顺德,革命党人便用“食平米都来当民军”作号召[15] (P249)。同盟会在乡村发动农民的方法五花八门,盗匪出身的同盟会员李福林曾记述自己与绿林首领陆领、谭义等在顺德龙冈(江)“唤起民众”的情况:“头班名剧演出,四乡民众来观剧了。于是每日锣鼓开场前,在棚正中搭起演讲台,在演讲台演讲三民主义……又于是开始招收革命党徒,手续越简单愈妙,只要在盟约上签一个名字,或打下一个指模,就认为是新同志。几日之间,前来加盟成为新同志的共有几千人。”[18] 日后李福林成为孙中山属下的军事将领,到了20年代,鲍罗廷称李福林为“唯一一个确实同农村、同农民结合在一起,而在城市里同商人结合在一起的将领”[19] (P109),这当与他出身乡村并在辛亥革命时期发动过农民有关。
没有资料显示,同盟会曾以土地问题去发动农民,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当然更不会用地主—农民这种阶级对立的观念去发动农民。但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是没有文化的乡村居民也听得懂的语言,此外,反抗官吏、豪绅也是宣传的内容。革命党人建立政权后,有些同盟会员对农民作过民生主义的宣传,例如,一批同盟会员1912年在广州创办的《民生日报》,宣称“以民生主义为宗旨”。该报有一首“龙舟”“劝农夫”有如下的句子:“故此富者买埋天咁阔嘅田土,贫者想话耕锄食力,可叹尺地全无……富者就把地权垄断为圈套,我地农民无奈,就要做佢富家奴……佢坐食安居,为做米蠹;任得我地两餐唔足,子泣妻号……短衣缩食,都要顾住交租,想起番来,真正喺唔公道……此事总因,全在地土,只为地权,全在佢的富豪操。想话把农业振兴,亦唔到你展布……想话把农业振兴,以边一件为首务?平均地权,乃喺法理最高……然后农业可以自由谋进步,何限好。”[20] 龙舟的作者用粤语、用通俗口语讲民生主义,自然是为了适应向文化不高的农民宣传的需要,应该也考虑到对不识字的农民演唱的可能性。这首龙舟触及了农民—土地问题,但对如何解决则只有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这类宣传应该不会是个别现象,只是类似的史料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很难作进一步的推论。
要分析革命党人获得政权之后与农民的关系,广东军政府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对象,因为这个政权基本上由一批最接近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掌握,同盟会员在各级政权、军队、警察、省议会中都始终占绝对优势⑨。广东的同盟会政权曾实行过限制、打击士绅的政策。例如,1912年,民国初年,朱执信根据都督命令裁撤顺德士绅把持的东海护沙局,禁止抽收各种沙费,反映了他们“共和时代,一切平等,故不能以绅富专制农佃”的理念⑩。但是,广东军政府在解散民军、清乡、大量发行缺乏准备金的纸币、恢复清朝的苛捐杂税等问题上,又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们没有取得农民的支持,不得不向士绅寻求合作,于是,基本只能够沿用清朝的办法施政[21]。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并没有把农民作为特殊对象的政策,也没有针对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的政策。革命党人无论从哪个阶级或阶层中都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支持者。今天我们可以讨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政策的各种失误,但革命之所以失败,农民政策的失误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三、关于孙中山晚年与农民的关系的一些问题
关于孙中山晚年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他的农民—土地政策,更是学术界几十年来非常关注的课题,有很多高水平的成果(11)。但一些具体问题,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众所周知,孙中山晚年思想、政策的变化与“以俄为师”有关,主要受苏俄影响。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动员工农参加革命,这对孙中山有极大吸引力。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孙中山和国民党在几个月内发布了一系列命令、章程,孙中山本人也为此有多次演讲和谈话。
在改组之前,国民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农村政策(12)。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为筹备改组颁布的党纲草案,讲到民生主义时,只是用“掌母财者,田连阡陌,事生产者,贫无立锥”这种在古代典籍都可以找到的语言带过乡村的土地问题[22]。不过,这个党纲并没有提交后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讲到民生主义时说到:“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23] (P82~83)。研究孙中山的学者都知道,这个决议便是“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蓝本,而宣言最后其实是孙中山本人、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共产国际、苏俄顾问(鲍罗廷)、一些中共党员(如瞿秋白)等意见的综合、妥协的产物。最后形成的宣言,虽有发动工农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内容,谈到土地问题时则没有采用共产国际关于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只是承诺革命成功后对缺乏土地的佃农“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以及“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但对国家如何获得土地再分给缺地农民则没有提及(13)。在差不多同时形成的、孙中山同样重视而且更反映孙中山本人观点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对土地问题的方针只是孙中山以往“平均地权”理论的重申,完全没有提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发动农民的问题[24] (P126~129)。
此后几个月,国民革命运动发展迅速,国民党推行“扶助农工”政策,以政府力量支持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开办农民讲习所以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尤其是1924年5月以后,政府同广州商界关系日渐紧张,8月,商团事件发生,革命政府面临严重的危机,在争取工农支持的问题上持更为激进的态度。现在看到孙中山关于发动农民的言论,多数是在商团事件期间发表的。7月28日,孙中山亲自对农民发表演说,对农民的境遇公开表示同情,号召农民“结成团体”、“练农团军”,承诺政府予以帮助,“以极低的价卖枪”给农团军,并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反抗田主、商人[25] (P460~466)。8月21日,孙中山又在一次演说中专门讲“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但他又强调不会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希望农民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25] (P554~558)。在稍早的“民生主义”第二讲(8月10日),孙中山主要还是讲“定地价税、照价纳税、涨价归公”[24] (P381~391);第三讲(8月17日)讲到“耕者有其田”,但所讲的办法是“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24] (P399~400)。与此同时,孙中山在一次私下的谈话中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承认国民党“不能与农民成功地接触”;表示日后要“把迄今在地主手中的所有土地转交给农民”,但农民必须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以后“才能对土地问题实行急进的解决办法”[26] (P515~517)。
如前所述,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已讨论过农民—土地问题,“必能耕者而后授之田”、“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等言论,其涵义与“耕者有其田”差不多。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只是私下讨论,到晚年则公开以“耕者有其田”向农民号召;不过,私下的态度还是比公开的言论激进些。孙中山之目标,既在发动农民以使革命取得成功,同时也在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境遇。但他又一再表示不接受俄国夺取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26] (P451)。对此,也是可以做些补充分析的。
在农民问题上,孙中山借鉴苏俄的经验,主要是通过苏俄顾问(特别是鲍罗廷)进行(14)。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孙中山又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
当然,首先是因为孙中山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主张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他主要是把苏俄的经验当作一种革命技术来看待的。苏俄顾问一些脱离中国国情的建议和言论,更会使曾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孙中山觉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才合符实际。在讲民生主义时,孙一再称不能从学理出发,要从事实出发,大概与此有关。
1923年,孙中山有一次与鲍罗廷一同乘船视察广州附近的水道和炮台,途中遭到不知来自何人的枪击,一名水手被打死。鲍罗廷认为“袭击来自农民,他们手执武器保卫自己的稻田”,并以此作为“必须在农民中做工作”的例证[27] (P372)。鲍罗廷在不知道枪击者的身份时就从自己固有的观念出发称之为农民,这就很难说服对广东乡村、盗匪有较多了解的孙中山。1923年11月中旬,孙中山的军队在东江前线溃败,孙本人狼狈退回广州,陈炯明的军队兵临城下。鲍罗廷建议“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尽可能地召集数量众多的党员,骑自行车、开摩托车、划舢板、乘汽车把这些法令带到农民中去”,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千万农民支持战争、消除对广州的威胁[28] (P41~43)。但孙中山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办。鲍罗廷1926年2月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使团报告时,回忆起孙中山反对其建议理由是:“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贯彻执行,因为我们的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组织起来,在我们和农民之间有豪绅,如果我们颁布法令,那么这个法令会首先落到豪绅手里(如果法令能传到农村的话),豪绅就会利用法令反对我们,并且他们不仅把军阀也把农民发动起来反对我们。因此首先应当着手组织农民。”[26] (P128)且不说鲍罗廷的建议未免缓不济急、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广东乡村(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民团基本为豪绅掌握,而民团又经常参与广东各派政治势力的战事。因为国民党在乡村地区毫无基础,如果真颁布了这个法令,直接的后果很可能是动员大批民团参与到陈炯明一边与革命政府作战。所以,孙中山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对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乡村,孙中山是熟悉的,他明白在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农民的力量远不及豪绅,前文提到的7月28日、8月21日的演讲,8月10日的私下谈话,都讲到地主豪绅力量比农民强大,必须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才可以同地主豪绅对抗。在当日的广东,地主豪绅拥有强大的武力,红兵起义以后,乡村士绅控制的地方武力,实际上成为基层权力机构[29]。仅从武装的比较即可看出广东地主与农民力量的差距。据日本人涉谷刚1925年到达广东后的调查,广东省民团仅新式步枪就有128,000支以上[30]。20年代末的又一项调查说,番禺、东莞等10个县的民团有枪20万余支,其中仅番禺县的民团就有10万余支[31] (P15)。1926年4月《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则称:“据前年调查,南海一县有二十万枪以上,番禺与顺德都有十八万以外,就举这三县作比例,可知广东能武装起来的民众不在少数。然而这些都是正当自卫的有枪阶级。”[32] 农民团体(如农民协会)虽也有武器,但无论数量质量都远不如民团。如果农民在未有充分组织与武装的情况下与地主冲突,那即使政府派军队介入也难于控制局面。珠三角虽然是农民运动兴起较早的地区,但农民运动发展的阻力一直很大,主要原因是珠三角地区地主士绅拥有强大的武力。从当时广东省的省情看,孙中山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孙中山希望在“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近代中国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始终珍视的“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的平均地权方法,在近代中国也缺乏可操作性。不过,孙中山关于工商发展必然会引起城市地价暴涨的预见,关于地价暴涨产生的财富必须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不能由少数人吞占,以及政府必须对乡村贫穷的居民予以特别的关心与帮助的主张,在今日应该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尽管未必可以按照他的具体方案去做。
注释:
①丁凤麟:《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见苏双碧主编:《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74~376页。林白克的《孙逸仙传记》第60页(徐植仁中译本,上海开智书局1926年版)提到孙家祖上有数千亩土地(英文原文" several thousand mow" ),应是不可能的事。
②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孙中山年谱初编编纂组:《孙中山年谱初编》第一分册(1965年油印本)有关部分;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收入《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罗香林:《国父孙公家世考》,广州《更生评论》第2卷第2期,1938年。后来罗香林在《国父家世源流考》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
④该帐册封面以毛笔写有“道光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记部”,并有“乐安堂号”、“仕合号”字样。“乐安”是孙姓郡望。帐册有“达成手收入”的记录,与若干口述提到孙达成曾管公尝相符合。但开头有孙敬贤借银的记录,其时管帐的应该是族内其他人。该帐册内容到咸丰四年为止。对帐册的内容,笔者尚未敢说完全读懂。
⑤各人生年据孙满编《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翠亨故居收藏)。
⑥香山绅士林谦留下的文件提到四、大两都团练实行“十家连坐”、“格杀勿论”等办法对待“贼匪”。见《广东红兵起义史料》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1~894页。翠亨村属大字都,正归该处公局管辖。
⑦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第2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把《天朝田亩制度》列入“志”中做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可作为代表。
⑧如1911年4月底为响应黄花岗起义,陆领等在顺德乐从起事。起义队伍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乐从圩还向居民说:“须候吾主帅在纽约发出命令始图进取。”(岭南半翁:《辛亥粤乱汇编》第5章第4节)其时孙中山正好在纽约。同盟会时期广东的起义或由孙中山本人直接策划,或由胡汉民等人按照他的指示统筹。
⑨关于同盟会员掌握广东军政府的实权,王晓吟的《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和周兴樑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都作了论述。
⑩东海主人:《东海十六沙纪实》之“东海十六沙纪实书后”、“广东军政府办理东海十六沙案之命令”。
(11)例如金德群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1905~1949)》(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和梁尚贤的《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都有很多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其他论著论文甚多,难以一一列举。
(12)1923年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批准之《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第一条即称:“兹为保障农民承佃权利,及维持业主所有权之安全起见,特设本章程保证之”(《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70~375页),这只是一个“整理财政”以及作为业佃诉讼审判准绳的法例,丝毫没有暗示日后要农村的土地关系会变化,反倒是一个维护原有土地关系的法律。
(13)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李吉奎:《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产生》,《孙中山研究论丛》第2集,中山大学1984年版;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见《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14)孙中山对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革命精神抱有好感,但这些年轻的新党员未必能在党的纲领、政策等问题上对孙中山起很大影响,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开始广泛深入农村对农民开展工作,在农民问题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的理论和政策。
标签:孙中山论文; 农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孙达成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