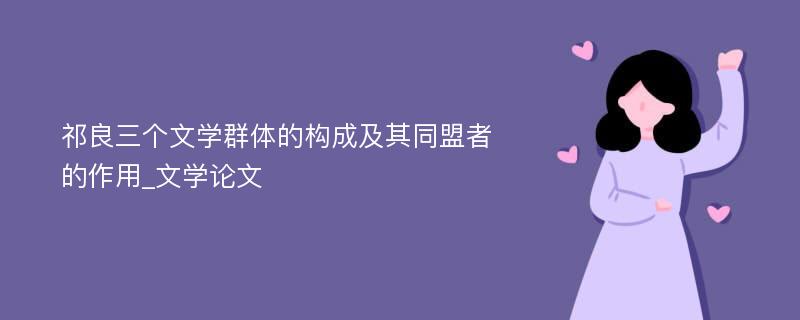
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盟主论文,作用论文,集团论文,文学论文,梁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朝(420—589)文学可谓士族、宫廷和家族的文学。在宋、齐、梁、陈四朝中,刘宋虽历时60年,占整个南朝的1/3还强,但因其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只具有过渡期的特点;陈朝33年,时间不长,且国力衰微、地域日缩,文化愈趋萎靡,已不足与北方相抗衡,又下转隋朝,亦仅具过渡性的特点。所以,真正能够体现和代表南朝文学特征的是齐梁文学。
南朝各代皇室皆出身于武将,他们对士族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接受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士族文人的贵族气息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高和培养起来的。他们以手中强大的政治权力、丰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文化特权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与士族融合。南朝初期的刘宋皇室成员,大多表现出“老兵”、“劲卒”的武夫形象。刘宋文学完全是士族文学,皇室实在是不登文学殿堂的。皇室对士族文人除了政治而外,缺乏其它吸引力和号召力。萧齐一代,皇室的文化修养大大提高。齐高帝萧道成十三岁即受学于鸿儒雷次宗,对诗文颇有鉴赏力。其他诸王也比刘宋皇室喜好文化。齐武帝萧赜虽极重治世,但亦认为“文章诗笔,乃是佳事。”(《南齐书·萧长懋传》)其子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更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他们接纳文士,网罗人才,把文学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萧梁一代,武帝萧衍及其诸皇子的文学素养之深厚、思想理论之精邃、创作实践之成熟,已与士族文人无异。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对士族文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帝王核心地位的不断稳固,皇室文学修养的极大提高,广招文士的蔚然成风,文人学士的望风相投,为以皇室为核心的文学集团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在齐梁不到80年的时间里,便出现了三个以皇室为核心的庞大的文学集团。这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以帝王之尊,积极参加并领导文学创作,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热潮,参与的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之多,产生的文学作品之富,是空前的。这是齐梁文学得以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齐梁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1
萧齐一代,皇室接纳文士已渐成风气。除竟陵王萧子良外,文惠太子萧长懋、豫章王萧嶷、随郡王萧子隆都曾招引文士。然其规模与名气皆无法与萧子良相比。史称,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南齐书·萧子良传》)永明五年(487),萧子良移居鸡笼山, 天下文士纷纭而至,迅速形成了一个以萧子良为核心的西邸文学集团。“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本纪·武帝上》)“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琊王融、陈郡谢脁、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梁书·沈约传》)“竟陵王子良好文学,我高祖(萧衍)、王元长、谢玄晖、张思光、何宪、任昉、孙广、江淹、虞炎、何僴、周颙之俦,皆当时之杰,号士林也。”(萧绎《金娄子·说蕃》)“(张充)与琅邪王思远、同郡陆慧晓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梁书·张充传》)“司徒文宣王及张融、何胤、刘绘、刘掞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慧皎《高僧传·法安传》)所谓“八友”、“得人”、“士林”、“宾客”、“法友”,皆为直接出入于西邸的文人。其他还有王僧孺等,“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南史·王僧孺传》)柳恽,“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梁书·柳恽传》)宗夬,“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并见图画,夬亦预焉。”(《梁书·宗夬传》)谢璟,“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璟亦预焉。”(《梁书·谢徵传》)江革,“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梁书·江革传》)在并游西邸的这些人当中,周颙、王俭、沈约原为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幕僚。周颙原“为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随府转征北。文惠太子在东宫,颙还正员郎,始兴王前军咨议。直侍殿省,复见赏遇。”(《南齐书·周颙传》)王俭曾为文惠太子少傅,“永明三年(485 )(文惠太子)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適句令太仆周颙撰为义疏。”(《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这三人中,沈约依附萧长懋时间最长,也最为萧长懋赏识。萧长懋入居东宫后,沈约为步兵校尉、管书记。“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所谈,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梁书·沈约传》)由于萧子良对兄长萧长懋“甚相友悌”(《南齐书·萧子良传》),二人感情笃厚,其文学活动多集中于一起,所以,仕东宫太子的周颙、王俭、沈约等也就成了萧子良的座上客,并引为子良的知己,成为西邸文学集团的主将。
从庞大的西邸集团成员的构成因素来看,既有政治的结盟,又有文学的结社。在子良周围,范云、王融、沈约不仅是子良的文友,而且是子良政治上的支持者。范云在“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始随王,王未之知也。会游秦望,使人视刻石文,时莫能识,云独诵之,王悦,自是宠冠府朝。”(《梁书·范云传》)从建元初至永明末,范云一直追随于子良的身边。王融可谓是子良最为坚定的拥戴者,为了扶助子良即帝位,还搭上了性命。“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南齐书·王融传》)永明末,“世祖疾笃暂绝,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立子良。上既苏,太孙入殿,朝事委高宗(萧鸾)。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释服还省。……郁林(萧昭业)深忿疾融,即位十余日,……诏于狱赐死。”(同上)沈约曾为萧子良司徒右长史。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子良病逝, 沈约因与子良过密而被萧昭业外放为东阳太守。张融、柳恽亦曾为子良幕僚,“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经佐吏,哭辄尽恸。”(《南齐书·张融传》)除上述诸人之外,其他人游于西邸,多是以宾客、文士的身份,在政治上与萧子良的关系似乎不是太深。因此其活动也就多为文学方面的。“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南史·王僧孺传》)萧子良本人的文学创作水平并不高,“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乏文彩,多是劝戒。”(《南齐书·萧子良传》)但他以亲王之尊,极有兴趣地组织文学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坛盟主。西邸文学集团的活动远不限于文学,但就其主要成就来说,则是在文学方面的。周颙、沈约创立的诗歌声律论以及王融、谢脁、沈约、刘绘等将声律论运用到具体的诗歌创作的实践而创立的永明体,虽然给齐梁文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刻意追求诗歌声律而忽视诗歌的自然美,但对后世近体诗的创立,无疑是功不可没的。这样追求同一文学审美趣味的集体创作,显然是在一定的文学集团内相互交流、切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应该说,诗歌声律论的提出和永明体的创立,是文学集团的集体成果。
西邸文学集团活动的主要时间在永明二年至七年(484—489)。永明七年(489),王俭病逝。永明八年(490),周颙病逝(注:周颙的生卒年,史无明载。 据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1《略成实论记》载,周颙参加了永明七年(489)十月萧子良主办的法会。这次法会延至“八年(490)正月二十三日解座,……即写《略论》百部等流通,教使周颙作论序。”故周颙撰成《抄成实论序》(载《出三藏记集》卷11)由是可知,周颙于永明八年正月尚在世。而萧子显《南齐书》卷41《周颙传》谓:“颙卒官时,会王俭讲《孝经》未毕,举昙济自代,学者荣之。”尚知周颙卒于王俭之前。据《南齐书》卷3《武帝纪》载,永明七年,“五月乙巳, 尚书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俭薨。”则知周颙卒于永明七年五月以前。显然,萧子显与僧祐的记载相左。萧子显与僧祐虽同为齐梁间人,然萧子显生于齐永明七年,他对这段史实只能从他人的回忆或其它文献记载而得知。而僧祐则是身之所历者,而且又与周颙为密友。按常理来判断,僧祐的记载应较可靠。石峻等先生谓周颙“约死于公元四八五年左右”,(《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68页。)不知所据为何?), 萧衍为随郡王萧子隆镇西咨议参军赴襄阳。永明九年(491),谢脁随萧子隆去荆州,范云亦离开扬州任零陵内史。永明十年(492), 王僧孺随王德元出守晋安郡。建武元年(494),王融被赐死,子良病逝,沈约被外放东阳太守。 至此,轰轰烈烈的西邸文学集团在盟主的病逝和主要成员的离去后,迅速地分崩离析,真可谓“树倒猢狲散”。一场热烈而有趣的文学运动就在复杂而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被湮没了。
2
在西邸文学集团凋零、败落的九年之后,“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代齐建梁。萧衍建梁的当年(502)十一月, 即立长子萧统为皇太子。从此,在梁代的前、中期就形成了以萧衍、萧统父子为核心的文学集团。这个大文学集团实际上由两个小的文学圈构成,“即以萧衍为核心的皇帝文学圈和以萧统为核心的太子文学圈。”(注: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63页) 这两个文学圈的活动时间既有先后、又有交叉。萧衍文学圈的活动时间大约在梁初至天监中晚期(502—约515);萧统文学圈的活动时间大约起于天监十四年 (515)左右,止于大通三年(531)。
萧衍建梁后,“初临天下,收拔贤俊”(《梁书·到沆传》),网罗了一大批原“竟陵八友”的故友及由齐入梁的文人,形成了以萧衍为核心的文学圈。“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繁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彩,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梁书·文学传》)“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燕坐。”(《梁书·刘苞传》)在“竟陵八友”中,只有王融、谢脁作了萧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英年早逝。其他五人皆随萧衍一起入梁。沈约、范云乃是萧衍称帝的积极策划者和拥戴者,为萧衍代齐建梁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萧衍的尚书左、右仆射,追随于萧衍身边,并为梁初文坛元老。天监初,“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以下同作。”(《梁书·王僧孺传》)梁初文人受沈约、范云奖掖、提携者甚多。任昉虽外任义兴、新安太守,但依然入朝以诗文赏见于萧衍,“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梁书·刘孝绰传》)“梁天监初,昉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若‘兰台聚’。……时谓昉为任君,比汉之三君(《后汉书·党锢传》:‘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南史·到彦之传》)。因此,任昉亦为其时文坛之耆宿。 (注:阎采平博士认为,任昉仕梁七年,外任义兴、新安太守, “显然也不曾预入萧衍文学圈。”(《齐梁诗歌研究》,第65—66页。)似不确)陆倕入梁后曾为安成王萧秀、临川王萧宏幕僚。然“是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高祖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梁书·陆倕传》)萧琛入梁后,长期外任,作过江夏、南郡、东阳、吴兴太守等职,但亦时常入朝,参与文学活动。“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琛亦奉陈昔恩,以‘早装簉中阳,夙忝同闬,虽迷兴运,犹荷洪慈。’ 上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勿谈兴运初,且道狂奴异。’”(《梁书·萧琛传》)萧衍曾“御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 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匹。”(《梁书·到洽传》)由上看出,“竟陵八友”的成员不仅在政治上是萧衍的中坚,而且在文学上亦是萧衍文学圈的主将,尤其沈约、范云、任昉则成为梁代前、中期文坛上的执牛耳者。其他诸人则多为萧衍的文友,在政治上直接受宠于萧衍的很少。
随着皇太子萧统的长大和参与政事的增多,“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梁书·昭明太子传》)萧衍文学圈的一部分文人转向了萧统。萧统“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词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萧统《文选序》)他“爱文学士,常与(王)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梁书·王筠传》)他还以“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南史·王锡传》)另有王锡、张缵等“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同上)以上诸人中,陆倕是“竟陵八友”的成员,张率、刘孝绰、到洽常为萧衍的座上客。这些文人进入太子东宫,可见萧统的文学影响日渐扩大。除上述诸人外,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沈约的推荐下,入朝为士,(注:参见王更生《刘勰是个什么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83页)很快成为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 ……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刘勰的加盟,更增加了萧统文学圈的学术气氛。然而,萧统文学圈的好景不长,随着萧统的早逝,这个文学圈即于中大通三年(531) 在文坛上过早地解散、消失了。
作为同一个文学集团,萧衍、萧统两个文学圈的活动是有其共同特点的。其一,这两个文学圈的许多成员相互交叉,出入于帝宫和东宫。其二,这两个文学圈的文学创作有不少是萧衍和萧统的“赐宴”、“游宴”之作,极尽赏赞、附和、吹捧之能事。其三,这两个文学圈的文学主张基本一致,皆为宗经、重教。萧衍置五经博士,亲自祭奠儒圣,又据《五经》制礼作乐。萧统亦主张文学应“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因此,把萧衍文学圈和萧统文学圈看作一个文学集团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这两个文学圈毕竟又有各自的一些特点。萧衍个人喜好创作,尤长诗赋,“千赋百诗,直疏便就。”(《梁书·武帝纪》)其乐府歌辞尤为清新、温雅、婉丽,故其文学圈内尤以擅长诗歌者多,诗歌创作成就亦较西邸文学集团高得多。萧统虽“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梁书·昭明太子传》)然其兴趣更多的是在学术上,“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同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兴趣,才有可能组织搜集、整理、编辑出工程浩大的《文选》和《文章英华》来。所以,萧统文学圈的活动更多地是侧重于学术性的。
3
在萧统文学圈的活动十分频繁的同时,另一个文学集团在外阜逐渐形成并不断崛起。这就是以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晋安王萧纲为核心的文学集团。萧衍很注意对萧纲的培养。天监八年(509 )萧纲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时,“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梁书·徐摛传》)由此,徐摛就成为萧纲文学集团中时间最早、最长、而且对萧纲影响最大的成员。另一位与徐摛一起辅助萧纲的是张率。“八年,晋安王戍石头,以率为云麾中记室。”此后,张率追随萧纲辗转南兖州、荆州、江州等地,“率在府十年,恩礼甚笃。”(《梁书·张率传》)张率原是萧衍、萧统文学集团的成员,天监初,奉诏“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甚见称赏。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其恩遇如此。”(同上)又为萧统太子家令。张率病故,萧统特意“遣使赠赙,与晋安王纲令曰:‘近张新安(率)又致故。其人才笔弘雅,亦足嗟惜。随弟府朝,东西日久,尤当伤怀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属有今信,乃复及之’。”(同上)萧纲在藩任上,不断扩充其文学实力。“初,太宗(萧纲)在藩,雅好文章士,时(庾)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注:陆杲当为陆罩,《梁书》不载,道宣《广弘明集》卷30载有其与萧纲之和诗。另参见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彭城刘遵、 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梁书·庾肩吾传》)庾肩吾,“八岁能赋诗”,“每王(萧纲)徙镇,肩吾常随府。”(同上)刘遵,“工属文”,入萧纲府,“甚见宾礼……遵自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梁书·刘遵传》)萧纲评其文为“文史该富,琬琰为心,辞章博赡,玄黄成采。”(同上)刘孝仪、刘孝威,乃刘孝绰之弟,“孝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梁书·刘潜传》)萧纲文学集团的初步形成是在他为雍州刺史任上的七年,“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梁书·简文帝纪》)增加了大量的新成员。“在雍州,(庾肩吾)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南史·庾肩吾传》)“高斋学士”中的大部分人的诗文今不存,但有这么多的文人学士围绕在萧纲身边,其文学创作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也正是这七年,萧纲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梁书·简文帝纪》)这样大的军事胜利在齐梁时期是少有的。(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谓“萧纲一生过着皇子的富贵生活,政治上并无明显的功过。”(《南北朝文学史》,第248页。)似不确)它为萧纲入主东宫奠定了基础,也壮了声威。 萧纲文学集团的正式形成和他在文坛上盟主地位的确立,是在萧统病逝,萧纲继立皇太子入主东宫后。“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同上)庾信和徐陵才华横溢,乃后起之秀,他们的加盟,对萧纲文学集团,无疑是锦上添花。
在萧纲文学集团创作宫体文学达到高潮的同时,作为这个文学集团中的另一个文学圈的核心人物湘东王萧绎,在荆州也拉拢了一批文人与萧纲文学圈遥相呼应。这一批文人中有刘孝绰、刘之遴、刘孺、刘孝胜、刘孝先等。孝绰原为萧统重臣,被萧衍免官后,萧绎多次致书邀请赴荆州任职,遂任萧绎咨议。刘孺曾为萧统太子家令、萧纲长史,后也被萧绎引入帐下。刘之遴原任中书通事舍人,被萧绎引为长史。孝胜很早即入萧绎府,任主簿记室。孝先在侯景之乱后,亦被“世祖以为黄门侍郎,迁侍中”(《梁书·刘孝先传》)。萧绎不仅用幕僚之职来吸引、拉拢文人,还以文学方式广交名士。“世祖(萧绎)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梁书·元帝纪》)裴子野仕梁近三十载,原为萧衍文学圈内人,颇受萧衍赏识。“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高祖深嘉焉。”(《梁书·裴子野传》)萧子云、张缵则出入于萧纲、萧绎二府。子云“迁晋安王文学……时湘东王为京尹,深相赏好,如布衣之交。”(《梁书·萧子云传》)张缵“有识鉴,自见元帝,便推诚委结。”(《梁书·张缵传》)这么多的名流文士聚集在萧绎周围,使得萧绎文学圈的声势不断壮大。然而,萧绎文学圈的文学创作的特色并不鲜明。除了刘孝绰兼善诗文,刘孝胜、刘孝先“兄弟并善五言诗,见重于世”(《梁书·刘孝先传》)而外,其他诸人均长于文而不擅诗。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萧纲《与湘东王书》)所以,这些人的宫体作品写得并不很多。之所以把萧绎与萧纲两个文学圈归并于一个文学集团,是因为萧绎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和萧纲基本上一致。”(注: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第254页)萧绎对文学特征的看法是,“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金楼子·立言》)这就要求文学要辞采华丽,音节宛转,语言洗练,感情细腻。这样的主张正与萧纲的“吟咏情性”和“放荡”相唱和;同时萧绎还创作了大量的宫体诗和艳赋,在实践上与萧纲相呼应。萧纲《与湘东王书》说:“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萧纲对萧绎如此称赞,并把萧绎比作曹植,也可看出二人的共同爱好和志向。
萧纲文学集团倡导并实践的宫体文学,从形式上来说,是齐梁文学追求新变的一种理论滑坡而导致的。“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梁书·庾肩吾传》)从内容上来说,则是齐永明以来艳情诗不断膨胀的必然反映。萧纲坦诚地说:“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此“性情”,实乃宫廷艳情之谓。从诗人主体来说,是长期正统伦理道德思想束缚、压抑、扭曲下情感的变态流露。萧纲曾教导他的儿子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所谓“放荡”,即是可以不受礼法约束、捆绑,任性抒发自己内心的情结和对女性特殊的审美情趣。太子的倡导,东宫的呐喊,亲王的响应,宫体文学之创作,自然是风动朝野,构成了梁末文坛上以形式、艳情为主的文学主流。随着侯景之乱,萧衍、萧纲被侯景所害,以及不久萧绎被西魏所杀,萧梁王朝彻底走向了衰亡。至此,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齐梁三大文学集团在新的改朝换代之前,终于拉下了那厚重的大幕。
4
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给齐梁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亦使得文学创作逐渐走上偏重文学形式、偏重文人内心情感的细腻表露的极端道路。这其中的功过自然与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与核心人物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山东版, 第52页)一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此,那么,在一个文学集团中盟主与核心人物的思想也是如此。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与核心人物都是帝王,他们不仅有着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拥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他们的文学修养和创作的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几与文人无异。因此,他们的文学观念、文学倾向、审美趣味、艺术偏好、艺术风格等就构成了每一文学集团的主导思想。特别是集团盟主与核心人物的政治地位、文学素养、艺术才能和创作水平愈高,其主导思想与核心思想的影响力与决定性也就愈大。萧齐西邸文学集团之所以会有周颙、沈约等“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史·陆慧晓传》),乃是因为其盟主萧子良偏好音律所致。《南齐书·志·乐》云:“《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永明五年,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陈寅恪认为周颙、 沈约等创立的四声理论是直接受到了佛教梵呗和佛经转读的启发。(注:参见陈寅恪《四声三问》,《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而萧子良招集名僧造梵呗新声,无疑给周颙、沈约提供了借鉴佛经转读而发现汉语四声的条件。因此可以想见,四声四病说的提出和永明体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萧子良怂恿的结果。
萧衍、萧统文学集团的文学思想则要受到萧衍的影响和左右。萧衍虽为“竟陵八友”之一,但并不喜好声律和永明体。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梁书·沈约传》)(注:蔡钟翔等先生谓“梁武帝萧衍是个博学之士,对四声却一窍不通。”(《中国文学理论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似不确。萧衍作为一个饱学之士,“素精乐律”(《旧五代史·乐志》),绝不可能不通四声,而是“雅不好焉”)萧衍虽雅不好声韵,但在永明时期,只是萧子良门下文友,无权也无能力左右西邸集团的文学倾向。萧衍代齐建梁后,提倡声韵的主张则大大降温。原来倡导四声四病说的沈约,也一变而提倡“文章三易”。“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这就是要求诗歌用事明白晓亮,文字通俗简浅,语言流畅和谐。显然沈约入梁后提出的“文章三易”主张与永明年间提出的四声四病说是相抵牾的。按“三易”要求下的诗歌创作,则更接近于乐府民歌。今存萧衍的诗歌,主要是乐府歌辞。这说明沈约“文章三易”的主张是适应了萧衍的浅近清新、素朴古雅的创作爱好和审美趣味的。
萧纲、萧绎文学集团的文学倾向则由萧纲所决定。萧纲在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上是不同于乃父乃兄的。他不满梁代文坛出现的一股学谢(灵运)模裴(子野)的风气,竭力抨击那种“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萧纲《与湘东王书》)的腐儒文风。正是在这种片面追求文学新变思想的驱使下,萧纲把梁中叶以后的文学引上了一条危险、极端的道路。宫体诗、徐庾体之所以在梁中叶以后独霸文坛,乃是因为萧纲继立皇太子入主东宫后,竭力追求文学新变的变态反映而引发的。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梁书·简文帝纪》)萧纲既有此“宫体文学”之好,东宫文士自然是趋之若鹜,推波助澜。“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递相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隋书·经籍志》四)萧纲麾下的元老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萧纲入主东宫后,“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梁书·徐摛传》)不仅徐摛作宫体,其子徐陵与庾氏父子也竞相效仿,遂滥为“徐庾体”。“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周书·庾信传》)如此泛滥的流丽轻艳、雕蔓琢藻的文风,显然是有违于萧衍崇尚古朴、素雅的文学倾向的。所以,“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梁书·徐摛传》)然而,萧衍不是这个文学集团的盟主,虽以皇帝之尊,怒斥徐摛,却难以遏制宫体文学的蔓延,扭转迷漫于文坛的这种靡艳之风。
当我们考察了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后,不难发现这样一些事实: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学繁荣,往往与这个时代、社会是否出现庞大的文学集团有关;一个文学集团的出现,往往需要一个能够为集团提供文学活动所需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的人物出现;一个文学集团的存在、发展及其影响力的大小,往往与一个是否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这个集团盟主的政治权力、经济实力、文学爱好、为人笃厚的程度有关;一个文学集团的理论主张、艺术作风、创作实践,又往往取决于这个集团领袖与核心人物的思想倾向、美学理想,这个集团的文学功绩与过失,也往往需要集团盟主来承担。尤其是盟主的文学理论修养和创作实践的水平愈高,其对集团共性特征的影响力和决定性就愈大,同时,他对集团的功过、是非所负担的责任性也就更大。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所产生的这些事实,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的复杂现象,无疑是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