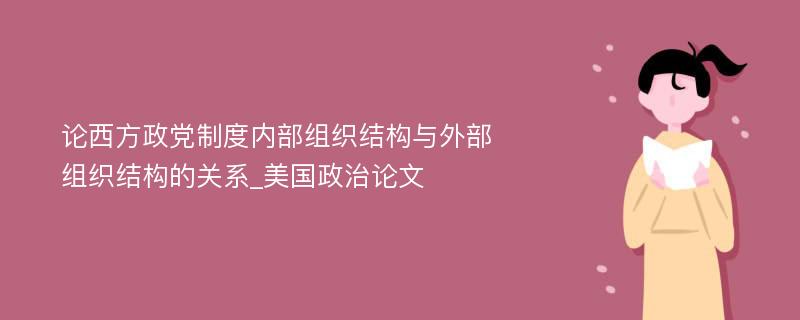
论西方政党体制内外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组织结构论文,相互关系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体制内组织与体制外组织的关系
西方政党体制内外组织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少数国家由体制外政党组织支配控制体制内政党组织;二、大多数国家则是体制内政党组织支配控制体制外政党组织。
第一种情况的代表是日本自民党、意大利的天民党和瑞典各大党。
在日本,自民党政调会内部按内阁各部的形式设立了相应的政策研究机构。根据自民党党章第四十条第二项规定,党的正式政策方针或计划首先由政调会进行研究并通过,然后,移送总务会,再由总务会讨论和通过。从理论上讲,总务会可以修改或不作修改即行通过。实际上,政调会提出的政策方案大部分不作修改或稍作修改即被总务会接受。同时,按规定,总务会通过的政策方案,可以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大会或代替它的两院议员总会所否决,但“事实上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事”。因此,实践中政调会制定、总务会通过的法案,即可直接送交党的国会对策委员会,原则上以内阁法案的形式,作为国会的议案提出来。另外,自民党国会议员一般都兼任好几个党本部特别是政调机构的职务。因此,虽然从原则上讲自民党议员可以有广泛的在内外政策上表达不同政见的自由,甚至有做出不同举动的自由,但是大量的兼职使他们本身直接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因而一般不会否决自己参与制定的政策,再者,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投票态度主要根据党内派系的利益和派系首脑的指令进行的。因此,政策分歧在议会投票前的派系冲突和妥协中实际上已基本解决。最后,由于体制内内阁的方案由体制外政调会决定,内阁态度又反映派系妥协的态度,从而,保证了自民党体制外政党组织支配和控制体制内议会党团和政府的政策选择。〔1〕
在意大利,与日本稍有不同。意大利体制外政党组织控制体制内政党组织主要不是通过职务兼任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以党纪约束的方式来进行。根据天民党党章和内部规定,地区支部书记不能兼任市长或陪审官(市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地区书记不能兼任省参议员,担任省的书记职务就不能再兼任众议员、参议员、市长或省会城市的陪审官、省长或省的陪审官、区的参议员、报社的经理或总编辑。根据惯例,党的总书记一般不兼任内阁总理和政府其他职务(只有加斯贝利和范范民在短期内兼任过党的书记和内阁总理)。由于党的候选人名单是由省的书记同选举委员会一起提出的,因此,体制内政党成员如不服从党纪而自行其是,就有可能冒下次选举被取消候选人资格的危险,而这等于丧失了政治前途。另外,在党的审议决策机构里(全国委员会及其核心领导机构),非议员的体制外成员占了大多数(三分之二)。候选人名单需交中央委员会讨论,中央委员会有权增删名单。因此,议员的政治前途实际上也就控制在体制外中央机关手里。再者,立法的准备工作是由天民党的领导机构和专门机构做的。如果议员们不是该党领导集团的成员,那么,他们的作用就只限于在议会讲坛上支持那些在他们并未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决议。原因:一是议会党团内部规章须提交全国委员会批准;二是对于所有政治问题,议会党团应遵循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及全国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的指示。这就从纪律上迫使议员按领导机构或书记的命令行事。〔2〕
在瑞典,政党的体制内外组织的关系与日本、意大利类似。瑞典体制内议员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大多数国会议员是些不知名的人物,他们很少偏离各自党的决策委员会通过的政治路线,而把执行这样的路线看作是他们在党组织内实施党纲的主要任务。”〔3〕瑞典政党的体制外组织,特别是主席的位子比较显眼, 主席是党的政策的发言人。体制外组织通过组织和纪律两个方面支配和控制体制内组织:一是各级立法机构的候选人名单完全由党组织决定,而瑞典是议会内阁制国家,控制了议会候选人名单,实际上也就间接地控制了内阁的提名机会。议会内执政党的政策首先由党内决策机构决定,然后交政府执行。二是按党纪规定,议员在投票时,一般须与党的态度保持一致,因此,议员“绝少投票时违反党的纪律”〔4〕。 三是政党之间发生政策分歧主要靠体制外政党领导人之间的商讨来解决,而很少由各党议员的投票取向来体现。
第二种情况的典型是英、美、法、德等国的各大政党。
法国独立共和党的全国联合会是“轮廓不清的机构”。全国代表大会名义上是最高决策机构,由众议员、参议员和他们的候补人员,三十名各联合会代表和九名平行组织代表组成的联合会议,是党内无职无权的会议。全国联合会下的指导委员会作用也很小。党内比较重要的机构是执行局。在执行局中议员占着主要地位(17名议员和14名非议员)。因此,有人戏称独立共和党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严格的选举纪律的议会党团”,也即主要由议员控制的组织。〔5 〕议会党团占居党内优势的情况在法国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德国各大政党、美国两大党、英国两大党中也是明显的。一般而言,这些政党的议会党团控制了政策决定权,体制外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只限于处理日常事务。因为,体制外政党的代表大会或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对体制内政党组织只有参考价值而无决定性意义。〔6〕在这种情况下, 当政党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组织在政府政策问题上出现矛盾和不一致时,一般以体制内政党的主张占上风。如,美国两大党的全国委员会主要作用是协助体制内政党开展竞选工作,而不是为体制内政党制定政策。体制外政党组织曾有人试图对体制内政党组织的政策制定指手划脚,但最后失败了。如,艾森豪威尔年代,美国民主党人企图利用以保尔·巴特勒为主席的全国委员会发表一项与艾氏政府的政策不同的政策,结果因受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和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等民主党体制内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作罢。〔7〕
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政党的体制内外组织关系上一般总是体制内政党占优势呢?原因主要有:其一,许多国家的体制内政党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受体制外政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约束,而体制内的议会党团、内阁等组织一般均服从体制内的领袖的领导;其二,体制内政党的活动主要受宪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制约,体制内政党组织必须适应和遵守这样的规范开展活动,而不以体制外政党组织自己的规章制度为转移,也即体制外政党在影响体制内政党组织的行为时,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这就给体制外政党组织约束体制内政党组织增加了难度。其三,政党的主要干部许多已在体制内,因此,党的领导力量本身就在体制中了,体制外的政党组织自然就无法领导和支配体制内政党组织了。其四,现代西方政党大多重政策而不重原则。政党间的分歧主要是政策分歧(实际上政策分歧也并不很大)而不是原则分歧。这是由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性质或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如,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体制外政党组织的纲领对体制内政党组织的政策选择的影响是很小的。何况有些西方国家的政党(如美国两大党)根本就没有长期固定的党纲以指导政策选择。相反,体制内政党在政策制定方面显然有许多优势(组织、技术、信息等)。
二、体制外组织与体制内个人的关系
西方体制外政党组织与体制内政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个人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下列基本特征:
首先,体制外政党组织大多无法支配体制内政党领导人的行为。英国保守党领袖在野时是下院反对党的领袖。执政时,成为内阁首相。他不受党的任何组织纪律约束:他有权批准与颁布党的政策;保守党年会和党内各种其它组织通过的决议只供他参考;领袖的工作和活动不受任何机构的审查,只受宪法和有关法律约束;保守党年会无权就领袖的演说进行辩论或审议,领袖个人的演说、谈话实际上就像政纲;无论是在野的“影子内阁”成员,还是执政时的内阁成员,均由他挑选决定交英王批准;体制外政党的重要领导人,如,负责中央事务所的主席、副主席、司库等人事安排也由他决定;他通过督导员要求议会中的本党议员按他的命令活动;他个人可以否决内阁全体作出的决定,内阁成员中如有人与他意见不一,要么服从他的意志,要么阁员辞职。由于领袖有这么大的权力,因而,体制外的保守党组织根本无法支配他的行为,而只能影响他的选择。保守党的情况是这样,工党的情况也类似。有人证实:“哈罗德·威尔逊像艾德礼那样,在成为领袖之前对党的年会决议是十分忠诚的。在他当选为首相后,他似乎发现自己比艾德礼更能确保大部分重要问题在他的领导下作出决定,可以说是年会忠于他,而不是他忠于年会了”。〔8〕在德国,体制内的总理是执政党的领袖, 议会党团听他指挥,内阁成员由他提名,执政党的政策由他阐述。对此有人感叹道:“德意志的民主好像只是以领导者的意志为转移。”〔9 〕这就是所谓的“总理的民主”。法国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体制外组织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支持总统和政府;二是向政府转达建议和批评。〔10〕因此,政党的权威是体制内的总理和总统。
其次,体制外政党大多也无法支配体制内普通政党成员个人的行为。美国两大党的议员在议会辩论和投票中可以与本党议会党团保持一致,也可以不一致。政党领袖,包括总统和督导员,只能劝说而不能强迫本党议员按领袖的意思行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议会中的委员会主席不听党团核心领导小组的决定,党员议员不听督导员的劝告。〔11〕对此,体制内的党组织都无可奈何,更不必说体制外两大党的全国委员会对此能有什么作为了。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稍有不同。一方面,保守党和工党的议会成员必须服从体制内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的领导,否则,将受到党纪制裁;另一方面,体制外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的任何纲领和决议均对体制内政党成员无强制约束力。体制外的政党组织一般也不会对体制内的政党成员指手划脚,因为这是体制内政党组织和领袖的职责。
在体制外组织与体制内成员的关系问题上,日本、意大利、瑞典等国的情况则绝然不同于英、美、法、德等国的情况。这些国家的政党要么有组织上的保障(党内候选人提名组织和政策制定组织等体制外组织的权力很大),要么有严格的党内纪律制裁作后盾(开除党籍、解除公职或不再被提名为候选人等),因而这些国家的体制内政党成员一般都自愿或被迫听从领袖或中央组织的命令。当然,也不排除在无记名投票时出现某些“自由射手”(投与本党党团不一致的票)的情况以及在执政党占绝对多数、个别党员投反对票并不影响本党执政地位时,某些党员抱与本党党团相反主张的情况。不过,这毕竟是例外。
为什么一些西方国家体制外组织无法支配体制内政党领袖和普通党员?原因主要有: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特别是二战以来,国家职能的扩大,使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力日益膨胀。与此相应,政府首脑(总统、总理、首相等)的权力日渐扩张。出现了所谓的“行政集权民主制”。因此,体制内政党领袖往往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体制外政党组织自然对他难以驾驭。二是一些政党在组织和纪律上对领袖行为没有作出约束的规定,相反,倒是形成了领袖个人意志支配政党组织行为的某些“惯例”。因而,除党的代表大会罢免领袖外,平时体制外政党组织无法制裁领袖。三是一些国家(如美国)的政党本身组织松散,纪律不严,体制外政党组织除大选忙碌一阵外,平时没什么大事可做。因此,它们不可能对体制内政党组织成员的举动有什么控制和支配力。四是一些国家议员候选人的提名控制在地方党组织或基层党组织的手里,而不是控制在中央组织手里,因此,党员议员更关心与自己的政治命运和前途联系更紧密的地方和选区的利益。当地方和选区的利益与党团的态度不一致时,党员议员当然按自己的考虑行动而不依党团的意思行事。五是一些国家的内阁成员、各部委负责人和地方政府中的某些官员是任命产生的,他们首先对任命他们的上司负责,其次才是对体制外本党组织负责。当两者出现矛盾时,他们主要服从上司的指令,因为这与他本人的利益更直接相连。可见,西方有些国家的政党已成为大选的工具、民主的摆饰,而不是一个内部团结坚强、组织纪律严明、真正代表公民利益、反映社会普遍意志的政党了。
三、体制外个人与体制内个人的关系
西方国家体制外政党成员个人(领导人和普通成员)与体制内政党成员个人(领袖和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细加考察,还是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大致上存在下列几种相互关系:
一,体制内政党领袖与体制外政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取决于两者的政见是否一致、私交是否密切、领袖个人的工作方式、性格脾气以及他对体制外政党组织领导人的信任程度等因素。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有名的“铁女人”,她的政府的重大政策基本上由她个人与一些亲密幕僚商量决定。只在如马尔维纳斯战争这样的非常大事上她才征求体制外政党组织领导人的意见,但也只是征求意见而已,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美国总统布什的内外政策主要由他和白宫班子、内阁商量后,由他本人最后拍板决定。只在较少的情况下,如宣布战争状态前夕,才在形式上召集体制外两党的领导人商讨问题,实际上也只是通通气,寻求政党支持而已,并非与他们共同决策。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情况与撒切尔夫人和布什不太一样。密特朗与社会党主席的私人感情甚笃,因此,他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决策上,常常召开四人早餐会来定夺:总统、总理、总统府秘书长和社会党主席。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四人实际上已商讨并决定了有关政策。〔12〕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上台主要靠党内元老金丸信的支持,因此,他出任首相后,在一些重大政策上,常常要与金丸信商讨定夺,金丸信是海部政府“看不见的手”。
二,体制内政党领袖和成员与体制外普通党员的关系。一般而言,除大选时政党领袖为了竞选胜利而频繁地与普通党员接触外,平时政党领袖极少与普通党员交往,普通党员对政党领袖的政策选择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日本政党的派系领袖在党内的地位和重新当选均离不开“个人后援会”的支持。原因是,“党组织缺乏群众基础,加上中选区制的影响,各候选人如果只依靠正式的党组织的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竞选活动的,因此作为实际上的拉拢选票机关的‘个人后援会’就产生了”。〔13〕在后援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除中小企业者和店主们外,还有纳税储蓄合作社、防犯协会、消防团、交通安全协会、青少年辅导联络会等“行政辅助团体”,农协和商工业者团体等“职业团体”,家长教师协作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社会团体”的干部。〔14〕这些干部许多都是自民党在地方上的党员骨干。派系领袖要从“个人后援会”得到基金,得到选票,当然得经常与之保持联系,并在政策倾向上尽可能有利于其后援会成员。另外,与体制内领袖相比,体制内普通成员与体制外普通党员的接触稍多一些。原因是,许多西方国家议员候选人的提名以及当选与否,主要取决于基层选区党组织及其选民的支持。议员们常常自己或委托其秘书、代理人去基层选区与普通选民党员谈话,了解情况,解释政策,或者写信与选区联络。而那些候选人名单由党的中央组织确定的国家里,体制内政党的议员们与选区普通党员的联系相对较少。可见,无论是体制内党的领袖,还是普通党员,与体制外普通党员联系是否密切,主要取决于前者的政治命运是否与选区普通党员有关。
四、体制内外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
现代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即由某个政党或政党联盟组织政府,执掌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这种政治形式的兴衰与政党本身的凝聚力、战斗力是紧密相连的。而政党本身的凝聚力、战斗力又与政治体制内外政党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有很大的关联。因此,政党体制内外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对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格局和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
一,一些国家体制外政党组织难以支配和控制体制内政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体制外政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衰退,使公民对西方政党政治丧失了信心。一般而言,现代政党应有组织选举、执掌政权、利益综合、民主监督、政治教育和社会稳定等项政治功能。然而,如前所述,许多现代西方国家的体制外全国性和地方性政党组织的功能已大大衰退,“它几乎仅仅是为了提供一种构架来提名候选人而已。”〔15〕各国体制外政党组织日常事务并不多,主要为竞选而忙碌,竞选一旦结束,政党的重大活动几乎就没有了。难怪法国政党问题专家博雷拉指责法国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是“十足的由社会名流组成的选举和议会的组织”。〔16〕一些西方国家的体制外政党组织组织松散、纪律不严。如,在美国,“在某些城镇里,党的总部很难被人找到,而且门虽设而常关”。〔17〕许多国家选民加入或退出某个政党很随便,对普通党员无严格的党纪约束。这样松散、软弱的政党组织怎能在利益综合、民主监督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起重大作用呢?!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政党虽然你上我下,热闹非凡,但一旦执政,体制内政党的政府政策就很少受体制外政党组织纲领或政策取向的影响。因此,各届政党政府实际推行的政策已大同小异,普通选民对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已感到无所谓了,对现代西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这一点集中表现为:(一)西方国家选民对政党政治的效能感大大下降。据统计,50年代末,约四分之三的美国公民认为,政党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为大众谋福利,而到197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8%。同样,50年代末,71%的美国公民表示相信华盛顿政府的行为是正确的,到197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2%。〔18〕这说明,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公民对政党组建的政府的宗旨和行为发生了怀疑,甚至不信任。(二)选民以不支持政党来表达对政党政治的不满。据统计,1964年,有75%的美国人支持某一政党,到1976 年, 这个百分比下降到67 %, 1980年为69%。〔19〕相反,认为自己是无党派倾向的选民人数在上升。1972年,美国选民中认为自己是无党派倾向的选民比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的人数多,三十岁以下的年轻选民中,认为自己是无党派选民的人数比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加在一起的选民人数还多。〔20〕这些事实表明,西方选民对传统的政党政治已大失所望。
二,体制内政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与体制外政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关系的松驰,特别是体制内政党组织和党员个人与体制外选民关系的疏远,大大削弱了现代西方政党政治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现代西方政党政治正处于“衰败”或“危机”之中。如前所述,现代西方许多国家的体制外政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与进入政治体制内的政党组织和党员个人无固定的日常组织和纪律关系,平时互相联系不多,更不可能由前者控制后者。体制外的普通党员与体制内的政党领袖和普通党员个人大多没有或很少有联系,所以,体制外的普通党员根本无法影响体制内政党组织、领袖和党员个人的行为。除少数国家外,因政党候选人提名权被政党中央组织、特别是体制内领袖控制,体制内政党成员与体制外的非党员选民的联系就更少了。这样,除在下届选举中普通选民的投票行为对体制内党的领袖和党员个人的政治命运有些影响外,大部分情况下,普通选民的意志根本无法影响体制内政党组织和成员个人的行为。加上二十世纪技术对政治(政策)的影响很大,体制内政党组织的政策方案也不可能真正反映普通选民的利益和主张。于是,许多国家的选民,包括政党党员,对西方政党政治开始抱冷漠、疏远的态度,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日益削弱。这集中表现为:(一)选民对现代政党政治的主要活动——选举活动不感兴趣。据统计,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公民投票参与率是64%,1980年下降到52%,1984年为53%。〔21〕特别在新生代的年轻人中,对政党政治抱冷漠、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更浓厚。如,70年代日本的一项对未来选择的民意调查表明,在20多岁年轻人中,22.4%选择了公民运动而不是政党政治,6.5%的年轻人反对政党和政党政治, 23.1%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公民运动而不是政党政治。〔22〕(二)普通选民认为政党政府的政策反映的不是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而是少数有钱有势有权的集团的利益。据美国的一项民众调查表明,1966年只有37%的人持这种看法, 而到1973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1%〔23〕。(三)二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一些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在大选中得票率下降甚至败北、一些小党(专业性小党、地方性小党和极右党等)日益成长、一些独立候选人走俏政坛等信号,均预示着:若传统的大党政治日益失去选民市场,则西方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就会更趋薄弱。
面对这种状况,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喊出了西方政党政治已经“衰败”,甚至已经“死亡”的警叹!〔24〕虽说这种估计本身是否科学、正确,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一个日益脱离普通党员和多数选民的广泛支持和认同的任何政党,要想在未来的国家权力角逐中始终获得成功,其社会治理政策和措施要赢得公民的普遍支持,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改革现代西方政党政治,以巩固政党的社会基础。还在5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对美国政党政治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后,起草了一份题为《走向一个更负责的两党制度》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对民主与共和两大党为上台执政互相扯皮、争斗,而上台后所执行的政策大同小异、愚弄选民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要求政党加强党纪,改革组织,完善政纲,推行切实可行的科学决策等,建立向选民负责的政党制度,巩固和扩大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25〕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西方的政党政治依然故我,其社会基础不仅没有巩固和强化,反而还有进一步削弱的趋势。究其深刻原因就在于: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西方政党受其阶级属性的限制,〔26〕它们不可能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其社会基础本身就不可能很广泛。加上二战以来现代化的发展和向后现代化的演进,社会阶级和阶层重新整合,西方政党从组织、纲领到政策并没有能同步地适应这种社会变迁。因此,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的削弱是必然的。可以预见,这种削弱对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必将带来一连串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日]福井治弘:《日本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的制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有关章节。
〔2〕[法]热纳维埃夫·比布:《意大利政党》,葛曾骧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157页。
〔3〕〔4〕[瑞典]斯·哈登纽斯:《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戴汉笠等译,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92页。
〔5〕〔10〕〔16 〕[法]弗朗索瓦·博雷拉:《今日法国政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9~90、97、84页。
〔6 〕[法]乔治·埃斯蒂厄弗纳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有关章节。[英]林赛·哈林顿:《英国保守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有关章节。[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有关章节。
〔7〕〔11〕〔25〕[美]哈罗德·F·戈斯内尔等:《美国政党和选举》,复旦大学国政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5、80和81、332~333页。
〔8〕[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第160页。
〔9 〕[法]乔治·埃斯蒂厄弗纳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党》,第66页。
〔12〕[法]莫里斯·萨米克兹:《法国政治内幕——密特朗的班底》,孙昆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4~5页。
〔13〕〔14〕[日]福井治弘:《日本自由民主党及其政策的制订》,第231、233页。
〔15〕〔19〕[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163页。
〔17〕[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美国共和党史》,复旦大学国政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页。
〔18〕〔22〕〔23〕[法]克罗齐、[日]绵贯让治、[美]亨廷顿:《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125、71页。
〔20〕“盖洛普调查报告”,载《纽约时报》,1971年10月17日,第34页,N·D·格伦:“政治独立的变化根源”,载《社会科学季刊》,第53期,1972年12月,第494~519页。转引自[法]克罗齐等人:《民主的危机》,第76~77页。
〔21〕Max J·Skidmore,Marshall Carter Tripp,La Democratie Americaine:Gouverner aux Etats-Unis,Traduit par Marc Saparta,St.Martin,Paris,1988,P.21.
〔24〕[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第163页。 [法]克罗齐等:《民主的危机》,第76页。
〔26〕本文所说的西方政党不是泛指西方国家的所有政党,而是特指资产阶级政党及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其他政党。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内阁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