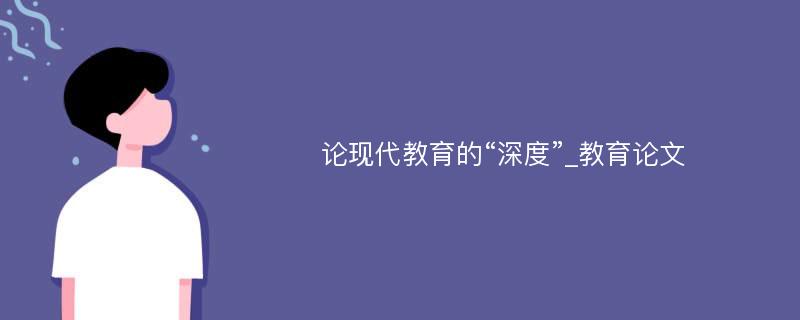
试论现代教育的“深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教育论文,试论论文,深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的教育事业正在现代化的大道上急速发展,在很多方面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特别是在教育的时空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在时间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知识激增”,老化速度加快,“终身教育”的观念正在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空间方面,“大教育”的观念也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亲睐,学校与国家、社区、家庭的关系正在重新地加以认识,各种各样的教育人员、机构、媒体、资源交叉勾连,形成了一个个不断扩大和延伸的立体教育网络,满足社会和个体不同涌现的多样化多层次的教育需求。这些突破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扩展了以往教育学教科书上的“教育”概念,开辟着教育事业的新纪元。
但是,在这些重要突破背后,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和“广度”(“大教育”)的同时,正在失去它应有的“深度”(“人的、人性的或人生的教育”),亦即,世界各国的现代教育在日益满足教育主体(如国家主体、集体主体、个人主体)不断延长和增加的教育需要,提高受教育者个体对于社会、集体和自身的“价值量”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作为“个体人”的受教育者生命本体的关怀,放弃了对作为“个体人”的受教育者的“人性”、“人生”或“人的意义”的引导,把具有鲜活生命的受教育者所时刻面对的“人性”、“人生”或“人的意义”问题简单归结为“人的价值”问题,以至于把受教育者的“价值量的增加”和“价值实现可能性的增加”作为全部教育的最高目的。其结果是,而且也只能是:在现代教育中,受教育者仅仅只是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在预设了他们对于自己、对于社区、对于企业或对于更大的价值主体的“有用性”的前提下,才能够得到教育的关照,而且被关照的程度也随着他们的现实的或可能的“价值量”的变化而变化,两者之间大致呈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需要教育、重视教育、投资教育,只是因为现代教育可以通过自己特定的环境和过程“增加”受教育者的价值,或者“改变”他们的价值属性,更好地满足与这相关的各类价值主体的需要。也正是在可以不断地“增加”受教育者作为价值“客体”的“价值量”的许诺和期待下,现代教育才获得了或被赋予了“优先”的地位,被视为解决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利器”,并成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本”。
由于这种教育目的论问题上的外向观察忽视了对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关怀,疏远了作为任何一种教育活动本体基础的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现代教育越来越表面化、肤浅化、技术化。在实践的方面,现代教育越来越把活泼可爱的教育对象作为一种预期的“教育产品”的“原料”来对待,只关注其外在特性的塑造,如知识的掌握情况、能力的发展情况、技术的熟练情况、行为举止的无过错等等方面,不关注其内在的希望、幸福、痛苦、困惑、焦虑、冲突、压抑、危机等等,把教育对象的目光引向外在世界的同时不再把它们引向自身,导致他们在不断地提高认识和控制外在世界能力的同时减弱了对内在世界的认识和控制能力,以至于自己最后不知道如何运用这种认识和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社会问题尽管是由于历史的落后、经济的贫困、人口的增多、生态的破坏、资源的危机、后殖民主义剥削等等引起的,但是与这种人性缺乏教育的关怀和引导,内心的生活过于昏暗,精神的世界开始塌陷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教育已退化为一种名符其实的“教育产业”,一种“没有根的教育”,一种疏离了人自身的“文化生产”。这种教育完全地建立在社会和个体狭隘的功利性需要之上,如直接地为经济发展服务,直接地以获得一定的教育文凭和为新的劳动力分工所需要的某种特殊能力为目的,等等。这些功利性需要由于其主体的不同,必然地是或多或少地相互冲突的,从而使整个现代教育的大厦建立在流沙或浮冰之上。现代教育是缺乏深度因而也是缺乏根基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失去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尊严和价值。“教育”的意义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被诠释为“教学”、“训练”、“灌输”或“甑选”。外在的教育评价方式把真正的“教育”和“教育家”从课堂中、校园中放逐了。学校作为文化场所的人文精神在根本上式微了。教育学理论也不再能以一种批判性话语激起教育活动本身所孕育的内在力量,而是堕落为纯粹的理智、技能、情感与筋肉的训练术。发达的理智、熟练的技能、虚假的情感以及强健的体魄并不能治愈蔓延在所有现代社会的人性与人心中的疾病。
这就是现代教育的悲剧。教育与个体存在的关系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不是这样的。在古代,教育没有过重的知识传递、技术训练的负担,而是直接地与人生意义的发现和生命境界的提升联系起来。这可以从古老“教育”概念的释义中得到证明。
在西方文化中,“教育”概念,不论是英语中的education, 法语中的éducation,还是德语中的Erziehung均起源于拉丁语的educare,其动词形式为educěre。educěre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前缀 e,一是词根ducěre。e在拉丁语中有“出”的意思,ducere在拉丁语中有“引”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引出”。但是,“引出”又是什么意思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通过“洞穴中的囚徒”这个著名的隐喻(注:拙文:《简论教育学理论中的隐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7年第 2期。)说明了“引出”的真正含义,即把人,把人的心灵、精神从低处引向高处,从黑暗引向光明,从意见世界引向真理世界,臻达善的王国。“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注: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第277页。)“真正的教育”,“好的教育”只是“促使灵魂的转向”并“用力将灵魂向上拉”,引导灵魂达到高处的真实之境。这种灵魂的转向实际上就是人生态度的转向,这种灵魂的牵引实际上就是人生境界的提升。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这个过程的实现之中,而不在于一些能够满足外在世俗性需要的具体知识、技能的掌握之中,后者最多只是帮助灵魂攀升的阶梯。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指称今天“教育活动”的实际上不是“教育”一词,而是“教”和“学”这两个词。对于“教”,《说文解字》将其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如何看待这个解释?我们认为,对“教”的意义的解释不能只局限于字面解释,而应该深入到原始的教育活动中进行考察。根据教育史的研究,在原始社会中真正可以称得上“教育”的活动是“成人礼”。一个儿童在接受这个仪式之前只是一个“自然人”,并不受到部落的重视。只有在完成了这种神圣的仪式的时候,才能进入具有神秘性质的原始社会生活。这个仪式对于儿童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考验的方式各部落随所处的环境和即将遭遇的困难有所不同,但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在仪式上对儿童进行“鞭笞”。鞭笞一般由部落中有威望的人进行,并非今天意义上的“体罚”,而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考验”。身体和精神软弱的儿童会因此而死亡。活下来的就被告知部落的历史、英雄人物、图腾禁忌、血亲仇敌,并从巫师那里获得象征性的饰物,以表明自己即将获得的社会身份。可见,“教”是诉诸儿童内在的精神感受的,其目的在于使儿童从自然性走向社会性,从个体性走向总体性,从现实性走向历史性。生命本身得到了关照。那么“学”呢?《礼记·王制》中解释说,“学者,觉也,以反其质”。“反”同“返”。意思就是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觉悟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返回到人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什么呢?朱熹认为就是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常。显然,这个解释反映了儒家“复性说”的思想。过去有一段时期,学术界把“复性说”批判为历史唯心主义,进而全盘否定。今天看来,这样简单化的做法不太合适。从本体论上说,“复性说”确实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而且也是被科学所证伪了的;但是,从人生论和教育论上说,“复性说”确有其可取之处,主要表现在它对于个体生命境界的提升,所谓的“复性”的过程实质上是个体走向历史、社会和人类的过程。仁、义、礼、智、信不正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类特性吗?可见,在中国古代,学的精神与教的精神是统一的,是源于人生,通过人生,并指向一个更广大更高尚的人生的。
实际上,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教育对人性本身的疏离就开始了。这不仅表现在统治阶级把许多的地位低下的劳动者排斥在文化教育过程之外,而且表现在教育与学校紧密地联系起来,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培养自己所需人才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政治等外在于个体的要求被置于首要的地位。但是,由于近代以前的人类社会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由宗教或伦理所控制的状态中,而宗教与伦理都是人生的事务,没有远离人生,所以尽管它们在很多时候压抑了人性,抑制了人的多方面需要,但是有一点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的,即它们在总体上为人们指出了存在的意义,克服了人类生活的有限性、个体性和虚无感,使个体的眼光不断地转向自身,追问生命存在的价值,寻找精神超越的道路。无论是基督教的“原罪说”,还是佛教的“轮回说”,还是中国儒家的“复性说”都是这样。因此,在世界各国的古代教育中,“修身”都是一种最基本的教育活动。这样,尽管近代以后的思想家,包括一些教育史家把那个时代及其教育叙述得很可怕、很压抑,甚至使用“黑暗的”这样的隐喻,但是一旦我们经由理解的途径真正地进入到中世纪或近代以前的社会与教育,在许多方面却并无窒息的感觉,相反,还能于内心深处获得深刻的启迪,获得精神的力量。
教育对于人性本身的疏离也即教育“浅化”现象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毫无困难地持续着。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以至于有人提出“回到中世纪”。在我国,现代化运动以来也不断地有人以各种方式肯定传统文化和道德生活的价值。究其原因,是因为政治的斗争、经济的发展、科学的普及、技术的培训等都一再以一种不容分辩的口气要求现代学校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教育对象内在生命感受以外的地方。教育的规模在扩大,教育的时间在延长,教育的内容在丰富,教育的结构不断地调整,教育的过程日益科学化,教育的评价也以满足社会功利性需要的程度为转移,然而教育却越来越不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教育学家们谈论着“教学与发展”,谈论着“知识的结构”,谈论着“道德行为规范”,可是就很少触及有着真实生命感受,在各种各样的内心冲突中不知所措的人的存在。教师们更多地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而认识不到教育与教育对象的存在之间的深层关系。学校不再是一个修养心性,传播学问,提高人生境界的场所,反而成了一个激烈的竞争所在。这种竞争是将来社会竞争的序曲或前奏,一点点也不轻松。课堂里不再有智慧的欢乐,校园中也难看到神采飞扬的面庞。厌学之风弥漫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教学活动非严格的纪律不能维持。精神疾病正在侵蚀着学生的心灵,出走、自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可是,教育者们只把这些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希望通过简单地改革教育方法来加以克服,而没有认识到是因为缺乏对人性的深度关怀,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教育的甘泉浇灌在人生的根基上。
现代教育深度的缺失与现代教育功能的急速扩展是有很大关系的。现代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政治、经济、文化、闲暇、社会化等等,一些新的功能还正在增加之中。正是由于承担的功能太多,所以把最主要的东西给丢失了。人们不禁要问:现代教育到底有多少功能?应承担多少责任?这应该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无论如何,现代教育不能像“消防队员”那样,哪儿有火情,就扑向那里!因为教育的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乱用的,恰如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在知识剧增、价值多元、变化多端的当今时代,学校教育必须考虑把自己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绝不能盲目地跟随着社会的需要亦步亦趋,那样就会出现“教育负担”过重问题。从对现代教育深度的分析来看,我们认为,相对于以前忽略了人的存在的教育来说,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学校教育应该加强教育对象的“存在的教育”,通过具有丰富客观文化精神的教育情境,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引发教育对象对自身存在的根本性思考,在不断追问和获得生存意义同时,实现一定社会对他们一定的素质要求,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如果说,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的话,那么自我教育只能是在教育对象不断地对自身存在意义问题进行追问和追寻的前提下产生。
对现代教育缺乏深度的现象已引起思想家和教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在日本池田大作与英国汤因比的一次对话中,两人对现代教育的功利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池田大作明确指出,“就教育来说,确实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实利效果,但这终因是作为结果而自然形成的,光把实利作为动机和目的,这不是教育应有的状况。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成了下贱的侍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他认为,现代教育应该复其根本,即“说明和回答人类应当怎样存在,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编:《面向21世纪的教育》, 求实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294—295页。)。德国学者孙志文在新近的一本书中批评到,“现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法都是人造的……是不能信赖和不稳定的,因此很少触及现代人的核心问题。……结合所有善意的教育家、教师来共同努力,努力的目标便是解答以下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人?在教育系统当中,我们该如何地对待他?”(注:孙志文著:《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 三联书店1994年9月第1版,第154页。)雅斯贝尔斯在早些时候也就指出,“当代教育已出现下列危机征兆:非常努力于教育工作,却缺少统一的观念;每年出版不计其数的文章书籍,教学方法和技巧亦不断花样翻新。每一个教师为教育花出的心血是前所未有的多,但因缺乏一个整体,却给人一种无力之感。”(注:雅斯贝尔斯著:《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3月第1版,第46页。)他把这种教育称为“放弃了本质的教育”,并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人的回归”才是真正的条件。我国梁漱溟先生在解放前也曾针对中国的新学制发表如下的讲话,“四十年来学校制度仿西洋;西洋之长,即在其迈越往世之知识技能。然吾人所见,知识技能乃生活之工具;求之在人,得之在人,运用在人。人之生命力消沉无力,则知识技能一切说不到。”学校教育遂“以荒芜粗暴之身心,杂求支支节节之知识”。(注:梁漱溟著:《梁漱溟随想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37页,第232页。)为此,他提出“全生活教育”的设想,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道”(注:梁漱溟著:《梁漱溟随想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237页,第232页。)。
这种对现代教育疏离人自身的批判对于完整地理解现代教育实践并不是无稽之谈,故做玄虚之论。教育现代化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要寻根究底的话,都会发现其与这种人性的缺乏关怀有着内源性的关联。比如,我们今天谈到教育的组成部分时,总要论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等,这是符合现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可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总是觉得这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没有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且觉得它们无所依托,好像彼此之间是孤零零地存在,有时在论及它们的重要性时甚至发生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议论。它们好像就是教育这个大口袋里的一块块土豆。这些教育的组成部分本该是都指向人生的,但是由于教育深度的缺损,由于教育对人性的疏离,它们也就失去了最终的依据和基础。又例如,失去了深度的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也就不再是他们人生的“家园”,而只是他们人生的“驿站”。学生们习惯于把学校生活与将来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当下的存在境况联系起来,真可谓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了,这是否是学生们普遍厌学的深层原因呢?
失去了深度的现代教育在广度和长度上的增加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言,这种教育也只能解决社会上的一时的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的长远问题;只能解决社会的表层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的深层问题;只能解决社会的个别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的整体问题。所以,现代教育要想在现代社会和人的生存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要想在人类与灾难的赛跑中发挥作用,仅仅把教育对象作为一种基质来“培养”,作为一种原料来“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来“训练”,作为一种价值的载体来“塑造”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首先把教育对象作为一种真正的人的存在来对待,通过教育条件促使人们在为解决生活问题做准备的同时重新深刻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态度与意义问题。抓住了这点才是抓住了现代教育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并细心培育,现代教育才能枝叶扶苏,果实累累。
总之,现代教育除了是“终身教育”和“大教育”外,还应该是“深度教育”,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本真的教育”。它是一种存在的教育,一种真正的人性的陶冶,而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技能的或行为规范的灌输或训练。它是古典的人文教育精神的复归,是教育活动向人本身的复归(当然是在更高程度上的复归),是对各种各样的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本性的审视和解决。现代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学者对它的体认必将对整个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变革起到一种积极的重新定向的作用。这,恐怕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