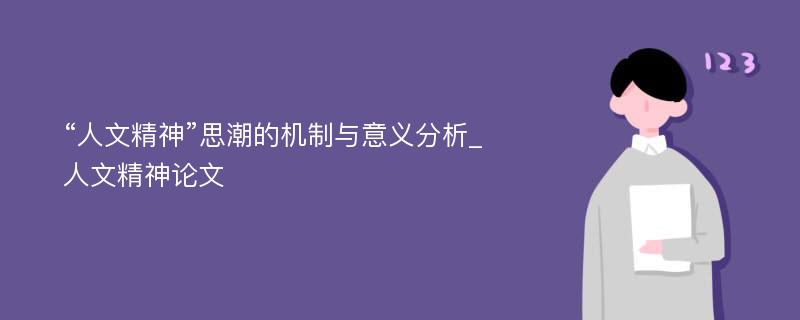
“人文精神”思潮论解析:机制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机制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在中国文艺论域,一个看似平常而又含义十分空泛的词:“人文精神”,陡然间热度升高,成为一批人文知识分子热议的中心。围绕该词的讨论组织起不同的理论话语和文化姿态,“人文精神”成了各种不同文化立场角力的空间和舞台。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还超出纯学术论域,呈现为文化思潮。本文试图从思潮论角度展示“人文精神”论争的语境、机制和意义,以期获得关于此次论争的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论争的语境:市场经济、文艺俗化、大众审美文化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记忆中,80年代是一个充满启蒙激情和精英理想的时代,文学艺术虽然常常引起观念冲突,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和由“惯习”① 所赋予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却使它仍然处在传统的中心位置上。然而,到90年代中前期,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中心位置和精英立场的销蚀带来的压力了。由此引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开展,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规模和深度,展现于世界面前,令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惊呼“历史强行进入”,其实,80年代知识精英启蒙的现代化诉求与此“历史”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历史因缘。
在90年代中前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其精神影响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思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些前提包括:其一,经济中心地位凸显和实用主义功利意识的增强,使文艺从原来的显要位置退出,似乎被“边缘化”了。其二,市场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意识渗入到整个文艺系统中,文艺生产受到利益与“利润”动机的有力支配,文艺创作的晕轮效应逐渐消解。其三,文艺家的创作日益受到阅读需要的影响,适应或迎合社会心理多层次需要的作品广泛存在。审美与感性欲望的界限正在被抹平,大众审美文化迅速崛起。
在某些学者的论述中,所谓大众文化是指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并称的一种新兴文化形式。我国90年代的大众审美文化具有这样一些突出特征:
其一,鲜明的消遣性和娱乐性。在主流和精英文化中,消遣与娱乐往往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它的重要性完全依赖于文化的其他目的和功能。主流文化由于内在具有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而总是负载着意识形态内容,它的娱乐消遣功能是为传达这种内容服务的;精英文化往往具有先锋性和精神贵族化的特点,它的消遣娱乐性本身也是非大众化的、从属于精英文化的某种崇高理念的。与此相反,大众文化则削平了深度感和中心意识,把消遣性娱乐性宣布为自己的目的。
其二,大众文化具有即时消费性的特征。传统的高雅的艺术往往追求艺术的永恒性,经受了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作品被称为杰出作品,那些转瞬即逝之作总是被讥评为缺乏艺术生命力的败笔。但是对于90年代以来的大众审美文化来说,评价作品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它是否具有即时消费性,具有这种即时消费性也就意味着它符合大众的口味,产生了“卖点”。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为大众所接受。90年代以来,不少大红大紫的文化产品大都具有即时消费性的特点,这些作品不去追求永恒的品位和深度主题,而是细心揣摩大众的心理,调制受众的胃口,煽动官能的欲望,迅速而有效地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
其三,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亲密无间。大众传媒的“大众性”使它不仅成为大众文化的一般载体,而且它现实地为大众制定文化策略,使得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成为重要的文化存在。学术界对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估价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有的学者对当前的大众文化和世俗化进程持赞成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具有“解神圣化”的作用,有助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有的学者则认为,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他们担心“经过大众化生产和标准化生产后,艺术是否会失去先锋的风格?……艺术家每创作一件作品,都是从一种独特的角度和视野对世界和自我作出的独特发现,经由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后的艺术能否保留这种独特的视野?”② 此外,有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持比较彻底的批判态度。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90年代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对人文精神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固有的人文传统以及从80年代继承而来的人文精神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某些价值形式确乎失落了,然而某些新的价值观念也在孕育和产生。在文艺领域,纠缠文艺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是文艺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文艺家以及人文学者在市场经济面前,必须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调整自己的文化姿态。
二、论争的焦点:对人文精神状况的不同估计、人文精神语义诠释
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一文率先提出“人文精神”问题,随后这一问题激起文化界的广泛兴趣,“人文精神”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大量的讨论和争鸣文章被发表,形成了90年代一次难得的文化思潮。“人文精神”讨论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概括起来,如下三个问题构成了讨论的核心。
问题之一:如何看待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如何评估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的“俗化”现象,如何看待文艺的价值与功能。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大对立见解。一种见解对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作了悲观估计,认为人文精神失落是不能否定的现实。王晓明从“文学危机”角度来审视当前的人文精神。他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③ 王晓明等人所说的“文学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文学创作上的“媚俗”和“自娱”倾向,这种倾向又表现为文学的消费性、商品化和“想象力的丧失”。在他们眼里,王朔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分别是文艺“媚俗”和“自娱”的代表,是人文精神危机的现实表征。张汝伦和陈致和等人的危机意识侧重在人文学术方面,认为他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衰竭”④。陈致和对“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表示怀疑”,在他看来,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一个稳定悠久的精神传统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知识分子现在要么学苏秦、张仪去做政治工具,要么把学术看作是自我逃避的场所,这两条路都无法重建起人文精神。”⑤ 很明显,张汝伦和陈致和等人的这篇对话落脚点是在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上,真正的危机“在于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而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则是这侏儒化和动物化的最深刻的表现”⑥。在这一阵营中,作家的姿态更为激情化。张承志于1993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以笔为旗》,同年3月21日张炜在《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他们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对当前人文精神失落的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张承志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抗战文学,指出危险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尤其在面对信仰失落人生缺乏精神导向、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满足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一个几千年文明12亿人的大国,被一批无原则无操守的文人占据了文坛联络了电视台报刊形成了称霸文化领域的势力,让这批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糟蹋,这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张炜则指出:“文学已没有了发现、批判,进入普遍操作、制作状态,匠人成了榜样,精神枯萎,那些包装好的制品只是垃圾。”此后,张承志张炜等人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现了与现实绝不妥协的态度。
另一种见解对当下的人文精神状况持乐观主义态度。王朔称从人文精神立场批评他的人为“假崇高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者”,在《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这篇对话中,王朔说:“有些人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哪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些人呼唤人文精神,实际上是要重建社会道德,可能还是一种陈腐的道德,这有可能又成为威胁人、窒息人的一种武器,如果是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可以永远不要。”⑦
问题之二:人文精神到底何所指?“人文精神”与现实、历史语境,与“人文精神”言说者的关系如何?
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关于“人文精神”的涵义,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论者大抵从个人立场和价值取向、自己占有的话语资源出发,对“人文精神”做出解说。从王晓明等危机论者对“人文精神”的使用情况看,“人文精神”大抵是他们所持有的一种基本立场,其涵义大体上包括:人文精神是人的一种精神素质,是“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兴趣,是生存的严肃性(文学创作的严肃性和神圣性),是“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人文精神不是对大众的“媚俗”和不负责任的“自娱”,不是“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不是“想象力的丧失”,不是对“人本身的意义”的“虚无主义”逃避,不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在危机论者中,张汝伦主要是从哲学和学术层面来思考人文精神问题的,他认为“人文精神是一切人文学术的内在基础和根据”,它体现为哲学上的“智慧与终极关怀”。在这里,人文精神与文明、人性和某种普泛的基本道德准则相近。这个东西一旦完全失落,“就必然会‘率兽以食人’,人文世界变成丛林世界”。对人文精神状况持乐观态度的王朔、吴滨等人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显然与上述诸说有异,王朔认为,“说到底,人文精神就是要体现在人对本身的关怀上”,而在吴滨看来,人文精神就是立足于现实,追求理想实现信仰。根据《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这篇对话,我们有理由断定,王朔所说的人“本身”并非抽象的思辨意义上的“人”,而是当下现实中的有着种种欲求和自由选择权利的个人。吴滨所说的“理想”“信仰”虽然语焉未详,但是从他强调“人文精神要落到人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这一点来看,他说的信仰与理想绝不会是王晓明、张汝伦等人所谈论的信仰与理想,它的形式与目标应当是与人对“自身”的关怀相适应的。
有些学者将对人文精神的探讨与知识分子自身联系起来,表现出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王干认为,当代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人文精神的危机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生存”与“思维”之所以会陷入“一种迷茫的困境”,是由于失去了西方人文价值传统这一“参照”物。同时他又认为,今天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独立叙事的程度和力度,看他能否和物欲横流的社会划开界限……知识分子独立叙事这样一种存在是人文精神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人文精神的重振就是一句空话”⑧。王干等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批判和否定精神作了高度强调,但是“独立叙事”的话语资源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问题之三:人文精神重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人文知识分子在价值重构中的地位与使命。
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大多数人文学者包括作家都认为当前的人文精神出了问题,应当进行某种调整或重构。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两个主要方面:
其一,主张从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本位意识出发,与世俗化现实划清界限,维护人文学术的独立品位,重建“学统”,同时保持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维度。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这篇对话中,张汝伦、陈思和等人自觉地将对人文精神的追寻归于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实践问题。在他们看来,人文原则既是普遍主义的,又是个体主义的。所谓普遍主义是指人文精神从形式来理解具有普泛性和共通性,而不是任意性的东西;所谓个体主义是指具有普泛性和共通性的人文原则必须落实到个体的具体实践。他们高度强调“这种实践的自觉性”,主张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反求诸己,从自己做起”(张汝伦语),坚持住“最后那么一点东西”(指人文精神。朱学勤语)。与上述主张退守人文知识分子本位,在自己的学科建设中坚持一种批判意识批判精神的见解不同,王岳川、肖同庆等人则主张,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人文知识分子的实践具有总体调节制衡作用,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拒绝堕落,拯救堕落。“人文精神需要的不是否定现实前提,而是承认现实前提的整合。他反对人文精神一味站在训导师的地位,企图以抽象的命题和理论的推演给社会强加规范和预设。这样只能事与愿违,人文精神也只能永远停留在知识分子个人操守的象牙塔内,难以形成有效的规范操作系统”⑨。
其二,主张挖掘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接续断裂的传统,以此来重构当代人文精神,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颓势进行批判。这一思想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人文精神论者的理论话语之中。比如陈思和所说的“庙堂意识”与“民间意识”,张汝伦所说的“无状之状,无象之象”都包含着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意向。关于重构人文精神,对王朔、吴滨等乐观论者来说是不成为问题的。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焦点问题大体如上所述,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焦虑的核心实际上还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三、论争的机制与意义:反思、转型与重建
发生于90年代中前期的这场人文精神论争,从思潮论角度看,具有如下几点机制性意义:
其一,这场讨论是在中国市场经济获得合法化依据,世俗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语境下发生的,是市场经济物质进程在观念上的特定产物。其二,这场讨论是由世俗化现实不自觉地触发和策动,由少数人文知识分子自觉发起,自始至终在人文精神界进行的具有自我调控色彩的讨论。借用某些人文精神论者的说法,“意识形态淡出”在这场讨论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其三,这场讨论的参加者主要为以文、史、哲为业的人文学者、部分中青年经济学者、著名作家和一些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感受出现了分化。人文精神悲观论者大都是学界精英,他们对西方人文精神话语资源大都擅长,从中获得了批判和审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资源和某些灵感,在他们身上可以依稀看到80年代启蒙精英的影子。对立一方论者如王朔,没有那样渊深的学术文化背景,但是,他们显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浪潮,他们的作品遵行商品化的规则,自觉迎合“大众”的口味,是标准化的大众文化产品。其四,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如人文精神的失落、滑坡或“遮蔽”,知识分子人格的萎缩和侏儒化,道统、学统、政统的离合关系,人文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等等,都是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但是由于它的“精英”特质,这场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讨论实际上疏离了现实,没有充分关注导致“危机”的具体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规律性。其五,从讨论的性质来看,这是一场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运动,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危机生存焦虑密切相关,正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人文精神的提倡其实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救行为”(王晓明语)。这里包含着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既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期待,也是对现实和未来的期待。
知识分子的自省和反思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主要话题。知识分子既是言谈发出者,又是言谈所及者,在知识分子的反思性谈论和对文化的批判性谈论中可以凸显知识分子对本身形象的自我勾勒和自我认同。
首先,知识分子是作为现存社会的反思之维批判之维而出现的,通过对当下大众文化的分析与批判,凸显了他们的精英身份。这一点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人文精神寻踪》等对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次,知识分子是以现存社会结构中的专业分子的面目出现的。正像讨论中表明的那样,这样的知识分子以文、史、哲专业学科为业,他们专擅的领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话语资源,尤其对西方现当代的“人学”话语操练纯熟。当他们以这样的学术话语参与到中国当下的精神现实中来的时候,显然就为自己开辟了一个专有的话题领域,在这里他们得心应手,常常流露出一种自炫式的快感和对“语词”魅力的崇拜。具有喜剧意味的是,当他们的“学术”企图和话语锋芒刺痛了现实中人,引起了受批判者的讽刺、嘲笑和攻击之时,他们却感到了“不能令人满意”的失望。第三,透过对立一方的反唇相讥,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现实一面。在王朔等人看来,“人文精神失落”论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自以为是“文明火炬的传递者”,但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有些文人已有的知识用不上了,这不能说是文明的失落”。某些批判他们的人心态是不正常的,而不正常的原因一个是由于贫穷而愤世嫉俗,一个是由于关注和崇拜他们的“视线的失落”而心理失衡。剔除嘲讽和挖苦的成分,应当看到王朔等人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90年代前期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由于社会结构调整、民族心态变化、利益重新分配等原因,人文学者的生存境遇前所未有地复杂化了。某些人文学者不仅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日渐疏离,而且日益被抛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成为衡量人文学识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和广泛普及日益侵夺着人文知识精英的传统领域,并对知识精英安身立命的人文价值产生侵蚀。这种复杂化使得人文学者产生了身份危机、价值危机和阐释的焦虑。由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对无所从属的恐惧,90年代前期的“知识分子”危机确实是十分深重的。应当指出的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中频繁使用的“知识分子”概念是不严格的,它无视80年代后期开始,90年代愈演愈烈的知识分子分化这一基本事实,企图以一个普泛的概念来使人文学者的情绪和立场大而化之,这恰恰“遮蔽”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真实状况,当然也无助于人文学者“拯救”世界和“拯救”自我的事业。
“人文精神”论争从开始到沉寂历时两年有余,其间数度掀起波澜,引起广泛注意。如何评价这次讨论,可谓言人人殊。毫无疑问,这场“人文精神”论争存在着种种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其一,具有鲜明的“人文知识分子”属性,它的与“大众”判然有别的精英立场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人文知识分子虽然关怀现实人生,但是这种现实人生却不是“引车卖浆者流”的现实疾苦,也非中国当下发生的改革进程,而是虚拟化精神化的心灵痛苦与失落感。如果说80年代“人道主义”大讨论是人文知识分子通过拯救世界来拯救自身的话,那么,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则是人文知识分子通过拯救自身来拯救世界。这种不断退却的精英立场在90年代的危险就是日益疏离民众,导致自身的孤立。
其二,这场讨论虽然就中国人文精神状况有感而发,但是它的话语资源仍然来自西方人文精神话语中心,大多数论者虽然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是其审视和批判中国固有和现有文化的视点和理论武器却仍然是西方的“人学”。人文精神“遮蔽”论显然与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有关,对工具理性消费主义的批判显然也重复了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某些论断。这种隐含着西方中心话语的中国人文精神批判有可能带来两个危险:一是有可能对当下的中国人文精神状况做出错误的判断,以偏概全,夸大人文精神的失落境况。二是有可能移植西方“人学”的批判性命题,用于批判中国当下的改革进程。这两种危险都有可能使当前的人文精神建设偏离理想的目标。
其三,由于这场讨论的“精英”性和“意识形态淡出”作用,加之对立双方的某种情绪化,在这种讨论运作模式下,既不可能有仲裁者断定谁“真理”在握,也不可能使对立双方的偏颇得到真正的清理。因此,当下人文精神状况虽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这场讨论却只能不了了之。
应当肯定的是,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话语权的持守和张扬,体现出其自身对自我明晰化价值最大化的最本己的需要,他们对现实人生的形而上关怀仍然与当下现实的形而下追求息息相关。人文精神论者对工具理性、消费主义、实用功利主义的批判,对艺术品生产世俗化、作家艺术家工匠化、审美趣味庸俗化的批判诚然有过当和不够妥帖处,但是这一批判却并非没有意义。遗憾的是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大多止于谴责和感伤,而甚少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建构,因此,这场讨论留给21世纪的精神遗产是极为有限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曲挽歌,挽歌唱罢,知识精英立场和它所倡导的批判性似乎更难得一见了。
注释:
①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其含义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就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本文使用这个概念,主要着眼于中国当代文艺家的由来已久的“性情倾向”,它表现为对中心意识和中心地位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接受与顺从。
② 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③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④⑤⑥ 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载《读书》1994年第3期。
⑦ 王朔等人的观点请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第84—99页。
⑧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第67页。
⑨ 冯天瑜:《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