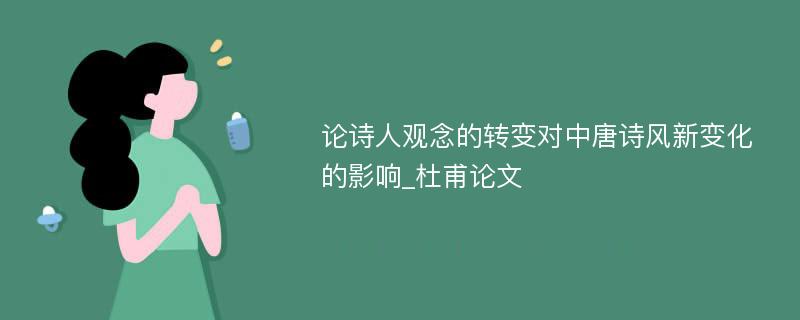
论盛中唐诗人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唐诗论文,构思论文,方式论文,论盛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构思方式是决定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从盛唐到中唐诗人们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产生的影响。指出盛唐人普遍以兴会作诗,而中唐人则有意打破兴会中意与象的平衡,从而写出了自己的风格。
【关键词】 盛中唐诗人 构思方式 诗风新变
诗人在创作时采用什么样的构思方式是决定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诗风从盛唐到中唐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构思方式的转变。盛唐人普遍强调兴会在构思中的重要作用,而中唐人则对这一方式做了很大的改造,直接影响了诗风的变化。本文拟对这一过程做具体的描述。
一
兴会是指诗人会心自然景物而产生的创作冲动,即所谓“兴会百溢”的心理状态。定义虽然如此,但不同时期诗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一致,理解不一样,在具体运用时就会各有侧重,从而影响到诗歌风格的形成。从单一的角度来说,盛唐诗的风格正是诗人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兴会创作出来的,我们姑且以盛唐人对兴会的理解为基准,看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如何处理情志和物象的关系,是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诗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的情绪是由物象所引发,又通过物象来表达的过程,“兴会”这一概念也逐渐得以确立。较早谈到这一问题的是陆机的《文赋》。作者虽然是在描写作文的过程和规律,但也触及到了情与物的关系。“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凌云”,说的就是物象对情志的感发作用。陆机还用“会意”、“应感之会”两个词语来表达物象引发情志以后的思维过程,已经很接近“兴会”的概念。明确地提出“兴会”这一概念的是沈约。齐永明六年(488)二月,他完成了《宋书》的修撰,书中《谢灵运传论》云:“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但沈约并没有对兴会做具体的解释。
其后对兴会做出明确揭示的则是作于三年后的《文心雕龙》。刘勰在《物色》篇中比陆机更加具体的描绘了物象对情志的兴发感动作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进一步指出,物色不仅引发了人们的情感,而且始终伴随着情感进行活动,直到再用物色来表达这种情感:“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可见刘勰特别强调表达时忠于物象的原貌,而不是为了情志抒写的需要随意改变物象。他赞赏“文贵形似”、“体物为妙”。更可贵的是刘勰还揭示了“兴”和“会”的关系:“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总之,刘勰在《物色》篇中,集中地探讨了情志与物象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入兴”、“会通”等概念,指出从“入兴”、“会通”再到表达,一直都离不开物象。其中“体物为妙”、“析辞尚简”、“物色尽而情有余”还触及到了兴会与神采和韵味的关系。可以说刘勰对兴会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
二
刘勰对兴会的认识,说明当时诗人已经有了大量的以兴会作诗的实践。篇中“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便说明了人们在创作中对物象的重视。而要做到“形似”,就必须“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凭借兴会来创作。但齐梁和初唐诗人在这方面尚缺乏理论的自觉性,诗中很少提到“兴”的问题。直到盛唐,“兴”才引起了诗人们的普遍重视。李白云:“试发清秋兴,因为吴会吟”[①],“今日赠余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②],高适诗云:“兴来无不惬,才大亦何伤”[③],李颀诗云:“兴来逸气如涛涌,千里长江归海时”[④]都表明了诗人们对“兴会”的自觉。盛唐人在诗序中常常写他们作诗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物象的兴发感动作用有清楚的认识。如张说在《洛州张司马集序》中就曾谈到“穷神体妙”、“遇物感兴”[⑤]。其他如张九龄云:“林修耸而垂彩,绿萝蒙茏以结阴。清流若镜,下照金沙之底;余花如锦,傍缘石菌之崖。则可以藻饰形神,挥斥氛滓,相顾风尘之表,无负云霄之概”[⑥],“盖因丘陵而视远,必有以清涤孤愤,舒啸佳辰。……江浦清明,南土阳和,觉寒气之向尽;东郊候暖,爱春色之先来。……悠哉薛公,无不寄也。意神奇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风景不殊,翦为茂草”[⑦],韩休云:“感物造端,藻畅襟灵,……发挥造化之微,鼓动江山之气”[⑧],李白云:“烟景晚色,惨为愁容。系飞帆于半天,泛绿水于遥海。欲其不忍,更开芳樽。乐虽寰中,趣逸天半”[⑨],“白月在天,朗然独出,既洒落于彩翰,亦讽诵于人口。……紫霞摇心,青枫夹岸”[⑩],“黄鹤晓别,愁闻命子之志;青枫暝色,尽是伤心之树”[(11)],“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12)],都可以看出盛唐人作诗,是特别看重兴发感动作用的。
由于“兴”主要是指山川风物、自然景色对诗人情兴的触发,所以盛唐的山水田园诗代表人物之一孟浩然在创作中更明确地强调“兴”的生发。葛晓音先生指出,在初盛唐诗歌复变中“陈子昂和二张重新提倡比兴寄托,对山水诗中存在的这种‘兴会’,一直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孟浩然多次在山水诗里强调“兴”的生发,“便明确指出了人对自然的会心在山水诗创作中的重要性”,“使山水清兴和托谕寄讽的‘兴’在理论上区分开来了。”[(13)]葛晓音先生指出这一点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从初唐到盛唐人们在创作方式上转变的轨迹。
在以兴会作诗方面讲得最多、最全面、最明确的还是盛唐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杜甫。现存杜诗当中谈到“兴”、“逸兴”、“佳兴”等有关兴的地方不下六十处。其中兴的含义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指游玩观赏之兴致,如“之子时相见,邀人晚兴留”[(14)],“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15)],“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16)]。另一类就是事物、景物引发的诗兴,从中可以看到诗人对兴的产生,兴与思维,兴与神采,兴与风骨的关系以及诗兴的概念都有清楚的觉解。
孟浩然“湖山发兴多”等句,虽然也是讲作诗时的一种感受,但并不明确。杜甫明确地将兴致和诗歌联系起来,提出了“诗兴”这一概念。如“草书何太古,诗兴无不神”[(17)]、“稼穑分诗兴,柴荆学士宜”[(18)]。孟浩然所谈的兴大都是就山水清兴而言。而杜甫所言的兴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云:“诗尽人间兴,兼须入海求[(19)]”,此种人间之兴,当不局限于山水之兴。再如“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20)],当时正是他作“三吏”、“三别”的时候,因此“潼关诗兴”就不是指山水之兴。总之,杜甫所说的诗兴包括范围很广,举凡一切事物、景物引发的情绪冲动都可称为诗兴。“愁极本凭诗遣兴”[(21)],“遣兴莫过诗”[(22)],他的许多诗直以“遣兴”为题,如《遣兴三首》、《遣兴五首》之类,所遣之兴,就是指需要用诗来表达的一切情绪冲动。由于诗兴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杜甫有时还做了分类,“高楼忆疏豁,秋兴坐氤氲”[(23)],“老去才虽尽,秋来兴甚长”[(24)],以及《秋兴八首》中所写的“秋兴”,就是按季节对诗兴做的分类,而能对诗兴进行分类,则表明杜甫对诗兴有了很清楚的觉解。
在兴的产生上,杜甫比孟浩然等人也讲得更为明晰。如云:“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25)],“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26)],都明确地表明了兴之由来。
关于兴会的具体活动情况杜甫也有所描述。如“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27)]写的就是兴随着景物的瑰怪奇特而至极,同时也引来了忧思。再如“老夫平生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28)],写的是作者由于生性好奇好古,所以见到画面便觉得和画中的精灵相聚一堂。杜甫有时还将诗兴和思想联系起来,如云:“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30)]便揭示了奇兴生发与忘怀自我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表明杜甫对兴会的思维特点有明确的认识。
杜甫还触及到了兴会和神采的关系。老杜平生作诗,有意追求神妙的境界,如云:“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31)],“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32)],“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33)]。入神的创作境界是创作出具有神采作品的条件,而神妙的境界则完全是兴会畅通入神的结果,正如杜甫所说的“草书何太古,诗兴无不神”[(34)],“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35)]。
杜诗中还触及到了兴会和风骨的关系。“平生意飞动”,讲的就是遄飞的意兴。而飞动的意兴,正是诗歌具有风骨的表现。
盛唐人的审美追求,都是通过兴会来完成的。他们所讲究的气骨、风神、蕴藉都可以统一在意兴当中,逸迈之兴就是有风力的表现,而诗兴有神也就是风格上的神采飘逸,至于兴象玲珑的特点更是强调兴会的结果。只有强调凭兴会作诗,将情理化入完整的意境当中,才有可能写出“一唱三叹之妙”。人们对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兴趣”做了许多解释,我认为“兴趣”的含义与兴会非常接近。严羽说“盛唐诸公,惟在兴趣”,说的就是盛唐人凭兴会作诗,把义理化入兴象当中,不露痕迹。由于构思方式对风格形成的作用极大,人们甚至把“兴会”这个影响盛唐诗风的一个因素当成了盛唐的特质。
盛唐人普遍重视兴会与他们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盛唐人也是爱谈玄说理的,如李白《赠别王山人归布山》云:“王子析道论,微言破秋毫”,崔宗之《赠李十二》云:“清论又抵掌,玄谈又绝倒”,说的都是人们见面后清谈的情景。可以说,诗人们见面之后,清谈赋诗是并行的两项活动。可是诗人们并没有留下什么论理的著作,倒是在他们的诗作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哲学思想,例如李白的《古风》同阮籍的《咏怀》、陈子昂的《感遇》一样,都是“子书”式的组诗,可他说理的成分远比阮籍的诗少。他正是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所要说的道理。
正是由于重视兴会,盛唐诗中即使是说理或包含理趣的作品,也是不易见出思理的痕迹,要说明这个问题,可把兴会活动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来看,一个是兴发感动阶段,一个是构思会通阶段,一个是用物色表达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可以有义理的活动,但在第三个阶段就不能有说理的痕迹。严羽特别强调“兴趣”,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诗有别材别趣,非关书理,又离不开书理,但在表达上要把才学义理形象化,化到“无迹可求”的地步。全部形象化,除去事理之魔障,就是“兴象玲珑”的境界。这种有限的形象可以给人以充分想象的余地,便可以写出“一唱三叹之音”,“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孟浩然的《春晓》,作者意在表达惜春之情,读者都可以联想到各种情景,许多禅僧甚至用来说明他们参禅悟道时的心得体会。作者、一般读者、禅僧各得一个意境。确实像严羽所形容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那样,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用佛家妙悟来形容盛唐人的创作,认为盛唐诸公已达到“透彻之悟”,说的就是盛唐人虽然在创作时加入学问义理,但关键是在表达时能隐去义理,“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就像参禅时除去一切魔障,直得妙道一样。前人对严羽所说的诗有别材别趣,非关书理,又必须多读书,多穷理一段话的解释多不甚明了,如果把兴会分成三个阶段,就很容易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前两个阶段,特别是运思会通阶段尽可能加入思理的活动,而到表达阶段则必须去掉思理的痕迹。如果我们讲盛唐人以兴会作诗,也只讲兴发感动,只讲以物色来表达,不讲会通这一阶段,兴会就会给人以简单而又神秘的印象。
还应该指出,盛唐之兴会和齐梁之兴会有一定差别。在情意和物象两方面,齐梁人更看重物象。刘勰就曾指出,“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可见当时人非常重视“形似”,描摹物象最好能达到“曲写毫芥”的程度。盛唐人也很看重物象,但也很看重情意。他们的情意虽然来源于物象,但他们在表达时并不要求丝毫不差地描摹物象,而是抽出物象中最能表达情意的特点,在情意的统一下,组成一个浑融的和谐的画面。在不损害物象原貌的条件下,使物象情意化;在尽量表达情意的基础上,描摹物象的特点,情意和物象不偏重任何一面,始终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我们姑且用“平衡”一词来概括。可以说,盛唐人与物象之间的距离比齐梁人与物象之间的距离远了一些,兴会从齐梁到盛唐的演变过程,就是情意的成分不断加重的过程。
三
然而自进入中唐以来,意与象之间的平衡逐渐被打破了:一方面是特别强调物象,不要情意的统合作用;一方面是特别强调情意的表达,以情意统摄物象,置物象本身特点于不顾。
本来中唐前期的大部分诗人仍是讲究兴会的。如刘长卿云:“客路风霜晓,郊原春兴余”[(36)],钱起云:“诗思行间得,道心松下生”[(37)],“感物乾文动,凝神道化成”[(38)],“斜景亦随诗兴尽,好风才送佩声回”[(39)],“青琐同时多逸兴,春山载酒远相随”[(40)],“江华胜事接湘滨,千里湖山入兴新”[(41)],张继云:“结念湓城下,闻猿诗兴新”[(42)],“诗句乱随春草落,酒肠俱逐洞庭宽”[(43)],“能令诗思好,楚色与寒芜”[(44)],“兴清湖见底,襟豁雾开天”[(45)],“知君心兴远,多上海边楼”[(46)],“过江秋色在,诗兴与归心”[(47)],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们是非常看重物象对诗兴的引发作用。诗篇之好坏,与物象之引发直接相关。
但中唐前期也有许多诗人又同时加大诗中的说理成分,尤以韦应物、钱起、张继、独孤及、戴叔伦为最。许多诗一半儿写景,一半儿谈玄,谢灵运诗“截分两橛”的现象在中唐前期又重新出现。这样的诗,往往造成意和象如油水之分离,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意兴,像元结则明确地反对指咏时物,所以也更不可能重视物色发兴的问题。
较早打破意与象之间平衡的,正是盛唐兴会理论的集大成者杜甫。《易经》上说“继往开来,谓之集大成”。杜甫继承了盛唐人兴会的构思就是“凌云健笔意纵横”,特别强调“意”的作用,以意统象,任意挥洒。其次,杜甫在创作中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特别重视物象,对物象加以精雕细刻,几乎到了“曲写毫芥”的地步。老杜本来就有观察细致又善于描画的本领。如《丽人行》中对丽人食馔、装束的描写,咏画诗中关于画境的描写都细致入微。特别是他的山水田园诗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盛唐其他山水田园诗作不同的特点:刻画特别的细致,给人以穷极物态之感。后来入蜀出峡所作的山水诗也是如此。总之,是杜甫较早地打破了兴会中意和象之间的平衡。
杜甫对盛唐人的兴会进行改造,是出于对诗歌艺术更高层次的追求。叶燮在《原诗》当中对诗人应该怎样表现“理、事、情”做了专门论述,他认为诗的高妙之处并不在于表现寻常即可言辨之事理。他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于理于事无不粲然于前者也。”他认为杜甫的创作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他举例说:“如《玄元皇帝庙作》“碧瓦初寒外”句,看似于量不合,“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48)],可见叶燮认为,高明的诗人就是能够表现“至理、至事、至情”。不唯求形似,而且力求神似,达到“入神之境”。叶燮总结说:“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49)]这是很高的艺术境界。杜甫的一些诗作已经达到这种境界,这说明杜甫已不满于盛唐诗那种图画性的特征,力图表现一般图画所不能表现的意旨,在提高诗歌表现能力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尝试。
诚然,盛唐人也是特别重视表现象外之旨的。王维、孟浩然等人对以有限的物象表现无限的情意方面有明确的自觉。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把能表现象外之旨作为盛唐诗的一大特点。但同样追求象外之旨,中唐人和盛唐人有很大区别。盛唐人追求象外之旨以不破坏物象本身的特点为原则。而中唐人求象外之旨则不再照顾物象本身的特点,对物象任意裁夺。这一转变就是从杜甫开始的。正如葛晓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王孟诗派将观赏和感觉相结合,以会景生兴,‘即景造意’为基本特点,诗兴由景物触发,景物大体上保持其本来面目。诗人虽然也凭主观感受取舍,或通过想象加以美化,但以客观描绘为主。杜甫强调心理感觉,便使景物有了较大的主观随意性。”[(50)]
不断地提高兴会活动中意的作用,是诗人们在运用这种构思方式时的一个发展趋势,从齐梁人的“文贵形似”到盛唐人的意与象并重,再到中唐人的以意役象,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它既是兴会这种构思方式本身发展的表现,也是诗人们对艺术的要求不断提高的结果。当然这种提高只是从理论上来划分的,并不是说盛唐人的作品高于齐梁,中唐人的作品又高于盛唐。因为审美价值的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中唐人的创作,特别是韩孟诗派的创作,基本上是朝着杜甫在兴会方面更重主观意趣的倾向发展的。不管他们是在有意学习杜甫,还是出于自发的对构思方式的选择。
皎然在追求象外之旨方面比杜甫有更明确的表述。《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皎然《诗议》《评论》云:“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51)]。杜甫讲“意惬关飞动”,“神融蹑飞动”,皎然也讲“状飞动之句”;杜甫讲“思飘云物外”,皎然也讲“采奇于象外”。为了求得寻常不可言辨的“冥奥之思”,皎然特别看重兴会中“运思会通”这一环节,特别强调“苦恩”的作用。他认为“诗工创心”,万象皆由心造:“如何万象自心出,而心淡然无所营”[(52)],“吾知真象非本色,此中妙用君心得。苟得上笔合神造,误点一点亦为道”[(53)]。《诗式》卷五“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格”中“立意总评”条云:“诗人意立,变化无有倚傍,得之者悬解”[(54)]。“变化无有倚傍”,就是彻底抛开客观物象的局限,这样诗人才能得到他所要表达之意。
孟郊早年曾参加皎然创办的“湖州诗会”,直接受到了皎然的影响,韩愈为孟郊诗友,作诗方式非常接近。他们作诗也是特别强调主观,一切物象都因主观的情绪而转移。他们把这种做法称为“象外求好”,如韩愈在《荐士》当中称赞孟郊时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安帖力排傲。敷柔肆纡徐,奋狂卷海潦。”[(55)]这“幽好”和皎然所说的“冥奥之思”意思相近,就是叶燮所说的幽渺之理、想象之事、惝恍之情。孟郊在《赠郑夫子鲂》一诗里提出了“物象由我裁”的口号:“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56)]根据主观感情表达的需要对物象做 适当剪裁本是一般的创作规律。但孟郊所说的肯定不是这一般性的写作常识,他指的是为了主观表达的需要,可以对物象任意裁剪,正如葛晓音先生谈到杜甫描写景物时所说的“较大的主观随意性”。韩孟诗派其他诗人作诗时也是这样。例如宋代张耒在读李贺诗时说:“独爱诗篇超象外”[(57)],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云:“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58)]“师心”,与皎然所说的“创心”意思相近,正是“超象外”、“出意表”的前提。
韩孟等人以意役象,对物象任意裁夺,在物象之外寻求玄妙意旨的传达,和盛唐人注意保持意与象之间的和谐平衡大不相同。而且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合于造化。造化本来是指自然,合于造化就应该客观描写自然,他们却认为胸中自有自然,自己可以创造造化,实际是说他们更能得自然之神。李贺在《高轩过》中称韩愈的诗“笔补造化天无功”[(59)],韩愈《答孟郊》中称孟郊“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60)],孟郊在《戏赠无本》中称贾岛说:“燕僧摆造化,万有随手奔”[(61)],都指出了他们创造造化的情形。他们在许多诗中还具体描绘了他们的创作过程。例如韩愈在《调张籍》中写道:“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62)],在《赠崔立之评事》中写道:“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才豪气猛易言语,往往蛟螭杂蝼蚓。”[(63)]前诗直写自己的创作过程。后诗虽是在评他人,其实也是在写自己的作诗体会。从中可以看出,他在作诗时任凭精神自由飞翔,不受任何物象的限制,而且,所有的物象只是随着精神的活动出现。“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与杜甫所说“意惬关飞动”,皎然所说的“通幽鬼神骇”的情形非常相似。韩孟等人这种过分强调“意”的比重,甚至完全把物象放到从属的地位,已经大大地悖离了盛唐人所遵循的兴会原则。精神漫无限制的扩张,必然造成物象的极度变形,韩孟诗派奇险的诗境正是以这种方式写出来的。
打破兴会中意与象之间的平衡不外两种办法,一种是加大“意”的比重,一种是加大“象”的比重。杜甫在创作中已经表现出这两种倾向。韩孟诗派大而化之,在创作上不仅特别看重“意”,也特别看重“象”,对物象的描摹不惜倾注大的气力,在求形似的基础上力求神似。例如韩愈在《南山》诗中,用了几十个“或”字句来形容南山景物之形貌,孟郊《石淙十首》写的不过是石头之间的流水声,却用了十首的篇幅,而常人所能见到的特征是有限的,所以必须搜奇发微,才能有东西可写。韩愈的许多诗只是对某一场景的细致描画,像《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咏雪赠张籍》、《叉鱼》、《郑群赠簟》、《嘲鼾睡二首》等诗写的不过是打马球、射野鸡、下雪、叉鱼、簟席、打鼾之类的具体场景,但作者都极尽描画之能事,并由某一具体特征联想到其它事物,引喻连类,以穷其貌。由于连接一组意象的往往只是某个物象的一个细小特征,因此难以构成一个浑融的画面。其情形仿佛把某一物象的某个特征放大成特写镜头,再由这个镜头展开广泛的联想,结果一首诗所写的常常不是一个统一的画面,而是许多幅画面。例如韩愈的《咏雪赠张籍》写下雪后,池塘、山坳、瓦陇、墙根各处雪的不同形状,并由此展开联想,其中就包含许多幅画面。《南山》中用几十种事物来形容南山景物之形状,各种画面之间也缺少统一的联系。盛唐人常常是杂取各物象的特点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韩孟等人却常常只顾物象特征的描画,而不管这些特征能否组成一个浑融的意境。这样可能写出极其生动传神的形象,也足以使读者感到惊奇可喜,但它只能是一些形象而已。
杜甫后期作诗力求句句惊人,句句有神,但他并没有因追求字句之神而忘记整体意境的描写。而韩孟等人由于特别看重物象,常常是不顾整体意境,只在字句上求神。韩孟诗派常常联句作诗,而事实上两个人或几个人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诗兴,因此作诗时,只能是自己写自己心中之所得,以传神之句来取胜。因此大量作联句诗表明韩孟等人并不看重统一意境的创造,只注意字句之神的传达。再如李贺作诗,通常是先将句子攒在锦囊里,然后附会凑成整诗。由于不是把一个完整的意兴一下子挥洒出来,写出来的往往是有句无篇。张戒《岁寒堂诗话》云:“杜牧之序李贺诗云‘骚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牧之论太过。贺诗乃李太白乐府中写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张戒也指出了李贺作诗走向了“以意为主”的另一个极端,犯了“以词为主”的偏至之病。以词为主正是过于重视物象的结果。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某一物象上,力求寻找它的特征,这样写出来的诗难免是字句有神而通篇少韵。“失于少理”就是没有用一种“意”把许多兴象统一起来。关于李贺诗有句无篇的特点,李东阳《麓堂诗话》说得更加明白:“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过分地重视物象,过分地对物象加以雕镂,反而失去自然之趣,这是韩孟诗派的共同特点。王夫之《姜斋诗话》也曾指出韩愈只在字句上弄巧而缺少兴会的毛病,“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先为外荡,生意索然矣。《松棱》体永堕小乘者,以无句不巧也。然皮、陆二子,差有兴会,犹堪讽味。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指出韩愈作诗但“于句求巧”,缺少盛唐人那种兴会,则是符合事实的。
其实盛唐人作诗有时也追求奇巧,不过他们的诗不因字句之奇而损害通篇之意韵。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中开奇正之说,认为李贺、孟郊的诗是属于“无正”之奇。相比之下,盛唐人应该说是正中之奇,奇不失正。而李贺等人只求奇特,不归根本,无正可言。这种奇正之辨若按兴会之说来解释,就是在统一的意兴范围之内求奇,是正中之奇;若抛开统一的意兴,只在个别物象上求奇,是无正之奇。
本来在兴会中极重意和极重象正好是相反的两个极端,可为什么韩孟等人同时朝两个方向偏至呢?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笔者在此做一点猜想式的解释:重意和重象虽然两极的,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追新逐奇,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极又相逢一处,对立的又得到统一。下面就分两个方面来讲。首先,重象也是重意的反映。韩孟等人为了抒写愤激不平的心理,因此经常寻找奇特的物象来表达。寻找奇特的物象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写那些不常见的物象,如蛟龙鬼魅,蝎子蚯蚓之类,一条就是在寻常的物象当中寻找不寻常的特点,他们重视物象实际上就是为此,和齐梁人“贵形似”并不一样。对齐梁人来说,肖其形貌,本身就是美,就是目的所在,而韩孟等人重物象是为了寻出象的特殊之处,以便抒发不寻常之情感。所以说中唐人重视物象并不是对齐梁人重视物象的复归,二者有很大差别。其次,重象也离不开重意。韩孟等人重视物象意在得物象之神,所以光像齐梁人那样“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曲写毫芥”是不够的。要想得其神,则必须加入“意”的活动,苦思冥想,发现象外之象,如果没有“意”的帮助,写出的物象难免质实有余而神采不足。例如李贺的“东关酸风射眸子”,以风吹人后的感觉“酸”来修饰风,“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以铜声来形容骏马之骨的不凡,都是诗人经过苦思后才有的神来之笔。综合这两方面可以看出,韩孟诗派有意打破兴会中意与象的平衡,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偏至,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审美追求所必须采取的途径。
前面说过,盛唐人所讲究的气骨、风神、蕴藉都可以统一在意兴当中。而韩孟诗派有意识地打破盛唐重兴会的传统以实现他们自己的审美追求,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也自然不同于盛唐。他们特重物象,有句无篇,因而气骨和风神只能体现在字句上面,他们不注重完整意境的创造,缺少浑融的意境,也难以表现出浑厚蕴藉的风格,而对物象雕镂过甚,也不会表现出平淡自然的特点。他们又特别看重情意的作用,对物象任意裁夺,必然造成物象的极度变形,从而形成险怪的风格,但这与盛唐诗歌兴象玲珑的特点大异其趣。
中唐后期的元白诗派也没有像盛唐人那样看重兴会。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张籍、元白的乐府诗创作“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是很符合元白等人创作实际的。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就曾说他五十篇新乐府“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元稹为杜甫作墓系铭,对前代诗歌提出批评,标准就是“意义格力”。他自己的讽谕诗创作,也是力求“感物寓言”。但元白等人的“以意为主”又不同于韩孟等人的“重意”。韩孟等人重意,是指出兴会中强调意的作用,以情意统摄物象,对物象任意驱使剪裁。而元白的以意为主是就意和文的关系而言:包括体裁的选用,字数的多少,题材的处理,手法和语言的运用,都要围绕意的表达来设置。因此,以意为主,有似作文的“主题先行”。这种意多半是由“感遇时事”而来,也无需多少自然物象来表达,只要把带有社会意义的人事物象组织起来,达到“其言直而切”就行了,因而创作中也就没有多少兴象需要会通处理,写出的诗也就没有多少景物和词采。张戒所说的“失于少文”大概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言。元白的以意为主,是沿着中唐前期诗人有意把说理引入诗中的方向而来,严格地说,已不属于兴会的范围之内,与在兴会中加入义理的活动是属于两个性质的问题。元白等人又把“以意为主”的倾向扩展到其它题材的创作当中,虽然不能说元白等人所有的诗作都没有兴会,但可以说“以意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凭兴会作诗。因而盛唐人凭兴会写出来的兴象玲珑、神采飘逸的风格也未能在他们大部分作品中体现出来。
当然,前面对盛唐到中唐诗人构思方式的对比,只是为了找出诗风变化的原因,并不是说中唐人不重视兴会或对盛唐人的兴会加以改造,写出的作品品位就低。中唐诗人,特别是中唐后期诗人,正是由于突破了盛唐人的兴会,以情意役物,从字句中求神,以理作诗,才使他们写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唐与盛唐在兴会上的差别只是就大体倾向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中唐诗创作都没有兴会。
On the Influence upon the New Change in Poetic Style
by the Transition of the Wayof Composing Poetry of High and
Middle Tang Dynasty
Wu Xiangzhou
Abstract:The way of composing poetr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decide the forming of poetic style.This thesis discusses systematically how the transition in the way of composing poetry from the flourishingTang to the mid-Tang Dynasty influenced the new change in poetic style,and points out that the prosperous Tang poets'composition of poetry was written generally at poetic inspiration moment while the mid-Tang poets would break the balance between impression and image in poetic inspiration moment on purpose,thus created the unique style of their own.
Key Words:Poets of flouring and Middle Tang Dynasty,way of composing poetry,poetic style,the new change.
注释:
① 《送鞠十少府》。
② 《酬张司马赠墨》。
③ 《别郑处士》。
④ 《放歌行答从弟墨卿》,《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三,页1349。
⑤ 《金唐文》卷二二五,页2275。
⑥ 《景龙观山亭集送密县高赞府序》,《全唐文》卷二九零,页2947。
⑦ 《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全唐文》卷二九零,页2947。
⑧ 《唐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赠尚书右丞相许国文宪公苏颋文集序》,《全唐文》卷二九五,页2987。
⑨ 《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页610。
⑩ 《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序》,《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页613。
(11) 《春于如孰送赵四流炎方序》,《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616。
(12) 《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七,页629。
(13) 见《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210~21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14) 《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二。
(15)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16)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一。
(17) 《寄张十二山人彪二十韵》
(18) 《偶题》。
(19) 《西阁二首》其二。
(20) 《峡中览物》。
(21) 《后至》。
(22) 《可惜》。
(23) 《对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
(24)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参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25)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26) 《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
(27) 《渼陂行》。
(28)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29)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30) 《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31) 《醉时歌》。
(32) 《独酌成诗》。
(33) 《寄薛三郎中璩》
(34)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35) 《上韦左相二十韵》。
(36) 《无锡东郭送友人游越》,《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九,页1532。
(37) 《题精舍寺》,《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七,页2626。
(38) 《奉和圣制登朝天阁》,《全唐诗》卷二百三十八,页2661。
(39) 《酬赵给事相寻不遇留赠》,《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九,页2673。
(40) 《山中酬杨补阙见过》,《全唐诗》卷二百九十三,页2773。
(41) 《送欧阳子还江华郡》,《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九,页2687。
(42) 《酬张二十员外前国子博士窦叔向》,《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三,页2720。
(43) 《重经巴丘》,《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七,页2723。
(44) 《送江陵元司录》,《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七,页2745。
(45) 《家兄自山南罢归献诗叙事》,《全唐诗》卷二百四十四,页2739。
(46) 《送张儋水路归北海》,《全唐诗》卷二百四十四,页2737。
(47) 《送元诜归江东》,《全唐诗》卷二百四十四,页2739。
(48)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第334页。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9)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第335~336页。
(50) 《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317页。
(51) 《文镜秘府论·南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52) 《奉应颜尚书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页9255。
(53) 《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页925。
(54) 《诗式校注》第255页。
(55) 《韩昌黎诗编年集释》卷五,页528。
(56) 《全唐诗》卷三百七十七,页4234。
(57) 《李贺宅》,《张右史文集》卷二十六。
(58) 卷四
(59) 《全唐诗》卷三百七十七,页4235。
(60) 《韩昌黎诗编年集释》卷一,页56。
(61) 《全唐诗》卷三百九十三,页4430。
(62) 《韩昌黎诗编年集释》卷九,页989。
(63) 《韩昌黎诗编年集释》卷五,页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