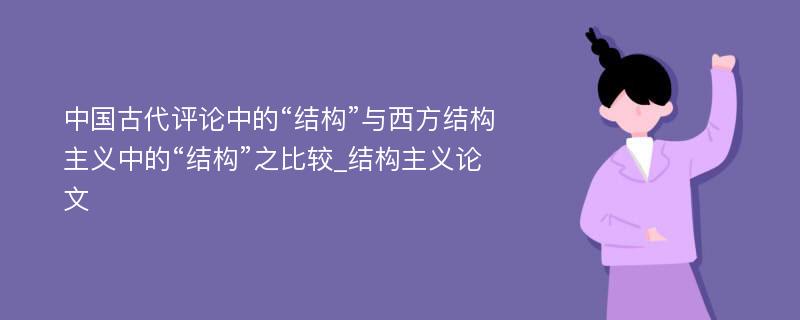
中国古代评点中的“结构”与西方结构主义的“结构”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结构主义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07)05-0098-07
1 引言
小说做法,古今中外都有研究,研究的角度也各有不同。本文只选取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中关于小说“结构”所作的阐释和西方结构主义文论中关于结构的论述作一比较,以窥二者之异同。中国古代文学评点大致始于唐代,在南宋走向兴盛,历元明清,至晚清逐渐消歇。评点是一种文学批评形式,也称批点、批评。批点是最早的一个词汇。批,指评论;点,指圈点。明以后渐渐使用“评点”一词,其中“评”是一种与文学作品勾连在一起的批评文字,“点”为圈点。评点最重要的特点是批评文字与所评作品融为一体,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圈、点、抹等等。宋代流传至今影响最大的古文评点范本有3种: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楼昉《崇古秘诀》。这三种古文评点本奠定了评点的基本形式:由3部分组成——卷前看文作文法;每篇前的总评;行文之中的批语和重点句子的圈点。随文批评和独立批评区别很大,它并不是把一般批评的内容分散到作品的各个部分,而是随文而生,有一般文学批评所没有的强烈的“现场感”。读一般文学批评文字如读山水游记,而读评点文字则如同在导游的引导下徜徉于山水之间。日后的小说评点大体承袭了文章评点的形式,小说评点置于篇前的“读法”即相当于看文作文法;回前评则相当于篇前总评;夹批、眉批、圈点就是文中的批语和圈点。小说评点在叙述技巧上的贡献是,它阐释了小说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文本特性和小说家的各种叙事技巧,尤其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结构”进行了探讨。
一般认为西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受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影响而形成。早期的结构主义文论家有普洛普、布雷蒙、格雷马斯、托多罗夫、罗兰·巴特等。1972年,出现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集大成之作——《叙事话语》,作者是法国的热奈特。所有这些结构主义文论家探索的是文学的内在结构,即文学的文学性,或叫“使作品成为作品的文学话语的潜在性”。
将中国古代评点中的“结构”思想与分析实践同现代西方文论、尤其是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结构”思想与分析实践放在一起,进行中西、古今文论的对话,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将首先引中国古代评点三大家对小说做法的评点,继之以当代西方的结构理论关于结构的概述,在展示双方论述的基础上,对中西的“结构”观作一探讨。
2 中国古代评点的结构观:以三家为例
何为结构?中国古代评点家对此有明确或不明确的表述。下面引用的是三家最具代表性的古代评点大家对中国古代几部名作的评点文字,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对此做出的阐释:张竹坡①评点《金瓶梅》;毛纶、毛宗岗父子②评点《三国演义》,及金圣叹③对《水浒传》的评点。张竹坡曾把小说写作比作盖房造屋,“要使梁柱榫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榫眼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毛氏父子在《三国演义读法》中认为,“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在具体例证之后,他指出:“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这里,张氏以房屋的具体形象阐释了“结构”,使我们有视文章结构如在目前之感。而毛氏父子则更是以具体的文字表述,明确表述了“结构”的概念,被赵景深誉为“见解深刻、才气横溢”。将中国评点式的评论方法推向高峰的金圣叹拈出一个“法”字来统摄一切文本分析方法。他将文本所有精妙的艺术都纳入“法”的范畴,而法又分4个层次: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④用现代语言来说,他的“法”也就是“结构”。张竹坡的“房屋”形象及与“房屋”有关的“起结”、“照应”概念;毛氏父子的“结构”;金圣叹的“法”等,都有共同的美学思想背景,即假定艺术作品的重要特征是文本具有结构形式,分析理解乃至把握文本,就要从剖析结构出发。因此,评点家们评点小说时的重要任务就是对小说结构中各种起结照应的分析。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具体阐释这一“结构”的呢?首先让我们看看毛评的《三国演义》。毛氏总结了《三国》一书中的16种结构法。兹举几例如下:
“追本穷源”法,如:三国之分,由于诸镇之角力。诸镇角力, 由于董卓之乱国。董卓乱国,由于何进之招外兵。何进招外兵,由于十常侍之专政。故叙三国,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
“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法,即题目可以雷同,人物可以雷同,事迹可以雷同,但写法却不雷同。反复叠用才能证明自己的文笔老练。既有犯之,又有避之,才能构成反复迭现原理的完整使用。犯,就是敢于一题多作。一番不够,比在一番出之;避,就是在犯的基础上追求意境、深度的新奇,翻奇出新。
“将雪见霰,将雨闻雷”法,指的是如有一段正文在后,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将有一段大文在后,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它是故事中心段出现之前的引文。其作用是暗示中心段的到来,让读者有所准备。设置悬念。闲文为正文之引,小文为大文之引。
“笙箫夹鼓,琴瑟间钟”,如《三国演义》中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纵横,忽有貂蝉风仪亭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娶二乔一段文字。……
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
“隔年下种,先时伏着”,正如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弈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
“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中间关锁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与前面核心事件相提并论,构成相互照应的“大关锁”。如《三国演义》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
以上各条,换用现代术语大致可以这样表述:第一条是因果推进法。因果而寻因,因因而有果,由此推动故事朝前发展。第二条是从相同或类似事件、相同人物的不同侧面进行叙述。第三条先写次要人物或次要事件,以为铺垫。第四条很像布莱蒙的插入法。即在第一叙事上插入一个次要叙事,以说明主要人物或主要事件,也可以缓和或调节紧张的气氛。第五条与现代之所谓“伏笔”极为相似。先埋下种子,待时萌发。直到后面事件发生,回想起来才想起为什么前面提到某人某事。最后一条则为现代之“照应”法。
金圣叹在对《水浒传》的评点中指出了其中文法凡15种。也摘选几种如后:
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
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
有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写周谨。
有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如武松打虎下岗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边月色是也。
纵览这15种“法”,我们可以看出,主要讲的是篇章与篇章之间的衔接、布局,或也可以说小说的结构安排,如事件或人物的反复迭现、正笔与闲笔之间的互相配合、比较与反衬的应用,闲文的点缀与穿插以缓解气氛。有些与毛氏父子的总结差不多,只是用语不同而已。
除了这15种法以外,金圣叹还对《水浒》的大结构作了评点。如在水浒开篇的“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诗后,金圣叹评曰:好诗,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在《水浒》的结尾诗后,又评道,好诗。以诗起,以诗结,极大章法。太平天下起,天下太平结。符合古代宇宙观。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金氏注重起结诗、起手结尾事件单元的含义相似性以及它们对其间故事的暗示、导引、解释作用。此外,他还提到“石碣”在整个文本的“首、尾、身”中起的结构和暗示作用。第一回,石碣被揭开,放走妖魔;第十四回,“七星聚义”于“石碣村”,导致后来的“梁山大聚义”。第七十回,公孙胜作法奏闻天帝时,忽然听得天上一声响,天门大开,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饶祭坛滚了一遭,钻入正南地下。众人忙掘地寻找,只见一个石碣。金圣叹评曰:“一部大书以石碣始,以石碣终,章法奇绝。”
张竹坡在评《金瓶梅》时,指出了地理意象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如玉皇庙、永福寺对角色的聚拢、发散、结穴作用。他是这样评论的:
永福寺,如封神台一样,却不像一对魂旗引去之恶套。如武大死,永福寺念经,结穴于永福寺也。杨宗保非数内人,故其念经用素僧。子虚又用永福寺僧念经,一样结穴也。瓶儿虽并用吴道官,实结穴于永福寺,千金喜舍,本为官哥也。至梵僧药,实自永福得来,自为瓶儿致病之由,而西门溺血之故,亦由此药起。则西门又结穴于此寺。至于敬济,亦葬永福。玉楼由永福寺来,而遇李衙内。月娘、孝哥、小玉、俱自永福而悟道。他如守备、雪娥、大姐、蕙莲、张胜、周义等,以及诸残形怨愤之鬼,皆于永福寺脱化而去。是永福寺,即封神台之意。
(张竹坡评《金瓶梅》第八十八回之回评)
上述几位评点家关注的大结构,是形式上的大照应。这种照应,从语言或文学体裁上看,可以是以诗起以诗结,(如《水浒传》之始终),或如《三国演义》之“以词起以诗收”;从意象来看,可以是开篇时的意象在终篇时再次出现,此次的出现表明了故事的大了结。(如《水浒传》中之石碣;《金瓶梅》中之玉皇庙、永福寺。)从社会观来看,可以是“天下太平——天下不太平——天下太平”的循环,或《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首尾大照应”、“大起大结”。从人生观看,还可以是“梦”“空”二字的形象演绎(如毛氏赞赏最后总结三国事迹的一篇古风,曰“此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空’字结之,正如首卷词中之意相合。”)。但不管是哪一种,一部巨制,都必须有个前后照应,才具有内在完整性的结构。
应该说,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对小说结构有了清楚的认识,在进行评点时有了“结构”的自觉。西方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又是怎样认识结构,并具体分析结构的呢?让我们首先对西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作一简单的回顾吧。
3 西方结构主义文论撮要
何谓西方叙事理论中的“结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结构。语言学家皮亚杰认为,“结构”应包括3个概念:即整体概念(the idea of wholeness)、转换概念(the idea of transformation)和自律概念(the idea of self-regulation)。
所谓整体,是指由一定的结合规律组合在一起的由各种成分构成的一个系统;“转换”是指结构中的各部分能根据某些规律被交换、被修改;“自律”是指这个体系的封闭性和自我调节性。从广义上看,结构主义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它不探讨个别的事物,而是把所有事物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并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个别事物是整个系统中的一分子。只有把它作为整个体系中的一分子的时候,或者说只有把它放在整个体系的关系中去考察时,我们才能找到它的意义。首先把这个观点应用到语言研究中去的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他把语言分为language,langue,parole。 Language指的是整个人类的语言可能性,这几乎是没法研究的;langue指的是一个语言体系,比如中文,英文;parole是我们具体使用的语言,也叫言语,是individual utterance。对一种语言体系没有任何知识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这种体系下的任何言语的。这一思想对文学的启迪是,由于文学的意义是由文学内外的关系网来决定的,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作品的意义,就一定要了解文学的“言语”(即文学作品)所处的文学总体系。因此,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学研究的适当对象就是“文学性”,即使文学成为文学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普适性的,因此,对结构的研究就不是对具体某部作品的分析讨论,而是要对使文学成为可能的成规进行了解。这样,结构主义诗学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使文学效果成为可能的潜在系统。这是关于内容的科学,但更是一种关于内容的条件的科学,即形式的科学。
西方文学研究中首先对这种“形式的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俄国的普罗普(Vladimir Propp),他是文学结构主义的先驱。早在20世纪20年代,普罗普就对俄国的民间故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尽管故事中人物不同,却起着同样的作用。他按人物行为在整个行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来定义,把人物的行为称为各种“功能”。人物的这些功能是故事中固定的成分,而无需考虑这个具体的人是谁。普罗普惊奇地发现,所有故事中“功能”的排列都一样,所有的故事都具有同样的结构,所有的故事都不超出他列出的31种功能。普罗普把前7种称作“准备”阶段,8~10为故事的“结扣”阶段,继之以转折、斗争、归返和认可。尽管这31种功能没有很强的内在逻辑,但却包括了所有俄国民间故事中的结构成分。普罗普还根据“行为域”将人物划分为7类(the villain,the donor,the helper,the princess [the souqht-for person]and the father,the dispatcher,the hero[seeker or victim],the false hero)。普罗普的贡献在于,尽管他没有对这些故事作美学的研究,但他找出了一种文类的基本形式单位,以及支配各单位之结合的原则,从很多文本中抽象出了这类文本的结构,从而揭示了这一叙事文类的语法和句法。他教会我们从情节功能和人物功能去寻找叙事的抽象结构,为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寻找结构的努力提供了难得的参考。
法国理论家布雷蒙和格雷马斯都从普罗普那里获得灵感。布雷蒙发现普罗普的一些民间故事的功能之间有逻辑关系,他要进一步找出这种关系的性质,从而获得“小说作品的首要因素”。他认为,叙事作品的根本结构因素不是普罗普的“功能”,而是作品的序列。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以互相交织的序列表现出来。为此,他设计了一个基本序列图:任何故事都有一个起因,这一起因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走向实现的过程,一是没有走向实现的过程。走向实现过程又有两种可能:成功和失败。为了使序列更具有解释力,布雷蒙增加了“连接”(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序列前后相连,前一个序列的结果引发后一个序列)、“镶嵌”(指在第一序列完成之前,插入另外一个序列,以补充说明第一序列)、“两面”(即用不同的眼光观察同一件事造成的结果,如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眼中有好有坏的判断。)等3项序列,构成复合序列。格雷马斯从普罗普的“行为域”中得到启发,从而从角色方面去探讨叙事中的各种关系和结构,这就是他的“角色模式”。他把角色(相当于行为功能,不指充当这一功能的具体行为者)分为6种:主角—对象;发送者—承受者;帮助者—反对者。在这一结构中,发送者引发主角行为,主角行为指向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帮助者帮助主角获得对象,反对者阻挠主角获得对象。主角通过努力获得对象的话,他就又是对象的承受者。茨维坦·托多罗夫借语言学的传统作为分析叙事结构的工具。他认为任何叙事都可以从语义、句法和修辞3个方面考察。“语义”考察作品的内容,“句法”考察作品的结构特点及其结合方式,“修辞”考察用词、视点及一切与文本的实际语言有关的东西。实际上他着意考察的主要是句法层面。他把叙事的结构单位分为4个层次,即故事,序列(sequence)——他的序列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小故事,或评点中的所谓“缀段”。每个故事一定包括至少一个这样的序列。命题(proposition)——一个命题就是一个基本的叙事语句。结构上就等于一个完整句或一个子句。词类(parts of speech)——在词类下他又分:a.专有名词(人物),b.动词(行为),c.形容词(特征)。罗兰·巴特吸取了普罗普、布雷蒙、格雷马斯和托多罗夫等各家所长,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把叙事作品分为3个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叙事从这3个层次的交互融合中找到意义。
被米勒称为“精明而深刻的批评家中最杰出的一位”的热内特,谦卑地称自己企图找出所有文学作品中的统一性和统领所有叙事作品的规律是不自量力。但就是他,以脚踏实地的努力,通过对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解读,找出了文学作品中“怎样说”的秘密,遂成一代叙事学大师。热内特区分了“故事”和“话语”,并在时间、视角、叙述3个层面上对叙事虚构作品的内在结构作了全面的研究。在时间层面上,他探讨了故事时间在叙事中的重构方式;在视角层面上,他探讨了叙事中以谁的眼光对事物进行聚焦的问题,或者说,“谁看”的问题;在叙述层面上,他探讨了“谁说”的问题。卡勒在为热内特的《叙事话语》写的序中对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宗旨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并非要阐释文学,而是要探索文学的结构及各种方法。其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诗学,它与文学的关系就如语言学之于语言。因此,他试图解释的,不是单部作品的意义,而是要揭示出使作品有其形式和意义的系统。结构主义非常注重情节结构(亦称情节语法),非常注重小说中使各种细节结合起来产生悬念、人物、情节序列、主题和象征模式的方法。在《叙事话语》的“前言”中,热内特解释了对《追忆逝水年华》这单部作品的阐释和理论创造的关系。同样表明了他探索的最终目标是一种普适性的叙事理论。他说:
正如任何一部作品、一种组织那样,《追忆逝水年华》是由普适性的,至少是超单部作品的各种成分组成的。它把这些成分组合成一个具体的综合体,一个特别的整体。分析这部作品,不是从一般到个别,而确实是从个别到一般。……因此,我必须承认,在对具体作品的探索中,我找到了一般规律;我原本是要让理论服务于批评,却出我意料地让批评服务了理论。
至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评点中的“结构”思想和西方结构主义叙事文论中的“结构”论作一粗略的比较了。尽管我们可以见出二者之间的很多共同点,比如都在寻找叙事作品的内在结构规律,甚至很多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草蛇灰线法”与西方概念中的“ foreshadowing”,“prolepsis”相似;“犯”、“避”的概念与“repetition”相似;“绵针泥刺法”与“irony”“satire”相似;“背面铺粉法”、“奇峰对插锦屏对峙”、“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与“contrast”“analogy”相似;“浪后波纹雨后脉沐”与“denouement”相似,等等。)甚至也都有为所有叙事文本立法的思想,但我们更着重于它们之间的不同,以期了解它们,使它们起到互补作用。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评点中,评点家们能凭自己的感悟和灵性体会到结构的存在,并以直观的形象指出结构的模型,但很多时候是心中有所悟而未对其进行系统的、具有逻辑性的描写。比如金圣叹对“部法”(应属对抽象结构的研究范围)的描述并不清楚,他具体指出的,多属他所谓的“章法”。比较而言,西方叙事理论有对结构的抽象探索,并由此出发,利用一整套术语对结构进行具体、细致、系统的描述。具体地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如下差异:
(1)结构理论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的评点明显地有着一种“寄生”现象,即评点依附于文本本身,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评点随感而发,包罗万象而未成体系。关于结构的论述,除了“读法”,“回前评”,“序言”以外,文本内的夹评也时有阐发,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独特的表现法,让研究者有“沙滩拾贝”之感。在零散中寻找系统结构的碎片,组合成结构之说。与此不同,西方的结构研究具有独立性、逻辑性、体系性,本身就很有“结构”意味。还有,很多学者指出的中国文论表述重形象,西方表述重逻辑的现象,在结构论中同样非常明显。在毛氏的16种结构法里,有12种是用形象表达的;在金圣叹的15种结构法中,有7种是用形象表达的。而上述的西方理论家们却无一以形象代替概念。
(2)结构认识中对情节和故事的偏重不同。总的来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叙事作品每一单元(章节)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单元与单元之间没有太多情节上的紧密联系,即所谓缀段性(episodic)结构。以主题为中心,而不以某一个角色为中心,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特色。《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莫不如此。这种小说更重视空间事件之“会”。这些聚合的事件往往由一个明确的主题(语义)来统摄,《三国演义》的主题是三国的纷争;《水浒传》的主题是逼上梁山;《金瓶梅》的主题是西门家的兴衰;《红楼梦》的主题是贾府的盛衰;《儒林外史》的主题是“儒林”的生存困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社会各方面的腐败;《官场现形记》的主题是官场的黑暗,《醒世姻缘传》的主题是因果报应、惧内等等。各“段”或者说各“插曲”之间看似松散杂乱,其实往往有一些特殊的故事单元分别置于开头、中间和结尾的醒目之处,起“照应”、“关锁”以及提示和加强主题的作用。前后故事单元之间则通过伏线和照应、引文和余波等方法穿插勾连。如《三国演义》首卷以十常侍乱政的故事开始,末卷以刘禅及孙皓宠中贵作结;首卷写黄巾妖术,末卷写刘禅信师婆和孙皓信术士,中间有李榷喜欢女巫、张鲁运用左道以关合前后。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分为十九卷,每卷六回或七回。第一卷除了桃园结义的故事外,都是乱政事件。首尾及中间“关合”的事件都是在不断暗示政治失序。金圣叹改造之后的《水浒传》,“一部大书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碣终止。”石碣就起着结构上贯穿整个故事和暗示其后有事发生以及解释事件性质的作用。《金瓶梅》的大起大结是具有地理色彩的意象玉皇庙和永福寺,以玉皇庙西门庆热结兄弟起,以身死名裂葬身永福寺结,以表“炎凉之旨”。
这样,尽管单元与单元之间没有太多形式上的联系,但整个小说有了“神理”上的贯通,有了整部书中的大照应,大关锁,就具备了评点家们认为的理想结构。与中国古典小说的这种不求形式而求语义贯通的结构相比,西方的小说(尤其是传统小说)能一以贯之,讲求以主角的故事贯穿整部小说的“首、身、尾”的有机结构和整体感。比如,《鲁宾逊漂流记》就以鲁宾逊为主角,讲他的故事,其他的人物都是配角。正因如此,在对具体小说结构的探索中,也就强调情节上的整体性。如普罗普的功能考虑的是主角为红线的情节发展的始终;布雷蒙的理论考虑的是情节发展的三阶段(开始、发展、结束)等。
(3)结构研究的层次和范畴不同。总的来说,西方结构主义研究的结构主要是超乎句法层面以上的结构,如叙事情景、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声音等,而不注意句法层面上的问题,那是传统文体学研究的范围。但评点学则不同。它可以对个别、具体字词的妙用作赞语,可以对事件安排作评价,也可以对整部小说的结构作判断——尽管是不成体系的。在这些零散的评论中,涉及的中心范畴主要是修辞性的“句法、章法、部法”,而少有上述的西方研究的主范畴。下面以对时间的考虑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的缀段式结构,是单个事件空间化安排的结果。叙事的空间化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的一个根本特征。其原因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家注重事物的自然运动,按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顺序组织叙事。这种顺序让人们感觉不到情节的因果特性,感觉不到时间在组织故事中的作用,于是对时间的探讨就变得可有可无,而只剩下对空间因素的考虑。这恐怕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诸评点家的论述中都没有提到小说中时间的安排。而在西方,小说中的叙事充分反映着时间的变化。时间安排是小说艺术中的重要部分,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都会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的利用。因此,敏感的理论家也把时间作为小说叙事技巧的重要方面去研究。叙事理论大家热内特在其《叙事话语》中用了近2/3的篇幅讨论时间问题。他从3个方面对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时序(order)讨论话语时间对故事时间的倒错;时长(duration)讨论话语时间表现故事时间的长短;频度(frequency)讨论故事时间在话语时间中出现的次数。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对小说中时间再现的最详尽的探讨,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4 结语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被西方批评界认为散乱无章。国内的学者也有同感。如陈寅恪就坦言:“至于吾国之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论再生缘》,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学者,他对中国小说的看法无疑有着西方思想的烙印。小说文本如此,在这些学者的眼中,中国古代评点式的文论,恐怕也会受到同样的指责。我们怎样看待中国古代评点与西方叙事理论对结构的阐述之间的差别呢?一方面,与西方结构理论相比,我们承认中国古代评点不具有它那样的独立性,那样的系统与缜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古代评点的丰富性。评点所涉及的,不仅有整部作品的部法,还有每章之中的章法和当今之所谓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其所涉及的是当今叙事学和文体学两种学科的内容。中国古代评点是感悟式的,随意性的。但这些文字充满了灵性,读来是口有余香的美文,而且最具一种评论家随时在身边与读者亲密对话的感觉,显得非常亲切。⑤这一点,是我们读西方文学理论时所不能期待的。中西之间的小说结构论有差异,这不仅是古今的差异,更是中外不同文化的差异。以古与今比、以中与西比,不是以今苛古,以西苛中,当然也不是为了显示“西方的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祖先早就说到了”的妄自尊大。在把二者进行比较时,我们完全是把它们放在同等地位上的。把它们进行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建设我们新的文学理论。
注释:
①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祖籍浙江绍兴,明代中叶迁居徐州。张竹坡自幼聪颖,15岁时参加乡试,然而一直仕途不顺。 1695年,张竹坡26岁时,在徐州家中评点《金瓶梅》,写下了10余万字的评论,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
②毛纶,明末清初茂苑(即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德音,号声山,生年约在明万历40年 (1612)左右,未曾出仕,中年以后,又不幸双目失明,享寿在60岁以上,在康熙五年(1666)以前评点过《三国演义》、《琵琶记》。
毛宗岗,毛纶之子,字序始,号子庵,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为一介寒懦,卒年自当清康熙48年(1709)以后。
毛氏父子修订、评点的《三国演义》刊刻以后,逐渐取代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明末清初的其他版本而风行全国。今天流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就是毛氏父子的修订本。
③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名喟。吴县人。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④《金圣叹全集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10-11。
⑤比如,当读到“柴进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领新纳红绸袄,带着个白范阳毡笠儿”时,评点马上提醒:“看官着眼,须知此处写个红袄白笠,正是为下文打虎渲染也。”这种“在身边”(presence)的“直接感”(immediacy)是西方文论无论如何都不可企及的。
标签:结构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三国论文; 追忆逝水年华论文; 金瓶梅论文; 读书论文; 儒林外史论文; 金圣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