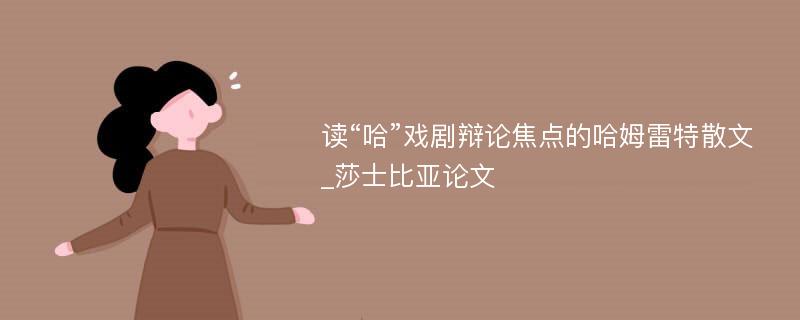
读《哈姆莱特》随笔——《哈》剧争论焦点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特论文,哈姆论文,随笔论文,焦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哈》剧的争论
“莎士比亚,不是想给你的名字招嫉妒,
我这样竭力赞扬你的人和书;
说你的作品简直是超凡入圣,
人和诗神怎样夸也不会处分。
这是实情,谁也不可能异议,
……
因此我可以开言,时代的灵魂!
我们所击节称赞的戏剧元勋!卞之琳 译)
这是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朋友,剧坛敌手,同行知己本·琼生在莎士比亚过世后的第七个年头,为在1623年编印的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对开本)所写的著名的题词中对莎士比亚做的最早评论。伟大的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离开人世已经几个世纪了。在这几个世纪中,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朝代兴衰,新旧交替,然而在这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中,在文学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里,对莎士比亚及其不朽巨著的评论却是长兴不衰,人们热爱莎士比亚,更热爱他的作品,从十七世纪一直到今天这三百多年之中,多少莎评派别,多少主义者、评论家、学者纷然杂陈,粉墨登场;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百家争鸣,世人受益匪浅。在浩如烟海的莎评中,对《哈姆莱特》的评论当属首位了,因为人们对《哈》剧的热爱也毫无争议地属第一了。
莎士比亚是在1600年末或1601年初写成《哈》剧的。此时,莎士比亚已经完成了十部喜剧,九部历史剧及三部悲剧。《哈》剧第一次上演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都在上演着《哈姆莱特》,热度有增无减。大多数名角都可望获得扮演《哈》剧主角的机会,而且都把扮演哈姆莱特这个角色的成功视为自己事业的顶极成就。这部剧被译成多种文字,为各国人民所赞赏,甚至西方一些高校也在其年鉴中印上《哈》剧中的名言,诸如“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莎剧第九集,第66页)作为学生攀模的格言。
文学批评家们在《哈》剧中发现了许多的宝藏:如宛延曲折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的人物刻划;晶莹剔透的无韵和压韵的诗行等等。同时他们也发掘了一批双一批的“问题”。三百多年来的《哈》剧评论可谓“浩翰无涯”,就连第一幕第一场开幕时军官勃那多在城堡前的露台上向前来换岗的士兵弗兰西斯多的第一句发问:“那边是谁?”都有专家做了大量的评论。评论说,这个“谁”字问的不仅仅是那个士兵是谁,而是莎士比亚在向这个世俗的世界发问。剧中的“主人公面临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在每一个场合中,人都要问问自己——你是皇帝,还是谋杀者?是王子还是小丑?”(注:“莎士比亚笔记”作者EDITH SITWELL.第82-83页)
可以说,《哈》剧是一个迷,评论家、戏剧家、学者不知做过多少次的尝试,并使出了混身解术,旁征博引,企图解开剧中错综复杂的“谜”:为什么哈姆莱特一而再,再而三地延宕,迟迟不对杀死自己父亲的叔父克劳狄斯动手?哈姆莱特的母亲格特鲁德在嫁给克劳狄斯的前前后后,在这一场血腥的谋杀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鬼魂所说的话究竟可信不可信?鬼魂从坟墓中返还人间,忽隐忽现,要求儿子替它报仇,是神话,还是现实?哈姆莱特是装疯,还是真疯?哈姆莱特曾经爱过奥菲利娅,可是后来突然变得那么冷酷无情,那么他是否还在爱恋着奥菲利娅?奥菲利娅的死是有意自杀,还是溺水身亡?是什么力量驱使哈姆莱特从自杀的念头转为相信上苍的安排,从“是生,还是死”,转为“有准备就是一切”?这些以及更多,更多的问题都是争论,评论,评说的热点,甚至连奥菲利娅在第三幕第一场中与哈姆莱特私下见面时哈姆莱特手中拿着一本什么书都引起不少的争论。根据统计,《哈》剧引出的评论比任何一个剧本都多。进入二十世纪对《哈》剧的评论,在十八、九世纪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百花争艳,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实为空前。在诸多的评论中,有发人深省的上上作,也有荒诞离奇的下下作,鱼龙混杂,色彩斑澜,这并非反常。哪一个人在拜读了《哈》剧这样伟大的著作之后,不想试一试拿起笔来,对深深打动他的心的主人公去评说一番呢?问题在于,我们读到的,听到的争论多,但各莎评派系对焦点问题的争论达到统一,做出定论和结论的甚少。有人说哈姆莱特延宕,就有人说那是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有人说哈姆莱特是真疯了,就有人反驳说哈姆莱特根本就没有疯,等等,等等。各自引经据典,振振有词,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准备一定要说服谁。然而,也正是如此,我们说这恰恰反映出莎士比亚在人物刻划上所表露的天才之道,他的智慧留给后人的是永远寻求解开他的巨著的金钥匙。
二、《哈》剧版本的评说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方面,专家们历尽千辛万苦似乎找到了打开其秘密的钥匙。批评家们对十四行诗的写作时间、出版前言、莎士比亚和他的赞助人的关系,莎士比亚和那个浅黑色皮肤的女人的关系以及他的同时代人及敌手的关系等似乎有了一个共识。同样,在《哈》剧的研究方面,专家们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西方一代代学者,参证各代舞台上的实践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背景,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对莎士比亚戏剧文本,进行苦心校勘、汰洗、增补、进行整理,作出了接近定局的解释和结论。大家知道,曾经有人公开地否定莎士比亚,否定他对著作的权威性,甚至荒谬到否定莎士比亚其人的存在,妄测其作品出于它人之手,耸人听闻,人们对这种评论早已不屑一顾了。最终专家们捋出了一条粗略的线索,合情合理,母庸置疑。
1602年7月26日在英国版权登记处记载中有这样一条记录:“近期由查伯伦勋爵剧团上演的名为“丹麦王子复仇记”一书在此登记造册。”1603年出现了此剧的第一个四开本,这一版剧文很不完善,不仅有错误,而且还有删减。有人认为此本不是悲剧的初稿,就是删节了的舞台本,未得莎士比亚本人同意或审查而印行的。在这个版本中,甚至有些语句与后来的版本有着许多明显的区别,它把原剧中最著名的一段哈姆莱特独白“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竟印成“是生,或是去死,啊,这到是有点意思。”尽管这一版的四开本质量很差,但剧本的题目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悲剧史——莎士比亚著,该剧由皇家剧团在伦敦市及剑桥和牛津两所高校中巡回上演。”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一,查伯伦勋爵的剧团已经由詹姆士一世批准升为皇家剧团,莎士比亚就是该剧团的一位演员、编剧和股东。第二,《哈》剧能在大学圈内上演,而且获得成功,说明该剧质量属于上成。1604年出版了《哈姆莱特》的第二个四开本,在内封上写道:“据真实完善抄本增补印行,较前增添将及一倍。”1623年,在莎士比亚逝世七年之后,《哈》剧的第二版对开本问世了。这个对开本是根据1604年出版的第二个四开本印行的,它比四开本的内容少了218行,可是又增加了85行新的内容。专家们认为这两个版本内容的增减部分都是真实的,其增减内容主要是在不同演出场合,根据演出的需要而增减的。
专家们一直对第一个四开本和第二个四开本的关系争论不休。曾经有人认为第一个四开本就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莎士比亚在最初处理《哈》剧时就是那样一个水平。然后最新的考证否定如上的说法,认为第一个四开本是某一剧团在巡回演出中一位拙劣的编剧为了演出而在莎士比亚的原剧本中进行粗制滥造的修改和删减而成的。专家们注意到在第一个四开本中载有一段马西勒斯的台词,而这段台词与第二个四开本中的台词一模一样,将之与那些粗制滥造的删改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明显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与莎士比亚的文笔相差悬殊。专家们几乎一致肯定这位盗改莎剧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那位扮演马西勒斯军官的演员本人。
自1623年出版第一个对开本《哈》剧之后,许许多多版本的《哈》剧相继问世。后来出版的种种版本基本上都是以莎士比亚的第二个四开本为依据印行的。
至此,有关《哈》剧版本真伪的争论总算告一段落,为大多数批评家所接受了。但是接踵而来的又是在《哈》剧故事来源上的争论。莎士比亚在决定编写《哈》剧时,他的创作素材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这个问题也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三、《哈》剧故事溯源
《哈姆莱特》这一剧作的故事情节并非莎士比亚自己创作的。在莎士比亚时代的剧作家一般都不自己编写故事。他们大都采用一些已经在社会中流传的故事,赋以戏剧的形式。并且,有时按照自己对人物性格和事件发展的意见改造原来的或别人写的剧本。《哈》剧故事情节亦是如此。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替父报仇是北欧一个广为流传的非常古老的故事。早在莎士比亚所著《哈》剧问世前十几年,伦敦的午台上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了。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丹麦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萨克索·格拉麦狄库斯所编写的拉丁文版《丹麦历史》(12世纪)中,故事写的是一位厚颜无耻的“冯”暗害了自己的长兄哈温狄里,并强占其妻葛汝莎,哈与葛生有一子,已长大成人,取名为阿姆莱斯。冯派部下对阿姆莱斯严加看守,而年轻的“阿”发誓为父报仇,为了转移视线,寻找机会,聪明的“阿”假装弱智,果然奏效;他先是说服了母亲,并在其母的帮助下杀死了“冯”及其部下同谋,最后阿被拥戴为丹麦国王。在原始情节中,没有鬼魂的出现,也没有踌躇不决,因为“阿”的父亲被害不是秘密,“冯”以哈温狄里虐待其妻为借口来为自己的暴行解脱。“阿”就是公开地,顽强地去复仇,因为在纪元前的丹麦,复仇并不违犯道德和宗教的法规,而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莎士比亚没有直接从这个古老的故事中取材。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贝尔福改编了阿姆莱斯复仇的故事,并将其译成法文,收入到他的《悲剧故事集》中(1576年出版)。贝尔福改编的《哈》剧中的叙事主线,人物模式以及故事的素材大都出现在莎士比亚编写的剧中,其中包括有奸情、杀兄、复仇、装疯以及利用哈姆莱特的同学和情人来刺探哈姆莱特等等。但是在莎士比亚的《哈》剧和贝尔福的《哈》剧之间,还有很多的差别,“贝”剧的主线是:
1.杀死老王哈姆莱特是公开的秘密,但篡位者成功地说服公众,谋杀是为了保护皇后。
2.哈姆莱特被描写成一个毫无防卫的青年人,他装疯卖傻是为了保护自己。
3.尽管哈姆莱特被美化成世人的楷模,但他为了复仇,时而表现得非常残酷无情。
4.哈姆莱特装疯时,有一个很可笑的动作,挥舞手臂,学着鸡鸣。
5.皇后忏悔自己的错误,哈姆莱特告诉她要杀死她的奸夫,替父报仇。
6.哈姆莱特娶了英国国王的女儿为妻,并逗留在英国整整一年
7.哈姆莱特返回丹麦,此时正值他的叔父庆贺哈姆莱特过世。
8.哈姆莱特施计灌醉朝臣,放火烧掉皇宫并杀死了国王。
如果莎士比亚是沿这条主线编剧,那么其故事情节的原始素材只有贝尔福的改编剧是最接近的框架。但是,在1589年左右,即莎士比亚刚刚在英国舞台上开始他的戏剧活动的时候,已经有了关于哈姆莱特的悲剧本了。这个悲剧被专家们称为“蓝本”,其作者是谁,不得而知,可惜的是,这个“蓝本”已经失传。但有人假定“蓝本”可能是托马斯·基得所写。基得是莎士比亚的同代人,比莎士比亚大七岁。他写过另外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剧本,名叫《西班牙的悲剧》,并以此出名。虽然蓝本《哈姆莱特》没有留传下来,但是可以从一部德国剧本中想象其大概。这部德国剧本名为《Der Bestrafte Brudermord》(“弑兄受惩记”),该书出版于1710年,此时莎士比亚早已过世。但批评家们猜测这个剧本是基于“蓝本”而写成的,可能是英国巡回演出团在德国演出时所使用的“蓝本”的翻版。恰恰在这个剧本中出现了鬼魂的招唤,戏中戏,哈姆莱特放过祷祈的国王,奥菲利娅的精神失常,以及毒剑、毒酒引出的全剧的高潮等情节。而这些情节与当时莎士比亚在世时他所属的剧团上演的《哈》剧的情节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专家们普遍认为莎士比亚的剧团一定有这个“蓝本”,而且在原剧中吸取了很多“蓝本”中的精华。如果说基得在故事情节的发展方面为莎士比亚提供了比贝尔福所编《哈》剧更多的素材的话,基得的剧本缺少的正是莎士比亚所独有的文学方面的探索,深入发展的一个又一个悬念,人物刻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整体构思的新颖独特性以及莎士比亚那无与伦比的诗行绝句。如果说“蓝本”所追求的是情节剧中奇异的情节和惩恶扬善的结局的话,那么莎士比亚的《哈》剧第一场演出就获极大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已远远超越了对情节的唯一的追求,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剧作家超凡的天才,他让人们感受这样一位天才给世人所带来的无穷的精神上启迪和享受,他让一代又一代世人为世界上曾经有莎士比亚这样一个大文豪而永远感到骄傲。
四、哈姆莱特之谜
对莎士比亚剧本的考证以及对莎剧故事的溯源工作历尽甘苦,风风雨雨,经过几个世纪的顽强奋斗,总算有了很大的成绩,并为大多数的批评家所接受。然而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批评,褒也好,贬也好,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从来没有统一过。人们记得很情楚,早在十六世纪末期,莎士比亚的同代人,剧坛上的敌手罗勃特·格林在临终前就曾经用词尖刻,辱骂莎士比亚是“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扮他自己,在演员的皮下包藏着虎狼之心。”这位“大学才子”格林先生对这位“打杂工”出身的诗剧天才莎士比亚的嫉妒、奚落和谩骂可谓蚍蜉撼树,不但丝毫没有降低莎士比亚的声望,反而说明了莎士比亚的成就之大,影响之大足以使当时剧坛上的名将都感到震惊。十九世纪的莎评以著名诗人柯尔律治等为代表,形成了莎氏崇拜。他们一味铨释欣赏而不一分为二。他们是英国最伟大的莎剧批评家,刺激了我们对莎剧的兴趣,帮助我们发现莎剧的深远奥妙。他们的缺点是主观、片面,甚至往往陷入牵强附会,走入了死胡同。进入二十世纪后,莎评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争论最多的仍是《哈姆莱特》。
对《哈》剧的评论集中表现在对主人公哈姆莱特的性格讨论方面。多数批评家认为哈姆莱特是一个完美的人文主义者,是“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朱生豪评),是个有德、有才、年轻美貌的王子,然而,在行动上是一个延宕、迟疑、犹柔寡断的人。可是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以及世界文坛上的泰斗,大文豪、大作家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中期,作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人物都先后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对《哈姆莱特》做了极端否定的评价。屠格涅夫在1860年1月10日为贫苦文学家学者救济协会而作的公开演讲中把哈姆莱特描绘成为一个“利己主义者。”他说:“他(哈姆莱特)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永远为自己忙忙碌碌;他经常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自己的境遇”,“哈姆莱特之流的的确确对群众毫无用处,何况哈姆莱特之流还会蔑视群众的。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他还能尊重谁,尊重什么呢?”他甚至把哈姆莱特说成是一个“好色之徒”,“狡诈,残酷”,一个没有“向心力”的人,但他也不得不把《哈》剧说成“属于那种任何时候都毫无疑义地叫座的戏剧”。(注:“莎士比亚译论汇编”,“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1860)第465-500页)(以上引号中为尹锡康译)
俄国大文学家、作家托尔斯泰在一生中曾再三反复阅读莎士比亚的全部名著,参考过各种译本(俄文本、德文本、法文本等等)之后,于1903至1904年写成《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一文。他认为,他始终感到莎士比亚的那些作品不仅不能称为无上的杰作,而且是很糟的作品。托尔斯泰在他的论文中竟然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抄袭的,表面地、人为地零碎拼凑而成、乘兴杜撰出来的文字,与艺术和诗歌毫无共同之处。”他认为哈姆莱特“完全缺乏性格,这怎样也不能证明莎士比亚的戏剧的优点是性格的塑造。”他还振振有词地讲,如果说“哈姆莱特”等莎剧中几个著名人物有性格的话,“所有这些性格,正象其它一切性格,并不属于莎士比亚,而是他从他前辈的戏剧、编年史剧与短篇小说假借而来的。所有这些性格,不仅没有因他而有所改善,大部分还被削弱被糟蹋了。”(以上括号中引语由陈燊译)两位大批评家的见解并非为所有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后来人苟同。他们两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理解莎士比亚,不能正确地理解现实主义,从而导致了如此荒谬的结论。
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在很多方面都引起了各家的评论,尤其是他总是不能干净、利落、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替父报仇。他的一举一动招致了很多的谴责。人们从对哈姆莱特性格的讨论逐渐扩展到了对《哈》剧的争论,甚至发展到象托尔斯泰等对莎士比亚的天才和能力的否定。哈姆莱特是一个谜,为了揭开迷底,三百多年来专家们绞尽了脑汁。人们说哈姆莱特迟迟不能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为外部的困难所包围,强大的克劳狄斯戒备森严,使他不能接近一步。在全剧中,他只有一次与克劳狄斯相遇时,“克”没有卫士在身旁。也有人说哈姆莱特是一位精神脆弱的梦幻者。正象哈姆莱特自己说的那样,他是因“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朱生豪评)还有人说哈姆莱特不能行动因为他早已成为过份忧愁的牺牲品,而这一类型的人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是常见的。一些批评家又从哈姆莱特的政治抱负方面,从鬼魂的真伪方面,甚至在近些年来还有一些人从所谓的恋母仇父的“俄狄浦斯情结”上找原因,以解释哈姆莱特行动的延宕。这些原因每种都有一定拥护者,但也都不能完全说服观众和读者。哈姆莱特这个“谜”究竟如何去解?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一个恰当的说法,那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了。
五、哈姆莱特性格剖析
文学作品总是时代的产物,我国著名翻译家卞之琳先生在他所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的译者引言中对莎剧做了这样一段精辟的分析,是可以做为解开哈姆莱特这个“谜”的金钥匙,他说:
他(莎士比亚)当然也知道一些西方古典戏剧教条,对中世纪民间戏剧传统有所继承与翻新,对同时代戏剧风尚有所沿袭,而当然不知道后世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说法,当然更无从想到现代西方不断标新立异,叫人眼花撩乱的烦琐文学理论,解剖活人的文字批评,当然也不可能予先明白这一个多世纪以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的权威理论家所谓“反映论”、“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等。但是从莎士比亚名下的大多数剧作……,从这些剧作本身看来,总不能不承认作者极有头脑,深怀激情,掌握了多种表现手法。他的同代人,剧坛敌手……本·琼孙说他是“时代的灵魂”……
(卞之琳)
要解开哈姆莱特这个“谜”,其实并不是不能做到的事,卞之琳先生的一席话,深入浅出,画龙点睛,其实已经破了这个谜底。
莎士比亚是在十六世纪末为当时他所在的剧团在舞台上演出而写的《哈》剧,莎士比亚当时并没有在写成剧本之后去请一位心理医生给哈姆莱特诊断一下,看他心理上是否有毛病。我们要找谜底也应该从这个地方入手。实际上,莎士比亚的观念并不认为哈姆莱特有什么问题,在《哈》剧上演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没有任何人担心哈姆莱特在性格上有什么毛病以致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复仇行动。到了十八世纪,终于有人对哈姆莱特的延宕问题提出质疑。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的一位批评家托马斯·汉莫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他说:“如果王子在第一幕里就干掉克罗狄斯,这个剧也就该闭幕了。”(注:《哈姆莱特》引言篇,第9页L.8.Wright和V.A.LaMar 合编:纽约、华盛顿广场印刷厂)在1600年当莎士比亚的观念来到环球剧院欣赏动人的《哈》剧时,他们所期望看到的正是一场时尚的情节剧——复仇剧,而这也恰恰是莎士比亚作为编剧所要写给他们的东西:一幕又一幕观众所预料到的悬而未决的场面;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包袱”,直到最后一幕,以暴力解决战斗。大家都应该很清楚,莎士比亚是个很讲究实际的人。他以超常的嗅觉,洞察市场,捕捉什么戏受欢迎,算是“好戏”,同时,睁大双眼盯着票房,考虑着如何改写剧本才能提高上座率。莎士比亚可万也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几百年间会有那么多文人学者用那尖刻的语言点评他的著作。如果莎士比亚在天有灵的话,他会感到后怕的。
《哈》剧是一部编写非常好的复仇剧。编者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满足伊丽莎白时期观众的胃口,因为观众寻觅的就是类似托马斯·基得所编的《西班牙悲剧》,莎士比亚所写“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以及那部丢失的蓝本《哈》剧所带给他们的快感和激动,这样说并不等于《哈》就没有伟大之处了。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剧,也正是那些在剧场内外最为广大观众和读者拥戴的剧。莎士比亚在《哈》剧中充分表现出他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而且在剧本中他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成为伟大的文学遗产,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人们在剧院中为莎士比亚的《哈》剧叫好,而那些没有机会去剧院看《哈》剧的人,则以极大兴趣拜读《哈》剧,从中获得教益。
许许多多的现代人从研究莎士比亚的《哈》剧的主要人物中获得审美快感,因为莎士比亚所奉献的每一个人物都在三维空间中表现得栩栩如生。我们感觉那些人物身上都带有个自的问题,因为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如果一个现代人,即使不像哈姆莱特那样有杀父之仇,他也会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呐喊;也会惊奇发现剧中各式各样人物的思想和态度与他所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人物的思想和态度是何其相像。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个奥菲丽娅,既讨人喜爱,又受制于父兄,而变得缺乏独立见解;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忍受象波洛涅斯那样一位世俗而又机敏,唠叨而又多事,诲人不倦但又成事不足的人;每一个人也都会在挣扎中求生,在走头无路时,想到哈姆莱特所遇到的困境。
《哈》剧使现代的读者和观众联想到现实生活,人们在联想的冥冥之中,不可避免的把思绪更多地集中在哈姆莱特这个人物身上。这出戏必竟是在写哈姆莱特遇到的问题,而且莎士比亚精雕细刻的这个人物也正是要表现他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以及他独特地处理哈姆莱特的问题的方法。我们似乎可以肯定莎士比亚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把哈姆莱特处理成为一枝弱不禁风的花朵,一位上不了大雅之堂的、神经过敏的白脸书生,一个面对暴虐从政的克劳狄斯束手无策的窝囊废,恰恰相反,哈姆莱特在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正是十七世纪初任何一个英国人所期望的在一位至尊的,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要以后当政的王子身上所应该具备的品德。《哈》剧一开场,我们便知道老哈姆莱特已经去世,且亡魂不断出现。第一幕第二场大幕一拉开,我们便知道哈姆莱特的母亲在丈夫死后不到两个月便嫁给了小叔子。这两件大事足以使哈姆莱特悲伤至极。他深深地陷入忧郁之中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他的忧患绝非一般。哈姆莱特自己说:“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朱生豪译)哈姆莱特也绝非深深陷入忧郁而不能自拔,以致行动迟缓。他以前也绝非是一个行动迟缓的人。哈姆莱特是一位有着“高贵无尚的理智”,“无比青春美貌的人”,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花、举世瞩目的中心”。(朱生豪译)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哈姆莱特所具有的品德和性格正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一位理想化的绅士所应具备的品德和性格:勇敢、豁达,有才气、有智慧、举止文雅、剑术高超,既懂音乐又识戏剧。天有不测,在遭受这场特大打击之后,哈姆莱特陷入忧郁之中,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哈姆莱特就此将一切高贵的品德一下子全都付诸东流。恐怕也只有头脑简单的奥菲丽娅才相信哈姆莱特是真疯了;也只有她才会认为哈姆莱特这颗高贵的心“殒落”了,“像一串美妙和银铃失去了谐和的音调”,“过去的繁华,变作今朝的泥土!”(朱生豪译)哈姆莱特在这样的情绪之中,作为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自然不会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莎士比亚在剧中创造性地安排了另外两位与哈姆莱特情况相似的角色——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和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他们三个人都年轻,都有杀父之仇,然而莎士比亚仔细地研究了这三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处境,小心翼翼地对这三个人的悲伤和复仇行动做了不同的处理:雷欧提斯性格暴躁,不分青红皂白,头脑简单,行动过激。当他得知自己父亲被害之后,马上聚众造反,冲进皇宫,欲向国王问罪。他这样轻举妄动,一下子就被老谋深算的克劳狄斯所利用,成了奸王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克劳狄斯借他的手和他的毒剑至哈姆莱特于死地,成为千古遗恨。试问,如果哈姆莱特要象雷欧提斯一样,恐怕他早已成为克劳狄斯的刀下鬼了。福丁布拉斯欲替父报仇,背景又不一样了。老福丁布拉斯是在一场决斗中被哈姆莱特之父杀死的,并失去了部分国土。但在这场决斗之前双方是有协议的:“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一切土地拨归胜利的一方……”(朱生豪译)福丁布拉斯替父报仇,首先从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报仇是假,要收复失地是真。于是他招兵买马,磨刀霍霍,欲与克劳狄斯一比高低。莎士比亚精心策划,避免雷同,既没有象雷欧提斯那不顾一切,肆无忌惮,也不像哈姆莱特那样审时度势,而是在接受其叔父批评之后,率一支部队长途跋涉,去攻打“一小块徒有虚名毫无实利的土地。”但是小福丁布提斯这位“娇养的少年王子,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朱生豪译)小福尔布拉斯表现出与哈姆莱特完全不同的性格:英勇、执著、不畏艰险、能曲能伸,不失王子的风范。我们很难把哈姆莱特与福丁布拉斯置换。哈姆莱特的气质要大大超过福丁布拉斯,思想境界也大大高于他。莎士比亚用这两个反衬人物成功地说服了他的观众和读者,哈姆莱特不能马上采取行动是符合逻辑的,是毋庸置疑的。
哈姆莱特受过最好的教育,学识渊博,有理性的头脑,真知灼见,折冲樽俎。他一直在威登堡大学读书,在那里他受到了文化的熏陶,明师的教诲。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懂得了如何去分析问题。因此,当问题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不会机械地去对待它,相反他要用他敏锐的头脑,冷静地思考,以便做出最恰当的决择。这个过程可能会较慢,但这一决策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结果。这也恰恰表现出一位具有真知灼见、善观风色,能深谋远虑的思想家的风范。
哈姆莱特精神上的痛苦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他那聪敏和机警的头脑,因为他洞察一切隐藏在背后的阴谋和平静中的不平静。在第三幕戏中戏之后,他发现克劳狄斯独自一人跪在神像前做忏悔。这是他所遇到唯一的一次在克劳狄斯身边没有警卫保护。哈姆莱特正好动手,杀掉仇人,报杀父之仇。但他没有这样做,如果要是雷欧提斯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定上前一剑刺死克劳狄斯,然而,哈姆莱特不是一位卤莽的人。他认为克劳狄斯“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为他开放着,这样算是复仇吗?”(朱生豪译)其实哈姆莱特心中有这样一本账:如果在没人时这样去偷偷杀死克劳狄斯并不能使丹麦国泰民安。丹麦上上下下还不了解老哈姆莱特是如何死去的,也不了解克劳狄斯的奸情。哈姆莱特此时强压怒火为的是要“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当他(克劳狄斯)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它邪恶的行为的中间”,哈姆莱特就要叫他颠踬在他的脚下,叫他的灵魂永堕地狱。莎士比亚的这一段戏安排得非常高明。莎士比亚的观众完全理解哈姆莱特的心情,也完全支持他的决定。观众不希望看到这出戏到此结束,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他们心中的偶像只是一位杀手,而不能担负起重整家园的重任。
六、结束语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是一位智勇双全,文韬武略的汉子。在行动上他采取的策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变幻莫测。莎士比亚塑造了这样一位能力非凡的主人公,也正是《哈》剧的超凡魅力所在,也正是《哈》剧能在几百年中不断地吸引着无数的观众、读者、学者、专家和批评家去研究它,去评说它,去争论它的原因所在。方平先生在他的论文《哈姆莱特的悲剧性格》一文中说得好,“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演员,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样,历来的评论家也一个个在各自心目中塑造着不同面貌的哈姆莱特的形象。”(莎士比亚戏剧论文集第344页)。莎士比亚以古喻今,借用古人凋零僻漏的草本和归入习俗的旧套,用自己天才的画笔和赋有的斑斓的色彩与神力,绘出了别具匠心的彩虹。这条彩虹造诣匪浅,有血有肉,富赋穷色,三百多年来,以《哈》剧为中心对莎剧的评论纵横交错,层出不穷,各有能自圆其说、不乏一得之见的不同领悟,不同阐发,足见戏剧本身内涵的深广,足见正是《哈》剧长兴不衰的道理。
几百年不过掸指一挥,对《哈姆莱特》的争论在数百年如一日地继续着。我想,今后几百年之中,人们也还会兴致勃勃地争论下去。这种争论的本身恰恰反映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作品万古长青,也恰恰证实了前人的预言:莎士比亚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魂!”他所编织的剧本色彩斑斓,内容饱满,跌宕多姿;尤如浩瀚的大海,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甘露;尤如当空的明月,晶莹剔透;尤如高悬的红日,照亮了世界戏剧发展的大道。正象历史和史学家的关系一样,戏剧和戏剧评论家的关系也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作品越是深奥、伟大,它所引起的评论也就越壮阔,越深刻,持续的时间也就越长久。《哈》剧亦如此。我们不想对争论的问题做什么最终的结论;我们也不可能做出最终的结论。那么,就让我们在评论家们的唇枪舌剑中欣赏莎剧,在他们的争论中吸取营养,在他们的循经取穴中获得思想上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