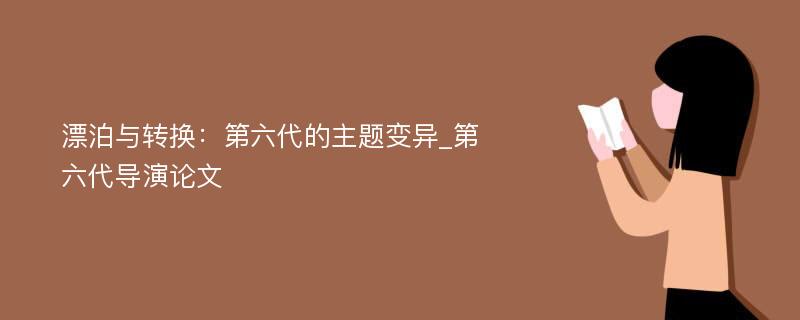
飘泊与皈依:“第六代”的主题变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第六代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1)02-0094-06
一、“代”群的表征和指向
有人把电影表述为是一种情感上的季节性消费品,就像更换性很强的季节性时装,通常是五年左右换一代。对此,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列·巴赞曾赞叹道:“电影毕竟是一门太年轻的艺术,它过于卷入自身的演变之中,以至于不能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在重复自身的过程中纵情享受,电影的五年相当于文学上整整的一代。”(注:巴赞:《电影是什么》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44-45页。)在文革后文艺得以正常发展的十年中,中国电影确实造就了两代导演,而其作为“代”的艺术活力呈现的时间也正好是五年,即“第四代”(1979~1983)的五年与“第五代”(1984-1988)的五年。也有人认为“第五代”电影运动应该从1983年延续到1991年,即从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到陈凯歌拍出《边走边唱》并以此作为终曲。此后,他们虽然都继续拍片,但不能视为一种“运动”的延续。这正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自1945~1952年,法国新浪潮从1958~1963年为界,道理是大致相同的。维斯康蒂、特吕弗、夏布罗尔、阿仑·雷内和戈达尔其后不断拍片但不能认为是运动意义上的新浪潮。
被称为“第六代”的电影创作活动是在“第五代”的终曲声中开始的。然而,在“第五代”电影运动澎湃潮声的遮蔽下,“第六代”的发轫之声更像是冰层下的细流,在流淌中发出时断时续的涛声。在90年代初,张元、王小帅和《妈妈》、《北京杂种》、《冬春的日子》这样的一些人名和片名经常出现在国外的大小电影节上,可以说“第六代”的发轫者们是以半业余化的粗糙制作、极端个人化的影像风格和制作方式的叛逆性而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的。他们的影片大多未经过电影主管部门的审查,被人称作“地下电影”,而无缘于与国内观众见面。“第六代”电影引起电影理论界热切关注是在90年代中期,其聚集点就是管虎的《头发乱了》。尽管此前的1993年已经有同属“第六代”的《北京杂种》在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上捧得大奖,但作为国家体制内的第一部“第六代”电影,《头发乱了》可谓是“第六代”的滥觞之作。
以后,胡雪扬(《留守女士》《湮没的青春》《牵牛花》《罪恶》《冰与火》)、王小帅(《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扁担、姑娘》《梦幻田园》)、管虎(《头发乱了》《都市情话》《再见,我们的1948》)、娄烨(《周末情人》《危情少女》)、李骏(《上海往事》)、张元(《妈妈》《北京杂种》《广场》《儿子》《东宫西宫》《回家过年》)、李欣(《我血我情》《谈情说爱》)、路学长(《长大成人》《光天化日》)、阿年(《感光时代》《呼我》)、王全安(《月蚀》)、王瑞(《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冲天飞钓》)、金戈(《青春旷野》《干戈春秋》)、贾樟柯(《小武》《车站》)、金琛(《网络时代的爱情》)、张扬(《爱情麻辣烫》《洗澡》)、施润玖(《美丽新世界》)、李虹(《伴你高飞》)、吴天戈(《女人的天空》)、马卫军、张前(《天字码头》)、宁敬武(《成长》)、张建栋(《童年的风筝》《紧急救助》)、章明(《巫山云雨》)等为代表的“第六代”,自90年代中期开始从冰层浮出海面,以集团冲锋的阵势,冲破“第五代”的遮蔽,成为中国影坛溢满青春活力的生力军。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群被人统称为“第六代”、大多有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导演学位的电影新锐,并不能像法国新浪潮或“第五代”一样构成一个电影运动或风格流派意义上的一个代群。“第六代”也只不过是理论界和媒体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并没有严格的科学界限。就是作为“代”的本身其并不只是一个代群,起码应包含两个群体,即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群体(张元、王小帅、胡雪杨、娄烨、管虎、路学长、李欣等)和70年代出生的群体(金琛、张扬、施润久、宁敬武、李虹、张建栋等)。这两个群体由于生活履历、艺术修养、思想内涵、电影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不同,他们的创作中呈现出的电影形态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冷峻、执拗和飘泊放逐,后者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轻快、亮丽和皈依主流的电影形态。
二、三重挤压下的文化飘泊
进入90年代中期,当“第六代”冲破“第五代”在银幕上构筑的文化屏障浮出海面时,面对的却是一个逐渐萎缩了的国内电影文化市场。有人把“第六代”面临的严峻生长环境表述为:“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压力。”实际上,应该是三重压力,还包括以“第五代”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挤压。在三重挤压下“突围后的这批年轻的电影人投入到这个电影空间里来了。他们在这个空间里游动、移位、选位、错位、退位、迷失,承受着从未有过的艰辛、苦涩和无奈,在成功与失败,欢悦与叹息,没有结局只有无尽的旅途中跋涉,以对电影痴迷的爱,为艺术执着地献身和当今年轻人少有的坚韧与信念,心甘情感地去经历着这一次没有曙光照耀的历史性的文化漂移”。(注:韩小磊.《突围后的文化漂移》.《电影艺术》,1999年,第5期。)
在新时期的电影创作中,作为“代”的电影主题,由于其生活履历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对于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学成于60年代的“第四代”来说,“文革”时期青春时光无端丧失构成了他们情绪抒发以求补偿的主要动机。这种补偿的期望反向移植于迷恋传统人情醇厚、平和安稳的生存状态的电影主题之中。第五代导演是50年代出生的群体,青少年时代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于是受磨难、被剥夺、被遗弃的痛楚经历则铸成了他们完全不同于“第四代”的性格情感体验和电影主题。他们在反思和忧患中,把历史过程中的传统文化现象摆在了分析思考、揭示的位置。从文化思潮和电影形态而言,第五代电影本质上属于现代主义精英化、浓度化模式,带有浓郁的精英文化气息。
在“第六代”的60年代群体中,张元、路学长、王小帅、管虎、娄烨、胡雪扬等人大部分出生于1965年左右。城市生活、自传书写、自我放逐、摇滚一族、晦暗青春,可以概括为60年代群体的电影特征。他们以冷峻、严酷和悲剧人生的态度,执着地在创作中寄寓理想破灭和青春受伤的涵义,以一种反叛和不妥协的姿态,在银幕空间中演绎自我放逐者的孤独悲剧和无可适从的飘泊主题。
《冬春的日子》描写艺术与爱的双重失落而导致主人公精神分裂的惨剧。当超凡脱俗、爱情至上的两人世界因情感飘泊而不可沟通时,就导致了无可挽回的毁灭。
《头发乱了》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女大学生叶童在阔别北京二十多年后重回故乡寻找儿时梦的一段生活经历。影片开头女主人公关于对当下喧嚣驳杂的城市生活的厌倦困惑的一段独白,实际上也反映了“第六代”的管虎们的共同心绪,然而,童年玫瑰色的梦幻记忆不再重显,儿时两个最要好的小伙伴卫东和彭威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和生活信念(一个是片儿警,一个是摇滚歌手),让“寻梦者”的叶童立即作为二者共同的欲望客体,陷入了一种面对两个不同男人(实际上也是两种不同人生信念)的苦痛和尴尬之中,在经历了一番爱恨情仇的胶着折磨之后,叶童在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和列车的喧嚣穿行中挥泪而去。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应该说《头发乱了》其实有它自身的“卖点”:文革浩劫的共同创伤记忆,“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的标准情爱纠葛,国人对当下剧变时代的共同人文困惑……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头发乱了》理应拥有不错的票房收入,然而,作为“第六代”的重要一员,管虎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十分在乎,对“第五代”屏障的跨越、突破的急切期待,直接促使他们迷恋于对一种迥异于前的“新风格”的追求:自传影片取材,情绪化的影片人物,拼盘式的镜像语言、MTV式的镜头快接方式,摄影镜头的激情晃甩,大段大段摇滚音乐演唱,这一切无疑营造出了“第六代”们在出道之初便心向往之的一种浓烈的失落、焦躁和茫然情绪,也导致了票房的惨败。
《周末情人》的浓烈自恋情绪和镜语,处处表现“我们这一群”的精神优越感和自我放逐的偏执。影片中激烈的冲突和恩仇误杀,与其说是主人公的与照,不如说是互为本文关系的需要。颇具叛逆精神的摇滚乐再次成为“第六代”中60年代群体影片的一致商标。“碎片”式生活幻影依然故我地在有限的银幕容量中大量显现,导致了观众接受的障碍。
《长大成人》的执拗真诚和寻觅苦涩,在电影影像构建中伸展。都市化和乡土化难能的交融,70年代的历史气氛通过一个少年人眼光的展露,两代人之间又相隔膜又相依恋的情感,得到了回肠荡气的描写。拒绝英雄又寻觅英雄,失去父亲又为父献身的复合主题,在“弑父行为之后”获得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升华。尽管《长大成人》在北京地区以92万的票房收入使路学长荣膺“第六代”第一个“百万导演”的称号。实际上,摇滚乐、拼盘式镜头语言、寻找主题等所有这些“第六代”60年代群体的指认性标志在《长大成人》中有着鲜明体现。然而,路学长在借助所有这些手段来抒发自我的都市成长体验的同时,并没有让“成长”的“过程”湮没在“成长”的“感受”当中。影片叙事从一场明显带有隐喻意义的大地震(实际也真有其事)开始,以意外捡获的半截小人书作为周青成长归宿的原初指示,应该说,这既合乎当时年少一代的思想真实,也为影片以后周青对“朱赫来”的找寻奠定了基础,少年时代承受着压抑以及“朱赫来”对这种压抑的代为解除更强化了周青对“朱赫来”不舍追寻的心理本源。影片在对周青三年的留法生涯一笔带过之后,回国后的周青的生活展现实际上从形态上已与管虎的《头发乱了》、娄烨的《周末情人》毫无二致。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除了影片表演本身的因素之外,重要的一点应归功于影片前半部分对“小周青”生活和心理状态的真实、细腻的展现,这影片后半部分的叙事给真实、可信的感觉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乎可以这样设想,没有了影片前半部分生活真实感的细腻表现,那么,《长大成人》将又是一部《头发乱了》或《周末情人》。也正因为将“寻找”心路加以了银幕化的具体展现,《长大成人》的“寻找”才获得了生活本身的质感,走出了此前“第六代”60年代群体们一味情绪宣泄的怪圈,以“可信”和“真实”赢得了电影观众的普遍认可,从而被不少圈内人士誉为“第六代导演向第五代导演发起的最有威胁的一次挑战。”
此外,胡雪扬、李骏、张元、李欣、阿年等的作品都体现出了60年代的群体特征,自我放逐、寻找和飘泊的主题。有人把6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的群体形象表述为“边缘人”形态,这种形态正是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飘泊形态的写照。
诚如“第五代”经历60~70年代文革风雨,受电影教育于1978~1982年,而产生宏观反思影片有其必然性一样;生于60年代,经历1985~1989改革大潮洗礼的“第六代”创作群体,其悲剧人生情绪和执拗的个人化电影语言,也是历史结出的必然之果。艺术的苦涩来自人生的苦涩。他们精神飘泊的感受和饱读经书的电影修养,构成了人文精神和电影模式上的精英化理想。在主旋律、第五代、商业化电影的三重包围下,自我放逐和精神飘泊便成为他们共同群体特征和电影形态。
三、文化时尚中的主流皈依
在90年代末期涌现出来的张扬(《爱情麻辣烫》《洗澡》)、施润久(《美丽新世界》)、金琛(《网络时代的爱情》)、李虹(《伴你高飞》)、张建栋(《童年的风筝》《紧急救助》)等等,属于“第六代”中70年代出生的群体。他们的作品体现出相同主题形态,这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对电影市场价值的双重皈依。7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身上既没有第五代的忧患意识和沉重反思,也没有60年代群落的悲怆情怀和执拗飘泊,他们许诺快乐人生,拒绝悲剧化情调和晦暗青春,提倡个人欲望和个人幸福,认同现实人生价值,回归秩序内的奋斗精神和目标理想,肯定市民社会的道德人伦和情爱模式,体现了文化消费的电影娱乐需求,表现出与主流话语、文化时尚和逐步健全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趋同的目标趋向。
“主旋律”影片作为我国电影市场上的主流电影是当今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电影市场的时尚性标志。我们从7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的整体电影形态中都可以找到向主流电影回归和皈依的主题。在张扬的《爱情麻辣烫》与金琛的《网络时代的爱情》中呈现出积极向上的主流电影形态:飞扬生命活力与青春朝气,时代跃动中的新鲜感,快节奏,都市生活及青春思绪与爱情的吟唱,明亮、欢快的镜语表述,自由开放的空间流淌,音符在飘散的生存情态里不安地跳荡。张扬们创制了一幅皈依主流电影、文化时尚的当代速写。这种积极向上的主流电影形态也呈现在旋润久的《美丽新世界》上。此片设定的乡下人进城,在大城市上海历尽艰辛跋涉,终于圆梦如愿,既得到了中头奖的房子,也得到了相知相爱的美女,是典型的快乐人生的如愿以偿,编织出一个美梦成真的“都市童话”。马卫军、张前以《天字码头》参与了“主旋律”电影的操练,尽管这部表现下岗工人的影片拍摄得不尽人意,但创作者认同主流话语的趋向却是十分明确的。
在对主流电影的认同和皈依中,如何在“主旋律”电影中揉进类型片的形式构架或以类型片的形式包容主旋律的主题,以提高“主旋律”影片的娱乐性票房价位是第六代以来年轻的电影人的创新课题。张建栋在获政府儿童片奖的《童年的风筝》一片中,着意战争中的儿童心灵的抒写,将战争的残酷折射在孩子的心灵创伤里,一改以往我国儿童片成人化模式。他的《紧急救助》表现的是一件发生在青岛真实事件,为救助一个大动脉划破出血面临死亡的餐厅女服务员,全社会都调动起来了,从经理到出租汽车司机,到武警战士、足球球迷,纷纷涌进医院急救室献血,女服务员得救了。导演免除了过去此类影片正面宣传、道德说教给观众造成的观赏逆反,力邀了众多明星助阵出演,还以好莱坞营救片的类型模式包装了这个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风尚的主旋律。全片18个人物,以群像表述、凝炼、鲜明地速写了一个个人物形象,又突出铺排医院献血营救与足球场上激烈比赛场面的空间对比。观众爱看,票房效益颇丰,为主旋律输入了艺术的清新露珠。
1999年上海青年导演发表了《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宣言。主张在“主旋律”电影操练中溶入个人风格,宣告了7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群体向主流话语整体皈依的态势。
实际上,在90年代末这种“第六代”向主流话语皈依的情态不仅仅体现在7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也体现在6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王瑞在拍摄了表现现代人无所依附、情感飘泊主题的影片《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后,又以一部表现科技强军的献礼大片《冲天飞豹》展现了自己对主流电影的皈依。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拍片的王小帅,以一部具有新主流电影韵味的《梦幻田园》证明了从“边缘”向“中心”的回归和妥协。管虎的《古城童话》也呈现出由边缘向中心某种修正的形态。路学长导演表现“见义勇为”行为的影片《光天化日》,在一个“主旋律”命题中体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成为“新主流”在量身定做和自由选题的转换中的一个成功个案。
在90年代末期的创作实践中,“第六代”整体电影形态呈现对主流话语皈依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电影市场价值的皈依和回归的态势。
90年代初、中期,6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们缘于初出茅庐的锐气和急于对“第五代”屏障的集体跨越和突破,使他们对电影作品的艺术性追求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他们对市场票房的关注,而导致票房的惨败。90年代的青年电影导演在面临如何克服自身影片在叙事真实性和现实感方面的缺陷的同时,还要正视自身无以驾驭的市场竞争不利环境。在这一点上,“第六代”们似乎除了空自叹息生不逢时,只能对当年的“第五代”导演羡慕不已。80年代中期,也就是今天的张艺谋、陈凯歌们初出茅庐的时候,国内电影市场尚未形成,国家对影片从生产到上映诸环节的大包大揽,使当时的“第五代”青年导演们根本无需承受来自市场的沉重压力,而其时的中国电影,正掀起一股从“影戏”电影美学往“影像”美学转变的理论高潮,有着全新电影创作观念的“第五代”导演,凭藉他们对电影影像造型的刻意经营,加上在国外电影评奖专家看来颇为新鲜的中国“民俗”化内容在他们影片中的屡屡展现,即使他们的影片迎合了国内电影思潮所需,也使他们的电影作品在国外电影节上深受青睐并频频获奖;因此,即使他们当时的影片在国内一时遭受观众冷遇,也可以假借影片在国外电影节的获奖而再次对国内电影市场“卷土重来”。几年之内,张艺谋、陈凯歌们便被理论界冠以“代”的称谓,并在事实上成为一个规模蔚然的导演群落,实属“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
实际上,缺乏当年“第五代”良好创作环境的青年导演们所谓对“第五代”的“突围”,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无必要。市场经济的强大离散力,早在90年代前期便将他们作为一个创作群落冲击得七零八落。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7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们一开始就表现出电影票房价值积极认同和皈依的姿态,他们力求戴着市场经济的镣铐尽量把艺术之舞跳得更漂亮更潇洒一些。
一位评论家把6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的早期创作表述为“创作性”电影,把7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表述为“操作性”电影。70年代出生的导演们,大都遵循了以制片人为中心的创作服从操作的商业电影机制。在他们建构的电影空间中,充盈着完整的故事、圆满结局、常规镜语、流畅剪接和亮丽影像,呈现出一个青春跃动的“美丽新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70年代出生的“第六代”电影创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低成本的策略。他们拍摄的影片大多在120万~300万人民币之间。投资仅120万的《网络时代的爱情》成了低成本运作成功的典范。《爱情麻辣烫》在国内一炮打红,单北京一地就创造了超过300万票房佳绩,跻身1998年国产影片票房排行榜前五的骄人位置。这部张扬的处女作创意新颖,故事贴近生活,比较真实地诉说了都市几代人爱情生活的麻辣烫,视角新巧,故事情节简约,叙述节奏明快,情调各异,有阅读本文的视听快感,又汇集了多品位的商业卖点;各个小故事都有明星出阵,组构成一部亲切、生动、感人、明亮的影片,受观众的欢迎在情理之中。当然,《爱》片的票房佳绩绝非在某种电影结构形式上便找到根本的解答,实际上,细腻、真实、浓郁的都市爱情生活刻划是该片最值得注意的商业品质。
真实与贴近百姓,实际已成为国产商业电影占领市场所应具备的一个起码的品质,这在比《爱》片后上映的两部青年电影《网络时代的爱情》和《美丽新世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反证。如果说,60年代出生的群体在最初的电影实践中票房上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缘于对“第五代”屏蔽的急切超越和突破,直接导致了他们市场意识的相对淡漠;那么,更年轻的“第六代”们拍摄《美丽新世界》和《网络时代的爱情》等片市场票房的不尽人意则完全可以归咎于影片主创人员特别是导演对影片叙事把握的欠妥。尽管金琛、施润久们不乏强烈的市场意识,但在影片创作的实际操作中,他们并没有真正做到“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而是凭借自己对影片“卖点”的主观臆想,作出对影片叙事的主观处理,从叙事内容到演员表演被观众认为“虚假”“做作”,票房失败,自属情理之中。
另一部在市场动作的成功范例是《洗澡》,这部融合本土景观和都市温情的艺术商业片中,导演张扬用一个家庭的故事为即将消逝的洗澡文化做了一个视像备忘录,为传统文化唱出一首精致的挽歌,在满足了本国观众观影快感的同时满足了西方看客的好奇和东方想象。
事实上,在90年代的后期,对市场价值的认同和皈依业已成为“第六代”的整体趋向。张元的《回家过年》、王小帅的《梦幻田园》、路学长的《光天化日》等就这种认同和皈依的明示。在跨入新世纪的今天,“第六代”群落可以说是联接纯消费性和纯文化性电影的中间一环,又是电影工业从昨天向明天转型的中间一环。链条的环环相扣显示出空间的横向和时间的纵向过度的有机的联系;体现着中国电影向全面市场化和新世纪转型的现实的步伐。
四、结语
黄式宪先生指出:“球已经踢到第六代脚下,但他们一直没有踢出高潮。”
的确,相对于“第五代”的电影创作,“第六代”的电影实践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他们共同的弱点在于文学价值方面普遍较弱,在戏剧矛盾的组织、结构、人物塑造方面尚欠功力,主题的开掘和深化也还显得很不到位。而这些显然都和导演的文化素养以及生活积累有关。此外,60年代出生的青年导演在由“边缘”向“中心”的皈依过程中,似乎身份的改变,也一起改掉了他们身上的锐气和深度,使人有新作品不如老作品之叹。尽管如此,从“第六代”身上毕竟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未来,他们肩负着复兴中国民族电影的历史重任。张艺谋曾经断言“第六代中必出大师”。我们满怀热忱地期待着、聆听着在复兴中国电影的新世纪中,新一代电影大师的叩门声。
[收稿日期]2000-2-26
标签:第六代导演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美丽新世界论文; 冬春的日子论文; 爱情麻辣烫论文; 童年的风筝论文; 周末情人论文; 梦幻田园论文; 紧急救助论文; 光天化日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伦理电影论文; 科幻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