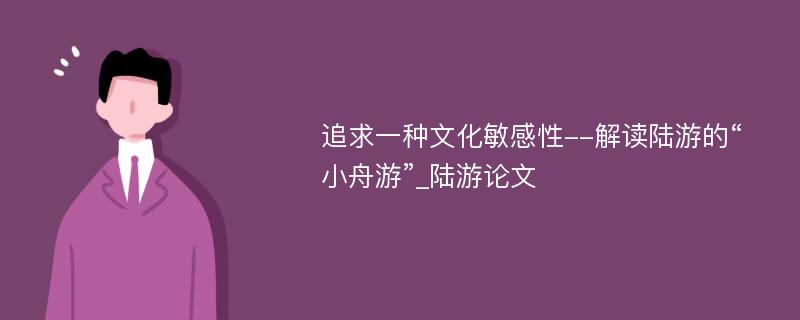
追寻一种文化敏感——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舍论文,小舟论文,陆游论文,敏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史上的“蔡中郎现象”
被梁启超誉为“亘古男儿一放翁”的宋代伟大诗人陆游,曾于公元1195年写下一组四首七绝小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中,第四首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一年诗人已经71岁。耄耋老人的陆游乘船游玩临近的村子,上岸后缓缓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一个名为赵家庄的村落,已是夕阳西下夜色朦胧时刻,村头高大古老的柳树下盲艺人正登台说书,锣鼓声声吸引了全村人观看。盲艺人说唱的是赵贞女蔡中郎的故事。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的文人蔡邕,字伯喈,官至中郎,故又称蔡中郎。
诚如郑振铎所言,此首诗说明“当时不仅有《赵贞女》的戏文,且有《蔡中郎》的盲词了”①,蔡伯喈故事在南宋已成为民间讲唱文学的流行题材;而且,蔡伯喈已被描述成反面人物,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一节著录《赵贞女蔡二郎》时所下的断语对此说得很明确:“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弃亲背妇”就是其“反动罪行”,“暴雷震死”就是其“反动下场”。根据传世元曲、各种地方戏和民间曲艺等资料,早期民间流传的蔡、赵故事的具体梗概大致是:蔡伯喈上京赶考,一去不回,抛开父母不养,遗弃妻子不顾,攀龙附凤,赘入豪门,尽享其荣华富贵生活。妻子赵五娘孝顺公婆,艰苦持家,公婆去世,以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为让公婆得到香火祭祀,又身背公婆遗像,卖唱寻夫,找到京城。但蔡伯喈却拒绝相认,并因担心赵五娘的出现会影响其前程,便将她害死。上天怒其不仁不孝、不忠不义,用暴雷将蔡伯喈震死。
这首诗歌是文学史上关于早期南戏题材——赵贞女、蔡伯喈故事,以民间艺人说唱形式,在乡村演出的最早记载。《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徐渭此语不知何所为据,但宋光宗绍熙年间即公元1190-1194年,与陆游此诗的写作时间公元1195年确乎极为吻合。这就意味着,当南戏刚刚在江南舞台兴起之时,陆游就将其“打头”、“招牌”故事《赵贞女》以其他形式流传的题材记载下来了。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院本名目《蔡伯喈》的时间自然晚于陆游,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中“刘后村书所见”条说刘克庄绝句有“黄童白叟往来忙,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始作俑者。②——纵使记载不误,因刘克庄生活在南宋末,他的诗也不过是抄袭陆游、瞒天过海的“马后炮”了。
宋金之际,北方戏剧产生的同时,南方戏文从温州一带的民间歌舞、村坊小戏中成长起来。“在宋元南戏中,描写婚变,批判男子负心的故事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是早期南戏中最突出的主题。”③今天能确定为宋戏文的有《赵贞女》、《王魁》、《张协状元》、《王焕》、《乐昌分镜》五种剧目(全本南戏只有《张协状元》),前三种就是这类题材的作品。《赵贞女》仅存名目,戏文内容大致即是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叙的蔡中郎、赵贞女故事。《王魁》叙王魁科举下第后遇妓女敫桂英,得到女方的爱情和金钱的资助,并于第二次赴考前双双于海神庙发下誓愿,要白头偕老。但王魁中状元以后,违背誓言抛弃女方,后者自刎身亡并索去王魁魂魄。《张协状元》写张协进京赶考路遇强盗,得到贫女的救助并以身相许,但张协状元及第后不仅不认妻子还企图剑劈对方,还把对方推下悬崖,但贫女得贵人相救认作义女,在贵人的安排下夫妻重圆。据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和张大复《九宫十三摄南曲谱》统计,宋元南戏作品如《三负心陈叔文》、《崔君瑞江天暮雪》、《李勉负心》、《李亚仙》、《张琼莲》、《李婉复落娼》、《吴舜英》等,也是这类内容。如《三负心陈叔文》里发迹的陈叔文把发妻兰英推落江中淹死,后被妻子的鬼魂活捉;《崔君瑞江天暮雪》里的崔君瑞先是诬陷发妻是逃奴,然后把她发配到远方;《张琼莲》里的崔甸士所作所为完全与崔君瑞相同;等等。
宋元明小说、戏剧发迹变泰三大题材类型(文士发迹、武人发迹和工商业者发迹)中,最为大众艺术家重视的是文士发迹题材,文士发迹题材类型中最重要的、拥有作品最多的模式是“王魁模式”④。该模式故事内容具有三个情节段落:(1)有真才实学的男主人翁,穷愁潦倒之时得到下层社会女子的鼎力相助(爱情、金钱),成立家庭,学业完成。(2)通过科举(多中状元),获得富贵,遂忘恩负义(或抛弃甚至谋害女方)。(3)受到惩罚(或以命抵偿;或因权贵介入,受些活罪后与发妻团圆)。早期南戏作品通过蔡中郎、王魁们的负心形象,暴露出人性残酷的一面,社会地位的变更是人的真实面目的试金石,人与人之间残酷的社会关系也因此暴露无遗。
二 “蔡中郎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
陆游诗中涉及的婚变题材在南宋民间文艺形式(南戏与说唱)中的大量存在,说明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原因多种多样。首先与男尊女卑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充分孕育并巩固了以男性主义为中心的男权意识。女子没有独立人格,只是一种物类的东西,是男人的一种附属品。礼教要求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的生存权利、情感需要、尊重需求等能否得到满足,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完全取决于身边男性的一己好恶。这种文化心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传统女性生活一如刘半农在《南归杂话》中所描绘的:“因为一失欢于男子,就要饿死,所以不得不讲‘四德’,不得不‘贤惠’,不得不做‘良母贤妻’。其实‘无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谓‘三从’,就是前后换了三个豢主;所谓‘四德’、‘贤惠’、‘良母贤妻’,不过是‘长期卖淫’的优等考语。”⑤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女子,其生存处境在几千年里都是非常不妙的,在宋代社会亦应如此。
当然,“蔡中郎现象”司空见惯的最主要原因和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科举制继承唐制,但发展得更为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唐制的一些弊端,也还没有发生明清时代因“年久生变”而窳败的种种情况。可以说,宋朝是古代社会科举制度最成熟、最有活力的时期。首先,鉴于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通病,确立“别头试”、“锁院”、“殿试”等制度,废除“公荐”(通榜)制,加强了对权贵子弟的监督。尤其是“弥封(糊名)”、“誊录”制度的严格实施,基本上排除了宋代以前长期存在的权贵对科举取士的垄断和相应的旁门左道(唐代行卷、温卷、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名次等风盛行)。这一系列的法规和措施为科场上的平等竞争廓清了道路。其次,考生录取名额大幅度增加,考试正常率几达百分之百。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年取士名额的五倍、元代的三十倍、明代的四倍、清代的三点四倍。⑥其中,南宋的录取率更高于北宋,因为每年的平均录取数虽然差别不大,但南宋统治的范围逼仄得多,因而参加科举的总人数也比北宋少得多。重要的是,宋代在正规录取通过科举考试的考生之外,还对那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能录取的人予以特别照顾。如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取进士409人,诸科430人,后又取“特奏名”900余人,总计竟高达约1800人。⑦以考试正常率而言,两宋均从来没有发生过停止科举的事情,即使在金兵围困、国难当头的徽、钦二帝时,依然“相沿不替”。⑧再次,较之既往朝代,宋代录取的考生均地位更高、待遇更优。宋代皇帝亲自鼓励读书人发奋攻读,如宋真宗曾写《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事实也确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宋代确立的殿试制度、皇帝赐宴制与恩科等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科举的地位与及第者的身价。不仅如此,宋代还简化、减少考试的类别和次数,宋代只要省试通过即可做官,而且官级也有很大提高。“名卿臣宦皆系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宋史·选举志一》)。据郭齐家的统计,在宋133名宰相中,由科举出身的文士达123名之多,占宰相总数的92.4%,大大高于唐代的比例,而唐代有宰相368人,进士出身为143人,占宰相总数的39%。这一切使得门楣、私交、黑金不再是科举考试的决定因素,仅靠自己文章的水平即能展开公平竞争,就能从寒门出身摇身一变而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戏曲舞台和说唱艺术中蔡伯喈、王魁、张协等等频频中状元的背后,是现实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寒门人物正在向社会权力的上层跃升,是社会权力的上层前所未有地向广大寒门人物敞开了大门。
社会历史脉动的另一方面必然是,豪门世家的权势难以为继,几代连续高官显宦的现象日益罕见。在唐代,一些大族世家父子相继做宰相,甚至几代做宰相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与此有很大不同。一切靠自己的头脑,即使父亲享有高官厚禄,权倾天下,如果儿子科场困顿,完全可能潦倒终生,如社会名流、富贵宰相晏殊之子、著名词人晏几道就是一例。因此,既有权贵向科场新俊招手结盟,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科场新俊为了加速其“崛起”,把社会上层的可能权力尽快兑现为现实权力,向既有权贵投怀送抱,也就不可避免。互相利用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之一就是婚姻。贫寒之士一旦“发迹变泰”,又成为权门的东床快婿,则其在官场的步步升迁就可指日而待;而在朝显宦不仅热衷招纳东床快婿,甚至还颇乐意在大女儿去世之后,以小女儿补缺,形成“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现象。于是“富贵易妻”的悲剧大量产生,北宋如此,偏安于江南半壁河山的南宋王朝,因其科举录取率更高亦即“鲤鱼跃龙门”的可能性更大,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追溯当时南方各种民间说唱文艺和从乡村小戏中孕育出的南戏题材,“蔡中郎现象”甚为普遍,“负心婚变母题在文学中的表现,在宋代出现了空前的盛况”,“宋代是负心婚变悲剧的成立时期”⑨,其原因不能不首先在此。
三 作为历史进步代价的“蔡中郎现象”
陆诗及同时期南宋说唱艺术与南戏涉及了穷书生变泰即变心的文化史现象,诚然“反映了封建文人一旦飞黄腾达就要弃妻再娶的现实,从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⑩。如前所述,这是与科举制度十分发达紧密相关的宋代社会问题之一。富贵易妻在宋代社会如此轻易发生,这使我们想到,它是否意味着中国历史在宋代的一种倒退?
当我们把鄙夷的目光从“蔡中郎现象”移开,站在一个更为深远的角度,就会看到上承先秦汉唐、下启元明清近代的宋代,确乎如许多通哲名流所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1)此可谓承前而登峰。近代著名学者严复又言:“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2)此可谓启后之全面。邓广铭先生复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13)此可谓睥睨世界而称雄。国际学术界,日本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并引起欧美汉学界广泛共鸣的一个看法——来自20世纪初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的考察——也以为,宋代乃“中国由中古向近世的一大转折”,是“中国近世史之开端”。(14)随着研究的深入,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地位目前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指出的:
第一,宋代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相当完善周密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各级重要机构的权利大门都通过这一制度向知识分子敞开,这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宋人曾自豪地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襄《蔡忠惠集》卷十八)北宋时期我国的各类人才如群星灿烂,与苏轼约略同时的文化巨匠就有一大批,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韩琦、苏洵、苏轼、苏辙、文彦博、富弼、晏殊、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程颐、程颢、张载、蔡襄、周敦颐、邵雍、沈括等,他们都是大师一级的人物,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偏安一隅的南宋,人才之盛也使其他朝代的统治者汗颜,如朱熹、陆九渊、李清照、陈亮、叶适、陆游、辛弃疾、杨万里、李纲、文天祥等。诚如明人徐有贞所言:“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则过之。”(四库全书本《范文正集补编》卷四《重修文正书院记》)科举制度的完善带来人才的兴盛,人才的兴盛必然带来学术文化事业的兴盛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二,在社会科学领域,宋人创造了中国思想学术文化中最精微的哲学理论体系——理学,又萌生了最富有创造性和解放精神的理学别流——心学。中唐时期的新儒学,到宋初得到“理学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继承与发扬,从而为“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奠定基础。理学真正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集大成者为朱熹。几代学者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他们融合儒、释、道思想,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发展儒家“内圣外王”的价值观,提倡理性主义与道德自律精神。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哲学——经学,从感悟经学和章句经学形态,向理论经学形态的完成。南宋陆九渊等人又从理学中衍化出一个“宇宙即是吾心”的心学流派,它在明代经陈献章继承,到王守仁发扬光大,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权威的解体运动,为传统中国社会由近世向近代的演变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受到民族矛盾的冲击,这一可能极可能在17世纪变成现实)。即使是就比较纯粹的理学而言,它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也是“儒家精神的解放”(15),可视为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逻辑先导。总之,可以说,理学的产生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宋代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在当时和后世”、“在国内”,甚至“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以理学为核心的宋代学术文化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第三,在自然科学领域,宋代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人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他进一步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总论》)与偏重人文主义的唐代不同,10到13世纪的两宋时期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取得的相应成就令人惊叹。中国饮誉全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被马克思誉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完成于宋代。不仅如此,位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宋代科学技术,其成就遍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学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以及相关的技术应用方面,如机械制作、建筑桥梁、陶瓷制作、航海造船、金属冶炼、纺织技术等。宋代在几乎所有中国传统科技的各个领域都“留下新的记录”(17)。宋代涌现了大量精通多种学科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如博学多才的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宰相苏颂精通“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宋史·苏颂传》);文坛领袖欧阳修努力探讨天文、地理等很多自然现象,著有专著《易童子问》;理学家朱熹对自然科学方面的众多问题也发表有很多高明的见解。
宋代的人才之盛、社会科学发达暨理学家之多、科学技术发达暨科学家之多,固然是宋代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表现,但归根到底,都牵涉到宋代社会阶层的一个重大变动,即下层庶民通过接受知识、教育,跨过科举门槛向上层跃升,向权力上层跃升的同时伴随了向知识文化上层的跃升。釜底抽薪地惩罚蔡中郎们忘恩负义的办法是取消科举制度,但那样一来,宋代社会阶层由下向上之重大变动必将不复存在,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的诸种品质亦必将不复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赵贞女们成了两宋时期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代价。
四 早期南戏与民间说唱的“审判”功能
但忘恩负义毕竟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到为成功再婚而丧心病狂时,毕竟已经是犯罪。
《宋刑统》卷十四《和娶人妻》说:“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宋代的法律似乎也在禁止男子的负义再娶行为,保护一夫一妻制,尽管它保护的是丈夫和嫡妻的一夫一妻制。——不论是从中国传统的习俗、法律,还是从《宋刑统》同时记载“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等来看,妾媵是不被看做丈夫的正式妻子,不享有相应的法律保护的。个别士大夫也曾在局部范围实际提倡过夫妇恩爱的和谐关系,如北宋陈襄做仙居知县时的敦俗劝谕文,有一条就是,“夫妇有恩:贫穷相守为恩,若弃妻不养、夫丧改嫁,皆是无恩也”(四库全书本《古灵集》卷十九《劝谕文》)。但是,在一个弃妻(士大夫阶层多称为“出妻”,一般民间称为“休妻”)行为被过分宽容,弃妻理论被公开张扬,轻率弃妻的法律漏洞又同时存在的社会,指望国家权力机构来惩处发生在科场新俊身上的“欺妄而娶”现象,无疑只能是一个天真的幻想。
司马光《传家集》卷二十六《言陈烈札子》(嘉祐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云)云:“臣等伏见朝廷向以福州处士陈烈好学笃行,动遵礼法,……故举之闾阎之中,以为学官,烈辞让未至。今闻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据福州勘到,烈为妻林氏疾病瘦丑,遣归其家,十年不视,陶因言烈贪污险诈,行无纤完,乞尽追夺前后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识烈,不知其人果为如何;惟见国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检,故举烈等以奖励风俗。若烈平生操守出于诚实,虽有底滞迂阔之行,不能合于中道,犹为守节之士,亦当保而全之,岂可毁坏挫辱,疾之如仇?……臣等欲望陛下……选差公正官吏通儒术识大体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于夫妻不相安谐,则使之离绝而已,湔洗其过,庶几复伸眉于后,又使四方节行之士,不忧横辱,得以安恬于闾里。”如此“识大体”的文字,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天大的讽刺。一个将憔悴变丑的病妻送回娘家十年不管的人,居然就是“动遵礼法”、“出于诚实”的“守节之士”,就是“举以奖励风俗”的国家稀有人才;即使这种行为真有什么不对,也是无伤大雅的“底滞迂阔之行”,应该“保而全之”、使其“伸眉于后”、“安恬于闾里”;而“湔洗其过”的主要办法,更居然是“使之离绝”,也就是让两人办理离婚手续,让他彻底地抛弃她!如此荒唐的见解和建议,却被一代名臣、时任天章阁待制的司马光一本正经地写进了呈给皇帝的奏札,又一本正经地通过他的“传家”文集在社会中流传开来。再看《二程遗书》卷十八载:
问:“妻可出乎?”曰:“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当出也。只为今人将此作一件大事,隐忍不敢发,或有隐恶,为其阴持之,以至纵恣,养成不善,岂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才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问:“古人出妻,有以对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无甚恶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之绝交不出恶声,君子不忍以大恶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见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亲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处,只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尔。”或曰:“彼以此细故见逐,安能无辞?兼他人不知是与不是,则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
这是稍后于司马光的大儒程颐在弃妻问题上“纠正”“世俗”的看法,堪称又一个重要指标。对女性要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颐,纵然不是在故意怂恿寻衅弃妻之不道德行为,为之撑腰壮胆,但从他的嘴里也出来如此理直气壮的弃妻论调,进一步说明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对弃妻行为的过度包容之甚。诚如研究中国婚姻史的学者所言:“古代男子单方面出妻,妇女无端被弃,无权提出离婚,本已极不合理,到程氏兄弟这里,又极力维护男子单方的出妻,更为无理,更不平等!”(18)无论如何,以司马光、“子程子”在北宋末以后到南宋对士大夫阶层思想和生活的指导性影响,这些论调的传播又足以为弃妻行为之更加偏离道德轨道提供借口和庇护,从而纵容它更加轻率、更加频繁地发生。何况法律的漏洞又同时存在,而且完全是和司马光的观点一鼻孔出气。《宋刑统》卷十四《和娶人妻》载:“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宋代,休妻的理由和不能休妻的规定在人们的思想上都不十分明确”(19),应该说都归因于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的这些著名学者的论调和法律本身的抵牾。总之,结果便造成了《宋史》中相当多丈夫动辄出妻再娶,而儿子毫无怨言地同等善待出母和继母的记载。宋末于石《紫岩诗选》卷一《母子别》云:“客游严陵道,中路哭者谁?哀哀母子别,云是夫弃妻。……儿啼哭恋母,母闻转悲凄。欲语别离苦,孩提尔何知?徒能抚汝顶,相顾空泪垂。”那些有子被弃者,尚可因为孩子的原因引起某些文人士大夫的同情和哀婉,那些无子被弃者,又有谁为之同样一洒清泪呢?在法律和权威舆论都在有意无意地鼓励弃妻之举,难以对可能的“欺妄而娶”者实施真正的挞伐之时,又有谁站出来为那些受害者主持公道?
“在人间法律领域中止的地方,剧院的裁判权就开始了。”(20)一点不错。宋元之交的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就记载,温州乐清官府审理一个奸僧结托权要,劫色害命之案,罪状昭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斃之于狱。越五日而赦至”。这是元初发生在南戏故里温州的真实事件,是关于“剧院裁判权”发挥作用的一个极为生动的例证,也提示了南戏题材和现实的紧密关系。不仅如此,联系元末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关于南戏起源的最早见解——与《南词叙录》“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的记载,应该可以认定,南戏问世的初始原因或许就是为了建立惩罚弃妻再娶恶行的裁判所。——即使不是全部原因,也应该是主要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明代研究戏曲最透辟的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五中不仅认同叶子奇的论断,还笑称“蔡中郎”历史原型的大不幸之一,是“千年后横遭风流案污蔑,日为里妇唾讥”。“里妇唾讥”,无疑是早期南戏和民间说唱社会审判效应的进一步扩散。
五 结语:陆游的文化敏感
陆游出身于诗书礼义之家,从小博览群书,自豪于“五世业儒书有种”(《闲游》)的身世;对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深度浸淫,使他多种题材的诗作均蒙上了明显的文化色彩,即便山水诗也是如此。可以比较言之:柳宗元对自然山水喜欢予以静态的观照和客观的再现,苏轼喜欢把强烈的主观色彩灌注在山水景物之中,我才舞蹈,物亦飘飘;陆游则不同,他总是怀着文化感悟和文化体察的心态来看待自然山水,在古今贯通的视野中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融合为一。例如,论者就曾提到他的入蜀记游诗,过当涂而吊李白,宿江陵而怀屈原,停巴东而思寇准,“将历史的沉思与现实的评议相结合”,“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文化认同心理”(21)。我们认为,如果《黄州》、《哀郢》、《公安》等入蜀诗中的文化感悟意味确可用“文化认同”一词来概括的话,那么,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第四首则更多地反映了他的文化体察和文化敏感心态。诗中仅有一句写景,“斜阳古柳赵家庄”,一半是为了弥补组诗前面三绝的写景不足,一半是为即将记录的故事提供一个背景;主体部分记录了一个有关“蔡中郎”之“非”的模糊故事,以及这个故事正是盲艺人嘴里喧闹上演的清晰场景:“负鼓”作场,一定增加了故事情节的惊天动地;“满村”听说,想必听众差不多是万人空巷。这其间意味着什么,或许陆游还来不及仔细分辨;但作为发生在当代乡里社会、底层民众中的一种生活现象也是文化现象,陆游肯定已经因其而有所触动、有所感觉。和许多或许曾经同样触动但很快淡忘者不同,陆游忠实于自己的文化敏感并用诗行将之固定了下来。文学史上这才有了探讨南戏婚变题材在乡村传播以及南戏本身起源的最早最及时记载,一项重大历史脉动也在方寸之间被记录下来。
注释:
①徐朔方、孙秋克:《南戏与传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②遍查各种文献,说刘克庄也作有“死后是非谁管得”者,最早就是明初《归田诗话》。此一误记后被嘉靖间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下、徐渭《南词叙录》、万历间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一和清代姚之骃《元明事类抄》、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五等所承袭。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部》“蔡中郎”条已明言,“陆游(诗)有云刘后村作者,误”;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二亦有同样判断。
③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
④潘承玉:《论宋元明小说、戏曲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⑤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⑥张希清:《论宋代的科举取士之多及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85年第5期。
⑦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下文郭氏统计见第114页。
⑧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⑨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4页。
⑩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286页。
(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12)严复:《致熊纯如信》,《学衡》第13期(1923年1月出版)。
(13)邓广铭:《国际宋史研讨会开幕词》,收入《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夏应元:《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期。
(15)庞朴、马勇:《中国儒学》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42—243页。
(16)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17)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3、908页。
(18)汪玢玲:《中国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19)[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20)马也:《戏剧人类学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21)章尚正:《从文化心理观照陆游山水诗》,《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2年第2期。
标签:陆游论文; 宋朝论文; 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宋代建筑论文; 南宋论文; 南词叙录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理学论文; 张协状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