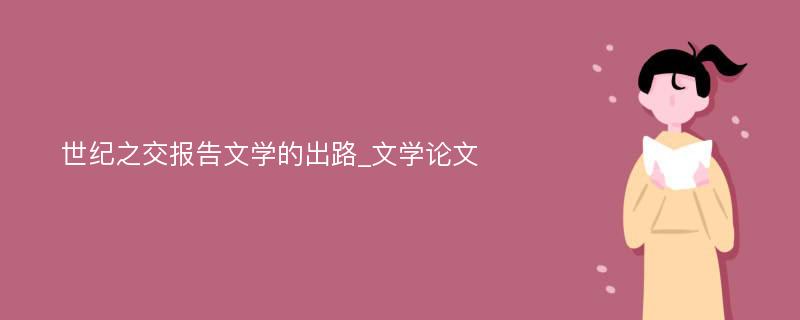
报告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报告文学论文,出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纵观历史,报告文学曾经有过灿烂迷人的时光。然而,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开始走入低谷。导致它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的垢病:虚构的侵入、思想的肤浅、作者独立人格在金钱面前的流失和削弱。因此,在世纪之交,报告文学必须迅速寻找到它的出路。而重振雄风的关键之一是紧紧拥抱生活。坚持真实则是它不可动摇的原则。再之,报告文学切不可轻描淡写了文学性,新闻因素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这一文体的主导特质。
关键词 报告文学 垢病 虚构 独立人格 真实 新闻
WAY OUT OF REPORTAG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IES
Wang Yi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y,there was a splendid and fascinating time for the reportage.However,the reportage has entered a declining period since the 1990s.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for its dilemma lies in its own diseases:intrusion of invention,shallowness in thought and loss & weakness of theauthor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wing to money.Therefore,the reportage must find its way out quickly at the turn of thecenturies.One of the keys to regain its splendour and fascination is to embracc life tightly.Then,to stick to the truthshould still be its unshakable principle.It should be notedthat literariness cannot be treated lightly and news factoris not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e dominating qualityof the genre.
Key Words reportage discase invention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ruth news
也许,是编辑这个特殊的职业,使我接触到大量的报告文学——成形的及不成形的,见识到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家——真正的及滥竽充数的,于是挡不住地想说一些也许得罪人的话。我觉得,在当代中国文学即将结束近年来长期低迷徘徊状态,走向世界的又一次紧要关口,认真探讨和清理报告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寻找它的出路和定位,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虽然这个话题过于冷寂。
报告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外延相当宽泛的概念,至今关于它的归属依然被许多理论家们争论不休。不少小说家毫不留情地将它驱逐出了文学的殿堂,认为谁若选择了报告文学就意味着放弃了文学。不少理论家则认为,小说的主要功能是审美,报告文学的主要功能是认知,如此说来,它应该属于新闻。然而在新闻这一大阵地里,已公然宣布它是一大变异,以至有些大学的新闻教科书里干脆将它开除出去……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它的归属究竟是什么,归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存在,而且是强有力地存在,存在的状况往往是我们剖析它的入门,使我们能对它的未来一目了然。
一、回顾历史,报告文学曾经何等辉煌
在文学殿堂里,诗是神圣的,小说是至高无上的,影视是宠儿,散文正在走红,而报告文学,则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冷落着,甚至被人轻视着。但是,这仅指它的现状,如果我们作一次历史的俯瞰,不难发现,在漫长、艰难而又壮丽的文学跑道上,报告文学曾经有过灿烂迷人的时光。
它的兴起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当时的记者们认为小说和戏剧已难以表达急剧发展的世界,他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报导形式——比新闻更形象生动,比小说更迅速及时。终于,他们从散文中得到了启示,于是,一种介乎新闻和一般文学作品之间的新兴的文体诞生了。法国的记者们将它命名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流入中国后也一直受到大众欢迎,一篇《包身工》,不仅成了夏衍同时也成了“五四”期间报告文学的代表作,解放后被选入中学课本,从我这一代一直读到我儿子这一代。解放初期,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走红全国,以至志愿军成了无数少女心仪的伴侣。60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不断被大学教师举为写作范木……报告文学的再度辉煌是在80年代,那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令当代作家最感到得意的时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全方位的复苏和跃动,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创作思想极大解放。一大批佳作迭出。小说和报告文学日月并辉。而且,随着小说家们越来越强化它的审美功能、人性的归返、生命价值的探讨及许多文体的实验而陷入困境,报告文学再次趁势掀起高潮……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时代呵!《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阴阳大裂变》、《西部在移民》、《唐山大地震》、《志愿军战俘纪事》、《5.19长镜头》……报告文学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代表着民族的良知,深沉地反思历史,审视现在,构想未来……这些作品有的尚嫌粗糙,但在这里,一切都被原谅了,因为它是那样的贴近你,似乎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是你在呐喊,是你在发问,是你在战斗……它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认知欲,而且同歌同悲同喜同怒,获得了渲泻情感、平衡心理的快感……
应该说,这时的报告文学家替代小说家成了读者的宠儿。小说家自我封闭进了象牙塔,而报告文学家们门庭若市——告状的、申冤的、求助的……全寻上门来了。报告文学直接参与社会,反过来,社会又慷慨地为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广阔的前景。
这个时期是值得报告文学家们骄傲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报告文学从来没有这样引起过社会的震动,报告文学家们也从未如此尽得风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辉煌并不久长,历史的车轮进入90年代,报告文学开始走入了低迷与徘徊的低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繁华胜景终于成了昨日黄花,报告文学不可避免地也如小说般呈现出“门前冷落车马稀”的不祥兆头……
二、当前报告文学的垢病
或许有人会将报告文学的这种低落推托为“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或者“影视传媒的冲击”。不得不承认,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学生存环境的变化,确是影响其繁荣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是其最主要的因素,导致它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报告文学本身的垢病。
当前报告文学的一大垢病是虚构的侵入——它使报告文学不再具有“报告”性。
报告文学具有三大特性,一是报告性,二是文学性,三是政论性。其中报告性则是区别它与其他文体的最主要特性。因此,报告文学必须绝对真实。严格地忠于历史,忠于事实,这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原则。
然而,这个原则有意无意地被人抛弃了。说来遗憾,最先抛弃这一原则的竟是当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家徐迟。徐迟是我所敬仰的前辈,他写了许多好作品。然而,据青岛作家纪宇撰文披露,徐迟的报告文学代表作《祁连山下》原标为小说,《人民文学》在发表时因考虑到他是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改标为“报告文学”。据说当时徐迟颇为不安,曾因此找到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模特儿向他说明。该主人公却一口认同了。这一说,徐迟就心安理得了。若干年后,他顺理成章将此文收进了《哥德巴赫猜想》这部报告文学集。一篇小说就这样成了报告文学。众所周知,小说的基本特征是虚构,而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真实,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两者竟可以一字不改地统一在一篇文章里。
虚构在报告文学中的侵入已越演越烈,我就曾看到颇有影响的文章《天网》滑稽地在不同的场合被标为两种不同文体,以至一直让人纳闷,这《天网》究竟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
以上两例,究其原因,或许并非都出自作者本意。有些杂志为了追求发行量,往往写了提纲让作者去“按图索骥”,这种找来的“非驴非马”的东西,一概被堂而皇之标上了“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但不得不看到,某些作家在写报告文学时确有哗众取宠之心。翻开杂志,常常可以看到不少标有“A小姐”“B先生”“D 城”等字样的纪实文学,其模糊性从侧面说明了它本身的不确定性。它让你查无实地。这种做法实际上将小说和报告文学两种极不相同的文体捆绑到了同一张婚床上——它诞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孩子,有人称为“纪实小说”,但该文体很快短命夭折,因为它引出了许多法律纠纷——不少人纷纷前来对号入座,这个时候你认它纪实还是认它小说?
虚构的侵入带来的恶果是失却了读者的信任度,因而读者们带着被愚弄的恼怒纷纷离报告文学而去……
当前报告文学的第二大垢病是思想的肤浅。
报告文学自问世以来,就以它的思想的深刻而先声夺人。然而,目前的不少作品却显得苍白无力,精神软化,远远达不到应有的穿透生活与拷问灵魂的力度和深度。肤浅,首先是由人们对题材的掠夺性开采带来的恶果。可以这么说,当今社会,已很难找到未被作家涉猎过的问题了。近10来年,报告文学家们几乎是用近似疯狂的速度开掘各种题材,作家们的笔触深入到了构成社会的细胞。这一煌煌战果带来的负面是后人很难再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了。报告文学这种特殊文体相对来说存在着“一次性”表现的问题,打个比方说,徐迟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后人若无大的突破,就没有必要再去写它。因为读者会产生阅读的“疲劳感”。因此报告文学家们必须将你的叙述观点一次性写透,处理完毕。然而,急功近利的思想却让不少报告文学家们象掘金矿的农民一样仓促上阵,或狂挖滥掘,破坏矿脉;或浅尝辄止,露出许多可以想见的空白。我们常常能见到极精采的题材被平庸的写手给写坏了,这真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题材的大小对报告文学的价值毕竟是极有影响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一篇写风情女子命运的作品,是无法与写香港回归的作品放在同一架天平上的。而香港回归如此重大的题材,150 多年才发生一次……
造成肤浅的另一个原因是题材的随意性。
与80年代相比,当前报告文学的题材似乎是越来越随意了。80年代的报告文学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学定位——以读者为中心,而90年代的一些报告文学家使人觉得他们的定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抓住什么就写什么,什么有趣就写什么,什么题材卖钱就写什么。缺乏自我意识,缺乏深入的辨识,缺乏必要的选择,在这种状态下,关注生活焦点矛盾冲突的少了,及时迅速报告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的少了,从更广阔、更深层次、更有理性地看待现实生活的几乎没有了……报告文学再也没有了往昔的飞扬神采,面对纷纭的生活,显得无所作为,软弱无力,见识短浅……
当前报告文学的第三大垢病是独立人格在金钱面前的流失和削弱。
报告文学之所以深得读者欢迎,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作家始终以一种清醒的独立意识进入社会和人生,在自由的心态下构筑出一个新颖的艺术世界。这是一种人格的魅力,独立的人格对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十分重要,越是希望作品公正、真实、客观地反映生活,越是要摆脱外在的种种干扰。
然而,当前出于金钱和商业的目的,为企业或个人写报告文学的已经越来越多,这种报告文学被称为“广告文学”。撰文为别人作宣传广告,或许不该作过多的指责,冷静地看,时代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阵痛,商品经济的浪潮已把文学推到了一个面临生存危机的窘境,作家们不得不在心理上和行为上作出相应的调整。然而,这种调整绝不能以牺牲或削弱作家的主体意识为代价。换言之,广告式的报告文学并非不能写,关键在于作家与描写对象之间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契约——我不是指金钱上的而是心灵上的契约。无论什么时候,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失去自我,变成他人的单纯的传声筒。而现状是如此令人伤心,目前我们读到的大量“广告文学”,并没有在拓宽文学的表现疆域和思考维度上下功夫,不过是简单的好人好事的复述,其区别仅在于有的复述得漂亮些,有的复述得拙劣些。更有甚者,无端的拔高,虚假的编造,肉麻的吹捧……这样的企业家传记比比皆是,不由得大倒读者胃口,也大败了报告文学的形象。
这种现象的大肆泛滥仅仅将它归罪于商品经济是不够公正,不够客观,不够全面的。我们且将它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显性的原因在于金钱的诱惑,隐性的原因则在于人的隋性——真正的报告文学家是艰苦的。若是说小说家有时可以凭借灵感“闭门造车”,而报告文学的生命却在于奔跑,不奔跑或疏于奔跑就没有作品。真正的报告文学又总是有棱有角,容易得罪人,相比之下,写广告文学既省力又得利,何乐而不为?这不仅是文学界的悲哀,更是人性的悲哀,长此以往,一个作家的价值和意义又如何体现呢?
三、报告文学必须找到自己
历数以上种种,并不是想将报告文学一棍子打死,恰恰相反,爱之深才会痛之切,对报告文学的热望才使我们密切关注它的兴衰。关键是,在世纪之交,报告文学迅速寻找到它的出路,重振雄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重振雄风的关键之一是:报告文学必须紧紧拥抱生活。
纵观报告文学的发展史,报告文学之所以辉煌,根本原因是它总是洋溢着浓烈的参与意识、批判意识、忧患意识和改革意识,表现出报告文学作家独特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报告文学的这种参与功能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报告文学就是因为它一直紧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大喊大叫才为万众瞩目。人们对它的欢迎,恰恰说明了它与现实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说明现实生活对报告文学的热切呼唤。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报告文学就是时代的全息摄影艺术。它的优势是任何一个文学门类无可取代的。只要我们紧紧拥抱生活,报告文学就能获得生机,获得出路,就不会被时代抛弃。
其次,坚持真实是它不可动摇的原则。“真实”这一特性是由报告文学自身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也是它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独特之处。犹如贾宝玉身上佩带的“通灵宝玉”,须臾不能离开。唯其真实,才造就优势,才造就魅力,才赢得读者,才使其葆有永久的巨大的创作活力。真实,对报告文学来说是如此重要,就像刺刀对于战士一样,以至于我们愿意为它作好牺牲一切的心理准备,以保全它的完整性。任何虚构对报告文学都是有害的,报告文学青睐虚构犹如饮鸩止渴,短暂的缓解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设想的后果……
再之,报告文学切不可轻描淡写了文学性。毋庸置疑,报告文学确实含有某种新闻因素,但它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这一文体的主导特质。报告文学是“报告”的文学。在这一个偏正词组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后者。人们常常强调了它的“批判价值”“信息价值”“宣传价值”“认知价值”……但却忽视了它最根本的“审美价值”。要知道,报告文学正是通过“审美”的手段达到了以上那一系列目的!
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报告文学这一特殊的文体,自出场那天起,就过分地被巨大的新闻市场所诱惑,以至不少报告文学家的文体意识不由自主地发生倾斜。但它毕竟是属于文学而不属于新闻。如同我们面对同一棵桃树,记者们注意的是它的果,而报告文学家们欣赏的则是它的花。这种差别就是艺术和现实的差别,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就是个性化的差别。差别永远是一个秘密,而每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孜孜不倦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秘密。
以上所述,仅是对报告文学当前状况思考的一个侧面。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已存在了长达80余年之久的文体,它确实有更值得拓展的内涵,尤其是它前几年所显示出来的不可小视的优势,应该引起理论家们的充分重视和关注——毕竟,至今为止,在中国,还没有哪一种文体能像它那样,达到和千百万读者这样贴心、这样休戚相关、这样血肉相连的程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报告文学家们将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以新的姿态参与生活,透视生活,重新担负起传送时代强健有力的脉息的责任。如果我们的报告文学家们真正让心中蕴含的理想之火充分燃烧起来,那么,明日的报告文学将再次异军突起,产生质与量的飞跃,建构起一种新的辉煌——那必将是超越昨天的辉煌!
收稿日期:1997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