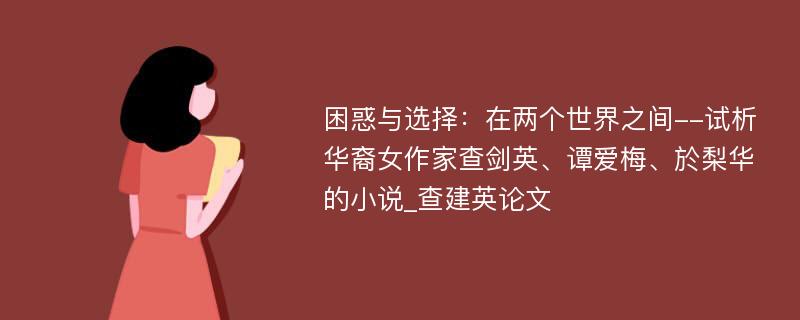
困惑与选择:在两个世界之间——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谭爱梅、於梨华小说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籍论文,女作家论文,困惑论文,两个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的本文分析,从民族(文化)与身份、语言(文化)与身份、性别(文化)与身份这三个方面,考察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於梨华、谭爱梅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人——身处异国他乡的知识女性,在男/女,东/西两个世界之间特殊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对自我文化身份与性别身份的理解和阐释,由此说明,这两位作家精心构筑的小说世界,隐现了中国及其文化在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困境,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她们小说中的人物便不再具有纯个人式的境遇。相反,这些人物的生命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和确认,都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存在总体经验联系在一起。她们的小说故事,成为与中国有相似政治经济背景的第三世界的隐喻。
主题词 小说 文学 东西方文化比较
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於梨华、谭爱梅(Amy Tan, 又译谭恩美)都是具有中国血统而现在身居美国,处于两种文化的临界点上的所谓“两栖人”。她们的作品在台湾、大陆及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无根的漂零与悬浮的自由
於梨华是三位旅美女作家中年龄最大、成名最早的一个。作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和“无根一代的代言人”,“寻根”是於梨华心灵深处永固的情绪。在这里,“根”已失却了它本身植物学上的意义,而成为於梨华自我文化归属的象征。之所以要寻,是因为离乡去国,飘萍天涯,自我了无着落。所以於梨华说:“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1)
的确,对于留学生而言,人们注定要在回去与出来之间徘徊,在中西两个世界文化之间徘徊。本土和他乡对于他们都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和排他力,他们自身无法彻底溶入其中任何一方而与之达成较深刻的内在和谐,而且任何一方也不把他们认同于“自己人”。於梨华笔下的牟天磊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进退维谷之中。
牟天磊出国留学十年。在出国前,他曾是个有勇气有梦想的青年。立志要“挺直无畏,出人头地”。(2)然而十年过去了, 归国回来的他,虽然学成业就,但他所渴望的理想和幸福并没因学业成就而到来,却反而离他更远了。十年的结果是自我的失落和人的“扭曲”。剩下的是挥之不去、无法摆脱、无法排遣的寂寞。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走出不自己那孤独、绝望的精神小岛。“我是一个小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3)。
在整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天磊的寂寞感就像一首乐曲的主旋律,忽高忽低,忽强忽弱,在书的每一页回响。这“比雾还迷蒙、比海还浩翰、比冰还要寒心的寂寞,来自于天磊自我文化认同的危机感,来自于他既接受了中美两个世界的文化,却又隔膜在两种文化中心之外的“陌生感”。
在美国,潜在于美国社会各种场合或隐或显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人毫不掩饰的民族自豪感,阻碍着天磊与美国人的融合。同时天磊身上的中国式的情思和思想行为,也使他抗拒对美国的认同。
回到台湾,天磊看到的是上自大学生下到厨师,都以洋为荣,以洋为美。他发现“自己仍是一个客人,并不属于这个地方”。(4 )天磊在美国没有根,在台湾也脱了节。剩下的是一个“空”字。
如果说於梨华通过塑造牟天磊创造了在两种文化间徘徊游移,无根飘零的“无根一代”的典型,那么,十几年后,查建英以谐谑的而不是於梨华式地感伤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悬浮的主体”的典型。这就是《丛林下的冰河》中的叙述者“我”。
“我”和牟天磊一样,当初也怀抱着壮志凌云踏上美国国土的。在异乡的最初几年,“我”俨然以全新的姿态,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地融进异国的生活和社会文化中。“我”对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认同,对同胞客人的不屑,都反映了“我”向往洗面革新,脱胎换骨,扯断与中国文化相联的根,而续结起西土的脉。然而,愿望与现实并不总是合二而一的。文化,一如胎记,岂能如此象披风似的轻而易举地披在人的身上,或者象抖落衣服的灰一样不费力气地从人的头脑中抹去?正如叙述者自我亦醒悟到:“归根到底,文化是‘泡’出来的。在这个缓慢自然的过程中,你所有的毛孔都得浸在水里。文化不仅有奶血之分,而且许多东西根本学不来”。(5)其实,岂止许多东西根本学不来, 许多东西也根本去不掉,它成为人身血肉之躯的一部分,就象一滴墨汁化入水中,你再也无法将那滴墨汁原封不动地分离出来。因此,当“我”在美国的生活似乎应该如鱼得水的时候,“一股似曾相似的陌生感从我心底冉冉上升”了。(6)
这种陌生感来自本土的呼唤中对异国文化的难以进入的心态。“我”与美国情人捷夫的分手成为这种“不能进入”的象征性仪式。对我而言,捷夫与其说是美国人,毋宁说是中国人。捷夫的典型意义在于他充当了一个文化符码,他的金发碧眼、开朗乐天、健康富有、肤浅幼稚,与其说是他本人的形象,不如说是“我”所指认的美国文化的具像。因此,“我”与捷夫的关系,就象征的意义上讲,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我”对异国文化的迎拒的具像化。我对捷夫从认识到分手的过程与“我”对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如鱼得水”之感到“笼中之鸟”之感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
小说中另一个与捷夫同样具有文化符码性质的人物,是我从前的恋人D。就像淡化捷夫的个人特征一样,查建英同样也通过淡化D的个性而将D符码化了。D的形象不能算丰满,但他所代表的我与故土文化的联系以及“我”心中中国式的理想主义,却因此而更加突出和清晰。D 死了,D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是否D所代表的理想精神和英雄主义也随着D 的消失而沉落冰河了呢?就像“我”注定要与捷夫分手一样,“我”与D的告别其实也是或迟或早都不可避免的,对我而言,D的死亡的意义在于,它使我意识到自己“与一长串宝贵的东西失之交臂”,意识到D “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与D完全认同,事实上,我虽然向往“D”生活的坚定、执着, 但“我”对他的整个“献身”精神却始终抱有怀疑态度。尤其,在“我”走完回国的寻找之路后,D对于我,也“永远永远地失落了”。
从上述可知,尽管查建英笔下的“我”比於梨华笔下的牟天磊晚出二十年,但它们的处境,她们的感受和心态依然有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作为在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陷入了文化身份困惑的危机之中:即认同于西方文化的同时感到惶惑与困扰;回归本土文化时亦觉陌生与不安。
其次,由身份危机演化而来的是他们内心的寂寞与隔膜,精神上无所归依,无所寄托的悲哀。
不过,由于於梨华、查建英的经历和心境以及人生选择的不同,因此,她们在各自作品中对身份危机的开掘以及情感判断又不尽相同。
总的来讲,於梨华的作品总是弥漫着台湾旅美华人回国留美都没有根,没有文化归属感的飘零身世的寂寞和失落心绪,因此於梨华始终固存着一个寻“根”情绪。但在查建英构筑的小说世界里,作者更倾心的不是去描写那种丧失故国家园放逐自我的哀伤,而是去感受放逐的自由,并清醒自觉地意识到这种自由的潜在的悲剧性。查建英在一封有关“边缘人”的通信中将出国留学喻为一个没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一朝跨进繁华都市,“她们所经历的异化与冲突自然有着某种悲剧性,但她若永远不出村,是不是也成为一种悲剧呢?”查建英的结论是,“有了选择的自由并不见得产生理想的选择,但你还是要这个自由。 ”(8)
看来,对于跨越中西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人而言,他们的优势和不利之处恰似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方面,居于两个世界之间,就意味着无法进入两个世界中任何一个世界的中心,而只能占有两个世界边缘的空地,这是一种既不属于任何一个领域,也不为任何一方所接受的悬置状态,使人产生无根漂零,身份不明,了无着落之感。但另一方面,居于两个世界之间,也可以被看作是立足于两个世界间,可以同时属于两个世界,自由进出于两个世界,悬置与疏离反而加深了自由,将一个文化视角扩展为两个文化视角。
二、语言差异与文化冲突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换句话讲,人不能没有语言而存在,他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居于存在之中,只有通过选择自己的语词来证明自己。语言并非是一个透明的、只须把意义填充进去的供人类摆弄的工具,或服务于其他外在目的的方法,相反,语言本身打上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戳记,它赋予人的永恒记忆是人生的见证,它使人找到了一个位置获得一种身份。因此,语言的转换就不只是一个工具的交换使用问题,而是意味着一个人身份角色的变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和移民们在说汉语与说英语的冲突与转换中所带来的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指涉与认同。谭爱梅的小说《福乐会》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和英语体系指涉意义的冲突与交融,如何影响着母女两代移民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和指认,造成母女间了解与误解,恩恩又怨怨的悲喜故事。
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了“美国英语”与中国故事的悖论问题。书中的四个中国母亲吴宿愿、许安梅、龚琳达和映映·圣克莱,都是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来到旧金山的,她们每个人都将自身的一部分,永远地遗留在中国大陆了;母亲一直等待着有一天能向女儿讲述自己遗留在中国的旧日往事,讲述那“千里鹅毛一片心”的情愫。然而母亲却无法用英语表达。当她们试图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女儿解释什么,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却耻笑她们的英语,母亲们难以让女儿理解自己,她们就这样怀着难言的隐痛活在过去的记忆中。
母亲无法与女儿沟通,她们与女儿的差别不只是发音的小错,也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而是潜隐在语言深处的文化差别所致。女儿们对汉语的不理解不仅仅是听不懂汉语,而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汉语语境中的文化。汉语语境中的母亲与英语语境中的女儿,她们对“母亲”、“女儿”这一能指符号所指涉的意义,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在母亲看来,母亲是女儿的权威,女儿必须是听话的、谦和的,因为你是女儿就注定没有反抗的权利,你必须去做母亲认为你该做的一切。然而在女儿看来,母亲是人,女儿也是人,她们是平等的,母亲没有权利干涉女儿的私事,女儿也没有义务承担母亲的指令。
因此,母女的冲突,无论是薇弗莱与琳达的争吵抑或是精妹与宿愿的不谐,其很大的原因正是她们各自对“母”、“女”这一能指符号所指涉的具体意义的理解的差异所致。
不过,对于女儿一代来讲,尽管她们极力反抗母亲的汉语体系中赋予“母亲”的权威意义,以及对于“女儿”必须谦和、孝顺、服从、听话的规定,但她们毕竟是说汉语的母亲的女儿,这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汉语对她们的影响,虽然是支离破碎的,但毕竟在她们的英语世界里留下了斑驳的痕迹。
同样,生活在汉语记忆世界中的母亲们,也不得不面对英语世界的现实,对于女儿把自己指认为美国意义的女儿,拒绝做中国意义的女儿的思想言行,母亲除了无奈地悲叹女儿与自己“隔着一条沟,我永远只能站在岸的这边观望她”外,她还是不得不卷着舌头学英语,不得不接受即使不是完全接受至少也是部分地接受女儿的那套语言指涉系统。《福乐会》中的两代移民,或被阻隔在英语语境之外,或被阻隔在汉语语境之外,两种语境交流的艰涩,它们之间的磨擦甚至对立给这些移民带来许多痛苦、困惑。但也有一些华人,他们既能操一口标准的汉语,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是不是就能自由自在地在中美两个相异甚大的语境中游刃有余了呢?在查建英和於梨华那些以留学生为题材的小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类人的心态。
在查建英的成名作《丛林下的冰河》中,有一段很有趣的情节值得我们注意。作品一开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极其西化,对美国充满浪漫幻想的现代女性。但在一次生日会上,当她渐渐酒力不支,口中喃喃自语时,冒出来的不是天天说着听着的洋文,却是久以忘怀的汉语。她的一段内心独白极能说明问题:“大约我骨子里企盼脱胎换骨,做个疯癫快乐的西洋人吧。我想象自己鼻梁升高,眼睛发绿,头发像收获前的麦浪一样起伏翻涌。无奈我仍旧是用汉语想这些事。”(9)
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在这里表现得很清楚了,通过对母语的压抑使自我的“中国性”回到潜意识当中,但一旦意识在酒精作用下放松了警惕,潜意识的东西就荡漾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当她用汉语动情地破口大骂的时候,美国朋友却以为她在满怀激情的诵诗。于是语言的意义本身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意义之外的情感的渲泄。也许,即使她本人也没有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在崇拜西方,习用西方话语,认同于西方文化价值观时,潜藏在心底深处的东方思绪以及强烈的民族压抑感,用她的中国话却把这一点毫不遗漏地泄露了出来。语言,承载着几千年文化的积淀,象无法摆脱的影子。长长短短拖在她的身后,在情感最激烈最隐秘的时候,就象高悬的太阳,把那影子照得更加清晰了。
我们在查建英的另一篇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的主角伍珍身上也能找到同样的情形。每天当太阳揭去黑夜的面纱,伍珍便披上盔甲精神抖擞地投入美国的角逐场,然而,每到深夜,白日里与现实环境认同中所带来的异化与冲突困扰和折磨着她,自身真情的失落,他人对自己爱情的失落,这双重的失落,象锋利的剑刃,即使再强硬的盔甲也无法抵御它在自我心灵上划下痕迹。而抚慰伍珍受伤的心灵的不是她所崇尚的色彩斑斓的美国生活,而是丈夫余宝发的中国来信。那些方块字,对伍珍来讲,是熟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她来自那些方块字的发源地,那里的文化、风俗、价值连同这方块字本身载着她的过去、她的情思。而陌生,则是因为要在这个洋文世界里,她必须疏离甚至忘却方块字的存在。
从上述分析可知,像“我”以及伍珍这样的留学生,虽可以懂得中英两种语言,但却不可能同时操作两种语言,对任何一种语言的操用,实际上意味着对另一种压抑身份的回避。
俄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米哈伊·巴赫金认为,在一个给定的结构里,符号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一个斗争和矛盾的焦点,语言是一个意识竞争的领域,没有任何语言不卷入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反过来又是更广阔的政治、思想意识和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根据这一理论,中西语言在留学生内心的对立与变换恰恰反映了中西文化意识之间的斗争。
《远行人》的作者苏炜在一次座谈会上曾回忆说,“我30岁到美国,我的英语基本上从零开始,我发现我永远是用人家小学生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大学生、研究生所达到的思维,觉得非常痛苦”。(10)隐藏在这种表达的痛苦背后的事实是话语丧失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痛苦。於梨华的经历可以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於梨华到美国留学之始,在一个叫依雷的美国人家里帮工,依雷太太为人刻薄,这不仅表现在她拼命使唤於梨华,更为恶劣的是,她在於梨华辞别她家的前夜,偷偷潜入於梨华的居室搜查她的行李,并公开宣称:“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面对依雷太太在行为和言语上对自己的侮慢,於梨华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她却无言。“不是我没有一肚子话可以回敬,而是英文太差,不足以表达我的愤怒。”(11)此时,英语成为权力的象征,掌握了英语似乎就获得了某种特权,而对英语的陌生就意味着自我现实中生存的困境。
显然,为了生存,就必须掌握英语,接受以英语为表征的整个西方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生存是以对汉语以及以汉语为表征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否弃,这种生存无疑意味着死亡,因此,同样是为了生存,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承继也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查建英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英语对汉语的压抑,以及后者在潜意识中对前者的抵触,充分表现了留学生在西方世界里对文化身份的取舍倾向,同时,也为居于传统与西方之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重建问题,提供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启示。
三、突围与落网:女性生存的困境
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体文化中心的边缘,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女性,她们在白人世界的处境又比少数民族男性的处境更为艰难,所受待遇也更不好。她们不幸地集三重“弱点”于一身:首先,她们是欧美世界中的中国人;其次,她们是东方男性世界中的女性;再次,她们还是西方男性世界中的中国女性。她们不仅要因此遭受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而且还要经历来自东西两个世界男性优越感对她们的冲击。欧美话语与男性话语以势不可挡之势将她们淹没,她们要在强大的其他话语中突围出来,找回失落的女性本真的存在,探寻和确认女性的自我意识,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任务。身为这些少数民族女性的一员,查建英、於梨华和谭爱梅出于对女性自我命运及其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共同关心,用她们的笔对女性在中西文化价值的冲突中的生存境遇及自我寻索的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
在关心女性自我的命运,自我的生存状况,探索女性性别真相这一点上,查建英、於梨华和谭爱梅可以说是现代女作家五四传统的继续和沿革。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并且更由于她们在更为广泛的中西文化的背景下接受教育、工作和生产,因此,她们对于男女两性的洞察,对于女性性别身份特征的认识,以及对女性生活状况的表现,较之以前又有所不同,而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她们的小说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
如前所述,由于美籍华人女性的特殊地位,因此,她们常常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因素的困扰,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常常摇摆在中西视点和男女视点之间。她们为此而受尽煎熬。
一方面,由于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价值系统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威力,女性依然像铆钉似的钉牢在次于男人的位置上,而更为可悲的是,甚至女性自己,也认同于这一“第二性”的位置。比如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变》中的女主角文璐,在她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她始终认同并习惯于丈夫仲达对她的看法:“我知道你会是一个最好的妻子,最好的母亲。你就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的典型”(12)。文璐没有意识到,在仲达对她的“好”的褒扬中,隐藏着一个男性对女性自我存在的无视的心态和要求女性对男性权威不容置疑地忠实的期望。
但是,毕竟,文璐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同于从前要求“三从四德”的时代,她所生活的环境也不再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地方。她上过学,留过洋,她也曾经“喜欢用笔画出她的感情、她的思路、她的梦想”。唐凌的出现,使文璐那早已习惯麻木的灵性的感受忽然敏锐了起来,这个迟了二十年的唐凌,与其说是爱情的使者,毋宁说是文璐自我觉醒的触媒,使她猛然悟到,“十年来她没有自己的身份”,成为丈夫和孩子的影子。她再不能忍受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于是,她提着那只箱子离开了丈夫。
小说是以文璐离家出走开始的,出走这一行为本身意味着对家庭的反叛,因而也是对妻性、母性这一女性传统性征的反叛。是她确认自我的第一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璐还没有迈出第二步的时候,她又收回了已经迈出的第一步。小说的结尾处,文璐在丈夫和一对儿女的切切哀恳声中,又提着箱子走上了回家的路。
记得张爱玲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然而,“走到哪儿去呢?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13)
也许,这是女人永难走出的困境。因为作为女人,除非她甘心孤独地走完人生旅程,那么,她终将免不了要去爱,并渴望得到爱,她要结婚,要生儿育女,她们从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庭,从一个男人的屋里走出,又走入另一个男人的屋中,而在这出出进进的过程中,女性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楼”在那里,但到楼上去开辟另一个空间,别有一番天地,楼上楼下的穿梭,留出一点空间,启发我们对爱:妻爱、母爱、异性之爱做一重新的审视,这正是於梨华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自我寻索的女性的贡献吧!
当然,对于“楼上”,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楼上”比“楼下”更糟,在“楼下”,女性可是客厅的主妇,是“坐稳了的奴隶”,而到了“楼上”,她甚至连“坐稳了的奴隶”也做不成,她只是一个丧家的被男性暂时领回去的雌性动物,成为男性欲望发泄的对象。在《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这篇小说中,查建英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女性“出走”的故事,揭示了“楼上”的另一份真相。
小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述伍珍在中国的经历,第二部分讲述她在美国的奇遇。在中国,伍珍小时候是好学生,上山下乡是好知青,结婚后,家庭生活不好不坏,平平常常,有时打打闹闹,有时恩恩爱爱。丈夫余宝发虽然其貌不扬,甚至还窝窝囊囊,但对伍珍是绝对忠心,绝对的顺从。如果伍珍是一个传统式的认命的女性,是一个没有欲望的女性,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事实是,按照中国传统女性价值来衡量,伍珍性格中不顺从听命,不甘心安贫乐素,不知足常乐的特征,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她“非女性”的基础,埋下了她最终冲出家门,甚至国门去发展自我的欲望的种子。如果说,伍珍身上的“非女性”在最初还具有反传统的性质,她的强烈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在当时中国令人压抑的环境下还具有极大的合理性;那么当踏上美国,走在纽约麦迪逊大道的时候,西方文化中极端个人主义和实用功利主义的思想致使她个人的私欲极度膨胀,在打工艰难,进商学院又无望的情况下,她的美国梦即将破灭。伍珍看准了在美国商业社会,她的唯一价值是出卖姿色。于是,伍珍收拾起做人的廉耻之心,依靠出卖色相骗得一大笔美金,拿到了绿卡,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但她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查建英以不无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在中国的伍珍作为一名女性,其合理的实现自我的欲望遭受压抑的不幸,又以不无痛惜的心情叙述了她在美国以出卖自我来达到私欲目的的行为。虽然她也像於梨华一样,不可能为女性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但是,她在真实的基础上将在美国的中国女性生活的一角以一种日常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对于男性社会文化中所必需的“女性神话”表象无疑是一种消解和颠覆。
於梨华和查建英小说中的女性是以“叛逃”的形式开始自我寻索,求取价值的历程,她们试图在“楼”外建立一个自我的世界,但她们在劫难逃,“楼”封闭着,但她们必须“走”,这是她们内心的呼唤,因此,她们只好委屈求全地从“楼”下走到“楼”上。
谭爱梅与上述二位作家不同,她通过反讽式地叙述灶神的故事,从根本上颠覆了父系社会男性崇拜的神话。在灶神爷的神话里,灶神与其妻的关系,是传统父系社会所认同的家庭夫妻关系的写照。妻子温柔贤良,心灵手巧,吃苦耐劳;丈夫好色好吃,挥霍无度。妻子为丈夫所弃,毫无怨言,而当丈夫有难,她还不记前嫌,慷慨相助。灶神自己作恶,本是死有余辜,但在男性社会里,男人有过,依然受到尊重、崇拜;而那受害者灶神妻子作为一名女性,她只能逆来顺受,无论好坏,永远沉默无言,被丢进时间的忘怀洞。
如果说,神话中的灶神是沉默而苦难的传统女性的象征,那么现实的“灶神妻”——故事的主人公薇薇则在苦难中激发了反抗男性权威的勇气。薇薇也曾经有过传统女性的梦想——找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但是,她那微薄的只想做一个善良主人的顺从奴隶的希望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像肥皂泡般地破灭了。三个孩子相继谢世,丈夫闻福不仅殴打责骂在生理上虐待她,而且还寻花问柳在心理上折磨她。薇薇最初是逆来顺受的,就像神话中的灶神妻。从这种意义上讲,薇薇与闻福和灶神妻与灶神爷组成一种同质同构的关系。但小说的后半部,薇薇的反抗使这种同质同构关系转换成一种异质同构关系,故事的最后,薇薇出走并烧毁了灶神,自己命名了一个新的女神——无忧。对于生活的命运根本上是为父权社会文化所决定的女性来说,薇薇的行为无疑是对生活命运的抗拒,因而也是对父权社会文化的否定。
谭爱梅通过薇薇对自己一生的自述,通过她与“灶神”的认同与背离以及对“灶神爷”由崇拜、害怕、厌恶到反抗以至最后砸碎的过程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传统女性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的艰难历程。
结束语
查建英、於梨华和谭爱梅的小说讲述在美国的华人的故事,讲述在男性世界中女性的故事,她们在这些故事中进行了跨越中/西、男/女两个世界的探究,从而将近代以来中国在传统与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的困惑与选择的现实图景戏剧化了。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之一,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而由于西方先于中国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并取得了全方位的杰出结果。西方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模式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不由自主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化的过程。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世界文化的多元倾向、多重意识的共生状态,但是,我们更不能否认的是,多元文化下所获得的生存和传播能力,最终取决于经济、政治以及传媒技术的发展程度。因此,目前还处于较低经济和文化层次的中国,事实上并不能充分展开自身文化和语言的可能性,以经济高度发展为特征的西方世界的影响,始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渗透着大陆及其他华人居住区。结果,我们一边还在讨论如何选择,一边却已不知不觉在社会文化上西化了。这一现象在上述三位作家的小说中有着程度不同的反映。
但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自己的生命象征物——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生活和发展于这种文化之中,民族与它的文化,是互相依赖不可分离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具有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在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撞击的激浪中,在欲摆脱耻辱的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它总是力图保持民族的独立,保持这个民族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东西。因此,自近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卷入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生死斗争(14)。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对矛盾的价值效应:学习西方是对西方的承认和接受,是对自己历史的觉醒和对自己传统的叛离;但保持传统却是对西方的拒绝与抗衡,是对自己历史的确认和对自己传统的继承。要彻底解决这一矛盾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它将伴随着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历程。走向世界的中国,恰如走出国门的华人,它必将经历中西矛盾冲突带来的困惑,经历文化价值观失衡所带来的失落,经历“如何采用他者的语言而同时不放弃自己的语言”的焦虑,以及选择和确认自身身份位置所带来的苦闷与彷徨。查建英、於梨华、谭爱梅这三位作家对在美国的中国人由于民族差异、语言差异和性别差异所引起的自我身份的困惑与选择的描写,用个别的独特的人物的命运与经历展示了在中西文化相互撞击下中国文化和社会普遍的生命历程。她们把古老文明的优越和现代中国的窘迫、民族的自尊和自卑、西方的咄咄逼人和东方的压抑屈从等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现实画面,以一种个人经历的方式凸现出来,赋予了她们小说以一种深度和意义。因此,她们的小说故事,她们笔下的人物,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寓言,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生存状况的映照。
注释:
1 於梨华:《白驹集〈归去来兮〉(代序)》,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
2 5.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49页。
3 同上,第81页。
4 同上,第131页。
5 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郏宗培、 刘绪源主编:《丛林下的冰河》,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6 同上,第203页。
7 同上,第238页。
8 小楂、唐翼明、于仁秋:《关于“边缘人”的通信》, 载于《小说界》1988年第5期,第132页。
9 同注释7.,第198页。
10 《留学生文学座谈纪要》,载于《小说界》1989年第1期, 第188页。
11 於梨华:《我的留美经历》,载于《人民日报》1980年4 月20日。
12 於梨华:《变》,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13 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载于《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14参见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 漓江出版社, 1988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