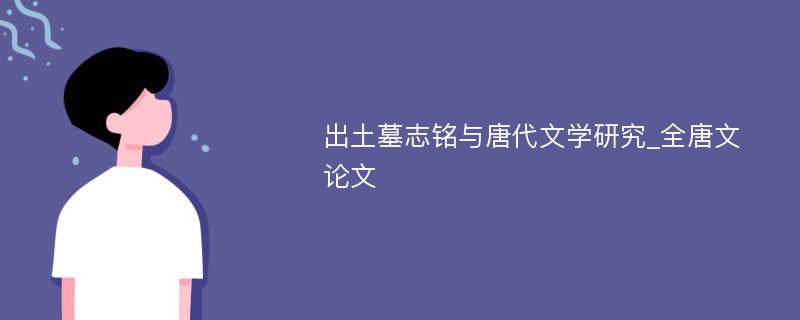
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论文,唐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几种,前两种为拓本,后一种为整理本。墓志作为重要的出土文献,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利用墓志解决了文学史上许多重要问题。墓志多以散文记叙死者姓氏、籍贯、生平,系之以铭,故又称墓志铭,铭则以韵文概括全篇,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之词,此为常式。因为墓志是埋在圹中,以防陵谷之变迁,与神道碑立于墓前供人观看,其用意微有不同。墓志的制作,始于东汉,宋洪适《隶释》卷13载章帝建初二年《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即圹中之物,清光绪末峄县所出延熹六年《临为父作封记》,也是圹中之物,可视为后世墓志的权舆,志墓之风实始于东汉之初,历魏、晋、宋、齐、梁、陈皆有行之者。然其时立石有禁,故砖多石少。北朝魏齐之际,此风最盛。隋唐以后,遂著为典礼。《全唐文》收有大量墓志,拓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洋洋巨制。“唐墓志流传独多,式亦最备。”(以上均参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10月,页89)唐代墓志对唐代文学研究有相当大的作用,墓志不仅是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且是研究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一 墓志是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
墓志为全唐文的一个组成部分,今人整理全唐文,作《全唐文》补编,其中占比例最大者莫过于墓志。周绍良等编纂的《唐代墓志汇编》就收有墓志三千六百余方,其中的极小部分与《全唐文》重复,是因为其文字间有出入并具有参考价值。从墓志的载录看,唐代散文作者除《全唐文》三千余人外,尚可增补千余人。这是一个宠大的散文作家队伍。
从文学自身的艺术价值考虑,无庸讳言,《全唐文》基本上反映了有唐一代的散文风貌,而出土墓志中不少作品因出自陋儒浅人之手,有的文字不畅,有的叙述繁冗。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印刷术尚未施行于文人诗集文集的唐代,藉物质形态以传的文学资料,数量之多要算敦煌宝卷和出土墓志了,这是多么珍贵的文学遗产。大量的墓志和他们作者的留存,有助于人们去认识唐代的文化特征和尚文的社会风貌,墓志的文学价值和文学研究的意义不容忽视。
第一、墓志可补时有文名而未有散文作品留存者
唐代人文昌盛,诗人散文家辈出,而一些史载其长于文学者,却不见作品留存,《旧唐书》卷177《毕諴传》载:“自大中末,党项羌叛,屡扰河西。宣宗召学士对边事,諴即援引古今,论列破羌之状,上悦。”毕諴当为一议论高手。又云:“长于文学,尤精吏术。”《唐语林》卷3载:“毕相諴家素贫贱,李中丞者,有诸院兄弟与諴熟。諴至李氏子书室中,诸子赋诗,諴亦为之。顷者,李至,观诸子诗。又见諴所作,称其美,諴初亦避之,李问曰:‘此谁作也?’诗子不敢隐,乃曰:‘某叔,顷来毕諴秀才作也。’諴遂出见,既而李呼左右责曰:‘何令马入池中践,浮萍皆聚,芦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对。諴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为夜来风。’李大悦,遂留为客。”毕諴所对,体现其文才和机敏,这一对句也是毕諴唯一传下来像诗的句子。像毕諴这样名重一时的文人,赖出土墓志保存了一篇他撰写的完整墓志:《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页2299,以下引用此书只出注页数),墓主葬期是大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撰人毕諴结衔为“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柱国”,毕諴大中四年二月十三日自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充翰林学士,大中六年七月七日授权知刑部侍郎出翰林院。
第二、墓志可补重要诗人无文留存者
一些以诗名世的文人,无一文存世,现在我们在出土墓志中发现他们撰写的墓志,这对研究诗人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如韦应物,诗歌创作成就杰出,卓然一大家,除《全唐文》收其一篇赋作《冰赋》外,无一散文传世,《千唐志斋藏志》存有韦应物作《大唐故东平郡钜野县令顿丘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拓本(页1758—1759载录),此参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532页。李颀,盛唐重要诗人,《河岳英灵集》云:“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但无散文存世,河南洛阳出土的《唐故广陵郡六合县丞赵公墓志铭并序》,系李颀所撰(《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一册,页153)这至少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去认识一个作家。
第三、墓志可补反映文人风格的重要散文作品
这一类作品固然不多,但一旦出现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旧唐书》卷190《文苑中》云富嘉谟、吴少微的文学成就时说:“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作《双龙泉颂》、《千蠋谷颂》,少微撰《崇福寺钟铭》,词最高雅,作者推重。”这些作品一时盛传,最能代表富吴体的风格,但他们的文章散佚很多,《全唐文》中收录其文极少,上述三篇文章也只存吴少微《崇福寺钟铭》一文,二人今存文章中也别无碑颂之作。唐代出土墓志中有吴少微富嘉谟同撰之《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上柱国安平县开国男赠卫尉少尉崔公墓志》(页1802-1803),这一墓志对了解富吴体是弥足珍贵的文学资料。《崔公墓志》已改六朝徐、庾的华艳夸饰,叙事写人典重质实,下面引数节文字以见其貌:
公正言于朝,多所讦忤,遂左为钱塘令。故老怀爱而愤冤,号诉而守阙者千有余人。期而得直,复为旧党所构,卒以是免。闭门十年,寝食蓬藿,终不自列,久乃事白,授相州内黄令,迁洛州陆浑令。南山有银冶之利,而临鼓者不率,公董之,复为矿氏所罔,免归。
范阳卢弘怿,雅旷之守也,既旧既僚,政爱惟允。及卢公云(之?)亡,公哭之恸,因有归欤人志。无何,张昌期乃莅此州,公喟然叹曰:“吾老矣,安能折腰于此竖乎?”遂抗疏而归。
公尤好老氏《道德》,《金刚》、《般若》,尝诫子监察御史浑、陆浑主簿沔曰:“吾之《诗》、《书》、《礼》、《易》,皆吾先人于吴郡陆德明、鲁国孔颖达,重申讨核,以传于吾,吾亦以授汝。汝能勤而行之,则不坠先训矣。”因修家记,著《六官适时论》。
岑仲勉先生盛赞此志,“今读其文,诚继陈拾遗而起之一派,韩、柳不得专美于后也。”(《金石论丛》209页)
第四、墓志可补重要散文作家的文体缺项
即使存文较多的作家,补拾遗文同样有意义,萧颖士是散文大家,但现存文章偏偏缺墓志一项,萧颖士《唐故沂州承县令贾君墓志铭并序》正可补阙,“此篇尤其片鳞只爪之可贵者矣。”(同上,页226)
另外,墓志尚可补唐诗,《全唐诗补编》利用了墓志,但尚有遗漏,陈尚君先生在《〈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中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千唐志斋藏志》1172页又检得女诗人谢迢《寓题诗》二句“永夜一台月,高秋千户砧”(《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页491)。又如《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12《大唐故右金吾卫胄曹参军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载:“父问政,和州刺史……时太守齐公崔日用许其明敏,因遗和州府君书曰:‘公尝为诗云,五文何彩彩,十影忽昂昂。今于符彩见之矣。’”李问政存有诗句:“五文何彩彩,十影忽昂昂。”此亦可补《全唐诗》。
二 文学家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
利用墓志考订文学家生平,在不少方面有重要突破,如王之涣生平,王之涣写有《登鹳鹊楼》(白日依山尽)和《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当时诗名很大,但两《唐书》无传,文献资料记载其事迹极少,靳能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页1549)的出土,使人们对王之涣生平事迹有了精确的了解。又如高适的世系,史传不详,周勋初先生据《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禾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考知高适就是高宗时的名将高侃之孙,父崇文,终韶州长史,与《旧传》互证(以上二例参《唐才子传校笺》卷2、卷3)。
即使有些材料看上对作家生平似乎并不很重要,但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如补其仕履,《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四册《赵珪墓志》云:“长史江西观察判官监察御史里行璘寄财毕葬事。”墓主葬期为大中元年九月十四日,由此考知《因话录》的作者赵璘在大中元年参江西幕,任观察判官;又如通过墓志提供的材料了解作家多方面的才能,程修己为文宗朝的著名画工,唐文宗有《程修己竹障诗》,《金石续编》卷11《程修己墓志》载其工于绘事草隶,又云:“大中初,词人李商隐每从公游,以为清言玄味,可雪缁垢。”李商隐与程修己交往还在于二人都在书法上有成就,《宣和书谱》卷3:“李商隐字义山……观其四六稿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声律,笔画虽真,亦本非用意,然字体妍媚,意气飞动,亦可尚也,今御府所藏二:正书《月赋》,行书《四六本稿草》。”
同样可以和当代研究成果互证。《唐才子传校笺》“李颀”下云:“《国秀集》目录卷下作‘新乡尉李颀’,此为唐人记李颀曾仕新乡尉之最早亦唯一之记载。”按,《千唐志斋藏志》923《唐故瀛州乐寿县丞陇西李公(湍)墓志铭并序》云:“酷爱寓兴,雅有风骨,时新乡尉李颀、前秀才岑参皆著盛名于世,特相友重,方镇雄藻,比肩莫达,孰是异才,而无显荣,以乾元元年终于贝丘,凡百文士,载深恸惜。”李湍墓志所载“新乡尉李颀”与《国秀集》互证,由此也可以知道李颀交游中尚有李湍,李湍与岑参也有交往。又,河南洛阳出土的《唐故广陵郡六合县丞赵公墓志铭并序》,也系李颀所撰(《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一册,页153),李颀结衔为“前汲郡新乡县尉”。
三 用于作家作品中人名的考订
人们在阅读或注释唐人作品时,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名难以搞清楚,而作品中的人物对我们理解作品往往又显得非常重要。有关《全唐诗》人名考证著作的出现,对人们阅读作品带来极大的的便利,其工作却是相当艰辛的。《全唐文》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充分展开,不仅题目中的人名,就是作品中的人名也应该能尽量考订出来,这也是文学研究基础工作的一部分。利用墓志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如《全唐诗》卷349欧阳詹《太原旅怀呈薛十八侍御齐十二奉礼》诗,诗中二人当为河东幕僚,我们可以借助墓志考出齐十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二册《张任夫人李氏墓志》,唐贞元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葬,撰人为“河东观察推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摄监察御史齐孝若”。欧阳詹诗当写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间(详下薛十八考),诗中齐十二奉礼者也,时齐孝若带朝衔“太常寺奉礼郎”,奉礼郎,从九品上,其后齐仍留幕,至贞元十七年带朝衔“太常寺协律郎”,协律郎,正八品上。因涉及到齐孝若在幕时间,这里还要考订一下薛十八。《全唐文》卷542令狐楚《为人作奏薛芳充支使状》:
右件官蕴蓄公才,精勤吏道。文章史传,无不该通。大历末则与臣及徐泗节度使张建封同时故马燧作判官。建中三年曾以公事直言,不合其意,遂被奏授交城县令……臣以其四居畿令,两任法官,有学有才,堪为宾佐,委令推断,无不详平,与之筹画,多所裨益,相谙相识,二十余年,滞屈最深,实希荣奖。伏望天恩,特赐改官,充臣观察支使。
据《状》,令狐楚文所代之人应符合两个条件,一与张建封曾同佐马燧太原幕;二现为观察使。此人必是李说。马燧大历十四年为河东节度使,大历十年马燧为河阳三城镇遏使时,薛芳、李说二人当相识。张建封,据《旧唐书》本传,大历十年马燧为河阳三城镇遏使,辟为判官,李说也是马燧河阳从事,依时间推算,若从大历十年(775)始,至李说为河东观察使(贞元十一年——贞元十六年),与《状》“二十余年”正合。薛芳在河东李说幕中,时当带监察御史衔。可参拙作《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河东”相关部分。
同样也可以利用墓志考订作品中的人名,这里举一个例子:《全唐文》卷708李德裕《掌书记厅壁记》载河东有掌书记“国子司业郑公”,郑公为谁,通过墓志则不难解决,《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二册《马炫墓志》,撰人是“中大夫国子司业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郑叔规”,此与李德裕文正合,又《唐代墓志汇编》有《郑叔规墓志》,其云:“王□以健笔奇画,意气名节,交马北平燧、李中书泌、张徐州建封,掌北平书记十年,笺檄冠诸侯,得兼御史丞,副守北都,入为司业、少仆。”李德裕《记》郑公失其名,幸以二墓志补之。
有时用墓志解决问题,简单明了,而用文章互证会复杂一些,这也是墓志用于考订的优点。
四 了解士人风尚及其学术文化环境
如,唐人重进士而轻明经,《李蟾墓志》云:“年未弱冠,以经明游太学,忽不乐,乃修文举进士,颇以行艺流誉于士友之间。”(页2137)这则材料就是一个辅证。
中晚唐士人进入方镇使府,是一普遍现象,原因很多,其中一点就是幕职在一段时期内其职绩可以军功叙录,《唐会要》卷81载,贞元八年敕,“诸军功状内,其判官既各有年限,并诸色文资官,不合军行,自今以后,更不得叙入战功,其掌书记及孔目官等,亦宜准此。如灼然功效可录,任具状奏闻。”方镇文职当屡有叙入军功者,故有此禁,事实上在方镇这类事情是无法禁断的,《李公度墓志》:“欲其速仕也,故不敢以文进用。”(页2305)社会上以军功进速度高于以文进,方镇是文人极好的升迁场所。
以上材料都可以考见一时风气。大量的墓志还可以让人们认识唐代的整体学术文化环境,友人程章灿君曾作《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石刻考工录补遗(上)》(《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利用墓志试图从某些方面入手,去勾勒一代学术的风貌。
五 了解文人所处时代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
不同时代的墓志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状况,相对于正史所载,墓志所表现的往往更具有普遍性,其记载更为具体,并有生动的细节描写。下面以安史之乱对当时士人的影响为例,说说墓志对了解文人所处时代的作用:
第一、为了避乱,当时有不少人流亡江南。
《崔氏墓志》载:“属中夏不宁,奉家避乱于江表。”(页1769)
《郭府君墓志》载:“属逆虏背恩,避地荆楚。”(页1772)
《独孤涛墓志》载:“会河朔军兴,避地江表。”(页1783)
《李府君墓志》载:“顷因中华草扰,避地江淮。”(页1815)
《张翃墓志》载:“属中原丧乱,随侍板舆,间道南首。”(页1820)
《崔祐甫墓志》载:“属禄山构祸,东周陷没,公提挈百口,间道南迁,讫于贼平,终能促全。”(页1822—1824)
以上所引墓志在时间上大致相近,说明了一时间阶段的普遍情况。当然也有就近避难的,《尚夫人墓志》载:“时逢难阻,戎羯乱常,河洛沸腾,生灵涂炭,长子南容,不胜残酷,避地大梁。”然而主要还是逃往比较安全的江南地区。一旦乱平,南迁的士人纷纷北归,“羁孤满室,尚寓江南,滔滔不归,富贵何有?”(《崔祐甫墓志》)这可以概括南迁士人的共同心理。
第二、安史之乱稍有平息,原来权葬于南方的坟茔此时大规模北迁。
《唐代墓志汇编》永泰003韦应物撰《大唐故东平郡钜野县令顿丘李(璀)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先为钜野县令,后因事贬武陵县丞,“以天宝七载九月十六日终于武陵,养年七十有二。前以天宝八载别葬于洛阳北原,长子浣尝因正梦左右如昔,垂泣旨诲,俾归先茔。旋以胡羯,都邑沦陷,浣偷命无暇,作念累载,如冰在怀。及广德二年夏,夏梦诲如先日,又期以岁月,授以泉阃。明年,永泰元祀,浣始拜洛阳主簿,迩期哀感,聚禄待事,乃上问知者,下考蓍龟,事无毫著,……以其年十二月九日归葬于河南府河南县谷阳乡先茔之东偏,奉幽旨也。”(页1758—1759)长子李浣朝思暮想,将先人的坟迁归故里,故夜有所梦,这同样反映了急切思归的恋土情结。大历014《唐故窦公夫人墓志铭》:“顷属时难流离,迁徙江介……其时中原寇猾未平,权殡于丰城县。”大历四年,国难方弭,改葬于北邙陶村之北原,依于父母之茔。(页1768)《崔氏墓志》:“顷以时难未平,权殡于吉州卢陵县界内。今宇内大安,弟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祐甫勒家人启殡还洛,以大历四年岁次夕酉十一月乙丑廿日甲申,窆于河南县平乐乡杜郭村之北原。”(页1770)《张颜墓志》:“时乱离斯瘼,权厝城隅,洎天衢之康……以大历八年,岁在癸丑,闰十有一月十九日窆于先茔之东。”(页1781)《独狐涛墓志》载墓主权窆于衢州,大历九年归葬于洛阳清风乡北邙。(页1783)《裴夫人墓志》:“权窆于长沙,属中原多故,未克返葬……以大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合祔于邙山北原。”(页1813)
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唐故杭州钱塘县尉元公墓志铭并序》载:“时属难虞,兵戈未息,乃权厝于县佛果寺果园内。贼臣思明,再侵京邑,纵暴豺虎,毒虐人神,丘垄遂平,失其处所……遂以大历四年七月八日,招魂归葬于□南金谷乡焦古村,从先茔。”(页1767)由于战火,已无坟可迁,只能招魂而葬。
安史乱起,士人南迁;战乱稍平,士人又北归。这种情况在诗人笔下都有较为概括的表述,前者如郎士元所云:“避地衣冠尽向南。”(《全唐诗》卷207《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后者如司空图所云:“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全唐诗》卷90《贼平后送人北归》)独还未必,北归在当时是普遍的,墓志可证。因此,人们在探讨安史乱后南方文化得到发展而许多士人活动在南方时,也不能忽视传统乡思回归情绪,另外京城还在北方,北方仍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
墓志的用途很多,除上面所论,比如还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唐代一般士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如门阀观念,门阀士族观念肇始于东汉,鼎盛于两晋,历南北朝而不衰,唐时士族仍有相当的政治地位,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墓志看,中晚唐人仍重门阀士族,文人十分推崇高门出身者,大中六年《崔芑墓志》云:“弱冠以族望门绪为士友所推。”(页2298)大中六年《卢就墓志》云:“卢氏自北魏著为望姓……卢氏历两汉魏晋,轩冕冒袭,至元魏以来,代居山东,号为名家。”(页2299)大中七年《唐故汴州雍丘县尉清河崔君夫人范阳卢氏合祔墓志铭兼序》:“卢氏与崔王等五姓联于天下,而夫人之家,又一宗之冠焉。故论道德,辨族氏者,必以为称者。”(页2309)忠孝观念,在女性方面,体现女子对公婆、丈夫和子女的关系上,《董氏内表弟墓志》:“娶乐安任氏,幼有妇德之□长,继移天之义,昼哭声咽,洒泪涟洏,鞠育四男,并天假秀异。”(页2300)《卢夫人墓志》:“夫人幼而明敏,柔邕婉娩,能尚孝敬之道,常慰慈心,莫不克于组纴,复绣绘之奇。”(页2307)在男性方面,体现在孝友之道上,《李公度墓志》:“公始自孩提,即知孝友。”(页2305)他如名利的观念,各方面的材料相当丰富,不胜枚举。
当然墓志作为史料有其局限,由于撰写者的态度和刻工的水平,墓志的历史信值不免有所减损,史学家们在运用墓志材料态度非常审慎,欧阳修《集古录跋》九《白敏中碑》云:“其为毁誉难信盖如此,故余于碑志,惟取其世次、官寿、乡里为正,至于功过,善恶,未尝为据者,以此也。”考诸实际,墓志中尚有世次、官寿、乡里之误,岑仲勉先生在《贞石证史·总论碑志之信值》中对这一方面作了认真讨论,并列举了碑志中诸多错误,约有姓源、朝代、名字、世次、官历、官谥、年寿、乡里八类(《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页79—81)。但应该看到,岑仲勉先生所举墓志之失,相对于数量众多的墓志来说,还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参考欧阳修的看法,墓志所载姓名、时间、官历、年寿、乡里等大致不误,而议论死者功过、善恶等内容只能作为参考,大部分材料如果作为了解社会一般风尚的“通性真实”来运用,其意义不可低估。尽管如此,我们在使用墓志时,仍然要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充分了解撰者的态度以及与墓主的关系。第二、和现存资料互证。第三、整理本和拓本对读,正确使用整理者的录文和注释。这里特别说一下第三个方面,整理墓志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困难,如石刻的残泐影响文字的识读,历代著录难免有疏忽等,稍不注意,就会出错。从今人整理的情况看,墓志系年、月最难,举两例以为说明:
其一、墓志不误,而注者误释。《千唐志斋藏志》427《大周左监门长上弘农杨君墓志铭并序》,编者说明云主人葬期为“万岁登封元年(公元六九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核诸拓片,志云:“以万岁登封元年壹月四日寝疾,终于立行坊之私第,其以其月廿七日葬于北邙山平乐乡。”编者注改志文“万岁登封元年壹月”为“万岁登封元年正月”,实误。武周时所用历法基本以十一月为正月。《唐大诏令集》卷4《改元载初敕》云:“今推三统之次,国家得天统,当以建子月为正……宜以永昌元年十有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改腊月,来年正月改为一月。”《旧唐书·则天皇后纪》云:久视元年“冬十月甲寅,复旧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岁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可知,从永昌元年至圣历二年,都是以十一月为正月。因此,编者所注之“万岁登封元年正月”应改为“万岁登封元年一月”。
其二、墓志阙泐,但可考补,注者未察。《千唐志斋藏志》1214《(中阙)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弘农杨公(中阙)志铭并序》,撰者:“(中阙)池等州观察判官将仕郎监察御史里行吴兴钱徽撰。”编者注云:“志前原题及志文右上部残缺,墓主姓氏、葬期不详。撰者钱徽,《旧唐书》有传。据记载撰(按,当为“钱”字误写)徽活动于天宝十三年(754)至大和三年(829)间。贞元初年中进士,元和八年入朝为官。以志文中记录的钱徽职称情况看,其任此职的时间大约在元和至大和三十年之间。由此推知,镌立这方墓志的时间,大约在这一时期。”周绍良先生《唐代墓志汇编》亦将此志归入残志无法系年类。《千唐志斋藏志》的编者注是有误的,此墓若考出墓主,即可准确系年。
第一、墓主姓氏。志云:“(中阙)秋八月有二旬又六日,宣歙采石军副使兼殿中侍(中阙)寝,河南长孙夫人称字以复,年龄卌六……”、“夫人生则聪爽,天然明智,不幸闵凶,在幼而孤,依于杨公之室……未及方笄年,遂若老成,才十有六岁,而归杨氏……”此志残泐较多,结合撰人姓名结衔以及墓志残题,可知钱徽时在□(宣)□(歙)池观察判官任上,墓主为杨某夫人长孙氏。《新唐书》卷177《钱徽传》载:“中进士第,居谷城,谷城令王郢善接侨士游客,以财贷馈,坐是得罪。观察使樊泽视其簿,独徽无有,及表署掌书记……又辟宣歙崔衍时………会衍病亟,徽请召池州刺史李逊署副使,逊至而衍死,一军赖以安。”知钱徽曾为崔衍宣歙幕僚,据墓志钱徽在幕为判官,孟郊有《和宣州钱判官使院厅前石楠树》诗。崔衍观察宣歙在贞元十二年至永贞元年,《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八月“癸酉,以虢州刺史崔衍为宣歙池观察等使”。《旧唐书·宪宗纪》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即帝位于宣政殿……甲寅,以常州刺史穆赞为宣歙池观察使,以前宣歙观察使崔衍为工部尚书”。《册府元龟》卷六八七《牧守部·礼士》云:“崔衍为宣歙池观察使,所择从事,多得名流。”此时和钱徽同幕者有杨宁,《千唐志斋藏志》1011《唐故朝议大夫守国子祭洒致仕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赠右散骑常侍杨府君墓志并序》:“公讳宁,字庶玄,弘农华阴人也……既冠,擢明经上第,释褐衣,授亳州临涣县主簿……退居于陕服,勤孝敬悌达州里,观察使李公齐运雅闻其贤,即致弓旌,从迁于蒲,益厚其礼,表授试金吾卫兵曹参军,充都防御判官……忤时左掾鄱阳,稍移陵阳,廉使博陵崔公优延礼貌,置在宾右,表授试大理司直,充采石军副使,进殿中侍御史,银艾赤绂,荐荣宠章。初宣城大邑,井赋未一,公以从事假铜印,均其户有,平其什一,蚩蚩允怀,主公赖之。永贞初,有诏徵拜殿中侍御中,迁侍御史,转尚书驾部员外郎。”《长孙氏墓志》虽阙泐较多,但墓题残存者与杨宁墓志皆合,且杨宁墓志亦为钱徽所撰,因二人同幕交厚之故。《千唐志斋藏志》一二一四残碑全题当为《唐故宣歙池采石军副使试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弘农杨公夫人河南长孙氏墓志铭并序》。
第二、墓主葬期。由于确定了墓主为杨宁夫人长孙氏,墓主葬期也就容易确定了。据杨宁墓志和残志撰者结衔,可知残志葬期必在崔衍为观察使的贞元十二年至永贞元年之间,且杨宁墓志已言宁“永贞初有诏征拜殿中侍御史”,大概崔衍罢镇,杨宁也就入朝了,此残志墓主葬期不会迟于永贞元年,更不会如《千唐志斋藏志》编者注所说的在永贞后的元和至大和三十年之间。《杨宁墓志》云:“有唐建元元和,乃岁丁酉四月孟夏,其日乙卯,大司成杨公得谢之二年寝疾……薨于是……□□粤八月壬申望其子汝士等祗服理命,卜宅先祖考妣于河南府河南县金各乡尹村之北原,启公从之,以故夫人河南长孙氏合之。”“夫人故长安县令縯之女,先公一十三年殁于故鄣明……有子四人汝士、虞卿、汉公咸著名。”可知,长孙氏早杨宁十三年而卒,杨宁卒后,夫妻合葬。杨宁元和丁酉(817)卒,则夫人长孙氏卒于贞元二十年(804),残志墓主葬期当在贞元二十年。
整理本用起来方便,但如果和拓本对读,并加上我们的思考,会在使用墓志上少出一些错误。
标签:全唐文论文; 文学论文; 唐代墓志汇编论文; 文化论文; 唐朝论文; 读书论文; 旧唐书论文; 全唐诗论文; 墓志铭论文; 李颀论文; 洛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