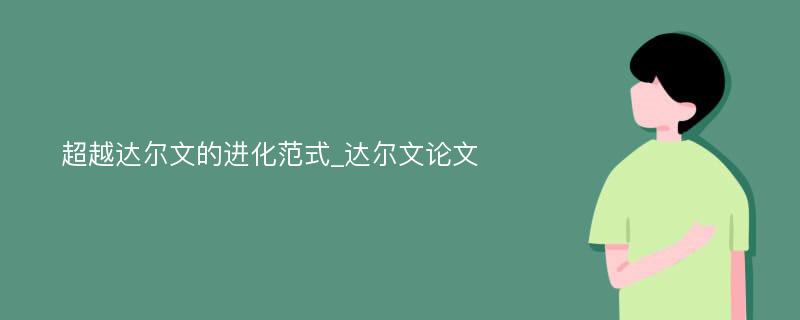
超越达尔文的进化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论文,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Q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3)-02-0115-08
一
从西方古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静止的、没有进化的宇宙观。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完全撇开了上帝,开始从新的角度,从动态、持续、进化的角度去认识生命现象,真正按照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和方式去解释自然。在哲学上,正是进化观念的确立,才使得人们的意识从古代那种“静穆的伟大”与“和谐的不朽”的世界幻相中开始解脱出来。惟其如此,19世纪便被波尔兹曼称之为“达尔文的世纪”。(注:参见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其实,达尔文主义并非完美无缺,恰恰相反,它一直未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证实。而这一理论之所以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很可能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幅与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社会极为相似的图像,并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进步”观念相互支撑,从而共同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取得了其支配地位。历史告诉我们,流行并不一定是思想的商标,寂寞往往是真理的伴侣;而与兴盛结伴而来的盲从则容易导致危险的堕落。换句话说,任何经典的理论都不应成为科学所崇拜的偶像,更何况,进化论本身就是在冲破“神迹”中发芽长大的。不管怎样,要对达尔文主义做出确切的把握和评价,我们首先得弄明白被达尔文主义者视为“圣经”的进化理论究竟说了些什么。
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世界看成是进化变化的,并以自然的原因解释生物的进化。正是由于进化论,才使得人们的一切认识都得按照自然的方式而展开,自然没有内在的计划和目的——那是人的特权。正是这种显明的人道主义因素,马克思才高度赞扬达尔文最终清除了自然科学中的内在目的论残余。然而,达尔文未能看到,有意识的人的选择要比通过机遇和偶发事件的自然选择更为重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不仅人类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乃至人类本身,而且整个有机系统界,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目的,即自发乃至自觉地趋向某一目标或形成某种秩序的能力。
达尔文学说的要义在于“物种增殖”,即主张新繁殖出的与其它种群相隔离的种群是由先前的物种经过小幅度遗传变化的初步积累(微观进化),可以导致由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转变(即造成宏观进化)。当然,从统计学的角度讲,事情总有发生的机会。因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进化是否能够发生,而在于是否有发生的或然性。丰富多彩的生命发展航线和经修复的化石所体现的进步似乎非常科学,但这一点一直未得到证实,达尔文在当时所能作的只是付诸于猜测。在当今所发现的大约2亿块化石中,依然没有适当的化石可以被认为突破了对生命形式转化的所有疑问。不仅没有化石证据证实不同的动物种类之间的任何较大的转化,而且也无法想象这些根本性转化如何能够通过自然选择而一步一步地实现。20世纪60年代,进化论者希望发现遗传密码转化的连续性以便证实宏观进化,认为持续变化的遗传密码将促成生命形式的宏观进化。然而,蛋白质和脱氧核糖核酸中化学元素的连续性并没有显示出那种转化特征,相反,自然界看来似乎是极其不连续的。(注:参见布里斯托:《进化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含义》,载美国《当代重要演说》,1995年2月15日。)。
进化论使人们相信,人类的直系祖先是猿,猿和一切动物的直系祖先都是植物,植物则起源于更原始的有机分子,有机分子又起源于无机分子。这样大千世界无数生命体便被认为源出于同一的生命种子。达尔文主义这种近乎画地为牢的方式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使得这一百多年来一些人尤其是人类学家们便开始了无休无止地寻找这一人类最早的“亚当”或“夏娃”。如果说当年达尔文仅仅是从生物性状上的相似性来揣测人猿同祖的话,当代的进化论者则更多的是依据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来论证物种起源的这种纵向单祖论的。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流行的是“非洲一祖论”,人们一般都相信人类的“始祖”最早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女人,她活力强大的基因保留在现今全世界的人身上,现在的我们大概是她一万代的曾孙。非洲“夏娃”发现不久,有人便又发现人类线粒体DNA类型与猿最相似的,以在亚洲的频率最高,从而认为“夏娃”又可能诞生在中国的南部。现代分子生物学揭示,人与猿尤其是与黑猩猩之间在基因的这种构成上,其差别非常之小,大约只有百分之一。于是,当今的进化论者为之欢欣鼓舞,便极力鼓吹达尔文“人猿同祖”的这种“先见之明”。然而,根本的问题在于,相似不等于相同,在基因构成上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差异,也会导致它们在性状上的重大差别,“以至于其中之一竟然拥有把另一种关进动物园和实验室动物笼中的能力与权力”(注:参见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因而如果仅仅根据两个物种在性状或基因构成上的相似性是不能判定它们之间是存在“血缘”的。达尔文的“单祖”论充其量只是一种表象分析,而非科学判据。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一般被公认为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应该承认,在自然界中,自然选择无疑是存在着的,但问题是,达尔文主义者所坚持的自然选择却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在达尔文那里,自然选择不仅仅是指通过生存斗争淘汰不适者,更重要的是通过“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即天择不但能使生物在遗传方面保持优势,而且这种自然力量有无比的建造功能,在几亿年间,它竟然可以将一个细菌类的细胞建造成花、木、鸟、兽,甚至人类的奇观。根据进化论的解释,繁殖能力较强的,可以生产更多的下一代;这样不同的繁殖能力就能渐渐将有利的因子分配并集中到生存的个体中,而这些较进步的生物又成为下一步进化的基础;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同时又有足够好的突变的话,那么通过这样渐渐积累不同的改变就能制造出极度复杂的器官和适应环境的行为,而不需要任何智慧者的协助。其实,由于达尔文本人并不十分满意“选择”这个词,它的最大缺点是含有“谁在选择”的意思,因而他在以后的《物种起源》版本中就采用了斯宾塞的简洁隐喻“最适者生存”: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将会产生更多的后代;同时遗下最多后代的生物最能适应。但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十分糟糕。这正如大多数反对意见所指出的,整个自然选择学说原来是奠基在同义反复上:“谁生存?最适者,谁是最适者?能生存的。”(注:参见詹腓力:《审判达尔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6页。)用哈肯的话说,“适者生存”的命题就好像是“一个猫在咬它自己的尾巴”(注:哈肯:《协同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因此,进化论的概念是混乱的,它的基本假设还是像达尔文进行环球旅行时那样高深莫测。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抱怨道:“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这一特别黯然的评价使得当时参加纪念《物种起源》问世一百周年的许多听众都感到震惊,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一失望中所表达的真理。(注:参见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序言。)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汤普森也哀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使人类对进化的研究进程延缓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物种起源》一书的成功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它使生物学者们陷入了一种无法实证式的空论中。”其实,何止半个世纪,即使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学者们仍然摆脱不了将自然选择说当作主因考虑的框框。日本学者浅间一男批判道:“如果自然选择始终都适用,那么,只要给予充分的时间,优胜劣汰的结果应该是目前地球上仅仅只有万物之灵的人。……但自然界中的现状是:下至低等单细胞生物上至高等动物人类的并存。这有力地证明了生物并不像遗传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根据有利、不利、优劣等原则进行有效的自然选择。”(注:浅间一男:《人为什么成为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62页。)
达尔文可能是与哥白尼、牛顿、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相并列的最大的观念制造者。进化论思想的胜利意味着那种认为世界是一种被有目的性创造出来的秩序的传统信仰的结束,于是,上帝的意志为赌台轮盘式的反复无常所取代。这一伟大见解被公认以及相应的上帝被驱逐出自然界的事实,对于西方社会信仰现世主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达尔文的理论破除了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联系,使人类漫无目的地在宇宙中飘浮。我们便成为这一思想遗产的历史继承人。但事实上我们只是接受了一个虚构的理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自己放弃了回答我们最基本的心理学和哲学问题(注:赵汀阳:《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载《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月25日,第6版。)。本来,在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链中,人位于自然阶梯的顶端。在基督教神学时代,《圣经》所描述的是,人是按照神的肖像造成的,具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在文艺复兴时代,哥白尼虽然使人脱离了神圣的中心地位,但在当时人们普遍的精神信念中,人仍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而现今为人们所普遍称道的达尔文的革命,则无情地撕去了昔日笼罩在人身上的神圣光环——人只不过是猴子的后代,就像其他生物一样,只是纯粹偶然的产物,是一连串大分子的组合。从而最终将人驱逐出了灵魂的庇护所。至此,人们才最终发现进化论对人的弥足珍贵的主动性、个体独特性和创造性的严重忽视。
二
显然,“不超越达尔文,无以进化。”(注:浅间一男:《人为什么成为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前言”。)贝塔朗菲通过“开放系统”来定义和描述生命体,在其看来,生命的形式不是存在着,而是发生着。贝塔朗菲认为,自然选择和随机突变在进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绝对不是全部。如果最适合就能生存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仍有可能是微生物,因为在与环境相适应的程度上,微生物远比我们要强得多。因此,生物的进化,除了受达尔文主义理论所设定的那些原则支配之外,必定还有一种原则在起作用,这就是有机体内部的自主进化,或者说有机结构的调整原理。在贝塔朗菲看来,进化的基本点不是物种的形成,而是有机结构的起源;新物种的形成则意味着在所有层次上有机结构的重新调整(注:陈蓉霞:《进化的阶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174页。)。这一极具价值的思想,为我们探究进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正是在一般系统论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末以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为先导,系统自组织理论开始蓬勃兴起。接着,70年代诞生了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一系列系统自组织理论,从而使系统思想和系统范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使人们惊奇地看到,一个活系统必定要通过一系列的不稳定性而进化,而非线性、非平衡性则构成了万物的组织之源、有序之源。这一重要结论的提出,使得过去被看作对整体行为偏差的涨落干扰在不稳定性中可以成为建设性因素,即“通过涨落达到有序”,这使得有机生命体的出现也具有了一定必然的成分,而不纯粹如达尔文等人所认为的是一种随机的、偶然的产物。这些全新的关于系统演化的自然科学的新表述,与以整体方式观测宇宙演化过程的系统范式思想一起,在坚持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基础上,从观测宇宙整体上和各个层次上向世人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组织演化的自然图景。这些思想的综合,就是所谓系统进化论,或詹奇所说的“自组织进化范式”或拉兹洛所说的“一般进化论”。
这一进化新范式,为我们在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上较好地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自然目的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彻底摈弃了神创目的论而具有伟大历史功绩的话,那么现代自组织理论则在新形式、新水平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而承认了自然进化的目的性。人们尽可以凭借“是否具有自觉意识性和预定计划性”对自然目的性和人的目的性作出区分,但自觉意识性和预定计划性并不是目的性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以此割裂自然目的性与人的目的性的相互联系和推移转化。如果说自然目的性是人的目的性的客观基础,那么人的目的性则是自然目的性的延伸和完成。否认这一点,我们将永远无法解释人的“目的性”起源。
按照自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世界是平衡在浑纯的边缘的一个具有动力的、永恒变化的系统。”(注:米歇尔·沃尔德勒:《复杂》,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2页。)当外界供给的能量流和物质流接近某临界值时,下层系统之间的关联便逐渐增强,使原来无规则的独立运动相应地减弱。当达到或超过一定阈值时,那数量巨大的下层系统好像能够互相识别和遥相呼应似地同时按某种方式行动起来,参加到协同的集体运动中,形成了稳定的或振荡的宏观结构。于是,自组织现象便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系统的这种自组织进化不仅需要稳定,也需要失稳,“一个系统只有在正好能够在稳定性和流动性之间保持平衡才能够产生复杂的类似生命的行为。”(注:米歇尔·沃尔德勒:《复杂》,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2页。)因为,如果没有外部和内部自发产生的非稳定性,那么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就不会产生。在这样一种动态环境中,系统总是不断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无规则变化的扰动,从而使系统失稳。如果说在一定的区域内,譬如说在热力学的线性非平衡区域内,这些涨落是干扰和破坏的因素,那么一旦超出一定的区域,即在非线性非平衡区域内,这些涨落就成了建设性的因素,担当起了非平衡相变的触发器。一个小的随机涨落可能在同其他涨落的竞争中迅速增长,通过相干效应不断增强,最终取得对整个系统的支配地位,从而驱使早已失稳的系统上升到一个新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现代浑沌理论所揭示的“趋于浑沌边缘的相变”,即系统只有达到这一状态,才有可能通过各种随机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新颖性”,进而创造出生命和智能。惟其如此,才有随机性本身是生物界每次革新的源泉,换言之,“浑沌乃结构和秩序之源。”(注:J·布里格斯,F·D·皮特:《湍鉴》,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82页。)
正由于复杂性的出现是由于在自然界这一大系统中,简单的组成因素以无数可能的方式自动地发生相互作用,而这种持续相互作用意味着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将系统的一部分取出来孤立地加以研究。从而与经典科学所强调的有序性和稳定性相反,我们在观测的所有层次上都看到了涨落、不稳定性、多种选择性和有限预测性。因此远离平衡的具有非线性相干作用系统的进化轨线就不是一条,而是许多条。在每一个临界点上,或者说分叉点上,系统究竟选取哪一条轨线基本上是随机的、不可预见的。系统进入的新状态既不决定于初始条件,也不决定于环境参量的变化。浑沌理论揭示,一个系统中最小的不确定性通过反馈耦合而得以放大,在某一分岔点上引起突变,使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也可能发生惊人的复杂性,从而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变得完全不可预测。因此,在非线性世界中,精确预测在实际中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进化的进程不是预先决定的,也不是可预见的。“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注:参见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惟其如此,普里高津通过将时间不可逆性引入对“新自然法则”的描述,从而揭示了“确定性的终结”。在普氏的宇宙中,未来不能被确定,因为它受随机性、涨落和放大的支配。为与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相区别,普称此为一个新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一新的不确定性原理描述的是:在某个复杂性阈值外,系统沿不可预见的方向演变,它们丧失其初始条件,不能被逆转或恢复。这一时间倒流的不可能性是一个“熵垒”。因而,这种由时间的不可逆性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并非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是出于我们人类的“无知”,而是我们这个“演化”着的世界的本真属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进化是没有方向的。艾根和舒斯特已经证明,催化循环是复杂结构能够持续存在的基础,而复杂结构又为生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使之成为可能。在相对简单的化学系统中,自催化反应近乎占据支配地位,而在表征生命现象特点的比较复杂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完整的交叉催化循环链。为生命有机体的结构编码的一系列核酸的稳定性就是建立在催化循环基础之上的。在更高的组织层次上,它们还是我们星球生物圈内所有生命形式持续存在的基础。在强度、温度和浓度保持在允许参量范围内的情况下,一股能量流持久的作用于有机组织系统,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那些基本的催化循环就趋向于连锁成艾根所称为的超循环。超循环的形成就使得动态系统能够在组织性逐级上升的层次上出现。由于组分和结构有更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新层次上,由超循环所能容纳的信息量要比在较低层次上的信息量大得多。因而进化就能越过那个本来会阻碍在已有组织性层次上继续前进的复杂性的功能优化极点,那里新结构的可能性又为进一步进化开创了新天地。这种可能性潜存于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中,随着这种可能性的增大,在某个分岔点上,这种随机联系的偶然性事件就有可能表现出一种必然的过程和趋势。“由于这种可能性具有普遍性,因而概率成为一种新的自然法则的表述。”(注: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上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根据普里高津所表达的这一“新自然法则”,我们可以说,确定性的世界观是解构了,但这个世界并不是纯机遇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可确定的概率世界,生命和物质在这个世界里沿时间方向不断演化。
此外,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观念在当代也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尽管达尔文对生存竞争有着较为宽泛的理解,他说:“我应当先讲明白,是以广义的和比喻的意义来使用这一名词的,其意义包含着这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也包含着个体生命的保持,以及它们能否成功地遗留给后代。”(注:达尔文:《物种起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7页。)但达尔文进化论的成功,使人们在看到竞争对于生存的推动作用的同时,又使人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将这一方面片面地扩大化。现代自组织理论以及其它一系列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一体化和合作的原则是生命系统的基本方式;合作比竞争更为根本。马格里斯指出,生命并不像新达尔文主义所假定的那样,是消极地去适应物理化学环境,相反,生命主动地形成和改造它们的环境。“这种有机体与新的生物群体融合的共生起源,是地球上所发生的进化的一个主要源泉。”(注:马古里斯、萨根:《倾斜的真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从而与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后者本质上是以物理学为中心的机械论哲学,它“毫无顾忌地把曾经解释过无机物的方法,用于有机世界的研究。”(注: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由此看来,如上这些以系统自组织进化为基础的新的生命观和传统的达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着许多根本的分歧。后者实际上把进化看作是随着有机体的日趋完善的适应于它们的环境而趋向平衡态的运动,倾向于集中在线性的、连续的过程,而忽视了是相互制约和共同进行的交互现象。而按照系统观,进化是远离平衡态进行的,通过适应和创造的相互作用而展现,并把环境本身看作是能够适应和进化的生命系统。同时,在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中,自然被看作是由基本建筑块构成的力学系统,生存的单元被定位于物种、亚种或其他生物世界中的建筑块,而从系统的观点看,生存的单元根本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有机体在与环境的相互制约中所采取的组织模式;也就是说,进化的单元是在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的;复杂性的展现不是来自于有机体之于一种特定环境的适应,而是来自于所有系统层次上有机体和环境的共同进化。
